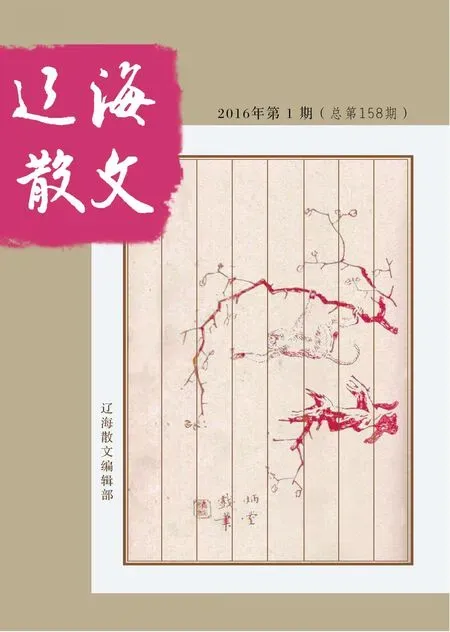五味小品(节选)
党兴昶
五味小品(节选)
党兴昶

党兴昶
(1953—2014),男,生于辽宁法库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共铁岭市委副秘书长、市委政研室主任,铁岭市作协主席。著有诗集、散文集、儿童文学集等十余部,主编各种文集五十余部。曾获中国图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辽宁省优秀儿童文学奖等。
捡石子记
在棒棰岛,海滩上的鹅卵石异常可观,大大小小奇形怪状地铺满了整个海滩。被太阳一照,绿色的、白色的、红色的,如翡翠、像珍珠、似玛瑙。真是色彩斑斓,夺人眼目。
我捡着,觉得每一枚石子都是一件不同凡响的工艺品。那奇特的造型和鲜艳的色彩自不必说,就连石子上的花纹也构成了各种美丽的图案。有的像山水画,有的像蓝天和白云,有的又像动物园,有的说不出像什么,只觉得好看,大有妙不可言之感。住同室的作家老刘,根据每枚石子的特点,帮我冠之以美名,有的叫“碧海红日”,有的叫“天地玄黄”,有的叫“出水芙蓉”,有的叫“鹰击长空”……真是玄而又玄了。
自然,我这个很少有机会来海边的人,倍加觉得这石子新奇和可爱。每天早晨,都要从宾馆沿着鹅卵石铺成的小路,赶到海边捡上一衣兜。五天的工夫,数量已相当可观了。见多识广的老刘对我说:“照这样下去,二十来天的会期,你要用汽车往回拉呀?”
说得也对。于是我便开始淘汰。尽管不太情愿,也还是把那些形状不够奇、色彩不够美的(当然是相比较而言),或掷之窗外,或弃之于一隅。这样,每天又有石子补充进来,每天又有石子被清除出去,算是“吐故纳新”吧。几日后,捡得多了,扔的就多了,使我对扔掉的又有几分惋惜。但失去的毕竟失去了,留下的反而令人觉得单调乏味,不再稀罕。索性一把、二把、三把地扔,居然一个也没留下。是失去了当初的那种新奇感,还是因分不清优劣所致,我说不清楚。反正有几个早上,我只是去倾听大海的潮音,而没有带回被浪潮遗落在海滩上的石子。
一晃儿半月过去,就要告别美丽的海岛,回到我那座北方味十足的小城了。我忽然想起临行时妻的嘱托:“告诉你,不要忘记带回几枚好看的石子呀!”唉,我真后悔,怎么把那些石子扔掉了呢?于是,我又跑向海滩,不管圆的、扁的、红的、白的,胡乱捡了几块。其质其形虽不能和扔掉的相比,但终于可以交差了。果然,看到这些小石子,妻笑了:“瞧你,一点小事也挂在心上。”她把石子擦净,装在盛满水的口杯里,认真地品评着、欣赏着,充满柔情蜜意地说:“这一定是你精心选的,不然怎么会这么美?”然后她眯起眼睛,似乎在想象我在海滩上苦苦寻觅的情景。我不由自主地点头了。妻更加高兴,经常当着客人的面,赞赏这些来自海边的石子,赞赏我对她的诚心厚意。日子长了,我本想告诉我的痴情之妻:“海滩上还有很多比这美丽的石子,只不过我没有捡拾。”或者和她说:“捡来的又被我扔掉了。”但我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说出,也许是没有必要说出吧。只是在内心深处多了点负疚,多了点醒悟与警策,便写下了这篇小文,以示悔过。但愿发表后不被我的妻看到。是为记。
鸽·鸟·人
雪霁。我和小儿漫步于郊外,捉得一只快要冻僵了的小鸟。这小鸟儿,红尖嘴儿,红细腿儿,头顶一撮绿缨,好漂亮,叫不出名字。
从此,这小鸟便和我家原养的小鸽子同居一室了。我不知道这鸽、这鸟原本是否沾亲带故,也不知道它们的遗传基因里有多少相同的因子,更无法探究它们的祖辈今世孰尊孰卑、孰善孰恶。至于它们和我及我的小儿,更是鸽、鸟、人不相及了。
说来怪有意思,这小鸟始而陌生,一双小眼睛不时地眨来眨去;继而活跃,在屋子里乱飞乱撞;进而又变得异常温顺,居然和认识不久的鸽子形影不离、卿卿我我了。虽然还不知道它们是否异性,是不是在谈恋爱,但我总觉得这中间有一种美好的东西联系着。
我的小儿是个出了名的淘气包。且不说他撕坏了我多少书页,碰坏了我多少花盆,就连我用心血写出的文稿也常常不翼而飞。自从有了这一鸽一鸟,这小子便和这两个小家伙打得火热。只要他用一种特定的声音一叫,那鸽那鸟便落在他的肩上;只要他一挥手,那鸽那鸟便在屋子里飞上一圈又一圈。他的手不停地挥,那鸽那鸟就不停地飞。从此,小儿也就很少乱闹,而多了不少悟性,变得很懂事。
以后的事情,责任完全在于我妻。本来她对这只鸟还是蛮有兴趣的,后来因为工作不顺心而心情不好,硬说这只鸟的存在使屋里有一股不好闻的气味,有碍了春天的情调。还说这两个野东西影响了她的宝贝儿子的学琴习画,必除之而后快。她先是打开窗子,把小鸟轰了出去,接着又自作主张,把鸽子送给了一位嗜酒的邻人。
这事令我至今耿耿于怀。
鸟
昨晚算是醉了,头痛并气闷,当然不仅仅是酒的缘故。很大成分是因为那个日本人装束叫什么茨山寺郎的中国人令我英雄气短,大失面子。来到了日本,看到邻国物资丰富,并对我们热情接待。本来怀有“阶级仇、民族恨”的心,稍得放松“警惕”,却被这个“假东洋”弄得五迷三道,很有些不是个滋味。
东道主田代夫妇,笃诚务实,经营一家木材工厂,收入肯定不菲。夫妻俩向来热情好客,特别是每位中国人莅临当地,必请府上,饕餮豪饮一番,方算尽了情谊。我们此次来访,未能例外,心中大喜。
家宴伊始,并没什么“寺郎”。只是听田代先生说一会儿有位来此定居不久的中国老乡来作陪,我们感激主人的周到,便边饮边聊。话题大体是中国书法、鉴真和尚、日本跆拳道之类,颇有些投机。酒过三巡,进来一位不速之客,此公身着和服,颈戴金圈,一副十足的大和民族的气息。这倒不怪,日本人历来喜穿和服,既潇洒又休闲,很有一种文化意味。怪的是,此人进来就是一阵鸟语,除我们主人之外,谁也不知他是何许人也。只见他盯着主人,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便来个向后转,飘然而去。我们皆在五里雾中,不知这位先生是个哪方“鸟”。
客人走后,只见田代先生起身、立正、频频鞠躬,连说:“对不起,对不起……”原来,刚才走的那位,正是打算来陪我们的 “中国老乡”茨山寺郎,听说我们只是个文化代表团,既不能谈生意又不想雇翻译,无任何可利用价值。于是乎,便溜之大吉了。
呜呼,亏他还是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手足之情殆尽,礼义廉耻也全不顾了。于是,心情郁闷,酒杯频端,几近酩酊。
(选自《新中国60年辽宁文学精品大系》)
责任编辑 刘宏伟
【点评】
那些生活的细小琐屑
潘石
曾经,我们是那么挖空心思地捕捉散文题材,为了叙事更宏大,情节更曲折,精心架构,巧设机关,唯恐被批不够缜密深刻;我们又是那么苦心孤诣地推敲遣词造句,生怕绕不开前人的窠臼,以至于“为赋新词强说愁,语不惊人死不休”,在无病呻吟中慢慢丢失了生活的本真和写作的趣味。
所以,相信每个读到党兴昶小品的人都会讶异,原来,散文是可以这样写的。海边捡拾鹅卵石的纠结,与鸽鸟同处一室的快乐和困惑,在日本遭遇“假东洋”的郁闷,那些尘世间细微如一束光线、一缕微尘的事物,竟在他的笔下活脱脱、脆生生铺排开来,一字一句看似不露声色,却又活色生香。
我始终认为,好的散文应与情致有关,与性灵相通,党兴昶的小品正应了这一点。《鸽·鸟·人》中只一句“把鸽子送给了一位嗜酒的邻人”,我的眼前不由浮现出烧烤摊前待屠的无辜影像,深深担忧这些禽畜的命运;《鸟》中与那位无良国人的交集,三言两语,如话家常,却真切道出了内心的不屑与悲哀。最绝的还是题目,将作者的立场一字捧出,鄙夷之意,酣畅淋漓。
由此,我不由得想起被贾平凹戏称为“文狐”的汪曾祺,老先生为文质朴含蓄,娓娓道来,却遍布人间真善美,处处呈现恬淡与雍容之态。在党兴昶的小品中,我们也读到了那种宁静、闲适的情状,更醉心于感观的审美与愉悦,在“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散文堆里洗尽铅华,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