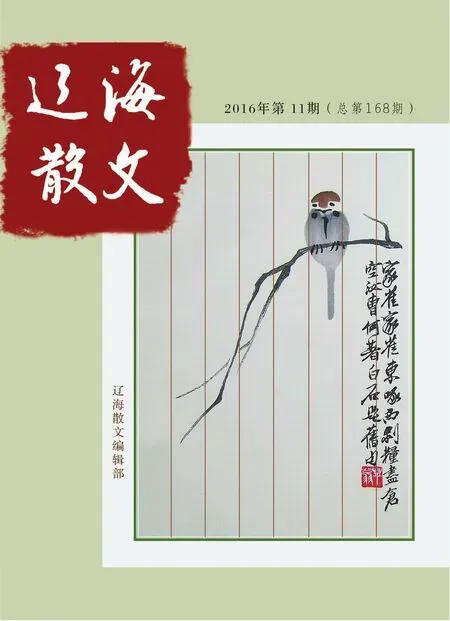我与“辽民三”
宗 晶
我与“辽民三”
宗 晶

宗晶
满族,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散文学会会员。作品散见于 《诗刊》《中国诗人》《诗林》《鸭绿江 》《诗潮》《诗歌月刊》《散文诗》等。出版诗集《行走的黄昏》《向阳的声音》。有诗作入选《新世纪辽宁诗典》。现居大连。
1996年的暑假,为了给自己的内心一个交代,我说服父母独身一人从岫岩老家来到了大连,当晚在码头随便找了一家旅馆住下,第二天便登上“辽民三”开往素有“黄海前哨”之称的海洋岛。
天气不是很晴,码头上空灰蒙蒙的,说不好是雾还是云。随着人流登上停泊在港口的“辽民三”是在早晨六点,从没有坐船经验的我有些小小的激动,出发前老爸嘱咐的相关注意事项早已抛得无影无踪。我把随身携带的包扔在床铺上,便信步踱到了甲板上。船刚驶离码头,速度不是很快(事后我才知道,这艘海军退役下来的“老牛船”也就是这个速度了)。码头的喧闹声渐渐远去,几只灰色的海鸥在船舷边似有目的地兜转了几圈便讪讪地飞远了。甲板上除了几个抽烟的男客,以及三个操着浓浓海蛎子味的胖女人外,剩下的就是我了,难耐的兴奋与豪情被这单调的灰色笼上了一层浓得挥不散的湿气。
海风渐渐大了起来,雾气不仅没有消散反而夹杂着丝丝细雨,一会儿的工夫,裸露出来的手臂便罩上了一层晶莹的小水雾,我想在甲板上逛一圈再回到船舱里,可没走几步,感觉脚底有些不听使唤,身子直往船舷上倒,只吃了一根油条的胃口也酸不拉叽地开始反酸水。坏了!我心里暗暗叫苦,真的被老爸说中了!我晕船了!门边上的一位扎着黄色头巾的大姐见状赶忙抓住我的手臂,搀我回到床铺坐下。事后我才知道,晕船时独自在甲板上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
我开始晕船了,仄歪在床铺上,旁边的人、桌子、床铺像荡秋千似的在眼前晃了起来。那个明明站在我左侧的铺位旁,倚着床栏杆吃火腿肠的小伙子忽左忽右地跳着,曾经鲜美的火腿味像一道钩子将我胃里少得可怜的食物拖曳而出,踉踉跄跄奔至门口,我已顾不上斯文,还好硕大的黑色垃圾桶能承接下这些呼之即出的残渣、酸水还有大把的眼泪鼻涕,食道、胃里像有一台搅拌机在搅动,说不清的苦说不清的痛。当连酸水也吐不出来的时候,我一头栽倒在铺上,闭上了眼睛。还好,闭眼比睁眼好受了许多。看来,当你睁眼难受的时候不妨闭上眼睛,眼不见心不烦还真的有一定的道理。慢慢的头不像刚才那么晕了,但我还是不敢睁眼睛,每次一睁眼,就感觉自己睡在了摇篮里。躺在铺位上的我只能侧卧,仰卧还是晕,闭眼是余下的行程里我唯一的奢侈。当一切简单到只剩下这唯一时,一切奢望都逃之夭夭。
船舱里人们谈话的内容忽而传入耳鼓,忽而又飘远。似睡非睡似梦非梦中船停了,睁开眼才发觉有一些人正准备下船,正疑惑中,一位身着蓝色工作服的人边走边喊:“大长山的下船了啊!”哦!原来船在海上还有站啊!
很快又上来一批新的乘客,嘈杂还在继续,晕船也还在继续,没有一个人会因为你的不适而改变自己,除非你自己。后来又有人喊“獐子岛到了”,到了就到了吧!该去的去该留的留,连自己都阻止不了自己还有精力去在意他人吗!
“到了!到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沉闷的空气顿时鲜亮了。邻床的那对刚才还为什么拌嘴的小情侣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哗啦哗啦地收拾着东西,好像是东西惹了他们生气似的;一个还在梦乡的小宝宝在妈妈的呼唤下睁开了眼,看来他睡得很甜,有些不情愿地把身子歪在一边躺了几秒,又顺从地配合着妈妈穿衣服。船舱里都动了起来,不过船却不晃了。我的头还是有些昏沉,肚子里的小器官虽不搅动了,却似都被挪位了似的无着落。倚靠在床头,我信口问了一句:“到海洋岛了吧!”“到了,但是船靠不了岸,等小木船泊渡呢!”“泊渡?”“对!”那位肤色黝黑的士兵憨憨地笑了一下又接着说:“你第一次上岛吧!看你躺了一天了!我们第一次坐船也是这样,多上几次岛就好了,不过今天的风是有些大。”说话间他已走出船舱,我这才发现,他的左手臂还吊着绑带。哦!一个伤兵啊!可我还来吗!
看看手表,北京时间晚上6:55了,我已漂泊了近13个小时。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我买的这个三等舱只不过是一个有着上下铺位的大散席,三十多张上下铺有序却又有些杂乱地矗立在偌大的舱间,船舱里虽然开着灯,光线却很昏暗。不论是舱门、舱壁、床栏还是地板都无一例外有漆皮剥落,好像事先约好了似的将我的不完美的旅程又着上了一层白霜,说不清的酸楚在眼泪即将流出来的那一瞬又咽了回去。很多的时候,忠于自己的内心并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好家伙!等吧!大约过了十多分钟,我随着最后一拨乘客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走出舱门,咸咸的海味氤氲在喧闹的声音中,漂泊了一天,自己都弄不明白现在是什么心情了,更无暇顾及他人以及周边的景了。其实,除了码头迷离的灯火,影影绰绰的乘客以及接客的家属,几近于声嘶力竭的船务工作者,又能有什么景又能看清什么呢!疲弱的我木木地走到舷梯旁,说是舷梯,其实就是两块大木板,一头搭在大船上,另一头伸到小船甲板上,小木板船在海面上起伏着。大船和小船上都有工作人员一左一右地在舷梯旁帮着把扶乘客,我看到前面的人踏上木板时,身子像踩高跷似的左右晃动,我的腿软了,挪不动半步。就在我几近于瘫痪地倚靠在船栏边时,小船下有人喊我的名字,原来他(后来我成了他的妻子)来了!看船上的人陆续走下来唯独没有我,他们正在焦急得不知所措时,刚好看到我站在大船边不敢下来,我身边那个胖胖的工作人员估计正想朝我发火,那张圆形的大嘴像一个枪口扫视着我,看两个当兵的人在下面喊我,枪口一扭,极不自然地抓住我的手臂可谓连拖带拽地推送给他们。我终于上了小船,那滴涌到眼角的泪有那么一秒的停留但又坚强地退了回去,尽管此刻的坚强是多么脆弱。
从小船上岸就容易了许多,踏上水泥路,真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我也终于相信了一位市里的女孩被介绍给守岛军官,上岛后知道在船上看到的高高的灯火是坐落在半山腰的房子时,就义无反顾地返程绝不是一个童话。登上等候多时的接站车,我才发现车上竟有一位即将生产的军嫂,而且是自己坐火车从山东老家到大连然后到老牛船上的……
开车了,我的泪终于没能忍住。还好,车厢里黑暗,谁也看不清我脸上的晶莹,人们沉浸在幸福中,沉浸在夜色里。那一刻,一颗行将湮灭的星瞬间又亮了,“辽民三”上13个小时晃荡的辛酸与痛渺小得如沧海一粟,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无穷尽地放大的喜悦,以至于有些崇高。对,就是崇高!
十五天的海岛之行,一部写不完道不尽的人间大爱之书。一个怀胎十月的军嫂,拖着笨重的身体来到孩子父亲坚守的海岛待产,当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撼动整个营房,父亲那高大的背影孩子似的颤抖诠释了所有的坚强;错落有致的营房深入山坳,官兵们训练的身影点缀在丛林中,18.98平方公里的海岛上空回荡的是付出与拼搏的赞歌;388高地上,“黄海第一哨”的大字在阳光的映衬下是那么耀眼,那么神圣!
…………
两年后的暑期,我也成了一名军嫂,一名真正的守岛军人的家属。
后来又坐过几次“老牛船”,真的如那个小战士说得那样,坐坐就好了。是的,返程时包括后来的几次,虽然仍旧有些不舒服,但你的前行一旦被感动与震撼所充盈,痛就不那么明显也不那么重要了。
从大连港到海洋岛三个半小时即可抵达的高速快艇是在哪一年取代“辽民三”,我不知道,我只想说直到我敲下这些文字,我仍旧想坐着“辽民三”再回一趟海洋岛,回到388高地上的鸽子旁,将一张行将衰老的脸再一次贴近它,贴近它,贴近神圣的殿堂。
责任编辑 黄文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