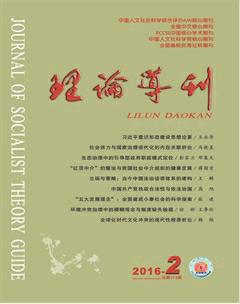布尔迪厄与英格利什的文化生产理论及其现实启示
芮小河
摘要: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文化生产理论以权力和区分为核心,强调文化场各类能动者在文化生产中对文化产品的合法性垄断权力进行争夺,文化场内的生产具有排他性的特征;美国学者詹姆斯·英格利什发展了布尔迪厄的理论,提出“声誉经济”的文化生产理论,认为以交易和协商为核心,文化场的能动者之间进行协商、交易,文化生产离不开大众传播,文化生产具有包容性的特征。两位学者的文化生产理论对于全球化时代发展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文化场”;“声誉经济”;文化生产;文化权力
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2-0038-04
文化生产是社会生产的特殊形式,不同于经济生产。二战后,资本主义生产逐步呈现出从工业生产向文化生产转向的趋势和特点,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的比重大幅度提高。即使是以物质生产为主的各类制造经济也受到了以文化创意为内容的文化生产的制约和影响,以非物质劳动为核心的文化生产的重要性愈益显现。进入新世纪,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流频繁,一个国家的文化生产状况越来越成为衡量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文化生产问题已成为文化学、文艺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学者进行跨学科研究的热点。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将政治经济学概念引入文化生产的研究,提出了“文化场”理论,揭示了文艺领域的文化生产规则,突破了艺术无法从科学的角度来研究的局限。2000年以来,美国学者詹姆斯·英格利什在布尔迪厄的文化生产理论的基础上,陆续在其专著《声誉经济:文化奖与文化价值的流通》及系列文章中进一步阐发了有关文化生产关系、文化资本、象征资本的构成和运作的理论,提出了当代文化生产的“声誉经济”(Economy of Prestige)理论。布尔迪厄与英格利什的文化生产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文化生产的性质、规律、发展趋势,而且对我们制定文化政策、完善文化发展战略有一定的启示。
一、布尔迪厄“文化场”理论视域下的文化生产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布尔迪厄在其代表作《文化的生产场域》《艺术的法则》《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等专著中,系统分析了文化生产涉及的核心问题,包括生产关系、生产者的能动性以及文化价值的创造和传播等。布尔迪厄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被称为“法国最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社会劳动分工产生了各种“场”,比如权力场、艺术场、文学场、政治场等。他将“资本” 概念广泛应用于文化领域的分析,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基础上提出了象征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概念,认为这些是文化场、文学场等文化领域中流通的资本形式,是文化场独立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场域,具有自主性的标记之一。
文化场内的文化生产是怎样进行的呢?布尔迪厄提出,由于文化艺术品是象征物品,文化生产包括“物质生产”(material production)和“象征生产”(symbolic production)两个方面。[1]37物质生产指艺术品的物质形态被创造出来,如画家的画作、作家手稿的创作。而象征生产意味艺术品的文化价值的生产,则是一个由合法的能动者来认可艺术作品合法性的过程。艺术作品“只有被人熟识或得到承认,也就是在社会意义上被有审美素养和能力的公众作为艺术品加以制度化,”其文化价值才得以实现。[2]276这样一来,文化艺术品“生产者”的定义不限于艺术家这个范畴。此外,文化生产除了追求文化价值认可之外,还包括文化价值的传播。文学场参与者作为一个集体,对游戏及其规则的神圣价值具有共同的信念,这保证了游戏能够进行,价值信念同时又是游戏的产物,二者形成循环机制。基于这个机制,对某一作品或某个作家的价值认可才有可能实现。能动者对艺术品合法性的认可意味着在文化场内传播其对价值的信念。“艺术作品价值的生产者不是艺术家,而是作为信仰空间的生产场,信仰空间通过生产对艺术家创造力的信仰,来生产作为偶像的艺术作品的价值。”[2]276由于对游戏神圣价值的集体信仰,文化场的所有能动者进行信誉交换,于是,在艺术家之间,艺术家与赞助人或收藏家之间,艺术家与批评家之间,形成了互相认可的循环关系。艺术家依靠评论和评论家的介入认可其作品的价值。
根据布尔迪厄的文化生产理论,文化生产者发挥能动性意味着对文化权力的运用。布尔迪厄发现,在现代资本主义出现之前,法国文学场一直屈从于权力场,受社会、政治、经济等势力的控制而并未达到自主和独立。法国现代文学取得合法地位是一场法国文人发动的文学革命,经过这场文学革命,封建王朝时期的当权者、贵族等资助人失去了把持文学评判的文化权力,这一权力被移交到了文学场,重新被分配给了包括批评家、作家在内的文学场的参与者们。文化权力的民主化使文学场达到了自主。由此可见,文化场内的文化权力源自于能动者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文化场内的艺术家、评论家等赋予特定的艺术品以声誉,认可其非同一般艺术品的品质,从而生产其象征价值。他们作为能动者的合法性取决于其所拥有的文化资本,而文化资本的数量大小决定他们的权威性的高低以及文化权力的大小。
布尔迪厄将文化场划分为“有限文化生产次场”和“大众文化生产次场”这两个次场,认为二者形成了垂直的等级结构,而前者占据着高端地位。在两个次场内分别进行着面向专业人士的“高雅文化”产品的生产,以及面向普通大众的“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高雅文化”产品通常被认为比“大众文化”产品更具有文化价值。文化场的自主性取决于两个次场之间的对立程度,二者对立程度越高,文化场的自主性越大;反之,亦成立。[2]265通俗艺术作品只能停留在文化消费品的层面上,不会得到专业人士的认可,因而并不具有象征价值。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属于“纯艺术”所在的有限文化生产场,为专业的评论家和艺术家所享有。
文化场内艺术家、评论家、收藏家、出版商、读者等参与者之间形成了生产关系。这些参与者的位置由其在文化场中拥有的资本总量和结构来确定。在布尔迪厄看来,文化场反转了经济场的生产规则,奉行“输者为赢”的逻辑。[1]98先锋派艺术家的“纯艺术”作品在大众文化生产场中遭到普通消费者的冷遇,艺术家因而无法获得经济资本;然而,他们却在“有限文化生产场”得到了同行和专业评论家的高度评价,从而获得了艺术声誉和艺术地位,积累了丰厚的文化资本;相反,通俗艺术作品在“大众文化生产场”受到普通消费者的拥戴,通俗艺术作品作者因此获得巨大经济收益。然而,他们却得不到“有限文化生产场”中的评论家们的认可,也无法获得文化资本。能动者为改变自身在文化场内不利的位置,对评判艺术品“合法性”的文化权力进行竞争,[1]42文化场的象征秩序不断发生变化。
根据布尔迪厄对文化价值生产的社会属性的阐述,在价值评判及社会区分的过程中,欣赏艺术品的趣味得到运用,造成了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的等级区分。[3]“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分别与社会的高层、低层阶级挂钩,文化价值具有等级区分。如此一来,布尔迪厄提出的文化价值生产的社会逻辑以区分为特征,具有“排除”性质。布尔迪厄发现,有关文化、语言、美学、文学的形式主义理论话语制造并维护权力集团的统治,文化生产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布尔迪厄的理论基于其对民族国家框架内的文化生产现象的研究。不过,20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趋势日趋加强,文化生产已经渐渐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跨国公司不断涌现并扩张,跨越国界的国际文化场逐渐形成,文化消费也出现了全球同步的现象。比如,好莱坞的电影、J.K.罗琳的哈里·波特小说的首发仪式能够同一天在纽约、伦敦、上海等地举行,全球消费者可同时获得这些文化产品。经济全球化是跨国文化生产的基础,当代文化生产的物质及空间条件已无法剥离经济因素的影响,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的界限也逐渐模糊。在当代文化生产的物质、空间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形下,英格利什发展了布尔迪厄的文化生产理论。
二、英格利什的“声誉经济”理论视域下的文化生产
詹姆斯·英格利什对布尔迪厄的“文化场”和“文化资本”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大幅度改造。英格利什认为“商业”与“艺术”并非是对立的,包括文化场、文学场在内的每个场域都是实践的“总体经济”(general economy)的一部分。[4]9他不再认同布尔迪厄对文化场两个次场的划分,对其将文化资本作为纯艺术场域独有的资本形式的看法提出了异议。
虽然英格利什认为文化场、政治场等不同的场域均具有独立性,拥有各自形式的流通资本,也拥有各自协商和交易的规则。但他指出,作为“总体经济”的一部分,每个场域都与其他场域有关联。比如,文化场与经济场并非彼此隔绝。任何场域中的任何一种形式的资本都具有混合资本的性质,这是因为特定形式的资本不仅与特定的场域相关联,而且与所有的其他场域和其他形式的资本有着各种的联系。不存在完全自律的或孤立的资本,也不存在只占据“纯文化”场域的资本。即使在“纯艺术”的领域,金钱、政治、名气、社会关系、族裔、性别等因素也会在文化生产中发挥作用。当然,不存在与社会经济、象征经济、政治经济一丝关系都没有的纯粹的经济资本。英格利什将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发展为“不纯粹”(impure)的资本,提示我们附着在文化资本上的文化权力具有多重来源,不一定完全取决于艺术家及评论家等能动者的专业权威性。
英格利什强调文化场参与者的互动与交易关系,发展了布尔迪厄有关文化生产关系的理论。英格利什认为,当代文化场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不完全是像布尔迪厄所分析的那样,是对合法性垄断权力进行你死我活的争斗关系,参与者之间更多是协商和交易的关系。这是因为无论在哪个场域内,任何形式的资本都是“不纯粹”的,而每一个资本持有者都会持续地投入资本,试图维护或修改资本的“不纯粹”比率。“这只是一个交换率、协商规则不同的问题”。[4]10英格利什以文化奖的文化生产来说明生产者之间的交易、协商的关系是当代文化生产的特征之一。他提出,文化奖是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等各种形式的资本之间进行交易的“最佳的商榷工具”。[4]10文化奖促使各类具有不同资本、利益和倾向的能动者产生互动,参与到集体的价值生产活动中来。围绕诸多国际文化奖的文化生产是当代跨国文化生产的一个缩影。
根据英格利什对文化奖的文化生产研究,文化场中文学奖的参与者按照其功能划分包含组织、颁奖机构的人员、评委、参评作家、媒体从业者和读者、观众等。他们是文化生产的能动者,持有不同形式的资本,通过文化奖将所持资本交换为他们希冀获得的资本。“声誉”(prestige)作为象征资本的一种形式,是所有能动者希望得到的,声誉从评委到获奖人、再到读者与观众并回到赞助人之间循环流通。在这个模式中参与者各有所得。首先,为了保证文学奖判断价值的权威性赢得公众的信任,文学评优必然是由文学场或社会场中掌握了相当话语权力的组织、机构、权威来完成,评委们凭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教育资本等被选择担当价值评判人,他们的声望因担任文化权威的角色得到加强;赞助者付出经济资本,但是从文化奖声望中得到社会资本作为回报;艺术家因获奖得到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资本,提升了艺术地位,反过来,艺术家的地位又增强了文化奖的声望。英格利什提出的“声誉经济”模式中,文化奖能动者们构成一个文化生产的联合体,而文化价值传播是文化生产中一个重要的环节,这是持有不同资本的能动者进行协商和交易以促进不同资本进行转换的阶段。文化价值传播的对象还包括普通大众,而且只有在普通大众接受并认可的情形下,声誉象征资本才会以较高的比率向经济资本进行转换。
除“声誉”象征资本外,英格利什还扩充了布尔迪厄提出的象征资本的内涵,创造了“新闻资本”(journalistic capital)这个术语来说明文化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新兴象征资本形式。他认为媒体已成为当代文化生产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媒体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生产者的社会可见性,“新闻资本”的内涵就是“可见性、名气、丑闻”,[4]123这是因为新闻资本在尽可能提高曝光率的情形下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新闻资本的核心是社会可视性,可视性就意味着“出名”,不论是好的口碑还是恶名。新闻资本加入其他形式的象征资本的行列,通过文学奖在参与者之间流通。文化奖从成立起就需要积累社会资源,以获得声望。英格利什发现文化奖在本质上具有遭到公众非议的一面,这些非议甚至丑闻会使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产生的效果是“增加文化奖的新闻资本,加速象征资本和文化声望的积累”。[5]208
英格利什的新闻资本概念反映了代表市场力量的普通消费者在文化生产中的作用。在媒体参与文化价值生产的情况下,消费者们并不按社会等级来被区分,这是因为媒体的大众传播性质决定其对观众不加阶级区分地予以吸收,从而改变了文化价值生产的社会条件。正如约翰·弗洛所指出的:“大众观众的形成原则是容纳而非排除,也非高层与低层的对立、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些在当代由于大众观众出现而被修正。出现了联合不同阶级的同质化的观众群,或者极度区分的小众化对象。特定的大众群体是非阶级的。”[6]23媒体的介入使当代文化价值生产形成了新的逻辑,这一逻辑以包容性为特征。在当代文化生产中,“容纳”逻辑而不是“排除”逻辑在发挥作用。在这一逻辑作用下,不同形式的资本之间的转换与交易越来越复杂,各个场域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
三、布尔迪厄与英格利什文化生产理论的现实启示
从“文化场”到“声誉经济”,布尔迪厄和英格利什研究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生产。布尔迪厄的分析案例集中在19世纪法国文学场中文学艺术的文化生产,以及20世纪上半叶文化场中视觉艺术的文化生产,而英格利什的研究则聚焦于20世纪后半叶以来欧美文化场中文化奖的文化生产案例;布尔迪厄的文化生产理论以权力和区分为特征,通过在文化生产中能动者对合法性垄断权力的争夺,说明了文化场内的文化价值生产过程具有排他性和垄断性;而英格利什的文化生产理论以交易、包容性为特征,强调文化生产能动者之间协商、交易的关系,并提出新闻资本作为象征资本在当代文化生产的传播环节的重要性,说明文化价值的生产离不开大众传播。此外,布尔迪厄和英格利什都对保障文化生产的文化权力构成形式和运作进行了分析,布尔迪厄通过对文化权力在文化场中的民主化现象的研究,否认文化权力与经济因素有直接关联,但却承认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或经济基础的同构性;而英格利什则通过声誉经济中普通大众对文化权力的分享,肯定了文化权力与经济因素之间的直接联系。
当今时代,文化已成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新要素。文化生产的研究对于认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属性,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形势下,全球化势不可挡,跨国的文化生产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但衡量文化实力却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全球范围内,文化产品的输出与输入的不平等、不均衡现象越来越突出。英、美等经济社会发达的西方国家的文化资源丰富,其图书、影视、娱乐、时尚、音乐等文化产业发达,在全球文化输出方面一直占据优势。近年来亚洲的日本、韩国也不甘落后,积极发展时尚、音乐、动漫等优势的文化产业,竞相输出此类文化产品并取得了很大成效。一些文化强国在其文化产业的长期发展中积累了声誉,始终在一些领域引领世界潮流。虽然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输出对比差异强烈,但采取封闭措施,阻断文化强国的文化输出已经不可能。
我国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应对日趋激烈的文化层面的国际竞争,就有必要进一步全面认识当代文化生产的特征、机制、规律等问题。在这一方面,布尔迪厄与英格利什的文化生产理论给我们以诸多启示:
第一,充分调动文化资源,发挥文化生产能动者的作用。两位理论家对文化生产的“物质生产”与“象征生产”两方面的阐述显示,文化生产的能动者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能动作用。文化生产并非仅仅事关艺术家、文化界人士等文化价值的直接创造者,文化生产的能动者还包括承担物质生产的文化生产实体以及承担文化传播的各类媒体。文化产业是文化生产的物质基础,文化生产的兴旺发达离不开具有高水平的出版社、影视公司、互联网公司等的支持,也离不开传播媒介,包括纸质媒体及电子媒体等各方面在文化再生产过程中的传播作用。因此,发展文化事业一方面要结合对文化产业的发展,重视培育文化产业,另一方面要注重在相关行业培养能够担当起创造文化价值的专业人材。
第二,科学制定文化政策,协调文化生产能动者之间的关系,并促进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及社会资本之间以较高的比率进行转换,以保障能动者应有的利益,促进其积极主动地参与文化生产。要特别尊重艺术家的独创性以及评判艺术的评论家的独立性,为积累文化声誉造就良好的基础条件。此外,由于传播与消费是文化生产过程中价值实现增殖的关键阶段,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文化市场的培育,在文化传播中引入经济、文化资本等社会资源,从而建立良好的文化生产体系。
第三,高度重视对文化价值生产权力的竞争与协商,构建并推行本土化的文化价值标准。中国市场是全球文化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品也是观念、意识形态的载体,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及其传播的内容,都无可避免地会受到能动者所在的文化的观念或意识形态的浸染,文化产品成为传播这些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工具。我们要辩证地看待输入中国的文化产品,在坚持本土化的文化价值标准的基础上与其他民族文化展开交流与对话,不断丰富本民族文化的内涵。无论从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还是加强国家文化安全方面着想,发展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特色文化并将其转化成为优势文化产品都是我国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Bourdieu, Pierre.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2]布尔迪厄. 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M]. 刘晖,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3]Bourdieu, Pierre.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M]. 1984.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 P, 2007.
[4]English,James. The Economy of Prestige: Prizes, Award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Cultural Value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 P, 2005.
[5]English, James. Winning the Culture Game: Prizes, Awards, and the Rules of Art [J]. New Literary History 33 (Winter 2002): 109-135.
[6]Frow, John. Cultural Studies and Cultural Value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责任编辑:黎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