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帝国查士丁尼反犹政策原因考
刘 宇 方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拜占庭帝国查士丁尼反犹政策原因考
刘 宇 方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收录在《查士丁尼法典》中的查士丁尼反犹政策对拜占庭帝国的犹太人、犹太教以及拜占庭帝国和整个东地中海地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强化基督教会的势力,确保国内政治环境的安定团结,弥补国库空虚,占据红海控海权并打开东方航路,查士丁尼成为坚定的反犹实施者。通过颁布反犹政策,查士丁尼不仅打击了犹太教势力,镇压了以犹太教为信仰的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武装起义,更为6世纪拜占庭帝国从拉丁化向希腊化转型,以及东地中海地区的政治局势埋下了伏笔。以《查士丁尼法典》为标志,查士丁尼将拜占庭的反犹活动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拜占庭帝国;查士丁尼;反犹政策
查士丁尼(Justinian)时期(483—565年)是拜占庭帝国从古代晚期向希腊化时代过渡的重要时期。因查士丁尼在任时做出诸多丰功伟绩,故他的反犹政策便显得不太起眼。然而,反犹政策却是关系到拜占庭帝国国内外局势的关键所在。首先,该时期的反犹政策有效遏制了犹太教势力的蔓延,保证了拜占庭国教的历史地位。其次,它打击了以犹太人为首、信奉犹太教的各民族对抗拜占庭展开的武装起义,保障了国内社会的稳定。更重要的是,它对东地中海地区,乃至于红海地区的关注是拜占庭帝国从拉丁化向希腊化转型的重要尝试。因此,查士丁尼的反犹政策贯穿于其施行的内政外交体系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对查士丁尼颁布反犹政策的原因考察,不仅可以梳理出拜占庭犹太人及犹太教地位下滑的流变过程,更可以由浅入深地理解反犹政策与查士丁尼内政外交体系的交融关系,故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
对查士丁尼反犹政策的研究,国外学界已经蔚然成风,比较著名的学者有尼古拉·斯·德·兰格(NicholasDeLange),安德鲁·沙尔夫(AndrewSharf),凯瑟琳·布鲁尔(CatherineBrewer)和阿姆农·林德(AmnonLinder)等。国内学界对此问题也略有涉及,①疏会玲:《保护与限制的双重性——查士丁尼犹太政策初探》,《世界民族》2015年第5期。但主要陷入到查士丁尼是否反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争辩中。有学者认为查士丁尼实施的并非反犹政策,而是保护政策;②Catherine Brewer, “The Status of the Jews in Roman Legislation: The Reign of Justinian 527-565 CE,” European Judaism, vol. 38, 2005. 疏会玲的作品也持类似观点。但其他学者则认为查士丁尼实施的就是反犹政策。③Andrew Sharf, Byzantine Jewry: From Justinian to the Fourth Crusad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imited, 1971; Amnon Linder, The Jews in Roman Imperial Legishation,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Oded Irshai, “Confronting A Christian Empire: Jewish Life and Culture in the World of Early Byzantium,” in Jews in Byzantium: dialectics of Minority and Majority Cultures, eds. by Robert Bonfil, Oded Irshai et al.,Leiden: Brill, 2012, pp.17-64.对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回归到查士丁尼颁布相关政策的原因和意图上,从源头进行分析和探讨,以便从本质上更深刻地领会查士丁尼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真实态度。这不仅关系到拜占庭犹太人的社会地位,更关系到查士丁尼内政外交体系的有机整体。因此,对查士丁尼反犹政策的原因考辨,是我们研究查士丁尼时期拜占庭历史另一个崭新又重要的切入点,具有较为重要的研究意义。
一
查士丁尼的反犹政策不仅包括反犹太人,还包括反信奉犹太教的各民族,如撒玛利亚人和北非的柏柏尔人等。总体上说,它是一个包罗政治、经济、宗教等多方面因素的有机体系。这其中,宗教因素是查士丁尼反犹的显要原因,而它也是证明查士丁尼施行的是反犹政策的第一个关键所在。
促使查士丁尼施行反犹政策的宗教原因在于犹太教势力过于强大,阻碍了国教基督教的发展势头。虽然犹太教早已被拜占庭官方定义为“下等宗教”,但是长期以来它对基督教徒却一直具有独特的吸引力。首先,犹太教抢占了基督教的信徒数量。从使徒时代起,安条克就有络绎不绝的基督教徒对犹太教产生兴趣。4世纪以来,聆听犹太传教者传教成为上流社会、尤其是贵妇人的一种风尚。*S. Joannis Chrysostomi Adversus Judaeos, in Jacques-Paul Migne, ed.,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es, series graeca, vol. 48, Caroline: Nabu Press, 2010, cols. 843-942; M. Simon, “La polémique antijuive de S. Jean Chrysostome et le mouvement judaÏsant d’Antioche,” Annuaire de l’Institut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Orientales et Slaves,No.4, 1936, pp.404-405, 407.在北非地区的许多城市中,古老的犹太社区势力强大,犹太教的传播速度堪比基督教,有几个城市甚至有犹太化的倾向。*FulgentiusFerrandus, FulgentiiFerrandiCarthaginensis ecclesiae diaconiBreuiatiocanonum, vol.88, Claude Chappelet ed., Salamanca: Universidad de Salamanca, 1588, pp.69, 185, 186, 196; John Climacus,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es, vol.221, in Jacques-Paul Migne,ed., Appendix ad saeculum X complectens Auctores incertianniet opera adespotika accedunt monumenta diplomatica, Paris: Parisiis Garnierrfratres, 1862, cols.827-828; P. Monceaux, “Les Colonies juivesdansl’ Afrique romaine,”Revue des Etudes Juives, vol.44, 1902, p.27.
其次,犹太教的教义和仪式逐渐取代了基督教的教义和仪式。比如5世纪,埃及行省的基督教徒依然狂热地遵守犹太教将安息日定于星期六的规定。*Victor A. Tcherikover, Corpus papyrorum judaicorum, vol.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110.同时期,一支被基督教会称为“天空礼拜者(Caelicolists)”的犹太-基督教派兴起,将犹太教的割礼作为洗礼仪式,否认三位一体,同时用犹太教礼拜仪式中的“天堂(theheavens)”概念取代了基督教的“上帝(God)”概念。*Augustini epistolae XLIV.6.13, in 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es, series graeca, vol.38, col. 180; J. M. Fuller,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Biography, vol.1, London: Wace and Piercy Press, 1911, p.589.6世纪初,仍有大量的基督教徒遵守犹太教安息日和其他宗教节日的作息,甚至有很多基督教徒还实行割礼。还有一些基督教徒将犹太教的经文护符匣(Tefillin)和“美祖扎赫(Mezuzot)”*即犹太人挂在自家门柱上的经文楣铭。带进基督教堂。*S. Kazan, “Isaac of Antioch’s Homily against the Jews,” Oriens Christianus, No.47, 1963, pp.94-96.由于这类行为过于频繁,最后导致基督教堂内的装饰都偏向犹太化,令基督教徒们产生一种走进犹太会堂的错觉。
再次,犹太教社区具有的强大权势甚至可以直接冒犯当地的基督教会。比如,北非的“天空崇拜者”因在当地强大的势力,常常以异教者身份蔑视法律,当地政府和基督教会只能敢怒不敢言。*C.Th. 16.8.19, in 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 eds. by C.Pharr, TS Davidson,et a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 p.469; C.J.1.9.12, in Corpus Iuris Civilis, ed. by Paul Krüger,Clark: The Lawbook Exchange, 2010, p.61.但是犹太人的不可一世激起了基督教会和神职人员的强烈不满。这正是基督教会长期以来反犹情绪高涨的主要原因。
上述种种案例都反映了犹太教在拜占庭帝国境内的强大生命力和权势。基督教作为国教的主导地位显然受到它的致命威胁。因此,为了安抚基督教会的不满,强化与基督教会的亲密关系,稳固基督教在国内的主导地位,加强基督教思想的传播,查士丁尼在立法中加大了打击犹太人和犹太教的力度。首先,《查士丁尼法典》中不断重申拜占庭早期撤销犹太人权利的各项法律条款。*C.Th. 12.1.158, in 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 p.463; C.Th. 12.1.157, in 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 p.466; C.J. 10.32.49, in Codex Justinianus recognovit et Retractavit, p.338.比如,它延续了《赛奥多西法典》宣布废除“犹太人拥有无需担任基督教神职人员的权利”的条文。*C. Th. 12.1.100, in 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 p.440; C.Th. 12.1.99, in 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 p.440; C.J. 1.9.5, in Codex Justinianus recognovit et Retractavit, Berlin: Weidmann, 1873, p.40.这便在律法上否定了犹太教的合法性,为随后大规模阻止犹太人改宗基督教埋下了伏笔。
另外,新法典中还延续了早期法典对犹太教宗教礼仪,尤其是割礼的严格限制。查士丁尼宣布禁止犹太人对非犹太人的孩童实行割礼*Digesta XLVIII.8.11, in Corpus Iuris Civilis, vol. 1, p.853, note 6.;一旦犹太人对具有独立人格的成年人实行割礼,犹太人将被没收全部财产并遭到驱逐。*C.Th. XVI.8.26, in 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 pp.470-471; C.J. 1.9. 16, in The Civil Law, vol.Ⅻ, ed. by Samuel P.Scott, Cincinnati: The Central Trust Company, 1932, p.61.查士丁尼还声明,如果犹太人劝基督教徒改变宗教信仰、信奉犹太教,哪怕只是试图劝说,并未施行割礼,犹太人仍将被处以死刑。*C.J.1.9.15, in The Civil Law, vol.Ⅻ, p.61.如果基督教徒信奉犹太教,其遗嘱的法律效力会受到限制,财产会被全部没收充公。*C.Th. XVI.7.3, in 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 p.466; C.J. 1.7.2, in Corpus Iuris Civilis, vol. 1, p.60 and C.Th. XVI.8.7, in 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 pp.467-468; C.J.1.7.1, in The Civil Law, vol.Ⅻ, p.58.另外,查士丁尼规定,犹太人不能与基督教徒通婚,如果犯法,将被处以通奸罪名,并遭到所有人唾弃;*C. J.1.9.5, in The Civil Law, vol.Ⅻ, p.61.而且,犹太人也不能保留任何与犹太民族和犹太教有关的婚娶习俗。*C. J.1.9.6, in The Civil Law, vol.Ⅻ, p.61.这样,查士丁尼便从宗教仪式上打压了犹太教的势头。
其次,查士丁尼颁布了新的反犹律法。比如,他禁止犹太人建造新会堂,只能修缮原有设施。不过,犹太人一旦被当地政府发现他们对旧会堂进行修缮,则又要处以50镑金币的罚款,被修缮的会堂也将没收充公。换句话说,查士丁尼试图用这种方式限制并缩小犹太会堂建筑群的规模。在此规定下,犹太会堂往往因年久失修而倒塌,犹太人也逐渐失去了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但这还仅仅是一个开端。随着后期犹太人武装暴动的频率越来越高,查士丁尼直接下令强行拆除那些犹太人闹事严重地区的犹太会堂。535年,查士丁尼宣布清除北非地区所有的犹太会堂,禁止犹太人和其他异教徒举办宗教庆典。545年,查士丁尼彻底解决了犹太会堂的问题:如果犹太会堂的选址正好位于基督教会占有的土地上,则该会堂会立即被认定为非法建筑予以拆除。*Novel 131, Schoell and Kroll, in Corpus Iuris Civilis, vol.3, p.663.以此,查士丁尼从宗教传播空间上打击犹太教,从而缩减犹太教的信徒数量。
此外,新的反犹律法对犹太教的宗教节日和经文语言做出了硬性规定。比如,查士丁尼认为犹太教的逾越节如果在基督教的复活节之前庆祝,会被看成“犹太教更为重要”的标志,令基督教徒蒙羞。因此他宣布,“按历法计算,即使逾越节排到了复活节之前,犹太人也禁止进行庆祝和举行宗教仪式”。*Novel 131, Schoell and Kroll, in Corpus Iuris Civilis, vol.3, p.663.又如,查士丁尼认为犹太人用希伯来语阐释旧约经文对基督教徒来说也是不光彩的。因此553年,他颁布了一条新法,规定犹太人不允许用希伯来语阅读或阐释摩西五经。*Novel 146, Schoell and Kroll, in Corpus Iuris Civilis, vol.3, p.714; Juster Jean, Les Juifs dans l’Empire Romain: leur condition juridiqu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vol.1, Caroline: Nabu Press, 2010, pp.372-373, note 6, and p.374, note 1, and pp.375-376. 英文译本参见James Parkes, The Conflict of the Church and the Synagogue, London: Lightning Source Inc., 2008, pp.392-393.有关查士丁尼对犹太人文学方面的法律规定,参见Salo Baron, A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 vol.3, 2nd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33, note 2.摩西五经只能用希腊文、拉丁文或其他非希伯来文进行阅读。*查士丁尼禁止犹太人阅读希伯来语圣经的重要原因是为了鼓励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减少希伯来语“不正确的经文阐释”带来的精神毒害。参见C.Th. XVI.8.11, in 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 p.468.由此,查士丁尼又在宗教作息、交流途径上打击了犹太教的势力。
更重要的是,为了从源头上压制犹太教,从根本上解决犹太教抢占基督教徒人数、取代基督教教义与礼拜仪式、冒犯基督教会等宗教问题,查士丁尼直接做出了组织犹太人改宗基督教的强势举措。在他看来,犹太人必须改宗基督教才能够被视作基督教胜利的活证明而存在于拜占庭帝国的国土上。但与后期多位暴力改宗犹太人的拜占庭皇帝相比,查士丁尼施行的改宗运动还是比较温和的。此时犹太人皈依基督教的途径或是通过与基督教争辩,或者是通过奇迹的降临,最终使其精神得到升华,灵魂得到皈依。查士丁尼宣称,犹太人的皈依必须来自内心的转变。如果犹太人是因对迫害的恐惧或是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而皈依,那么就是对基督教极大的侮辱。*原文出自于《克莱门汀检别》(Clementine Recognitions),可参见Jacques-PaulMigne ed.,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es, vol.1,Charleston: Nabu Press, 2010, cols. 1456B-1461B; James Parkes, The Conflict of the Church and the Synagogue: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Anti-Semitism,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61, pp.397-400; F. Cumont, “Uneformulegreècque de renonciation au juda? sme,” WienerStudien,No.24, 1902, pp.230-240; V. Ermoni, “Abjuration”, Dictionnaired’arche’ologiechrdtienne et de liturgie, vol.1, 1924, cols.98-103; V. N.Beneshevit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Jews in Byzantium from theSixth to the Ninth Centuries,” Yevreiskaya Misl, No. 2, 1926, pp.305-318(Greek texts), pp.197-224 (commentary in Russian).因此,该时期改宗运动的宗旨还是在于打动犹太人的内心,使其身心灵都得到皈依。这种精神得到官方认可,并于787年第二次尼西亚宗教会议中写入教会法。*有关查士丁尼时期的文献资料,可参见Timothei Presbyteri De Receptione Haeriticorum, in Jacques-PaulMigne ed.,Patrologiae cursus completes, vol.86, Charleston: Nabu Press, 2010, col. 72.有关第二次尼西亚会议的文献,可参见J. D. Mansi, Sanctorum conciliorum nova et amplissima collection, vol.14,Florence and Venice, 1759, col.427.
然而,犹太教遭到压制的结果并不像查士丁尼希望的那样被同化到基督教中去了。相反,信奉犹太教的各民族内部的宗教情结和民族情结却越发高涨。他们与国家和政府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与拜占庭人之间的民族隔阂越来越大,从而成为社会上极不安定的因素。因此,查士丁尼在宗教层面的反犹活动逐渐过渡到政治领域当中。
二
纵观拜占庭早期史,宗教领域产生的思想碰撞往往会引发政治混乱。由于犹太教势力在宗教领域遭到打压,信奉犹太教的信众们便选择在政治领域掀起一轮又一轮的武装起义。因此,在政治上打击犹太教和犹太人的势力是查士丁尼施行反犹政策的第二个原因,也是确定他施行反对犹太教和犹太人政策的第二个关键所在。
首先,查士丁尼需要解决的是局部地区的武装起义,北非地区首当其冲。尽管查士丁尼制订了严苛的法律限制犹太教势力的发展,但北非位于偏远地区,法律效力延伸到那里便薄弱许多。因此,当地的犹太教势力依然十分顽强。另外,数量庞大的柏柏尔人皈依了犹太教,成为当地规模最为庞大的犹太教族群。有了他们的加入,犹太教徒的数量激增,犹太-柏柏尔部落迅速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强大团体。他们的影响力遍及所有柏柏尔村落,组成的武装力量竟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持久地对抗帝国军队。*N. Slouchz, “Hébréo-Phéniciens et Judéo-Berbères-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es Juifs et du Judaisme en Afrique,” Archives Marocaines, No. 14, 1908, pp.192, 378-386.这种形势让北非地区面临脱离帝国统治而独立的危险,查士丁尼对此十分恼火。因此,在534年,查士丁尼命令大批帝国精英部队前往北非镇压犹太-柏柏尔人的暴乱,并于535年制定新律,除了拆除北非所有的犹太会堂之外,还禁止北非传播犹太教,以强化镇压的军事成果。
在局部地区的武装起义中,查士丁尼面临的更大威胁来自信奉犹太教的撒玛利亚人(Samaritans)。他们活跃在巴勒斯坦地区,从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I)时代(324—337年)就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和犹太信众,并接连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第一次起义发生在484年。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动乱中,撒玛利亚人趁机夺取了纳布卢斯(Nablus,又称Shkhem),杀害当地基督教主教,宣布独立并选举出自己的国王。帝国政府对他们的镇压十分困难,最后不得不派遣一支军事实力最强的卫戍部队驻进纳布卢斯,才最终摧毁了撒玛利亚独立王国,并将撒玛利亚人的圣所改建为基督教堂。*John Malalas, The Chronicle of John Malalas, trans. by Elizabeth Jeffreys, Michael Jeffreys and Roger Scott, Melbourne: 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 1986, pp.110-112.但是至阿纳斯塔修斯皇帝(AnastasiosI)时期(491—518年),国内的动乱又为撒玛利亚人反抗拜占庭统治制造了时机,撒玛利亚人将实力逐渐虚弱的卫戍部队消灭后又重新占领了纳布卢斯。*Procopius, Procopii Caesariensis Opera Omnia, J. Haury ed., Leipzig: B. G. Teubneri, 1963, pp.165-166.
529年,撒玛利亚人发动了第二次起义。他们占领了从凯撒里亚(Caesarea)沿海到加里利海(Kinneret)的太巴列(Tiberias)之间所有的古撒玛利亚地区,查士丁尼不得不调动大批出外征战的军队回来镇压撒玛利亚人。最终取得的军事成果是将撒玛利亚人的活动范围缩小至基利心山(Gerizim)一带,并用高墙将他们禁锢其中。为防止他们继续暴乱,查士丁尼还为他们新建了5座基督教堂,用以瓦解他们对犹太教的忠诚。*John Malalas, The Chronicle of John Malalas, p.455.同年,查士丁尼还颁布新法,宣布没收撒玛利亚人的全部财产,强迫撒玛利亚人的妻子儿女皈依基督教。直到瓦西里一世(BasilI)时期(867—886年),这些法令依然有效,并随着撒玛利亚民族的消亡而转移到犹太人的身上。*Novel 144, Schoell and Kroll, in Corpus Iuris Civilis, pp.709-710; C.J. 1.5.17-21, in Corpus Iuris Civilis, pp.56-60; Basilicorum libri XX, in Groningen Gravenhage, ed. by H.J.Scheltema and N.Vander Wal ed.,Series A, vol.1, 1955, pp.11-12.
然而查士丁尼的整治措施并没有彻底削弱撒玛利亚人的锐气。他们于555年再度发动起义,杀害了驻守在凯撒里亚地区的驻军首领。*John Malalas, The Chronicle of John Malalas, p. 487; Michael the Syrian, La Chronique de Michelle syrien, IX. 31, vol.2,trans.Jean-Baptiste Chabot,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p.262; F. Nau,“L’histoireecclesiastique de Jean d’Asie, ”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 No. 2, 1897, p. 489. 关于他们起义的正确日期可参见E. Stein, Histoire duBas-Empire, vol.2, Paris: Hakkert, 1949, p.374, note 2.更让查士丁尼感到棘手的是,大批支持撒玛利亚人的犹太人也纷纷加入到这次起义中。该起义的规模之大,甚至对整个帝国的统治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为了粉碎撒玛利亚和犹太人的武装力量,查士丁尼不得不调动远征在外、身处北非的精锐军队,才最终将起义镇压下去。*资料来源于埃及留存的主要文献:John of Nikiu, The Chronicle of John of Nikiu, trans. by R.H.Charles, London: Evolution Pub & Manufacturing, 2007, p.148.
此外,除了局部地区的武装斗争,查士丁尼面临更致命的威胁来自于以君士坦丁堡为首的各大城市中,尤其是大竞技场(Hippodrome)内的犹太人。犹太人对大竞技场的游戏规则十分熟悉,因为它是完全仿照古以色列国王所罗门(Sdomon,公元前970—前930年)定下的规矩修建而成。*犹太教讲解《旧约》的布道书卷《米德拉什》(Midrash)详细记载了所罗门王的荣耀。书中将所罗门建立的赛马场看作是其荣耀的主要标志。相关资料可参见Kissēve-ippodrominshelshlomo ha-melekh, in A. Jellinek ed.,Beth Hamidrasch, vol.2,Jerusalem: Bamberger and Wahrmann, 1938, pp.83-86; J. Perles, “Thron and Circus des Koenigs Salamo,” Monatsschriftfuer Geschichte und Wissenschaft des Judentums, vol.21, 1872, pp.122-139; Albert M. Hyamson and Dr. A. M. Silbermann, Vallentine’s Jewish Encyclopaedia, vol.2, London: Shapiro, Vallentine & Co., 1938, p. 442. 有关拜占庭赛马场完全复原所罗门荣耀的资料可参见J. Perles, “Juedisch-byzantinischeBeziehungen,” ByzantinischeZeitschrift, No. 2, 1893, p. 127; John Malalas, The Chronicle of John Malalas, pp.173-6; A. Vogt, “L’Hippodromede Constantinople,” Byzantion, No.10, 1935, p. 472.因此,大竞技场成了犹太人开展各类政治活动的主要场所。另外,由于赛马场车迷群体的蓝、绿党也起源于犹太人的政治习俗,*Cassiodori senatoris variae LI, in H. Droysen ed.,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Auctorum antiquissimorum XI, Hanover and Berlin: Hahnsche Buchhandlung,1892, p. 105; J. Perles, “Juedisch-byzantinische Beziehungen,” Byzantinische Zeitschrift, vol.2, No.3, 1962, p.124.这更为犹太人在这里举行政治集会提供了便利。他们经常利用赛场表达政治意愿,发泄对当局政策的不满。*陈志强:《拜占庭帝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92页。
在查士丁尼统治之前,犹太人曾几次卷入到严重的竞技场动乱中。比如484年,安条克地区的蓝党爆发了一场反对泽诺皇帝(Zeno, 474—491年)的起义,犹太人作为蓝党的中坚力量积极效力。而后,因其锋芒毕露而成为大家打击的对象,泽诺皇帝亲自率领当地支持自己的绿党对蓝党、尤其是犹太人进行大规模镇压。不仅当地的犹太会堂被焚毁,就连犹太人的尸骨竟也被从坟墓中刨出来一并烧毁。*John Malalas, The Chronicle of John Malalas, pp.389-90; 若想参阅更全的文本可参见John Malalas, The Chronicle ofJohn Malalas, trans. M. Spinker and G. Downe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0, pp.111-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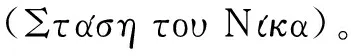
由此可见,有犹太人参与并制造的政治混乱对查士丁尼的打击是极为致命的。他们热衷参与政事的性格成为一颗不定时炸弹,不仅严重危害公共秩序的稳定,更严重威胁查士丁尼的帝王统治。与局部地区的武装起义有所不同,犹太人在大竞技场上引发政治动乱造成的危害不仅直接冲击了查士丁尼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而且政治破坏性更强烈,社会影响力也更广泛。这些政治成本都是查士丁尼支付不起的。因此对他而言,从根本上反对犹太人、打击犹太人的政治势力和武装力量是最有效、也是最安全的解决方法。
当然,反犹政策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政治上打击犹太人势必会在经济方面产生相应的连带反应。而查士丁尼在经济方面反对犹太人的政策不仅对拜占庭犹太人带来影响,更成为拜占庭帝国从拉丁化向希腊化转型的重要尝试,对帝国和整个东地中海地区都带来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三
拜占庭国内的经济因素并非查士丁尼施行反犹政策的主要原因。相比于上述宗教和政治因素,拜占庭犹太人在国内经济方面遭受的打击只是查士丁尼反犹政策这个有机整体所带来的余震。不过其效果却为查士丁尼带来了巨大的收获,即查士丁尼通过犹太人积累的个人财富为帝国国库填补巨大亏空。
其实,大流散时期的犹太民族在寄居国内一般是被限制拥有土地的*王亚宁:《犹太民族与土地的特殊关系》,《世界民族》 2006年第6期。,这使得犹太人只能从事一些商业贸易类的行当。但头脑灵活的犹太人却因此积攒起大量财富。慢慢的,“犹太人”似乎成为“金钱”的代名词。据史料记载,早在瓦伦斯皇帝(Valens)统治时期(364—378年),犹太人的财富就十分可观,足够买得起一座豪华的私人花园。*Michael the Syrian, La Chronique de Michelle syrien,VII.7, vol.1,p.294; James Parkes, The Conflict of the Church and the Synagogue: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Anti-Semitism,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61, p.181.有鉴于此,查士丁尼便在立法上强迫犹太人必须担任“百人长”(Decurions,拉丁文为decurio)*或译作“地方事务官”。一职。百人长不同于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同名官职。它的责任不再是管理当地人口,而只是负责征收当地税金,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征收税金看上去是一个好差事,但背后埋伏着更大的诡计。因为如果征收的税金没有填补掉当地政府的财政亏空,那么其余的财政亏空必须由百人长以个人之力填补完。若百人长无力填补亏空,则将受到极为严酷的惩罚:剩余的亏空较小,要被斩手;剩余的亏空较大,则直接处以死刑。*C. Th. 16.8.2, 3, 4, 13, in 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 pp.467-468; C. Th. 16.8.24, in 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 p.470.赛奥多西二世皇帝(TheodosiosII)执政时期(408—450年),部分犹太人特别是在犹太社区担任重要职务的犹太贵族尚可以通过缴纳违约金等替代品避免承担该职责。*C. Th. 12.1.99, in 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 pp.356-357; C. Th. 12.1.157 and 165, in 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 pp.364-366.但是,在537年颁布的《新律》中,查士丁尼宣布废除“犹太人可以用替代品规避担任百人长职务”的法令。从此以后,任何犹太人都无法以任何手段避免这项惩罚。就这样,查士丁尼把自己穷兵黩武、连年征战所造成的国库巨大亏空全都算在了犹太人的头上,*A. A. Vasiliev,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vol. 1, Madison: Wisconsin University Press, 1958, p.180. 同时参见陈志强:《拜占庭帝国通史》,第124页。用犹太人的个人力量为整个帝国的财政赤字买单。这对犹太人来说是巨大的财政灾难,但是对查士丁尼来说却获得了巨额经济利润,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经济与财政危机。
尽管如此,国内经济的利益依然无法构成查士丁尼在经济上施行反犹政策的全部内容。对查士丁尼和整个拜占庭帝国来说,在经济上施行反犹政策的关键在于它能够有效帮助帝国夺取到红海地区的控海权。这不仅关系到拜占庭帝国的国际贸易利益,更关系到拜占庭帝国向希腊化转型的命运。因此,它构成了查士丁尼施行反犹政策的第三个原因,也是确定他施行反对犹太教和犹太人政策的第三个关键所在。
尽管在6世纪中前期,查士丁尼重新收复了西部地区包括北非和意大利在内的部分领土,再度将地中海变为拜占庭帝国的内海。但取得这样的战绩却支付了高昂的代价。它建立在查士丁尼穷兵黩武、连年发动多次对外战争的基础之上。维持战争的投入耗尽了帝国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人民对此怨声载道,以至于同时代的史家背地里将查士丁尼视作暴君和魔鬼的化身。*Anthony Kaldellis, Procopius of Caesarea: Tyranny,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t the End of Antiquit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pp.118-159.总体来说,帝国对西部地区的控制已如强弩之末。此时的拜占庭帝国必须考虑放弃掉对昔日拉丁罗马帝国荣耀的追求,重新找到适合于东罗马帝国发展的道路。为此,它必须将目光转向东部地区,获得对东部地区的控制是拜占庭帝国生存的关键。这种从拉丁西部地区逐渐转移到希腊东部地区的尝试,被称为拜占庭帝国的希腊化转型。它涉及到地域、文化、语言、宗教、习俗、军事、行政等多方面的转化,是一个更为复杂且庞大的系统。但所有这一切存在的根本在于对东部地区土地的占有上。
从这一点上来看,能否获得红海地区的控制权,是拜占庭帝国能否占领东部地区大片土地的核心。因为红海对整个东地中海地区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不仅是连通整个欧亚非大陆东部地区贸易航线的必经之路,更是连接亚、欧、非三大洲、控制整片地区的咽喉要道。然而,红海地区早在4世纪中叶便由埃塞俄比亚(Ethiopia)控制,其中河道东侧的控制权暂由希米亚里特(Himyarites)王国*是由前文所述的“天空崇拜者”教派所建立的国家名称。和埃塞俄比亚大领主共同掌管。长期以来,当地的基督教势力积贫积弱,犹太教势力一支独大。*Philostorgii historia ecclesiastica, 111.4-6, in John Flemminged., Die griechischen christlichen Schriftsteller der ersten drei Jahrhunderte, vol.21, Leipzig: Hinrichs, 1901, pp.32-36;R. Devreesse, Le Patriarcat d’Antioche depuis la paix de l’ églisejusqu’àlaconquêtearabe, Paris: Hachette Livre-Bnf, 2013, pp.256-258; Gregentiiepiscopi Tephransis disputatio cum Herbano Judaeo, vol. 86, in Jacques-Paul Migne ed., Appendix ad saeculum X complectens Auctoresincertianni et opera adespotika accedunt monumenta diplomatica, cols. 621-784; A. L. Williams, Adversos Judaeos: A Bird’s Eye View of Christian Apologiae untilthe Renaiss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5, pp.141-150.至518年,希米亚里特国王换成了犹太人的强硬派代表都·努瓦斯(DhuNuwas)。他成为拜占庭帝国征服红海地区的强劲对手。
首先,都·努瓦斯组建了一支阵容强大的国内和国际武装力量。他先是用自己强大的号召力凝聚了当地全部的犹太人。同时,凭借个人魅力,他还号召了一批同情希米亚里特、反对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徒和异教徒。他们共同构成了强大的国内武装。更重要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都·努瓦斯还与拜占庭帝国的巴勒斯坦、叙利亚犹太人及拜占庭的劲敌波斯帝国结为同盟。*John Malalas, The Chronicle of John Malalas, p. 433; John ofNikiu, The Chronicle of John of Nikiu, XC.7, p.142; Michael the Syrian, La Chronique de Michelle syrien, VIII.2, vol.1, pp.183-184; OdedIrshai, “Confronting A Christian Empire: Jewish Life and Culture in the World of Early Byzantium,” p. 60.强大的国际同盟阵容不仅有分裂拜占庭帝国的危险,更给拜占庭帝国的东部防线带来了巨大的隐患。至此,都·努瓦斯牢牢控制住了红海地区的控海权。
其次,都·努瓦斯公开挑衅和反对拜占庭帝国。他上任后颁布了一条重要法令,规定拜占庭帝国从此禁止使用“红海地区”进行贸易运输。禁运令的颁布对拜占庭来说意味着帝国的东部航线就此瘫痪,所遭受的贸易和经济损失不计其数。似乎这依然无法令都·努瓦斯感到满意。因此,他又随后大规模地囚禁了往来至此的拜占庭商人,作为他对拜占庭帝国长期不公正对待犹太人的报复。*有关具体时间的文献,请参见J. B. Bury,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I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 vol.2,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2011, p.323; Salo Baron, A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 vol.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66-67.
都·努瓦斯近似宣战的挑衅行为令查士丁尼大为恼火。为了尽快恢复贸易航线、解救人质、控制红海地区,以及对都·努瓦斯的嚣张气焰进行打击报复,查士丁尼开始了国际战场上的反犹运动。他首先从宗教层面入手,加大了对当地基督教的传播力度,逐步瓦解敌人的精神信仰。大批基督教传教士被运送到希米亚里特,当地再度掀起一股信奉基督教的狂潮。至522年,基督教徒已经收复了部分也门地区,战绩颇丰。其次,查士丁尼加大了武装攻击的力度。一支由70艘舰艇组成的海上精锐部队被派往红海地区的附近海岸随时待命;尔后,东部地区的陆军战队又被派往那里,从而构成了海陆两方面的夹击。再次,查士丁尼结合国内施行的反犹政策,有效遏制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的独立倾向,掐断了都·努瓦斯的国际支援。
拜占庭的强势反击逐渐扭转了红海地区的局面。埃塞俄比亚国王见机立刻投靠到拜占庭一边,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希米亚里特王国的基督教信众因得到拜占庭的支持,也恢复了高昂的士气。*Andrew Sharf, Byzantine Jewry: From Justinian to the Fourth Crusad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imited, 1971, p.32.更重要的是,拜占庭帝国在波斯战区的屡战略胜,成功削弱了都·努瓦斯引以为豪的强大后援。努瓦斯势力逐渐被拜占庭瓦解、分散,他在红海地区的地位岌岌可危。最终,524年都·努瓦斯逝世后,他的犹太王国再次落入已成为拜占庭盟友的埃塞俄比亚手中。至此,拜占庭帝国经过漫长的两个多世纪的等待,终于获得了红海地区的控海权。
从此,拜占庭帝国不仅打通了欧、亚、非大陆东部地区的海上贸易航线,成为整个东地中海地区的商业霸主;而且它还成功地借助红海地区作为支点,迅速控制住小亚细亚等大片东部领土,为帝国的希腊化转型铺垫好腾飞的道路。
总而言之,宗教、政治和经济三方面共同构成了查士丁尼施行反犹政策的有机整体。三者环环相扣,相辅相成。更重要的是,它们还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促进帝国的希腊化转型。从宗教层面上,查士丁尼旨在打击犹太教的强劲势力,强化基督教的国教地位,又在一定程度上为经济制裁犹太人埋下了伏笔,并且从文化、习俗、语言等方面加速了帝国向希腊化转型的进程。从政治层面上,查士丁尼镇压了不断起义的犹太教信众,清理了大竞技场的犹太人集团,以政治和军事的手段巩固了在宗教上的立法成果,为帝国带来了较为稳定的治安环境;东部地区的稳定又为希腊化转型提供了政治保障;从经济层面上,查士丁尼在国际上的反犹政策刺激了国内反犹政策的施行与推广,而对都·努瓦斯势力的打击、夺取红海地区的控海权不仅为帝国带来巨额的商贸利润,更为帝国向东部地区的扩展做好了物质准备,是帝国在东部地区推行宗教和政治上反犹政策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查士丁尼的反犹政策并非类似于20世纪希特勒纳粹政府执行的反犹恐怖主义。尽管犹太人被查士丁尼驱逐出各大政府机构,并在宗教和社会生活方面受到多重限制,但他们并没有遭受到大规模的屠杀。甚至,将《查士丁尼法典》中的反犹政策完全付诸实践的情况也是屈指可数的。正是上述特点致使一些学者将此看作是查士丁尼对犹太人的温柔举措,是一种保护政策。但此观察流于表面化,忽略了查士丁尼反犹的本质原因。宗教、政治和经济上的三重原因,令笃信基督教的查士丁尼势必对犹太人做出毁灭性的打击。只是,这些改变需要时间来显现。查士丁尼的反犹政策仿佛一颗种子,在拜占庭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为其后相当长时间里拜占庭对犹太人的暴力打击埋下伏笔。以《查士丁尼法典》为标志,查士丁尼将拜占庭的反犹活动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责任编辑:冯 雅)
2016-08-22
刘宇方(1988-),女,内蒙古赤峰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A
1674-6201(2016)04-0016-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