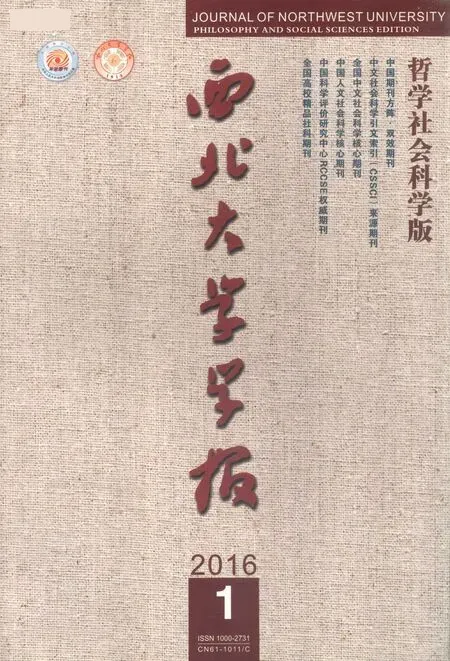乡村传统伦理与阶级意识的博弈
——论柳青的中篇小说《狠透铁》
仵 埂
(1.西安音乐学院,艺术学研究室,陕西 西安 710061;2.中国文艺评论(西北大学)基地,陕西 西安 710069)
乡村传统伦理与阶级意识的博弈
——论柳青的中篇小说《狠透铁》
仵埂1,2
(1.西安音乐学院,艺术学研究室,陕西 西安710061;2.中国文艺评论(西北大学)基地,陕西 西安710069)
柳青的《狠透铁》,写出了初级社向高级社转变中,新社会形态与传统乡村伦理之间的不融合性。描写了以王以信为代表的上中农与以“狠透铁”为代表的底层贫民的对抗。儒家的社会秩序安排,以一种变异的方式,改变和融合新制度,并将自己的伦理秩序原则,注入这一新事物之中,构成一种潜在而深刻的隐形影响,艰难地弥合着乡村因阶级划分而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强烈对峙和分裂。曾被批为“小农意识”的乡村传统,对抗国家主义的改造;宗族亲缘的私相关怀对抗大集体的“一大二公”;仁和亲善的乡绅意识,弥合阶级对抗而构成的裂痕鸿沟。小说里,柳青写出了狠透铁因自身能力导致的权力丧失,也不得不写出王以信最终的失败,表现出“形势一片大好”,并且对故事的发展作了乐观性处理和理想化展望。但在现实生活层面,乡村社会的儒家传统伦理常常是隐形的胜利者,这一历史意识的复杂融合与变形,还很少被人重视和研究。柳青的敏感在于,他无法忽略乡村中实际存在的传统构成的乡村伦理秩序和乡村社会权威。这种伦理事实影响着乡村社会生活的构建。刚刚翻身的穷人,难以胜任其在公众生活和事务中担当的责任,难以从容地站在社会舞台上,形成令人敬重的当然权威。这些地方,恰恰是柳青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深刻之处。
传统伦理;阶级意识;柳青;《狠透铁》
柳青无愧于一个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当我强调这一点时,意在表达现实主义作家身上那些受人尊重的特质,这就是当他观察体验到现实与自己原先的政治理念不一致时,他不会断然排斥现实,让现实为理念让道,他会认真对待这些与自己理念构成尖锐冲突的生活事实,尊重鲜活的生活,会在作品里呈现出这种现实的样态,甚或不惜与自己原有的政治理念主张冲突。真正尊重现实的作家,虽然受制于一定历史时期政治文化氛围的统辖和制约,但是他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尊重自己的内心直觉,会直面自我观察体验到的现实,尽管这一现实常常会与观念的要求相抵牾。他的笔下,却总会无意有意地流露出现实生活中的“暗面”,而绝不无视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事相,从而闭目塞听,写出完全意识形态统摄下的对生活诠释的文字。尽管大的时代政治背景,具有强大的规约性和强制力,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总能折射出这个时代的丰富信息。固然,严酷的规约使其作品无不打上那个时代的标准化烙印,但是,正因为他面对生活本身的勇气,抵御了简单图解生活的倾向,拒绝了将小说等同于口号和宣传,捍卫了小说艺术的尊严。所以,他的作品即使放在大的历史时空下,以大历史尺度衡量,依然价值丰盈。柳青的作品正是如此,半个世纪之后,我们还是能从其作品里见出历史的特异风貌,见出有温度的人物和令后人唏嘘的故事。
一
柳青虔诚地面向生活的姿态,以十四年的岁月,留下了他躬行实践的深深足迹。为了创作而有意去过另一种生活,这一点大约在中外文学史上所少见,所以也就更为希贵。1952年9月,柳青就搬到了长安县,一住十四年,直到“文革”开始。
柳青全程亲历了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动。1950年代,中国可谓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这个时代,几千年的社会格局被打破,富有者被夺取土地、牲畜和财物,贫穷者从底层翻身上位,成为乡村的领导者。这样的时代,中国几千年未曾有过。即使在王朝更替、政权易手的动荡年月,战争是所有灾难的直接原因,这些灾难也仅仅是权力变换酿就,等到新王朝建立,社会结构又循环如初,原有秩序恢复如常,上个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原封保留,真应了那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文化自信。但是,在1950年代,这个“道”却翻了个过,乡村秩序从头再造。那么,几千年儒家伦理下乡村秩序所形成的运行规则,与新的社会结构,也即是互助组、合作社之间,构成了什么样的状态?是隐伏性的对抗,还是接纳性的磨合?或者说,在看不见的生活战线上进行角力缠斗?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哪些事情?出了哪些状况?这是一个研究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能不能简单地下断语说,政权的更替就意味着一切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改变?或者说,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显然不是这样。柳青敏感地感受到传统社会与新体制之间的冲突,尽管他完全站在新体制立场上,但还是因了强大的传统力量的对抗而不安。他观察到的问题是,底层贫穷农民的代表,被推上乡村政治舞台之后,并不能一下子完全适应这一新角色,往往还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经过磨砺,才能真正获得管理乡村的能力。柳青深刻意识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强大力量,或者说,意识到了传统社会长期积淀而成的乡村文化权威的存在。地主富农作为被打倒被专政的对象,其曾经的统治地位被颠覆,而被置于社会权力的控制和打压之下,但是由其所代表的乡村士绅文化所构成的隐性力量,却并不见得就同时退出乡村舞台。其表现形态是,尽管作为其头面人物的地主富农不能在乡村秩序的构建里起到任何直接性作用,但是中农和上中农却自然地跳上乡村舞台,很可能成为事实上乡村政权的掌控者。他们在经济上富有,政治上未臭,文化上通达,还被作为团结的对象,同时也是乡村社会民众艳羡的目标,他们自然成为构建乡村社会的一股势力。这一势力,并非外力推动而形成,而是长期以来乡村文化传统威权自然形成。柳青女儿刘可风在《柳青传》里记载了柳青的看法:一些穷苦人,“解放前他的日子过得很可怜,现在依然可怜……什么原因造成的?(柳青)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看法。”*参见刘可风《柳青传·第十章》原稿第5页、第7页、第10页,这是一部暂时还未曾出版的传记,作者为柳青的女儿。这些想法,后来在《狠透铁》和《创业史》里,都有所表现。《狠透铁》这部中篇长达四万余字,是柳青在强烈的现实刺激下写成的。现实的触发使他坐卧不安,他对乡村政权建设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但他看到的现实却是,乡村政权建设中,因为高级社的急速发展,出现了一系列令人忧虑的问题。共产党所依靠的底层穷人,无法在高级社这样的大格局中顺利行使领导权,无法很好地驾驭和领导生产队。尽管这些人品德好,拥护共产党,热爱新社会,但在新的急剧变革中,还无法适应这种变化,无法从领导十几户的初级社状态里,一下子就过渡到驾驭七八十户组成的高级社合作社,因而呈现出困窘的局面。“共产党所依靠的贫下中农,他们的管理能力没有经过锻炼,没有提高到适应管理这么多人,这么大社的水平。他们都是穷人,一般没有文化,而一些上中农,大多殷实富有,也有经营能力。”正是这样一批中农、上中农,成为大社里呼风唤雨的人。柳青通过小说,要回答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他曾经对周围亲近的人说:“这篇小说是我对高级社一哄而起的控诉。”*参见刘可风《柳青传·第十章》原稿第5页、第7页、第10页,这是一部暂时还未曾出版的传记,作者为柳青的女儿。
二
《狠透铁》写一个叫水渠村的生产队,队长叫“狠透铁”,这是村里人送给他的绰号。他干活的狠劲令人咂舌,“要是拿起铁锨和头,唾两唾手干起活来,水渠村没有一个小伙子比得过他”[1](P179)。狠透铁是穷苦人出身,从小熬长工。1949年一解放,第一个和地方工作组接头,开始组织起农会,当农会小组长;后来当人民代表,1954年春天,以他为首,成立起十一户的初级合作社。但是,当1955年成立高级社后,这个十一户穷人社,呼啦啦一下子涌进来五十多户,这样大的摊子,狠透铁“自己吃了许多苦头”,“却给人民办不好事情”,“他羡慕那些头脑聪明的人,羡慕拿起报纸念出声音的人,羡慕在大社开会的时候,虽然困难却也低头在本本上写着什么的人。他恨自己脑筋迟钝,没有能耐。”[1](P179)大社工作头绪多,他常常忙得丢东拉西,狠劲用拳头砸自己的脑袋。就这样,还常常耽误了重要的事情,忘记了种洋芋的事情,忘记了将三包合同交给会计。最要命的是,队上的红马得病,他拿着药方去买药,结果回到家被老伴咄呐抱怨,“愣吵愣吵”,竟“被老伴咄呐的脑筋错乱了,腰里装着红马的药方子,脑筋里只知道‘有事’,到底有啥事,开始模糊起来了”[1](P182)。后来被老伴拉上去了大女儿家看望外孙满月,把红马买药的事完全忘掉了。等到第二日回来,红马死了。他好像被谁“当头抡了一棒,栽倒地下。他呜呜咽咽的哭了,哭声凄惨”。因这个事件,狠透铁不能再担任生产队长了。副队长王以信升任了队长。王以信的户族叔叔王学礼,担任了副队长。
这是小说故事的开端背景。王以信是一个上中农,但却是有个能耐的人,在村里很有势力,许多人乐意听他的,狠透铁也担心整不赢他。在狠透铁当队长的时候,他是副队长。他看见狠透铁丢东拉西,从不提醒。狠透铁有难以抉择的事情,征求他的意见,他从来总是一句话:你是队长,你看么。等他当了队长,“几乎一下子变了另一个人,起早贪黑地奔波,饲养上、副业上、保管上,样样项项理料得井井有绪”[1](P186),赢得了一片赞誉。他很会俘获人心,一切都在为水渠村人的利益考虑,他最得民心的是,常常为了水渠村的利益考虑,“尽嗓门愣吵愣吵”,他企图瞒产,提高水渠村的劳动日报酬,他知道群众最在意的是自己锅里饭的稀稠,他“把群众落后的因素当做资本,尽量迷惑、利用农民的自私、本位、不顾大局的一面。他到大社去,又把自己装作群众的代表”[1](P198)。这样一个人物,一时间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与狠透铁一比,大伙觉得老队长差远了,不会说话,不会为群众争利益,不会安排生产项目,不会周旋事情等等。在故事的前半部分,狠透铁处于受委屈的状态下,一心为了水渠村好,却得不到大家的同情和理解,更多是被孤立和冷漠。故事的后半部分主要是表现狠透铁作为监察委员与王以信的斗争。王以信在粮食入仓时,没有叫上监察委员,自己伙同几个队委把粮食放在了王学礼家,并且做了手脚,在王学礼的楼上堆放了大量的粮食,企图悄悄私分。这一行为,被来娃他妈发现,并且传扬了出去。当然,这一事件最终暴露,王以信被处理,狠透铁重新获得大家的信任。
柳青认为,像狠透铁这样的贫农,他眼下的能力也只是管理初级社十余户人家,再大就超出了他的能量范围。若要管理一个五十来户的大社,非得经历一段时间的磨练不可。但现实的发展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铺天盖地而来的大跃进浪潮,一下子将他推到了大社的舞台上。于是,狠透铁不适应了,手足无措,露了怯,下了台。这是柳青构思创作《狠透铁》的初衷。他惋惜狠透铁这样的农村基层干部,他看到的现实是,狠透铁斗不过王以信。他担心,农村的基层政权最终会被王以信这样的人所掌控。
《狠透铁》创作的时间开始于1957年,初稿写成于1958年3月,小说的题目下面有一行字:“1957年纪事”。这一年,正是高级社成立一年多时间,柳青固执地坚持保留“1957年纪事”这样一行带有说明意味的小说注释*参见刘可风《柳青传·第十章》原稿第5页、第7页、第10页,这是一部暂时还未曾出版的传记,作者为柳青的女儿。,正好反映出柳青创作的意图,表达了自己对冒进高级社的委婉含蓄的批评。小说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也有人批评柳青“对社会主义描写得有点阴暗”。到“文革”时,被批为“大毒草”,认为“将合作化道路描写得一团漆黑”。这部作品,创作于柳青正在写作《创业史》的间隙。《创业史》开笔于1954年春,1959年4月在《延河》月刊连载。能够暂时搁置柳青认为宏阔的倾注自我生命心血的《创业史》而开笔另一篇小说,实属关系重大。这就是他所忧虑的问题:在共产党的天下,农村基层中最终起主导力量的是哪种人?柳青眼里,理想者应该是“狠透铁”这样的穷苦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即使党能够一时将狠透铁扶上马,但是,若让他能长期有效地在村庄行使权力,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他们本身的文化素养和个人能力的局限,不能一下子解决,而政权会被王以信这样的上中农所掌控。而我们的政策却不能给狠透铁一个从容历练的时间机会。一下子从初级社跳到高级社,几年时间瞬时完成,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没有给农村干部留下成长发展和锻炼的机会。当狠透铁不能胜任一个五十多户人的管理职能时,权力就自然地落到了在村庄中具有传统文化权威的上中农王以信身上。
三
狠透铁是共产党在水渠村依靠的对象,他忠诚、踏实、勤勉、顽强,为了大伙儿的事情,操心操劳,鞠躬尽瘁。但是,他没文化,少条理,缺能耐,他也曾对自己有过仔细的盘算:先领导着十几户穷兄弟们干,慢慢发展壮大,自己的能力也就慢慢锻炼出来了。王以信那样的富裕中农,他预备放到最后再说。这人说话做事都很强势,他一入社,一部分上中农就会以他为中心,扭成一颗疙瘩,和他为难。但形势完全打破了他的设想,却让王以信得了手。这些问题,也被真正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柳青所抓住所感到。甚或觉得,贫下中农在农村实际拥有权力也颇艰难,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就难在贫下中农身上的传统文化承载极其薄弱,尽管新政权赋予其主宰乡村生活的权力,但是,传统的乡村秩序,不仅体现在上中农身上,也体现在他们身上,他们必须学会依照传统伦理行事,才能获得乡村社会的认可。而仅仅依靠权力弹压是不够的。小说里的一个关键情节,是来娃他妈的逆转,因为她是发现王以信偷偷藏粮的亲历者,但是来娃他妈却受制于这个“逆鬼”儿子来娃,来娃是个蛮性子人,因为共产党的新婚姻法使他的媳妇退了婚,于是与共产党结了仇,也就不大喜欢狠透铁而亲近王以信。来娃妈把自己看见的秘密传播开来,得罪王以信,让他愤怒,他用暴力让他妈闭了嘴。来娃妈反水,一口咬定自己那天什么都没有看到。怎样打开来娃妈的嘴,关键是怎样扭转来娃对狠透铁的看法。狠透铁想不出什么好主意,还是乡党委高书记为他出招,让他给来娃介绍外村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来娃一下子发生变化,王以信的计谋被来娃妈揭穿,整个事件水落石出。我要说的是,乡村社会的运行,不是狠透铁成了监察委员,于是一切人理所当然地配合你的工作,而是你须得有大家乐意配合你的德行意愿才行,这些乡村社会的人文生态,构成一种力量,推动着事物的运行。狠透铁不是依靠自己的权威,而是依靠族亲伦理,设身处地为乡亲来娃谋划个人的福祉,才能逐渐在整个水渠村站住脚。这一点,狠透铁想不到,他是通过高书记的点化,但王以信却能想到,他开始就能拉住来娃,失去来娃后,他为自己的大意十分后悔。他身上自然承载着乡村社会运行的秘密。尽管小说里不得不把他赶下台,把他定为漏化富农,但是在现实里,他往往是一个在新制度下变形了的成功者,王以信如此,郭振山(《创业史》人物)亦如是。这是儒家传统思想在乡村社会的隐形存在和抗争。
传统秩序有着强大的再生能力,暗暗地抵御着这种破坏,同时,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在修复被破坏了基本伦理。所以,乡村社会在运行中,始终昭彰一种不变的原则,这就是血缘亲情下的“仁和”精神。无非是这种原则隐伏在生活的深处,暗流涌动,推动着事物的走向。比如,基本伦理所要昭彰的是做人做事之法,为人处世之道,它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传递承载。传统文化以韧性的力量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毛细血管里,与阶级意识对抗着。在《狠透铁》里,王以信以和善仁义的面目出现,与村民和平相处,与新制度的阶级划分形成对峙。而狠透铁呢,村民对他的污名化称呼是“搜事”,就是给人找碴。在村民的眼里,狠透铁总是想把哪个人整一下,实际上,狠透铁的“搜事”,就是在1950年代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打头阵,找出对立阶级的破绽,从而为运动树立起对立面和靶子。这是当时特定氛围里群众对狠透铁的一种看法。这样一种人,在乡村社会极为普遍。
王以信与狠透铁展开的另一对抗是,到底以村民的利益为大还是以国家的利益为大?王以信常常会站在村民的利益上,对抗国家的粮食征收政策,这也是他最能号召群众的法宝。他更多的是从宗亲本位出发。而狠透铁更多的是站在国家的利益高度,赞成小利益服从大原则,牺牲村社利益服从国家要求。所以,在王以信藏起粮食为私分而暴露时,却找出一个极为正当且能赢得群众理解的理由,这就是我将好的粮食藏起来,为群众私分,而给交公粮的部分,掺杂了“出芽麦子”。小说提供的细节是王以信藏起部分粮食,是为了个人的私利企图私分,当然失去了哪怕是最落后群众的道义信任,假如他藏起粮食的确是为了群众私分好麦子,这样的矛盾将是一个难题,狠透铁又该如何应对?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在农业社极为普遍。老家所在的生产队,当年一个队长为群众私分粮食而被批斗,他被批斗了,但是救了一村子人,度过了最艰难的三年困难时期。乡村伦理原则对抗国家意识形态,血缘亲情并没有因阶级划分而完全失去效力。
数千年之传统秩序规范,被阶级属性划分下的等差关系替代,历史上占有统治地位的乡村士绅被打翻,接受原来处于下位的穷棒子们的指使。在这样的态势下,镇反的高压、工商业改造、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等等运动,处于社会下层的乡村,在这疾风暴雨般的运动中,传统乡村文化惯性和乡村社会秩序,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运行体系,即从私有化过渡到公有化形态这一天地翻覆,传统怎样在转型中艰难地抵御、弥合和再生?我想从柳青在《狠透铁》中的忧思里,反向探索这一问题。
四
柳青无疑是一个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作家,但同时又是一个对党在一定时期政策持有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他出生在陕北吴堡县寺沟村,在他出生之际,伴随着一次匪患,在土匪的暴力抢劫中,三岁的小哥哥被打死,大哥二哥被打伤,父亲刘仲喜跳墙逃跑摔折了腰。几天之后,母亲生下他,此时是1916年农历六月初三。在这样的处境中,他差点被遗弃,后又差点被送人。父亲原先苦心经营挣得一点钱,投到商人薛敬修的字号里,没想到被骗了个净光,伤愈后告官又输了官司。县衙让父亲跪着,让被告坐着,因为被告考取过功名,是读书人。这个刺激父亲终身不忘,从此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儿子读书。父亲后来认准两件事:修水地,栽树。领着儿子们搬石头、修水槽、栽枣树,过了数年,父亲又发家了,不仅供老大上学,还买进了一些土地。大哥刘绍华后来考上北京大学,成为吴堡县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柳青原名刘蕴华,也被送去上学,他后来深受大哥刘绍华的影响。1927年大革命之后,因国共合作破裂,刘绍华避难逃回陕北,1928年带着刘蕴华来到米脂县城,把他领上革命之路。后来柳青又上了具有强烈进步色彩的绥德师范,深受革命熏染。大哥到西安高中任教,1934年又让他到西安看病并继续读书。大哥对小弟柳青有着美好的设想,自己独身节俭,攒下三千元给他,希望他读好英语和数理化,然后到西洋留学,做一名学者。但此时柳青已经有了自己成熟的想法,热衷于阅读革命书籍和小说,并且于193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不愿接受大哥为自己安排的前途,开始与大哥发生矛盾,令大哥非常伤心。柳青最终毅然走向革命道路,编刊物,走延安,去敌后根据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从抗日战争走到解放战争,成为一个成熟而又忠诚的党的作家。从柳青的生平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热忱追求进步、投身革命事业的鲜明形象*这部分关于柳青生平的论述,引自柳青女儿刘可风的《柳青传》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正因为如此,柳青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抱有发自内心的热情。他认为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假如自己身处局外,没有亲历,将会一生遗憾。于是,1952年他到长安县体验生活,践行他的人生理想和实现他以创作来表达这场变革的梦想,一蹲十四年。这一时期,他充满激情,全身心投入互助组和初级社运动。他在参与整个农村变革的同时,也警惕自身陷入生活本身,而失去一个观察者的视点,因之,与乡村生活保持着一定距离。他始终以一个观察者的眼光,感受农村这一时期发生的林林总总的事变。他以一个共产党人的忠诚和热望,记录乡村社会变革的进程,对乡村社会存在的问题,进行思索和研究。他不仅是一个作家,还成了一个乡村问题的研究者。1961年,柳青因为几年来牲畜的大量死亡,特意撰写了《牲畜饲养管理三字经》,通俗易懂,好学好记,深受群众欢迎。在《陕西日报》发表后,被上海一家出版社印成小册子推向全国。 这期间, 他正在写作《创业史》, 一个大作家,腾出时间写这样的“三字经”, 可见其对农村生活倾注的深情。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 柳青在《狠透铁》中, 表现出“形势一片大好”下的暗影, 同时又对此作了乐观性处理和理想化回答。 正因为柳青在农村长大, 原有的生活背景和深入长安农村的经验,使他敏感的神经无法忽略农村权力运作中的深层的问题, 无法忽略农村中实际存在的传统文化构成的乡村伦理秩序。 这种伦理以隐性方式,影响着乡村社会生活的构建。 作家尖锐的问题意识构成了他的忧思。 刚刚翻身的穷苦人, 难以胜任其在公众生活和事务中担当的责任,难以从容地站在社会舞台上, 形成令人敬重的当然权威。 他们缺少文化, 缺乏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甚至在播种收割的经验运筹中, 也缺乏让人服膺的统筹能力。 要让公众从心底接纳这样的领导者, 还有待一个长长的过程。
中国的乡村是以儒家的立身处事之道构成的宗法社会威权,这个威权的根底就是依照乡约规矩修身之道修炼成的正直人格:尊老爱幼,谦逊和善,友爱相邻,救危扶困等等,这些要素里,蕴含了儒家的基本思想。他们在乡村社会生长了几千年,成为乡村人际关系的标尺,以此衡量一个人的高低短长,是值得信赖的人,还是让人鄙弃的怀疑的人。新的社会结构,打破了原有的生产单元,将一家一户生产变为整个村庄生产核算,人和人的关系也发生剧烈变动,血缘亲情的家族制度,变为“亲不亲,阶级分”的新共产伦理。这种新社会伦理,按其理论的彻底性而言,的确是应该全村人一个食堂吃饭的,因为生产方式是全村人一起耕作,一起过日子。但是人民公社食堂化失败后,其分裂形态是村子里生产活动在一起,但却保留了旧有的生活方式,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形态。“家”却不得不存在了。家的存在,构成新社会伦理的最后障碍,以彻底性而言,只有彻底消除了这种以家为单位的生活形态,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以家依托的意识形态。所以,当初级合作社建立的时候,它更多具有互助性质,还没有完全打破这种以家为核算单位的耕作分配生活模式。当家本身存在的时候,以家作为考量和运行的生活单位,自然会演化出代表这种形态的劳作方式与文化形态,这种亲情血缘的纽带,实际上成为乡村社会运行的深层秘密。故在表层上的社会主义权力运作,其下涌动的却是以家为本的宗法社会体位。
有意味的是,在大跃进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度曾经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还差点跃进到以大队、公社为核算单位,就是说,在一个大公社内进行统一劳动核算,这样,就从根本上打破了宗法单位的残留。因为在事实上,所谓的队为单位,是以自然村落而划分,而自然村落的形成,多是一个或数个大姓构成,宗法社会还在暗处起作用。将多个生产队合为一个核算单位,两种力量一直在较量。很多时候,国家权力所推动的“一大二公”设想,遭到普遍的抵抗。大社若形成,当然会瓦解宗法社会的根基,但是形成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人会真正关心生产,没有人会真正为百姓操心,因为劳动的果实分配权远离自己的掌控,自己也决定不了劳动付出和分配之间关系。因之,铺张浪费、消极怠工、效率低下迅速蔓延,危机也相伴产生。这种危机,足以影响整个运动的成果,或者说,足以使公社化道路崩塌,这才使这种跃进戛然而止。
五
在水渠村,高级社运行之后,传统乡村秩序是否存续?本文以《狠透铁》作为分析样本,提出的问题是,水渠村这样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村庄,实行以阶级区分作为统治手段之后,以儒家思想作为核心的原有乡间秩序,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呈现在农业合作化的村庄里,它对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是消解是对抗、还是融合或转化?柳青的创作中,或隐或现都涉及这一问题,特别是在中篇小说《狠透铁》里,这一意识更为明晰而尖锐。本文认为,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柳青从现实生活出发,敏锐地感到了这一对抗,感到了新的社会形态与原有乡村秩序之间的不融合性,感到了以上中农为代表的这个群体,实际上承继着原有的文化传统,在一定时期,他成了事实上的乡村政权的主宰者,也即是说,儒家的社会秩序安排,在暗暗地以一种变身的方式,改造和融合新的变迁,并将自己的秩序原则注入这一新事物之中,构成一种潜在的深刻的隐形影响。乡村社会以家作为基本生活单元,合作社以宗族为主的自然村落作为基本生产单位,这些根基没有动摇时,儒家的文化思想事实在起着作用,艰难地弥合着乡村因阶级划分而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强烈对峙和分裂。这种曾被批为“小农意识”的乡村传统文化,在对抗国家主义的改造;这种对本族亲缘的私相关怀对抗大集体的“一大二公”;这种仁和亲善的乡绅意识,弥合因倡导阶级对立而构成裂痕鸿沟。在小说里,王以信顺利跳上水渠村舞台,实则是水渠村的文化传统在起作用,尽管柳青不得不写出他的失败,但同时我们看到的是,王以信是在公社党委书记的直接干预下而失败,在现实生活里,王以信却是胜利者,或者说是儒家乡村社会传统的隐形胜利,这一历史意识的复杂融合与变形,还很少被人重视和研究。
[1] 柳青.狠透铁[M]∥柳青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赵琴]
I206.7
A
10.16152/j.cnki.xdxbsk.2016-01-008
仵埂,男,陕西富平人,西安音乐学院教授,中国文艺评论(西北大学)基地研究员,从事文学研究与艺术批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