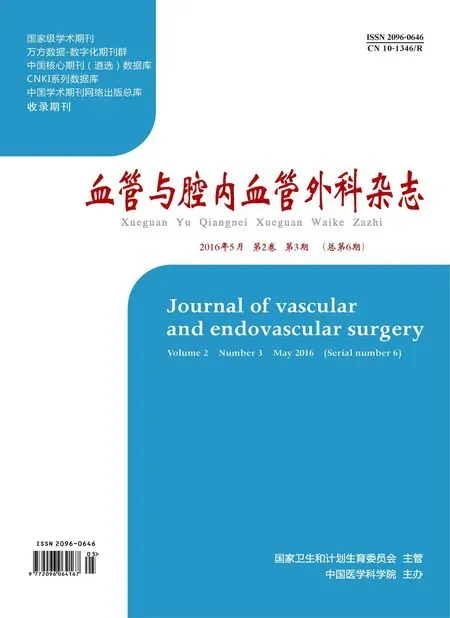介入技术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的进展
钱宇轩 杨 涛 郝 斌山西医科大学,太原 030001
介入技术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的进展
钱宇轩 杨 涛 郝 斌*
山西医科大学,太原 030001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nous thrombosis, DVT)是目前临床住院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抗凝作为其最主要的治疗方式,被大家广为接受。然而,一部分DVT患者在接受单纯抗凝治疗后,仍然形成了严重的血栓后综合征,表现为下肢的色素沉着、肿胀、酸痛、静脉性湿疹以及溃疡的形成,且多见于髂股静脉血栓患者,因此对于髂股静脉血栓要尽早清除。手术取栓及目前新兴的各种介入技术都是清除静脉内血栓的有效方法,现就通过介入技术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的进展综述如下。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介入技术;治疗;进展
下肢 深 静 脉血栓形 成(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是指血液在下肢深静脉内不正常地凝结引起的疾病,血液回流受阻,进而出现一系列临床症状的血管疾病。血栓脱落可引起肺动脉栓塞(pulmonary embolism,PE),DVT在国内的发病率尚无准确的统计资料,但有逐年上升的趋势。DVT如在急性期未得到有效的治疗,血栓机化,常遗留静脉功能不全,称为血栓后综合征(postthrombosis syndrome, PTS)。
一直以来,抗凝治疗作为DVT的最基本治疗方法,被大家广为接受。有效的抗凝治疗可以抑制肺栓塞的发生、DVT的扩展以及复发。然而,越来越多资料[1-3]表明,一部分DVT患者在接受单纯抗凝治疗后,仍然形成了严重的血栓后综合征,表现为下肢的色素沉着、肿胀、酸痛、静脉性湿疹以及溃疡的形成,且多见于髂股静脉血栓患者,因此对于髂股静脉血栓要尽早清除。手术取栓及目前新兴的各种介入技术都是清除静脉内血栓的有效方法。但手术取栓相比介入技术创伤大,手术后再发率高,远期治疗效果不满意[4],故使用介入技术消除静脉内血栓尤其是髂股静脉血栓越来越受到推崇。本文通过复习山西医科大学血管外科的文献,结合实际临床工作经验,对近年来出现的通过介入技术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方法做一综述。
1 下腔静脉滤器的置入
1.1 下腔静脉滤器的概述及种类
肺栓塞是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严重并发症之一,急性大面积的肺栓塞是患者猝死的常见原因之一。下腔静脉滤器(inferior vena cava filter, IFCF)是为了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栓子脱落引起肺栓塞而设计的一种装置。经过多年的不断改良与研发,滤器已由当初的单一种类及置入方式,发展为多种款式、多种置入方式以及更高的滤过效率的滤器系统[5]。目前滤器的种类有临时性滤器、永久性滤器、可回收滤器3类。滤器的选择应根据患者的病程、年龄、血栓的大小及游离程度、下腔静脉的形态及直径来决定。年轻患者和新鲜、较短的血栓,尽量选用临时或可回收滤器,肺栓塞的危险期过后可将其取出;年老患者或预期寿命较短的患者可放置永久性滤器。
1.2 下腔静脉滤器置入的适应证及争议
目前公认的放置下腔静脉滤器的绝对适应证包括[6]:⑴ 有抗凝禁忌,包括近期出血病史、抗凝后出血史以及血小板低于50×109/L的患者;⑵ 经过积极足量的抗凝治疗后,深静脉血栓仍进行性发展;⑶ 拟行导管介入溶栓治疗;⑷ 下肢深静脉血栓或易栓症,伴有肺栓塞。近些年来,由于国内外医学界对肺栓塞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预防性使用下腔静脉滤器的情况屡见不鲜,导致与下腔静脉滤器相关的并发症的报道也日益增多[7,8]。在美国胸科医师协会(American College of Chest Physicians, ACCP)最新发布的抗血栓治疗指南[9]中指出,对于已接受抗凝治疗的DVT或PE患者,不推荐放置下腔静脉滤器(推荐等级1B)。尽管目前关于下腔静脉滤器置入的适应证仍有争论,但滤器可降低致死性肺栓塞的发生率已得到广泛认可[10-12]。因此,对于符合适应证且有严重肺栓塞发生风险的患者尽量使用临时或可回收型滤器,以降低长期置入滤器而导致的相关并发症的发生[5],且在置入滤器期间进行必要的检测与管理,并根据不同情况及目的合理选择使用滤器。
2 经导管直接溶栓
2.1 经导管直接溶栓治疗下肢DVT的优势及有效性
经导管直接溶栓(catheter directed thrombolysis,CDT)是目前临床较常用、清除血栓效果得到公认的一种治疗方法。它是利用血管腔内技术将溶栓导管插入血栓部位,通过导管侧孔直接灌注溶栓药物溶解血栓。该技术的优势在于将高浓度的溶栓药物直接与血栓接触,达到最佳的溶栓效果的同时减少了全身出血并发症的发生。1994年Semba等[13]首次报道应用该技术治疗急性髂股静脉血栓,显示了该技术对于治疗有症状的髂股静脉血栓的有效性及安全性。Vedanthan等[14]在2006年回顾性分析应用CDT技术治疗急性DVT的19个临床中心共计1046例患者的临床资料,统计结果显示出总的溶栓成功率高达88%。此外,CDT还可以降低PTS的发生率,保护静脉瓣膜,减轻肌肉泵的功能损害[15]。来自挪威的学者在2012年所做的一组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实验[16]中证实,行CDT+抗凝治疗的实验组PTS发生率(41%)明显低于行单纯抗凝治疗的对照组(55.6%)。
2.2 CDT的适应证及入路选择
鉴于CDT的有效性,它受到ACCP[17]和介入放射协会(Society of Interventional Radiology)[14]的推崇,并于2008年在其临床指南中达成共识[17],制定了应用CDT治疗DVT的适应证:急性广泛近端DVT,预期寿命≥期年,低出血风险及良好的身体状态(推荐等级2B)。2012年,中华医学会外科分会血管外科学组制定的深静脉血栓形成的诊断和治疗指南(第2版)[18]也将CDT作为急性中央型或混合型DVT的治疗首选。根据血栓的范围及部位选择CDT的治疗入路,可顺行(患侧腘静脉、大隐静脉、小隐静脉)或逆行(经颈静脉或健侧股静脉)进行置管:对于全下肢或仅累及腘静脉以远的DVT患者,可采用逆行置管;对于仅累及髂股段DVT的患者,可采用经患侧腘静脉顺行置管。溶栓药物一般采用尿激酶,剂量为40~100万U/d,置管时间一般不超过7 d,期间需反复造影观察血栓溶解情况,并注意检测血常规、凝血系列等指标[19]。
2.3 关于CDT过程中是否放置下腔静脉滤器的争议
虽然下肢深静脉血栓患者下腔静脉滤器置入的绝对指证已取得共识,但CDT过程是否常规放置下腔静脉滤器以预防溶栓过程中血栓脱落导致的肺栓塞目前仍有争议:李晓强等[20]认为下肢DVT行CDT治疗时可考虑行下腔静脉滤器置入,因为下腔静脉滤器虽不能有助于血栓的清除,但在CDT过程中,血栓的崩解、导管和导丝的机械性刺激、高压造影时血管内压力梯度改变均可诱发血栓脱落而发生致死性肺栓塞;而Protack等[21]随访了1996—2006年间行CDT治疗的69例患者,其中14例在行CDT前预置了下腔静脉滤器,随访结果发现所有进行CDT治疗的患者均未发现肺栓塞,他们认为不常规置入下腔静脉滤器是安全有效的。因此,CDT治疗时滤器的置入指证有待于循证医学证据的支持。
2.4 关于CDT的展望
在ACCP最新发布的抗血栓治疗指南[9]中指出,对于罹患急性腿部近端DVT的患者,抗凝治疗的优先度高于导管直接溶栓(推荐等级2C)。抗凝作为DVT治疗的最基础治疗方式,其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对于急性期髂股段血栓单纯抗凝显得过于被动与保守,现有众多临床研究已显示出使用CDT早期溶栓在对于去除血栓、防止PTS发生以及保护静脉瓣膜功能的作用上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3 经皮人工抽血栓清除术
3.1 经皮人工抽血栓清除术的概述及入路选择
经皮人工抽血栓清除术(manual aspiration thrombectomy,MAT)是指利用大腔导管鞘插入深静脉血栓处,外接大容量注射器反复负压抽吸血栓,以达到去除血管腔内血栓的目的。该技术最初主要用于医源性血栓形成的治疗,因是一种简单而又实用的技术,以后得到迅速推广。MAT有多种入路途径,虽各有特点,但也有其局限性:经腘静脉入路[22]顺行抽吸髂股静脉内血栓,虽已取得明显效果,但对于高龄或肥胖患者难以耐受长久的俯卧位;经颈内静脉入路[23]逆行抽吸血栓,抽吸长鞘收回过程中因穿越右心房,路径长,需严格保持负压以防未完全吸入鞘管内的血栓脱落而致肺栓塞,且多次抽吸长鞘均需通过滤器间隙,操作复杂,尤其股腘静脉内血栓,因受路径较长而影响吸栓效果。
3.2 采用MAT治疗下肢DVT的新方案
有文献报道[24],对于累及腘静脉以上的DVT患者,可在下腔静脉滤器保护下,使用8~10 mm的球囊将血栓顺行拖拉至同侧髂静脉处,再采用大腔导管进行抽吸。此方法可以尽可能地将主干内的血栓清除干净,并能够在快速消除肢体肿胀的同时,保护瓣膜的功能,避免了术后发生下肢深静脉瓣膜关闭不全。
3.3 应用MAT的注意事项
MAT最主要的缺点是有一定的失血量、负压过大容易造成血管内膜损伤,因此操作过程中应注意保持恒定负压并严格控制失血量,每次不应超过200 ml[19]。
4 经皮机械性血栓清除术
4.1 经皮机械性血栓清除术的概述及种类
经皮机械性血栓清除术(percutaneous mechanical thrombectomy,PMT)是指利用穿刺技术将特殊的导管装置送入血管腔内,这些特殊的导管装置可以起到消融血栓的作用。目前常用的PMT根据原理不同可分为机械旋切血栓清除装置(包括Amplatz血栓消融器、PTD血栓消除装置、Straub Rotarex血栓旋切器等)、流体动力血栓清除装置(包括Angiojet、Hydrolyser、Oasis导管等)、超声消融装置(包括Acolysis系统等)。
4.2 PMT的有效性及优缺点
研究指出[25],单纯利用PMT消除血栓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采用有侧孔的PMT导管装置,通过侧孔局部喷洒尿激酶等溶栓药物,可大大提高消栓效果。Dietzek 等[26]利用PMT装置联合CDT治疗2024例急性期DVT患者,血栓清除率高达95.5%,说明PMT联合CDT治疗急性期DVT的效果亦明显。因此,PMT在治疗急性期下肢DVT中显示出了独特的效果。但PMT在使用中会导致机械故障、失血、溶血等情况的出现需引起术者的注意,且这些装置大都费用昂贵,在国内广大的基层医院使用受限,很难得到推广。目前,关于使用PMT治疗DVT的复发率情况尚无报道,远期治疗效果也有待进一步观察。
5 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angioplasity, PTA)及支架置入术
5.1 采用PTA及支架置入治疗下肢DVT的必要性
髂静脉压迫综合征(也被称为May-Thurner或Cockett综合征),是指在盆腔内的髂静脉受到临近组织压迫,使管腔狭窄或闭塞,造成静脉回流受阻,并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临床症状[27]。近年来,髂静脉病变是导致下肢DVT形成的一个重要诱因的观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多项研究表明[20,28,29],DVT患者中的71.7%~100%存在髂静脉病变的情况,当髂静脉狭窄超过正常直径的50%时,血栓的发生率将增加2倍以上。李小强、王深明等专家[20]不仅肯定了髂静脉狭窄在下肢DVT发病中的重要作用,更进一步指出通过CDT、MAT或PMT后同时矫正髂静脉狭窄或闭塞可以提高通畅率,改善治疗效果,减少PTS发生,推荐成功实施血栓清除后,如髂静脉狭窄大于50%首选球囊扩张和(或)支架置入,必要时行外科手术解除髂静脉阻塞。
5.2 PTA及支架置入治疗下肢DVT的临床应用
结合山西医科大学血管外科中心临床经验,在急性下肢DVT经导管溶栓或机械血栓清除后,如造影发现仍有严重狭窄或存在髂静脉卡压的情况,根据狭窄或卡压的长度及部位选择合适的球囊进行扩张,如反复扩张后局部仍有明显狭窄时可置入合适直径及长度的支架。有学者亦通过研究[30]发现,若对受压变窄或闭塞的髂静脉仅行球囊扩张而未行支架置入术,下肢DVT的复发率将高达73%,建议凡是由受压导致的髂静脉狭窄或闭塞,引起下肢DVT、下肢肿胀等临床症状的患者,均行支架置入术。顾建平、何旭等[19]推荐使用12~14 mm自膨式支架,病变段应完全覆盖,当髂总静脉汇合处受病变累及时,支架近心端宜深入下腔静脉0.5~1.0 cm,髂静脉支架置入后规律口服抗凝剂至少6个月,如选用华法林作为抗凝治疗药物,国际化标准比值(INR)应控制在2.0~3.0之间。放置支架应尽量避免跨越腹股沟韧带,虽目前没有在这一部位放置支架会导致移位、断裂的报道,但跨越腹股沟放置支架是导致支架内再狭窄的危险因素之一[31]。
5.3 支架置入治疗下肢DVT的有效性及并发症
Kwak等[32]报道自腘静脉置管溶栓治疗22例下肢DVT患者,放置27枚髂静脉支架,1期通畅率95%,2期通畅率100%,近中期临床效果良好。支架置入的主要并发症为血管破裂、支架断裂、支架移位以及支架内再狭窄,支架内再狭窄可通过再次行介入治疗来开通,其余并发症的目前报道较少。关于支架远期通畅率的情况有待进一步观察。急性下肢DVT是临床常见的深静脉疾病之一,治疗的理想目标应是预防肺栓塞的发生、消除深静脉梗阻及保护瓣膜功能。近来新兴的各种介入技术在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上取得了不错的进展,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随着科技的进步,还会有大量的新介入技术引入临床治疗过程当中。然而,任何一种介入技术都有其优缺点,应该在充分掌握各种介入技术的基础上扬长避短,采用多种介入技术联合应用,针对患者采取个体化治疗方案,以求为患者带来最好的收益。
[1]Hye R J, Turner C, Valji K, et al. Is thrombolysis of occluded popliteal and tibial bypass grafts worthwhile? J Vasc Surg,1994, 20: 588-597.
[2]顾建平, 楼文胜, 何旭, 等. 髂静脉受压综合征及继发血栓形成的介入治疗. 中华放射学杂志, 2008, 42: 821-825.
[3]杨冬山, 李学锋, 刘汝海, 等. 下肢深静脉血栓取栓术后复发与Cockett综合征的关系. 中国普通外科杂志,2007, 16: 539-541.
[4]卢辉俊, 刘辉, 原野, 等. 外周途径置管溶栓治疗左髂静脉压迫并急性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分析. 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2015: 605-609.
[5]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介入学组. 下腔静脉滤器置入术和取出术规范的专家知识. 介入放射学杂志, 2011, 20: 340-344.
[6]郭伟, 赵渝. 腔静脉滤器的临床研究进展. 保健医学研究与实践, 2014, 11: 84-87.
[7]Millward SF, Grassi CJ, Kinney TB, et al. Reporting standards for inferior vena caval filter placement and patient follow-up: supplement for temporary and retrievable/ optional filters. J Vasc Interv Radiol, 2005, 16: 441-443.
[8]曹满瑞, 窦永充, 胡国栋, 等. 腔静脉滤器预防肺动脉栓塞的长期追踪. 中华放射学杂志, 2001,35(11): 42-45.
[9]Kearon C, Akl EA, Ornelas J, et al. Antithrombotic therapy for VTE disease: CHEST guideline and expert panel report. Chest, 2016, 149: 315-352.
[10]Onat L, Ganiyusufoglu AK, Mutlu A, et al. OptEase and TrapEase vena cava filters: a single-center experience in 258 patients. Cardiovasc Intervent Radiol, 2009, 32: 992-997.
[11]顾建平, 范春瑛, 何旭, 等. 常见下腔静脉滤过器的临床应用. 临床放射学杂志, 2002, 21: 456-460.
[12]徐克, 周玉斌, 王爱林, 等. 国产ZQL型可回收式腔静脉滤器的初步临床应用与观察. 中华放射学杂志, 2003,37: 228-231.
[13]Semba CP, Dake MD. Iliofemoral deep venous thrombosis: aggressive therapy with catheter-directed thrombolysis. Radiology, 1994, 191: 487-494.
[14]Vedantham S, Thorpe PE, Cardella JF, et al. Quality improvement guidelines for the treatment of lower extremity deep vein thrombosis with use of endovascular thrombus removal. J Vasc Interv Radiol, 2006, 17: 435-448.
[15]Baekgaard N, Broholm R, Just S, et al. Long-term results using catheter-directed thrombolysis in 103 lower limbs with acute iliofemoral venous thrombosis. Eur J Vasc Endovasc Surg, 2010, 39: 112-117.
[16]Enden T, Haig Y, Klow NE, et al. Long-term outcome after additional catheter-directed thrombolysis versus standard treatment for acute iliofemoral deep vein thrombosis (the CaVenT study):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Lancet, 2012,379: 31-38.
[17]Kearon C, Kahn SR, Agnelli G, et al. Antithrombotic therapy for venous thromboembolic disease: American College of Chest Physicians Evidence-Based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8th Edition). Chest, 2008, 133 (6 Suppl): 454S-545S.
[18]李晓强, 王深明. 深静脉血栓形成的诊断和治疗指南(第二版). 中华普通外科杂志, 2012, 27: 605-607.
[19]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介入学组.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介入治疗规范的专家共识. 中华放射学杂志, 2011, 45: 293-296.
[20]李晓强, 于小滨. 导管接触性溶栓在急性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治疗中的相关问题再探讨. 中国血管外科杂志(电子版), 2014(1): 9-11.
[21]Protack CD, Bakken AM, Patel N, et al. Long-term outcomes of catheter directed thrombolysis for lower extremity deep venous thrombosis without prophylactic inferior vena cava filter placement. J Vasc Surg, 2007, 45: 992-997.
[22]Oguzkurt L, Ozkan U, Gulcan O, et al. Endovascular treatment of acute and subacute iliofemoral deep venous thrombosis by using manual aspiration thrombectomy: longterm results of 139 patients in a single center. Diagn Interv Radiol, 2012, 18: 410-416.
[23]徐克, 冯博, 苏洪英, 等. 经颈静脉髂-股静脉血栓清除术的临床应用. 中华放射学杂志, 2001, 35: 768-771.
[24]潘晶晶. 急性下肢深静脉血栓的腔内治疗现状及进展.医学综述, 2013, 19: 3726-3728.
[25]Vedantham S, Vesely TM, Parti N, et al. Lower extremity venous thrombolysis with adjunctive mechanical thrombectomy. J Vasc Interv Radiol, 2002, 13: 1001-1008.
[26]Dietzek AM. Isolated pharmacomechanical thrombolysis of deep venous thrombosis utilizing a peripheral infusion system: Manuf. Int Angiol, 2010, 29: 308-316.
[27]张福先, 龙燕好. 静脉血栓栓塞症治疗的现代策略. 心肺血管病杂志, 2011, 30: 454-463.
[28]Kim JY, Choi D, Guk KY, et al. Percutaneous treatment of deep vein thrombosis in May-Thurner syndrome. Cardiovasc Intervent Radiol, 2006, 29: 571-575.
[29]黄晓钟, 梁卫, 叶猛, 等. 导管直接溶栓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介入放射学杂志, 2008,17(1): 11-14.
[30]Binkert CA, Schoch E, Stuckmann G, et al. Treatment of pelvic venous spur (May-Thurner syndrome) with selfexpanding metallic endoprostheses. Cardiovasc Intervent Radiol, 1998, 21: 22-26.
[31]Knipp BS, Ferguson E, Williams DM, et 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outcome after interventional treatment of symptomatic iliac vein compression syndrome. J Vasc Surg,2007, 46: 743-749.
[32]Kwak HS, Han YM, Lee YS, et al. Stents in common iliac vein obstruction with acute ipsilateral deep venous thrombosis: early and late results. J Vasc Interv Radiol, 2005,16: 815-822.
Interventional technology progress for the treatment of deep venous thrombosis
QIAN Yu-xuan YANG Tao HAO Bin*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1, China
deep venous thrombosis; interventional technology; treatment; progress
R658.3
A
2096-0646.2016.02.03.15
郝斌,E-mail:summervibe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