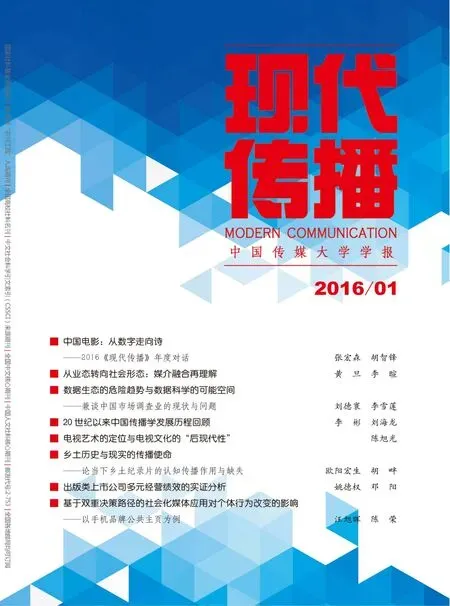权力视野中典型报道的媒介形塑及社会效能*
■ 朱清河 汪 罗
权力视野中典型报道的媒介形塑及社会效能*
■ 朱清河 汪罗
【内容摘要】 典型报道是中国大众传媒领域最富有特色的新闻话语表达方式,从历史实践经验上看,它常以做出不俗业绩的社会各行业普通人作为媒介形塑与传播主体,对先进典型所体现的高洁品行进行广示与张扬。但若将其归置于权力及其运作机制的视域中来鸟瞰,便会很容易发现媒介典型的框选、裁制与传布并非如一般人想象那样仅受传者偏爱或受众期许所制,相反,正是始终处于优势地位的权力对于媒介典型的身份选择、议题建构与评价,对公众社会记忆的统摄及对公众行为的规制,才规约着典型报道价值诉求的多彩之花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时代变迁的纵轴次第绽放。
【关键词】权力;典型报道;媒介形塑;社会功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项目编号:12BXW014)、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文化社会学视野下‘群众办报研究’:历史、实践、理念”(项目编号:NCET130888)的研究成果。
兼具“信息属性、舆论属性及宣传属性”(1)的典型报道,在本质上讲也是一种新闻,具备着新闻的一般属性,因为它要求“典型”必须真实且具有新鲜性,在价值指涉层面与新闻事实彰显的时代精神与伦理基调保持一致。典型报道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新闻话语方式,责无旁贷地担负着建构无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构性要素的职责。
现实中,公众所“直接面对的现实环境实在是太庞大、太复杂、太短暂了,我们并没有做好准备去应付如此奥妙、如此多样、有着如此频繁变化与组合的环境”(2)。媒介权力由此衍生,它通过有目的性地选取、呈现、建构议题,来重构整个社会、国家的变迁图景。在此,媒介权力似乎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不偏不倚、公正、客观。但实际上,这个过程是一个夹杂着对国家意志、价值观念体系及现实境况判断的经验性实践活动。媒介议题的“偏向性的陈述”(3)必然依附甚至是服从于国家意志、制度安排、社会期许等权力构成体系。因为“所有的表意活动——也就是所有带有意义的世间——都牵涉到权力关系”,(4)典型报道的话语形成与运作体系自然毫无疑问也被显在权力与隐在意识形态领域所规制。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媒介建构“典型”的过程从始至终都受制于权力的主使,担负着主流意识形态对公民的询唤,并最终也把自己自觉不自觉地变相演化成了一种规训人们社会言行的一种权力。
一、报道典型:权力的倾情与询唤
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典型报道文本应当具有相应的组成(叙事)要素,身份、议题、评价则是构成典型报道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在具体要素对新闻典型形象的建构过程中,权力都参与其中,如影随形。设若检视典型报道的话语形态、意义承载及价值取舍,省察权力“制造”典型及其背后的运作模式,首先我们有必要将其放置于一个历史脉络的发展沿革之中进行历时性的分析。
(一)身份:权力的倾向性意图及介入行为
典型报道中,身份要素的设定与评价绝对不可能脱离权力机构而独立存在,其合法性更是需要权力机构的首肯与认可。这是基于典型产生主体的维度来考察的,即确定典型的身份,也是确立典型的第一个环节。“制造”典型,就其本质而言,是权力机构实现其政治治理方式合法化的重要方式。在不同的历史分期,权力机构形塑、挖掘、展示诸多典型人物,并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中介作用,实现了对社会力量的整合,赢得公众的认同。于是,典型人物便承载了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权力对媒介呈现的典型积极评价与把关,在一定意义上,带有明显的倾向和目的;而在媒介具体的新闻生产中,采取了“制造”典型的实质性行为。
“使典型成为典型的乃是它身上一切人和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决定因素,都是在它们最高的发展水平上,在它们潜在的可能性彻底的暴露中,在它们那些使人和时代的顶峰和界限具体化的极端的全面表现中呈现出来。”(5)这其中,当然包括对典型身份的展现及确立。而典型报道正是在身份确立过程中设立“模范”“英雄”称号,以此组织、动员群众。
关于典型报道的内涵界定,尽管众说纷纭,但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无外乎“典型报道是对一定时期内产生的同类事物中最突出或最具代表性的事物进行的重点报道。其目的是,通过对具有典型意义的人或事的剖析,引出普遍性的经验或教训,用以指导工作,教育读者。典型报道有典型人物报道、先进集体报道、典型事件或典型经验的报道等”(6)。据此定义考量,国内最早的典型报道,当发轫于大生产运动时期的《解放日报》。“《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报道是党报新闻史上最早的典型个体人物报道,而该报对三五九旅的连续报道,则是集体典型的首篇报道。”(7)
“春耕运动期间,劳动英雄出了很多,但究竟谁种的庄稼最好,记者为明白这个问题,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亲至各地农村访问,现在已经找到了众所公认的标准劳动英雄。这位英雄姓吴,名唤满有,今年49岁,生就一个大个子,精强力壮。”(8)“二月初旬,戈壁滩上还是风雪漫天的时候,玉门油矿今年计划钻凿的生产井很多已经开始开。此外,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中,涉及“模范”及“英雄”身份的典型报道就有《张振财和模范城壕村》《难民劳动英雄陈长安》《纺织女英雄刘桂英怎样发展妇纺?》《植棉英雄郭秉仁》《六十岁劳动英雄孙万福》《双重英雄武生华》等近百篇。
透视上述典型身份的遴选过程,即可发现典型报道中作为主体的身份要素本身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受权力主导与使唤,用以教化群众向先进样板学习、模仿的精神图腾。典型的此类彰显方式,表面上是媒介报道塑造了典型,其实质是权力描摹好得以体现自身意志与愿景的典型模板,媒体再据此框选具体典型身份加以广之告之,已达到塑造一种满足权力预期的人生理念、生存伦理与价值标杆之目的。
(二)议题:“不由自主”的典型与“无拘无束”的权力
作为能够影响公众认知、态度、行为的议题设置者,媒介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传声筒。媒介中的典型话语是权力主体意志与要求的体现。权力主体御使下的媒介及其建构的媒介环境将公众的注意力指向自身所预设的议题之上,也在一定程度上诱导公众依据媒介的话语序列思考问题。因此,权力为媒介关于典型报道的议题设定卷入了一场围绕认同、规训及其合法性生存的意识形态斗争之中。身份要素是典型报道的存在性前提,而议题则是典型报道不断推陈出新,花样翻新的百变魔杖。典型报道的议题催生要素通常是权力规训的政治使命与时代召唤。它们原本就会跟随时间不离不弃地按照自身运行逻辑进入公众的视线。但现实是,权力有时喜欢赤膊上阵,钳制着媒介,按照自己的行事逻辑与运作方式,或借由某类所谓的良好愿望与高尚目的由头(需求)不断美化与粉饰典型,使典型报道议题本身时常发生事实引用矫情、舆情引导失聪与价值定位异化的悲情局面。
典型报道的议题,是一种话语图式,它或为经验、或为故事,讲述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图腾。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和平建设年代,党和政府都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活动,也在此过程中,媒介本文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典型经验。这是一个经典的权力体系通过媒介设置议题来实现民族、国家与制度共同体的建构的过程。具体措施包括权力体系发出相关议题号召,媒介以此议题命定自我议题与之积极配合,并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进行宣传。
雷锋及“雷锋精神”是整个20世纪后半叶至今的媒介典型奇观,更是“中国人道德生活乃至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价值要素”。(9)相继数代领导人题词亦为雷锋及其“雷锋精神”典型的重要运作方式,尽管题词具体的历史语境无法完全统一,但其价值指涉却大抵相似,即权力(机构或个人)通过询唤(interpellate)个体,号召公众效仿典型人物。如“向雷锋同志学习: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周恩来题)、“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周恩来题)、“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朱德题)、“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邓小平题)、“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叶剑英题)。(10)
媒介作为生发共时性观念与想象的关键,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共同体提供了技术的支撑。以《人民日报》为例,通讯《苦孩子成长为优秀人民战士》介绍了雷锋身份的转变;此后《人民日报》开设《学习雷锋》的专栏,刊载相关议题的文章多达百余篇,运用诗歌、通讯、消息等文体形式讲述、宣传雷锋。如此,权力体系凭借自上而下的组织原则,赋予雷锋及雷锋精神仪式般的叙事结构,激发、塑造着公众的共同价值观念。
(三)评价:权力视野中“典型”生存的合法性来源
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认为,媒介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不自觉地囊括了社会主导阶级的观念,并在具体的仪式表达、传媒生产、组织等层面有权力机构的烙印。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如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也笃信,媒介的绝对独立性是不可能实现的,宣示媒介作为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更是没有现实的生存土壤。此外,他们也对受众能动性选择、接触媒介及其信息持批判、否定的态度,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内容、形式的高度发达只是遮蔽了其异化、物化受众的本质,受众在批量生产、复制、传播的“文化工业”产品的消费快感中无法自拔。大众文化、大众传媒成为权力体系的附庸,它们以此为基础,来保证自身的合法性。技术决定论范式的代表麦克卢汉也承认,电子媒介破坏了原有社会的价值构成、社会结构。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基于权力对于媒介的干预、掌控。从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及麦氏的观点中至少可以窥到,权力体系对于媒介本身或者是媒介议题的评价是其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合法性基础,尽管他们用以论辩权力效能的实据都是来自当代西方社科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
典型报道中,权力机构对于典型的积极评价经常出现在各类会议、文件之中。而媒介也应对其塑造的典型积极配发社论、评论员文章等评论形式以表明立场、态度。媒介的评论是一种回向性的权力,以权力导向为基点,旨在对公众产生影响。权力体系是媒介评论的力量生发点,也使得评论存在于一定的权力场域之中。布尔迪厄认为,场域“作为一个空间的隐喻,它暗示着买方和卖方之间的等级以及交换关系,行动者之间在场域中的互动是由其在位置等级系统中的关系性定位塑造的”。(11)场域对媒介评论范式的影响一直存在,尤为体现在媒介对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及典型经验进行的评述,因为它承载着权力机构与媒介之间某种心照不宣的契约。
肇始于2002年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作为典型人物呈现的平台,已持续10余载。在典型的身份选择中也最大化地实现了去政治化,如2006年总计130名的候选者有近七成的草根阶层。它能够让华夏儿女心灵得到净化与启迪,正如白岩松所说:“每一次《感动中国》节目结束……这个时候,我会有一种真实的清洁感,就像一次精神上的沐浴……就像是一次年度的充电,一个缺电的电池再度内心充实。”(12)然而,不可否认,《感动中国》在其草根话语最大化的同时也逃避不了权力经由媒介放大普通人的不普通。《感动中国》中权力机构对典型的评价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是作为权力话语载体的颁奖词,这是一种在场的身份授予,以表明权力机构的意图;二是主流媒体中配发的相关议题的评论,旨在通过涵化效果,对受众产生影响。这两方面是使典型得以合法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制造”典型流程中必要的一个环节。
二、示范与规训:权力视野中典型报道的效能
自媒介诞生之初,其自始至终都在扮演着政策传导、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组织公众的重要角色,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传媒体制中,媒介更是充当着权力机构的“耳目喉舌”。而媒介中的典型制造及典型报道因其广泛的动员机制、鲜明的宣扬理念及利他的价值指涉正是权力机构看重并用以有选择性地整合社会记忆、达到道德示范及规训公众的重要手段。
(一)构筑社会记忆的一种工具
社会总是处在不断地更迭中,记忆穿透着历史,更是人们探究、反思“过去”的重要途径。社会记忆的成型,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进程,被媒介选择并呈现的社会记忆是多种权力互相角力并达到相对平衡的结果。而媒介本身也在建构社会记忆的环节中有重要作用,它会不自觉或不由自主地选择、压缩某种记忆,亦可以凭借其叙述手段及逻辑全方位、多角度、不计次数地凸显、放大记忆。社会记忆不单单是社会成员对“过去”的缅怀或回想,它还是大众媒介重构整个社会的有机要素、一种信息社会独具影像格调的媒介景观。
权力掌控媒介,媒介整合公众的记忆属性,媒介将有关典型的社会记忆呈现在公众眼前,典型不仅成了社会记忆共享和意义建构的平台,更延伸了社会的边界,集结、整合了新的群集,并使之成为诸多媒介中典型的簇拥。但在某种程度上,媒介只是站在时代要求、自身定位、体制约束及价值取向等角度关联媒介典型与典型本体之间的关系,不免忽视、遗漏了一些媒介中典型本该存在的议题。典型报道则重新拼合了公众脑海中关于社会记忆的碎片,将文字中的典型、影像中的典型、仪式中的典型等典型存在的介质整合起来,避免了因记忆不完整而造成的断层。将社会记忆放置于整个公共领域之中,在社会成员的互动、想象中呈现记忆共同体。
一直以来,社会记忆都有其独特的叙事框架及传承手段。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认为:“人们通常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他们的记忆,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13)对典型人物的崇拜、认同(如任长霞、雷锋、黄继光、郭明义等)的观念是公众在精神层面一以贯之的集体记忆,这当然源于这些典型人物的丰功伟绩,媒介的地位授予更来自于权力机构的形塑。典型形象在具象与拟象之间相互编织、缠绕、撕扯:他们是伟大的公务员、战士、公仆,他们也有普通人的爱情、友情、亲情,喜怒哀乐;在另外一个层面,他们是权力机构建构出来的典型,被视作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有重大贡献的人物而被公众所铭记、被国家所纪念,成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典型报道重组着社会记忆的叙事模式,在媒介文本中常常采用记忆还原、再现等运作手段,展现着典型的丰富意蕴。
此外,典型报道重塑着社会记忆的表述逻辑。经过“典型化”的社会记忆会被糅合进很多传统意义上社会记忆结构之外的内容,在展现“典型”自我的叙事体系外,还会拾取“典型”背后更为复杂、厚实的意义图谱。从而产生新的、更为宏观的文化意义。
(二)受众化性起伪的一种途径
所有的典型呈现、传播都需要观众,观众接受与消费是典型得以产生意义的前提,离开了观众的积极参与,典型则毫无意义。就典型报道而言,无论是身份、议题如何运作,其目的都是为了得到受众的认同,使得其所承载的话语表达符合受众的期许,使其表述的意识形态得以被正确地解码,使其裹挟的权力体系得以合法化。媒介文本中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典型经验等作为人类价值传承的符号与象征体系,是公众尊崇和学习的优秀典范,具有道德示范的效能。“典型”之所以能够在公众与道德本体之间架起桥梁,首先就在于“典型”遵循了道德本体和外延的基本价值取向,自觉地树立、捍卫着社会主流价值观念。
中华民族是一个道德观念极为强烈的民族,其道德传统更是源远流长。无论古代、近代抑或现代社会,权力体系都很注重用道德来导向、调节人际关系,从而达到人心向善的境界。但事实是,在媒介生态由单一向多元的过渡、姿态由封闭走向开放的现实境况中,典型的道德示范机制受到消解;媒介技术的人性化演化路径赋权于受众,强化了他们自主选择、接触信息的能力,尤其是后现代主义与消费主义思潮对受众的强烈心理浸淫与日久精神孵化稀释着典型道德示范的影响力、持久力。典型报道渐显乏力,认同感、影响力、持久力都有所下降,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媒介中的典型似乎成为消费浪潮中快餐文化的代表。因此,“典型”的生存现状需要权力逻辑主导下的媒介通过“建模”,在公众思维模式中生成共有的、符合媒介期待、社会期待、权力期待的价值规范。继而形成一种认知图景,与公众心灵产生共振,构筑起公众精神的共同家园。
就典型报道的道德示范效用,具体而言,包含以下两个层面:
典型对公众现实中具体的道德实践具有明显的引领作用,她们所传播的时代典范向公众鲜活地再现了具备崇高道德目标和理想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也为公众提供了不再是遥不可及、虚无缥缈的目标。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主张:“党报的基本任务是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以及党的政策。”(14)更使得媒介摒弃典型形象“高大全”甚至是神化的叙事惯习,而是注重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因此,“典型”似乎更是一个介质,搭建了公众的目标设定与具体的道德实践、道德风范之间互动的桥梁。
媒介通过典型报道与宣传筛选、树立、呈现一定规范与频度的“典型”不仅仅是对其进行褒奖和肯定,更重要的还在于,媒介以“典型”为中介,强化公众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知,塑造公众健全、良好的道德人格,进而促进现代道德范式的确立。因为,人是应该“被操纵、被塑造、被规训的。它服从、配合,变得灵巧、强壮”(15)文化化与社会化。当下社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市场主义不但消解着传统社会中以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的“纲常”为本位的道德体系,而且还冲击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本体的社会主义价值“伦理”。而典型报道的不断改进与推陈出新,她们所刊布的典型身上的忘我、奉献、利他等特性犹如灯塔般,牵引着公众合理的道德人格,建构着现代社会的道德范式。
(三)言行规训的全息魅影
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著作《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中详实地论述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规训”现象。在他的理论视域中,“规训”可以被视作是一种对权力的凝视(gaze)。规训以威权性注视为主要方式,而这个注视不仅仅是来自个人,而且也有来自隐形的权力的参与。“规训权力是通过自己的不可见性来施展的。同时,它却把一种被迫可见原则强加给它的对象。在规训中,这些对象必须是可见的。他们的可见性确保了权力对他们的统治。”(16)
作为规训的方式与手段,典型报道的重要性在于,通过媒介凸显、赋权为主要的规训手段。权力机构以此来实现对公众的身份与精神面貌的再造。典型的典型无疑延伸了我们的想象,诉诸于公众的追捧与规范自身的言行举止。正如福柯所言“话语即权力”,想象也是一样,公众想象的权力就是使典型得以浮现的权力。典型作为媒介文本的表征具备了很强的迹象性,这种迹象性的一个突出表现即在于:电视、电影等媒介中的典型的存在如同建筑、雕塑一样反映着被呈现典型的存在。大众传播媒介(在此特指电视、电影等)诞生之前,存在于特定时间节点的典型人物也好,典型事件也罢,都会稍纵即逝。而具备机械复制、保存、再现技术的电影、电视等媒介却可以将典型成为永恒。
这种永恒的效用生发是典型成为权力机构对公众进行规训的最好武器,它表现在诸多利用典型进行具有一定观念导入的整合、规制现象的存在。观点导入的整合与规制对于公众的规训效果是显而易见的。精通于此的权力机构在各种媒介场域中树立、建构典型,以求在一个类似于全景式监狱(panopticon)的社会中达到其特定的目的。“为了行驶这种权利,必须使它具备一种持久的、洞悉一切的、无所不在的监视手段……它必须像一种无面貌的目光,把整个社会机体变成一个感知领域。”(17)媒介中,铺天盖地的典型对公众行为构成指引或约束,如高悬于道路两旁、学校、企事业单位等的LED电子屏亦或是十几年前街头巷尾的高音喇叭中近乎24小时的各类模范的事迹宣传。在这种典型之音容笑貌持续饱和展布的状态中,公众必将自觉不自觉地把典型的光影蓄积在自己脑海中难以抹去,从而有意无意地以典型的品行作为自己日常行为的价值尺度,并最终达到权力体系规训诉求的意义典范。
三、走向公众:重构新闻典型的遴选路径
以弘扬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时代精神为主旨的典型报道在现代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一般是官方话语诉求的体现,蕴藉着一种马克思主义政党践行“利他主义(altruism)”宏大叙事的新闻理念,它旨在通过媒介建构“典型”与“非典型”之各种差异来彰显“典型”的出类拔萃,实现“典型”的示范效应,最终维持社会主义主导阶级——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秩序,故而,在日常新闻传播实际运作过程中,典型的遴选、形塑与刊布无时无刻不折射出内隐其中的政治权力、媒介权力等各种权力要素之间的协调、合作、博弈与争斗的印痕。
长期以来,典型报道处社会主义新中国主流新闻话语体系的中心,甚至被冠以是“当代中国新闻传播领域最富特色、最有别于西方的新闻报道样式”。然而,在后现代社会的转向中,公众的话语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原先的传统典型报道“高大上”的宣传模式逐渐被新型的被视为“上帝”的受众敬而远之。政治权力、媒介权力机构主导、制造“典型”的局面被打破。典型步出前现代、现代社会语境中“不由自主”的被神化境况,使得典型报道原有的价值取向呈现出一元独占到多元纷呈的政治脱敏状态。
另一方面,典型报道虽然在我国的新闻实践传统中颇有启迪意蕴,但却“没有形成一套清晰明确的话语共识,在典型报道的价值、典型报道的实践和典型报道的评价等关键问题上,新闻界的论述往往存在矛盾,令人困惑”。(18)因此,笔者认为,重构新闻典型的遴选与评价应为改进典型报道的当务之急。
典型报道在前现代及现代社会,基本处于被异化的状态,“高产典型”“假大空”,甚至是“虚假典型”时常存在。就当下现实语境而言,传统典型报道在权力规制下所展示出的“一贯政治正确”“永恒真理”与“绝对真善美”,常常遭遇以“不确定性”“非中心性”“非整体性”“非连续性”为价值标示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无情批判与解构。加之媒介中广而告之的很多“典型”亦是缺少深入社会机理部分的“悬空”抑或“虚置”典型。如此久而践之,典型报道的社会正能量示范效应难免不被消解得风卷残云,烟飞星散。典型报道运作的基本逻辑与方式若只是政治与强势权力的联手强使,它能展示的也只能是被权力体系宰割了的事实片段,距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及典型经验的原貌还有很长的征程要行进。因此,典型报道应试图跨越现行的权力场域,一方面需要媒介在选取“典型”时做好把关,控量而重质;另一方面,更需要媒介在讲述“典型”时尊重客观事实,在建制内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与现实的语境,消弭预设的立场与取向,从而达到一个典型报道得以健康形塑、发展、传播的媒介生态体系。
越来越密集的草根话语似乎在映衬着典型报道中阶级的界限不再明显,与之相对应的是威权话语、精英话语的隐匿。但是若想让典型报道获得进一步的实践拓展及机制保障,就必须在报道方法上秉持走向公众而非趋向公众。走向公众,即要求媒介将自身的报道旨趣与公众生活的现实形成观照,并在观照的过程中更加从容、主动地深入基层、深入公众生活;而趋向公众则指媒介摒弃专业理念,完全依附于公众的消费心理与欣赏口味,失去典型报道所能赋予人的心灵涤荡、精神内省的人生观导向作用。无论是在任何时代,典型报道中的所有要素都应是鲜活的、真实的、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走向公众,便是新时期典型报道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重要路径,因为它能够连接基数最为广泛人群的心理期待、精神寄托与梦想诉求;它能够使媒介放下身段,紧扣社情民意(而不只是仅作权力的附庸)建构一种可广泛参与的、可上下沟通,且鲜活、生动、接地气的新闻典型媒介遴选、报道与传播机制。
注释:
(1) 郑保卫:《当代新闻理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2) [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闫克文、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3) [美]赫伯特·甘斯:《什么在决定新闻》,石琳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
(4) Jordan.Glenn and.Weedon.Chris(1995)Cultural Politics:Class,Gender,Race and the Postmorden World.Oxford:Blackwell.p.1.
(5)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委会编:《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8页。
(6) 余家宏等:《新闻学简明词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4页。
(7) 周海燕:《记忆的政治》,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年版,第93页。
(8) 《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连年开荒收粮特多,英雄群众积极春耕》,《解放日报》,1942年4月30日。
(9) 许秋红:《媒体权力的式微受众权力的张扬——审视雷锋的媒体宣传》,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5页。
(10)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和国家领导人为雷锋同志题词》,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7159718.html。
(11) [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页。
(12) 白岩松:《感动是一种支撑》,《意林》,2006年第6期。
(13)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
(14) 毛泽东:《对晋绥提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见《新闻工作文献选编》,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71页。
(15)(16)(17) [法]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4、211、240页。
(18) 王辰瑶:《意义的困惑——从典型报道看最近30年新闻理论的艰难探索》,《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9期。
(作者朱清河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校社会科学处副处长;汪罗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