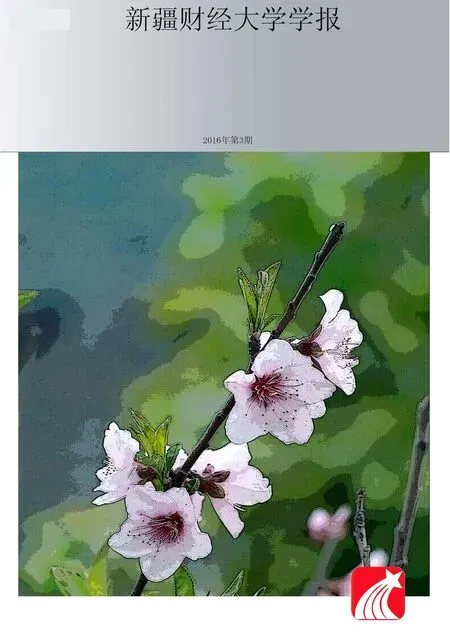爱情的新面向
——重读刘心武新时期早期小说中的爱情书写
彭 超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爱情的新面向
——重读刘心武新时期早期小说中的爱情书写
彭超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刘心武在新时期早期小说创作中对爱情的书写,召唤爱情,尝试引用私领域打破“革命+恋爱”模式,赋予爱情主体性位置,同时探讨资本对爱情的影响,以服饰为代表的物质渗透到爱情当中,也可以看到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气息逐渐浓厚并影响着爱情观的改变,爱情与婚姻不再具有神圣感,性与身体的叙事逐渐涌现。
爱情;私领域;资本;服饰;全球化
评论界通常将刘心武新时期的创作分为三阶段,主要是源于刘再复在《他把爱推向每一片绿叶》①详见刘再复著《他把爱推向每一片绿叶》,原载于《读书》1985年第9期。中对刘心武创作所作出的评价:以《班主任》为代表,包括《爱情的位置》等作品,构成刘心武新时期创作的第一阶段,该时期多为问题小说,以战斗的姿势撕下“文革”中惯用的面具,揭露“文革”给心灵留下的巨大创伤,唤起疗救的注意,社会影响重大;《我爱每一片绿叶》开启了刘心武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第二阶段,标志着刘心武从以文学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进入到“人的文学”阶段,将社会视为人的社会,呼唤社会关爱每一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如意》为该阶段的代表作,被刘再复称为“刘心武第一部人道主义的优秀作品”;《立体交叉桥》是刘心武走向第三阶段的标志,目光深入人物内心深层,充分展示人性的复杂性和差异性。长篇小说《钟鼓楼》等作品也在此阶段陆续发表,但文风有变,用“满怀的爱”加上“冷漠的外壳”写出社会文化发生史,也给读者留下想象及审美再创造的空间。刘心武不仅在作品的观念上不断突破自我,在艺术思维方式上也不断尝试、不断成熟。与刘再复对刘心武新时期创作三阶段划分相呼应的是跟随作品的三次轰动研究②详见王克安著《近20年刘心武研究述评》,原载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第一次是围绕着《班主任》的发表,评论多肯定《班主任》提出了重要社会问题,创造出谢慧敏式团支书的独特文学形象;第二次围绕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钟鼓楼》展开,认为《钟鼓楼》具有“清明上河图”式的美学追求,“橘瓣儿”式的新颖解构,具有社会学价值;第三次是围绕着《5·19长镜头》和《公共汽车咏叹调》两篇纪实文学展开,给“问题”注入新鲜而深刻的含义,认为只有用理解和宽容才能把握小说的真正本质。
刘心武新时期小说创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被称为“新时期的一面镜子”也是实至名归,本文主要是重读刘心武1977年—1982年创作发表的短篇小说,也会涉及部分之后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关注其中对于爱情的书写,尤其是在全球资本主义视野中来重读刘心武早期的爱情书写,更可以在文本的缝隙当中清晰地读出他对爱情的暧昧态度。或许刘心武在写作的过程中未曾刻意安排爱情所扮演的角色,但如今看来,爱情恰好在他的小说中戴了双重面具,有着矛盾的两面,而并非像我们所想象的单一角色。此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逐渐被卷入全球资本主义浪潮当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现代性的面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自然也对爱情发生作用。
一、私领域:改写“革命+恋爱”的尝试
爱情与革命纠缠不清,在不同时期扮演不同的角色。鲁迅《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为了爱情而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他们大胆地抛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勇敢地同居,尽管他们的爱情最终破裂,但却唤醒更多的人反对封建礼教;巴金《家》中的觉慧冲破阶级地位的界限爱上家中的侍女鸣凤,尽管他未能帮助鸣凤逃脱封建家庭的魔掌,但鸣凤的死却成为觉慧反抗封建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的催化剂;曲波《林海雪原》中的团参谋长少剑波与护士小白鸽的朦胧爱情发生在革命当中,给红色革命增添了一抹柔软的玫瑰色调;杨沫《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爱上高大英俊的卢嘉川与走上革命道路几乎是同时发生,革命与爱情演绎双人舞;欧阳山《三家巷》中的周炳爱着陈家小姐文婷,周炳要革命,陈文婷要建立自己温暖舒适的小家庭,无产阶级的儿子与资产阶级的女儿在革命的关卡上产生分歧,二人最终分道扬镳,革命与爱情只能二选一;宗璞《红豆》中的江玫与齐虹注定要分手,大学生江玫与银行家少爷齐虹的爱恋在时代的面前不堪一击,搏斗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革命再次战胜爱情。从这些随机举出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爱情时而与革命关系和谐,充当革命的导火索或是革命的催化剂,爱情引导着革命,牺牲了的爱情换来了无穷的革命力量,爱情被革命所置换,革命代替爱情成为精神的原动力。爱情有时候又与革命同在,在革命的同时爱情也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二者相辅相成,爱情让革命充满激情,革命让爱情荡漾神采。然而,爱情有时候又与革命不太同步,好似有了爱情,革命便受到牵制不太彻底;有了革命,与之冲突的爱情就一定要被抛弃,爱情与革命忽而又成为一对敌人。
那么,“革命+爱情”的模式在新时期刘心武的笔下有没有得到拆解呢?答案是有些暧昧的。
新时期,爱情曾经一度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通过召唤爱情来召唤“文革”中被压抑的情感,进而召唤出具有主体性的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讲,爱情是文明的象征,呼唤爱情就是冲破愚昧向往文明,爱情继五四新文学之后再次成为文明与愚昧冲破的媒介。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写出婚姻应与爱情同在,无爱的婚姻是不幸福的;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写出每个人都应该有爱的权利,正当的爱情应该受到保护而不是摧毁;张抗抗《爱的权利》同样书写爱情的权利,再次探讨爱的问题。新时期文学之初,关于爱情的探讨格外重要,被视为“禁区”的爱情再次开放,爱情可以成为被讨论的话题,更重要的是这象征着国家权力层面承认情感的合法性,人最真实的情感应该得到正视,爱情尤为如此。谈爱情不再被视为资产阶级作风,或是生活腐化,相反,人们开始要求自己有爱情的权利,每一个人都应该爱或是被爱,爱情的合法性应该受到国家政权的保护。与此同时发生的是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复归。卢新华《伤痕》中的晓华最终回到母亲的身边,“文革”中被撕裂的家庭亲情伦理再度归来,与其说晓华与母亲的遗体达成和解,不如说子一代与父一代最终达成大和解。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母亲被正名,所以晓华与苏小林的爱情也得到了发展的可能性,他们才可以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过去,开启自己的幸福生活。
在刘心武新时期早期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为爱情正名的努力。《班主任》中的谢慧敏和宋宝琦同时认定《牛虻》是黄书,他们在没有读过的情况之下,自然而然地认定它是黄书,造成这种愚昧的罪魁祸首则自然而然地被指认为“四人帮”。宋宝琦在凡有女主角琼玛出现的插图上都为之添上八字胡须,他补充说“我们算命,看谁先交上女朋友”①详见刘心武著《班主任》,原载于《刘心武文集(第四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虽然宋宝琦和谢慧敏一样认为《牛虻》是黄书,是不应该读的,但是宋宝琦心底还是充满对爱情的渴望,他想比他的同伴先交上女朋友,所以才会比赛给插图上的女人添上胡子,至少宋宝琦敢于承认这一点。而谢慧敏在随意翻阅《青春之歌》之后便“心跳神乱”,恰好证明谢慧敏内心的青春期冲动,她也会存在对爱情的朦胧幻想,只不过她不会也不敢承认自己的情感波动,那是被压抑的存在。《班主任》在发出救救被“四人帮”迫害的孩子们的呼声的同时,也轻轻地触动了关于爱情的记忆。
《爱情的位置》通常被视为刘心武讨论爱情的作品,被评论者认为是为爱情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爱情究竟有没有自己的独立位置,这的确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快满28岁的亚梅搞对象被认为是天经地义,“连前几年把她管得紧紧的魏师傅,半年前还给她介绍过一个小伙子呢”②详见刘心武著《爱情的位置》,原载于《刘心武文集(第四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前几年亚梅也是20多岁,正是谈恋爱的好时光,魏师傅为什么要把她管得紧紧的呢?为什么一定要到年龄大了才放松约束,督促赶紧找对象结婚呢?魏师傅们作为父一代约束子一代的行为原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过分约束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造成只有婚姻没有爱情的局面,这其中固然有“四人帮”的原因在里面,但是父一代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他们曾经扮演过帮凶的角色,至少在恋爱的事情上如此。管得严固然可以防止年轻女性犯错,让她们集中精力搞建设,但是恋爱也并非完全是坏事,她们年龄大了不是也一样介绍对象,然后象征性谈谈恋爱再结婚么?
亚梅所寻找“最满意对象”的行为也并不为孟小羽所赞成,因为在孟小羽看来,爱情与物质条件无关,爱情是种纯粹的精神追求,一旦沾染上物质就显得世俗。孟小羽的恋人陆玉春是一家普通饭铺的炊事员,她认为“我不是在搞对象,我是在恋爱”③详见刘心武著《爱情的位置》,原载于《刘心武文集(第四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因而与亚梅拉开了距离,因为亚梅认为无产阶级不需要爱情,《白毛女》中的喜儿和大春之间只有阶级情谊。爱情究竟应不应该存在,孟小羽去向冯姨寻求答案,在革命者的生活里,爱情不必占据一个位置,即便是健康的爱情也会成为一种牵累,应当压缩到最低限度,还是说爱情应该建筑在共同的革命志向和旨趣上,经得起斗争生活的考验,在革命生活中给爱情留有一席之地?对此,冯姨给出的答案是:“当一个人为爱情而忘记革命的时候,那便是把爱情放到了不恰当的位置上,那就要堕入资产阶级爱情至上的泥坑,甚至做出损害革命的事来。当一个人觉得爱情促使他更加热情地投入工作时,那便是把爱情放到了恰当的位置上,这时候便能体会到最大的幸福。总之,爱情在革命者的生活中应当占据一席重要的位置”④详见刘心武著《爱情的位置》,原载于《刘心武文集(第四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
孟小羽得到冯姨的肯定之后才敢放心大胆地将自己的恋爱情况告知父母,向魏师傅汇报。尽管恋爱或是搞对象在有些人的心目中与经常迟到、早退、工作中的走神、花枝招展的装束联系在一起,但孟小羽和陆玉春完全没有这般行迹,因而孟小羽的爱情是值得赞扬的。
值得玩味的是,爱情一定要与革命工作联系在一起,对革命工作产生正能量,这才算得上是爱情。爱情与革命,要么是相互促进,要么是产生副作用,没有第三种模式。怎样的爱情是可取的?那就是孟小羽式的,因为恋爱而迸发出无穷的激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用新刀具试车零件,在攻关战斗中能够冲锋陷阵,身先士卒,将革命事业永远摆在爱情的前面。一旦爱情可能危及革命事业,即便这种感情本身是正确而健康的,那也要遏制住自己的感情。《面对着祖国大地》中的尤跃辉喜欢那穿着紫罗兰上衣、摇着手绢的双辫姑娘,希望能够悄悄地邀请她到公园散步,但这种念头刚起就被掐死,不是不爱姑娘,而是他觉得自己应该首先爱自己的学业。“才二十岁,不能过早地沉迷于那种虽然合理而且健康的感情。亲爱的党,亲爱的祖国,派出了伯乐,把我当作千里驹选了出来,给了我这么难得的学习机会。我得发奋学习,把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学到手,而且还要去向前发展”*详见刘心武著《面对着祖国大地》,原载于《刘心武文集(第四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86页。,所以为了学习、为了更好地进步,就要暂时放弃爱情。与自己祖国的未来相比,爱情又成为自己的私事,不能因为自己的私事而耽误祖国的大事。尤跃辉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才要放弃对身穿紫罗兰上衣的姑娘的情感,全身心地投入到大学学习当中,为的是将来更好地为祖国建设事业添砖加瓦。革命依然压倒着被召唤回来的爱情,爱情依然没有获得主体性位置。
爱情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私领域呢?现在看来,爱情是属于个人的私事,在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所进行的活动,不应该是组织所全面掌控的。健康的爱情应该受到保护,在私领域中不受干扰地茁壮成长。如果说刘心武在新时期初仅仅召唤爱情并没有出奇之处,那么他尝试引用私领域打破“革命+恋爱”模式,赋予爱情主体性位置就能称得上是伟大之举。这种伟大的尝试是在文本的缝隙当中被呈现出来的。
刘心武在《门外一株合欢树》中借男主人公之口说:“其实恋爱是不应也不能禁止的,应当禁止的是荒废学业,而明智的恋人是不会因恋情而放弃事业上的奋进的。”*详见刘心武著《门外一株合欢树》,原载于《刘心武文集(第四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页。比起尤跃辉来,这位男主人公进步很多。尤跃辉担心爱情会耽误学业而放弃心中萌发的对紫罗兰少女的爱恋,而这位男主人公相当明智地思考了爱情与事业的关系,认为爱情并不会影响学业。爱情开始具有自己的主体性位置,发出自己的宣言,为自己争取合法性地位。
《我爱每一片绿叶》则将私生活从公共生活中脱离出来,脱钩的手法是强调爱情。也许魏锦星对那位姑娘的爱情甚至算不上爱情,而只是单恋。在魏锦星的抽屉底,“搁着一张同底面积差不多相等的大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微笑的姑娘的大头”*④⑤详见刘心武著《我爱每一片绿叶》,原载于《刘心武文集(第四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189页和192页。,而正是这触动心灵深处最柔软处的照片给他引来无穷的灾祸。“文革”不许魏锦星在工作之外再保留个人的“自留地”,人人被教育要用“事事离不开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一切,个人情感不再被允许表现,所有被称之为个性的东西也不能存在。魏锦星的私藏照片被粘到了大字报上,那张照片寄托着他全部的情感,尽管这种情感并不为他人所理解。照片上那长得并不漂亮但是青春焕发、爽朗地笑着的姑娘可能是他思慕的对象,是他隐藏在心底的秘密,不愿与他人分享的秘密,也许那位姑娘也并不知晓他的一往情深。当隐藏最深的隐私被公开粘到大字报上,可想而知他内心受到多大的创伤,那甚至可能比将一个人赤裸裸地袒露在众人面前更为凶残。后来,照片上的这位姑娘成为40岁上下的妇女,“矮矮的,没有什么腰身,脸庞瘦瘦的,眼角鱼尾纹很明显,看上去很憔悴”④,但魏锦星仍然对她倾心照顾,他的心底藏着对心爱姑娘的柔情,不管别人的看法,保持着自己的性格,即便会招来误解。《我爱每一片绿叶》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一个人在努力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工作的前提下,能不能保留一点个人的东西,比方说,能不能有一点个人的秘密”⑤,能够具有自己的私领域,在8小时工作之外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对于渴望具有主体性的个人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
正是刘心武对私领域的强调,对私人空间和隐私权的重视,使得《我爱每一片绿叶》至今仍能闪烁光芒。除了公共生活,具有主体性的个人还需要有自己的私生活,那是不受干扰的、远离8小时工作的空间。在私领域当中,可以放心地搁置自己心爱姑娘的照片而不用担心随时被人粘在大字报上,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而不用担心被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当爱情与文明联系起来的时候,追求爱情空间即为追求文明,原本是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被巧妙地转化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话语转换之后,被视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私领域转而被视为文明的象征物,从而顺利地在文本当中被接受。至此,“革命+恋爱”的模式因私领域的引入而得到破解,革命是8小时之内的事情,8小时之外的爱情空间不再与革命发生重大联系,现代性的进入以及现代文明使得时间首先被区分开来,8小时内是上班时间,其余时间是私人时间,也不再提倡将所有时间奉献给革命。至于私领域究竟应该做些什么,除了爱情之外,是否还有其余事情可做,等到全球资本主义全面进入中国之后就揭晓了。
二、服饰:精神与物质的合谋
刘心武在新时期早期创作的小说中多次描写人物的服饰。《班主任》中张老师让谢慧敏带头换上短袖,谢慧敏热得喘气却不愿脱下长袖衬衫,只有宣传委员石红才会穿带小碎花的短袖衬衫,在她看来那是“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的表现。同时,也只有穿小碎花短袖衬衫的石红喜欢读《牛虻》与《青春之歌》。这与计划经济时代的“蓝蚂蚁”相比,单一的色调开始丰富起来,在服饰上的选择也开始多样化,服装设计行业逐渐兴旺,人们对物质的享受也开始光明正大。
服饰起初是可以用来区分人的阶级地位的,例如在重农轻商的时代,商人就不允许穿丝绸衣服。古代只有皇帝才可以穿明黄色,也只有皇帝的衣服上才可以印上龙的图案,如果其他人使用只有皇家才能使用的颜色、图案或者花纹,那就是僭越之举,会被视为大不敬,轻则受罚重则掉脑袋。在正式场合穿错衣服也会被视为没有教养的不当之举,一个著名的文化研究案例就是工党领袖米歇尔·福特参加在伦敦纪念碑举行的纪念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殉难者的仪式上,因为没有穿合适的服装,没有显示出对殉难者的尊重而受到媒体的强烈批评①详见阿雷恩·鲍尔德温等著、陶东风等译的《文化研究导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44页。。在“文革”期间,人们的服饰通常都比较单调,审美化和个性化受到政治上极左思想的压抑,情愿或者不情愿地成为政治符号。代表无产阶级革命的绿军装在全国迅速流行,穿一身绿军装,带着红色的毛主席像章,背着军挎包和语录袋,戴着红袖章,那是革命的象征。没有资格穿绿军装的人则还有中山装、工装、青年装等普通服饰供他们选择,但大多造型单一色彩单调,看不出性别上的区分。1966年8月红卫兵贴出大字报《向旧世界宣战》,宣称“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店、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飞机头’、‘螺旋宝塔式’等稀奇古怪的发型,‘牛仔裤’、‘牛仔衫’和各式各样的港式衣裙,以及黄色书刊,正在受到严重的谴责。我们不要小看这些问题,资产阶级的复辟大门正是从这些地方打开的。我们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毁黄色书籍和下流照片。”②详见王星著《百年服饰潮流与世变》,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82页。
服饰通常与时代紧密互动,新时期初人们的服饰迅速发生变化,而这一切在刘心武的小说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在《神秘的姑娘》中,服饰就具有如此的对比意义。神秘的姑娘“头上是化学冷烫过的披肩发;上身穿着黑白相间的花格呢窄腰上衣,下面穿着条咖啡色的略呈喇叭口的料子裤,脚上蹬着黄黑相间的半高跟皮鞋;肩上还挎着个深红底带白色图徽的大皮包”③详见刘心武著《神秘的姑娘》,原载于《刘心武文集(第四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页和263页。,而后神秘的姑娘换装为“身穿一身国防绿军服,带着军帽,没有帽徽领章,左臂上却套着个足有一尺长的红绸袖章;眉眼横立,满脸怒容,威风凛凛,杀气腾腾”④详见刘心武著《神秘的姑娘》,原载于《刘心武文集(第四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页和263页。。这正好是“文革”前后的服饰,给人的感觉相差万里。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早就成为历史,现在是穿米黄色大衣的时候,“邹宇平的大衣是米黄色的”⑤详见刘心武著《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原载于《刘心武文集(第四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匪不匪,看裤腿;狂不狂,看米黄”,邹宇平穿米黄色大衣,他上班就好好干活,下了班就张罗张罗自己,而在晁老师看来那米黄色大衣正是苍白、庸俗、浅薄灵魂的写照。而只有当邹宇平再次投入到火热的新生活中,跟着大伙去打扮祖国,让祖国穿上现代化的服装,而不再想着打扮自己的时候,不再顾着自己的米黄色大衣的时候,他的灵魂才得到了升华。服饰在这里并没有起正面作用,反而成为单薄心灵的写照。
爱情同样与服饰分不开,人人都爱漂亮的姑娘,穿漂亮衣服的姑娘会让人多看两眼。《乔莎》中“我”第一次遇见“她”的时候,就注意到“她”的服饰是多么的美丽:“夕阳在她的身后,给她俊俏的身姿勾了一道暗红的边,她头上飘逸的发丝,全成了近乎透明的蜂蜜色,这时我才意识到她上身那件柠檬黄的膨体纱毛衣,与周围景色是那么协调。”*②③④⑤详见刘心武著《乔莎》,原载于《刘心武文集(第四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85页、286页、290页、292页和297页。
“她”美丽的身影加之身上的漂亮衣服随即打动了“我”,原来这是舞蹈系的学生,“她”跳着芭蕾舞的模样即将出现在脑海中,这时候对其服饰的想象是《天鹅湖》中的天鹅裙,伴随着优美的造型,在“我”的脑海里荡起了神秘的涟漪,接着“我”有了新的发现:“她那毛线衣的高圈领里织有金线,使人联想到莲花瓣上的纹路,她真美。”②
乔莎评论“我”,认为“我”会冥思默想,其实“我”是在脑海中想象乔莎穿着天鹅裙跳着《天鹅湖》的美妙场景,在刚刚认识乔莎的时候,他已然将其作为幻想的对象,对其从身体和服饰上加以仔细的观察,这分明就是男性对女性的凝视,却被天真或曰假装天真的乔莎称之为“冥思默想”。而“我”陶醉在对女性的幻想当中,但却非常乐意接受乔莎对自己的评价,好似自己显得神秘或者有学问。这又是一种男性的虚荣。当乔莎第一次来到“我”家的时候,乔莎服饰上的变化再一次吸引了“我”眼光:“她穿着一身暗金色的灯芯绒衣裤,敞开的西装领里,露出墨黑的开司米毛衣,这回的毛衣是无领的,把她的面庞和脖颈衬托得格外雪白。她把带来的伞撑开晾在门厅里,那不是折叠的,也不是淡绿的,而是一把小巧的桔红色的南式纸伞。”③
在乔莎到来之前,男主人公幻想的是在下雨天乔莎会打着一把淡绿色的折叠伞,而现在看到的乔莎却是打着一把桔红色的南式纸伞,于是男主人公宗晓钟立刻认为在雨天里还是暖色能够给人带来乐趣。很明显,在短短的接触中,宗晓钟喜欢上了乔莎,虽然他们以兄妹相称,但他对她的迷恋显然已经超越兄妹之情。宗晓钟借给乔莎三本书,还有小泽征尔指挥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录音带,乔莎将书和录音带搁到“一个小巧的淡褐色的手提包”④里,然后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后离开。从乔莎的服饰和所携带的手提包来看,乔莎就像真的是从上海考到北京的舞蹈系学生,外貌姣好,教养又好,注重服饰装扮,懂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能够与男主人公聊了音乐再聊文学,从乔治·桑聊到海明威,从文学期刊聊到旅游杂志,还有诸多听说的外国见闻。如果乔莎真的是像她所说的那样来自上层社会,那么也就不会有接下来的戏剧性反转:“她又穿上了我们头一次见面时的衣着。我发现她的右颊上有小米粒大的一块红肿,这又使得我觉出她的面部轮廓并不那么和谐。”⑤
有意思的地方也正在这里。乔莎穿上他们第一次见面的衣服,宗晓钟一眼就注意到这一事实,而后才注意到乔莎的脸上有红肿。第三次见面就穿了重复的衣服,可见乔莎实际上并没有很多衣服来打扮自己。因而,即便这红肿只有小米粒那么大小,那也使得宗晓钟倍感不适。不仅仅因为红肿使得乔莎显得不如前两次那样漂亮,更重要的是宗晓钟发现乔莎假冒自己是舞蹈系的学生,她是改变了或者故意隐瞒自己的身份来与之交往。估计宗晓钟在这时候是不可能记起当初自己是如何为乔莎的风采所倾倒,并且是他主动回应了乔莎的微笑。而这个时候乔莎的真实身份成为一个谜,显然她并不是和宗晓钟一样来自上层社会,没有高贵的出身,也没有著名电影配音员李梓这样的大姨。这时候乔莎提出来要洗脸和擦香脂,宗晓钟都答应了,唯独没有答应提供一面大镜子供她擦脸时使用。于是乔莎就对着厨房水池上方的一面小圆镜来细致地往脸上擦着香脂。女性为了美化自己需要付出大量的心血,显然乔莎并不能经常享用擦香脂的待遇,而且去掉了舞蹈系学生的光圈之后,她依然还是她本人,但在宗晓钟的心中她已经欺骗了自己,犯了不道德的错误。爱情自然离不开真实和诚信,然而在这里很难说宗晓钟是真正地爱乔莎,爱乔莎本人,还是爱自己想象当中的学古典芭蕾舞的出身高贵的上海女生。至于是什么让宗晓钟对乔莎产生错误的观念认识,其中的原因固然有乔莎自己的过错,她出于不可言说的私心而故意向宗晓钟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在未曾得知对方真实身份之前,宗晓钟的确为乔莎倾倒而迷恋于乔莎,因为认识了乔莎这样一位妹妹感到虚荣心的满足,甚至主动邀请萍水相逢的姑娘来自己家作客。服饰可以说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第一次见面吸引宗晓钟的就是乔莎的服饰,他甚至幻想穿着天鹅裙的乔莎摆出优美的造型,跃起,落下,足尖点着湖水,逗起梦一般神秘的涟漪;第二次见面时无领的黑色毛衣衬托出乔莎白净的脸庞,这让他们的聊天进行得愉悦并很快约定下次见面的时间;而第三次见面则是穿着同第一次相同的衣服,而且宗晓钟也已经知道她并非舞蹈系学生,她的身份现在对于他而言已经不再重要,他也不再想与之发生进一步的联系。而这一切的谜底也很快得到揭晓,他们的第四次见面发生在乔莎意料之外,因而乔莎的服饰装扮是那样的糟糕:“正当我要把事情向她挑明的时候,门‘砰’地被撞开了,进来了一个衣着邋遢的姑娘,她脸上的皮肤显得粗糙,头发蓬松,一手提着半网兜切面,一手托着半碗黄酱。”*②详见刘心武著《乔莎》,原载于《刘心武文集(第四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00页、301页。
宗晓钟一看到乔莎这幅模样就僵住了,他心目中那位原本衣着得体、举止优雅的乔莎立刻死去,那只是被表演的乔莎,而真实的乔莎竟然是如此世俗与不堪,尽管这样真实的乔莎是日常生活经常可以在胡同中见到的普通女性。她是衣着邋遢的,没有穿柠檬黄的膨体纱毛衣,也没有墨黑的开司米毛衣;她显然也没有香脂可以擦,因而皮肤是粗糙的,就连她手中拿着的切面和黄酱也因为过于生活化而显得俗不可耐,这和古典芭蕾舞系的乔莎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随后宗晓钟看到了乔莎的全部装备,那是在前几次见面当中引起他美妙幻想的道具:“我仔细一看,就看出在固定于两墙之间的铁丝上,挂着三个衣裳架,衣架上是我所熟悉的两件毛线衣和一件灯芯绒上装。两双显然是上街时才穿的鞋,一双半高跟的皮凉鞋,一双灰色的细工布鞋,掸刷得干干净净,摆放在衣架之下。”②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他们第三次见面时,乔莎穿着重复的衣服出现。而后,宗晓钟的目光仍然在屋中搜录,于是引发了乔莎的激烈行为:她爆发般地掀开床褥子,露出床褥子下面压着的灯芯绒喇叭口裤,而后将床头柜狠狠打开,那里搁着淡褐色的考究的手提包,而在屋角则靠着那把红油纸伞。这一切让宗晓钟感到痛心,亲眼看到道具的行为让他更真实地感受到乔莎对自己的欺骗,她只是北京胡同里普通的待业女青年李月梅,她的父亲在外地调不回来,母亲瘫痪在床,自己自学没有人辅导。在这一刻,李月梅的自尊心同样受到了伤害,这种伤害犹如《我爱每一片绿叶》当中魏锦星看到姑娘照片被粘在大字报上的感觉。宗晓钟在得知乔莎的真实身份之后,在了解李月梅的真实处境之后,也未曾伸出援手,反而认为原谅李月梅对自己的欺骗就是伟大的了不起的举动。在宗晓钟为自己的伟大的原谅与宽容感到自豪之时,显示出来的却是他的自私与无情。
服饰在宗晓钟与李月梅的交往当中扮演的角色之伟大是不可低估的。如果宗晓钟爱的是乔莎本人,即真实的李月梅,那么李月梅穿什么衣服对于宗晓钟来说还会显得那么重要吗?宗晓钟是爱穿着漂亮衣服的乔莎,服饰正是给李月梅施加了魔法,将其从灰姑娘变为公主,然后送到王子的面前。被打回原形的灰姑娘不再被王子所爱,而李月梅也并没有隐藏的公主身份,所以,他们的故事只能到此为止。
同样的公主被打回灰姑娘原形的故事发生在《她有一头披肩发》中,只不过这里是披肩发起到了服饰的作用。这位姑娘有着一头黝黑浓密的披肩发,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黑亮的波晕,然后迷住了“他”。当“他”得知姑娘的头发因为伤寒病全部掉光了,而“他”所见到的诱惑人心的头发和睫毛都是人造之时,便断绝了对姑娘的想法。爱情在这个时侯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这位姑娘和李月梅一样凭借着出色的外貌便轻而易举地获取男性的关注,男主人公则声称自己喜欢的并不是姑娘的容貌,而是爱着姑娘的灵魂。一旦男主人公发现姑娘的披肩发是假发,即便佩戴假发是因为姑娘受到过伤害,男主人公仍毫不犹豫地放弃与姑娘建立进一步交往的念头,不再认为自己爱的是灵魂而非外貌。值得注意的是,姑娘的假发是从香港带过来的。
在这里,爱情与物质性存在发生着紧密的联系,爱情不是因为灵魂的相互吸引,而首先是外貌上的吸引,合适的服饰和可以掩盖缺点的披肩发是穿破男性谎言的利器。物质一方面可以帮助女性更好地吸引男性的目光,成为爱情的催化剂;另一方面也成为爱情的试金石,即没有外在的物质条件,男性是否依然会对心怡的女性保持着同样的爱恋。在此意义上看欧亨利《麦琪的礼物》才显示出真正爱情的可贵,那是不会因外在物质条件改变而改变的爱情,不会因为少了头发或是没了金表而发生变化。
三、缝隙:全球资本主义的渗透
从《乔莎》和《她有一头披肩发》中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爱情的观念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爱情不再是单纯的精神层面的追求,爱情的不及物性已经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爱情不能够冲破阶级的界限,巴金《家》中的觉慧可以爱上封建家庭中自己的侍女鸣凤,在鸣凤跳湖自杀后,深刻认识到封建礼教对人性的破坏与摧残,毅然决然地冲破封建家庭的阻碍,愤而转向革命,追求革命带来的新生命新生活。在《乔莎》当中,家庭条件优越的宗晓钟可能会爱上胡同里的姑娘李月梅吗?宗晓钟是物理系的学生,他看《量子力学》,也看《安吉堡的磨工》,他还给乔莎展示过自己的藏书,那是“两个新的玻璃书橱,橱里巧妙地排列着我心爱的文学书和专业书,并配置着一些雅致的工艺品:一座贝多芬的石膏像、一只造型奇特的白瓷天鹅、两个泥塑的傣族少女、一只妈妈从罗马尼亚带回来的玻璃猫、一盒京剧脸谱”*详见刘心武著《乔莎》,原载于《刘心武文集(第四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虽然他的父亲已去世,但他的母亲是从事外事工作的,姐姐在西安上大学,家庭条件优越,有知识有教养并且前途有保障,他与觉慧有着相似的优越条件,只不过觉慧生活在封建家庭当中。但即便是在封建家庭当中,觉慧依然存着一份对侍女鸣凤的感情,而宗晓钟在未曾得知乔莎的真实身份之前也曾对乔莎保持着一份真挚的情感,然而一旦乔莎成为李月梅,这种不牢靠的情感即刻随风而逝。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宗晓钟不能爱李月梅呢?很显然这不仅仅是关系到诚信的问题。李月梅的确是利用自己仅有的服饰作为道具,在一定意义上欺骗了宗晓钟,可是这完全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甚至说李月梅装扮为乔莎,在主观目的上并不是想要欺骗宗晓钟,只是宗晓钟误打误撞进入李月梅的关于乔莎的梦中。李月梅渴望成为乔莎那样的女性,可以与宗晓钟这样的男性自由交往而不存在身份上的障碍。李月梅积极向上,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学来达到在社会结构层级当中地位上升的目的。她在看英语广播讲座的课本,在看《青年自学丛书》中的几种,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完成命运的改变,可惜自己能力不够,课程太难,没有人能够辅导她,没有人帮助她、鼓励她。她穿上自己唯一能够够得上档次的衣服出门,不仅仅是为了装扮为上层社会的女性,更可能是为了曲折地满足自己心底对上层社会的向往。一位生活在北京胡同中的年轻女性难道不可以存在对未来生活的幻想么?即便这种幻想只能提供暂时性的满足。李月梅凭什么不能成为宗晓钟不许她当的那种人?她完全拥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宗晓钟所不能剥夺的。而宗晓钟为什么不会爱上李月梅?宗晓钟爱的只是与自己同属上层社会的小姐,而非平民的女儿。他首先在社会层次上圈定自己所爱的对象,他爱的人应当与他一样是上层社会有知识有教养前途有保障的,他们可以一起听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可以一起谈论文学和音乐,聊旅游与国外见闻,而不是衣着邋遢,皮肤粗糙,与切面和黄酱打交道的胡同小市民。宗晓钟在得知乔莎就是李月梅之后,也没有像我们期待的那样依然深爱着李月梅,毫不嫌弃她的出身和暂时待业的生活,然后毅然决然地承担起帮助李月梅自学的任务,从而携手李月梅走上幸福而光明的生活大道。
爱情的神话已经在这里破解,不及物的爱情成为历史。爱情的观念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爱情开始变得及物。早在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中就已经暗示着爱情与婚姻观念的改变,尽管都是经受过革命的熏陶,但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丈夫与工农兵干部出身的妻子仍然会在解放进城后的生活中发生着种种矛盾。即便在日常生活一瓢一饮最普通的家庭琐事当中,他们依然会产生分歧,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影响着他们的生活观念,尽管他们最终达成和解,但是曾经发生过的矛盾依然暗示着爱情与婚姻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复杂。爱情与婚姻不可能仅仅是出于共同的革命目标,政治无法与最日常的生活完全融合在一起,而到了宗晓钟和李月梅的年代,婚姻讲究的是门当户对,纯粹追求精神上的共舞已经不能成为爱情的全部,表面上看宗晓钟放弃李月梅是因为诚信与欺骗,而背后的原因是爱情的观念已然改变。爱情再也无法完成与革命的双人舞,“革命+爱情”的模式已经被私领域的进入而打破,既然爱情已经不能起到革命催化剂的作用引领青年人冲破封建礼教走向革命,爱情也不能给激烈的革命带来浪漫的色泽,为革命英雄人物增添人情味和生活感,而且现在人们也不再为革命还是爱情这种两项选择题感到烦恼,那么,爱情也就失去了宏大的命题感和神圣的光环环绕,爱情就是个人的私事,不关系伟大的革命建设事业,也不关系社会结构的稳定,甚至也不会有人为了宗晓钟不担负起鼓励李月梅向上的责任而指责他。关于爱情的任何选择,都受到尊重。这种尊重意味着在形式上,国家或组织不再干预爱情婚姻生活,爱情婚姻也无需承担意识形态的功能。
需要关注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爱情观念的转变,最简单的回答是时代变了。
时代首先让单调的社会开始变得颜色丰富起来。新时期以来关于色彩的记忆从绿红蓝等具有丰富政治内涵的颜色,逐渐变得多姿多彩。计划经济时代将消费压缩到最低,只要能够保证基本生活需求之外,对普通百姓而言,便没有其他更多的消费品,与此同时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市与农村也不可能有多种色彩的出现,那是“封、资、修”的危险标志,社会运转能够最有力地被国家计划所掌控,而不至于出现脱序的现象。新时期,计划经济逐渐被市场经济所取代,国家从生产性社会向消费性社会过渡,过去被压抑的消费欲望一旦觉醒便势不可挡,城市的色彩也随之产生爆炸性增长。张颐武曾经认为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有着巨大的物质性吸引的背景,“却是在精神的层面上展开自身的,它依然是不及物的”*详见张颐武著《新世纪的中国色彩记忆》,原载于《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文集25:色彩与城市生活》,中国科协第25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2008年12月7日。,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在刘心武新时期早期作品中找到蛛丝马迹。虽然新时期初消费欲望刚刚觉醒,但是它的到来随即引起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爱情的位置》中,亚梅要去与对象约会,用洋红的拉毛围脖配宝蓝色的呢外套,让身为团小组长的孟小羽觉得非常刺眼。洋红色配宝蓝色是否不能够搭配倒不是真正的问题,这实际上正好是最近几年非常流行的撞色,但在新时期初孟小羽未能接受亚梅这样的装扮,觉得颜色过于刺眼,这是刚从计划经济中摆脱出来的正常反应。在《神秘的姑娘》中的那位姑娘上身是黑白相间的呢上衣,下身是咖啡色的料子裤,脚上是黑黄相间的皮鞋,挎着深红底带白色徽章的皮包,身上的颜色极其丰富。《乔莎》当中乔莎的柠檬黄的毛衣与墨黑的毛衣也曾经深深打动过宗晓钟。时代的变化开始让城市美丽起来,而让城市美丽起来最重要的标志是年轻姑娘身上色彩丰富的服饰。
随着生产性社会逐渐向消费性社会转型,人们对物质的追求逐渐得到合法性的承认。而之前在《千万不能忘记》中青年工人丁少纯下班后不再主动去厂里加班,而是去郊外打野鸭子卖,并在岳母的怂恿下买了呢外套,被认为是讲究吃穿,有修正主义的嫌疑,而如今工作之外的时间属于私人空间,不再受到干涉,正常消费欲望也不再被抵制。在《没有讲完的课》中,丁朵走出校园的时候,“她渴望着赶回到暖气扑人的家中,落身到新买不久的沙发椅上,让小女儿冲上一杯麦乳精递给她喝”*详见刘心武著《没有讲完的课》,原载于《刘心武文集(第四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面对着祖国大地》中的李抗脑海中也闪现过这样的念头:“还是找点木料给自己打了大立柜,留着结婚时候用实惠”*详见刘心武著《面对着祖国大地》,原载于《刘心武文集(第四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私人空间得到保证,消费欲望得到伸张,若是丁少纯生活在新时期,那么他打野鸭子和买呢外套的行为也不会受到指责,而是要被他人眼红的举动。可以理解的是在新时期初,人们对于社会的改变还抱有观望的态度,担心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再来一次大变革,赤裸裸地追求物质也许被别人在心中加以指责,甚至找对象也不能名正言顺地选择物质条件最优越的。《爱情的位置》中孟小羽就曾经在心底批评过亚梅的爱情观念。“想问她:‘他个人究竟怎么样呢?你摸透了吗?你——爱他吗?’我想,归根结底,你亚梅不是嫁给照相机以及那许多东西,最重要的是他本人——你要跟他度过今后的一生呢。倘若他一旦没有了存款折、大立柜、照相机以及许多现在吸引你的东西,你将怎么同他生活在一个屋顶下呢?”*详见刘心武著《爱情的位置》,原载于《刘心武文集(第四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固然亚梅的对象是大学毕业,工资不用上交家里,个人有存款,会木工活,给结婚准备了大立柜、沙发和书桌,单位能够分宿舍,表姐是文工团合唱队的因而看演出方便,这位男性的条件可能的确是吸引亚梅的原因之一,可是亚梅就要因为对象的物质条件而受到孟小羽的指责吗?追求物质的享受是个人完全正当合理的享受,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而且亚梅与对象也并不是没有感情上的交流,亚梅分明是非常享受与对象的交往,她沉浸在自己的幸福当中,更何况她已经被耽误为28岁的大姑娘了,她的选择不对么?并不是只有孟小羽和炊事员结合的爱情才称之为爱情,爱情在这里仍然是不及物的,一旦染上物质的因素,就可能被他人质疑为单纯为着物质的诱惑而非精神的结合。在孟小羽看来,不考大学去写一些关于青年工人的小说,激发同龄人为祖国的“四化”拼命劳动创造比上大学更有意义,把工厂和整个社会当作大学比进入真正的大学更有人生价值,这种观点得到了陆玉春的理解,这在孟小羽看来才是真正纯粹的爱情。陆玉春自己在准备考大学的英语系,却能够支持恋人不去考大学。他们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崇高追求,是为祖国建设奉献终身。我们不能否定他们将自己献给祖国“四化”建设的伟大精神,但是同样也不能否定亚梅为了自己的小幸福生活而努力。祖国的“四化”建设是为了让百姓的生活更美好,而不应该是专门吃苦不懂得过好日子。这种对爱情的理解很快在刘心武的小说中发生改变,起码不再用讽刺的笔调写来,而是以冷静客观的手法展现。
《月亮对着月亮》本意是讽刺,但在文本的缝隙当中可以看到爱情观念的悄然改变。“大拇哥”并非是干部子弟,他的父母是一般职员,他自己也是在厂子里当普通工人,但是“大拇哥”非常有能耐,社会活动能力超强,能够玩转各种事情,并且交上了上层社会的小姐“小天鹅”,而现在“小天鹅”的父母就要来到“大拇哥”的家中来相他。“大拇哥”发挥自己的交际网络和朋友圈子,居然能够整出像样的配置来接待即将到来的“小天鹅”的家人,因为“小天鹅”和她的母亲及她姐姐都是金眼皮,喜欢荣华富贵:“我已经从我们厂弄出一小桶汽油,说动‘小驹子’他三叔借了我一套刚分得还没搬进去的房间,又靠‘二拐子’和‘大锁眼’给我准备了一桌酒席,‘阿臭’、‘萝卜须子’他们给我借了四个喇叭的三洋收录机和唐三彩瓷马摆设,加上我自己早就制备好的沙发、立柜、落地灯、活动式酒柜……配上拐几道弯弄来的花格子地席、蝶式吊灯、出口茅台酒和金鱼酒心巧克力,估计准能把他们唬住,席上就把事儿定下来,初五办事处一开门我跟‘小天鹅’就去登记。”*详见刘心武著《月亮对着月亮》,原载于《刘心武文集(第四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46页。
物质与爱情的纠缠已经改变“革命+爱情”的老套话语,物质已然不可避免地渗透进爱情的考量当中。不能说这种婚姻完全没有情爱的成分在其中,但是如果撇开物质而专谈爱情显然已经不可能。“大拇哥”相信时代的改变,相信以自己的能力在新时代中将如鱼得水,即便是今天用借来的东西骗得“小天鹅”,他也相信可以在一两年之后真正拥有这些东西,因为“小天鹅”的父亲是厂长,他可以通过不断地走门子来获取他想要的东西,他能够把所有的关系网络玩转,变为可以利用的资源,并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他将成为新时代的新人物,办事灵活而有头脑。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与政治合作,资本高于一切,其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已超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国进入全球化时代,消费欲望的合法性得到国家政权的认可,而国际上的战略合纵连横当中,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合作并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作为基础,大大区别于之前的中苏合作。在这个时代,不再会发生妻子检举丈夫,儿子检举父亲,没有人会再时刻提高警惕,防止“封、资、修”的腐蚀,现在倒是渴望自己有一个海外的亲戚可以给自己提供出国的机会,或者能够捎来国内难以买到的高档商品。若是能够移民海外,更是难得的好机会。《夜半雨停》中的景伊慕在看到莫总的房屋装饰之后,不也在心底想着“倘若我家生活也能达到这种水平,我也许就不会走了”*详见刘心武著《夜半雨停》,原载于《刘心武文集(第四卷)》,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91页。。著名的《5·19长镜头》中就有“天灵灵,地灵灵,我们大伙要开心,一请奚秀兰,二请张明敏,三请汪明荃,四请徐小明,五看《霍元甲》,六看《万水千山总是情》,七要牛仔裤,八要迪斯科加‘华姿系列化妆品’,九要夏普、东芝、日立‘家用电’,十要‘铃木’、‘雅马哈’、‘西铁城’”*详见刘心武著《5·19长镜头》,原载于《刘心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1页。。当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对接之后,原来的革命力量也会追求来自外国的高档商品,人们不再以追求物质为耻辱。资本主义将革命大集体中的个人变为赤裸劳动力,男女的恋爱婚姻不再受组织审查,他们成为原子式的个体处于游离状态,自由的恋爱改写革命的爱情,这是在消费过程中产生爱情,而不再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爱情,这已经是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恋爱逻辑。
很快,伴随着全球化进入中国的消费观念不仅影响着爱情,影响着婚姻,而且人们对身体与爱情的看法也发生着改变。在此,阎连科《最后一名女知青》可以为其提供有力的佐证。在后期刘心武的作品中关于性的描写开始逐渐增多,虽然在刘心武的笔下,性的描写没有那么直接,但是显然这一时期的作家已经不可避免地将笔端触及到了身体与性的层面。《小墩子》写到群龙感到小墩子女性肉体所传递出来的特殊温柔,还有群龙与姑娘的亲嘴儿和相互掏摸;《凤凰台上忆吹箫》中的“她”显然是被包养的情妇,“即使是大白天,他也不在乎,连窗帘也不让拉,她一进屋就必须直抵卫生间。不等她冲洗完,他就会花样百出地同她白昼宣淫”*详见刘心武著《凤凰台上忆吹箫》,原载于《刘心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页。;《吉日》更是直白,虽然敏感的词语都省略,可是省略符号所占据的空格更是让人联想浮翩,“他结过婚,也有过几次露水姻缘……可是,他确实盼着……什么?就是,就是,有的书上用‘……’所表达的那些个东西”*详见刘心武著《吉日》,原载于《刘心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页。。可见身体与性已经不再神秘,婚姻与爱情也都失去了原有的神圣感,性有时成为了可以用来交易的东西,女性可以用身体换取物质享受,摆脱酒店服务员的身份,过上超越普通百姓的生活,所付出的代价就是自己的身体,而男性则可以通过付出金钱来换取女性的性服务,不再受家庭的束缚。至于更为激进的下半身写作等已然不是太遥远的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刘心武在新时期早期小说创作中对爱情的书写,随着时代的变化发生着巨大的改变。在新时期之初,刘心武通过在小说中召唤爱情,讨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进行人的解放,塑造具有主体性的人,他们将成为新时期的主人;并且,他也尝试引用私领域打破“革命+恋爱”模式,赋予爱情主体性位置,这个时候爱情还与革命与国家事业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爱情需要在不影响学业和工作的前提下,获取自己的生存空间,唯有不影响国家建设事业的爱情才能够称为合法性的爱情。很快,爱情便成为完全私人的事情,在私领域中自由进行,同时资本对爱情产生影响,以服饰为代表的物质渗透到爱情精神层面当中并且物质也逐渐渗入爱情,人们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为自己的小幸福而积极谋划。当中国进一步卷入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爱情观和婚姻观进一步改变,一些人不再重视对婚姻家庭的忠诚,开始出现婚外情与包养情妇的情况,这恰好印证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的文明时代的一夫一妻制度必然要以通奸和卖淫作为补充,而与此同时,关于身体与性的叙述逐渐压倒关于爱情与婚姻的叙述,开启着关于所谓“爱情”的一种新面向。
[1]刘心武.刘心武文集(第四卷)[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3.
[2]刘心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3]阿雷恩·鲍尔德温,布莱恩·朗赫斯特,斯考特·麦克拉肯,等.文化研究导论[M].陶东风,和磊,王瑾,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4]王星.百年服饰潮流与世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5]刘再复.他把爱推向每一片绿叶[J].读书,1985(9):35-44.
[6]王克安.近20年刘心武研究述评[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4):97-99.
[7]张颐武.新世纪的中国色彩记忆[A].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文集25:色彩与城市生活[C].中国科协第25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2008.
[8]张颐武.刘心武:面对未来的抉择——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例证[J].文艺争鸣,1994(1):21-27.
【责任编辑:甘海燕】
Changed Love: Narratives of Love in Xinwu Liu’s Early Novels
PENG Chao
(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The narratives of love in Xinwu Liu's early novels in the new period call for true love, trying to break the "Revolution and Love" mode by using the private sphere and giving love subject position. The capital also has a marked impact on love, for dress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material permeating love. The era of global capitalism gradually affects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love, love and marriage are endowed with new meaning, narratives of sex and body emerge.
Love;private-sphere;capital;dress;global-capitalism
2016-04-12
该文受中国留学基金委资助
彭超(1989—),女,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现为美国杜克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7.42
A
1671-9840(2016)03-0062-12
10.16713/j.cnki.65-1269/c.2016.03.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