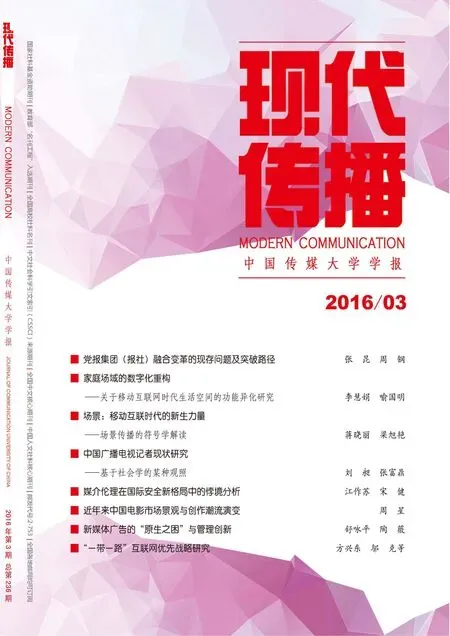“青鸾舞镜”与侯孝贤的双重困境
■ 宋锦轩
“青鸾舞镜”与侯孝贤的双重困境
■ 宋锦轩
在电影《刺客聂隐娘》中,叙事高度节制的侯孝贤详尽讲述了“青鸾舞镜”的典故:“鸾三年不鸣,夫人曰,尝闻鸾见类则鸣,何不悬镜照之,王从其言,鸾睹影悲鸣,冲霄一奋而绝。”伴随着聂母旁白的是一个极尽渲染的抚琴段落。这个段落与影片叙事无关,然而却是一个相当有意味的呈现,侯孝贤显然是用它来隐喻聂隐娘无枝可栖的悲凉,以及侯孝贤自己“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的落寞。2007年完成《红气球》后,侯孝贤蛰伏八年,试图通过《聂隐娘》“冲霄一奋”却遭遇市场冷遇。这个结局可以视作侯孝贤青鸾式的一语成谶。
一、背离观众:类型尝试的取败之因
任何成熟的电影类型都是作者和观众的共同产物,任何成功的类型电影都和该类型的叙事惯例捆绑在一起。侯孝贤选择武侠片这一在中国拥有最广泛观众的电影类型,却背离了这个类型的基本特征:快意恩仇的侠客,黑白分明的正邪对抗,华丽的打斗场面,简洁的线性叙事。当侯孝贤用中国最典型的电影类型把观众招揽到影院后,他们却只看到了无法出手的刺客、正邪难分的人物、浅尝辄止的搏杀和隐匿在风景之后的故事。当观众的期待与影片现实形成巨大的落差时,影片的商业失败就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了。
“类型是基于电影工作者、影评人、观众之间的默契而存在的……观众期待类型的公式,但他们也需要新鲜感。导演可以稍加或大肆修改,但都仍须根据传统来改变。”①类型电影的演进,从来都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观众与作者在规范的镣铐下共舞,偶有新的节奏变化,也要建立在旧有范式的基础之上。以武侠片为例,张彻、胡金铨借鉴日本剑戟片,融入中国传统戏曲的舞蹈性,完成武侠片的第一次革新;徐克则从胡金铨那里汲取造型风格,引入好莱坞的特效手段,快速剪辑节奏,塑造更具喜剧效果的人物,讲述更简练明快的故事,更好地适应了当代观众的娱乐口味,构建了新派武侠的范式;到李安的《卧虎藏龙》,又在保留华丽的打斗场景的前提下,融入了文艺片中细致入微的情感描述。但无论如何革新,作为武侠片的规范:大侠、正邪对立、华丽的动作性场景都得到保留。相比而言,侯孝贤以《刺客聂隐娘》为名,前述三个要素全部抛弃,自然会遇到大众欣赏惯性的沉重打击。
侯孝贤曾以“背对观众”形容自己的创作态度。然而,在类型电影这一需要和观众“共舞”的影片形态里,背对观众演变为远离观众,对着自己的影子效“青鸾舞镜”,必然会遭到观众的遗弃。我们可以说,一面恨无知音,一面对镜独舞,这是侯孝贤的类型尝试遭到市场冷遇的内在原因。
二、远离生活:艺术追求的华丽牢笼
侯粉常以曲高和寡来解释侯式电影的票房失利,但这个“高”也许是艺术上的高妙,也有可能是在艺术的象牙塔内被供的太高,离真实的人间太远。失去了泥土的侯孝贤,自《海上花》始,显然沉浸于纯粹的形式与意境的追求中去了。
侯孝贤多次说:“我要坚持属于我的叙事方式,这方式在古代的《诗经》里,在明志不在故事,世界电影的走向以戏剧性为主,但中国人讲求的不是说故事的form,是抒情言志的form,是意境。”②这话固然没错,但是意境也罢,抒情也罢,所有的形式都跟作者身处的时代以及自己的切身感受相关,《诗经》的吟唱者不会考虑他的form问题,他只是有感于心、发之于声。历代流传下来的经典范式,所容纳展示的情感与意境肯定是那个时代的风潮。诗经楚辞,至汉变为赋,至唐变为诗,至宋元而为词曲,至明清而成小说。每个经典范式里都有其附着的生活源头。
问渠何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最自然的诗意,是在不加修饰的自然呈现中流露,而不是漂浮于表面的刻意营造。侯孝贤早期作品的优势在于对所拍摄人物与生活细节的熟悉,因此故事固然是创作的,然而环境、气氛却洋溢着鲜活的生命气息。
1983年侯孝贤以《风柜来的人》震动影坛,成为台湾电影新浪潮的领军人物之一。整个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期,侯孝贤创作活力迸发,先后完成《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恋恋风尘》,以青少年的视角,审视台湾社会的乡土人情,为华语电影带来一个新的电影角度与表达方式。1989年他通过更加宏大的《悲情城市》,以对台湾社会造成深刻影响的二二八事件为核心,全面展现自1945年以来国民党迁台的历史,直面台湾社会族群撕裂的隐痛,本片为他赢得世界的关注以及殿堂级的荣誉。
侯孝贤带给电影界最大的影响是他独特的电影风格。以长镜头尽量保持时间的自然流程,以大量的全景、远景镜头营造空间的完整。一经一纬编织出的浑然时空保留了生活的本真,在给影片带来质朴气息的同时,也获得了东方特有的含蓄悠远,讲求意境的诗性风格。这与西方电影中强调、冲突,重视对抗本身的奇观叙事形成鲜明的对比,创造出一种新的电影可能性。
侯孝贤并非不明白自己电影的活力之源,他在评价贾樟柯《小武》之后的创作时说:“你想一股脑的把想过的东西全呈现出来,就把人放到一边,专注到空间、形式上去,反而太用力,太着痕迹了。《海上花》之后,我是等人出题来应,应题的意思就是,你不知道你现在想拍什么,也无所谓拍什么,但你有技术在身、累积了非常多的东西,所以人家给你个题目,你就裁剪这个题目。从创作上来讲,这阶段也是蛮有趣的。”③
这是侯孝贤的夫子自道,也是他自《海上花》之后走向自己反面的明证。艺术创作诚然需要娴熟的技巧,需要创造一个独特的形式。但艺术的本质却是去表达创作者对于世界和生命的认识,去呈现自己对于生活抱有的态度和情感。没有后者,创作一个纯粹形式的过程诚然有趣,最后呈现的作品也许华丽精巧,但也只能是工匠奇技淫巧般的炫技。
因此侯孝贤在《刺客聂隐娘》的创作中,尽管于唐代历史典章、生活器具、建筑陈设方面做了细致的功夫,在视听语言上也极尽雕琢,但看此片,却每每让人有鞋底上绣花、窗棱上雕琢的小气。不可否认,电影《刺客聂隐娘》的好处在于斑驳的光影、服饰的华美与场景的考究,但它的好处也止于此。如同脱离了火的烟、不见了菜肴的香,电影影像虽然华丽精致,但却充斥着鸦片般颓败的死亡气息。纵使美,却不复生命本身的活力。被供奉在艺术神殿之上的侯孝贤,以及他穷尽一切努力所创造的独特形式和刻意营造的古代气韵,成为博物馆里冰冷的陈列品,散发着淡淡的腐朽气息。
三、结语:刻意不会成就诗意
重新审视侯孝贤的电影序列,我们或者可以说:从《风柜来的人》到《恋恋风尘》,是侯孝贤汪洋恣肆的青春挥洒,是举手投足佳作天成,是最美的时光;《悲情城市》与《戏梦人生》是他四十不惑的中年,作品严谨恢弘,气魄雄大;而从《海上花》到《刺客聂隐娘》,我们似乎看到人至暮年,试图抓住即逝的生命,沉迷于米粒上雕刻、鼻烟壶上绘画。这可以解读为抗拒创作生命力消退的隐晦折射。
侯孝贤的成就得益于电影中洋溢的独特的东方气质,但这种气质是来源于真实生活的,是有生气的人世气息,而不是固化在文本里的古代想象,更不是博物馆中恒温环境下的陈列品。如果用诗性来概括侯孝贤电影的气质,那这种诗性不是隐于高山深谷的道家逸气,而是植根于民间的强悍生命力。如若脱离了土地,沉浸于文人的小世界,生命力就变成了匠气,诗意自然就变成了刻意。
注释:
① [美]大卫·波德维尔:《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曾伟祯译,世界图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5、376页。
②③ 贾樟柯:《贾想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175页。
淮阴师范学院传媒学院)
【责任编辑:赵 均】
——论女性主义视域下电影《刺客聂隐娘》的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