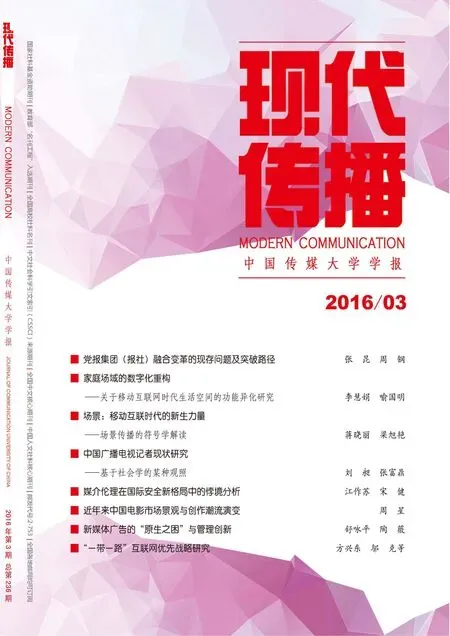华夏舆论传播的概念、历史、形态及特征探析
■ 谢清果 王 昀
华夏舆论传播的概念、历史、形态及特征探析
■ 谢清果 王 昀
华夏舆论传播研究是针对中国古代传统社会舆论传播活动、现象的研究。在长期中央集权体制下,中国古代之舆论一度受上层建筑的影响较大,并在后期集权政治的制度运作中逐渐调整为以上层建筑“舆论监督”为主导的舆论传播模式。伴随封建王朝的兴衰轮替以及传统士族、地主、士大夫、乡绅等不同社会阶层之更迭、介入,舆论生态环境多少呈现出极权政治下的生动面貌。回溯华夏舆论传播,有利于通过历史梳理,进而探究当代中国舆论传播机制是如何成型的。
华夏舆论传播;舆论监督;表现形态;传播机制
一、华夏舆论传播研究的价值、对象及意涵
近年来,伴随新媒体舆论研究的兴起,舆论事件频发,华夏舆论传播研究对于梳理中国当代舆论传播的社会基础和文化背景有着重要的助益。
(一)为何研究华夏舆论传播:“两种范式”之下的提问
依照西方语境,舆论与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一词较为接近。而“公众”与“意见”合为一个术语,往往用来形容在行政领域之外,依社会、经济、政治形势而出现的,影响政治决策的集体性看法(collective judgments)。①因而,舆论通常亦用来反映公众与国家机器之间的互动关系,表达出强烈的政治诉求。
在古典自由主义代表洛克看来,国家是“基于每个人的同意”而组成的共同体,当其作为整体行使权力时,需要经过“大多数人的同意和决定”②。其通过“契约论”明确了舆论的合法化地位,暗示舆论是公众实现言论自由权利的必然产物。而据Noelle-Neumann考证,“公众舆论”(Opinion Publique)一词首次出现于卢梭1744年左右出版的《社会契约论》。③卢梭在书中将舆论推上更为神圣的地位,其强调公众舆论来自理性表达,“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④。
早期启蒙运动者的观点对后世舆论研究的影响相当之大。利用舆论实现市民社会与上层建筑的政治对话,进而维护社会正义,一时之间成为西方舆论研究的主流范式。在被认为是舆论作为独立学科的奠基之作《舆论学》中,李普曼便谈到,因为能综合社会意见从而影响政府意图,舆论故而成为“民主政体中的原动力”⑤。舆论被视为可以成为公众抵抗政治压迫的手段,其相较于暴力而言,是一种理性的社会改良方式。⑥此种范式视域下的舆论成为公民社会自下而上的压力机制,其通过建构社会话语,刺激社会运动,对于公共政策有着显著影响。⑦因而,尽管如哈贝马斯所说,“公众舆论既不受制于公众讨论的规则或其表达形式,也不一定非得关注政治问题或向政治权威发言”⑧。但是,向来的研究实践仍然一直试图将舆论与政治目标协调起来,舆论的被关注焦点始终徘徊于公共领域所发挥的政治功能。
随近现代西方选举制度而兴起的“民意测验”(Public Opinion Research),更强化了舆论研究的政治对话色彩。民意测验与近代资本主义市场需求下诞生的市场调查(Marketing Research)渊源颇深,⑨这一方式较早可以追溯至由美国新闻界发起的模拟投票(Straw Poll)。1824年,美国一家名为Harrisburg Pennsylvanian的报纸通派记者调查、测算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的选民对当年总统候选人的评价,试图了解选民对总统候选人的投票意向。⑩此后,各种民意测验形式蔚然成风、经久不衰。舆论亦与选票意向相联系,成为可以被数据检验而具化的形态。
依照这种“投票箱”式的共同体运作模式,使得全民意志有了表达渠道。社会冲突自身将按规定路线发展,其将“讨论作为行动的开端,并且鼓励采取讨论的方法,然后利用可能存在的自我约束和宽容的传统”。总的来说,舆论固然可以利用公关(public relation)等方式来加以引导,却绝非是可以完全控制的对象。这种“选举舆论”标榜的前提乃是社会政治动力源自民意,“民意,即绝大多数国民的见解和意见,是决定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最后判决”。因而,政治家不得不顾忌公众意见以及舆论情绪,在制订社会政策之时考量舆情意向。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民主式的意见依然存在一些问题。美国学者Buresein曾反思美国社会科学界的民主实证研究,认为过分强调公众意见对于政策变化的影响,使得其他一些影响因素遭到遮蔽。公众舆论对于政府的影响效力,始终存在疑问。而与西方传统自由主义相对应,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体制则运用了另一种舆论传播模式。其中,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的观点被广为引用,“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与一般自由主义有关言论自由或报刊自由的看法不同,此模式的观点在于:“所谓自由的报刊是指它不仅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在此观点下,舆论不仅仅是民众自由意见的表达,亦可以成为国家/政党用以完成其政治目标的手段。其强调了舆论可以被主动控制与建构,并重点关注了媒体在公众舆论与国家意见之间的联结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结构借鉴的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国内舆论传播自然也向其靠拢。在中国语境内部,舆论很多时候不一定指代公众舆论,而与新闻舆论有关,两者在社会意识内有着一定区别。郭镇之即提到,“舆论监督”可能更需中国特色,因为相较于西方守望监视(watch)作用的媒体表达,作为政党“喉舌”的中国媒介更具有“监督”的权力实质。这意味着,媒体在结构上更为接近国家意识形态,其新闻舆论往往带有官方性质。受到传统“开、好、管”方针的影响,国内的新闻批评往往还要配合党的介入与回应。
从传统西方自由主义到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舆论传播模式观念之不同,根植于社会历史渊源与国家体制建设的不同。回溯华夏舆论传播,试图通过历史梳理,探究当代中国舆论传播机制是如何成型的。其至少有助于回答以下问题:
其一,华夏舆论传播的历史进程为何,其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有何关系?
其二,华夏舆论传播有哪些特征,能否通过检视其历史性继承的一部分,进而观照当代中国舆论传播生态?
(二)华夏舆论传播研究现状及概念辨析
据《说文解字》,舆论之“舆”,“车舆也,从车舁声”,始作“车厢”解。《道德经》即有曰,“虽有舟舆,无所乘之”。此处的“舆”,便是车的意思。同时,“舆”又往往和赶车之人、造车之人相联系,指代从事差役工作,身份相对低微之人,如《周礼·考工记·舆人》言“舆人为车”,便是指造车之人。尔后,“舆”的词性逐渐变化,渐渐作“众、多”之解(《广雅》),“舆论”也就被指代为“众人的议论”。因而,胡钰便指出,古时的舆论概念,乃是先有“舆”再有“舆人”,进而演变为“舆人之论”,即“舆论”。从字面上看,“众人之议”的舆论看起来十分接近西方概念中的“公共意见”。不过,古代的“舆论”却通常用以表示处于社会下层的百姓议论,并未将统治阶层纳入考量,带有鲜明的等级色彩。
华夏舆论传播研究,即针对于中国古代传统社会舆论传播活动、现象及其思想积淀的研究,包括经史子集等浩瀚文献中的舆论传播智慧以及五千年文明中各朝代政府的舆论管控与士人、百姓等社会阶级的舆论抗争实践。其主要可包含三个面向:一是舆论的传播主体,即公众的言论发声,就古代中国舆论环境而言,需要尤为关注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二是舆论的接收方,其中往往指代社会上层建筑;三是基于社会整体结构功能变迁,考察古典社会制度与舆论之间的关系。
如陈力丹所言,由于古代社会生活环境封闭而狭窄,舆论的变化通常很小,呈现为僵滞态势,故“传统社会的舆论通常不处于哲人们的主要视野内”。不过,此处所言的却是以古典“舆人之论”为视角之“舆论”。其之所以认为古代舆论不必过分讨论,基本是基于将“舆论”仅仅作为“普通大众的言论”,其前提乃是古代公共领域并未形成,而忽视了古代在上层建筑内部,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社会话语运动。
舆论作为一种活跃的社会现象,反映着人们在不同时代之呼唤,是社会结构变迁之症候,成为感受社会冷暖的“皮肤”。基于此立场,讨论华夏舆论传播,应当结合古代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和历史图景,将舆论纳入社会宏观体系变迁的视野,通过探讨舆论传播之源流,进而解释上层建筑、精英阶层与民间文化之间的互动过程。一如林语堂所声称,关注古代中国舆论如何表达,作者和学士们通过何种形式在专制统治下进行公众批判,有助于讨论在现代语境下,中国未来出现敢言和诚实新闻话语的可能性。
关于华夏舆论传播之论述,散见于各种舆论学、传播学或史学作品。可以看到,其中大部分正是将舆论纳入中国两千年独特的封建帝制情境下进行考察的。而其中,又多以观照西方思想史上“民意”“公众意见”之“舆论”,以近现代意义的民主自由视角来回答中国的古代舆论。这种方式至少在目前看来,依然十分适用。
邵培仁等人认为,中国古代舆论思想有两种最具代表性:一是民本主义舆论观,二是轻言主义舆论观。前者发端于原始公社民主制。张玉霞即以尧舜时代为例,认为此时期“舆论决定社会管理”。《尚书·洪范》有言“汝者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说明普通民众在社会决策中确实占有较高地位。而轻言主义舆论观自秦汉中央集权帝国建立后日盛,此类论述多与君主专制相互捆绑,集中于对封建社会制度方向之分析。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此两种舆论观都基于统治者立场,反映的实际上是上层建筑对于社会舆论的态度。
此外,民本主义舆论观与轻言主义舆论观两者并不一定天然对立,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舆论环境一直由两者混合贯穿的观点可能更为中肯。兰金Rankin便指出,或出于获取信息的需要,或出于对高阶官僚力量的约束,再强力的统治者也需要鼓励批评声音出现。他以清议(Pure Discussion)为例,认为古代中国的清议现象在理论上是公正的、纯粹的意见表达。清议往往出现于社会危机前,在虚弱、焦虑的开明官僚政治体系中进行。这种通过关注于古代历史上特殊舆论活动或舆论形式的研究方式也颇为常见,通常能以点代面地投射出特定时代或阶层的舆论传播结构。
基于上述,考虑舆论之内涵在现代大众传播意义上已有所改变,讨论华夏舆论传播,或可结合现代“公共领域”概念,以不同历史阶段的特殊舆论形态为线索,探讨舆论在古代社会结构之中的影响及其在制度上与现实权力之互动,如此观之,大抵对于当下而言最为有益。
二、华夏舆论传播的历史演变
舆论传播状况与各个朝代的国家言论控制政策有着密切关联。总的来说,政府或积极主动收集舆论、引导舆论,或严格控制甚至打压舆论。无论在哪个朝代的政治生活都不可能脱离舆论,只不过表现为不同历史情境下的政府与社会两股力量的博弈。
(一)先秦以百家争鸣为高峰的言论相对开放时期
相较于秦汉以降的封建集权政治格局,早期古代社会的舆论环境一直为后世所称道。在原始公社民主制下,尧舜时代便设“敢谏之鼓”“诽谤之木”,以作采纳民意之场所。随着氏族部落向奴隶制国家过渡,采风制度作为一种颇具影响的古典舆论形态逐渐流行开来。乐工将采集的民谣收集献给天子,以便让深居宫廷的君王了解天下之事。这些包括舆论意见的民谣通过以《诗经》为代表的典籍让后人广为熟知。又如《尚书·汤誓》所载:“时日曷丧,予及女偕亡!”其语言通俗直白,正是商纣暴政时期,百姓通过民谣抒发的对统治者的愤怒情绪。
至春秋战国时代,社会诸侯割据的多元格局亦造就了较为宽松的舆论语境。这一时期,“国人在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国人的舆论‘谤言’具有相当的威信,很像古希腊罗马城邦中自由民的议论,相对地表现出了古代社会的民主主义”。《左传》载有知名的故事“卫懿公好鹤”,曰:“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余焉能战!’”公众可通过舆论公然抵抗国君的不良行为,当时舆论环境之活跃可见一斑。而“百家争鸣”作为中国历史上极为突出的社会思潮,不仅呈现了上层建筑和士大夫群体之间的多元舆论生态,诸子各家的学术主张亦在很大程度上为后世奠定了舆论传播的学理性基础:一方面,无论是以孔孟为首的儒家民本观念,或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皆在某种程度上侧重于社会舆论之开放;而另一方面,以法家“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篇》)思想为指导,秦孝公首开中国禁书之先河,标志着以传媒管制为手段的舆论管理机制开始成形。
(二)秦汉时期中央集权下的监察制度与士人清议为特征的舆论传播
伴随秦朝大一统政治体系的建立与巩固,中国封建帝制时代宣告来临。在始皇以“焚书坑儒”为标志的思想统一政策下,舆论自由之表达一度被认为遭到极大损害。不过,通过御史监察制和谏议大夫等一系列制度匹配,秦代依然在上层建筑设计了符合集权政治需求的舆论传播渠道。其中,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之一,其职责乃是“典正法度”“举劾非法”(《汉书·百官公卿》)。监察机构的一般官员则被称为“御史”,《通典·职官十四》曰:“秦置监察御史”,设立御史履行朝廷监察职能。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统一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此处的“监”便指地方郡一级政府的御史。汉代则继续继承发扬这种舆论监督机制,汉武帝时期,御史监察制衍化为“刺史制度”,全国分为13部,每部皆设一个刺史对所属郡国实行监察,中央集权程度进一步加强。此外,汉代的谏诤氛围也在统治者的政治制度调控下呈现别样风貌,按照朱传誉的概括,一是“承六国之例,设谏议之官及博士”;二是“常不定期的举召直言进谏之人”,营造了相对良好的舆论环境,使得汉代知识分子能够较为自由地开展政治批评。至汉末,知识分子的舆论传播进一步演变为史上闻名的“清议”。清议的传播主体由士族阶层所担当,其内容往往包含对时政的议论与批评。不过,东汉“党锢之祸”后,社会言论受到极大钳制,清议逐渐蜕变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清谈”。
(三)魏晋南北朝政局动荡下以清谈为形式的舆论传播
一般认为,清谈多涉及黄老之学,乃是魏晋时期知识分子为处理自身与上层建筑之间的敏感关系,所不得已的避祸之法。但实际上,清谈依然多少发挥着社会舆论之作用。《抱朴子·疾谬》即有载:“俗间有戏妇之法……或清谈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此处的清谈便接近于“清议”,其与“峻刑”为代表的正式手段共同发挥着社会控制功能。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格局相对动乱,受制于庞大的士族势力,君权无法得到有效伸展。在松散的政治权力结构下,民间舆论尚可占有一席之地。例如竹林七贤,相聚于竹林,以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玄谈易老庄,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他们对时局的厌恶态度,对政治高压态势的消极抵抗。
(四)隋唐宋时期舆论监督机制进一步完善,兴旺出版事业和活跃的市民生活进一步推动舆论传播
至隋唐再次恢复一统格局,国家舆论监督之权力自然重新上升:一方面,隋朝开辟科举制度,知识分子这一社会舆论主体被进一步纳入政治系统;另一方面,“三省六部”之设立也推动了朝廷舆论监督机制逐步完善。至唐代,御史台成为独立的监察机构,拥有弹劾百官的权力。御史台下属台院、殿院和察院,三院各司其职,标志政权内部已经形成很严密的监察系统。尽管官方的舆论监督占据极为强势之地位,社会舆论作为“双轨”之一依然在民间流行,如隋末一时广为传唱的《无向辽东浪死歌》,便乃是民间所作的政治歌谣,表达着人们对隋政权之不满。不过,这种舆论多在朝代衰亡期出现,民间之舆论诉求与官方之舆论监督随着朝代政权稳定性的变化,处于相互交织与博弈的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隋唐时期,随着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出版领域迎来新的发展面貌,媒体舆论逐渐进入历史视野。唐代政府即有提供给地方官员,以了解中央诏令、信息的邸报。至宋代,传播媒介进一步繁荣,衍生出判报、小报、边报、榜文等多种形式。这些媒介多承载时政消息,虽由官方主导,以官吏为主要受众,其出发点乃是履行朝廷舆论监督之效力。但新闻泄露与私人刻报事件时有发生,客观上促进了整体舆论环境的多元化。因而,为了达成上层建筑之舆论控制,政府亦开始出台相应的新闻检查制度与出版法令,宋代就设所谓“定本誊报”与出版审阅制,即事先对文本内容进行审核,同时对各类出版物有着一系列限制政策。
此一时期,随封建经济之发展,民间舆论也迎来新的转机。唐宋以来,城市化发展迅速。宋代城镇已打破原有的行政区与商业区之界限,在城镇内部,店铺可以随处设置。这种空间布局的变化直接刺激市井文化和市井舆论的繁荣。《东京梦华录》记录当时市井生活之繁荣,“诸酒店必有厅院,廊庑掩映,排列小阁子,吊窗花竹,各垂帘幕,命妓歌笑,各得稳便。”市井之中的酒楼、瓦舍既是百姓文娱之地,亦成为酝酿民间舆论的场所。
在官方层面,宋廷有尊重文人,不杀大臣之意识,这为知识分子争取言论自由,开展舆论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伍伯常亦认为,在文教传统下的宋代,“文人采用非常规的自我表达方式时,只要不过于挑战统治威权或抵触国家政策,一般而言都会得到当政者宽容”。宋代文人,如以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历史名家为代表,皆有谏言范例。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朝廷对言论自由的绝对宽容。宋代已开始出现台谏合一之趋势,即御史台和谏院由各司其职向事权相混转变。御史、谏官都拥有对百官的监察之权,共为“人主之耳目”。沈松勤即指出,台谏惯以“文字罪人”,在朝廷政治纠葛中常被党派策略性运用以制造文字狱,牵制舆论发挥。这种“台谏合一”之做法后来在元代被正式确立,继而成为一种常态的中央监察机制。
(五)元代严控出版物传播以及森严的等级制度使舆论处于高压之下
元代社会的传播语境发生了一些新变化。据朱传誉所考证,元代的邸报已经出现社会新闻。不过,政府对小报之查禁以及出版之压制一度相当严厉,明代陆容在《菽园杂记》中即记载:“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许刻印。”对于出版物之管理,元代既保持着禁令姿态,又试图借助“尊儒崇经”的文治传统消除本身作为“外来政权”之不安。《元史·世祖本纪二》云:“(世祖)敕选儒士编修国史,译写经书,起馆舍,给俸以赡之。”在官刻方面,元朝廷建立了一套严整的刻书出版管理体制,也客观上推动了儒家道统更加深入人心。
在舆论支配方式上,元代吸收了一些蒙古贵族之传统,如改“常朝”为“视朝”,即朝奏的时间、地点与人员并不固定。李治安认为,这体现出“行国”“行殿”等草原习俗被糅进决策活动。值得注意的,他还指出,元朝以降的君臣关系已呈现越来越强烈的尊卑反差。姚燧的《领太史院事杨公神道碑》记载,至元十七年授时历成,负责修历的官员入奏。“方奏,太史臣皆列跪。诏独起司徒(许衡)及公(杨恭懿),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授学汝者。’故终奏皆坐毕其说。亦异礼也。”说明元代御前奏闻时除年老者特许就座外,一般大臣都需要下跪。御前奏闻时与会大臣是立还是跪,折射君臣关系之间有着巨大落差,君权象征地位之拔高隐约暗示出专制深入下舆论自由之艰难。
(六)明清时期政府对精英士人的拉笼与防范手段更加多样,近代意义舆论正在萌芽
按照钱穆的观点,中国真正的皇权独裁专制乃是在明清时期被塑造。明代不设丞相,废“中书省”,六部直辖于天子,君主专制几乎被绝对化。此外,监察官吏倍增,机构重叠。据彭勃考证,明代监察御史“多至一百一十人,近四倍于元,近二十倍于宋,十倍于唐”,社会控制壁垒空前森严。值得注意的是,就文化层面而言,约翰·达德斯(Dardess.J.W.)亦指出,在明代,儒学开始衍变为某种公共服务式的职业认同(public-service profession)。在这种职业认同之中,“忠诚”(loyalty)成为超越其他标准选项的最高信仰。文化精英对朝廷是否忠诚,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在于朝廷能否创造提升儒家学说的环境与机会。精英阶层与接纳它的政权组织之间,存在脆弱的政治承诺或情感依附。在文化精英与国家机器之间的此种微妙关系中,知识分子的舆论发声必然变得慎之又慎。
清代集权专制继续深入,其中央机构大都承袭明制,只是根据自身具体情况略加损益。在舆论控制上,清廷出台了一系列社会保密政策,民众难以接触消息源,舆论表达自然更无从谈起。此外,为预防国家内乱,朝廷亦对舆论表达进行一系列迫害。其一方面开设博学鸿儒科,借以笼络汉族知识分子,一方面进行严格的思想控制,“凡有崇信异端言语者,令加严参问罪。若有私行刊刻者,永行严禁”。相较于始皇时代的焚书,清代之毁书更体现官方意志的计划性与目的性,形成常态的法制化机制,编织出严密的文网控制,建立文化领域的绝对威权。
明清时期的专制威权虽为严厉,但即使在集权政治体系内部,政权存在的固有矛盾也会为舆论营造空间。贺凯(Hucker)以明代政府组织系统为例,认为古代中国的政府系统始终存在三种矛盾:“内廷”(inner court)与“外廷”(outer court)之间的矛盾,“集权”(centralizing)与“放权”(decentralizing)之间的矛盾,军权官僚(military bureaucracy)与市民官僚(civil bureaucracy)之间的矛盾。不过,需要指出,此种矛盾冲突下所释放的舆论张力,基本只能徘徊在上层建筑本身,舆论往往只是被权力所有者策略性地运用从而完成其政治意图,民间舆论之自由度其实依然相当有限。
到明代晚期和清代晚期,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国人睁眼看世界,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一批传统知识分子向近代转型,争取言论自由的努力,不仅体现在对传统经典的重新诠释,甚至发扬出民主与科学的因子,而且直接借助近代报刊展开舆论攻势。统治阶级内部洋务派积极回应,试图推动政府自身的改良,模仿西方制度,外部则有诸如“公车上书”事件,以及维新时期和辛亥革命时期报刊的舆论动员都史无前例的剧烈。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在新形势下传统舆论斗争向近代舆论抗争的转型。
总而言之,古代舆论环境一直处于尴尬境地,这种尴尬与上层建筑的舆论观息息相关:一方面,统治者很早便警惕到舆论传播之力量。在强调道德秩序的中国,众人之议似乎很容易招致“圣人”身份的破坏与污点。因而,历代王朝都实行有对舆论的控制措施,其中相当一部分都以法律的形式被明确下来;另一方面,出于维系社会结构之需要,统治者又试图开辟一些舆论渠道用以缓解社会压力,不过,这些渠道毕竟始终被掌握在王权绝对“可控”的范围之内。随着后期极权政治不断加强,至清初乾隆时代,“私”的范围已经被成功由儒家精英向君主体制转移,“皇帝以欧洲历代专制君主所无法相比的方式宰制了中央帝国”,君主成为几乎所有社会资源的中心。中国舆论环境也就由此进入一种无可奈何的喑哑状态。
三、华夏舆论传播的主要形态与历史特征
华夏舆论传播士人群体常以讽谏为主要表现形态,而民间民意常以歌谣等形式表达,当然,士人群体的舆论对象以国事为主,而民间民意对象则以民生为主,两者彼此呼应。毕竟有担当的士人总有“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感。
(一)华夏舆论传播的主要表现形态
古代中国之舆论环境由不同社会力量所共同塑造:一方面,中央集权体制下,君主执政开明与否似乎对于社会舆论影响显著;另一方面,伴随封建王朝的兴衰轮替,伴随着传统士族、地主、士大夫、乡绅等不同社会阶层之更迭、介入,舆论生态环境呈现极权政治下的生动面貌。
其一,言谏制度。中国关于“谏”的传播艺术由来已久,《周礼·司谏》曰:“谏,犹正也。以道正人行。”又《周礼·地官·保氏》言:“保氏掌谏王恶”。“谏”一开始便有指正过失之意,其中尤以君主尊长为对象。秦始皇时期即设有言谏制度,用以“匡正君主,谏诤得失”。《史记·陈涉世家》即载:“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而自隋唐开始,随着三省六部、一台九寺政治体制的确立,社会监察制度与言谏制度的配合已经趋于完善。言谏制度作为一种合法的舆论形式,乃“专制时代不可多得的舆论力量”。同时,言谏制度下亦有诸多极富特色的变体,如“讽谏”,多以文学性的书写方式出现,既是个体说服艺术的体现,又代表“某种社会阶级的发声,某种文化习染的投影”;又如官方所塑造的,君臣集中讨论的“朝议制度”,甚至于包括向来被民间故事所称道的“微服私访”。不过,总的来说,其毕竟是统治者自上而下所缔造的社会“安全阀”,受上层建筑之政治风气影响较大,其实际效用有待斟酌。
其二,出版舆论。作为较为大众化的传播方式,古代出版物往往由官方所主导。无论是官刻典籍,还是官报、官榜等,都是朝廷通过媒介管制,使之按照政治意图进行文化信息选择与引导。不过,游彪以宋代邸报为例,认为尽管邸报以传达政务为令,扮演着朝廷“传声筒”之角色,但仍时常出现指名道姓的时政批评文字。这说明在此时期,媒介就作为官方喉舌,发挥着舆论监督的职能。此外,民间出版也发挥着一定舆论功能。宋元时期即有民间小报、小本的新闻传播活动,其内容多是关于朝廷政事,在市场广为流通。《元史》便有禁止“条画民间辄刻小本卖于市”的记载。不过,在封建政权的言禁之令下,这些民间出版物的生存与发展都较为困难。
其三,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城镇舆论。封建经济的发展,手工业基础扩大以及拥有一定财富和土地的士绅阶层之聚集为知识分子开展舆论活动奠定了前提基础,其中以“清议”“清谈”为代表。这些城镇舆论的开展一般拥有相对独立的言论场所,知识分子或通过学理对话影射政见、社会观点,或通过诗词歌赋抒发胸臆,体现了早期公共传播之雏形。此类舆论的代表场所如汉武帝时期设立的太学。尤其在东汉朱穆、皇甫规事件中,太学在学生运动下成为舆论风暴中心,一时之间,“太学风潮”影响颇巨。不过,随着后期科举制出现以及官僚政治体制逐步深入,知识分子进一步被上层建筑收编。在极权政治的“禁言令”下,人们一般不被允许私下集会,城镇舆论的力量也就大为淡化。
其四,民间歌谚。按照林语堂的说法,公众批判以诗歌体裁发端而非散文体裁。普通百姓利用歌谣谚语这一口语传播形式对统治阶层发表舆论意见的现象在古代中国并不少见。只不过,这一事实“在人民对其统治阶层表面的驯服下经常被掩盖起来。”民间歌谚在早期采风制度下的夏周就已经颇为普遍,这一舆论传播方式后来在封建集权时代依然得以延续。《史记·项羽本纪》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后汉书·皇甫嵩传》亦记载张角黄巾起义时,为鼓动反对朝廷的舆论所制造的民谣:“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可见,这种歌谚舆论常常在社会动乱时期被人为“炮制”,为“蓄势”某一政权营造合法化空间。
(二)“舆论监督”之渊源:华夏舆论传播的历史特征
舆论在中国古典语境中,向来拥有很高地位。在较早将“舆”“论”两字并作一词的《三国志·王朗传》中便有记录,“设(孙权)其傲狠,殊无入志,惧彼舆论之未畅者,并怀伊邑。”北宋苏舜钦亦在《诣匦疏》中指出,“朝廷已然之失,则听舆论而有闻焉。”这说明社会舆论对于上层建筑的政治决策确实有着一定影响。
不过,与源自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公众意见”迥异,在公共领域始终缺席的情况下,中国古代之“舆论”几乎很少出现作为“私人”概念的利益诉求。此种现象的原因固然作用复杂,但往往与农业经济、封建宗法制下的社会共同体联结方式有关:作为个体的自我既无法在经济上实现独立,更无法摆脱家天下的法律与道德契约。哈利(Harry)关于晚明东林党的研究可以作为上述观点之佐证。他认为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舆论往往导致派系之争,真正公共领域意义上的“私人”(private people)无法达成话语权的实现。并且,这些知识精英的舆论运动往往建立在对商业原则进行抵抗的基础之上,并未对商品经济表示有多少欢迎。知识分子的种种舆论活动,实际上乃是对自身士绅身份(gentry identity)的重构以及士绅原则(gentry rule)的维系。
有意思的是,如Cho所指出,舆论在古代中国还成为与“个人修养”(personal cultivation)相联系的存在,“公共意见”被作为一种个人修养的规范用以服务社会控制,这种社会控制包含三个层次——普通民众、统治者和社会政治系统。这意味着舆论与传统道德秩序的深刻捆绑:一方面,就个体而言,传播者同时纠结于“慎言”的君子道德暗示以及士大夫历来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矛盾之中。因此,传统知识分子对舆论的使用其实十分慎重。而亦是出于对“道德”的坚守,古典舆论环境甚至推动造就了一种独特的以“不言”为表态的舆论方式,即隐士传统(eremitic tradition)的出现——隐士脱离世俗乃是为了超越世俗,从而表达他们自身的一种完美主义情结。而另一方面,对于统治者或者政治系统而言,舆论很可能会在对道德系统的非议基础上,进而导致政权体系的崩坏。因为与西方哲学视角所强调“每个人通过道德代理的所作所为”中的“道德”(moral)不同,中国传统的“道德”概念常常会归咎于“社会共同体做了什么”,在讲究“圣人德治”的君主体制下,社会共同体的“道德失格”很容易延伸到君主的“执政失格”,影响政权根基的稳定。按照Reed的观点,宋代以来的“新儒学”(Neo-Confucian orthodoxy)确立了政治权威是“圣人”的特权,官员的个人修行品质与政治等级挂钩。这就规定了一种明确的社会政治秩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高阶位的执政者一直受到“圣人”教条原则的约束,这也在客观上导致了其面临的道德压力以及对舆论非议的恐慌。可以说,古代社会后期舆论压制程度之不断上升,与此不无关系。
正是基于舆论这种巨大而潜在的政治威胁,在社会抗争时期,舆论经常被地方军阀或起义领袖主动建构用以破坏现有秩序的合法性。三国时代,陈琳在《为袁绍檄豫州文》中,便是一开始先否定曹操一族的道德优越,意在“布告天下,咸使知圣朝有拘逼之难”,从而为战争制造舆论。与之异曲同工,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亦是以武氏自身经历为引,进而验证政权的非法,其“移檄州郡,咸使知闻”的舆论目的显而易见。面对古代社会“君君臣臣”的深刻观念,比起直接向君主王朝进行抗争诉求,上述舆论手段看起来或许更加行之有效。
大体而言,相较于在社会动荡时期,直接面对上层建筑的“抗争舆论”,在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传统中国,舆论很少被用以实现日常生活中的“私人”利益诉求。在以“忠孝”为价值尺度的社会认证体系内,个人的利益和需求被认为不符合“君子之道”。并且,传统社会自有一套建立在“人情”与“关系”之上的传播系统,此种系统弥补了舆论之缺席,成为用以协调、解决利益关系的常态。乌特Utter在研究古代中国人的诉讼观念时也发现,中国人平日总是尽量回避打官司,对私人权益的重视程度并不高。他将这种现象归结于三个因素:孔孟之道,法治信仰的缺乏以及强调小群体的社会共同体防御系统。因而,强调公众意见的“舆人之论”其在“私域”的范围实则影响有限,反而是作为官方权力的“舆论监督”占据了封建王朝舆论传播的主流地位。
这种“舆论监督”的社会控制系统在始皇时代就已经呈现设计雏形:一方面,在民间开展大规模的社会言禁运动,另一方面,则通过御史监察制度等防止官员玩忽职守,即似乎试图依赖对民间的“绝对控制”与上层建筑的“相对监督”来稳定政权。此后,虽然王朝历经更改,但这种社会控制模式的本质和功能都未有变化。并且,还被通过进一步的制度建构所完善修补。威尔金森(Wilkinson)曾从中国古代教育出发,认为儒家道统的传统教育体系吸收并改造了原本属于“非精英个体”(non-elite individuals)的人们,强化了介于公共领袖和社会高阶地位之间的双向联结方式。魏特夫也以“一夫多妻制”为例,探讨了东方专制主义的制度。其认为“一夫多妻制”能够使得君主利用独特机会使自己的血亲/姻亲获得显要的社会地位。这种以亲属为基础的等级附属关系,使得相当大一部分士族阶层被笼络于国家政治机器之中。上述研究都表明,古代社会通过制度运作团结了一批为数可观的权力精英,这些人共同构成舆论监督的实质主导者,权力共同体由此凝结。因而,舆论,在中国历史中向来就被作为官僚政治中的精英意见(elite opinion)而存在。这支以君主为核心,网络复杂的上层精英意见队伍,既保证着社会有效信息之流通与舆论控制,也共同支撑起了庞大中央帝国的系统运作。
总而言之,在梳理华夏舆论传播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传统中国概念中的“舆论”与西方哲学自启蒙运动以来奉为圭臬的“舆论”(或“公众意见”)相比,两者在内涵上呈现出一定区分:西方所谓的“舆论”往往混合了关于自由、民主、法治、理性等诸多概念,是近现代公共领域意义上的观念集合体。因而,这种视野下的舆论十分注重“私人”利益的实现,其讨论舆论与政治机器之间的制约关系,根本上乃是为实现“私域”利益不受侵犯,实现“自由人”的权利。而古代中国舆论往往强调对一个社会系统的道德评价,这种舆论对于现实政权的实质威胁更大,历来为统治者所恐慌,社会舆论政策之实施也多偏向为注重“防御”而非“疏导”。在整个历史发展时期,舆论皆受上层建筑的影响较大,并在后期集权政治的制度运作中逐渐调整为以上层建筑“舆论监督”为主导的舆论传播模式。这种舆论传播模式在近现代中国舆论环境中得到一定继承,但是,与之显著不同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私有财产下独立“自由人”的出现,传统合并在“家天下”理念中的个体被分离出来。同时,现代意义上公共领域的成形和民主力量的强化,使得社会内部,尤其是中下层民众关于具体利益诉求的舆论声音日益扩大,这是古代社会所难以想象的局面,也是当代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社会进程中所面对的挑战、抉择与希望。
注释:
① Price,V.:PublicOpinion,NewburyPark.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1992,8.
②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9-60页。
③ Noelle-Neumann,E..TheSpiralofSilence:PublicOpinion-OurSocialSkin.Chicago,Illinoi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
④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页。
⑤ [美]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林珊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系1984年版,第197页。
⑥ [英]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何慕李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67-292页。
⑦ Burnstein,P.:TheImpactofPublicOpiniononPublicPolicy:AReviewandanAgenda.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2003,56(1): 29-40.
⑧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 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⑨ Crossley,A.M.:EarlyDaysofPublicOpinionResearch,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1957,Vol.21,No.1: 159.
⑩ Cantril,A.H.:ThePressandthePollster,TheAnnalsoftheAmericanAcademyofPoliticalandSocialScience.AAPSS,1976:46.
(作者谢清果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昀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毓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海峡两岸数字公共领域与文化认同研究”(项目编号:15BXW060)、厦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项目“中国话语权研究”(项目编号:2011-2021)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