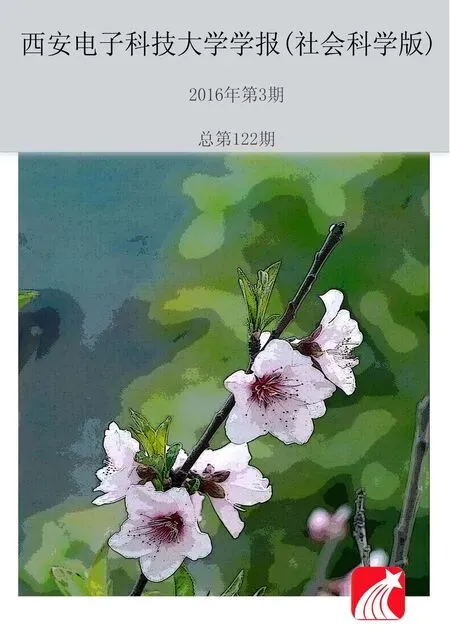审判中心改革背景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落实与完善
——基于2013年来486份刑事判决书的实证考察
张健(江苏大学 文法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法学
审判中心改革背景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落实与完善
——基于2013年来486份刑事判决书的实证考察
张健
(江苏大学 文法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完善证据规则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关键。通过对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文本规定与司法实践考察,发现非法排除规则在启动门槛、启动方式、证明标准、庭前会议与排除效果等方面存在司法与立法相背离的严重问题。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与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质上相辅相成。在审判中心改革背景下推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落实,应强化侦查、公诉服务审判的意识,实现审判对侦查、公诉的有效制约;构建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新型检律协作关系;消解法律治理化的政法传统,为刑事司法场域独立运行提供条件。
非法证据排除;以审判为中心;证据;证据规则
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标之后,“以审判为中心”成了实务界与理论界炙手可热的话题。刑事证据是诉讼的灵魂,证据制度的完善是实现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前提。如果把“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目标比作高耸入云的大厦,那么证据规则的完善则是建构大厦的基石。证据裁判规则作为现代刑事司法的核心内容,体现了现代法治与技术理性对刑事司法的要求。可以说,完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抓住“严格证据标准”这个关键,就抓住了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牛鼻子”,以此推动刑事司法活动整体质量的提升。本文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证研究入手,对其作出讨论。
2010年,《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此后,《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为2012年《刑事诉讼法》所吸收。《刑事诉讼法》自2013年1月1日起实施至今已逾3年,在这期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满足了制度预期?证据裁判规则是否需要进一步完善?这有待于司法实践的进一步检验。笔者以“中国裁判文书网”自2013年1月1日起《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以后至2015年12 月31日发布的判决书为标准,选取最高人民法院遴选的精选案例为本文的研究对象。自2013年到2015年整整3年间,在全国范围内涉及非法证据排除案件共计486起。这些案件涵盖了我国东、中、西部二十几个省市法院,可以说,在地域覆盖上,样本具有代表性。因此,以此样本来观察我国法院 2013年以来在常规的刑事一审、二审案件的审判中,贯彻落实《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况具有可行性。
一、实证考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几近“名存实亡”
(一)启动门槛:高申请率与低启动率
2010年《非法证据排除规定》、2013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以后,司法实务界普遍反映,被告人当庭“翻供”现象激增,辩方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的比率明显上升①。尽管“翻供”现象说明被告人存在侥幸心理,但毋庸置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为当事人辩护提供了契机。不过,与此相对应,法庭审查后真正开启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案件却极少。486样本案件中,面对当事人的申请,有53起案件法院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比例为10.9%。
众所周知,由于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多发生在秘密性很强的侦查程序中,往往难以查实和证明,所以,《刑事诉讼法》将证明证据合法性的举证责任交由控方来承担。要求被告人只需提供非法证据异议的相关线索或证据即可。这是一种标准相当低的初步责任。它要求辩方提供“相关线索和材料”。“只要被告人或者其辩护人提供了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等细节信息,以使法官形成非法取证的合理怀疑,法院就应当开启非法证据排除程序”[1]。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法院的处理方式却极不统一。有的案件并没有出现举证责任倒置,而是法官要求被告方承担举证责任,并要证明到“查证属实”的程度。比如陈建龙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一案中,辩护人提出侦查机关曾对陈建龙采用威胁、引诱、欺骗以及指供等非法手段取证,陈建龙的口供应予排除的辩护意见,但法官认为:“经审理认为,辩护人所提上述非法手段并无实质性证据,且均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的条件,于法无据,不予采纳”②。有的则是用侦查部门出具的一纸书面说明来否定刑讯逼供存在,比如,苏士沧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判决书写道:“公安机关对其讯问是依法进行的,无非法证据排除之情形。最终被告人的翻供以无法查实为由不予认定”③。
从判决书和裁定书的内容来看,在评价上法官明显倾向于否定非法取证的事由,但对于为何否定辩护意见,判决书或者裁定书中并没有记载更为详细的理由说明,甚至根本就不加以说明。在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现象是被告人或辩护律师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法官往往采取了近乎无视的态度,以“不要再纠缠这个问题了”草草收场。
(二)启动方式:极高的依申请率与畸低的依职权率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在非法证据排除启动方式上,可以分为依职权启动和依申请启动两种。前者要求审判机关在庭审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依职权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后者是辩方有权申请审判机关依法予以排除[2]。从立法上来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方式是比较广泛和多样的,然而,实践中,审判机关依职权启动的情况极为少见。486起案件中,仅有8起案件是法院依职权启动,比例仅仅为1.6%。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基本上还是依靠当事人或者其辩护人的申请,甚至找不到法院主动排除非法证据的典型案例。
我们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非法证据的认定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法官在中立、保守的情况下,当事人如果不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法官一般不会主动认为证据的取得达到了严重影响人权或者司法公正的程度。另一方面,基于“案多人少”、案件审理效率及处理难度等功利因素考虑,法官也不希望开启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给案件的审理带来麻烦。其中,后者是依职权启动难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立法文本已经规定了法院的告知义务,以保障被追诉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知情权[3]。但是,从486件样本看,没有一起案件审判人员对被告人的此项权利进行告知。非法证据排除权是被告人的一项重要权利。法院在诉讼程序启动之初告知当事人有利于督促其行使该权利,尽早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但法院对此规定置若罔闻。对于此问题,法院有自身的考虑——一旦案件开启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将导致案件庭审时间延长、重心偏移。并且,在有些案件中,辩护律师不是一次性全部提出线索和材料,而是不断提出新事实和新证据,要求法官排除有关证据,使庭审一拖再拖。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进入正式的庭审环节对庭审造成了较大的冲击。比如被誉为“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的章国锡案,案件在一审时,法庭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此案经过了四次庭审。再比如广东佛山程捷职务侵占案,法院开启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以后,该案审理经过多次休庭、开庭,审理长达八个月④。这就使得法院要么不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要么开启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庭审就面临重心偏离、案件审判效率低下的窘境,所以,法院主动依职权审理的模式遭遇了严重的水土不服。
(三)证明标准与证明方法:立法高标准与实践低执行
举证责任分配的本质是实体权的合理配置及司法正义的实现问题。考虑到控辩双方自身取证能力的差异,立法对控方科以更多的诉讼举证义务。《非法证据排除规定》首次吸收了“排除合理怀疑”,并将其作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标准。“立法上明确了最为严格的证据标准:控方提出的证据必须达到确实、充分,以使法庭确信该证据确系合法取得的程度”[4]。控方不举证或者举证不力而达不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时,则应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
与此同时,《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控方证明其证据合法的证据包括同步录音录像、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健康证明与加盖公章的情况说明四种。其中,原始的同步录音录像被公认为最具有证明力。但在司法实践中,控方在证据方法的使用上明显存在着主动性和选择性。关于提供同步录音录像,在486起案件中,提供录音录像的有57件,占到11.7%。这57起案件一般是涉及死刑、无期徒刑的重要案件或贪污受贿类案件。关于讯问人出庭,在总数为486件案件中仅仅有3起案件讯问人员出庭作证,比例为0.6%。关于健康证明,这也是实践中控方应对非法讯问抗辩的常用方法。其中,控方提供体检健康证明的有280件。关于加盖公章的“情况说明”,使用最多,达324起,比重为66.7%。关于“情况说明”,立法之前就有学者猛烈批评,“此种完全不符合法定证据形式的‘非驴非马式’的材料根本不能具有证据资格”[5]。因为加盖公章的“情况说明”不仅在证据证明力上无力,而且回避了讯问人员亲自出庭作证的尴尬。这在相当程度上助长了控方滥用“情况说明”取代法定证据形式的风气。
实践中,法院也一再容忍了控方在证据方法使用上的选择。毕竟,检察机关向法庭提交全程录音录像并不是法律的强制性义务。如果控方不愿提供录音录像资料,法院也置若罔闻,明显偏袒公诉机关。对此,辩方更是无能为力——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大大缩水。控辩双方依旧在讯问笔录上做文章,庭审基本以走过场的方式收场了。
(四)启动时间:法庭审理阶段高与庭前会议低
非法证据排除作为庭前会议的重要内容,既涉及到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又关系到庭审的效率与质量。2012年《刑事诉讼法》要求被告方尽量在开庭前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并将此申请作为启动庭前会议的充分条件[6]。学界对此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认为法院有了庭前解决非法证据排除的空间。毕竟,不具备准入资格的非法证据进入了审判阶段,会使法官形成心理预断,影响裁判者自由心证。庭前会议阶段排除非法证据,也有利于提高庭审效率,节约司法资源[7]。
但统计显示,关于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时间,审判阶段远远多于庭前会议。庭前会议提出排除申请的比例极小,为7起,仅为1.44%。也就是说,在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提出的时间上,有小部分案件是由辩护方在起诉书副本送达之后,开庭之前提出,但绝大多数案件是在法庭审理中提出。我们认为,庭前会议申请率过低主要是两个原因。其一,在庭前会议中,控方撤回了证据,或者法院通过“做工作”使被告人撤回了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判决书对此没有记载;其二,也即最主要的,一些辩护律师基于辩护策略的考虑,为了防止公诉机关提前有所防备,会选择在庭审时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一方面拖延审理时间,一方面给公诉机关的反击增加难度。
立法为提高庭审效率,将非法证据排除设立在庭前会议。但为功利计,辩方将非法证据程序选择在了审判阶段。庭审时的非法证据审查直接影响到实体裁判结果。这既给法院的审理带来巨大的压力,也会使实体审查的法官先入为主,被告要承担极为繁重和程度较高的证明责任也难以得到法官的支持,导致庭审的变数增加,大大降低了庭审活动的效率。
(五)排除效果:高申请率与低排除率
53起开启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案件中,只有8起排除了非法证据。比例为15.1%,占样本总量的1.9%。非法证据成功排除案例极少,并且没有一起案件因为非法证据而全案推翻或者全案做无罪、从无处理。也就是说,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不仅开启难,而且排除效果更是差强人意——非法证据排除在司法实践中“几近沉睡”。上文提到的章国锡受贿案一案,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法院一审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采纳被告人章国锡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侦查机关违法获取章国锡审判前有罪供述的意见并对该证据予以排除。但是,该案二审出现“惊天逆转”。二审法院断然否决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判处章国锡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再比如轰动一时的樊奇杭案件,当事人庭审时拿出了被殴打染血的血衣,身上多处明显瘀伤,但是最高人民法院最终也没有启动证据审查程序[8]。
非法证据排除立法之目的在于捍卫国家刑事追诉的程序合法性,在于保障被追诉人的人权。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被架空。立法文本中规定的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在实际上得不到执行。特别是在基层法院,审判机关顾虑重重,因为基层法院审理的案件不涉及生杀予夺,被告人获取非监禁刑的可能性又很大,存在非法证据的案件也往往不容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但宣告无罪和撤诉对公、检机关的绩效考核影响甚大,基层法院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更是稀少。所以,面对被告人庭审时翻供多、律师对证据合法性质疑多、法庭对证据合法性调查多排除的实例少的难题,就必须解决法院“无法排”、“不敢排”、“不愿排”的难题。
二、以审判中心改革落实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上文的实证研究表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遭遇到近乎悲观的命运——尽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立法文本上确立下来,但其实施效果却不尽人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几近沉睡。成功案例寥寥无几。这其中固然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模式、运行设计、标准制定、程序安排等因素相关,但更为重要的是立法之外的环境因素,尤其目前的刑事诉讼构造使然。
(一)强化侦查、公诉服务审判的意识,实现审判对侦查、公诉的有效制约
要走出非法证据排除难的困境,就要建立科学的刑事诉讼结构,落实以审判为中心。在现代化法治国家,尽管存在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模式区别,但其诉讼构造都有一个相同之处,即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构造。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经历了数次修改,但很少涉及到对纵向诉讼结构的改革,要真正实现以审判为中心,关键在于重新配置、调整公检法在刑事诉讼中的关系,这是以审判为中心的根本保障。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视角下,在纵向的诉讼结构中,应该形成以“审判”为中心,通过审判来规范和限制审前程序,防止侦查权的滥用和遏制非法取证等程序性违法,协调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和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关系。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构造“都必须由司法机构通过亲自聆听的方式作出裁判,而且裁判具有最终的权威性”[9]。以审判为中心就是树立司法权威,实现庭审实证化。改革应该选择以审判工作中的庭审为重心,并作为改革的突破口,逐步过渡到以审判为中心,使得法官在面对非法证据的时候敢于排除。
落实审判中心,必须保证审判活动以证据为中心展开,侦查起诉机关制作的案卷不应对法官裁决产生决定性影响,相反,侦查起诉机关要根据庭审的需要准备证据材料。这包括人证、物证在内的各类证据都在法庭得到充分展示。在控辩审三方均在场的情况下,接受以言词辩论方式进行的质证。如此,法官才会对证据形成自己的判断,而不必受侦查机关与起诉机关案卷意见的约束。不难看出,排除非法证据在本质上是审判权对追诉权制约,是司法权力对政府权力的程序性制约。综上,明确审前证据收集的唯一目的是服务审判,在证据的实体内容和程序方面都应充分考虑法庭审判的要求。这就要求公诉部门应树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将庭审前所有准备活动都集中到“审判”的这一目标上来,切实提高公诉质量。
当然,在法律治理化的背景下,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是一场事关司法机关权力再分配乃至诉讼程序重构的革命性变革。这一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的成功依赖于宏观权力架构的改革,配套制度的跟进。否则,仅由法院倡导如同“孤军深入”,战略上被动且战术上亦难以为继[10]。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改革缺少任何一方努力,改革都可能失败。长期以来,我国侦查工作、审查起诉工作与审判相对独立,此一诉讼模式可以称为诉讼阶段论。诉讼阶段论导致侦查、公诉机关产生程序自控与自我中心意识,侦查与审查起诉服务审判的观念不强。但从司法规律上看,侦查取证和审查起诉作为审前程序只是审判的准备程序,所以,必须强化侦查机关与公诉机关面向审判、服务审判的意识,有必要在公安、检察机关普及一些基本的程序法知识。突出庭审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的决定性作用,使法官能够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到疑罪从无。
(二)构建以人权保障为目的的新型检律协作关系
辩护权理论根基之一就是以辩护权制约公诉权,并对法官的司法裁断施加积极的影响。统计发现,8起非法证据排除成功的案件的辩护效果远好于其他案件。这里以唐友用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为例分析。该案被告人唐友用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唐友用在侦查阶段受到刑讯逼供,被告人唐友用没有贩卖毒品,辩护人申请进行非法证据排除。经过辩护人充分辩护以后,法院认为:“被告人唐友用认为腰部骨折系在审讯期间被审讯人员坐压所致,是审讯期间造成的新伤而不是陈旧伤;眼部青紫系被审讯人员用鞋底殴打所致。辩护人认为,从审讯录像上看,审讯人员对被告人唐友用连续审讯十七八个小时未让其休息,审讯过程中有用脚踩搓被告人唐友用脚等行为,被告人唐友用的骨折伤和眼部青紫不排除是审讯期间所造成,故对被告人唐友用的有罪供述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不应作为有罪证据采用。根据公诉机关所举上述证据以及本院所调查核实的证据,不能排除侦查机关在审讯期间以非法方法获取被告人唐友用有罪供述的可能性,故对被告人唐友用的有罪供述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不予采用。辩护人就此提出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⑤。这是486份样本案件中最典型的一份成功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件。
在8起非法证据排除成功的案件中,辩护人都做了充分的辩护意见。这说明被告人辩护权保障越充分,辩护律师发挥的作用就越大,庭审中的举证、质证过程就会越规范。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被告人辩护权缺乏保障,律师阅卷权保障、被告人质证权保障、法律援助制度等直接关系到被告人辩护权实现的制度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当事人往往无法充分行使其辩护权利。这导致庭审的质证环节无法充分开展,非法排除程序难以深入,最终影响了证据裁判原则的实现。
审判中心改革要求庭审活动实质化,使庭审落地。而庭审实质化的前提是要确保控辩双方在庭审中保持实质平等。律师在以审判为中心诉讼改革中承担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律师的有效参与与权利的充分实现与否直接关系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落实。完成“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目标,就要提高律师地位,落实证人出庭制度,充分发挥刑事辩护律师在庭审中的作用,确保法庭质证不流于形式。让律师进行充分质证与辩论,实现控辩双方的均衡对抗。基于司法主体性理念,要求在刑事司法设计和运作中,必须合理配置控辩双方的权利,对于控方而言,应强化其当事人地位;对于辩方而言,要加强其辩护权等诉讼权利的保障。赋予辩方完整的主体性权利与对抗机会,使控辩双方在平等武装的前提下相互质证与反驳。这是基于程序正义的设置,也是控辩关系理想模式建构的基础观念[11]。同时,应该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强化辩护律师维护特殊群体利益的作用,确保被告人及时获得辩护人帮助。建立辩护意见回应机制,切实尊重辩护律师辩护行为。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具体到非法证据排除方面,则应重视法官的裁判文书说理工作,杜绝裁判文书“语焉不详”、回避辩护意见、回避证据争议问题的情形。公诉人应当摒弃陈旧理念,主动增进与律师的协作理解,和律师构建一种新型平等协作化的检律关系。
(三)消解法律治理化的政法传统,为刑事司法场域独立运行提供条件
从一定意义上讲,立法文本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法治图景,其核心在于程序正义与保障人权;然而,目前刑事司法体制依旧是强调国家权力优先的现实图景。非法排除程序开启以后,由司法机关通过自我否定排除非法证据,无疑是与虎谋皮,因为这涉及到了司法体制的根本改造。理想的司法场域是一个闭合、自洽空间。然而,现实中的刑事司法场域则受政治场域、社会场域的影响而运作异化乃至扭曲。法官的司法裁判不再是在现有社会条件与制度环境下保持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统一,而是整合了各种因素、带有机会主义的考虑与妥协;法官司法裁判的目标也不再是单纯地追求公平与正义,而是服从社会治理和社会稳定大局的要求。法官作出裁决的依据不再仅仅是既有的法律法规,这其中还夹杂了各种力量的影响其中的“潜规则”,比如政法委的决定、服务大局的考量、法官对于自身升迁和政治前途的考虑、案件裁判之后的社会影响、法院的形象建设、媒体的曝光等等。
并且,高发的刑事案件客观上削弱了法院非法证据排除的动力。正处于经济与社会转型的中国,其社会矛盾呈现多发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从最高人民法院近五年工作报告中所得数据看,刑事案件数量呈明显增长态势,可以预见,该增长态势未来将长期存在。在司法机关被定为于“社会治理工具”的前提下,法官就不再是中立的裁判者,而是代表国家公权力打击犯罪。它成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的管理者,其践行的是权力角色。即法律治理化的政法传统是导致非法证据排除难的根本原因⑥。
刑事案件发生后对政权建设合法性构成的挑战迫切需要刑事审判加以回应,权威弱化后的治理压力是错案接连发生的深层动因。法律治理化背后的真正逻辑是对政权合法化建设的回应。打击刑事犯罪与保障程序正义、避免冤假错案关系此消彼长。一方面,严重的刑事案件对公众的安全感和社会秩序带来极大的破坏。它们往往也是普通公众最关心的案件。老百姓对司法公信力的最直观感受就是这些社会影响力较大的标志性案件。如果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尽管为数不多,但其影响力会被无限放大。当前执政党强调打击犯罪,强调命案必破,强调法律治理化的政法传统以及其对司法场域强有力的影响是在回应社会秩序安定的诉求,也是对公众对整个政权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的回应,进而及时回应了政权合法性的质疑[12]。司法政治化是为了保证司法在维稳政治的统领之下服务于国家的中心工作,法律治理化背后的法律工具理论也就成为了迅速扭转某一特定地区社会治安面貌、打击违法犯罪分子的有效手段。法院坚持程序正义与其承担的“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责相违背。法官坚持排除非法证据,往往遭受“打击犯罪不力”的质疑。
然而,另一方面,法律治理化对司法场域带来的影响导致法官不敢排除非法证据,刑事司法脱离其自身的运作逻辑进而诱发冤假错案发生却大大破坏了司法的公信力,也从根本上动摇了民众对司法的信任与尊重。在法律治理化的刑事司法场域中,一旦发生恶性的刑事案件,司法机关就以“维稳”名义采取及时、高压处理,办案过程留下了更多的隐患,潜藏了危机。如果日后发现案件误判,更会激发民众对司法公信力的质疑。如此恶性循环,后果不堪设想。审判权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众权利救济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维系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刑事错案的接连发生不仅使法律人蒙羞,更是直接削弱了司法的权威、裁判的公信力,损害社会公众的法律安全感进而威胁到了国家政权合法性建设本身。毕竟,司法公信力是公权力合法性的基础,直接关系到了政权的合法性建设。这两种目标之间的冲突,使得法律治理化的政法传统处于难以自圆其说的悖论之中。所以,真正实现以审判为中心,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需要执政党正确认识和理清政权合法性建设和法律治理化对司法场域带来的直接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悖论。完善司法场域,摒弃法律治理化的传统,为刑事司法场域的独立运行提供保障是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乃至推进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根本出路。
四、结论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落实在本质上相辅相成。一方面,确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格局是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础。没有以审判为中心的宏观架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缺乏实现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以审判为中心诉讼格局要得到实现,其关键内容就是证据裁判原则的落实与贯彻,以实现法院对证据审查的最后判断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出台的背景正是审判阶段案件事实认定过程失控导致的错案频发,这是倒逼我国刑事司法变革,诉讼格局由侦查中心主义开始向审判中心迈进的直接动力。从这一层面上讲,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其过程具有同源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落实与证据规则的完善构成了当前刑事司法改革的核心。转型能否成功的一项重要标准就是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解决案件事实认定的失控问题,而这也是今后司法改革所要努力的方向[13]。
[注 释]
① 以江苏省海安县法院为例,2011年,该院办理案件的翻供率为5%;2012年翻供率为17%;2013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以后,不到8月份,翻供率就上升到15%。参见徐德高等“解析翻供现象增多的成因”一文,载于《检察日报》,2013-10-16。
② 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刑事判决书,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15)浙杭刑初字第78号。
③ 参见施甸县人民检察院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刑事判决书,云南省施甸县人民法院案号:(2015)施刑初字第109号。
④ 调研发现,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对法院庭审程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法院庭审期限普遍延长;二是法官的工作量明显增加;三是因翻供而适用普通程序的比例较大。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司法机关之所以对非法证据排除比较反感的原因——在“案多人少”的大背景下,这无疑加重了他们的工作量。更为详细的讨论参见张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背景下的庭审翻供问题研究”一文,载于《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⑤ 参见唐友用、孟云兰等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孟云兰、吴某容留他人吸毒罪等二审刑事裁定书,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15)宿中刑终字第00018号。
⑥ 根据学者的界定,法律治理化的政法传统主要表现在:(1)法律是贯彻政治意图的工具;(2)法律的目的不仅仅是审判,更重要的是治理社会、改造社会;(3)审判机关功能的治理化与司法机关的一体化;(4)特征表现为“司法的政党化”和“法律的惩罚化”。法律治理化的政法传统形成于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在上世纪50年代的“镇反运动”和80年代初的“严打”中得到了强化。参见强世功“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中国法律的新传统”一文,载于《北大法律评论》2001年第2期第250页。周长军“后赵作海时代的冤案防范——基于法社会学的分析”一文,载于《法学论坛》2010年第4期。法律治理化现象在当前中国尤为突出,尽管全能主义国家开始转型,“市民社会”理论话语试图来消解这一现象并取得了某种程度的胜利,但是都无法对其形成致命性的冲击。法律治理化的现象也许将是中国的必然。参见陈俊敏“法律治理化与刑事和解制度探析——基于法律社会学的视角”一文,载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1] 宋英辉,叶衍艳.我国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启动程序问题研究-基于《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分析[J].法学杂志,2013(9):1-8.
[2] 樊崇义,吴光升.审前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文本解读与制度展望[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11):3-13.
[3] 杜豫苏.非法证据排除审理程序的困境与完善[J].法律科学,2013(6):184-189.
[4] 刘彦辉.非法证据调查程序在我国的立法确立[J].中国法学,2011(4):143-154.
[5] 陈卫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喜与忧[EB/OL].(2010-8-11)[2015-12-15]. http://news.sina.com.cn/o/2010-08-11/074717946538s.shtml
[6] 陈瑞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再讨论[J].法学研究,2014(2):166-182.
[7] 莫湘益.庭前会议:从法理到实证的考察[J].法学研究,2014(3):45-61.
[8] 徐昕,黄艳好,卢荣荣.2010年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J].政法论坛,2011(3):133-153.
[9] 闵春雷.以审判为中心:内涵解读及实现路径[J].法律科学,2015(3):35-43.
[10] 龙宗智.“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及其限度[J].中外法学,2015(5):846-860.
[11] 单民,董坤.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诉审关系探讨[J].人民检察,2015(12):19-24.
[12] 张健.迈向回应型法[J].云南社会科学,2014(1):132-136.
[13] 吴洪淇.审判中心主义背景下的证据裁判原则反思[J].理论视野,2015(4):34-36.
本文推荐专家:
韩松,西北政法大学,教授,研究方向:民商经济法。
焦和平,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民法和知识产权法。
On the Exclusionary Rule in the Concept of Proceedings Centered on Trial: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486 Criminal Cases from 2013
ZHANG JI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s,Jiangsu University,Zhenjiang,212013,China)
Perfecting the rule of evidence is the key to Proceed centered on Trial. We found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judiciary and the legislation on start threshold, startup mode, the standard of proof, and the effect of pre-trial conference through legislative texts and judicial practice of the exclusionary rule. Proceedings centered on trial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xclusionary rule essentially complement each other.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xclusionary rule in the context proceedings centered on trial,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ciousness of investigative and prosecutorial work serving the need of court trial, establish a new type of procuratorial work for the purpose of safeguarding human rights, eliminate the legal tradition of legal governance, and provide conditions for the independent operation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field.
exclusionary rule; proceedings centered on trial; evidence; the rules of evidence
D925.113
A
1008-472X(2016)03-0040-07
2015-10-12
中国法学会 2015年度部级法学研究项目《落实非法证据排除法律制度实证研究》,项目批准号:(CLS(2015)Y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龙泉司法档案整理与研究”(13&ZD151)阶段性成果
张健(1986-),男,山东临邑人,江苏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诉讼法与法社会学。
——以“被告人会见权”为切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