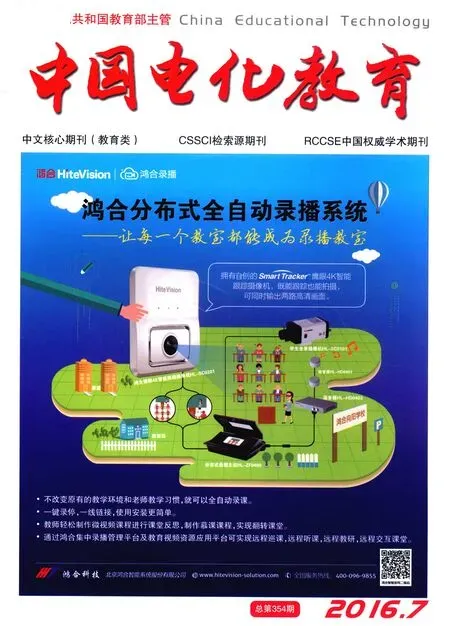工作记忆和长时记忆与教学设计 *
[澳大利亚]约翰·斯维勒,陆 琦(译),盛群力(译)
(1.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教育学院,新南威尔士 悉尼 2052;2.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工作记忆和长时记忆与教学设计 *
[澳大利亚]约翰·斯维勒1①,陆 琦2(译),盛群力2(译)
(1.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教育学院,新南威尔士 悉尼 2052;2.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认知负荷理论常与教学设计相联系,因为该理论中阐释的有关人类认知的许多方面都对教学设计有着重要意义。首先,该理论认为人并不能轻易地习得教育或培训机构中教授的专业知识;其次,要习得这些知识需要学习者具备特定领域而非通用认知类的知识;最后,通用认知类知识的掌握并不需要明确具体的教学指导,因为人早已具备习得这类知识的能力。相反,特定领域的概念与技能则需要明确具体的教学指导。这些因素与人类工作记忆的容量及持续时间等约束因素相互作用,勾勒了个体的认知系统架构,从而影响着教学设计。工作记忆的这种限制性并不会对生物初级知识的习得产生约束,但对生物高级知识的学习则会产生约束效用。如上所述,掌握通用认知类知识并不需要特定的教学指导,而习得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则需要专门的教学指导。由此,认知负荷理论可为教学设计提供具体指导,以减少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必要的外在工作记忆负荷,有利于习得涉及专门教学指导的、属于生物高级知识范畴的、特定领域的专门知识。
认知负荷理论;工作记忆;长时记忆;教学设计
一、工作记忆和长时记忆与教学设计
基于认知负荷理论[1],本文将讨论工作记忆的作用和它与长时记忆的关系,并分析工作记忆的特征是如何随着加工信息的类别变化而发生变化。本文旨在说明组成人类认知系统架构的哪些因素可以作为教学过程设计的依据。工作记忆的性质是认知负荷理论的重点,也是教学设计的关键。
从教学设计的角度来说,人的认知系统架构的三个方面内容常常被研究者所忽略:(1)区分不同类型的知识,一类是我们已具备独立习得能力的知识,另一类是需要我们具备大量专业素养前提的知识;(2)明确知识的作用,即通用认知类的知识和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之间的差异;(3)界定学习的情境,即教学指导者需要厘清在何种情况下向学习者提供明确具体的教学指导。以上三个方面各自都有独立研究的价值,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些因素会通过与工作记忆以及长时记忆之间相互作用从而影响学习。综上,本文先概述一下认知负荷理论中所阐述的人的认知系统架构,接着按照顺序逐一讨论其意义,最后简要介绍该理论在教学设计领域中的若干实践应用。
二、生物初级知识与生物高级知识
Geary对生物初级知识与生物高级知识(Biologically Primary and Secondary Knowledge)的区别给出了相应说明[2-4]。随着人类不断的进化,我们已具备独立掌握生物初级知识的能力,如学会倾听与说话、识别面孔等,又或涉及到通用认知加工过程(Genericcognitive Processes),如使用问题解决策略来解决相关问题。
由此看来,初级知识与技能均有模块化的特点。我们现在所具备的自然习得母语的能力可能经历了不同世代的更迭与进化,而能够识别与区分面孔的能力也可能涉及到运用不同认知加工过程。引用现代科学发展的观点来说,习得与掌握生物初级知识是不费力的、无意识的,并且也不需要他人指导。这一点很好理解,如何倾听和说话,找到从点A到点B的路径,这些都是无师自通,自然而然就能掌握的。因此掌握这些综合技能均是自动化的,并不需要意识的主动参与和加工。
不少学者对工作记忆的限制性已经研究了数十年[5],不过他们并没有考虑过将这一点与生物初级知识的习得联系在一起[6-8],而且在过去研究的相关文献中也很少提及到两者之间的联系。然而,大多数人在识别与区分面孔时,需要大量记忆人脸的差异,并不会觉得有困难。同样,在学习与记忆母语中,学会各种发声音调也不会觉得辛苦。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已经掌握了与面部识别以及母语发声相关的生物初级知识。
生物高级知识则是由各类不同的知识所组成的,这是传承文化的需要。与生物初级知识的模块化特点不同,掌握生物高级知识需要初级知识的积累作为前提[9]。在教育或培训机构中所教授的每个主题基本上都会涉及到生物高级知识,而在工作场所或文艺活动的学习中也会涉及这类知识。
然而,为了掌握各种高级知识所进行的认知加工过程与习得初级知识所进行的加工完全不同。掌握高级知识是有意识的、相对困难的和需要付出努力的,并且往往需要明确具体的教学指导。事实上,无论是创办学校还是设立其他教育以及培训机构都与生物高级知识的性质与特点息息相关。不同于生物初级知识的特点,即只要成为社会的一员就能自动地在生存过程中习得,掌握生物高级知识不能脱离专门的社会结构如学校以及其他教育和培训机构的辅助。每个人几乎都可以不借助学校的力量就学会倾听与说话,但却没有什么人能够在不接受学校教育指导的情况下学会阅读与写作。
生物高级知识的掌握需要初级知识的协助。例如,倾听与说话的能力会影响阅读与写作的能力。所有高级知识的概念与技能都基于初级知识的概念与技能,因而,个体掌握初级知识的程度会影响其在高级知识概念与技能学习上所呈现出的与他人的差异。
工作记忆在初级知识与高级知识的学习中显示了明确的认知差异。工作记忆的容量以及持续时间上的限制只会对习得生物高级知识产生约束,当需要处理新的、属于生物高级知识范畴的信息时,工作记忆就会受到容量以及持续时间的严格限制,因而对教学设计产生重要的影响[10]。
三、特定领域知识与通用领域知识
生物初级知识与高级知识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前者往往由通用类的认知技能所组成,而后者则指向特定领域的专业技能[11],即同时包含了概念性以及程序性知识。通用认知技能是一类心理过程,可运用于大量不相关的领域中,如一种通用的问题解决策略可在多种不相关的问题解决中使用,又如我们在任何领域中遇到新的问题时经常会使用的“手段—目的策略”[12],即问题解决者首先要指明每个问题目前的状态,并试图缩短问题状态与目标状态之间的距离。相反,特定领域技能则属于一类程序,只能运用于某一个特定范围的领域中,如当我们遇到代数问题(a+b)/c=d,求a的值时,最佳的做法是先消除分母(即c*d),然而这一方法只适用于这类分数式的代数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不是所有的生物初级技能都属于通用认知类,也不是所有的高级技能都属于特定领域类。例如,虽然说初级知识具有模块化的特点,不过它们对特定领域来说是专门的、特殊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知识属于“特定领域的知识”,而不是“通用知识”。不过,一般来说,通用认知类技能还是属于生物初级知识范畴的。上述所介绍的“手段—目的”分析法、通用问题解决策略等均是这类技能运用的一些实例。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技能,如归纳技能或元认知技能等都需要我们掌握。我们不仅需要学会如何解决问题,还需要学会如何去学习,如何去计划或如何去思考。这些都是关键的通用认知类的技能(或能力),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也是目前的教育研究中关注的重点内容。从这个角度来说,通用认知技能似乎比特定领域技能重要得多,若没有作为前提的通用认知技能,人类恐怕很难作为人类而生存下去。不过,尽管这类技能如此重要,它们也不需要被刻意地教授,因为人类经过世代进化,早已具备独立习得生物初级技能的能力,因而也不需要外来指导。
虽然生物高级技能在性质上并不属于通用认知类,不过这之中的部分技能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例如,阅读属于生物高级技能的范畴,它虽不属于通用认知技能,却具有通用领域的性质。当然,一般来说,在教育和培训机构教授的高级技能往往都是特定领域类的而非通用认知类的专门知识。例如,人即使不掌握特定领域的专业技能,如习得复杂的数学或精通国际象棋也可以活下去。因此,我们并不能轻易地掌握属于生物高级知识范畴的特定领域的专业技能。我们可能会去习得通用的问题解决策略,但可能不会去专门学习为了解决(a+b)/ c=d,求a的值的代数知识,且若不具备与这一问题相关的知识,我们很难知道最佳的方法是先消除分母(即c*d)。这两类知识的区别对教学设计有着重要的意义。
创办学校以及设立其他教育和培训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教授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即生物高级知识[13]。这些社会机构并不会专门教授通用认知类技能,因为这类技能中的大部分都可在不接受指导的情况下自动习得。值得注意的是,如上述介绍的“适用于特定领域类的初级知识与技能”,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虽然不需要学习这类技能本身,但需要学习如何将这类特定的通用认知技能运用到某个特殊领域中去[14]。
如果特定领域的知识与技能可归类于生物高级的范畴,那么它们就需要与能够加工生物高级技能相同的工作记忆运作模式。在设计教学流程时就需要考虑工作记忆容量与持续时间的限制所产生的影响[15]。相反,如果通用认知类的知识与技能可归类于生物初级的范畴,那么这部分知识并不会对工作记忆产生严重的负荷;若是尝试专门去教授这类技能,反而会“画蛇添足”[16],因为生物初级知识的习得是无意识的、自动化的,并不需要明确具体的指导。
四、专门的教学指导
在教育背景下掌握生物高级知识,即特定领域专业知识,其中会涉及到一些相关的教学启示。虽然我们能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自动习得生物初级技能,即通用认知类知识,如倾听、说话、面孔识别以及使用“手段—目的”分析法来解决问题等,但是我们却不能在相同的情况下掌握生物高级技能,即特定领域类知识,如在教育和培训机构教授的专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需要学习者接受专门的教学指导,如向学习者口头讲解或书面指导等[17]。不过,我们应避免这样一个思想误区,即简单地认为在排除正规教育的情况下更容易掌握生物初级知识,而高难度的生物高级知识则应该依赖于正规教育。事实并非如此,在这两种情况下之所以会出现学习难易度之分,是由人类的进化水平差异所决定的,而不是由教学程序引起的。所以,要针对不同的教学情境设置不同水平的指导以调节学习者对学习容易度的感知水平。
那么为什么需要在教学情境中安排专门的教学指导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与工作记忆在处理新的、属于生物高级知识范畴的、特定领域的信息时所呈现的性质和特点有关。如上所述,工作记忆在处理需要深加工的信息时会改变原本信息的类型,此时工作记忆本身的限制就会对这一流程产生影响,因此对教学设计来说,很重要的一步就是要减少所有无关的外在认知负荷,而这正是安排专门的教学指导的意义所在。与少教不需要教的教学程序设置不同,教学指导的目的则是要尽可能地减少工作记忆的加工负荷。针对这一假设,学者们给出了强有力的证据来说明。样例效应是认知负荷理论实证研究中所发现的一个成果,即与必须独立解决问题的学习者相比,被告知问题解决方案的学习者的表现会更加出色[18-20]。基于这一效应,学者们以实证说明了专门的教学指导的重要性,也从侧面验证了该理论的根基——认知系统架构的存在。
五、人类认知系统架构
人类认知,尤其是当人类需要处理生物高级类信息时,可以描述为“自然信息加工系统”,与自然选择中的进化信息加工流程有些类似[21][22]。将人类认知与物竞天择进行类比的这一说法经常被引用[23-25],当然其他还有不少说法可以描述这一“自然信息加工系统”[26],这里作者将引用“五项基本原则”来解释这一概念。
(一)信息存贮原则(the Information Store Principle)
为了能随时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自然信息加工系统需要存贮大量的信息。基因通过自然选择与进化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可能性,人类认知系统架构中的长时记忆就起着与之类似的作用。
有关于人类认知系统架构中的长时记忆的作用,可以借助象棋大师的例子来解释[27]。正如我们所知,象棋大师能够做到“未雨绸缪”,他们在布局每一颗棋子时所考虑的移动范围会比常人深广得多。事实上,尽管象棋大师们与那些业余棋手相比,似乎并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但他们总是能下得一手好棋。迪格罗特(De Groot)对这一现象做了研究,他在象棋大师和业余棋手面前同时呈现了一块棋盘,该棋盘的布局与真实比赛中的布局一样,在随意更改棋盘上的棋子位置后,要求他们将棋盘还原成之前的样子。不出所料,在相同的时间内,象棋大师能够精准地还原80%的棋局,而业余棋手仅能够还原30%左右。
这一实验的结果中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若在实验中使用随机排列的棋盘,尽管象棋大师在还原过程中一度占据了优势,但从最终结果来看两者的表现并没有呈现太大的差异[28]。象棋大师只有在处理真实比赛中布局的棋盘才能呈现出与普通棋手的差异。第二,在任何一个领域内想要成为专家,需要多年的努力与磨练,象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9]。第三,无论是象棋大师还是普通棋手,在还原棋盘布局的过程中,认知系统架构上所发生的主要变化,或者说唯一变化就是工作记忆中的信息通过深加工进入到长时记忆中。经过多年的历练,象棋大师的长时记忆中已存贮了成千上万种棋盘布局形式以及相应的棋子的最佳走法[30]。在下象棋时,他们能认出绝大多数他们遇到的棋局,也知道每一步的最佳走法。与这些早已熟知最佳策略的专家们相比,普通棋手之所以在下棋时总显得差强人意,是因为他们需要在几秒内找到棋子的最佳走法,而这种想法往往会使得他们在最后一刻走出一步“差棋”。这种现象不仅是在象棋,在任何一个“术业有专攻”的领域内都会出现,特别是与教育相关的领域[31-34]。例如,象棋大师需要学习识别棋盘布局,而专业读者则需要学习识别文章中的词句。所谓的专家,就是指其在长时记忆中存贮了大量特定专业领域的,属于生物高级知识范畴的信息。
需要指出的是,个体在长时记忆中存贮的知识或信息量的不同会导致个体差异,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因素会造成这种差异。例如,梅兹和汉布里克(Meinz and Hambric)[35]发现优秀钢琴家与普通钢琴师之所以在技术上有这么明显的区别,是两者在工作记忆上的差异所引起的。当然,造成这种区别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工作记忆上的差异是由长时记忆中存贮的知识量的不同所引起的。举个例子,会弹钢琴的人与不会弹钢琴的人在与钢琴相关的知识上存在“天壤之别”,因而他们在工作记忆上也会呈现明显的差异。对知识量之间存在差距的人来说,工作记忆上的小小差异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再如,让一个懂英语的人与一个不懂英语的人去重写一篇英语文章,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这种巨大的反差反映了他们知识储备量上的差异而不是他们工作记忆容量上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知识量上的差距可能显得更加重要。换句话说,当个体的知识量之间不存在明显差距时,工作记忆上的差异会更能说明问题。
(二)引用与重组原则(the Borrowing and Reorganizing Principle)
自然信息加工处理系统所攫取的大多数信息都是从其他存贮源中“引入”的。与之类似的,在生物进化中,有性繁殖与无性繁殖就是遵循这一原则。无性繁殖中引入了不会发生原有基因改变的基因组备份,而有性繁殖则引入了男性与女性基因组的信息并对其进行重组。
长时记忆中的大多数内容也是来自于他人的长时记忆,因为我们总是会向他人学习,模仿他人的行为[36],倾听他人的话语,阅读他人的著作。这种倾向于从他人身上获得信息的行为是生物初级能力的体现。如前所述,我们不需要被刻意教会如何模仿他人或倾听他人以及与他人沟通。但我们需要学会如何阅读和写作,这些技能属于生物高级技能。不过,一旦我们学会了这些高级技能,就没有必要强制使用。我们能够自然习得生物初级技能,如与他人沟通的能力,不过要以某种方式传输这些信息,如阅读和写作等,就属于生物高级技能的范畴了。换句话说,与他人沟通虽然是生物初级能力,但需要交流的信息则属于生物高级知识,这些知识我们并不能自动地无意识地习得,而是需要一定的专业文化素养作为学习基础。在现代社会,教育与培训机构中所教授的知识就属于这种类别。
引用与重组原则不仅意味着长时记忆会从其他存贮源头引入大量的信息,也意味着信息引用后需要重组。我们很少能够精确地还原信息,因为引用后的信息会经历重组,即将这些新信息与在长时记忆中存贮的旧信息进行整合。当需要记忆某种信息时,若材料所包含的内容能与长时记忆中已存贮的信息“产生共鸣”,就能加深这部分内容的记忆;若材料所蕴含的新信息与长时记忆中已存贮的旧信息无法“产生联结”,就会淡化这部分内容的记忆。也就是说,不同的人拥有不同构造的长时记忆,因而会对相同的信息产生不同的重组方式,就像有性繁殖中不同的基因组重组后会产生不同的后代。
有不少学者对这一原则在人类认知中的重要性给出了实证解释,即样例效应[38-40]。正如上述介绍的那样,这一效应是在研究提供给学习者问题解决策略后所产生的学习成果中发现的,被教授问题解决策略的学习者会比那些仅给出问题且要求独立解决的学习者在随后的测试中获得更加出色的表现。也就是说,与我们独立解决问题的情况相比,当我们能够借用他人的智慧,即问题解决策略来处理问题时,我们能学得更好。
(三)随机组合与生成原则(the Randomness as Genesis Principle)
自然信息加工处理系统是通过从其他渠道引入信息后进行重组以实现海量信息的存贮,然而,加工后所形成的新信息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就得以生成。随机组合与生成原则则为这一过程提供了必要的机制。
无论是同种族还是异种族繁殖,个体所形成的最终的遗传信息都是随机组合的结果。当然,除繁殖以外的其他过程可能也会通过随机变异造成这种独特的基因组合结果,但若要真正追溯基因组合的形成原因,那肯定还是会归于遗传信息的随机变异。
随机变异所产生的影响是逐步生成的且需要对其过程进行检测。也就是说,随机变异的价值只有通过效能检测才能得知。大多数的随机变异都没有什么实际的功效,有的还会产生消极影响,当然,消极的这部分肯定会被舍弃,仅有少部分会产生积极作用的变异过程会得到保留。另外,在检测变异有效性时,也只有会产生有效变化的变异过程会被留存。
生物进化是一个自然的,具有创造性的系统。而人类创造性在问题解决时所发挥的作用也遵循着相同的逻辑[41]。当要决定问题解决的策略时,会考虑两种情况:第一,如果个体能够正确认知问题所处的状态以及如何改变这一现状的合适的做法,那么这一部分知识就会从长时记忆中唤醒并且能够指导我们的日常活动,正如基因能够自然而然地决定人体的生理活动(如人体内的蛋白质合成)一样。这一点也和之后会介绍的第五条原则——“环境组织与联结原则”所阐述的一样,在给定环境中所进行的生成活动是信息存贮最主要的功能。第二,如果个体面临的是一个新的问题,并且认识到并不能简单地通过从长时记忆中提取信息从而获得问题解决策略,那么合适的做法就是在从长时记忆中提取信息时使用“生成与检验法”。一般来说,生成与检验法是“手段—目的”问题解决策略的一种衍生。使用这两种策略以及从长时记忆中提取信息的步骤都属于生物初级活动,即可以在没有专门指导的情况下自动习得,无师自通。当然,除了这两种方法,还有很多具有实用性的办法能缩短问题当前状态与目标状态之间的距离。如果你拥有足够可观的知识量,那么你总能选择最佳的问题解决策略。如果已有知识并不够丰富,可行的办法就是使用“随机生成与检验法”,也就是说先随机地选择一个策略,然后检验其有效性。如果该策略能够缩短问题当前状态与目标状态的距离,那就接受这个策略;当面临下一个新的问题时,就重复采取同样的步骤。正如我们的基因会选择并存贮那些能够适应未来生存的变异,试验成功的策略会存贮在长时记忆中以备未来不时之需。
(四)变化最小通道原则(the Narrow Limits of Change Principle)
随机组合与生成原则会对信息加工系统产生一些结构性变化。换句话说,该系统在随机生成信息组合使得信息数量不断递增的同时也加剧了信息组合爆炸的风险。例如,3!=6,这个等式包含了3个元素的排列组合,而10!=3628800,这个等式包含了10个元素的排列组合。当使用生成与检验法时,要决定哪6个数进行排列组合时是很容易的,然而若要决定能生成3628800这一结果所需要的排列组合数字时就没那么容易且变得很耗时。由于这个原因,自然信息加工处理系统需要一个机制来保证信息组合的数量是可控且适度的,即能够以某种方法进行检验。在人类认知系统架构中,工作记忆的性质呈现了这一原则的重要性。而在自然选择的物竞天择中,表现遗传系统也遵循类似的原则。
表现遗传系统在环境与基因系统中起到沟通桥梁的作用,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基因的存在形式,在遵循变化最小通道原则的前提下,也可以决定基因变异发生的位置与频率。为了维护基因的完整性,基因变异的频率必须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因为基因组内的大量变异信息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分条处理。
与表现遗传系统在生物进化中所起的作用类似,工作记忆在人类认知系统结构中也承担着联接桥梁的作用。它缔结了外部环境与长时记忆中已存贮信息之间的联系。如前所述,当面临处理新的、属于生物高级知识范畴的信息时,工作记忆的局限性便会完整地呈现出来。
工作记忆的这种限制仅会对处理外来环境中的新信息产生影响。随机生成与检验法也仅能在处理有限数量的新信息时发挥作用,它并不能同时处理大批量的元素。这也正是工作记忆的局限性所在,即它不能同时处理大量的从外部环境涌入的新信息。有限的工作记忆使得每次能够加工的信息仅有一小部分,极大地限制了任何对长时记忆造成冲击的变化以维护已有的发展成熟的认知结构。同样,人的基因也不会频繁地改变。变化最小通道原则保证了每次发生的变化都是小范围且具有间隔性。
(五)环境组织与联结原则(the Environmental Organizing and Linking Principle)
这一原则有效地证明了上述原则的重要性。如变化最小通道原则,它缔结了外在环境与长时记忆中已存贮信息之间的联系,同时限制了能进入长时记忆中存贮的外在环境信息的数量。不同于该原则,环境组织与联结原则旨在从环境中提取信息线索并激活已存贮信息来指导实践活动。在这一过程中,表现遗传系统与工作记忆再次承担了联接桥梁的作用。
表现遗传系统的重要性在环境组织与联结原则上体现得最明显。让我们想象一下人类身体内的细胞,比如皮肤细胞与肝脏细胞。这两种细胞有着非常不同的结构和功能,但在细胞核内却有着相同的DNA结构,即两者在遗传学的角度上可以说是一致的,但在形态学的角度上就不可比较了。形态上的差异是由表现遗传系统造成的,该系统能够根据环境的特征相应地改变基因的存在形式。也就是说,虽然存贮在基因中的信息决定了细胞活动的种种可能性,但实际的活动信息却是由表现遗传系统所决定的。
环境组织与联结原则与人类认知系统架构一样重要。工作记忆在不同原则下的运作方式是不同的。例如,在变化最小通道原则指导下将新信息添加至长时记忆中的运作原理与在环境组织与联结原则指导下提取环境信息线索以激活已有信息来进行实践活动的运作原理是截然相反的。在使用环境组织与联结原则的情况下,环境中的线索能够向工作记忆指明何种信息应该从长时记忆中提取出来,这部分信息随后可用于控制行为。
工作记忆在变化最小通道原则的约束下,若想将加工处理的信息添至长时记忆中,就会受到容量与维持时间的限制,然而若只是从长时记忆中提取旧信息,则不会受到这种限制的影响,这是环境组织与联结原则发挥作用的结果。一旦信息在长时记忆中被有效地组织与存贮,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可以再将这些信息迁移至工作记忆中。
工作记忆处理信息的能力因人而异。这种差异会影响个人绩效表现[42],并且一旦信息在长时记忆中得到妥善存贮,长时记忆的质量可能会盖过个人在工作记忆能力上的差距。工作记忆在处理新的、属于生物高级知识范畴的信息时总会受到严格的限制,而在处理已存贮于长时记忆中的、熟悉的信息时则不会受到太多的约束。这是因为长时记忆中的持有信息能够有效减少工作记忆加工处理时所产生的与已有认知不对称等差异。正是环境组织与联结原则的存在,使得一名在特定领域内拥有丰富知识的专家能够在相似的领域内比新手表现得更为出色,这是长时记忆中已存贮信息量的差异而与工作记忆能力差异无关。
工作记忆在从环境中收集信息以及从长时记忆中迁移信息上所呈现的巨大差异使得学者们提出了一个假设,即存在另一个不同构造的长时工作记忆,它能够有效处理从长时记忆中提取而来的信息[43]。不过这一假设还存在争议,工作记忆可能是一个能够根据信息来源进行功能切换的单一结构,也可能是其本身就存在两个独立的结构,因而有两种不同的信息处理功能。
上述五种原则共同构建了人类对于生物高级信息加工的认知系统。这种架构在处理生物高级信息时会借助生物初级信息的加工系统。总的来说,在长时记忆中存贮信息时需要遵循信息存贮原则,引入其他来源的信息并加以改造时需要参照引用与重组原则,生成新的信息时需要考虑随机组成与生成原则,在工作记忆中加工处理新信息时需要顺应变化最小通道原则,而要从长时记忆中迁移大量信息至工作记忆以生成实践行为时则需要使用环境组织与联结原则,这些原则都属于生物初级技能的范畴,因此我们并不需要特意地教授或学习这些关键技能,人类的进化历程已使得我们具备自动掌握这些技能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说,生物高级系统确确实实基于初级技能。
六、实践应用
认知负荷理论以人的认知系统架构为基础来设计相应的教学程序。基于这种架构,该理论假设教学的主要功能是促进学习者掌握特定领域的、属于生物高级知识范畴的信息并协助学习者将这部分内容存贮在长时记忆中已备将来使用。当然,要将从外部环境中收集的新信息存贮于长时记忆中,必然会受到工作记忆容量与持续时间的限制,而若想从长时记忆中提取存贮的信息以指导行为时便不会再受到工作记忆的限制约束。
基于工作记忆的结构与加工过程,在设计教学时需要重点考虑工作记忆在处理新信息时所受到的限制约束。近年来从随机控制的实验中得出的若干认知负荷效应,使得认知负荷理论能用于提出各种教学处方[44]。认知负荷效应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帮助学者们认识到减少外在认知负荷是可以通过缩减教学信息数量而实现的,即通过教学程序来减少无关的认知加工。不过如果教学程序中所包含的信息需要学习者在工作记忆中同时进行加工,则可能会由于信息之间的交互影响,加重学习者学习时所承担的外在认知负荷[45]。教学程序能够调节学习者的外在认知负荷,而信息本身的性质则会影响学习者的内在认知负荷。某些信息,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质,需要学习者在学习时同时习得多种相互关联的信息,因而会造成高水平的内在认知负荷。而外在认知负荷与内在认知负荷的总和就构成了工作记忆的总负荷。大多数认知负荷效应之所以能够有效减少外在认知负荷是因为这些认知负荷都是由不合理的教学程序直接产生的,因而只要改变教学程序中的不合理设计,就能有效发挥其作用。
如上所述,“样例效应”(the Worked Example Effect)是认知负荷效应的一种典型应用,因而能够有效减少学习者的外在认知负荷。从样例中学习会比自己解决同等程度的问题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这是因为在解决未知问题时工作记忆需要同时处理的信息数量过于庞大,因而会加重工作记忆的负担,而从样例中学习时由于已知晓问题解决策略,工作记忆不需要同时处理大量的新信息,从而减少了认知负荷量。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认知负荷效应的典型应用,不过仅在这里介绍其中的部分。“注意分配效应”(the Split-attention Effect)[46]是另一种常见的能够减少外在认知负荷的应用。例如,某种问题解决策略或教学指导需要学习者针对多种不同的信息来源分配注意力以实现信息的心理整合,此时在工作记忆中需要处理的相互关联的信息数量会比那些结构上已具有完整性因而不需要心理整合的信息数量庞大得多。另一种常见的应用是“信息冗余效应”(the Redundancy Effect)[47],这一效应往往会在学习者需要同时处理必要与不必要的信息时发生。大多数必要的信息都会在工作记忆中得到处理,而无关紧要的信息则会被剔除,从而减少工作记忆的负担。
尽管我们需要尽可能地减少外在认知负荷,但同时也需要重视内在认知负荷的作用。“可变性效应”(the Variability Effect)的实证研究说明增加内在认知负荷能够有效促进学习者学习[48][49]。如果样例的可变性可以提升,学习者就不仅能学习如何解决某一类别的问题,也能学会辨别问题的种类并且能根据问题类别分配适宜的问题解决策略。也就是说通过提供新信息以增加信息的交互性是很重要的。当内在认知负荷水平提升时,学习者就会有充分的工作记忆资源来处理新增的信息元素,从而促进学习。这一结论由帕斯和范梅里恩伯尔(Paas and Van Merrienboer)[50]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相反地,如果学习者没有充分的记忆资源来处理这些新增的、重要的信息元素,学习效率就会因这些来不及加工的信息冗余而下降。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因为信息冗余而造成工作记忆超负荷,那就有必要略去部分信息。在工作记忆处理新信息之前就剔除部分信息元素可能更能有效地促进学习,这一现象在之后也被学者称为“分离元素效应”(the Isolated Elements Effect)[51]。由此可见,内在认知负荷需要调节至最佳水平才能有效发挥其积极作用。其中,可变性效应能够提升内在认知负荷水平,而分离元素效应则会降低这一水平。
元素交互性效应(the Element Interactivity Effect),尽管这一作用只直接发生于工作记忆当中,但其产生的结果却能影响所有其他的认知负荷。这一效应的作用在近年来对“生成效应”(the Generation Effect)与“样例效应”之间关系的研究中也有所体现[52]。所谓生成效应,指的是与直接提供给学习者教学指导所产生的学习效果相比,让学习者自己生成问题解决的答案会产生更好的结果。而样例效应则与这种情况相反,即直接提供给学习者现成的问题解决策略会让他们学得更好。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是由学习中所涉及的元素交互性水平所决定的。教学指导仅在内在工作记忆负荷比较繁重的时候能够发挥积极作用,而当工作记忆负荷比较轻的时候,教学指导成为了另一种形式的信息冗余,因而给学习者带来消极的影响。因此,生成效应会在元素交互性以及内在加工负荷水平比较低的时候发生,而样例效应则在两者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发挥作用。
专长逆转效应(the Expertise Reversal Effect)[53]是元素交互性效应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指的是当学习者自身的专业知识增加的时候,教学程序的设计优势就显得不再重要。例如,对于新手来说,学习具有高水平元素交互性的样例会比独自解决同等程度的问题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不过当新手逐步成长为知识丰富的专家,样例效应的效果可能就会减弱,甚至会出现相反的学习结果[54]。这一现象可能是环境组织与联结原则的作用所造成的,随着学习者专业知识的增加,学习者对学习材料中元素交互性的感知水平就会下降。对于新手来说,他们会倾向于将信息视为个体因素,因而给工作记忆带来了沉重的负荷;而对专家来说,他们的判断则更为理性,即将信息视为独立于个体以外的因素,因而不会对工作记忆带来过重的负担。总的来说,如果要调节元素交互性,可以通过改变材料的性质或学习者的专业知识水平而实现。无论是通过哪种手段,教授高水平元素交互性的信息均需要向学习者提供专门的教学指导,而教授低水平元素交互性的信息则不需要这么做。
对认知负荷理论的研究生成了一些教学设计的新效应。总的来说,这些设计思路都围绕着几个核心点展开,即减少外在认知负荷或调节内在认知负荷至最佳水平。从这个角度来说,更好地理解人类认知系统架构中的工作记忆的作用对教学设计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七、结语
以上对人类认知系统架构的概述可以帮助我们对知识的类别形成更加完整的理解。对于学术领域而言,使用更广的是属于生物高级知识范畴的,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而非通用认知类的信息[55],而且也只有前者具有教授的价值和意义。掌握通用认知类知识并不需要我们刻意地去学习,人类的进化历程已使我们具备了在没有任何指导的情况下无师自通的能力。因此,截至目前似乎也没有学者专门通过实验去验证那些“具有效用的、可以教授的”通用认知技能。既然如此,那我们不妨换个思路,即努力让学习者在特定领域的学习中使用他们已经掌握的通用认知类知识[56]。
大量的研究文献都在尝试阐述教授特定领域专业知识的方式方法,强调在设计教学程序时必须要重点考虑人类认知系统架构的性质与特点,尤其是工作记忆在不同学习情境下所受的约束力的变化,当工作记忆处理的信息是新的,属于生物高级知识范畴的专业知识时就会受到容量以及持续时间的限制约束,而当其处理的信息是从长时记忆中提取而来的时候,这种限制约束就不复存在。这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即在设计教学程序时,有必要事先理解人类认知系统架构的相关知识以及工作记忆的性质与特点,否则就是两眼一抹黑。
[1][10][15][21][40][44][46][47][49][51] Sweller, J., Ayres, P., & Kalyuga, S. Cognitive load theory[M]. New York, NY: Springer, 2011.
[2] Geary, D. Educating the evolved mind: Conceptual foundations for an evolution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A]. J. S. Carlson, & J. R. Levin,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issues[C]. Greenwich, CT: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2007.1-99.
[3] Geary, D. An evolutionarily informed education science[J].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2008, (43):179-195.
[4] Geary, D. Evolution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A]. K. Harris, S. Graham, & T. Urdan, APA Educational Psychology Handbook(Vol.1) [C].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2.597-621.
[5] Cowan, N. The magical number 4 in short-term memory: A reconsideration of mental storage capacity[J].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001, (24):87-114.
[6] Miller, G. A. The magical number seven, plus or minus two: Some limits on our capacity for processing information[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56, (63):81-97.
[7] Peterson, L., & Peterson, M. J. Short-term retention of individual verbal items[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959, (58):193-198.
[8] Shipstead, Z., Lindsey, D., Marshall, R., & Engle, R. The mechanisms of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Primary memory, secondary memory, and attention control[J].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2014, (72):116–141.
[9] Paas, F., & Sweller, J. An evolutionary upgrade of cognitive load theory: Using the human motor system and collaboration to support the learning of complex cognitive tasks[J].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2012, (24):27-45.
[11] Tricot, A., & Sweller, J. Domain-specific knowledge and why teaching generic skills does not work[J].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2014, (26):265-283.
[12] Newell, A., & Simon, H. A. Human problem solving[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72.
[13][55] Sweller, J. In academe, what is learned, and how is it learned? [J].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5, (24):190-194.
[14][56] Youssef-Shalala, A., Ayres, P., Schubert, C., & Sweller, J. Using a general problem-solving strategy to promote transfer[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Applied, 2014, (20):215-231.
[16] Redick, T., Shipstead, Z., Harrison, T., Hicks, K., Fried, D., Hambrick, D., et al. No evidence of intelligence improvement after working memory training: A randomized, placebo-controlled study[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2013, (14):359-379.
[17] Kirschner, P., Sweller, J., & Clark, R. Why minimal guidance during instruction does not work: An analysis of the failure of constructivist, discovery, problem based, experiential and inquiry-based teaching[J].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2006, (41):75-86.
[18] Cooper, G., & Sweller, J. Effects of schema acquisition and rule automation on mathematical problem-solving transfer[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87, (79):347-362.
[19][39] Renkl, A. Toward an instructionally oriented theory of examplebased learning[J]. Cognitive Science, 2014, (38):1-37.
[20] Renkl, A., & Atkinson, R. Struct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example study to problem solving in cognitive skills acquisition: A cognitive load perspective[J].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2003, (38):15-22.
[22] Sweller, J., & Sweller, S. Nat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J].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2006,(4):434-458.
[23] Campbell, D. Blind variation and selective retention in creative thought as in other knowledge processes[J].Psychological Review, 1960,(67):380-400.
[24] Darwin, C. The descent of man[M]. London: Gibson Square,2003.
[25] Popper, K.. Objective knowledge: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9.
[26] Sweller, J. Evolution of human cognitive architecture[A]. B. Ross. 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and motivation [C].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2003. 215-266.
[27] De Groot, A. Thought and choice in chess[M].The Hague, Netherlands: Mouton, 1965.
[28] Chase, W. G., & Simon, H. A.. Perception in chess[J].Cognitive Psychology, 1973, (4):55-81.
[29] Ericsson, K. A., & Charness, N. Expert performance: Its structure and acquisition[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4, (49):725-747.
[30] Simon, H., & Gilmartin, K. A simulation of memory for chess positions[J]. Cognitive Psychology, 1973, (5):29-46.
[31] Chiesi, H., Spilich, G., & Voss, J.. Acquisition of domain-related information in relation to high and low domain knowledge[J].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 1979, (18):257-273.
[32] Egan, D. E., & Schwartz, B. J. Chunking in recall of symbolic drawings[J]. Memory & Cognition, 1979, (7): 149-158.
[33] Jeffries, R., Turner, A., Polson, P., & Atwood, M.. Processes involved in designing software[A]. J. R. Anderson. Cognitive skills and their acquisition[C]. Hillsdale, NJ: Erlbaum,1981. 255-283.
[34] Sweller, J., & Cooper, G.. The use of worked examples as a substitute for problem solving in learning algebra[J].Cognition & Instruction, 1985,(2):59-89.
[35][42] Meinz, E., & Hambrick, D. Deliberate practice is necessary butnot sufficient to explai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piano sight-reading skill: The role of working memory capacity[J].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0, (21):914-919.
[36] Bandura, A.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M]. Englewoods Cliffs, NJ: Prentice Hall,1986.
[37] Bartlett, F. C.. Remembering: 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M].Oxford, England: Macmillan,1932.
[38] Glogger-Frey, I., Fleischer, C., Gruny, L., Kappich, J., & Renkl, A. Inventing a solution and studying a worked solution prepare differently for learning from direct instruction[J]. Learning & Instruction, 2015, (39):72-87.
[41] Sweller, J. Cognitive bases of human creativity[J].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2009, (21):11-19.
[43] Ericsson, K. A., & Kintsch, W. Long-term working memory[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5, (102):211-245.
[45] Sweller, J. Element interactivity and intrinsic, extraneous and germane cognitive load[J].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2010, (22):123-138.
[48][50] Paas, F., & van Merrienboer, J. Variability of worked examples and transfer of geometrical problem-solving skills: A cognitive-load approach[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94, (86):122-133.
[52] Chen, O., Kalyuga, S., & Sweller, J. The worked example effect, the generation effect, and element interactivity[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5, (107):689-704.
[53] Kalyuga, S., Ayres, P., Chandler, P., & Sweller, J. The expertise reversal effect[J].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2003, (38):23-31.
[54] Kalyuga, S., Chandler, P., Tuovinen, J., & Sweller, J. When problem solving is superior to studying worked examples[J].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1,(93):579-588.
作者/译者简介:
约翰·斯维勒(John Sweller):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心理学荣誉教授,当代国际著名认知负荷研究理论专家(j.sweller@unsw.edu.au)。
陆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教学设计(3120103102@ zju.edu.cn)。
盛群力: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学理论与设计(qlsheng57@12.com)。
Working Memory, Long-term Memory, and Instructional Design
John Sweller1,Translated by Lu Qi2& Sheng Qunli2
(1.School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Sydney NSW 2052;2.College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8)
Cognitive load theory is used to design instruction. Several aspects of human cognition are critical to instructional design. First, the theory assumes we have not speci fi cally evolved to learn the topics taught in educational and training institutions. Second, these topics require learners to acquire domain-specific rather than generic–cognitive knowledge. Third, while generic-cognitive knowledge does not require explicit instruction because we have evolved to acquire it, domain-speci fi c concepts and skills do require explicit instruction. These factors interact with the capacity and duration constraints of working memory to delineate a cognitive architecture relevant to instructional design. The working memory limits do not apply to biologically primary, generic-cognitive knowledge acquired without explicit instruction but do apply to biologically secondary, domain-speci fi c knowledge that requires explicit instruction. Accordingly, cognitive load theory has been developed to provide techniques that reduce unnecessary working memory load when dealing with explicitly taught, biologically secondary, domain-speci fi c knowledge.
Cognitive Load Theory; Working Memory; Long-term Memory; Instructional Design
G434
A
2016年4月6日
责任编辑:宋灵青
1006—9860(2016)07—0043—09
* 本文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系浙江大学2016年重大基础理论专项课题“面向意义学习的现代教学设计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6ZDJC004)研究成果。
① 资料来源:John Sweller: Working Memory, Long-term Memory, and Instructional Design.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Memory and Cognition, Available online 19 December 2015。本文翻译得到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