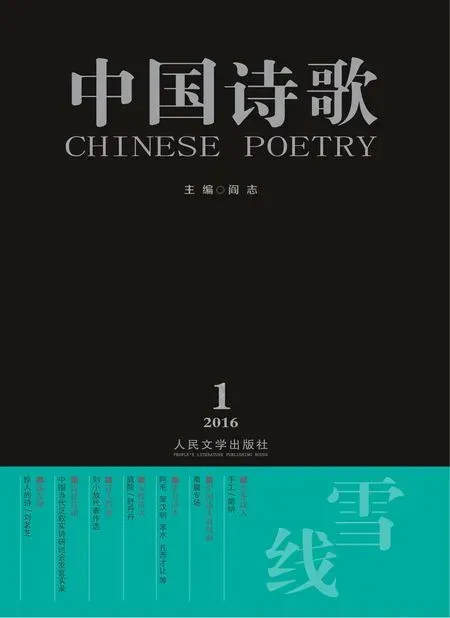舒丹丹诗歌阅读札记
✿高春林
舒丹丹诗歌阅读札记
✿高春林
一个诗人首先是那种有着自由精神的人,可以不无怀疑地说这是一个高贵的人,以其语言的力量,走向事物深处和走向世界的一种方式。当然一切关于自由话语的前提就是不自由因此陶渊明式“归去来兮辞”、“心远地自偏”的那种境界一直以来也就成了人们所感念和探寻的一个自然情怀。尽管魏晋时代深有土壤的自由不会再被我们所拥有,尽管从琐碎的日常化的生活场景走出都成为一个难事。在生活现实与超验世界之间,诗人从未停止过内在精神的诉求,这也是诗之为诗的意义所在,即便“搭建一座云中的庭院/没有人知道这种虚构和专注/带给我怎样的意义”(舒丹丹《庭院》)。舒丹丹在这里“怎样的意义”的疑问,相对于深居都市之霾,或“从栅栏间我打量路过的麻雀”的一个处境,也就有了让人深思的美学意义。美的情愫在其中,叹息也就紧跟其后。我们的都市和历史上的都市大概没有什么两样,多出来的或许是高楼、灯光和速度,人们在感受物质带来的一种幸福指数的同时,月亮退隐到了云层的另一面,精神的向往在几乎不断的雾霾里变得迷离,“我深陷在樟树的浓荫里/与一个看不见的声音独语”,诗人试图在这种“深陷”中建造一个“庭院”——一个让“一种缓慢”属于自我,一个让喧哗、争吵、命令关在门外的“独语”空间。在这里,自然事物与人的内在追寻之间的对应就是一种自由精神,这几乎有着陶渊明式的情怀和浪漫主义的主题,但舒丹丹没有停留在对浪漫的认知上,在她干净而安静的诉说背后,一种现实与自然之间的悖论关系、日常世界的迷津与纯美自然的悖论关系,转义为语言上的交锋。当人们在一味强调先锋、现代、甚至那种词语破碎之处的现场感时,先锋也许会反方向而来,自然和自然中自由的部分会自觉地站在我们面前。唐人不解陶渊明——多半的理解只是“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的“饮者”;宋人发现陶的真谛——苏轼独好渊明诗,“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这里包含了一个“理”字,有着追寻自由精神的历史语境中所蕴含的现实意义。现实的问题是我们的修辞上的审美在探寻精神活动时发现了什么样的历史社会和生存的真相。在舒丹丹的诗中,“路灯,貌似无辜地暧昧着,灯影/随时插足树影。墙角下,千万条潜流/像来历不明的悲哀,涌起,汇聚”,现实有着这样的不堪,这首《暴雨将至》所带来的一个象征的世界指定不是我们想要的一个境遇,但问题就在这里——“一场风暴就带来一个冬天”。这首诗看似在写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但唤起内心的却是一个生存意识。“当季节像心性一样无法信任,/还有什么可诉说的呢”……诗人的悲哀也许就是所有人的悲哀,“悲哀,应该像尊严一样珍贵——/她慢慢揉碎,桌上未完成的半首诗”。愤怒由此可见,或者换一个角度说,一种对自然美的呼唤,从另一个方向就如同风的意思一样自然而然地到来了。“诗是长了脚的钉子,自己跑到了/墙上。”无论是《兰德庄园,或杏林在望》,抑或《登黄花岭》,“寻一种与灵魂对应的植物”,就成了一种必然。
“风景”不是我们所求,但经历了都市城市、雾霾命令的生存经验之后,自然事物作为一种远离现实的矛盾特性,出现在我们的诗篇中,也就产生了剥离现实的力量。当自然与自我相统一,当干净的语言在自然中更为干净,“一朵云、一棵树、一条河流,吁请我们与之相融,并在这种相融中把世界给予我们,把存在的完整性给予我们。……进入世界,进入存在和自我的逍遥,人与物化是同一条道理。”耿占春在《事物的眼睛》中说,“站在一座烟囱、一辆汽车面前,我们的自我是不会消失的,是无法与之物化的。我们即是钻进其中,也还是一个物我两元的主体,而站在一朵云、一棵树下,我们也会已经是进入了其中”。自然就是一种美的审视,是自由给予了内心一方“满足感”的天空。如果说舒丹丹的《庭院》是深陷在巨城与俗世中对自然事物的一种渴望和诉求的话,那么《登黄花岭》可以算作是对这种精神游历的一次较为彻底的兑现,在一个自然之所——黄花岭的美,物化了一个人的自我。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空间,自然的修辞学在作用于世界时,它的象征性首先是从美这个深具魅味的词诱发而生的,对现实保持了排斥性排他性的隐喻关系,这种关系更多是一种距离。在我们的世界,人与自然之间,因为现实的沉重与破碎很难完成自然之物与人类自我的一次统一,即便多数时候身在自然。但诗的语言始终在探寻着,从挣脱现实到自然之魅,从“抗拒”到“逃离”。也只有在此时此地人才彻底放下心来,如舒丹丹所写,“天空蓝得没有一丝缺憾,每个人脸上/都有光辉”。
当审美遇到了真正的美,会是什么样子?自然会不会带来语言上的信任感?我们的修辞学在这一时刻该保持怎样的一种敬畏?茨维塔耶娃的诗句是“在天空之上是我的葬礼!”(《约会》王家新译),菲利普·拉金写道“随后长久的叫喊/喧闹地漂浮着,直到消失”(《草地上》舒丹丹译),蓝蓝的诗写道“‘啊!一切都完美无缺!’/我在草地上坐下,心酸如脚下的潮水/涌进眼眶”(《哥特兰岛的黄昏》)。美,在一个历经沧桑的人的眼中所呈现出来的力量,像电流,让语言回到了事物诗意化的本质。现在来看看舒丹丹的《登黄花岭》,诗人一开始保持了一种谦逊、小心、甚至女性的那种羞涩,貌似是生怕打扰了那个寂静,而深藏在内心的其实是迫切的期待,她深知这是“高处的风景”,因而并不容易,其中的“曲折”需要的是探寻的勇气和热望。我因也是一个在场者,在看到她的这个曲折时,分明知道是一种写实,但读到“肠胃或灵魂的微微晕眩”这样的句子还是有着微微的震动。对于舒丹丹来说,她的语言的优越(也可能是缺点)就是在这首诗中维持了一个诗意化的场景或者说保持了一个女性单纯的天性。她的审美,在这一天性中建立在了对自然信任的基础上,人与自然相处有了一种合情合理的美学成分和自由空间,甚至沉浸在一个对植物辨认的喜悦中,可以忘却所有的现实与现实给定的生存困境,“我们的姿势……/随松针间的夕光摇晃,闪烁”。自然的优雅带来了语言的优雅,但诗人不刻意于炫耀,毕竟我们都清醒地知道,这不过是一次“迷恋”,接下来可能是“岔道”。但从一种审美现象上看,语言的触须一经接触到这个“美”便有了一种心境,这是修辞上的力量,也是一个诗人敏感于感知的事物带来的境界。“审美现象毕竟是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有能力不断见到周围的活跃生机,不断生活在一群精灵的包围中,他便是诗人”(尼采《悲剧的诞生》)。在《登黄花岭》的最后一段,舒丹丹机智地从“迷恋”回到了思考——“寻一种与灵魂对应的植物,/或者吹一吹山风,消解/从山下带来的恍惚和羁索”。这种思考或思辨,正如她的另一首诗《兰德庄园,或杏林在望》中的句子“星空下的夜路,通向疾驰的语词的列车,/需要来来回回地走”。审美与修辞,就像是语言在上升的风景中的一次游历,相互对视、触摸、交融。这从另一个层面看,自由精神并不在某个风景中,而在我们的内心以及给出的语言的一个锋刃上。德国哲学家谢林说:“美这个词是从更高一层的柏拉图的意义上来说的。我坚信,理性的最高方式是审美的方式,她涵盖所有的理念。……精神的哲学就是审美的哲学。没有审美感,人根本无法成为一个富有精神的人,也根本无权充当人的精神去谈论历史。”对于诗人来说,诗的语言也就是审美的语言,从现实到自然,一个审美的过程也就是自由精神打开的过程,在这里,诗如何唤请灵性,我的理解是从澄明开始。
大学生诗群

王子瓜 西 哑 赵燕磊 朱光明 莱 明 张左左杨默 徐英杰 何 骋 何 冲 吴 猛 向浩源黑 多 陈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