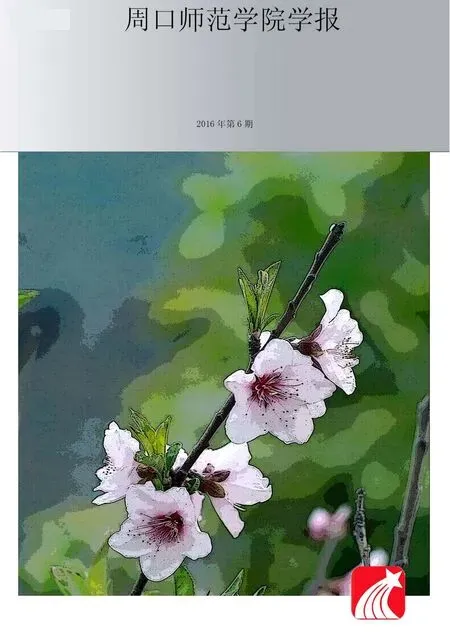“花情人性”入诗来
——论孙新华诗歌中的自然美
崔晓艾
(周口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周口 466001)
“花情人性”入诗来
——论孙新华诗歌中的自然美
崔晓艾
(周口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周口 466001)
周口女诗人孙新华的诗歌着重刻画自然美。其笔下的自然美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以目观物”审美模式下等同于艺术的自然美;“以我观物”审美模式下承载道德伦理的自然美;“以物观物”审美模式下生命绽放的自然全美。她的诗歌所运用的自然美观照方式呈现出杂糅性的特点。其诗歌中“以物观物”视角下的自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有的只是独立无依的生命绽放之美,这在生态日益恶化的今天,对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孙新华诗歌;自然美;审美模式
从古至今,自然就是很多诗人钟情的对象。进入现代以来,生态女性主义者把女性的目光投入自然领域中去,在他们看来,强大的男权社会认为“男性等同于‘人’,属于精神世界,女性等同于生理和自然的领域,属于物质世界”[1]。这与西蒙·波伏娃所说的“男性的行为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将生存本身变成了一种更高的价值;这种行为战胜了生命的无目的,也使自然和女性臣服在脚下”[2]是一致的。在这样的社会传统浸淫下的女性似乎先天地更亲近自然,本能地可以与自然和睦相处。
作为女诗人的孙新华在诗歌《花情人性》中写道:“这些花草不张扬,不显耀,不狂妄,尽情尽兴地接纳阳光雨露的滋润,在你蓦然不经意间已抽芽、吐穗、绽放。……愿如一株平淡的花厚实的草,铅华洗尽,只注重生命的厚实和平淡。”其诗集《结香花》中的花情人性无不流露出作者对自然的关注与向往。“花情人性”入诗来,自然在作者的笔下,大多以花为载体呈现出来。或长或短的诗,或浓或淡的花,于花情人性中显示出作者强烈的自然情结。读者透过作者对花情人性的描述,可以窥见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北宋哲学家兼诗人邵雍在《观物内篇》中说:“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圣人之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3]这里提到了几种观物方式:“观之以目”“观之以心或以我观物”“观之以理”“以物观物”。当然,邵雍是在谈如何把握“物”,即认知“物”,这与对“物”的审美不同,但仍然可以借此切入对自然审美的研究中,因为他所说的观物方式在审美实践中同样存在。借鉴邵雍的观物(花)方式,孙新华诗歌中花的美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以我观物,承载道德伦理的自然美;以目观物,等同于艺术的自然美;以物观物,生命绽放的自然全美。
一、“以目观物”:自然美等同于艺术美
在孙新华的自然诗中,观花亦是观物。“以目观物”在邵雍看来是初级的观物方式,只是靠感官实现对物的把握,从实现对事理认知的角度来看,这是认识的低级阶段,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以目观物”则是审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目”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利用身体感官去感知,任何审美活动都不能脱离审美感知而仅凭抽象的理性推断。作者在《三月的红盖头》中写到了对紫藤花的感知:“满院的紫藤花开了,那一串串淡紫色的花坠悬挂在藤蔓,一树树,一行行,排列着,无拘无束,若绚烂的紫色云霞,恰似青春的火炬手。” 这些诗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诗中有画”的念头会闪现在大多数读者的脑海中。这些美丽的诗句凝成的是一幅画,读者也如同在欣赏一幅图画。在这里,紫藤花表面上是被作者视为自然美“以目观之”的,但本质上则是被视为艺术美来欣赏的。
首先,作者笔下的自然美与艺术美的感知方式相似。自然物和艺术品一样都属于物,不仅有为人而存在的外在合目的性即有用性,而且还有其内在的合目的性。“内在合目的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有机性”,是个别事物自行将“原来零散的因素结合成为一体”[4]。这里的“一体”就是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物”,或是自然物或是艺术品;“零散的因素”对自然物来说指阳光、空气、水、种子等因素,这些本来零散的因素被凝成一体成为固化的自然物,也就是为自身存在而不是为人存在的自然物;同样,艺术品也是有其“零散的因素”的,如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原》中所举的凡 ·高的油画《农鞋》,无论是质料还是形式,构成自然物和艺术品的“零散的因素”显然不同。这就决定了对自然物的感知不仅仅“以目观之”就够了,还需要审美的其他感知参与,即除视听觉之外的嗅味触等感觉,但艺术品大多却只需要视听觉参与再加上丰富的想象力即可。拿紫藤花来说,在“以目观之”时,这里的“目”不应局限于视觉,还应该包括“听”——紫藤花在风中的摇曳,“嗅”——紫藤花淡淡的香味,触摸——紫藤花的花瓣或叶片等。
因此,作者的诗歌在对紫藤花这一自然物描述时更多地采用了视觉这一感知,与艺术美的欣赏方式相似。在作者的某些诗歌中甚至看不到自然物的“模样”,即视觉的作用似乎也没有凸显,如《隐隐地散发一种气息》中提到的“龙胆花”和“观音草”。对自然的审美如果能奠基于鲜活的感知,尤其是调动全部感知参与其中,由此生发的真情实感用轻灵的语言表达出来或许更能打动人。
其次,作者笔下的自然美与艺术美的欣赏方式相似。在传统主客二元论支配下的艺术欣赏中,艺术品作为客体被主体进行欣赏,客体被框定在有限的范围内,审美主体关注的是客体的感官与设计属性,以及所具有的表现属性,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联想和想象。这种传统的艺术欣赏模式往往被审美者带到现实的自然审美中去,如作者对紫藤花的欣赏。作者静观紫藤花的美,从作者的语言描述中可以感受到,紫藤花这一自然物被设置为静观的审美客体,被作者在想象中从周围的环境中移除出来,装上了无形的画框,其实质与一幅艺术作品毫无二致。而事实是,作为自然物的紫藤花不可能脱离周围的环境存在,这也是它被称为自然物的重要原因。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对紫藤花这一自然物进行审美时,要考虑到自然物与周围环境的联系,因此它有更多不同的审美属性,这就是它与周围环境存在有机联系的体现。也就是说,当紫藤花被作为客体静观的时候可能体现出来的是“满院的紫藤花开了,那一串串淡紫色的花坠悬挂在藤蔓,一树树,一行行,排列着,无拘无束,若绚烂的紫色云霞,恰似青春的火炬手”。因此,无论是从对自然美的感知方式还是欣赏方式来说,作者自然诗中的自然美更倾向于把自然当作艺术品描述。所以,在“以目观物”中,自然美等同于艺术美,这是传统自然审美中较为普遍的欣赏模式。
二、“以我观物”:承载物质功利和伦理情感的自然美
从古至今,人们在欣赏自然美时不仅关注其外在形式,而且往往把它与物质功利和伦理道德联系在一起,即采取“以我观物”的方式去观照自然物。邵雍提到“以我观物”时这样说,“以我观物,情也”。说明这里的“我”是属人的,“以我观物”即是指人类自封为主体,从主体的视角审视作为客体的自然,把人的情感放在自然物上,自然是被人化的结果,自然因人而美。
孙新华的很多诗歌着力展现自然之美,如《那一丝的柔情》《君子兰》等。作者笔下的自然美大多着上了“我”的色彩,体现出“以我观物”的审美方式,即“我”用人的伦理道德情感观照自然物:所以“一朵花已经和一段忠贞的爱情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君子兰被称为“谦谦君子”;桔梗“质朴美丽,而又用心良苦”;白兰花则用“纯洁的心开花”,懂得“保持一种乐观向上的心态”;等等。总体来说,从“以我观物”的视角看,这些象征功利伦理的自然诗歌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功利情感下的自然美;一类是伦理道德情感下的自然美。
首先看功利情感下的自然美。墨子曾说:“食必常饱,然后求美。”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明确提出物质需要是人类的最低层次的需要,也是高一级精神需要产生的基础。这些都在告诉我们,审美是需要物质基础的。因此,在人类审美意识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从功利性向非功利性过渡的特征。尤其是在人们无法满足最基本的物质需要时,评判自然的标准只是有用与无用,即用物质功利性的标准评判自然,有用即美,如古代把“美”字解释为“羊大为美”,就是从物质功利性出发判断“物”的美丑的。
在诗歌《我的心情被染得金黄,金黄》中,孙新华这样写道:“是花也是药,除了能给人带来视觉上的美感,亦能祛除病痛。……只知道向大自然一味索取的人们呀,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其中提到的能祛除病痛的花是“连翘”,本来兀自生长的花此时被人们赞美,原因就是对人有用,可以祛除病痛。另一首诗歌《只是一种花的味道》所说的桔梗,“能生出清肺的枝,长出止咳的叶,吐出化瘀的蕊”,其枝其叶其蕊,无不是人类可资利用的药材。物质功利左右下的“以我观物”,以人类的价值偏好审视自然,很容易就会做出善(有用性)即美、不善即丑的审美判断。
其次看伦理道德情感下的自然美。“以我观物”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我”赋予自然以伦理道德情感,即自然是伦理道德的象征。
庄子曾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里的“天地”被赋予了“不言”的美德。中国美学关于自然美的理论“比德说”就是认为自然的美在于与人的道德品质和伦理性质相通。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里的山和水不是因为其险峻和清澈得到赞赏,而是与仁者的宽厚和智者的灵动相似才得到喜爱的。这种象征伦理道德的自然审美观的形成与人类社会文明的飞速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各个领域的文明成果使人类的精神意识变得更加开阔,此时的自然不再是仅仅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对象,也是人们精神寄托的对象。可以说,把自然美当作伦理道德的象征也是人类自然审美意识的发展,是儒家对人重视的具体表现,而社会作为自然的高级表现形态,以人为核心的社会美必然要高于自然美,而自然之所以美也必然与人的因素有关系。
在孙新华的诗歌中,把自然美与人的伦理道德情感联系起来的例子比比皆是。《有一种爱》中,白杨是“伟岸”的;《心向长空》中,量天尺有“丈量天空的勇气”;《哦,让我如此醉心》中,君子兰是“谦谦君子”;《娶荷为妻》中,荷花“深入泥土,在污泥淤土的深处安放一颗坚定而澄澈的心”……在这里,“以我观物”下的自然美被赋予了人的伦理道德情感,契合人们的伦理道德情感,满足了人们精神上的功利性需求的自然物便会得到钟情,这样的自然是美的。王国维也涉及了“以我观物”,具体表现为其提出的诗歌意境——“有我之境”,诗人在审视“物”时,赋予“物”以主体的情感,这里并没有提到伦理道德判断,更多地是指主体的情感注入“物”中,着上了“我”之情感色彩。虽然“有我之境”与伦理道德情感下的“以我观物”有区别,但总的说来,这里的“物”还是带着“我”——人的因素。
三、“以物观物”:生命绽放的自然全美
以上提到的“以目观物”倾向于把鲜活的自然当作静观的艺术品去观照,而“以我观物”则倾向于带着“人”的因素观照自然,如杜夫海纳所说:“仍然是人在向他自己打招呼,而根本不是世界(自然)在向人打招呼。”[5]这两种观物方式虽然出发点不同,但在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却是一致的,都是把人类放于高高在上的主体地位,把自然看成是为人而在的客体对象。
显然,这些审美模式是为欣赏艺术品量身打造的,但在自然审美领域的运用中却有捉襟见肘之处。自然在人类的审美标准筛选下必然会有美丑之分,这种等级区分直接会导致人类对自然的好恶之心,其产生的恶果显而易见。西方的一些学者却认为“自然总是美的,自然从来就不丑”。彭锋在《完美的自然》中取中西方理论支持“自然全美”的观点,如庄子的“齐物”、禅宗的“见性见佛”、儒家的“忠恕”等思想[6]。这就从根本上排除了人类赋予自然的高低优劣之分,才能真正地实现邵雍所说的“以物观物”。
邵雍在解释“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的原因时认为这是因为“圣人之能反观也”,“反观”就是排除了“观之以目”和“观之以心”,就可以做到“以物观物”。其大意是指回到万事万物的本原,去关照事物的原本状态。由此推及自然审美,则要求人类能做到“齐物”,万物齐一,无优劣大小之分,才能观照到自然之大美。这种自然的大美就是万物生命绽放的美。
在孙新华的自然诗歌中,也不乏“以物观物”这样的诗句。《叶中花,花中叶》里,诗人这样写东方的花和西方的花:“让我们各自弥漫各自的芬芳,各自抖露各自的风采。”各种花虽然地域不同,但都是自然的物种,无所谓优劣高低,都有自己生命绽放的风采。作者笔下的狗尾巴花也全然没有世俗眼光中的卑贱、低下,她由衷地感叹道:“作为客观存在,它们都在植物王国里占有一席之地……万物共存共荣,才有我们芸芸的大千世界。”孙新华在《刈后的田野》中,充满激情地表达着对自然的亲近:“我决定把自己放低,一直低到田野里,低到能和泥土自由自在地亲吻,能倾听到它们急促而兴奋的呼吸。”人类如果一直持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微不足道的泥土,是永远也倾听不到它们的生命在绽放时那“急促而兴奋的呼吸”的。
综上所述,孙新华的自然诗歌是“观之以目”“以我观物”和“以物观物”审美模式下的产物。诗人在感知自然中,既有运用传统的审美模式把自然等同艺术品进行观照的描写;又有运用自然“人化”的手段,赋予自然物质功利和伦理道德意味的赞美;也有强调万物齐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自然全美理念。作者诗歌所运用的自然美观照方式呈现出杂糅性的特点,是作者多视角观察自然的结果。如能在对自然进行感知时投入更多的感知觉,全方位地体味自然,而不是把自然当作静观的艺术品去观照则更好。她的某些诗歌中以“我”之功利和伦理道德评价自然物似应更含蓄。可贵的是,作者诗歌中“以物观物”视角下的自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有的只是独立无依的生命绽放之美,这在生态恶化的今天,对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王丽丽.自然·平等·和谐:解读《达洛卫夫人》生态女性主义意识[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1(1):12.
[2]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李强,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31.
[3]邵雍.皇极经世书[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900.
[4]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76.
[5]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M].孙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46.
[6]彭锋.完美的自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43-287.
2016-03-01
2017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河南当代女作家创作中的女性形象建构”(2017-ZZJH-632)。
崔晓艾(1972-),女,河南孟津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
I207.2
A
1671-9476(2016)06-0034-03
10.13450/j.cnki.jzknu.2016.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