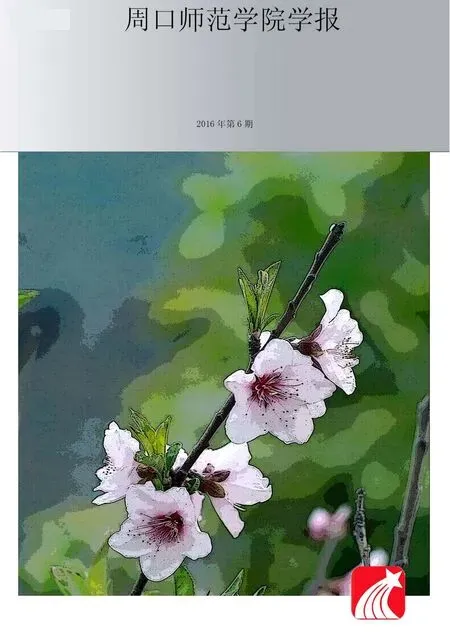论方世举的韩愈诗歌批评观
丁俊丽
(陕西理工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0)
论方世举的韩愈诗歌批评观
丁俊丽
(陕西理工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0)
清代方世举深研韩诗,其《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是最具价值的韩诗单行注本。通过《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还可以窥见方世举的韩诗批评观。方世举用“诗要有理”“师古不泥古”的诗学思想,注重诗歌体格、音韵、宗派的诗评观批评韩诗,深入揭示韩诗意旨,并解决了韩诗评论中的许多纷争。
韩诗;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诗歌批评观
方世举(1675—1759),字扶南,晚号息翁,康熙监生,安徽桐城人,清代学者方章钺之孙、桐城派创始人方苞之从弟。方世举师从朱彝尊,与当时名儒多有交往,如李绂、马曰璐、马曰琯等。方世举曾受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南山集》案”之累,远戍塞外。雍正元年(1723)恩诏放归田里,尝寓扬州。方世举布衣一生,潜力学问,淹通文史,著述宏富,著有《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春及堂集》《兰丛诗话》《汉书辩注》等。《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中有笺注,有诗评。方世举笺注韩诗,成就卓著,展现了其深厚的考据学功底。同时,方世举用自己的诗歌理论及诗歌批评观批评韩诗,也颇具特点,值得后世韩愈研究者借鉴。
一、用“诗要有理”的诗教观探析韩诗之“理”
方世举《兰丛诗话》曰:“诗要有理……一事一物皆有理。只看《左传》藏孙达之言‘先王昭德塞违者,如昭其文也’之类,皆是说理,可以省悟于诗。杜牧之叙李贺集种种,言其奇妙,而要终之言曰:‘稍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可见词虽有余,而理或不足是大病。”[1]784鲁隐公纳郜鼎于宋,置于宗庙。臧孙达以君主应发扬各种美德为依据对鲁隐公违礼之举进行劝谏,方世举将此要求移之于诗,强调诗歌要有传达儒家道统思想的功能,起到教化人心、美刺讽谏的作用,即“诗要有理”。这实际秉承了儒家的诗教观,与韩愈“文以贯道”创作理论一脉相承,与方苞“言有序,言有物”的古文“义法”说相呼应。韩愈提倡“文以贯道”的创作观,历来学者多认为韩文是道之载体。方世举则认为诗与文一样要有昭德塞违的作用,以其“诗要有理”的诗学观对韩诗探幽抉微,深入揭示韩诗蕴含之“理”。之后魏源也曾评韩诗曰:“当知昌黎不特约六经以为文,亦直约风骚以成诗。”[2]190《送进士刘师服东归》一诗,宋黄彻评曰:
昌黎《送刘师服》云:“携持令名归,自足贻家尊。”苏州《送黎尉》云:“只应传善政,朝夕慰高堂。”诚儒者迂阔之辞[3]446。
元和八年(813)刘师服下第东归洛阳,韩愈欣赏其才华、勇气,作诗勉励其来年再来考。“令名”是好的声名。《左传》“令名载而行之”,有使德行传播四方之意。韩愈在诗中以“携持令名归,自足贻家尊”劝勉刘师服,即坚持以美德行事,可慰藉亲人。黄彻认为韩诗所言是迂腐之词,方世举驳斥黄氏观点,曰:
按:……此诗“携持令名归”,自是粹然醇儒之言。巩溪迂之,何耶?诗中“骨鲠”二语,从“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得来[3]446。
方世举认为韩愈劝勉刘师服应以美德行事,属于儒家正统的教育观,此种行为才是真正醇儒思想的展现。方世举还特意诠释出“骨鲠”典故源出刘琨狱中所作《寄赠别驾卢谌》诗,以比刘师服的高尚气节。方世举可谓尽可能地寻绎韩诗的每一个细节,从中诠释出韩愈的“明道”意图。又如《元和圣德诗》,苏辙曰:
韩退之作《元和圣德诗》,言刘辟之死曰:“婉婉弱子,赤立伛偻。牵头曳足,先断腰膂。次及其徒,体骸撑拄。末乃取辟,骇汗如泻。挥刀纷纭,争刌脍脯。”此李斯颂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谓无愧于《雅》《颂》,何其陋也?[3]328
元和元年(806)朝廷斩叛党杨惠琳、刘辟,收复夏、署,平定青、徐之乱,出现了暂时的中兴局面。元和二年韩愈作《元和圣德诗》歌功颂德。苏辙批评此诗描写朝廷斩首西川节度副使刘辟及其家族、党羽场面过于残忍,有失《雅》《颂》温柔敦厚之风。张拭批驳苏辙,曰:
诵退之《圣德诗》至“婉婉弱子”“处世荣举”,子由之说曰:“此李斯颂秦所不忍言。”……盖欲使藩镇闻之畏罪惧祸,不敢叛耳。今人读之至此,犹且寒心,况当时藩镇乎?此正是合于《风》、《雅》处,只如《墙有茨》、《桑中》诸诗,或以为不必载。而龟山乃曰:“此卫为狄所灭之由。”退之之言亦此意也。退之之意过于子由远矣,大抵前辈不可轻议[3]328。
张拭认为此诗正合《风》《雅》,有教化人心之作用。方世举对二者观点进一步辨析曰:
按:苏、张二说皆有理,张更得“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义。《甘誓》言不共命者则孥戮之,而况乱臣耶?言虽过之,亦昭法鉴[3]328。
方世举对二人观点都持肯定态度,但更赞同张拭的看法。方世举将此诗以比《春秋》《尚书》儒家经典,认为其有昭德塞违的作用。诗歌语言描写虽过,但对当时狼子野心的藩镇却有警示作用,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大一统。方世举对这首歌功之作评价可谓极高,确实融进了自己“诗要有理”的诗学观。又如《琴操十首》,方世举认为是韩愈贬潮州后效先贤而作,评曰:
按:《琴操》十章,未定为何年所作。但其言皆有所感发,如“臣罪当诛”二语,与《潮州谢上表》所云“正名定罪,万死犹轻”之意正同,盖入潮以后忧深思远,借古圣贤以自写其性情也。若《水仙》、《怀陵》二操,于义无取,则不复作矣[3]602。
方世举以“诗要有理”的诗学观分析此诗作于贬潮期间,并用《古琴操》进行解释。《古琴操》十二首,多是表现古圣贤为维礼而发出的不平之鸣,《水仙》《怀陵》二操无深意,因而韩愈无取。这很符合韩愈因维护儒统驳斥佛法被贬潮州后的心情。在韩诗诸多注家中,钱仲联吸取了方世举的观点。又《将归操》后评曰:
按:“涉浅”、“乘深”四句,从屈原《九章》“令薜荔而为理兮,惮举趾而缘木。因芙蓉而为媒兮,惮褰裳而濡足。登高吾不悦兮,入下吾不能”化出。“无与石斗”、“无应龙求”,即“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之义也[3]604。
韩愈此时正处怀才不遇之时,方世举用屈原不遇时的作品《九章》阐释韩诗诗旨,甚是恰当;接着又用孔子教育弟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美德解释诗句“无与石斗”“无应龙求”的意思。孔子以周礼之道告诫弟子,不去不守礼的邦国谋职,在守礼的邦国必须谨记行周礼之道。方世举此解道出了韩诗所表达守礼之理。
方世举还依“诗要有理”的标准批判韩诗中的浅显之作,如评《赠族侄》“词浅意陋,或非公作”。又如评《独钓四首》曰:
按:四诗之中,纤小字太多,一首藤角芡盘,二首柳耳蒲芽,四首芡觜梨顋,小家伎俩耳,不可法[3]562。
方世举认为此诗纤弱,缺乏韩诗磅礴雄浑的特点,没有深刻意义,不足为学。
二、以“师古不泥古”的诗学观论韩诗,承中有变
方世举提倡诗歌创作学古,但不落古人窠臼,自具风标,自开派别。这一点与韩愈的诗学理论较为契合。沈德潜编《国朝诗别裁集》时欲收方世举诗,方世举止之,作《沈归愚宗伯方选今诗闻以余入放言有作寄而止之》诗,其中“过情犹记题黄绢”句下自注曰:“前来书,以为熔铸古今,自开生面,而不受前人牢笼云。”此是沈德潜对方世举诗的极高评价。方世举能结合韩诗创作背景,挖掘韩诗承中之变,自成一家的特点。
韩愈《叉鱼招张功曹》与杜甫《观打鱼》同题材,但用意不同。《巩溪诗话》曰:“老杜《观打鱼》云:‘设网提纲万鱼急。’盖指聚敛之臣,苛法侵渔,使民不聊生,乃万鱼急也。……‘吾徒胡为纵此乐,暴殄天物圣所哀’,此乐而能戒,又有仁厚意。亦如‘前王作网罟,设法害生成’,不专为取鱼也。退之《叉鱼》曰:‘观乐忆吾僚。异此意矣。’亦如《蕲簟》云:‘但愿天日恒炎曦。’”[3]135黄彻认为杜诗是以打鱼讽刺扰乱民生的行为,是关心民生疾苦的表现,而韩诗则是描写打鱼之乐,不免对韩诗有所不满。方世举辩解曰:
按:论人当观其大节,论诗当观其大段,不可摘其一事一句而议优劣也。且杜作于前,韩继于后,固自不肯相袭。诗甚工细,有何可议?至于《蕲簟》之愿天炎,乃反衬簟之凉也[3]135。
黄彻认为二诗题材相同,题意必然也要一致,不免过于牵强。方世举从诗歌创作要能自树立的原则上给予辩解,认为“杜作于前,韩继于后,固自不肯相袭”,也符合韩愈自己的诗歌创作理论。诗歌创作有特殊的背景,特殊的用意。此诗贞元二十一年(805)春韩愈在阳山作,当时与张署同贬南方,二人距离相近,同病相怜。韩愈邀张署前往打鱼,以表达对同僚的想念之情。二诗虽都与打鱼有关,用意则截然不同,必不能同论高下。又如《城南联句》,方世举曰:
按:此诗凡一百五十韵,历叙城南景物,巨细兼状,虚实互用,自古联句之盛,无如此者。……其铺叙之法,仿佛《三都》《两京》,而又丝联绳牵,断而不断,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非其才大,安能如此?诗云:“肠胃绕万象,精神驱五兵。”又《送灵师》云:“纵横杂谣俗,琐屑咸罗穿。”可移评此诗也[3]281。
此诗极尽铺叙城南景物,手法又似汉大赋,但方世举在大同中看到了韩诗的细微变化。与《三都赋》《二京赋》铺叙零散景物相比,韩诗“丝联绳牵,断而不断”,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方世举还以韩评韩,用韩愈《送灵师》“纵横杂谣俗,琐屑咸罗穿”概括此诗特点,可谓恰当,又极具说服力。又如《秋怀诗十一首》,樊汝霖认为此诗学《文选》“偶丽翰藻”风格,是《文选》体,曰:
《秋怀诗十一首》,《文选》诗体也。唐人最重《文选》学,公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文选》弗论也。独于《李郱墓志》曰:“能暗记《论语》、《尚书》、《毛诗》、《左氏》、《文选》。”而公诗如“自许连城价”、“傍砌有红药”、“眼穿长讶双鱼断”之句,皆取诸《文选》,故此诗往往有其体[3]437。
而刘辰翁则以为此有韩诗一贯的豪宕之风,并非《文选》体,曰:
《秋怀诗》终是豪宕,非《选》体也[3]437。
以上两说各执一词,都只是抓住了此诗特点之一面,无对错之分。方世举进一步解释:
樊、刘二说皆有可取,盖学《选》而自有本色者也。《文选》之学,终唐不废,但名手皆有本色。如李如杜,多取材取法其中,而豪宕不践其迹。韩何必不如是耶?[3]437
方世举从此诗创作的根本分析,即“学《选》而自有本色”,学古不拟古,有韩愈自己的特色,这正是各评家所忽略的方面。
方世举诗歌有以才学为诗的特点,追求用典,但反对用古太过,强调诗要保持自己的风格。方世举对韩愈用典过多的作品甚为不满,如评《赠崔立之》:
按:此诗不足为法。凡引古过演,文且不可,而况于诗焉。有寥寥小篇,演至大半者?演则精神不振,演则气势不紧。其下又并无精神,并无气势。惟落落漠漠,就缴六语以了之,此岂起衰八代者之合作乎?一时败笔,人所时有,但学者不可乐其易为而效之[3]451。
方氏认为此诗用古繁多便失去了韩诗特有的磅礴气势,属韩愈一时败笔,不值得效仿。
三、注重从体格、音韵、宗派角度分析韩诗特点
关于如何评点诗歌,方世举认为应从诗之大端,即体格、用韵、宗派方面评析。“余少学朱竹垞先生家,见《草堂诗话》之专言杜者,凡五十家,他可知也。然可取者少,又仅以字句为言,其于学诗之大端,体格异同,宗派正变,音韵是非,绝未及之……”[1]769当然,方世举的看法不免有些绝对化。但在韩诗评析中,方世举注意从这些方面探究,使得韩诗中一些争论不止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而且可以从中看到韩诗的特点及渊源。
(一)从体格角度评韩诗
方世举认为评体格是评诗之大端。《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中对多首韩诗从体格方面分析,如评《刘生》诗曰:
《刘生》本乐府旧题……《古乐府解题》云:“刘生不知何代人,观齐、梁以来所谓刘生诗者,皆称其任侠豪放,周游于五陵、三秦之地,大抵五言四韵,意相类也。”公以师命姓刘,其行事颇豪放,故用旧题赠之,而更为七言长篇。集中有用乐府旧题而效其体者,如《青青水中蒲》及《有所思联句》是也。有用乐府旧题而变其体者,如《猛虎行》及此诗是也[3]112。
在方世举之前较少学者分析此诗体格所属。方世举首先从文体角度分析此诗为乐府旧题,并进一步确定为乐府旧题之变体,古乐府旧题为五言,韩诗为七言。方世举还对韩集中其他乐府旧题诗进行了分类。王元启则认为此诗不属乐府古题,曰:“题曰‘刘生’,与《孟生诗》同旨。或以为乐府古题,非是。”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刘生诗》之“往取将相酬恩仇”句下评曰“形之于声诗也”,何焯所说“声诗”应指乐府诗,但没进一步阐释。翁方纲与方世举观点相同,评此诗效乐府旧题,曰:“昌黎《刘生诗》,虽纪实之作,然实源本古乐府横吹曲。其通篇叙事皆任侠豪放一流。其曰‘东走梁汴’,‘南逾横岭’,亦与古曲五陵、三秦之事相合。……不惟用乐府题,兼且用其意,用其事。”[1]1388从韩诗所纪内容看,刘生是一不羁之子,甚是符合《古乐府解题》观点。张德恒、沈文凡《韩愈乐府歌诗创作刍议论》[4]一文考证了韩诗中的乐府歌诗,其中有《青青水中蒲》《猛虎行》等,认为韩愈具备创作歌诗的条件,其做过协律郎,懂得音乐,是创作歌诗的重要基础。这一点方世举早有认识,在《听颖师弹琴》中就已分析韩愈有极深的乐理知识。
韩愈以文为诗的长篇险韵也常引起后人争议,方世举从文体学角度辩解:“昌黎受到刘贡父‘以文为诗’之谤,所见亦是。但长篇大作,不知不觉自入文体。”[1]774如《南山诗》,历来备受争议。明代王嗣奭评曰:
昌黎《南山》,韵赋为诗;少陵《北征》,韵记为诗,体不相袭。而孙莘老、王甫平相提而争优劣,固非。至断定于山谷之评,亦为是也。《南山》琢镂凑砌,诘屈怪奇,自创为体,杰出古今。然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固不易学,亦不必学,总不脱文人习气[5]58。
王氏从文体角度评论韩诗与杜诗不同,抓住了根本。在方世举之前较少学者从文体学角度展开分析此诗。方世举亦从文体角度进行了更为详赡的分析,曰:
按:古人五古长篇,各得文之一体。《焦仲卿妻》诗传体,杜《北征》序体,《八哀》状体,白《悟贞寺》记体,张籍《祭退之》诔体,退之《南山》赋体。……又按《南山》、《北征》各为巨制,题义不同,诗体自别,固不当并较优劣也。此篇乃登临纪胜之作,穷极状态,雄奇纵恣,为诗家独辟蚕丛。无公之才,则不能为,有公之才,亦不敢复作。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者也。近代有妄人,讥其曼冗,且谓连用“或”字为非法,不知“或”字本《小雅·北山》,连用“迭”字本屈原《悲回风》、《古诗十九首》,款启寡闻,而轻有掎摭,多见其不知量也[3]215。
从方世举的言论中可知他应没见到王氏评论,但和王氏的评价一脉相承,其分析更加透彻明晰。方世举肯定《北征》《南山》的成就,指出二诗根本的区别是文体不同,不可并论。又分析了同是巨制而文体不同的原因,即选题有别,所用文体必然各异。方世举对诗中连用“或”字、“迭”字的现象又追溯到了《诗经》这一源头,有力驳斥了蒋之翘以此批驳韩诗的看法。方世举还从文体的角度对古代五言诗中体格有别的作品逐一梳理,加以定性。虽然关于二诗的此种论断不是方世举发凡起例,但在韩诗批注本中却先而为之,并且被认可。近代学者徐震曰:“顾嗣立谓之光怪陆离,方世举称其雄奇纵恣,合斯二语,庶几得之。自宋人以比《北征》,谈者每就二篇较洁短长。予谓《北征》主于言情,《南山》重在体物,用意自异,取材不同,论其工力,并为极诣,毋庸辨其优劣。”[6]462谭嗣同《思篇四六》认为:“宋人以杜之《北征》,匹韩之《南山》,纷纷轩轾,闻者惑焉。以实求之,二诗体与篇幅,各有不同,未当并论。”[7]1632皆是从文体角度进行分析。
当然,这种方法运用得过于拘泥,则有失判断的准确性,如《早春雪中闻莺》,方世举单从文体角度断定此诗属于韩愈早期作品,则稍显牵强。
(二)从音韵、宗派角度析韩诗
韩诗工于用韵,后人对其评价轩轾纷呈。方世举在此方面有过细致分析,如《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诗,评曰:
按:此篇用韵,全以《三百篇》为法。如《楚茨》“济济跄跄”一章,跄、羊、尝、亨、将、祊、明、皇、飨、庆、疆,是庚、阳二韵也。《瞻彼洛矣》末章,泱、同、邦,是阳、东、江三韵也。《凫鹥》首章,泾、宁、清、馨、成,是庚、青二韵,旁乃侵韵也。四章潀、宗、降、崇,是东、冬、江三韵也。诸如此类,不可枚举[3]38。
宋代欧阳修、洪兴祖、胡仔,明末俞玚已评此诗有杂用韵、叠用韵的特点,没有详细分析。方世举与前人观点基本一致,但分析详尽且更深一步,探究出此诗用韵完全以《诗经》为法。他首先分析此诗用东、冬、江、阳、庚、青六韵,与《诗经》中《楚茨》“济济跄跄”一章、《瞻彼洛矣》末章、《凫鹥》首章和四章相同;其次是叠用韵现象,俞玚认为此诗叠用韵本于杜甫,方世举则追溯于《诗经》,并列举《诗经》中大量叠用韵的例子加以证明。方世举还在韩诗叙述手法、用字法方面也溯源于《诗经》,如《病鸱》《南山诗》《嗟哉董生行》等。方世举将韩诗内在思想、外在形式追源于《诗经》,实证了韩诗与《诗经》的渊源关系。又《会合联句》,洪迈《容斋四笔》曰:“除‘冢’、‘蛹’二字《韵略》不收外,余皆不出二‘肿’中。”方世举考曰:“按:‘冢’、‘蛹’二字《唐韵》所收,此诗未尝出韵,洪亦失考。”[3]256
方世举熟读唐诗,还曾校过唐诗,“凡唐诗误句、误字、误先后次第者,余辩之,批于各集甚多……”[1]780其对唐诗纷呈的流派变化情况也颇为熟悉。唐诗自大历以降多变调,韩诗便是其中之一。如《盆池五首》,工与否,便存在争议。刘攽《刘贡父诗话》曰:
退之古诗高卓,至律诗虽可称善,要有不工者。而好韩之人,句句称述,未可谓然也。韩云:“老翁真个似童儿,汲水埋盆作小池。”其谐戏语耳[3]380。
洪兴祖曰:
或云:《盆池》诗有天工,如“拍岸才添水数瓶”“一夜青蛙鸣到晓”,非意到不能作也[3]380。
刘攽与洪兴祖所引观点相反,前者认为此诗不工,后者则认为“有天工”。对于见仁见智的争论,方世举从宗派正变上分析辩解,曰:
按:刘、洪两说,一言正,一言变也。大历以上皆正宗,元和以下多变调。然变不自元和,杜工部早已开之。至韩、孟好异专宗,如北调曲子,拗峭中见姿制,亦避熟取生之趣也。元、白、刘中山、杜牧之辈,不得其拗峭,而惟取其姿制,又成一格[3]380。
元和诗坛出现两大主流诗派,即韩孟诗派和元白诗派,以改变盛唐诗难以企及的局面,转而另辟门路。韩孟尚险怪,元白尚平易。方世举从诗歌正调、变调方面对以上两种观点加以辨析。方世举认为刘氏依盛唐诗评其为不工,洪氏则放入中唐变调之诗中评其极工,这就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方世举还进一步明晰唐诗之变始于杜甫,应是对朱彝尊“俚语俚调,直泻胸臆,颇似少陵《漫兴》、《寻花》诸绝”的解释,也对严虞惇“此等语杜诗中最多,何不工之有”的含糊评论做了解答。方世举评析《奉和虢州刘给事使君三堂新题二十一咏》中《月池》诗,对五绝分派梳理。方世举评“寒池月下明,新月池边曲。若不妒清妍,却成相映烛”句曰:
按:五绝分派,王、李正宗之外,杜甫一派,钱起一派,裴、王一派,李贺一派,昌黎一派。昌黎派遂为东坡所宗,而陆放翁承之[3]464。
诸评家对此诗略有微词,蒋之翘评曰:“王元美尝云:‘绝句固自难……得此法者,仅太白一人。王摩诘亦具体而微。此退之《三堂二十一咏》盖亦步武摩诘《辋川杂诗》而未逮者,已不免落宋人口吻’。”[6]898朱彝尊评曰:“首首出新意,与王、裴《辋川》诸绝颇相似,音调却不及彼之高雅。”[6]898査慎行评曰:“二十一章效王、裴《辋川》唱和,古渐远。”[6]898李宪乔评曰:“五绝王、李之外,端推裴、王,老杜已非擅长。至昌黎诸作,多率意为之,实不足以见公本色。”[8]39方世举依凭其对唐诗的深熟掌握,仍从诗歌宗派流变角度分析,对唐诗五绝继王维、李白正宗之外的变调梳理清晰,各家为什么诘难此诗便易理解。
方世举结合韩诗特点,融入自己的诗学观分析韩诗,多有精到之见,其成果也多被后世韩愈研究者参考借鉴,可谓对韩诗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郭绍虞.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陈沆.诗比兴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张德恒,沈文凡.韩愈乐府歌诗刍论[J].中山大学学报,2011(2):16-23.
[5]王嗣奭.杜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7]吴文治.韩愈资料汇编[G].北京:中华书局,1983.
[8]程学恂.韩诗臆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2016-08-10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清代韩愈诗文文献研究”(14FZW037)。
丁俊丽(1979-),女,河南邓州人,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
I206.2
A
1671-9476(2016)06-0001-05
10.13450/j.cnki.jzknu.2016.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