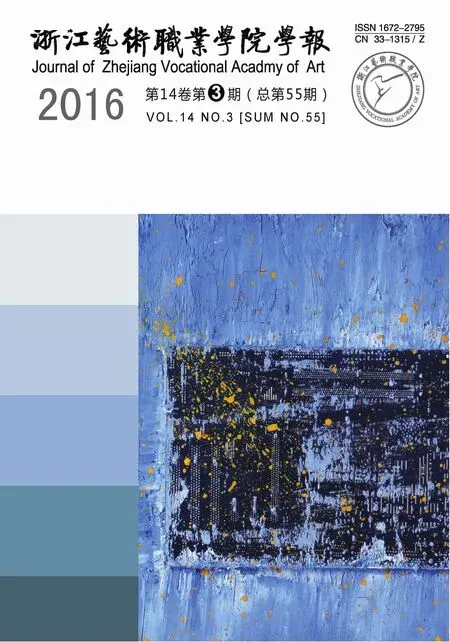中国民乐创作的现状与发展思考∗
——为创作民族音乐舞台能够保留下来的经典作品而努力
刘锡津
中国民乐创作的现状与发展思考∗
——为创作民族音乐舞台能够保留下来的经典作品而努力
刘锡津
一、从不同时期音乐会上的保留曲目,看民乐的创作走向
追溯中国民族乐队的出现与发展,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建鼓呈现的“钟鼓”乐队,证明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规模相当庞大的乐队,而且在音律建制、音色对比、演奏方式等方面,都有了相当的规范。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被世界叹为奇迹的巨型乐器,可以想象,它在当时会有多么辉煌的曲目。可惜没有给我们现代人留下任何资料。
中国的民族乐队在历史上基本是以宫廷乐队、宗教乐队和民间乐队等几种演奏形式存在的。至今,也只有文字记载,而没有任何音像资料。
20世纪20年代,上海“大同乐会”的出现展示了“大型”民族乐队的风采,开启了探索新型民族乐队的重要开端。这个拥有30余人编制的民族乐队,基本上分为吹、弹、拉、打四组。乐队在中国传统音乐的基础上改编了一批适合于这种新型乐队演奏的民族管弦乐合奏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根据琵琶曲《夕阳箫鼓》改编而成的民族管弦乐合奏《春江花月夜》。大同乐会的出现,开创了大型民族乐队生存与发展的先河。
至此以后,从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刘天华的创作,特别是他的10首二胡曲《病中吟》《月夜》《苦闷之讴》《悲歌》《空山鸟语》《闲居吟》《良宵》《光明行》《独弦操》《烛影摇红》,为中国民乐创作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当之无愧地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他的创作,既掌握了民族音乐的创作规律,又吸收借鉴了西洋技法。他将流于民间状态的二胡进行了升格,成为富于独特艺术魅力的独奏乐器。他的二胡曲在人民大众中广受喜爱,成为中国民族音乐宝库中的经典。因此,刘天华被公认为近现代二胡艺术的奠基人,当代中国的二胡创作、演奏艺术无不受他的理论与风格的影响。刘天华逝世时,有人作了一幅挽联:“良月苦独病,烛光悲空闲”,取上述10首二胡曲标题的首字,蕴含巧妙意境,为人们留下无尽的艺术联想。
之后,我们还要说到一位著名的民间音乐家华彦钧,就是瞎子阿炳。人们称阿炳是三不穷:人穷志不穷(不怕权势),人穷嘴不穷(不吃白食),人穷名不穷(正直)。作为民间艺人,他不仅用音符表达了自己的情怀,还借助音乐这种工具感染了人们的心灵。
杨荫浏教授在1950年,用刚从国外进口的钢丝录音机录下阿炳演奏的二胡曲《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琵琶曲《大浪淘沙》《龙船》《昭君出塞》,留下了这些在今天已为世人所熟知的音乐作品。这的确是一件万幸的事情,这也许是有史以来无数有才华的民间艺人能够留下艺术财富的唯一一次。
阿炳是来自草根的艺术家,他的传播途径是街头巷尾的即兴演奏。经过几十年演奏传统音乐的积累,融合自身对生活的感悟,他在每一次演奏时都会进行自由即兴地发挥。阿炳的即兴演奏,摆脱了街头艺人那种赏玩式的心态,深化为一种人文关怀,使历经磨难的阿炳成为中国民间艺人的典型代表,他的作品也成为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真实记录。至于后来有人把阿炳无限拔高,成了各种戏曲、舞剧里的“英雄”人物,就实在不可取了。
3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花好月圆》《彩云追月》《金蛇狂舞》以及《喜洋洋》等小型民乐合奏作品。广东音乐、江南丝竹、长安社火、东北吹打等流传于民间的数不尽的民间艺术家创作演出的各种乐曲,由于具有强烈的民族音乐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短小精悍,通俗易懂,为广大民乐爱好者所喜爱而流传至今,历久弥新,实在值得好好研究它们的生存规律。为什么短短几分钟的音乐作品能够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久演不衰,成为音乐方面的国之瑰宝?这是我们当代民乐人一定要关注并回答的问题。
到了20世纪50年代,解放后的新中国万象更新。中央广播民族乐团,在彭修文先生的带领下,建立了由拉弦乐器组、弹拨乐器组及吹打乐器组成的民族乐队,借鉴西洋交响乐队的组成方式,改编演奏了《陕北组曲》《瑶族舞曲》等作品,使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发展有了质的飞跃。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在宽广的音域、丰富的音色、统一的音律、逐步合理的声部组合等方面,得到了空前的完善与发展。中央广播民族乐团在彭先生的带领下,创作排演了一大批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从《彩云追月》《月儿高》《花好月圆》《丰收锣鼓》《乱云飞》,到后来的《二泉映月》、音诗《流水操》、交响曲《金陵》《兵马俑幻想曲》等,强力地巩固了民族管弦乐在音乐舞台上的地位。后来,彭先生受东芝公司之邀,改编了一批西洋交响乐作品,由中央广播民族乐团演奏并录制唱片,贝多芬的《雅典的废墟》、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等经典作品的移植,做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交响乐的基本音色得以保留,还增加了民族管弦乐的特色,得到音乐界的广泛叫好和热评。彭修文先生以移植、改编、创作等手法,涉足了合奏、组曲、套曲、协奏曲、交响诗、交响乐等音乐体裁和各类乐队的组合形式。这些努力成为他生命的全部意义。作为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的创始人之一、首届会长,彭先生也是中民族管弦乐艺术的伟大奠基人。
60年代,出现了以“前卫民族乐团”为代表的新型民族乐团,开创了民族乐器改革的先河,先后改革研制了四弦高音柳琴、带键中音低音大唢呐、金钟、云锣、编磬、芦笙大筒、低胡、多管多簧笙、花盆式定音鼓等多种优秀民族乐器,使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乐器组合、音色和表现功能产生了大的飞跃。他们创作演出的《旭日东升》《水库凯歌》《迎亲人》《凤凰展翅》《红军哥哥回来了》《彝族舞曲》《春到沂河》等作品,在全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有力地促进了民族乐团的发展与建设。著名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运用交响乐队和民族乐队的混合编制,说明在国家层面上,民族乐队已经和交响乐队并驾齐驱。前卫乐队的独特音响,当年影响了作曲家刘炽的创作。他在写作电影《英雄儿女》音乐时,在交响乐队中加入了云锣等民族乐器,我们听到的《英雄赞歌》乐队飘在高音区云锣的音响,至今留着特殊的听觉印象。
经历了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过政策调整,政治经济稳定,也带来了文化的亮点。刘文金的《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黄海怀的《赛马》,简广益的《牧民新歌》,王昌元的《战台风》等,因为深得广大听众的喜爱,成为了一批保留下来的时代名曲。
70年代“文革”时期,作为一个扭曲的特殊年代,有两部大型民族乐队作品给全国民乐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而且两部作品都是大寨题材。一部是许静清写的《大寨红花遍地开》。这是一部以山西民间音调创作的三部曲式的大型民族乐队作品,由天津歌舞剧院民族乐队首演。作品山西风格鲜明,乐队写作成熟老练,富于舞台演出效果。在全中国,几乎有民族乐队的地方,无论专业、业余,都演奏过《大寨红花遍地开》。还有一部作品叫《你追我赶学大寨》,由笔者原来所在的黑龙江省歌舞团民族乐队首演。当时写作的目的,是参加全国文艺调演。1974年在北京演出后,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简谱版总谱,是“文革”后期为数不多正式出版的大型乐队民乐作品。
当然,在那个“革命”的年代,也有受到群众欢迎的小型民乐作品,如陈耀星的《战马奔腾》、魏显忠的《扬鞭跃马运粮忙》等,受到音乐爱好者的欢迎而保留至今。
从20年代大同乐会乐队起步、50年代彭修文乐队成型、60年代前卫乐队的特色推动到70年代“文革”中残存的凤毛麟角的民族乐队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这60余年中国民族乐队及其演奏的各类作品,能够认真学习传统音乐文化遗产,较好地继承了优秀民族音乐传统,创作、演出了一大批广大音乐爱好者喜闻乐见的优秀民乐乐队作品,走过了从起步、成型、发展,到被摧残隔绝到近乎停滞地步的过程。但是,据说台湾的民乐爱好者,在“戒严”时期,驾船到公海,通过收音机记录大陆的民乐作品,带回去整理乐谱,偷偷演奏。所以,看来“铁幕”也挡不住民族音乐传播的强大魅力。
二、从现实活跃在音乐生活中作品的特点,看民乐创作的现状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民族音乐涌现出了大批的优秀作品和优秀人才,有必要对民族器乐的创作、演奏、理论、教育及乐器改革与制作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总结。中国民族管弦乐在世界音乐发展历史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地位与成就,民乐创作应在此基础上厘清认识,明确发展道路,全面继承传统,更开放地学习吸收世界优秀音乐文化的精华,从而创作、演出能跻身世界音乐之林的优秀民族管弦乐。
“华乐论坛”活动是由文化部艺术司、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主办,新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协办的,2012—2015年连续举办四届,共评选出改革开放30余年来44部大家公认的经典民族管弦乐作品。论坛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引起了音乐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这些30年来活跃在海内外民乐舞台上的优秀作品,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乐创作的基本面貌。
1.完美继承传统,打造时代经典
改革开放初期,彭修文、刘文金等民乐大师,全面深刻地继承中华音乐文化的传统底蕴,以他们多年磨砺的深厚的民族管弦乐功力,丰富鲜活的生活阅历等,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民乐作品。其中彭修文先生的《流水操》,刘文金的《长城随想》《达勃河随想曲》《蜀宫夜宴》《丝路驼铃》《秋湖月夜》《观花山壁画有感》以及《边寨之夜》(第三届全国音乐作品评奖一等奖作品)等,展示出一个全新的民乐创作面貌。这些充满鲜明生活气息和生命活力的作品,让人感到既有深厚的民族音乐传统,又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代表了新时期民族音乐的创作走向,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欢和认同,其中许多作品传播多年而历久弥新。
2.突破写作藩篱,颠覆传统技法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学院派为代表的青年作曲家,率先挑战传统写作技法,在创作上另辟蹊径。谭盾在中央音乐学院推出一台全新音乐语言的民乐音乐会,用完全不同于传统写作方法的新形式,以“激烈”声音张力的“难听”音响作为全场的音乐表达样式,在中国音乐界掀起轩然大波。无调性“新音乐”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写作方式的藩篱,解放了音乐创作思维方式,特别是在音乐院校形成绝对的统治地位和“主流”。同时,也割裂了现实的音乐生活——一些国家重要评奖评出的作品,失去了舞台上的号召力,评奖结束,也就消失殆尽。而广大音乐爱好者又苦于没有新作欣赏而十分不满。现实音乐创作,不接地气,远离生活,满足不了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这成了民族音乐创作的燃眉之急。
3.寻求合理结合,打造国之经典
面对现实,民乐界有识之士认识到,我们必须回答一个严酷的问题:中国人的音乐生活,到底迫切需要什么样的民乐作品?我们应该写作什么样的精品佳作奉献给人民大众?
我们曾经走过以演奏家为创作主力的阶段。演奏家以他们丰富的民族民间音乐积累和娴熟的演奏技艺,写出了不少具有深厚传统艺术精华的好作品,从作品到演奏技艺都传承了前辈们开创的艺术精粹。但是,囿于在专业作曲技术方面的缺失,相当一部分这样的作曲家没有更大后劲超越自己,受到局限的“用武能力”,阻碍了他们写出更多跟上时代的作品。
我们也曾经历过有的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的高材生不屑于写民乐作品、不会写民乐作品的情况。他们不熟悉民族乐器,不掌握民族音乐艺术的精髓,生吞活剥地用西洋作曲法套写民族音乐,写出的作品总谱满满却没有效果,洋腔洋调不受中国听众待见。近30年来,开放的国策使外来音乐文化大量涌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很多年轻学子和作曲家,不注意努力学习宝贵的传统音乐遗产,一心追求新潮技法,写出的作品形成了乐队不愿意演奏、听众不愿意听的尴尬局面。
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给我们带来了欣喜和希望:我们一些智慧的作曲家在他们的创作活动中,一方面,将手伸向世界,学习所有的人类优秀音乐文化,拿来为我所用,因为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写作技术是世界共用的;另一方面,又将手伸向中华传统音乐文化宝库,因为在世界音乐之林,民族特色是绝不可忽略的生命之根。
由此,在日益成熟的中国作曲家努力之下,一大批既有深厚的传统基础,又有经过消化的现代作曲思维,结合完好的优秀作品涌现出来。谭盾的《西北组曲》、郭文景的《滇西土风三首》、赵季平的《古槐寻根》、顾冠仁的《花木兰》、刘锡津的《靺鞨组曲》、唐建平的《后土》、刘湲的《维吾尔音诗》、刘长远的《抒情变奏曲》、王建民的《第一二胡狂想曲》、杨青的《苍》、刘星的《云南回忆》,以及青年作曲家王丹红的《弦上秧歌》、陆枟的《弄狮》、姜莹的《丝绸之路》、谢鹏的《奔腾》等等,成为被广大音乐爱好者喜爱并活跃在海内外华人生活中的音乐作品。
实事求是地讲,“华乐论坛”评出的44部民族管弦乐作品,还不能完全显示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优秀民乐作品的全部,但是,这些作品大致可以代表30年来中国民乐人在民族管弦乐创作领域的大突破、大发展和大繁荣。所以,有中央音乐学院的音乐学教授将这一批作品和作曲家创作集体,称为“迟来的中国民族乐派”,给予了极高的发人深省的评价。
聆听华乐论坛成功推出的40余部经常在音乐会上演奏的优秀作品,清楚地告诉我们:艺术要发展繁荣,创作是第一生产力。而创作,离不开作曲家不可分割的文化母体。无论是西洋交响乐几百年的发展,还是中国民族管弦乐近百年的艰苦历程,都清清楚楚地证明:没有大批真正代表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经典作品流传于世,一切繁荣发展都是空谈。所谓的“迟来的民族乐派”,应该是成功创作思路的必然产物,也是能够催生经典作品的必由之路。
三、未来民乐创作发展的思考与实践
对从事民族音乐创作的群体或个体来说,写什么样的作品,怎样写才是我们艺术追求的正确路子,这几个问题若要问100个人,可能得到几百个回答。
经过50多年的创作历程,累积了一些思考,笔者将自觉得比较重要的几个问题,提出来与大家分享。
艺术的生命在于特色与创新,这是谁也不会怀疑的真理。中国民族管弦乐艺术,作为世界上独特的艺术品种,自有其自立于世界民族艺术之林的基础条件和发展空间。随着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的发展、壮大,不断有中国民乐演奏团体走出国门,让世界音乐爱好者欣赏到中国作曲家最新的创作成果。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士,对中国民族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国民族音乐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得到世界音乐爱好者的密切关注。如何大力强化中国民乐作品的艺术特色和艺术创新,正确地按艺术规律发展繁荣中国民族管弦乐艺术,成为全体中国民族音乐家共同的关注目标和未来发展方向。
优秀的中国民族音乐作品,首先必须植根于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传统。这已是不需讨论的命题。灿烂的中华民族音乐文化,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优良基因与土壤。聪明智慧的中国音乐家,会在我们祖国辽阔广大的神奇土地中,在我们数千年的灿烂文化中,溯根寻源、优生基因、汲取营养、成熟自我,为中国人民写出更多更好的优秀音乐作品,特别是能够代表中华文化的经典作品。
当代音乐家要想与时俱进,跟上时代潮流,还必须将自己的视野扩展到全世界。要将手伸向世界,学习所有的人类优秀音乐文化,拿来为我所用。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写作技术是世界共用的,但是,民族特色是绝不可忽略的生命之根。智慧的中国音乐家,在学习人类共同遗产的过程中,应该始终把握与自己民族音乐相结合的根本,这样,才能不断创作出既是世界一流,又深具自己民族特色的优秀作品。结合的出色,是成熟作曲家功力的最重要表现。
我们中国的作曲家,在努力学习世界各国、各民族优秀音乐文化,创作高技术作品的同时,不要忘了为广大群众中的音乐爱好者写作他们亟需的“普及”性的作品。从社会需求来说,创作大批接地气充满生活气息的优秀作品,尽力做到雅俗共赏,让广大音乐爱好者喜闻乐见,心情舒畅地享受音乐,这更是燃眉之急。从社会遗存的历史角度讲,通过长时间音乐生活的磨练、考验、筛选,一定会留下具有无限生命力、经得起时间和历史考验的所谓“传世之作”。应该说,这也是我们中国作曲家努力追求的最高境界之一。
有创作经验的作曲家都知道,创作到一定程度,技术已不是主要问题,而创作思想与智慧、成熟的生活阅历和深具艺术特色的创作构想,才是作品成功的关键。文化、历史、对各类姊妹艺术的熟悉与了解,以至于人生观、世界观等等,都是作品能否成功的重要条件与关键因素。成熟的艺术家写作成熟的作品,相信是大家的共识。愿我们的作曲家活到老、学到老,在攀登人生智慧与成熟的过程中,完善自己的创作思想,在正确的创作道路上,不断创作出自己满意、人民也满意的优秀作品。
21世纪以来,古老又年轻的中国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大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努力,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何使我们的文化软实力能够跟上国家的地位与影响力,是文化人包括我们音乐家的光荣使命。我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自由创作空间。愿我们的作曲家,珍惜这千载难逢的机遇,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勤奋努力,不断创造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用我们的经典之作,报效国家,报效养育我们的中国人民。
2016年3月6日再修改稿
(责任编辑:黄向苗)
2016-05-30
刘锡津(1948— ),男,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一级作曲,主要从事民族音乐创作与研究。(北京100054)
∗本文根据作者2016年5月23日在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的讲座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