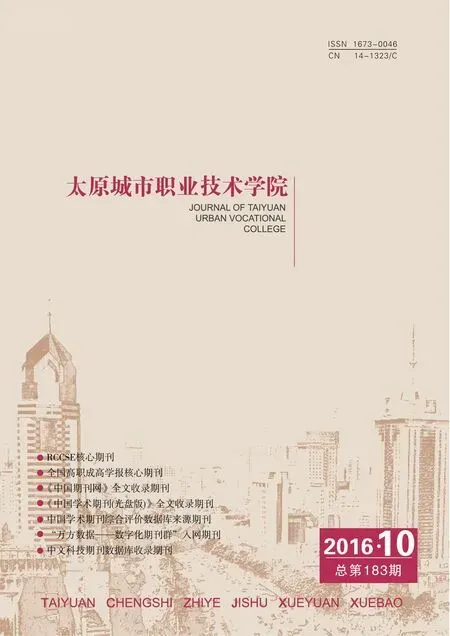柳宗元诗歌的无色枯淡
刘卫华
(湖北大学知行学院,湖北武汉430011)
柳宗元诗歌的无色枯淡
刘卫华
(湖北大学知行学院,湖北武汉430011)
柳宗元诗歌一直以“淡美”著称,本文以色彩为切入点着重分析柳诗在色相呈现、光照书写、空间建构多方面呈现出淡美特色,而诗歌中色彩的缺失促使作者采用更积极的方式成就其诗歌,如画面的渲染、隐喻的表达使柳诗寓目成悲,长于比兴。
柳宗元;色彩;枯淡;比兴
在中国诗歌审美体系中,诗人对诗歌色彩之“艳”一直关注较多,如《楚辞》会给人“耀艳而深华”的感受,曹植的诗被评之为“词采华茂”,谢灵运诗“富艳难踪”,颜延之诗“错彩镂金”,李贺诗“五色炫耀,光夺眼目”,李商隐诗“色彩丽”,并形成了一个与“设色艳”相关的文学审美体系,六朝时期诗论尤其强调华艳。但中唐时期以柳宗元为代表的诗人背离了传统“设色艳”的用色范式,以无色、枯淡来为他们的诗歌着色,形成了迥异于“丽”的清淡甚至枯淡的色彩书写。本文即以柳宗元诗为研究对象,考察柳诗的无色枯淡有怎样的特点?柳宗元为何会放弃色彩?他放弃色彩后,又以怎样的方式来成就其诗歌?
一、柳宗元诗歌色彩特征
(一)无色枯淡的色相呈现
日本学者中岛敏夫教授《对李白诗中色彩字使用的若干考察》一文对唐代李贺、陈子昂、杜甫、王维、李商隐、韩愈、柳宗元等十八位诗人诗歌色彩字运用做了一个统计,其中柳宗元的色彩字总数是153个字,排名第十八位,而颜色字使用的频率是每首诗0.85字,排名第十六,但因为有的诗人长篇诗多,有的少,不能说对双方都是公平的。所以,《考察》又计算了杜甫、韩愈、柳宗元诗中色彩字平均使用频度与李白进行比较,最终结果是李白每33字有一个色彩字,杜甫约每47字有一个色彩字,韩愈约每82字有一个色彩字,而柳宗元约每89字才有一个色彩字。
由以上研究数据统计来看,柳宗元诗歌较少对色相的刻意渲染,诗中色彩字出现频率低。即使出现色彩字,也以冷色调居多,尤其是柳州时期的诗歌,以黑、白、灰等为主色调,呈现出无色枯淡的一面。
他的山水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满是“青”“绿”“碧”“翠”“素”等色彩,在无色暗淡中给人压抑幽冷之感。
而《别舍弟宗一》中描述当地的环境是“桂岭瘴来云似墨”,瘴气弥漫、乌云密布,弥漫在整个画面中的是一片青黑,柳宗元感慨自己在柳州处境险恶。而与此相对的是行人前往的“洞庭春色水如天”,则明丽鲜亮,彼岸与此岸的强烈对比,不仅不能让画面明亮起来,反而增添了一股荒寒之意。
(二)幽深晦暗的光照书写
色彩往往还会受到季节、天气、光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黎明与黄昏、日光与月色,风晴雨雾,同样的景物必然会因光源的改变、气候的更迭而呈现出千变万化的色彩效果。
柳宗元在诗中摒弃了传统“月明华屋,画桥碧阴”的绚丽之景,偏爱选取黄昏、雨幕、黎明、夜晚、雾气、月色等背景,诗中意象如“瘴江”“云烟”“岭树重遮”“密雨”“茫茫”“寒烟”等多幽深晦暗。
甚至单从他诗歌的标题来看,也体现了光线的晦暗,《秋晓行南谷经荒村》、《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梅雨》、《初秋夜坐赠吴武陵》、《酬娄秀才寓居开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见寄》、《独觉》、《夏夜苦热登西楼》、《夏初雨后寻愚溪》、《法华寺西亭夜饮》、《雨中赠仙人山贾山人》等等不一而足,这类诗歌背景皆设定于视觉能见度低而又阴暗潮湿的夜晚,色彩冷寂。即便偶有秋天独游亭午,也依然是“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秋风萧瑟,树深林密,幽深静谧,同样充满了萧索之意。似乎只有黑暗沉寂的光照下,作者才能摆脱明亮的日色对于自身境遇偃蹇、身世不幸的提醒,才能忘却自身远离君王与朝堂的失意。
从内容上看,作者多以幽深晦暗的光照来衬托其“凄神寒骨”。在《独觉》中“觉来窗牖空,寥落雨声晓。”一片寥落的雨声,勾起了他诸多的回忆与流年如水的感叹。《夏初雨后寻愚溪》“幽幽雨妆霁,独绕清溪曲。”书写雨后的愚溪幽深静谧,如同作者身居贬所遗世独立的寥落。《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中“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描绘漆黑的深夜、苍白的月色,更能让人感受到现实的无情与苍凉。《登柳州城楼寄章汀封连四洲刺史》中则呈现了一个惊风密雨的世界,似乎只有惨白的月色、密遮的雨幕才能触动作者敏感的心弦,勾起他平生身世遭际不幸的痛苦,渲染弃置蛮荒、离群索居的孤独凄凉,宣泄被官僚体系排挤、边缘化的忧愤与焦虑。
(三)压抑逼仄的空间建构
空间形态是有感情的,这种感情可以通过色彩的语言、空间的构图经营,逐步去理解。也就是说,空间建构对色彩表现也有很大的影响,要谈色彩绕不开视觉意象的空间建构。
柳宗元的诗,除了枯淡的色彩、晦暗的光线,同时往往置身于一个压抑逼仄的空间中,如“雾密前山桂,冰枯曲沼”,如此之境,所在皆是。
其典型作品是《寄韦珩》诗歌是寄赠给前往贬所的韦珩,回忆自己从京城到柳州十年来的辛酸凄楚。虽天高地广,作者却身心俱疲,被迫囚居一方,以山林为牢,原本文人理想化、诗意的山水在柳宗元笔下是“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蒲萄。”空间上的压抑、逼仄也隐喻了作者内心的压抑、困顿、沉沦以及对命运无可改变的绝望。
《登柳州城楼寄章汀封连四洲刺史》一诗,一开篇就是劈面而来的茫茫愁思,遥望远方,苍茫未卜,返顾眼前,黑云压顶,虽天高地广,奈何“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接下来的“惊风”、“密雨”、“岭树重遮”同样是一个又一个压抑暗沉的环境,将作者内心的孤寂忧愤融入景色的描写之中,景中含情。
二、柳宗元诗歌无色枯淡的产生背景
(一)盛极之后的反拨
盛唐诗歌所展现的美学世界异常丰富,有光明澄澈、雄浑悲壮、清新淡雅等,把人类一切美好都表现到极致。活跃于中唐的诗人在前人的高峰面前“盛极难继”。中唐诗歌的发展面临了一个极大的挑战,如何展现中唐自身的特色,成为中唐诗人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叶燮曾指出,中唐是诗歌美学典范上的重要转型期,当时活跃在诗坛的诗人,据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所录在百人以上,其中不乏大量个性鲜明的诗家,呈现出旺盛的创作力、蓬勃的创新性。
他们大胆使用与前人相悖逆的意象、创作方式与素材,呈现极具个性的风格特色,表现出盛极之后的反拨背逆。文体方面上的古文革新,题材上的由雅入俗,诗歌语言、体式的推陈出新,审美的由美向丑的转化,语言上形成尖新、平俗的两大极端。
而色彩的书写,也呈现出对于前代的反拨。中国古典诗歌强调自然浑成,反对过分的人为痕迹,盛唐肯定了这一审美理想,并推之至极致。盛唐诗歌的色彩大都是自然天真的意趣,而中唐诗人则开始另辟蹊径,展现他们无与伦比的创造性,韩愈甚至提出了“笔补造化”之说,强调在诗歌创作中的刻意经营。
由此,相对于盛唐高华典雅的色彩书写,中唐诗歌的色彩书写呈现出迥异于前代的态势。李贺诗充分利用色彩的表现力,营造出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而柳宗元诗则洗净繁华见真纯。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力图突破盛唐,形成中唐独有的个性与特色。
(二)个体的生命经验(人生经历、心性气质)
诗歌是作家将所看到的世界以文字创造出另一个微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的色彩,正是诗人心灵图像的具体展现。元好问曾在《论诗绝句》中评价柳宗元说:“谢客风容映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柳宗元自己也曾在《夏初雨后寻愚溪》中写道“寂寞固所欲”,寂寞可以说是投射在柳宗元诗歌中的情感核心。那么,柳宗元诗中的无色枯淡呈现了他心灵深处怎样的寂寞痛苦与绝望呢?
柳宗元出身于“世胄显贵”、“祖德辉煌”的书香门第仕宦之家,年少才高,少年时代“以利安元元为务”“辅时及物”“进而不能止”,一往无前,以身许国,但一朝事败,“罪谤交集,群疑当道”“群言沸腾,鬼神交怒”《寄许京兆孟容书》。
柳宗元等被视为权奸小人,遭抛弃放逐,万死投荒来到永州,“沉埋全死地,流落半生涯”,屡遭火患,妻死女亡,老母离世,知交尽丧,饱经人世的沧桑与苦难,丧亲之痛,绝嗣之忧,体魄之弱,寂寞之感构成了柳宗元心灵的痛苦。一个不快乐的人在诗歌世界里也呈现出一片晦暗,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提到“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抑郁沉沦成了他人生情歌的基调,“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乐。”十年后远贬更为荒远的柳州,心境的忧虑自困使柳宗元开始在佛境中寻求平静,以期借佛的出世与疏离来医治心中的寂寞与不甘,之后逐渐进入“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的境界,无念无住,无悲无喜,淡化了现实的痛苦,也使其诗歌带上了空静的意味。大自然是丰富多彩的,而柳宗元受佛教的影响也非常偏爱或者说只偏爱静寂荒冷、色彩幽暗的景物。他对清冷幽寒的山水景物非常敏感。
三、柳诗意象中色彩缺失的弥补
朱光潜曾经说:“所谓意象,原不必全由视觉产生,各种感觉器官都可以产生意象。不过多数人形成意象,以来自视觉者为最丰富,在欣赏诗或创造诗时,视觉意象也最为重要。”视觉意象在诗歌中如此重要,柳诗舍弃了意象中重要的色彩元素,又以什么来成就他的诗歌呢?
(一)淡墨点染的写意画境
作为中国绘画的正宗,水墨山水画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抛弃了繁复绚丽的色彩,因其清幽、高雅、简古,淡泊的士大夫情怀而为人所称道。柳宗元的诗就深谙传统水墨山水画的精神内核,以意摄象,虽然不以色彩取胜,却靠具象化的景物书写达到画意的营构,既延续了中唐注重视觉印象的趋势,又独具个性特色。
他的《江雪》、《渔翁》都展现了传统水墨山水的重要主题,以表层的画面传达深层的意蕴内涵。首先看他的《江雪》,这首诗开篇就展现了严酷的自然环境,大雪压境,生机全无,肃杀茫然,然而在寂静无声、与世隔绝的背景中却有一位执着坚持的渔翁,他不为外界所动的执着、孤独中的凛然,也传达了柳宗元自己对人生的体味,营造出一种遗世独立、峻洁孤高的人生境界。
《渔翁》一诗与《江雪》中孤独中的坚守,隔绝中的淡定不同,传达的则是淡泊宁静、超脱闲适的人生况味。在青山绿水之中,江水荡漾,白云无心,一位潇洒淡泊的渔翁形象跃然纸上。
此外,他诗集中还有很多充满诗意的画境,清淡着色,韵味无穷。如《与崔策登西山》中“鹤鸣楚山静,露白秋将晓”,秋天早晨,白露为霜,空山寂静,白鹤长鸣。一连串明静清丽的意象,展现了一幅清幽高远的画面。如《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中“木落寒山静,江空秋月高”一句,同样是淡墨点染的水墨山水,秋江月冷,木叶萧萧,孤高清冷。
(二)比兴式的隐喻表达
贞元元和间,当位于京城的韩孟诗派、元白诗派各展风采,创造出或奇绝险怪,或平易浅切的诗歌时,身居贬所的柳宗元则直追前代,仿古拟古,自成一家,形成了冷峭的诗风。在他的诗中,没有如李贺那样鲜亮丽的色彩,没有韩孟那么夸张排比的铺陈,而是以比兴手法来营造意象,使诗歌充满了隐喻色彩。
柳诗中的意象除了上面提到的一类写意画境的呈现,带有恐怖、压抑、痛苦的意象也不在少数,如尖山热水、孤城野树、惊风密雨、射工飓母、蝮蛇蛊虫、瘴疠毒气等。这类意象往往有极为强烈的刺激意味,迷离尖刻,饱含沉沦之痛、隔绝之殇。
主体情绪感染了山水,山水加重了了主体的孤独,于是满目苍凉,寓目成悲。而一切的痛苦不安、孤立无援最终凝结为望乡怀乡意绪,“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投迹山水地”的埋厄感郁,“放情咏离骚”的郁悼凄恻在对家乡的遥望中都获得了抚慰,心灵的不安与躁动也于此栖息止泊。
陶渊明的平淡诗风在当时尚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及至中唐追随者多,尤以柳宗元得渊明之旨趣。柳诗的枯淡之美虽有陶诗的淡泊,但也有屈原的深隐,诗意的画境弥补了色彩缺失的遗憾,呈现出其独有的“似淡实美”的美学特质。
[1]中岛敏夫.对李白诗中色彩字使用的若干考察[A].中日李白研究论文集[C].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2]李广元.绘画色彩系统——绘画色彩个性的时代选择[M].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0.
[3]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4]朱光潜.诗论[M].上海:三联书店,1984.
[5]王树海.佛禅对柳宗元山水诗的影响刍议[J].社会科学战线,2000(1).
I206
A
1673-0046(2016)10-0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