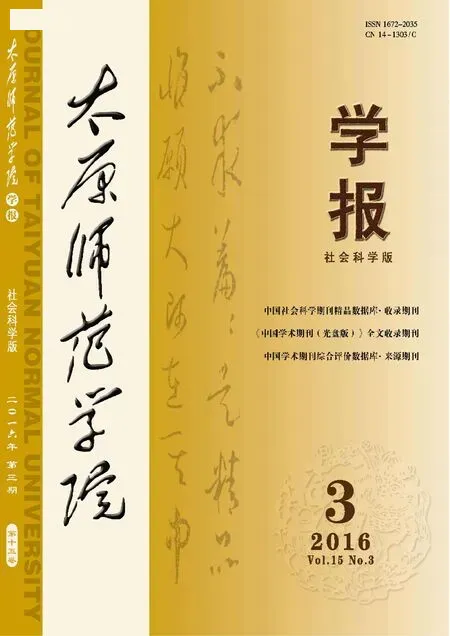论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人道主义内蕴
杨婷婷
(安徽大学 文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00)
【文学】
论张纯如《南京大屠杀》人道主义内蕴
杨婷婷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合肥230000)
[摘要]张纯如在强烈的个体意识驱使下选择揭开南京大屠杀的史实真相,运用战争亲历者的回忆重现血腥残暴的屠杀事实,探析人性之渊。同情和人道主义在战争期间的展现很值得深究。书中关于人性的呈现是朦胧而有张力的,尤其是两个参战士兵在战后不彻底的忏悔与反思,透析出忏悔意识停留在初级阶段。但是,在这里忏悔精神体系的建构是运用物质的外化,这种程度的人道主义只能称其为闪现。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人性;人道主义; 忏悔; 反思
时人对于张纯如的研究大都是围绕她短暂而有力的一生和她创作的《南京大屠杀》一书进行。张纯如的一生在她36岁那年画上了终止符,这终止符,是她抵在自己太阳穴上的一颗子弹。张纯如去世之后,有极多的相关影视作品井喷般出现,在各界学者的探求和艺术创作中,很多人看到了这位女性作家对战争的愤怒和抒写,却容易忽略书中关于人性的呈现是朦胧而有张力的。说它朦胧是因为,人性往往与灵魂最深处、最难以碰触的渴求相关,但它又是有张力的,一旦人性在文本中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它必定会呈现出放射性的强度来凸显自身的“表现单位”。而这种状态下的人性话语是很容易勾连出人道主义及更深层次的反思、忏悔意识,这些都是《南京大屠杀》这本书中最值得被梳理和解读的话语。
一、个体意识下的创作呈现
张纯如将个体话语凝结在文本中为南京大屠杀受害者辩护。在她看来,南京大屠杀之所以不被世人广泛知晓,除了跟大部分受害者对过去选择沉默有关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对这一事件的态度。书中提到:“甚至到了1997年,日本作为一个国家仍然试图再度掩埋南京的受害者——不是像1937年那样把他们埋在地下,而是将这些受害者埋葬在被遗忘的历史角落。”[1]213不久前,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被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南京大屠杀”郑重上升为世界记忆,从国家民族层面跨越到世界国际层面。“南京大屠杀”的申遗成功不只是让中国人得到了慰藉,也同样告慰了张纯如。在强烈的个体意识驱使下,张纯如选择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课题。1997年,《南京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战被遗忘的大屠杀》英文原版在“南京大屠杀”60周年之际于美国出版。这样的一本书,不可能存在温馨的场面和动人的情节。翻开书我们发现,里面有太多关于南京浩劫中反人道的残暴描述。这些描述不是张纯如个人的幻想,而是当时南京国际安全区负责人埋藏了多年的真实记忆:
日军的活埋行动就像生产流水线一样精确而高效。日本士兵强迫第一批中国俘虏挖好坟坑,第二批俘虏埋掉第一批,再由第三批埋掉第二批,以此类推。日本士兵故意将有些受害者只埋到胸部或颈部,为的是让他们遭受更多的痛苦,比如用刺刀将他们砍成碎块,或者让他们遭受马匹践踏和坦克挤压。
另一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是,将受害者活埋至腰部,然后观赏他们被德国黑贝撕碎的场面。曾有目击者称看到日本士兵扒光一位受害者的衣服,然后指挥德国黑贝去咬他的敏感部位。那些狗不仅撕开了受害者的肚子,甚至还将他的肠子在地上拖出很远。
强奸妇女经常与屠杀受害者全家同时发生……在这场大规模的强暴中,日军还常常杀害儿童和婴儿。
类似的纪实性描写充斥在整本书中,无法将它们具体地一一列出,日军对南京的罪恶确是罄竹难书。战争洗礼后,再也看不到秦淮河如以往那般温柔软静。历史从这条河看到了一座城市性命的末日。战争如此无情,它可以带走一切,连整座城市所有人的生命都随时可能会灰飞烟灭。这惨烈不得不引发我们对战争的反思,与此同时,对战争的思考及罪恶应被重新审视的心理认同也影响着张纯如的创作。在创作过程中,张纯如始终坚信埃利·威塞尔对世人的警告:忘记大屠杀就是二次屠杀。她探求史实真相的心理不完全是构筑在对南京大屠杀的普世观点,而是掌握它的细枝末节,并从中推演出一套逻辑叙述方式,将文本与个人意识相结合,最大程度上激发读者的强烈共鸣。
二、对人性的微观性探析
人性的首要法则就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就是对于自身的关怀;而且,一旦当他达到了有理智的年龄,可以自行判断维护自己文本生存的适当方法时,他就从这时候起成为自身的主宰。[2]7-10作家基于此,便可以借由自身的理性维度去触碰人性在战争中的展现。如果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一旦超越文本层面去驾驭精神,他感受到共同的心灵(即战争亲历者的共同记忆)并且将之化为自己所本有,这一共同心灵便为所有人所共有,且是为每一个人所独具。与此同时,文学必须要依附于人而存在,如果文学不借助人,也无以表示人性。张纯如把握人性在特殊时期的无阶级性,用文学描写永恒不变的人性,但是她的切入点又很是独特。虽然张纯如不是浩劫的亲历者,但是她确信可以将共同心灵进行和谐转化,将创作精神寓于自己本身中并且于他者中再创造。《南京大屠杀》的完成有赖于读者的精神构造,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文本会进行或多或少的干预,难能可贵的是,张纯如意识到人性的表达与历史的回顾必要攀附在怀有真实记忆的战争亲历者身上,且这种攀附不是只采用中国受害者的讲述,而是将屠杀者、中国受害者、西方亲历者这三者的真实记忆环环相扣为一个三角结构,让他们互相佐证,加强可信度的同时又从微观上全方面把握了各个立场上的人性,拷问微观处的微小差别。
用亲历者的经历去探究人性话语的作品有很多,且在各国剖析战争人性的作品中都有体现,较为权威的是普里莫·莱维的《被淹没和被拯救的》[3]一书。当然,与张纯如的创作有很大的不同,普里莫·莱维的人性切入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自我的反思,是对其自身罪恶感的清洗。普里莫·莱维是从奥斯维辛集中营活着走出来的人,他是战争最大的受害者。但是作为受害者的他要在书中讲述当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他发现了一个可以多喝几口水的地方却因要维护自我的生存而选择隐瞒。尽管他很清楚地意识到,在那个集中营中,多喝一口水可能意味着离死亡更远。该书从人性最隐晦处证明,人性的首要法则便是维护自身生存。战争结束,当普里莫·莱维回看被囚禁的那段经历,他绕不开人性深处的反思与忏悔,这个切入点是极具微观性的,也是很具有私密性的,通过个人记忆来证实战争中的微观细节很冒险,很多时候个人的主观感知会裹挟着自我保护的立场去歪曲过往真相。尽管普里莫·莱维是将自己想要忏悔的“人性污点”写在书中,但是对于书中与他为伍的其他人而言,这种决断式的审判又是不公平的,这个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是源于一个人或者说一个共同立场的人对人性的解读往往是带有私欲的,这与张纯如想要表达的人性拷问有着很大的不同。张纯如看到冲突与对立,进而用多方回忆探究人性,凝结出朝向共同性,这种解读就更有说服力。
从某种程度来说,人就是他自己的目的,同时,人也忠于自身的人性。一世纪又一世纪过去,对人性的解读难免要从个人记忆出发。真实的记忆和虚假的记忆同为人性的折射面,这种通往个人主义的人性很可能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构成反思战争和罪恶的主核心。
三、来源于同情的人道主义
从《南京大屠杀》前言来看,张纯如将研究视角放到南京大屠杀的原因大致有三点:一是她在童年时期便听父母讲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残忍与恐怖,这激起张纯如对南京浩劫中受害者的同情;二是在她成年之后参加纪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会议时接触到南京大屠杀照片时对生命之脆弱的同情;三是她对中国受害者饱受折磨后,在日本的威胁和施压下却只能保持沉默具有强烈的同情。三个点的核心,都在于同情。我们有理由相信,张纯如编写《南京大屠杀》首先建立在同情之上。同情是人道主义的逻辑起点,这很符合人道主义精神。这样一个美丽的华裔女子,看到远在大西洋彼岸的中国曾遭受这样的剧痛,她一定是像你我一样满怀愤怒。但她并没有一味地指责日军或者发泄不忿,而是更深层次地运用个体记忆呈现南京大屠杀,展现人道主义。
把“南京大屠杀”这一群体受害者的共同经历再现在读者面前,领着我们去透析受害者的感受与想法,张纯如用广泛的叙事强化读者对该事件的感知。美国学者迈克尔·沃尔泽说,正义战争应是对诸如侵略、滥杀无辜这些显而易见的邪恶的一种回应以及对于使用武力时的某种限制,如避免诉诸强奸、向平民发动战争、酷刑和恐怖主义等暴行。[4]日军在占领南京之后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1937年12月13日,日军在南京对平民和战俘犯下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一系列罪行,30万以上中国人被日军杀害,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军纵火烧毁。这些数据对罪恶的展现或显苍白,但在这些数字背后,有着太多凄惨哀号与悲痛屈辱,看到的是日军对南京城的占领是多么的残暴和泯灭人性。
张纯如从人性的视角重新挖掘抗日战争中最黑暗、最血腥、最惨烈的南京大屠杀呈现给世人看。书中“人道”一词大概出现了四次。第一次:南京国际安全区的领袖贝拉在战争刚刚打响之时遇到了尚未撤走的中国军队,贝拉突然产生了一种人道主义的冲动。第二次:为了保护中国士兵的生命,贝拉恳请日本人对这些过去的士兵施以同情,并根据公认的战争法人道地对待他们。第三次:日本投降后,远东军事法庭判决谷寿夫死刑。人们聚集在街道和人行道两旁,观看谷寿夫在雨花台被执行枪决。许多大屠杀的幸存者认为,他的结局比大多数死在他手上的受害者要人道得多。第四次:拉贝在日记中写了德国去纳粹化委员会的判决,提出鉴于他在中国出色的人道主义工作,委员会决定支持他洗脱纳粹罪名的请求。我们看到这四次中有三次都与一个人有关,即约翰·拉贝。在巨大的悲剧面前,人道主义的光辉在不断放大,有时候会在同一个人身上放大。约翰·拉贝是张纯如人道主义叙述的重点,在战争期间,留在南京的拉贝自发建立国际安全区,收容南京战俘和百姓。这是一位无私的德国人,竭尽全力与日军抗争,努力保护所有的难民,可是最后回到德国却受到了政府的诽谤和神行太保的调查。张纯如结合拉贝个人的命运,展现出对战争中人道主义在人性悲悯下的思考。
四、人性深处下潜出的忏悔
西方意识形态主流话语也在反思战争与人道主义中人性的抒写,在谈及大屠杀时多会往“屠犹”上靠拢,去剖析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故事,谈及拉贝时只是称他为中国的辛德勒。张纯如打破以往创作的局限,以新的视角和战争空间进行创作,想要捕捉那个发生在南京的极难被捕捉的现实,进而发散出线状结构,用拉贝的记忆展现战争时期人道主义在人性深处的下潜,并且不只局限于这一点,跨出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用人道主义超越战争。忏悔是人性心灵深处的奏章,是沙漠中的枯井渴望触碰甘泉的地方。《南京大屠杀》记录了太多日军的罪恶与丑陋、贪婪与血腥,但是最具有人道主义闪光点的是两个在战争结束之后的士兵的忏悔与赎罪。第一次:战争之时,普通士兵永富在南京也犯下了杀人和凌虐无助平民的反人道罪恶。战后,永富在日本成为医生,在自己的候诊室修建了一个忏悔神龛。经过六十年的反省,他由一个曾经的杀人狂魔变为了态度和蔼的医生,不断向自己的病人讲述自己的罪恶,忏悔与赎罪深深刻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第二次: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在战争结束后理所应当受到最强烈的指责,虽然病中的他在战争中几次试图阻挠部下对南京的残暴施虐。战后,为了弥补在南京犯下的罪行,他在家乡的一座小山上修建了一座忏悔寺庙,供奉观音菩萨的塑像。塑像是由长江沿岸的几袋泥土和日本当地的泥土混合制作而成,并请尼姑在佛像前祷告,哀悼在战争中死去的中国亡灵。
从这两次忏悔我们看到了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结束,参战者回到家乡过上平凡人的生活,往日的罪恶成为他们融入平静生活的最大阻碍。战争背景已然消失,身为一个人最根本的人道意识被逐渐唤醒,从而,永富和松井石根都选择了对过去的罪恶进行忏悔,这便向“忏悔—赎罪”型人道主义靠拢。“忏悔—赎罪”型人道主义的逻辑表达式在这里可以这样描述:犯罪施恶→人性发现、归罪忏悔→赎罪拯救、人性升华。[5]这升华一般包含人性演进的这三个发展过程,很明显战争结束后犯罪者的精神逻辑还未上升到发展过程的第三阶段。他们在南京大屠杀中由犯罪施恶到人性发现、归罪忏悔,但是并未走向赎罪拯救、人性升华。永富和松井石根的忏悔意识停留在初级阶段,精神体系的建构是用物质的外化,赎罪的意识是在犯罪之后由心底萌发,驱使他们做出同样的举动,即“修建忏悔神龛/寺庙”。如果说“忏悔—赎罪”型人道主义是对人道主义在战争期间的内化表现,那么日本人的忏悔意识只是外化叙事。
为什么说日本人的忏悔意识只是外化叙事呢?我们知道整个日本在二战结束后虽有所反省,但这个国家反省的重点集中在战争的最后四年,也就是“太平洋战争”那四年,或者,用他们当年的叫法叫做“大东亚战争”(日本政府曾在二战期间为愚惑百姓,将对外侵略分为几个阶段的叫法,分别为“满洲事变”、“上海事变”、“支那事变”和“大东亚战争”,以此混淆视听)。在战争来临之时,日本的部分知识分子从之前的拥抱自由、崇尚人性一下子转向,而去附从军国主义、听从天皇的指示。这种盲目的转向蒙蔽了整个日本国民的心智,就连孩童都理所应当地认为日本是二战中最强的一方,中国终有一天会成为日本的附属国。这种思想就必然导致那些参战的士兵在战争结束后最关心的问题不是死了多少人,而是如何快速从这一战争中脱身,不受谴责地回归到战前生活。在战败成为现实的时候,日本自上而下的另一种反思是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偷袭珍珠港,为什么当年他们会蠢到那个地步,为什么那样的不自量力,落得了战败的下场。所以,二战结束的时候,日本人满脑子想的都是关于他们认为一定必胜的这场战役没有打赢,他们想要构建的大东亚共荣圈没有形成,他们想要称霸亚洲的意图最终破灭。而对于对他国人民造成的伤痕,恐怕只有零星的士兵或者军官做着零星的忏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日本国内几十年来给国民灌输的军国主义思想有关。永富忏悔了,松井石根也忏悔了,他们在家乡找一个僻静的地方,花点钱修上一个忏悔神龛/寺庙,这忏悔能给中国受害者带来任何的补偿吗?能洗刷他们满手沾染的中国人的鲜血吗?恐怕,他们所做的事只是为了驱散心中对所犯罪恶的恐惧,又或者,我们可以猜测,这种行为也不过是想要在家乡洗脱一点杀人狂魔的罪名。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两个人已经比千千万万的日本参战士兵好上许多,最起码,他们还能够承认自己过去所犯的罪恶并且想去忏悔。不过,我只能将这两人身上的人道主义描述为“闪现”,他们所代表的人道忏悔意识,究其根源,还是跟自私的本性相关,远达不到深层次的人性升华和赎罪拯救。这种停留在第二层面的人道忏悔(即人物由第一层面的犯罪施恶到第二层面的人性发现、归罪忏悔,不涉及第三层面的赎罪拯救、人性升华)只能让人感到遗憾。
遗憾之后就是深思:战争只能带来伤痛。对于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来说,最大的伤痛莫过于南京大屠杀,这种痛,具体、沉重而持久。或许,这伤痛带给世人的恐怖会因为时间的洗刷而成为隐痛,但这痛永不会消失。我想,真正让人感到恐怖的不只是战争的暴行,最可怕的是受害者的忘记过去、战争的反人道性和犯罪者的拒绝忏悔。
[参考文献]
[1]张纯如.南京大屠杀[M].谭春霞,焦国林,译.厦门:中信出版社,2013.
[2]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3]普里莫·莱维.被淹没和被拯救的[M].杨晨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
[4]韦宗友.西方正义战争理论与人道主义干预[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10).
[5]王达敏.“忏悔—赎罪”型人道主义的中国化——再论方方长篇小说《水在时间之下》[J].文艺争鸣,2011(11).
【责任编辑冯自变】
[收稿日期]2016-01-09
[作者简介]杨婷婷(1992-),女,安徽阜阳人,安徽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
[文章编号]1672-2035(2016)03-0070-04[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