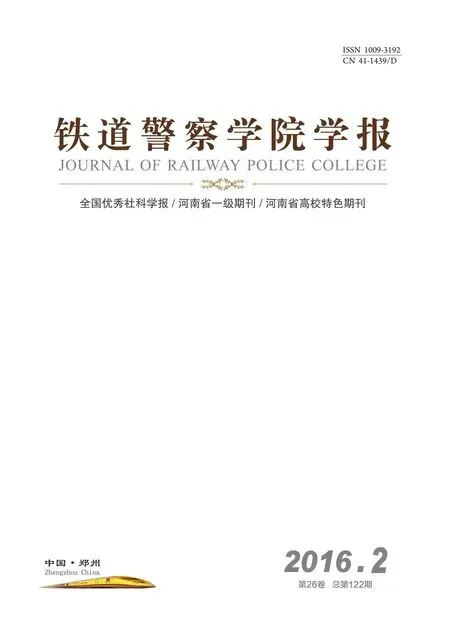论中国古代警务结构与特征
胡建刚(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治安系,江苏 南京210023)
论中国古代警务结构与特征
胡建刚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治安系,江苏 南京210023)
摘 要:中国的警察职能发轫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尧舜阶段。春秋战国时期,警务工作虽然出现了较为细致的分工,但形成的是军警不分与行司合一的混合形态。中国社会的“蜂窝状”结构形态,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而基本定型,国家警察的职能也就相应地解剖为朝廷、地方与基层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按照不同的运行机制安排着警务结构。保甲制度通过强制性的集体责任连带关系,实现基层横向的水平监控,大大降低了纵向的垂直监视的成本,从而实现了社会治安秩序的逆向控制。传统中国农耕社会处于一种非竞争的环境中,警务控制借助于低成本的株连方式,通过制度的激励机制,以及熟人社会维持的信用制度,维系着社会秩序的稳定。
关键词:古代警务;治安治理;警务结构;保甲制度
一、警务混合形态:军警不分与行司合一
在生产力极低的原始社会,人们借助血缘关系结成氏族部落,群居生活,共同抵御外界侵扰,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日常警务和治安秩序靠世代相传的习俗和图腾的禁忌来维持。《商君书·画策》中所言的“神农无制令而民从,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1],正是这个时代社会内生性自治秩序的生动写照。
私有制与阶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原始社会的解体而产生,无为而治的时代结束后,出现了奴隶制国家和体现奴隶主意志的法律法规,也产生了执行奴隶主意志的警察机构。
中国的警察职能发轫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尧舜阶段,当时部落联盟议事会所设的九种官职中的司徒和士承担着警察的职能。舜为部落首领时,契担任司徒之职,皋陶担任士之职。据《尚书》的记载,舜对契说:“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百姓之间不和睦,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这五层伦理关系不理顺,作为司徒之官,要负责教化和调解纠纷。舜对皋陶说:“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2]对于夷族的侵扰、杀人越货等行为,狱讼的官员应视之为违法的行为和情节,予以相应的处罚。司徒和士的职能,清晰地表现出警察职能的萌芽[3]。
夏王朝时有三种官吏分别承担了警察的部分职能:司徒负有警察的处置和调解民事的职能,司马负有边防警察的职能,士负有刑侦警察和狱警的职能。处于萌芽状态的警察职能分别寓于行政、军事、司法三种职官之中。
商周时期的警察职能仍然是一种混合的形态:司徒主要负责所有民众的教化、土地等事务;司马掌管军事,由于军警不分,司马在负责保卫边境的同时也承担维护城市治安秩序的任务;司寇掌管刑狱和监察,除了监禁未决犯,还要监督已决犯的改造。
春秋战国时期,警务工作出现了更为细致的分工。如在司徒之下设司武,负责禁止打架斗殴、寻衅滋事;司稽负责巡市、查获犯禁、拘捕盗贼;司市负责维护市场治安。在司寇之下设禁暴氏,负责禁止聚众滋事和暴乱;司民负责户口登记和统计;野庐氏负责道路交通管理。在司马之下设司煊,负责对火灾的查处和消防监督等。
庞大的警治禁卫机构、严厉的惩戒法规与刑事手段,迫使所有社会成员在其规范的强制下,有机地组合在一个“军警不分、政刑一体”的国家政治网络之中,各级政府行政长官直接负责辖区社会治安,各职能部门分担警治禁卫安全任务。这种军警一体、政刑不分的国家权威力量组合方式,与《周礼》所设想的大一统政权政府组织方式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也是整个封建王朝警务实施的精髓。
二、专制与自治:封建制度下社会治安的分层控制
政府的统治总是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中,国家借助一定威权的运行,通过整合治理资源而实现社会的秩序化。在绵延2000多年的统治中,中国独特的“皇权专制—差序格局”[4]式治理传统不断沉淀。Vivienne Shue(1988)提出的“蜂窝状”[5]结构本质上就是“皇权专制—差序格局”路径依赖的延续。由于组织体系的欠发达和技术手段的落后,在幅员辽阔、地域复杂、人口众多且交通不畅的情况下,虽然是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但不同地域之间事实上的割据造成了各自的独立运行,形成“蜂窝状”结构。在这种蜂窝状结构的治安控制中,地域性的警务自成一体,形成相互独立运行的格局。学术界对传统中国“皇权专制—差序格局”的总体认识可以概括为“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6]。它们受到中央政府的统一指导,但是由于天高皇帝远,在很大程度上在各自地域里按照自己的逻辑执行法令,这样便形成了在中央集权专制框架下的地方警务自治。“正式的皇权统辖只实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减弱乃至消失”[7]。皇权政治“在人民实际生活中看,是松弛的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8],这是因为“一端是血亲基础关系,另一端是中央政府,在这二者之间我们看不到有什么中介组织具有重要的政治输入功能”[9]。事实上,皇权的渗入并不是以组织的方式,而是以意识形态的专制思想形式,将其“政治影响延伸至乡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10]。总的来说,“三代之始虽无地方自治之名,然确实有地方自治之实,自隋朝中叶以降,直到清代,国家实行郡县制,政权只延于州县,乡绅阶层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性力量”[11]。
中国社会的“蜂窝状”结构形态,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而基本定型。秦朝的政府建制不仿夏商,不循《周礼》,而是根据帝国统治的需要,贯彻皇帝独裁和专制主义的原则,确立了朝廷三公九卿、地方郡县首长负责制的官僚政体。官僚体制遵循着明主治吏不治民的基本准则进行架构,政府的行政权力只及于州县,即“皇权止于县”。国家警察的职能也就相应地解剖为朝廷、地方与基层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按照不同的运行机制安排着警务结构。秦汉时期定格的警务结构标志着封建社会治安体制的成型,确立了中央—郡县—乡里的“三级警务体系”。
中央与郡县层面的正式警务,建构了以“尉”制职位为主干的覆盖全国的警务网络,中央与京师的层面上有太尉、廷尉、中尉、卫尉的设置,分别主管朝廷的、宫廷及皇城内的警务与禁卫,保障京畿之安全,同时统筹全国之警务和警治;地方的郡县则设有不同的“尉”职,如郡尉、县尉、关都尉、骑都尉、农都尉、分部尉等,在郡守和县令领导下掌管辖区内军事和警务,负责各自范围内的安全防范和治安秩序维护。郡尉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境内的治安,同时巡行辖区各县,考察地方警务状况,治安形势复杂的郡也可能配备两个或三个都尉,分区治理。县尉执掌本县的治安,“尉主盗贼,凡有贼发,主名不立,则推索行寻,案察奸宄,以起端绪”[12]。这意味着县尉主管缉拿盗贼,侦破案件,向县令报告案情和提交人犯,县尉经常巡视交通要道、乡里街亭,在治安复杂场所布建耳目,以便及时掌握社情动态和罪案信息。县尉在行政上隶属县令管辖,但治安业务受郡都尉的领导和支配,同时负责指导乡与亭的警务活动,在国家警治体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
县以下的乡里层面,乡设游徼,里设里正,负责乡、里的治安。游徼直属县尉管理,负责辖区的巡禁捕盗,维持本乡的秩序;里正直接对本地户籍进行登记管理。凡郡县执法人员下乡办案,所在地的里正必须到现场,案情报告书必须附有其签字画押方才有效。
县以上的正式警务归属于中央,而县以下的基层非正式警务则完全是依靠地方乡绅和民众的自我管理。中国古代非常强调“地方自治”,中央政府的规模始终很小,家庭、宗族、士绅等组成了复杂的、多元的地方权威,基层警务和大多数纠纷都在这个层面上解决。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正式警务层面,在京城有左右金吾卫负责皇帝宫廷警卫和掌管京城的巡警,直接维护京城的治安秩序。在地方,府设户曹参军、法曹参军,州设司户参军、司法参军,县设司户、司法等专职官员,负责各层次不同范围内的辖区治安,执行户籍管理、缉捕盗贼等警务职能。非正式警务层面,在基层推行邻保制,让老百姓自己组织警务保障。四家为邻,四邻为保,百户为里,五里为乡,设里正,行使“掌按比户口”“检查非违”的治安管理职责。有人在保内出入,必须向保长申报;如有长年外出或迁徙者,里正要负责调查外出者的户等、奴婢驴马的去向及谁人代承其户的缴税服役义务等,查实上报县司,县司据报发给迁徙人通行凭证。从治安角度讲,对农民这一社会层面的控制,最艰难的是对其中流民的控制。流民问题始终是历代封建政府的一大困扰。唐政府用“摊逃”的办法来应对,将逃户应缴纳或承担的各项赋税转嫁到近亲邻保身上(“应赋租庸课税,令近亲邻保代输”)。
宋朝的正式警务层面设有两套行使国家警察职能的机构。一套叫巡检司,维护大城市、农村、河道、海上、驿道和边境地区的治安,并管理城市消防;另一套叫县尉司,维护县城、集市的社会治安。非正式警务层面则依靠乡里制和保甲制。乡设书手,里设里正,户设户长,其职役是督征赋税。乡里治安则由营长率领本乡弓手、壮丁负责。王安石变法之后推行保甲制,将周秦时期的兵农合一体制与什伍联保联防连坐措施结合起来,负责基层治安。
辽金元的警治体制一脉相承,这里主要介绍辽。辽代五京为辽国政治经济重镇,辽人特设警巡院专司五京治安,其名称分别是上京警巡院、中京警巡院、东京警巡院、西京警巡院和南京警巡院。每京警巡院都设一名警巡使与一名警巡副使。辽代地方上又有军巡使,有巡逻之责,主管各地治安。警巡院的创制是契丹族在古代治安史上的一大贡献。由于五城分布在全国各地区,五城警巡院的建立实际上相当于各地警巡院的建立,也就是全国城市警治安全专职机构的建立,这是史无前例的。
明朝为代表的后期封建社会,专制制度高度强化,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加强了治安管理机构。正式警务层面,京师有四套警务机构,一是五城兵马司,负责缉捕盗贼、查禁街市的斗殴赌博奸淫等行为,以及夜间巡逻、查缉户口和消防,维护治安秩序。二是亲军卫和留守卫,负责京师警戒、守门和夜间巡逻。三是锦衣卫,是皇帝的心腹特务机构。四是巡捕军队,参与京师捕盗和维护治安。在地方,府设捕盗判,州设捕盗同知,县设判官或巡捕主簿,辅佐府、州、县行政长官掌管治安和司法。各府州县关津等要害处均设巡检司,负责查验过往人员证件,查获奸细、逃军、逃犯及可疑之人。县以下非正式警务层面,城郊和农村实行里甲制度,建立保甲组织。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也促使清朝统治者建立更为庞大的警察机构。正式警务层面,在中央仍设六部,但其规模已大有增加(仅刑部就有400多人),其中户部和刑部兼管县级治安。在京城设步军统领衙门,下辖由满人组成的八旗步兵营和由汉人组成的绿营与步军巡捕五营,“兼有警察的性质”[13]。满人守卫内城旗人居住地区,负责夜间巡逻、捕盗、防火,汉人负责外城和近郊的治安。另设五城兵马司,受步军统领衙门节制,分别负责各城区的治安。在地方,治安工作由地方行政长官负责,同时设道员、巡检等职位辅佐省和州、县行政长官,缉捕罪犯,盘查奸宄,维护一方治安。八旗兵在地方也有布防,但根本目的是对当地行政军事进行监督和控制,并不负责地方的具体治安[14];绿营兵承担的是各地守护、解送、缉私、承催、察奸等警务工作[15]。清后期崛起的练军和防军替代以往的八旗和绿营,虽在军事上有所革新,但警务功能却一直延续。非正式警务层面,在基层强化了保甲制度。清朝出于管理各民族的需要,并用里甲和保甲两个系统。里甲专管征收地方赋税,保甲则专管警事治安。康熙在《圣谕十六条》中专门发布了“联保甲以弥盗贼”的谕令。官府强制推行的保甲总的来讲是“没有效率的”[16],这是因为保甲长只是官府的民间代理,没有俸禄报酬,良民多不愿担当此角色,充任者多是乡间的无赖;无赖充任保甲长大多是为了依仗职权进行讹诈勒索钱财,这就导致实际的治安状况更加恶化[17]。清代的家族组织实际上承担着家族内部的治安责任,族、房、户三级组织管理族人,家法家规极严,从辱名、罚跪直到处死的私刑得到了官府的许可和默认[18]。
三、相保与连坐:中国古代社会治安控制的深层基因
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警务结构,本质上是人类历史长期发展和选择的结果,而且往往是成本与效益的最优组合。此处所言的效益,虽然必须将其放在整个社会综合考量和阶级分析的视角加以认识,但基本的着眼点在于社会秩序稳定。社会的控制能力取决于当时的基本生产力发展水平,控制工具的设计只有在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时才有着被选择的可能与机会。
中国古代的社会控制方式摆脱不了农耕文明的制约,也受着地理环境的影响,形成超稳定的“家国同构”格局,其中宗族体制、依附关系和集体性共同责任是构成社会控制的基本形式。构成基层社会的主要管理结构,一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宗族制度,二是以区域空间关系为纽带的保甲制度。这两者又都以户籍制度为基础进行架构,在反复重合中形成相互交叉的网络,由相保与连坐制度形成的集体性共同责任进行统一的规制。因此,中国传统农耕社会治安秩序的维护并不仅仅依赖国家的强制力,特别是基层社会,其治安秩序靠着宗族关系、户籍制度和保甲制度的三重交织结构而结成一个自组织的网络,在根本上是基于血缘和地缘的关系,并通过连保和互坐得以强化,虽然最终要依靠国家的强制力维系,但是基本上能够有效地进行自我规制,而不需要官方的介入作为威慑。即使是21世纪的中国农村,这种路径依然起着一定效用。LiLy L.Tsai(2007)的一份对中国316个乡村的调查结果表明,即使正式责任机制相当薄弱,非正式惯例和规范的约束也同样能够促使地方官员建立并履行其公共责任。这些非正式的责任机制可以由包含性(encompassing)和嵌入性(embedding)的连带团体(solidary groups)提供[19]。
家族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结成的亲缘群体单位。宗族是家族的扩延,是指源于同一祖先、按照父系血缘积聚而成的同姓集群。家族与宗族没有本质的区别,有时会存在规模上的不同。中国式的治理非常重视宗族作用,孟子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早在茹毛饮血的人类社会早期,族治就已显出雏形。“古无今所谓国家,抟结之道,惟在于族,故治理之权,亦操诸族”[20]。
户籍制度是征税和征役的基础,而通过进一步的数字化编排而形成的保甲制度则细化了社会群体中家庭权利和义务的等级关系,同时构成了基层治安秩序的基础。
现代法的基本精神之一是“罪责自负”原则,即一人做事一人当,个人在其自身理性能够预期或者应当预期的范围内承担违法过错的责任。而古代法的精神却以连带责任制度与之相对应,即使不是自己犯了罪,只要是犯罪者的关联人,也同样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种集体承担的责任并非以自己的份额为限,而是全部关联体的共同责任。
连带责任广泛存在于古代的中国,这增强了宗法宗族制度的自身惩戒功能,族长成为事实上的基层行政代理,这是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管控基层社会的一种替代性设计。连带责任的具体运行方式为:一是通过连坐制度,对有血缘关系的家族进行集体性惩罚;二是通过保甲制度,对处于同一地域的社区邻里进行公共责任的分担;三则是在公共权力领域,对通过举荐、科举等社会活动而产生关联的人同样采用连坐制[21]。
制度通过三条路径调整个人行为:一是设定制约条件,形成约束个人行为的规则;二是通过参数变量改变人们的价值偏好;三是明确人们的预期收益,进而调整选择的结果。警务模式作为控制社会的工具,必须形成对民众的有效激励。一项有效能的警务运行机制,必须满足激励相容约束(Incentive Compatibility Constraint)。这表明,警务效能的实现必须以个人收益最大化为前提,当一项治安强制措施对某项行为进行规制时,当且仅当在该强制措施下该行为在个人的最优选择方案之外时,此项治安强制措施才有效用。如果在该强制措施下实施某项行为仍旧构成个人最优的选择,该强制措施就是失败的。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把强制措施作为一种激励机制(incentive mechanism)的设计。激励机制作用下的强制措施,必须实现一个纳什均衡[22],即对于包括执法者在内的群体都有遵守警务规制的积极性。在我国漫长历史中形成的警务规制,作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博弈性的选择,一定是符合纳什均衡的。
作为激励工具的社会控制,核心在于合法性和服从。对制度合法性认可的关键不在于制度是否合理,而在于制度是否具有一致性和执行力。
历代统治者并不是要将保甲制度建构成消极防范和单纯惩戒性的结构,而是更多地强调和注入互保(systems of mutual guarantee)功能,提倡其相互帮助和相互救济的作用。通过某种方式形成集体性互助组织制度,是非常有利于低水平生产力的农耕文明的。井田制是由周公提出来的,这样可以形成最基层的社区互助组织。从“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和“五家相受相和亲,有罪奇邪则相及”的规定中不难发现,在相保基础之上,更重要的连带责任思想实际上已开始萌芽。连带责任意味着“集体对其成员的犯罪负有不可分割的责任”[23]。
龚自珍认为后世的保甲制度和井田制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24]。但闻钧天认为春秋时代齐国实施的“闾伍制”改革,是中国保甲制度的起源性形态[25]。
管子主要是通过士农工商“四民分治”以及“编户齐民”的方式,将连带责任进行了法律化的固定。从商鞅时代的秦国开始,刑事上的连坐制度正式确立,作为“集体性惩罚”的连带责任导致亲属之间、邻里之间和上下级官员同僚之间都负有相互检举和报告的义务。自承袭秦制的汉朝以后,历朝历代均相效仿。这种连带责任自始至终也包括田地的赋税,体系中某一户逃亡的后果,就是由邻保代为耕种其抛弃的土地,自然也承担了逃亡者应缴纳的赋税。宋代在王安石的推动下形成的保甲制度则更为完善。直至清代,保甲制度附着的责任连带的范围不断扩大,成为中国古代国家对基层社会实行控制的得力工具[26]。制度的设计必须适应激励相容约束原则,规则只能“诱导”而不能“强制”个人行为。作为激励机制,保甲制度显然符合一个纳什均衡。
信息不完全对称带来了交易成本,从而也引发了制度经济学中产权激励理论(the theory of incentives)的兴起。经济学上“理性人”的假设,基于私人得利(private benefit)与私人支出(private cost)衡量之后而进行的行动选择。当某项决策有着正收益时,即私人成本的付出小于私人收益的获得,该行为被认为是有效益的[27]。
个人实施的行为,不仅涉及其本人的成本和其本人的收益,同时也可能影响其他人的利益,此时的个人行为即存在“外部性”,它促使该行为的私人成本加上溢出的负外部性成本之和形成了真正的“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加上溢出的正外部性则形成了最终的“社会收益”。激励理论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把个体行为的外部性内部化,通过规则的强制,迫使产生外部性的个体将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转化为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从而通过个体的最优选择实现社会最优”[28]。
国家的目标不外乎两个方面:实现政治支持的最大化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29]。古代社会的政治支持在于禁止叛乱,这进一步取决于政府的日常监督和军事动员能力;经济利益在于征收公共赋税、进行公共建设,这进一步依赖于政府获得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而古代社会由于技术的限制,在社会控制中信息成本的支出是很高的,虽然伴随着秦帝国横扫六国完成大业,文字和度量衡得到了统一,历代统治者也都努力构建街亭驿站来降低传递信息的成本,但山高皇帝远,基层社会的信息收集成本仍是很高的,中央政府不得不组建特务组织或派遣钦差大臣来规避失真的信息。
农耕文明社会中人口的流动速率远远低于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交通工具的局限、道路的阻塞、户籍制度的限制将整个社会割裂成一个个相对孤立的村落。本村与外村的信息流量很少,然而村庄内却是一个熟人社会,朝夕相见的居民靠着“闲谈”(gossip)便完成了传递信息的过程,信息在村内不仅传播速度快、失真小,而且共享程度高,容易形成共识同质的价值观念[30]。
信息的分布在村落内部和外部出现了显著的不均衡性,社区内部的村民相互距离短、相处时间长、相互沟通多,信息获得的成本极低,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而外部观察者则很难得到信息,信息获得的成本很高。这种情况下,让获取信息成本较低的内部人群进行本村落的监控就可以大大地降低规制成本。更进一步,如果制度规定占有优势信息的群体同时必须对被规制对象的行为承担连带的责任,该群体也就获得了监控他人的义务和权利[31]。信息的向上传递带来的是正激励,而信息的相匿则会带来负激励。对于整个社会的控制,这种强加于优势信息的责任连带是一种很有成效的制度安排。官府处于信息获取的极端劣势,而民间的邻里亲属处于信息获取的明显优势,通过保甲制度的集体责任汲取民间的信息资源,成为作为“经济理性人”的政府管控社会的必然选择。
商鞅变法,首先“令民为什伍”,利用法定的制度将人们分为不同的结构性群体,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其次“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32]。“什伍”制度的要点在于:(1)组织和划分责任群体,实际上就是明晰“产权”;(2)同一群体内部负有相互监控和告发的义务;(3)对于越轨行为的信息,向官府报告会得到奖赏,不察或隐匿都会受到官府处分;(4)构成群体的个人违法,则由群体共同承担后果。第一、二项决定了责任承担的范围,第三、四项规定了激励性措施。如果不奖励告发者或者不惩处失察和隐匿者,就没有积极性;如果不实施“集体性惩罚”,而仅仅对知道信息的人进行处罚,就无法鼓励其他人主动去获取信息。
保甲的规模有着限定性,否则难以保证村落自我规制的成效,信息的获取、筛选、鉴定和传输就会由于群体的扩大而产生困难,规模太小的居民之间容易形成“搭便车”而导致激励机制失灵。历史上一般都选择十进制来组建保甲体系,尽管“十”并非经过精确计算的最优规模,但它便于组织和统计,是一个经验上的最优规模。
保甲制度是理解中国古代警务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关键所在,通过强制性的集体责任连带关系,实现基层横向的水平监控,大大降低了纵向垂直监视的成本,从而实现了社会治安秩序的逆向控制。传统中国农耕社会处于一个非竞争的环境中,警务控制借助于低成本的株连方式,通过制度的激励机制,以及熟人社会维持的信用制度,维系着社会秩序的稳定。
参考文献:
[1]商鞅.商君书[M].石磊,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24.
[2]王世舜.尚书译注[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7.
[3]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法制史研究室.中国警察制度史简论[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1-2.
[4]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3.
[5]Shue V.The Reach of the State: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6]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与其变革[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3.
[7]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110.
[8]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3.
[9]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63.
[10]张新光.质疑古代中国社会“皇杖不下县、县下皆自治”之说:基于宏观的长时段的动态历史考证[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85-94.
[11]吴理财.民主化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J].天津社会科学,1999(4):75-79.
[12]范晔.后汉书[M].长沙:岳麓书社,2009:1202.
[13]中国军事科学院.清代前期军事史[M]//中国军事通史(第16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329-335.
[14]朱绍侯.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738-739.
[15]中国军事科学院.清代后期军事史(上册)[M]//中国军事通史(第17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26-29.
[16]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M].范忠信,晏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53-254.
[17]陈涌清.中国古代基层乡村治安主体的演变[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73-82.
[18]李交发.论古代中国家族司法[J].法商研究,2002,(4):135-144.
[19]Lily L.Tsai.“Solidary Groups,Informal Accountability,and Loc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J].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2007,101,(2).
[20]吕思勉.先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60.
[21]张维迎,邓峰.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对中国古代连坐、保甲制度的法和经济学解释[J].中国社会科学,2003(3):99-112.
[22]郭鹏,杨晓琴.博弈论与纳什均衡[J].哈尔滨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2006(4):25-28.
[23]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M].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40.
[24]龚自珍.保甲正名[M]//龚自珍全集(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96-97.
[25]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80.
[26]韩秀桃.中国古代礼法合治思想在基层乡里社会中的实践[J].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1):94-98.
[27]丰霏.论法律制度激励功能的分析模式[J].北方法学,2010(4):108-116.
[28]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72.
[29]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4:24-26.
[30]Sally Engle Merry.Rethinking Gossip and Scandal[M]// Donald Black.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Social Control.Salt Lake City:Academic Press,1984.
[31]Armen Alchian,Harold Demsetz.Production,Information Costs,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62:777-795.
[32]司马迁.史记[M].武汉:崇文书局,2014:148.
责任编辑:时 娜
中图分类号:G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92(2016)02-0050-06
收稿日期:2015-12-04
作者简介:胡建刚,男,江苏宜兴人,管理学博士,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警务改革、治安管理。
基金项目:本文为公安部公安理论与软科学项目“我国公安辅警体系的构建与规范化研究”(2010LLYJSL06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