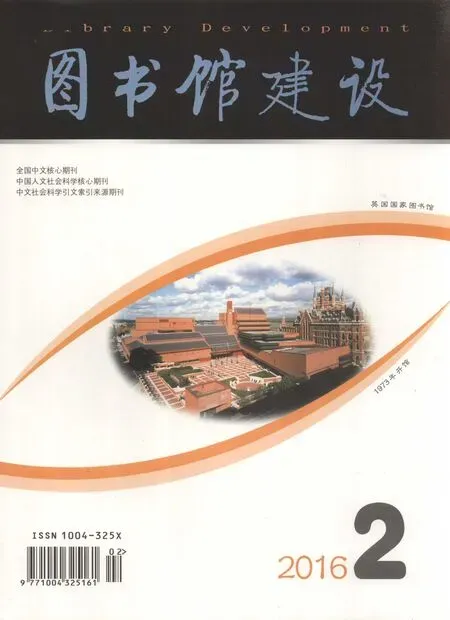民国时期图书馆职业女性形象的塑造*
——以图书馆学教育与职业活动考察为据
任家乐(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姚乐野(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民国时期图书馆职业女性形象的塑造*
——以图书馆学教育与职业活动考察为据
任家乐(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姚乐野(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民国时期,随着妇女解放运动及女学教育的兴起,中国传统封建思想被打破,女性读者群体逐渐形成,图书馆界也开设了妇女图书馆。并且,女性图书馆员也出现在图书馆界中。作为近代以来出现的新职业,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图书馆界的西方女性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使中国女性图书馆员不断加入图书馆界并且加强学习与研究,从“花瓶”成为图书馆事业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民国时期 图书馆职业 女性形象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几十年中,女性在中国社会分工中的地位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开始走出家庭,进入到许多原本属于男性的职业之中,并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近代图书馆职业的发展过程中,女性的参与程度逐渐加深,发展至今已成为女性占多数的社会职业[1-2]。这种性别角色的转换可谓潜移默化而又结果惊人。女性是如何进入到这一职业,图书馆职业女性形象又是如何塑造的?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2014年,苏全有曾发表《论近百年我国图书馆人的性别轮回》一文,透过民国时期与当代女性图书馆人在人数比例上的变化对比来反映女性的崛起[1]。然而,女性图书馆人数量比例上的变化只是事物发展的结果,还不足以反映当时女性对图书馆职业的认识及图书馆女性形象的塑造过程。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民国时期女性在图书馆学教育与职业活动中的考察,探讨这一时期图书馆职业女性形象的塑造、她们发挥的作用及取得的成绩。
1 女性涉足图书馆职业的时代背景
1.1 妇女解放运动及女学教育的兴起
19世纪末,一些社会精英认识到妇女解放的重要作用,并把它上升到发展强国的层面。1896年梁启超在《论学校:女学》中指出,“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3]报纸杂志纷纷对比西方诸强教育现状,宣扬妇女解放,力劝重视妇女教育。例如,《万国公报》载文称,“泰西各国,莫重于读书……无分男女,例必入学……女徒入院读书,美国最多,其学问造于精微,英、法、德三国亦然。”[4]这一时期,在华的西方传教士也颇重视高等教育与女子教育,“很多人明确信奉男女平等的原则,而且决心投入一场十字军运动,以解取中国妇女的‘平等权利’”[5]。在妇女解放运动浪潮的推动下,清政府对女性教育的束缚日益松动。1903年《鹭江报》报道:“固伦荣寿公主奏请开设女学堂于京师,现闻已蒙慈允,即谕派公主为学总监督,具延聘女教习则由公主转请美公使康格之夫人及日钦使之夫人代办其学堂,日内即起手缔造云。”[6]同年,清政府颁布的《癸卯学制》开始放宽妇女接受教育的限制,规定女子可以接受家庭教育[7]。1907年学部又拟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及《女子小学堂章程》,标志着中国女子学校教育在学制上得到了合法地位[7]。据当年学部总务司所编的《光绪三十三年份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统计,当时全国已有女学堂428所,女学生15 498人[8]。可见,女学教育在20世纪初已经有了惊人的成长。
1.2 女性读者群体的形成与妇女图书馆的开设
作为长期以来的信息弱势群体,妇女知识获取能力的培养在清末及民国时期受到重视,不仅各类妇女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许多报纸杂志还开设了女性专刊。笔者以“女读者”为检索词在民国期刊数据库进行全字段模糊检索,查到的论文就有181篇,其中绝大多数为女性读者与期刊编辑的交流文章。例如,其中一则具有普遍性的读者反馈:“每日费阅报时间一小时,喜看本埠新闻。每日读书二小时,喜读妇女杂志,结婚的爱民众生活等一类小说。”[9]这些文章多刊登在1920年以后,又以三四十年代居多。可见,这一时期广泛的女性读者群体已经形成。
民国时期,许多公共图书馆、民众教育馆曾经针对妇女、儿童专门开设妇女图书馆与儿童图书馆,对这两类读者群体加以特殊照顾。这种专门场所的设置与妇女受封建习俗影响不习惯到公共场合阅览有密切关系,“女子天性畏羞,居家静读者甚多”[10]。又受“男女大防”的传统礼教影响,即便在20年代文化发达的上海地区,女性利用公共图书馆阅览的情况仍不普遍。“然吾于各图书馆中,见男子阅书室中,则有人满之患,而一观妇女阅书室,则位空无人,即有之其数亦廖廖二三人,近日商务印书馆为提倡本埠妇女阅书兴味起见,特设一妇女阅书会,将妇女应用书籍,分排陈列,藉供女界之流览,并逐日派女招待员,周至招待,此诚女子选择书籍之一极好机会也”[10]。妇女图书馆在民国早期开办较普遍。随着男女平等思想与女学教育的不断发展,女性读者的性别特殊性日益淡化,民国早期很多图书馆的阅览统计中曾有读者性别的划分,到30年代以后亦逐渐为“成人”“职业种类”等划分所替代。至民国中后期,除妇女读书会仍较活跃外,公共图书馆专设妇女阅览室的情况已较少见,远不如儿童图书馆实践与研究的热度,这一现象从侧面亦反映出女性读者利用图书馆状况的改善。
2 女性图书馆员的出现
中国图书馆最早的女性图书馆员基本上是西方女性。韦棣华女士于1910年在武昌创办文华公书林,她是笔者查阅到的第一个女性图书馆员。各教会大学图书馆最初多为西方女性担任图书馆员。以华西协会大学图书馆为例,在1930年以前有沈克莹夫人(Simkin M.L.)、客士伦夫人(Carscallen C.R.)、林则夫人(Lindsay A.T.)、苏继贤夫人(Small Lottie)在图书馆任职[11],30年代以后则渐为中国女性图书馆员所替代。
中国女性图书馆员出现的时间大致在20世纪10年代末。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举行开学式,其图书馆也随之开放,并由冯陈祖怡担任该馆第一任主任[12]。1921年,出现有关北京高师图书馆女事务员陆秀的报道[13],后陆秀选择到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文华图专)进修。在20年代初至30年代初,女性从事图书馆工作仍是一个非常新潮的事件,报纸杂志屡屡将其作为新闻加以报道,诸如对于鲍益清女士任远东大学图书馆主任(1927)[14],北平市第一普通图书馆馆长罗静轩女士(1929)[15],图书馆添聘女职员(1929)[16],对图书馆学有兴味服务于本女校图书部之屈寿徵女士(1930)[17],广东省党部图书馆管理员何章锦女士(1933)[18]等报道,这些情况反映了图书馆职业中女性还较少。1928年,杜定友撰文道,“国内从事图书馆的人,虽是很多,但女子还不满十余人。以专门图书馆毕业的人而论,全国还只有男子九人,女子一个还没有。”[19]杜定友的看法可能较为片面,当时受过图书馆学教育的女性已有冯陈祖怡、王京生、胡芬、熊景芬、施何珍、徐佩珍等多人。从《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刊载的文华图专历届学生招考结果来看,很多女性在入学前就有过图书馆工作经历;又如,成都民众教育馆图书馆职员簿上就登记有“廖宗淑,儿童图书馆管理,十三年(1924)十一月到馆”[20]。这些情况都表明,在20年代虽然女性进入图书馆职业的人数很少,但已不罕见。总的来说,直至抗战全面爆发前男性仍然牢牢占据着这一职业,女性图书馆员只是点缀其间,图书馆界对于女性加入持接受的态度。
3 图书馆界对于女性执业的认识
杜定友较早关注女性进入图书馆职业这一问题。他在1928年、1935年、1941年3个不同时期发表了3篇有关图书馆与女子职业的文章。1928年,杜定友撰文称,女性具有沉静、整洁、耐久、温和4个性格特点,适宜图书馆的工作[19]。他又从国外经验与男女平等的角度论述这一问题,“据各国的调查,因为上述种种关系,所以女子服务于图书馆的非常之多。以美国而论,全国图书馆中,女子要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可见美国图书馆差不多是女子的专业了。我们中国,现在正高谈女子职业解放,要求男女平等。但是‘平等’二字,并不是专指男子做总统,女子也可做总统,男子要当警察,女子也要当警察。‘平等’二字的真谛,是各尽所能,各安其位的意思。我们所要求的,是男女在社会上,要有相当的地位。”[19]1935年,杜定友谈到这一问题时认为:“图书馆事业,应先注意内部的整理。而此项工作,最需要清醒冷静的头脑,整齐雅洁的习惯,循序而进的步骤,和蔼谦恭的态度,能忍耐稳定,而不见异思迁。能始终为社会服务,而不好高骛远。就此种个性而论,则妇女较为相近。所以各国妇女,从事于图书馆事业的多,也不是偶然的。”[21]1941年,杜定友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讲演时指出,图书馆职业类似服务业,而女性无疑是最为适合的[22]。“因办理图书馆是最需要条理和规律,而女子优势是最有条理的,管理图书馆好像管理衣服一样,要分门别类……旅店化图书馆,图书馆可以说是精神的疗养院,全世界医院中的护士以女子为最多最好,同样精神疗养院的图书馆,亦显见以女子处理为最适宜”[22]。
其他图书馆界人士亦提出相似的看法。例如,陈伯逵在上海图书馆学函授社的招生广告中特别提到女性的优势,“书事业于女性最合宜。女性好静,书中只有伏案阅览之士,无粗鲁高声之徒,幽静不俗,非他处所能比拟;女性好美,书中布置,均含美术化,清洁雅致,随处可赏心悦目;女性都柔和,书中满贮书香,不损天然柔和之质;女性都谨防饬,书中均名儒硕学之宏著,可以葆真,可以养气。推论之,今日女子职业之合宜者甚少,经商则近俗,何况商界中随处有人浮于事之象;执教则颇劳,何况学校中亦已有人满为患之苦;惟书界女性最少,又以女性合于书事业,故书界莫不盛倡女性管理之说,取物要从多处伸手,择业须在稀处着眼,凡我女性,幸垂注意!”[23]刘自昭认为,“因为儿童阅览室与成人部不同,馆员不仅是办理书籍出纳的手续,并且同时还要管理引导鼓励儿童。能够兼管这些事的馆员,必定要有以下几个条件:A爱儿童也能得儿童亲爱;B懂儿童心理教育学及有幼稚园的经验;C容貌态度和蔼,说话声调也好听;D自身的行动习惯足为儿童表率。具有上例条件,以女子为最多。所以儿童阅览室内的馆员,必定要用女子。女子生性好静,能安于教导儿童,同时不论是男孩女孩子都亲近女子。我们的幼稚园为什么要用女子?就是这个同样的理由。”[24]
为此,上海图书馆协会在1930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提交的《提倡图书馆职业案》中提出,“(图书馆职业)且于女性最是适宜。吾国职业教育正在盛倡之际,几乎多数人主张两性均须有职业,是则图书馆职业之提倡,亦不可或缓矣。”[25]郑婉锦为争取妇女权益,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上提交了《图书馆应多用女职员案》,并获全场议决通过[26]。30年代以后,图书馆学女子教育的兴起与图书馆界普遍的赞同态度有着重要关系。
1941年,吕绍虞翻译的《美国妇女在图书馆界的地位》[27]讲述了美国妇女在职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并认为其与当时的中国妇女在职业发展中的情况有相似性,如外界认为男性总是占据图书馆中较高的位置,而女性则恰恰相反。而文章通过调查认为情况并不如此,实际中,女性在中小规模图书馆的馆长任职上占有优势,大型图书馆的副馆长也基本由女性担任,在部门主任这一级别的职位上女性占有明显优势;随着女性受专门教育程度的提高及工作经验的累积,女性在图书馆界必会有更好的表现[27]。这篇文章以当时图书馆事业最发达的美国为例,解答了女性对于职业发展空间的一些疑惑,对于吸引女性加入图书馆职业起到了宣传作用。
4 女性接受图书馆学教育的情况
冯陈祖怡和王京生是最早留学海外攻读图书馆学的中国女性。冯陈祖怡于1917—1918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图书馆学校学习并获得图书馆学学士学位; 王京生于1924—1925年就读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学院[28]。在中国,1921年文华图专第二届本科班已有胡芬、熊景芬两位女性;1924年10月上海中西女塾曾开设有图书馆学课程,学生徐佩珍师从郎罗得女士(Miss Ruth Longden)学习图书馆学,1927年《图画时报》称,“徐佩珍女士中西女塾毕业生并在高等班习图书馆学三年,现在母校为图书馆主任,中国女生习图书馆学者甚少,女士实难得之人才也。”[29]中西女塾图书馆的另一位女馆员施荷珍,在1924年夏曾参加圣约翰大学组织的暑期学校图书馆学教育培训班[30]。
如果说20年代的女性受图书馆学教育的情况还只是极个别的现象,30年代以后女性接受图书馆学高等教育的情况则有明显的改观,到40年代以后已占据多数地位。通过查阅文华图专学籍档案,我们发现30年代以后对女性的招录明显增多,以1930年招录的新生为例,已有朱瑛、张保箴、李絮吟、沙鸥、宋友英、黄连琴、罗家鹤共7位女生[31]。40年代内迁时期及复员时期,文华图专女生人数有很明显的增长,有些年份可以占到一半以上①。在1941年建校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中,这样的趋势更加明显。到1944年,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学习图书馆学的女生人数已大大超过男生,“图书博物馆学系,现有一二三四年级学生一○○人,内男生四○人,女生六○人。系主任汪长炳,教授徐家麟,严文郁等”[32]。
在职业教育与短期培训上来看,女性人数增长的趋势亦相当显著。20年代末,女性接受图书馆学教育的报道逐渐增多。从一些图书馆学短训班的开办情况来看,女性的参与程度提高,“山东省立民众图书馆为普及民众图书馆之组织,设备,管理的知识及技术起见,特举办一民众图书馆讲习会。讲习时间,定为星期日上午九时至十一时,四星期毕业,并不收费。讲习期满,经测验及格者,发与证明书。各方面闻讯后,报名者甚为踊跃,计有百九十八人之多,其中女性居半,可见女子对于图书馆职业之兴味”[33]。20年代末以后,一些专为女性开设的图书馆学校开始建立,如1929年开设的广州市立职业学校图书管理科[34],1932年开设的创制中学女子部图书馆科[35],1940年开设的成都女子职业学校高级图书管理科[36]等,这反映了图书馆界加强女性图书馆员职业培养的倾向。例如,1932年《妇女生活》曾记载:
“创制中学……近以男女两性,生理心理,各具特征,特设女子一部,以图书馆科为中心,课程章程,已由高乃同君商同图书馆大家杜定友氏订定,敦请杜定友,洪有丰,李小缘,刘国钧,戴超,戴超夫人,七专家担任指导委员,俞庆棠,王立明,高君珊,钱用和,杨葆康,五女士担任顾问,……讲授实习并重,管理特别严格,俾成为吾国造就图书馆人才及训练女子新职业技能之一新场所云。”[35]
1940年成立的成都女子职业学校高级图书管理科则成为民国后期专门培养女性图书馆员的办学机构,该专业学制3年,至1949年底共毕业5个班级,共计77人;后停办于1954年,解放后又毕业学生3个班级,培养学生共139 人[36]。在40年代的一些有关图书馆入职培训的文献中,女性已开始占据多数,“采用了考核后的淘汰制,那三月后,我们只留下十二位(女同学七位,男同学五位)”[37]。
1935年文华图专教师费锡恩(Grace D.Phillips)对中国图书馆界的男性垄断地位仍感到不可思议,她提出,“假如你厌倦了美国图书馆工作的女性环境,那么来中国吧。这里男性主宰着图书馆工作。我们二年级的学生都是男性,一年级者男女各占一半。”[38]实则当时女性接受图书馆学专门教育的实际情况已较20年代有明显的改观。可见,从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情况来看,民国时期女性受图书馆学教育的情况虽历经波折,但受教育人数的总体趋势是在增加,在40年代以后女性已占有多数地位,与20年代的状况完全不同。
5 女性图书馆员的工作体会与职业贡献
5.1 工作体会
在一些文献中可以看出,女性图书馆员的工作是繁琐和枯燥的,每天需要面对不同性格的读者,还要具备且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在工作上也常有一些烦恼,如一些女性馆员表示:“我的工作是在书库里,「提线装书的善本」,同时,又是中国的古书,这也的确很不容易,当你取出一本书来,先得打开看看版本,次其看序跋,再次是内容,不说是精通,至少你得懂得是怎么回事,这就不容易了。尤其给一个文字能力并不高的人来做,那苦味非身临其境的人所能知道。”[37]“这些应份的工作,忙的时候可以叫你喘不过气来,但借书员是能够「习以为常」的。最难把捉的倒是一千多读者中成份的混杂,……因而一千多人便也生出一千多副态度来”[39]。
这些繁忙枯燥的工作并未影响女性的工作积极性,她们表现出了对工作的热诚,“为大多数人谋幸福,总是快乐的事,虽说这事还说不上为大众谋幸福,但顶少算得一点贡献,为了这神圣的贡献,我一分不敢忽略自己的任务”[40]。有的女性馆员呼吁更多的女性参加到图书馆工作中来——“亲爱的姊妹们,若有尚在选择职业而未决定的话,我觉得图书馆还是一条不算巷道的人生途径,不信可以先试试看”[37]。这些情况表明,女性图书馆员对图书馆职业是非常认同的,她们的职业表现对其他女性形成了示范作用。
5.2 职业贡献
民国时期女性在图书馆界的活动主要集中在20年代末以后,虽无法与男性相比,但其贡献仍可圈可点。除努力服务于图书馆工作外,女性图书馆员在为图书馆事业发展献计献策、开展学术研究、普及图书馆学教育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
以冯陈祖怡为例,以她首提的议案有《呈请中华教育改进社转请各省教育厅增设留学图书馆学额培植师资案》[41]、《为推广民众教育馆拟请本会组织民众教育委员会案》[42]等。此外,她在1929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上提交的论文《训政时期之图书馆工作》具有重要的建设性,并且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会呈教育部的文件中,亦以《训政时期之图书馆工作》为题列举五大重要事项,经教育部批准后转发各省府参酌执行[43]。其中虽未提及冯陈祖怡的名字,我们亦未查知该文原文,但可以推测中华图书馆协会转送教育部的同名文件应受该文影响很大。文中提到的“颁发各行政机关之出版品于各图书馆”“组织中央档案局”“减轻图书馆寄邮费”等主张都是富有现实意义和远见的。
在20世纪以前,女性尚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没有学术研究的传统,至民国时期女性忽然获得极大解放,其反差极为鲜明。女性从接受教育转而重视研究需要经历一段过程,因此女性直至20年代后期才逐渐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崭露头角是有其原因的。传统上,照顾家庭是女性的主要职责,并且女性又较为安于现状,因此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整体表现不如男性,不过民国时期仍出现了诸多优秀的研究者。以文华图专为例,因为教学中注重科研能力的培养,陈颂、胡文同、曾宪文、朱瑛、刘华锦等许多女生都曾发表了为数不少的学术文章,或为译著,或为独著,针对尚处幼稚时期的图书馆事业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其他一些未经专门图书馆学教育的女性图书馆员,也非常注重对图书馆工作中所发现的问题进行总结,提出改进的方法。例如,蒋侣琴发表的关于中学图书馆实践的文章有《阅览室管理杂论》[44]《改进中等学校刍议》[45]《中学图书馆之活用问题》[46]等;胡耐秋发表的关于民众图书馆方面的文章有《图书馆里的一个普遍现象》[47]《江苏省立教学院: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二十年度实施计划》[48]《民众图书馆的认识与商榷》[49]等;并且胡耐秋还撰写有图书馆学著作《活的民众图书馆设施法》[50]。对于一个未经科班教育的女性来说,这样的研究成果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些发表的论文与著作,数量虽不多,但已充分证明了女性图书馆员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创造力。
民国时期女性图书馆人的贡献还表现在普及图书馆学教育方面。例如,文华图专毕业生刘华锦在1930年秋安徽省立图书馆举办的面向中小学教员的图书馆专班中担任图书馆学教师[51]。在陈伯逵创办的图书馆学函授学校中,亦有冯陈祖怡、胡卓两位女性担任教员[52]。
6 余论:从“花瓶”形象到图书馆事业的重要力量
作为近代以来出现的新职业,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图书馆界的西方女性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特别是美国图书馆界女性(如韦棣华)及文华图专外籍女性教员的重要影响,为中国女性进入图书馆界扫去了性别歧视的障碍,使之加入到图书馆职业的过程显得颇为顺利,女性的优势又为图书馆界所认同和支持,为女性逐渐在图书馆界发挥作用奠定了基础。
由于当时女性解放运动及女学教育开展时间还较短暂,传统思想仍严重影响着女性的阅读、教育及就业活动,同时早期的图书馆学还处于萌芽阶段,社会对其专业性、职业化的认识还较模糊,因此家长不愿将孩子送来读书。1941年11月,成都女子职业学校校长罗家蕙在呈报教育厅公文中谈到这一问题:“此次本班(图管科第二班)新生图管科,原经遵照名额收录,但开学以后,已经录取之学生,复多不到校者,以故同等学历生,比率不免较多,兹因该科开班仅及一年,社会人士,多未明了宗旨所在,幸逾额之同等学历生,成绩尚无大差,拟请钧厅从宽核定学籍,以示倡导。”②
尽管图书馆界和社会对于女性的加入抱以接纳的态度,然而从当时的文字及图片报道来看,女性多是充当“花瓶”形象,起着点缀作用,社会对于女性图书馆员常冠以“女招待员”“女事务员”的称谓,并未与其他行业女性相区别,女性尚处于较低的地位,这也与中国“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有关。
30年代以后,随着女性意识的逐渐觉醒及男女平等思想的发展,女性在图书馆学教育领域逐渐占据多数地位。而在图书馆实践领域,经历了抗战内迁及复员时期艰苦环境的考验,女性图书馆员特有的坚韧和耐心等优点得到了图书馆界的广泛认可。越来越多的女性投身于图书馆职业,像梁思庄、胡耐秋、冯陈祖怡等女性逐步成长为图书馆馆长、主任,女性的影响力得到显著提高。她们关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认真地工作,不断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开始成为图书馆事业中的重要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女性图书馆员很少提及性别的差异,也未曾因为女性的弱势地位而去谋取相应的利益。从各类议案、论文、讲演来看,女性图书馆员总是从整体的角度去考虑图书馆事业的改进,这可能是她们有意回击社会认为女性只不过是“花瓶”“陪衬”的传统印象的一种方式。女性在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及实践中的渐进发展,对1949年以后女性在图书馆事业逐步占据主要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
注 释:
①数据来源于武汉大学档案馆, 档案号:全宗号:7; 案卷号:1-8; 1943-8。其原为私立武昌文华图专档案, 各届毕业生名册案, 档码:230-2; 教务类; 毕业纲。
②文献来源于四川省档案馆,档号为民107-02-2412,即省立成都女子职业学校图书科一二班学生学籍、成绩册: 为赀呈高级图书管理科第二班新生一览表及证件,请予从宽核定学籍由。
Female Image-Building in the Library Occupation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Based on the Study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Key words]Republic of China; Library occupation; Female image
[Abstract]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with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and the rise of female educatio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feudal thought was broken, female readership gradually formed, the library circle opened the women's library, and female librarians worked in the library circle. As a new kind of occupation emerged in modern times, the image of western women provided a strong demonstration effect to Chinese library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ese women continued to join the library circle and strengthen learning and research, changed from the ''vase'' to the important force in librarianship.
[中图分类号]G259.296
[文献标识码]A
*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研究”的成果, 项目编号:14BT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