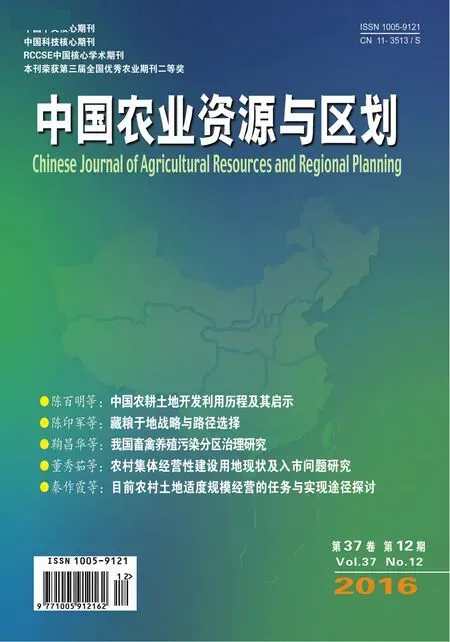村集体在建立规模化家庭农场结构中的角色作用*
张学艳
(郑州工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河南郑州 451400)
村集体在建立规模化家庭农场结构中的角色作用*
张学艳
(郑州工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河南郑州 451400)
文章基于土地流转背景下,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基础,构建以家庭农场主、土地流出户、村集体、地方政府为行动者的家庭农场结构,探讨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与监督下,村集体与家庭农场主、土地流出户利益博弈的过程。分析村集体为了实现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与家庭农场结构产生互动。村集体的行为既受到外部政策制度方面的约束,又受到内部管理自主性的约束; 村集体通过自己的能动性反作用于家庭农场结构,最大限度地弥补外部政策制度的缺失,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突破家庭农场结构的内部制约。促使家庭农场结构不断改变,产生新的规则与资源,再形成新的结构,并在实践中接受新的调整与改变,经历新结构化过程,保持着动态的变迁。在与家庭农场结构的互动过程中,村集体发挥着沟通协调、经营协助、中介桥梁、引导服务等角色作用,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促进家庭农场结构中各行动者利益的实现。
结构化理论 村集体 规模化 家庭农场结构 角色作用
0 引言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使得“谁来种地、地怎样种”问题日益突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经成为创新农业经营体制的重要任务。2013年,党中央在一号文件中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首次提到了家庭农场,家庭农场在这一大环境下应运而生,为中国现代农业指明了发展方向,同时也是改变传统农业经营的必然选择。村集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以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家庭农场经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充当着家庭农场主与土地流出户值得信赖的中介组织。近几年学术界比较关注这一问题。秦文通过对粤东2个村庄的调查,提出欠发达地区村集体在村务中的角色定位及功能[1]; 石磊基于农村集体经济视角下,指出村民委员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行使其经济职能的过程中出现了组织的“同构”,需要理清各自的功能与角色作用[2]; 许伟从地方政府、农民、村集体3个主体出发,提出村集体要摆正自己的角色,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3]; 王淑丽基于现行的农地管理制度下,对村集体与农民在农地管理的行为进行分析[4]; 于洪彥、刘金星、杜金亮等人,基于结构化理论的视角探讨制度变迁与农户经营行为的关系[5]; 刘镭运用结构化理论分析农业经营方式选择行动与农村社会结构的关联[6]; 姚上海、李莉、潘华基于结构化理论视角探讨农民工的生存及社会角色转型问题[7-9]; 刘静、张艳基于结构理论视角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变迁及政治参与[10-11]。
大量的研究成果对村集体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角色作用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大多侧重研究村集体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角色作用,很少有人从建立规模化家庭农场角度研究其角色作用,特别是利用借鉴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研究村集体角色作用的更少,基于结构化理论视角的研究更多侧重于农民工的角色转型,鲜有学者从农业经营方式选择和农户经营行为与农村社会结构及制度的关系研究,但较少展开,缺乏针对性。文章以结构化理论为视角,研究村集体为了实现农村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与地方政府、家庭农场主、土地流出户进行利益博弈,在与家庭农场结构互动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角色作用。以期为我国家庭农场及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和有价值的理论支撑。
1 结构化理论:村集体为中介的家庭农场结构的构建
1.1 结构化理论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通过对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反思,提出了结构化理论,主要研究人的行为及主观能动性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吉登斯提出个人的行动与社会结构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5]。他认为“结构”是不断地卷入到社会系统的再生产过程之中的规则和资源,结构具有二重性,既制约着行动者的行动,同时又为行动者的行动提供资源和条件,使行动者的行为成为可能,结构中的行动者既受到结构的约束,又改变着结构,两者之间相互依持,并反应在社会实践之中[6]。行动者通过自己的能动作用促进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与调整,进而趋于稳定。行动者具有反思性和实践性的知识,行动者行动时,既需要有自己行动的理由和动机,还会对自己的行动及所处的环境进行反思性监控,但行动者的知识是不完全的,其行动总会受到一些“未被认知的行动条件”的制约,这些“未被认知的行动条件”就是社会结构,因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导致出现“非预期的行动后果”,产生新的社会结构。行动者未认知的行动条件、反思性监控行为、理性化行动、行动背后的动机以及“非预期的行动后果”构成了吉登斯的“行动自我的分层模型”[12]。吉登斯认为,人类的所有行动都表现为这个模型,且都是以实践意识作为认知基础的。
1.2 村集体为中介的家庭农场结构的构建
在家庭农场经营模式中同样存在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家庭农场结构模型。首先,以盈利为目标的家庭农场主,为了获取高额的经营利润,与家庭农场结构产生互动,争取较大规模的土地,以及高额的农业补贴和高水平的社会化服务。家庭农场结构通过有限的资源与相关的规则对其行为进行约束,并要求其对土地流出户提供相应的土地租金,将家庭农场主的利润与行为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其次,以保障为目标的土地流出户,家庭农场稳定经营的根本条件就是土地,土地流出户只有在生活有保障的基础上,才会将土地流转出去。土地流出户以保障为目标,与家庭农场产生互动,既为家庭农场结构提供了必要的资源,也对其他行动者的行动进行了制约; 第三,以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为目标的村集体,村集体充当家庭农场主与土地流出户中间桥梁,负责他们之间的协调与沟通工作,并负责宣传运用家庭农场结构中的规则和资源,家庭农场结构的产生与调整势必会影响村民之间的人际关系,因此村集体是在政府的指导与监督下,处理家庭农场主与土地流出户产生的各种经济纠纷,推进家庭农场的稳定发展; 第四,以管理与监督为主要目的的政府,地方政府作为资源的提供者与规则的制定者,监控着家庭农场结构的运行,把家庭农场主、土地流出户及村集体的行为规定一个合理的“度”,三个行动者在规定的范围内争取各自的利益,并为之做出相应的付出[13]。
2 村集体与规模化家庭农场结构的互动过程
村集体作为农村土地的所有者,充当着家庭农场主与土地流出户的中介,实现家庭农场主与土地流出户之间土地与租金的交换,并将结构中的规则与资源提供给家庭农场主与土地流出户,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利益,以促使本村集体资产的合理利用,确保集体资产的保值与增值。
2.1 结构制约性表现
家庭农场结构的目标是确保粮食的安全、高效生产,农民之间的和谐稳定,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村集体的行为。因此,村集体的行为必然受到结构的制约,具体表现为外部制约与内部制约。
2.1.1 外部制约——政策制度的限制
政策制度是对村集体行为影响最大的外部因素,不完善的土地流转制度,家庭农场准入与退出机制的缺失,农民保障体系不健全、社会服务化体系不到位等都约束着村集体的行为。
首先,土地流转与农场准入退出制度对村集体的行动具有重大的制约作用。从土地流转制度上来看,适度规模的土地是实现家庭农场健康发展的先决条件,土地是家庭农场主实现利润、土地流出户获取保障、农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国家实现粮食安全生产的根本所在。我国土地产权模糊,土地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农民只拥有农地的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导致在实践中土地流转难、流转期限短。从而导致家庭农场主不愿意或者不敢投入大量资金改善基础条件,同时挫伤其他投资者的积极性。并且土地流转市场不健全,土地流转合同多为口头协议,发生纠纷时,难以调解。土地转让者与土地需求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沟通不畅通,双方很难找到合适的交易对象。土地流转的市场价格缺乏统一的标准,土地转让者漫天要价和农场主压低土地租金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些都给村集体的工作开展带来很大的难度。从家庭农场准入退出机制上来看,虽然国家出台了家庭农场的发展指导性意见,但在实际操作中缺乏规范性,家庭农场的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造成家庭农场市场主体地位不明确,经营规模也没有具体的标准,家庭农场的界定缺乏统一的标准,注册流程相对简单,注册条件相对宽松[14]。并且政府对已注册成功的家庭农场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许多在形式上注册的是家庭农场,但实为农业公司,与家庭农场的经营理念相背离,进而导致土地流转成本增加,家庭农场主的利润降低,出现非粮化倾向,这都是村集体无法解决的难题。
其次,农村社会保障与社会化服务不完善也制约着村集体的行动。土地流转难,流转期限短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的恋土情结重,土地是他们的生活保障,而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自己生活、就业、养老、医疗等保障问题,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圆满解决时,农民是轻意不会将自己的土地流转出去。土地租金问题也决定着农民土地的流转,许多地方存在着土地租金过低,或者没有租金,也都影响着农民土地流转的积极性。另外,家庭农场实现规模化生产经营,必须配套相应的机械化作业、病虫害防治、动物防疫、科技服务、农业金融与保险、农产品购销等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而目前社会化服务体系尚未全面构建,一些实力不强的家庭农场,自身无力改善农田基本条件、购置配套的农机具,抗御自然灾害条件差,耕作水平不高,经济效益偏低。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也制约着村集体的行动[15]。这都降低了农户申报家庭农场经营的积极性,增加了村集体协调沟通的难度。
2.1.2 内部制约——管理自主性受限
村庄的土地归村集体所有,而在家庭农场结构中,村集体管理的自主性受到家庭农场结构的制约,在结构中,村集体只充当了解释、宣传的角色,也就是把规则与资源提供给农民,鼓励农民把土地流转出来,动员少数农户来经营家庭农场。
首先,村集体被结构限定为规则和资源的传达者。在家庭农场结构中,村集体的任务主要是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农村经济工作,村集体的行为要对地方基层政府负责,代理行使基层政府的部分权力。但由于局限于自身权力与行政关系,对地方政府制定的决策和规定的相关制度缺少表决权,不能根据本村的实际情况来争取更多的资源,无法更好地满足家庭农场主生产经营所需和土地流出户的保障需求。家庭农场主经营所需的规模化土地、先进的农机设备、完善的社会化服务及相关的农业补贴政策,以及土地流出户就业安置、生活、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这都是村集体难以突破的难题。最终赋予村集体的职能就是来传达、宣传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为家庭农场的发展流转出更多的土地,安抚失地农民的情绪,发放政府给予的土地补偿金[16]。由于村集体自身权力的局限,对农地补偿标准与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缺乏话语权,只能充当一个上传下达的中间角色。
其次,村集体仅充当着家庭农场结构的基层执行者。在家庭农场的准入、经营、退出都要严格把关,依据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对家庭农场经营者进行筛选与换届。随着更多的村民知晓家庭农场的收益状况,会出现更多的竞争者参加家庭农场主的竞选。面对更多的竞争者,村集体必须制定合理可行的方案。家庭农场的实施方案要通过党员议事会、老干部、老党员及村民代表共同商议决定,决策时不得靠关系、金钱等,方案确定后还要上报给地方政府进行审批,获得审批后,最终的实施方案要予以公示,接受村民报名,严格按照家庭农场准入要求进行筛选,确定家庭农场主人选并予以公示。另外,要对家庭农场主的经营状况进行核查,核查其是否按照要求种植粮食,有无转包土地现象,核查家庭农场主是否按要求养地、科学种田、增加土壤肥力和改良土壤结构,并按照相关标准对所有家庭农场主进行打分考核,确保公平公正。因此,在家庭农场结构中,村集体村庄管理的自主性降低,被定位于家庭农场结构的基层执行者。
2.2 村集体能动性表现
以村为单位推行的家庭农场制度,既保证了土地归村集体所有,又可以发挥村集体在村庄中的影响力。村集体通过能动作用,弥补了土地流转、家庭农场准入与退出、农民社会保障、社会化服务等政策制度的缺失,推动家庭农场结构的运行,同时也削弱了结构的约束。在实践中,村集体通过发现问题并有效地解决问题,促进家庭结构的调整与再生产,并趋于稳定。
2.2.1 冲破外部制约,最大限度地弥补政策制度的缺失
首先,对土地流转与家庭农场准入退出机制的突破。在家庭农场结构中,村集体通过自己的能动作用,规范土地流转程序和农场准入退出机制,保护家庭农场主和土地流出户的合法权益,实现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一是村集体对土地流转双方制定规范的流转程序,要求双方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办理相关事宜。规定土地流转时必须签订书面合同,并在合同中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尽量避免口头形式的土地流转,做到有据可依,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 要求双方严格按照合同履行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尤其是土地流转期限的遵守; 并对农民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增加其守法意识,双方严格按照合同规定履行自己的权利义务,避免在农场主获得收益时,土地流出户要求提前中止合同,而导致家庭农场主的权益受到损害。二是建立家庭农场准入与退出机制,家庭农场结构中的村集体,从本村实际出发,借鉴其他家庭农场的成功经验,制定适合本村发展的家庭农场认定标准,对农场主的年龄、土地规模、生产经营条件、投入资金等方面做出量化规定。根据农产品生产与销售特点对家庭农场进行划分,不同规模和类型的家庭农场分别制定注册和认定标准,并根据家庭农场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不同的经营管理办法,保障家庭农场的顺利发展。规范家庭农场的退出机制,淘汰因经营不善导致破产和不适合市场发展需要的家庭农场,提高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和经济效益。简化家庭农场审批程序,为家庭农场主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与政策支持,并有效监督已注册成功的家庭农场,防止注册为家庭农场而实为农业公司,背离国家支持家庭农场发展的初衷,抬高了土地租金,损伤了家庭农场主的经济收益,导致非粮化现象的发生[17]。
其次,突破农民社会保障与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制约。农民的生活、养老问题得不到圆满的解决,是不会自愿地把土地流转出来的,为了促进农村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村集体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根据本村农民的生活水平、农民收入状况及农场主盈利情况制定合理的土地租金标准,并根据物价与企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的调整,对土地租金进行调整,让农民的生活有保障。合理转移农村劳动力,为其提供农业或非农就业机会,妥善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同时村集体通过宣传、引导,让更多的农民了解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提高农民的参与意识,积极参保,使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另外,村集体通过能动作用突破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制约。村集体通过借助地方政府的力量,建立农村图书馆,给农民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鼓励农民学习家庭农场知识,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定期对家庭农场主进行农业科技知识培训,促进相互之间的交流学习,进而提高家庭农场主的经营水平; 引导家庭农场主自发成立中介服务机构,建立专业协会、产销服务队、专业合作社等,提高服务化水平,增强农场主抵御自然灾害及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并为家庭农场的中介服务机构提供各种便利条件; 并为家庭农场主做好金融服务工作,引导其以农场土地、自家宅基地、大型农机设备等进行抵押贷款,村集体出面成立联保小组,把各家庭农场联系起来进行联保贷款,积极联系当地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让他们为家庭农场提供信贷支持,进行担保贷款。同时鼓励家庭农场主积极参加各种农业保险,通过保险转移家庭农场的经营风险[18]。村集体通过其能动作用,突破结构中社会化服务的制约,并创造新的资源与规则。
2.2.2 通过实践经验,突破内部制约
首先,村集体利用自己在村庄内的影响力推行家庭农场结构。村集体由于行政权力的局限,在家庭农场结构中,充分发挥自己在村庄内的影响力来突破结构的制约。以村庄管理者与土地所有者的村集体作为中介,组织家庭农场主与土地流出户之间进行租金与土地交换,容易取得土地流转双方的信任; 村集体工作人员具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便于解决家庭农场经营与土地流转中的实际问题,当申请家庭农场经营者过少时,村集体可以根据村民的实际情况,找出村里的种粮高手及曾经当过村干部的村民,对其进行劝说动员,让他们加入到竞选当中,最终选出合适的家庭农场经营者。当申请家庭农场经营者过多时,村集体会对只为利益而不适合经营家庭农场的村民做思想工作,劝说他们退出竞争,让其明白家庭农场主应该是纯农户,不单单是赚钱的工具,让他们做出更理性、适合自己的选择。村集体通过自己的能动作用,根据家庭农场结构中的准入规则,为家庭农场找到真正合适并善于经营的农民,促进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
其次,村集体通过能动作用削弱结构的规范性并提供新的思路。对家庭农场主的一些违规操作,村集体采取默许态度,进而削弱了家庭农场结构的规范性。如已到退休年龄的家庭农场主以子女名义申请再获得经营资格、通过“种养结合”方式延长家庭农场经营期限、未经地方政府允许调整种植结构、找无意经营的亲戚朋友参与家庭农场主竞选再转包等违规行为,这也足以说明家庭农场结构的不完善,缺乏对违规行为的惩罚措施,由于都是村集体成员,村集体也碍于情面不好制止他们的违规行为。另外,村集体考虑到家庭农场主与土地流出户双方的经济利益,破坏了家庭农场的准入与退出规则,不以现金形式预付土地租金的农场主,条件不符又不办理退工手续的土地流出户等,村集体照顾他们的难处,但削弱了家庭农场结构的规范性,也给自己增添了不少麻烦。作为家庭结构的主体,村集体通过自己基层工作经验,为家庭农场结构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如帮助家庭农场主试验“种养结合”模式,探索新的抵押、联保、担保贷款形式,为家庭农场健康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19]。同时,村集体农民利益出发,结合本村实际情况,向地方政府反映家庭农场主的获利、稳定地块、稳定经营期限与土地流出户获取保障、公平的需要,为地方政府提供可供参考、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2.3 村集体与家庭农场结构互动的结果
家庭农场结构的推行需要家庭农场主和土地流出户的配合外,还需要一个中间人,将结构中的资源与规则传达给家庭农场主与土地流出户,以村为单位推行的家庭农场,最合适的人选就是村集体了。在日常实践中,村集体受到外部与内部制约,村集体通过自己的能动性,弥补家庭农场结构在土地流转、家庭农场准入退出、农村社会保障、农业社会化服务等制度的缺失,突破结构的外部制约。同样,在实践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冲破内部制约,如放松家庭农场准入与退出条件、为家庭农场发展提出新思路等,村集体在家庭农场结构内外部制约下,与结构展开互动,村集体发现突破家庭农场结构的制约会给自己的管理工作带来更多的麻烦,为了避开麻烦,而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并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解决家庭农场发展的问题,促使家庭农场结构再生产与调整,趋于稳定。通过家庭农场结构的推行,可以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的增收,也可以巩固其在村里的权威地位,进而提升村集体的声望。在此情况下,村集体愿意接受家庭农场的安排,在政府的监督下,承担好执行者的角色,为家庭农场主与土地流出户传递结构的规则与资源,促进家庭农场结构的稳定。
3 村集体在家庭农场结构中的角色作用
村集体是家庭农场关系最密切的组织。在家庭农场的创建和实践过程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需要协调好政府、家庭农场主、土地流出户三者的关系,引导家庭农场主的经营行为,为其争取更多的政府支持,捋顺农场主与土地流出户之间的关系,为家庭农场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打造独具特色家庭农场。
3.1 发挥沟通协调作用
作为集体组织的农村,村民的生产生活都是相互合作、相互联系的。每个村民的行为都会影响到村庄家庭农场的创建与发展。在家庭农场结构中,村集体大力宣传家庭农场,为农民之间的土地流转提供便利条件,并制定出合理的土地租金标准,保证农民土地的经营收益,满足土地流出户的生活所需,并对困难农户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根据村里的种养情况,选出能力强的农户,鼓励他们注册家庭农场,并上报地方政府,为其争取相关的农业补贴及财政支持,帮助经营者提高家庭农场的效益。全面了解家庭农场主和参与劳作的其他村民,保证农场生产过程的有序进行,保护双方的经济权益,促进其和谐共处。合理安排农机设施设备与技术物资的使用,避免因资源的使用而产生矛盾。协调好农场主之间的关系并促进其交流合作,提高农场的经营管理水平。并积极联系批发商、销售商及合作企业,打开市场促进农产品的销售。从家庭农场的创建、生产、销售都离不开村集体的沟通协调作用,为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20]。
3.2 发挥经营协助作用
在家庭农场结构中,村集体另一重要作用就是对家庭农场经营的协助作用。一是在地方政府的指导与监督下,制定出合理的家庭农场准入与退出标准,对家庭农场的申报者进行筛选,挑选出最适合的经营者,并对申请者的申报条件进行核查,剔除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者,并建立考核机制,对家庭农场主的经营进行考核评估; 二是对家庭农场的经营过程进行协助。协助家庭农场主在保障粮食安全生产的前提下进行生产经营,杜绝以家庭农场名义申报,实为农业公司现象的发生,并核查土地流出户的土地租金是否及时到位、是否根据企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的调整而调整、进入农场辅助劳作的农民报酬是否合理等,保证满足土地流出户的生活所需; 三是核实家庭农场主与土地流出户合同履行情况[21]。避免农场主艰辛创业时合同正常履行,获得收益时土地流出户要求提前解除合同,避免因提前解除合同导致家庭农场主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村集体要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来确保土地流转合同的正常履行。
3.3 发挥中介桥梁作用
村集体是联系地方政府、家庭农场主、土地流出户的纽带,在推进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发挥着重大作用。一是在政府与农户之间,村集体作为地方政府和农户之间的中间人,负责把家庭农场经营的规则和资源传达给农户,农户在地方政府的监督下进行土地流转,并在监督下发展家庭农场,在经营过程中,村集体为家庭农场主争取更多的农业补贴、财政支持及社会化服务,为土地流出户争取更多的生活保障; 二是在家庭农场主与土地流出户之间,村集体作为家庭农场主与土地流出户双方都信赖的中介组织,收集土地流转信息,为双方的选择提供便利,减少额外成本,完成农场主与土地流出户土地与租金的交换。并为双方提供规范的合同文本,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减少矛盾的发生[22]。同时村集体为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提供尽可能多的农业技术培训、农机设施设备、农业补贴、金融保险、农产品销售等方面的服务,促使家庭农场主的获利目标的实现,同时也解决了土地流出户土地流出后的后顾之忧。
3.4 发挥引导服务作用
在家庭农场结构中,村集体的另一重要作用在于对家庭农场经营的引导与服务。村庄的自然条件与经济基础不同,家庭农场的发展模式也不能照搬照抄,要根据当地的产业结构与产品差异,结合自身优势特点,打造特色家庭农场模式。村集体为家庭农场主提供多方面的支持与服务,积极组织家庭农场主进行实地调研与考察,掌握农产品的市场需求情况,有针对性地发展市场需求量高或潜力大的农产品。带领家庭农场主向农业农家咨询,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种植优质高产的农产品,拓宽农场主的经营思路和农场的产品结构。村集体通过深入考察农产品加工行业,了解他们的需求,使家庭农场根据农产品加工行业的需求进行生产,实现产销对接。对当地成熟的特色产业的深入了解,为家庭农场生产的农产品找寻稳定的销路。联系当地农业技术学校,鼓励家庭农场主参加学习,学习农业科技、市场营销、农场经营管理、农业融资与保险等知识,充分利用网络教育,提高农场主的农业知识和经营管理水平,并通过网络渠道为自己的农产品找寻更多的销路。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家庭农场结构是在地方政府引导和监督下,以村集体为中介在村庄内进行土地流转,将土地集中起来,流转给有能力经营的部分农户,进行规模化经营。从村集体与规模化家庭农场结构的互动行为,可以得出结论如下:第一,家庭农场结构并不是静止的,是一种结构化过程,是家庭农场结构中各行动者与结构反复互动,得以再生产与调整,趋于稳定,形成暂时稳定、新的家庭农场结构,并在新的实践中与行动者继续互动,不断调整以适应实际发展需要。第二,在规模化家庭农场结构中,村集体既受制于土地流转、家庭农场准入与退出、农村社会保障、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政策制度,又受制于村庄管理的自主性,结构的制约导致村集体工作难度的加大。第三,村集体通过自己的能动性反作用于结构,通过自己的动员实现土地平稳地流转; 根据村庄的实际情况,建立本村家庭农场准入与退出机制; 通过各方协调,进一步完善土地流出户的社会保障与家庭农场主的社会化服务; 并利用自己在村庄内的影响力推行家庭农场结构,削弱结构的规范性,为家庭农场的发展提供新思路。第四,村集体在家庭农场经营过程中的作用重大,村集体发挥着沟通协调、经营指导、中介桥梁、引导服务等作用,实现农村集体资产的保值与增值,保证粮食的安全与稳产,成为地方政府、家庭农场主、土地流出户之间稳定、信赖的中介组织。
从以上结论可以得出的重要启示在于:村集体家庭农场主与土地流出户共同信赖的中介服务组织,在家庭农场健康发展过程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作用重大。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的制度规范其行为,把村集体的行为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并通过培训和指导,提高村集体在家庭农场经营中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首先,村集体要依照地方政府的农业总体规划,做好本村农业生产详细规划,确保土地资源高效、合理用于农业生产,并对家庭农场土地的用途、家庭农场主的经营行为、土地租金的给付等进行管理,确保农地农用,为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铺平道路; 其次,加大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培训力度,引导村集体对家庭农场进行规范化管理,通过开展土地流转政策、法规教育、标准合同文本、经费保障机制等相关培训,使其认清家庭农场目前发展的形势与政策,提高村集体的中介服务能力; 第三,村集体要承担好服务保障功能,组织建好农田水利、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积极宣传农业优惠、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政策,创新资金筹集方式,为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做服务工作; 第四,村集体要组织引进优质智力资源,组织有实力的大农场联合起来,外聘农业科研单位的专家教授定期来考查指导,或去农业技术院校招聘优秀毕业生到农场工作,为农业生产经营提供智力保障,开阔视野,拓宽发展思路。以促进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
[1] 秦雯.欠发达地区农地流转中农民意愿与村集体决策.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12, 11(2): 44~50
[2] 石磊. 试析农村集体经济视角下的村民委员会职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5:151~155
[3] 许伟. 集体土地流转中集体角色的错位与回归.云南电大学报,2011, 13(2): 75~77
[4] 王淑莉. 中国农地管理中村集体与农民的行为分析.开发研究,2012, 24(2): 80~84
[5] 于洪彥,刘金星,杜金亮,等.制度变迁与农户经营行为的结构化理论分析.调研世界,2008, 6(6): 15~17
[6] 刘镭. 农业经营方式的选择行动与社会结构互动关系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2): 93~97
[7] 姚上海. 结构化理论视阈下农民工社会角色转型问题研究.学术论坛,2010, 8(8): 20~24
[8] 李莉. 结构化理论视角下农民工的生存抗争.泰山乡镇企业职工大学学报,2011, 18(3): 3~4
[9] 潘华.“回流式”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新趋势——结构化理论视角.理论月刊,2013, 3(3): 171~174
[10]刘静. 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变迁及对策探析——从结构化理论视角看.学理论,2013, 32(32): 67~68
[11]张艳. 村民自治制度下的新生农民工政治参与——以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为分析视角.产业与科技论坛,2009, 8(12): 17~19
[12]周达,司聃.经济结构研究亟待深化的几个问题.兰州商学院学报,2015,(2); 90~95
[13]董凌芳. 结构化理论视野下松江家庭农场制度研究.上海:华东理工大学,2013,12:18~19
[14]陈振,程久苗,费罗成,等.土地流转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以芜湖市为例.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5,36(3): 72~78
[15]刘金蕾,祝新亚,李敬锁,等.山东省土地流转的因素分析.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4,35(6):32~38
[16]Dogliotti S,García M C,Peluffo S,et al.Co-innovation of family farm systems:A systems approach to sustainable agriculture.Agricultural Systems,2013
[17]Acharya S S.Domestic agricultural marketing policies.In:Acharya S S,Chaudhari D P,eds.Indian agricultural policy at the cross road.Jaipur,India:Rawat,2000
[18]Allen,Douglas W,Lueck,et al.Family Farm Inc.Choices:The Magazine of Food,Farm,and Resource Issues,2000, 15(1): 13~17
[19]Ciolos D.The Diversity of Family Farms is a Strength for World Agriculture.EuroChoices,2014, 13(1): 3~4
[20]丁志帆,刘冠军.家庭农场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选择.农业经济,2014,1:7~9
[21]武峰,陶志刚.对天水市麦积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调查与思考.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4, 35(2): 138~142
[22]陈利颖. 乡村治理视角下的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研究.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4, 35(4): 20~25
THE ROLE OF VILLAGE COLLECTIV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LARGE-SCALE FAMILY FARM STRUCTURE*
Zhang Xueyan
(The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Zhengzhou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Zhengzhou,Henan 451400,China)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land circulation, and Giddens′ structure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ed the structure of family farm including the family farmers, land outflow households, village collective, and local government, explored the benefit gambling process among village collective,family farmers, and land outflow households, under the guidance and supervision of local govern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village collective needed to interact with the family farm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value of collective assets. The village collective behaviors were constrained by both the external policy and internal management autonomy. The village collective can make up the lack of external policy system through their initiative reaction in family farm structure, and break the internal control through practice experience. The structure of the family farm constantly changed and generated new rules and resourc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with the family farm, the village collective played the roles of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business assistance, intermediary bridge, and guide service in achiev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d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actors in the family farm structure.
structure theory; village collective; scale; family farm structure; role function
10.7621/cjarrp.1005-9121.20161203
2015-11-26
张学艳(1982—),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管理。Email:zhangxueyan1215@sina.com
*资助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河南省家庭农场经营模式与管理制度创新”(2015BJJ053); 河南省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粮食主产区农业技术选择对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评估”(152102110162); 河南省社会科学普及规划项目“解读新型城镇化与百姓生活”(053)
F306.1; F321.4
A
1005-9121[2016]12-001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