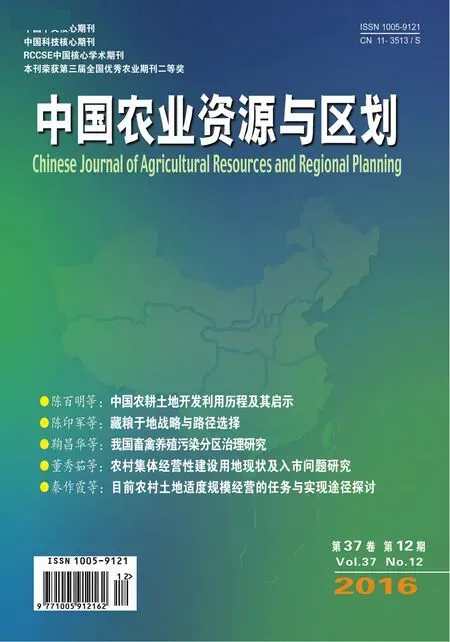藏粮于地战略与路径选择*
陈印军,易小燕※,陈金强,陈章全,韩 巍,杨瑞珍
(1.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北京 100081; 2.农业部发展计划司,北京 100026)
藏粮于地战略与路径选择*
陈印军1,易小燕1※,陈金强1,陈章全2,韩 巍2,杨瑞珍1
(1.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北京 100081; 2.农业部发展计划司,北京 100026)
针对长期实施的藏粮于仓、以丰补歉策略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中央提出实施“藏粮于地”战略。何为“藏粮于地”?实施“藏粮于地”有何益?实施“藏粮于地”面临哪些挑战?如何实施“藏粮于地”?对此,文章进行了系统分析论述。我国粮食生产“十二连增”,粮食库存丰富,粮食生产稳定性增强,近年国际粮食价格低廉,这些为我国实施“藏粮于地”战略创造了条件。然而,实施“藏粮于地”并非易事,面临许多问题与挑战,包括:耕地面积有可能再次大幅减少,耕地质量堪忧; 水资源约束日益突出,粮食生产能力提升的难度越来越大; 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农业自然灾害突出; 规模化生产经营与社会化服务水平低,粮食生产调控能力弱; 国内粮食生产大萎缩和世界粮食价格危机有可能再现,冲击“藏粮于地”行动计划。实施“藏粮于地”,关键在“地”,核心在“藏”。数量充足和高质量的耕地是基础,同时,还必须有完好的“养地”与“用地”机制。因此,应强化“护地”、“建地”、“养地”与“用地”,即走护、建、养、用“四结合”之路。
藏粮于地 粮食安全 耕地保护 耕地质量 粮食生产能力
1 藏粮于地”概念的提出及内涵
1.1 “藏粮于地”概念的提出
经文献检索,在我国最早于2000年出现的是“藏粮于土”,出现于封志明、李香莲发表的“耕地与粮食安全战略:藏粮于土,提高中国土地资源的综合生产能力[1]”一文。文章针对我国耕地数量不足并且还在不断减少,耕地质量欠佳,劣质低产田增加等威胁我国粮食安全而提出“藏粮于土”,主要目的是提高中国土地资源的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周健民于2004年提出“藏粮于土,确保耕地数量和质量及粮食生产的可恢复性[2]”。龚子同等人也于2004年提出“要大力提倡变藏粮于库为藏粮于土的行动计划; 藏粮于库只能解决一时的粮食余缺,只有藏粮于土才能全面提高中国土地资源的综合生产力,才能保障久远的粮食安全[3]”。
在我国,“藏粮于地”最早出现于2004年。一是许经勇针对粮食储备成本过高,维护过高的粮食库存储备,政府财政不堪重负,而且粮食储备调控效率低、时效差、透明度低,同时,在由于粮食减产而出现粮食短缺时,靠大量进口粮食满足国内之需,既不现实,也不经济的现状,提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是在“地里”,而不是在“库里”,更不是在外国的“库里”,提出要突破单纯追求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的观念,由单纯“藏粮于库”向“藏粮于库”、“藏粮于地”和“藏粮于科技”相结合转变[4]。二是王华春等提出增加粮食供给的载体是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的保护,因此,应该十分珍惜并合理使用每一寸土地,实施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实现“藏粮于地”[5]。
“藏粮于田”最早出现于2001年的文献之中[6],但作为研究主题则最早出现于2004年。杨正礼等人的“我国粮食安全的基础在于藏粮于田[7]”一文针对我国人口多,粮食需求总量大,国际粮食贸易数量有限和价格波动大的特点,提出以保护和强化粮食生产能力储备为基础,坚持“以我为主”,积极实施“藏粮于田”战略。该文的“田”即“农田”,是指耕地。
“藏粮于地”最早出现于中央文件之中是2005年12月29日,出现于温家宝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需重视的问题”一文。但“藏粮于地”上升为国家战略始于2015年。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守耕地红线,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全面划定永久基本农田,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3月8日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研究和完善粮食安全政策,把产能建设作为根本,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8]。
1.2 “藏粮于地”的内涵
何为“藏粮于地”,目前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习近平在2016年3月8日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时所指“藏粮于地”,强调的是“研究和完善粮食安全政策,把产能建设作为根本”。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说明时提出“经过长期发展,我国耕地开发利用强度过大,一些地方地力严重透支,水土流失、地下水严重超采、土壤退化、面源污染加重已成为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矛盾。当前,国内粮食库存增加较多,仓储补贴负担较重。同时,国际市场粮食价格走低,国内外市场粮价倒挂明显。利用现阶段国内外市场粮食供给宽裕的时机,在部分地区实行耕地轮作休耕。休耕不能减少耕地、搞非农化、削弱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急用之时粮食能够产得出、供得上”。从“说明”中体现了“藏粮于地”的轮作休耕内涵。封志明、李香莲所说“藏粮于土[1]”是指加强对现有耕地的保护与能力建设,开发后备耕地资源补充耕地之不足; 立足全部国土,挖掘非耕地食物资源生产潜力,弥补耕地粮食生产能力的不足,其目的是通过耕地保护建设与土地开发,提升粮食与整个食物的生产能力。周健民所说“藏粮于土[2]”,是指在农业结构调整和土地开发过程中,尽可能地避免破坏耕地或永久性占用耕地,要保护土壤,保护耕地,即保护我国的粮食生产能力。许经勇所说“藏粮于地[4]”是指保护和提高基本农田粮食产出能力、农业基础设施抗灾减灾能力、粮食发展科技支撑能力,切实提高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降低粮食生产波动,稳定地为社会提供所需粮食。王华春等所提“藏粮于地[5]”是指实施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通过保护耕地资源,保护粮食产能。杨正礼等人所提“藏粮于田[7]”是指强化农田基本生态因子的系统保护与改善,提高农田以粮食为主体的农产品可持续发展的综合生产能力,在复杂的国际形势变化中,建立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基础。唐华俊所述“藏粮于地[9]”是指藏粮于综合生产能力,即通过提高耕地质量和土地生产力,实现粮食生产稳产高产,一旦出现粮食紧缺,就可很快恢复生产能力; 而在粮食相对充足的情况下,则可以利用部分土地种植经济作物或从事其它经营,迅速增加农民收入。周小萍、陈百明等人所述“藏粮于地[10]”是指闲置于土地的那一部分粮食生产能力,即通过撂荒地恢复、复种指数提高和可调整地类转换而增加的粮食产量。
综上所述,可将“藏粮于地”概括为:“藏粮于地”是指通过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实现粮食生产稳产高产,在粮食相对充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加大粮-经(含瓜菜)轮作比例,将部分粮食生产用地用于种植经济作物,增加农民收入; 或通过粮-豆、粮-草轮作与休耕的方式,给予过度利用的耕地休养生息的机会,以提升耕地地力。在出现粮食紧缺的情况下,迅速调整耕地种植结构,快速恢复粮食生产,满足国内粮食需求。
1.3 实施“藏粮于地”战略目的
实施“藏粮于地”战略的短期目标是调减粮食种植面积,降低国内粮食库存,减轻仓储补贴负担,这也是中央财政部门最为关心的问题; 中长期目标是提升土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确保粮食稳定供给。其主要目的可概括为4个方面。
1.3.1 稳定耕地粮食产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供给
实施“藏粮于地”根本在耕地,通过强化耕地资源保护、耕地质量提升和农田基本建设,解决粮食生产能力不稳定的问题,在必要时能够根据国家需求,生产出数量充足、优质安全的粮食。
1.3.2 提升耕地产出效益,促进农民增收
实施“藏粮于地”战略,就是在粮食数量充足和粮食价格下降的情况下,让农民将部分粮田调整用于种植高效经济作物,这样即可以提升耕地产出效益,又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民扩大再生产的能力。
1.3.3 缓解粮食库存压力,减轻仓储财政负担
长期实施的藏粮于仓、以丰补歉策略为保障国内粮食安全供给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与此同时也造成巨大的库存压力和巨大的仓储财政负担,并产生大量的陈化粮,造成粮食浪费。实施“藏粮于地”战略,可有效缓解粮食库存压力,减轻仓储财政负担,减少仓储粮食浪费。
1.3.4 缓解生态压力,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实施“藏粮于地”战略,在国际市场粮食数量充足和价格低廉的情况下,可以利用国际市场,适度进口粮食,对那些地力严重透支、水土流失、地下水严重超采、土壤退化、面源污染加重区域的耕地通过粮草轮作与生态休耕等方式,给予休养生息的机会,以缓解生态压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2 实施“藏粮于地”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2.1 面临的机遇
2.1.1 粮食生产“十二连增”,粮食库存丰富,为农业结构调整优化创造了条件
在一系列有利于粮食生产政策的推动下,我国粮食产量实现了2004~2015年的“十二连增”,并于2013~2015年连续3年突破6亿t。2015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6.21亿t,人均粮食产量452kg,创历史最高纪录。在粮食连年增产的情况下,我国粮食库存数量也不断增加,如谷物库存数量从2008年的1.45亿t上升至2015年的2.49亿t[11-12],增长72.1%,年均递增8.1%; 全国谷物库存量占谷物总产量的比重从2008年的30.3%上升至2015年的43.6%; 2015年全国小麦、稻谷、玉米期末库存量分别占了2015年小麦、稻谷和玉米产量的67%、23%和51%。充足的粮食,为近两年适度调减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和扩大高效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创造了条件。
2.1.2 国际粮食价格低廉,为适度进口粮食,推动耕地“休养生息”创造了条件
近几年国际市场粮食价格走低,国内外市场粮价倒挂明显。如美国2号硬红小麦、2号软红小麦、2号黄玉米价格分别从2012年10月的373美元/t、339美元/t、320美元/t,下降至2016年8月的188美元/t、157美元/t、150美元/t[13],分别下降49.6%、53.7%、53.1%。以1: 6.67的汇率折算,2016年8月美国硬红小麦、软红小麦和黄玉米价格分别为0.32元/kg、0.26元/kg和0.25元/kg,明显低于我国价格,这为我国利用国际市场,适度进口粮食创造了有利时机。可利用现阶段国内外市场粮食供给宽裕的时机,在部分地区实行耕地轮作休耕,既有利于耕地休养生息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又有利于平衡粮食供求矛盾、稳定农民收入、减轻财政压力。
2.1.3 粮食生产稳定性提升,为改“藏粮于仓”为“藏粮于地”创造了条件
实施“藏粮于仓”的主要目的是应对粮食产量年际波动,以丰补歉。随着科技支撑能力以及耕地质量建设和农田基础设施不断强化,粮食生产波动性明显缩小。如近10年(2006~2015年)我国粮食单产与粮食总产量的波动性(相对波动系数[14])分别较前10年(1996~2005年)缩小了75%和96%。粮食生产波动性缩小,即粮食生产稳定性增强,为实施“藏粮于地”战略创造了条件。
2.2 面临的挑战
2.2.1 耕地面积可能再次大幅减少,耕地质量堪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耕地面积曾出现过2次大幅减少的现象,一是1981~1988年耕地面积以年平均44.8万hm2的幅度减少; 二是1999~2003年耕地面积以年平均125万hm2的幅度减少。通过采取一系列保护政策,2004~2015年耕地年平均减少幅度下降至16.47万hm2,尤其是2009~2015年间耕地年平均仅净减少6.67万hm2。但令人担忧的是,随着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项目和新一轮结构调整的启动,新一轮耕地面积大幅减少的局面有可能再次出现。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调整方案》,至2020年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24亿hm2,较2015年的1.35亿hm2减少0.11亿hm2,年平均减少213.33万hm2。以目前的生产水平测算,减少0.11亿hm2耕地,将损失粮食生产能力500亿kg以上。
我国耕地质量总体偏低[15],全国耕地中中低产田面积占70%。尤为突出的是耕地的环境与健康质量令人担忧,我国农田土壤受污染率已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不足5%,上升至目前的约20%[16]。另外,在本轮的永久基本农田划定过程中,个别地方存在划劣不划优现象,影响基本农田质量。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方案要求先从500万以上人口特大城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开始,按照城镇由大到小、空间由近及远、耕地质量等别和地力等级由高到低的顺序,稳步有序开展。然而,在永久基本农田划定过程中,一些地方为便于未来土地开发,不愿将城镇周边的优质耕地划入,甚至利用本次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之机,将原已划入基本农田的优质耕地调出,而将低质耕地补充划入(沈阳农业大学土地与环境学院,董秀茹,刘小庆,周群新:新要求下的永久基本农田划定问题研究-基于吉林省部分地区的调研)。
2.2.2 水资源约束日益突出,粮食生产能力提升的难度越来越大
我国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 000m3左右(2014年1 993m3,2015年2 059m3),不足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3; 平均每667m2耕地水资源量不足1 400m3,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 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很不均匀,尤其是我国13个粮食主产省区以占全国66%的耕地,仅拥有不足40%的水资源,人均水资源仅1 352m3,其中黄淮海3省区人均水资源仅346m3,明显低于国际公认的500m3/人的极度缺水标准。因缺水,全国1/2的耕地无灌溉条件,处于雨养状态; 尤其是东北4省区80%的耕地无灌溉条件; 而黄淮海地区水资源过度利用严重,在海河流域形成大面积的地下水漏斗区。
2.2.3 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农业自然灾害突出
2010~2014年间,全国农作物年平均遭受自然灾害面积0.30亿hm2,占年均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18.5%; 其中受旱灾面积0.13亿hm2,受水灾面积0.09亿hm2,分别占农作物受灾总面积的43.2%和30.2%。近5年,全国农作物年平均遭受自然灾害成灾面积0.14亿hm2,农作物自然灾害成灾率46.0%,其中旱灾成灾率46.9%,水灾成灾率47.3%。而成灾较严重的年份,旱灾成灾率高达67.8%(2010年),水灾成灾率高达57.1%(2014年)。
2.2.4 规模化生产经营与社会化服务水平低,粮食生产调控能力弱
实施“藏粮于地”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有很强的粮食生产调控能力,即一旦需要粮食,可以快速地通过调整种植结构来增加粮食生产。然而,由于我国粮食生产仍然以小规模的农户生产为主,2014年(全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资料),农民户均耕地0.38hm2,85.9%的农户经营耕地不足0.67hm2,粮食生产调控决策难以及时落实到千家万户;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化服务体系还不健全,很多地区的基层农技推广部门专业人才缺乏,农技推广、农机服务、病虫害防治等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相对滞后,难以及时根据国家需求动向为粮食生产者提供信息与技术服务,所以目前我国粮食生产调控能力还很弱。
2.2.5 国内粮食生产大萎缩和世界粮食价格危机有可能再现
我国粮食“三量齐增”和国内外粮价倒挂现象,再次诱发1998年前后那种打压国内粮食生产的呼声,如一些学者、官员和媒体提出“中国应大量进口国际粮食[17]”、“要大胆解放思想,鼓励进口,放弃‘粮食安全’的谬论[18]”、“放开价格,进行进口[19]”、“进口更多粮食,解除‘粮食安全’对农民们的束缚[20]”,等等。在此情况下,如果掌控不好,1999~2003年粮食生产大萎缩的局面有可能再次重演。历史经验一再证明,粮食生产大落容易,再起很难,一旦退出生产,诸多生产要素就会丧失,科技进步停滞,尤其是会种地的人流失,再恢复到原有的生产水平就要用相当大气力,花相当多的钱,经历相当长的过程。如1999~2003年全国粮作面积减少0.14亿hm2,2003年粮食总产量一下子回到了1990年以前的水平,而人均粮食产量回到了1982年以前的水平。通过采取综合之策,至2008年粮食总产量才达到(超过)1998年的水平,历时10年; 人均粮食产量至2011年才达到(超过)1998年水平,历时13年。
另外,近年国际粮食价格下滑为我国进口粮食,缓解耕地压力创造了条件。但2007/2008年世界粮食价格危机表明,一旦出现世界性的粮食减产,尤其是像我国、美国等谷物生产大国出现连续性粮食减产,国际粮食价格有可能成倍增长。如2007年5月至2008年3月,美国2号硬红冬小麦价格上涨了137%; 美国2号软红冬小麦价格上涨了121%; 阿根廷中质小麦价格上涨80%; 泰国白大米价格上涨了74%; 泰国碎米价格上涨了107%[21]。
3 实施“藏粮于地”路径选择
实施“藏粮于地”,关键在“地”,核心在“藏”。数量充足和高质量的耕地是基础,同时,还必须有完好的“养地”与“用地”机制。因此,应强化“护地”、“建地”、“养地”与“用地”,即走护、建、养、用“四结合”之路。
3.1 强化耕地管护,将有限耕地好好保护起来
我国耕地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坚持“十三五”规划再次强调的“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做到耕地数量基本稳定。
3.1.1 强化耕地保护与土地整治,2020年全国耕地面积不少于1.32亿hm2
《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调整方案》提出到2020年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24亿hm2,较2015年净减少0.11亿hm2,年均净减少213.33万hm2,减少幅度过大,必须加以控制。
2009年全国耕地1.354亿hm2,2015年1.35亿hm2,6年净减少40万hm2,年均净减少6.67万hm2。“十三五”期间,在加大生态建设力度的情况下,将耕地年平均减少面积控制在90万hm2,5年减少450万hm2; 通过土地整理每年新增23.33万hm2,5年新增116.67万hm2。增减相抵,5年净减少耕地333.33万hm2,年均净减少66.67万hm2,到2020年全国耕地面积1.32亿hm2。
3.1.2 调整基本农田保护目标,2020年基本农田保持1.08亿~1.10亿hm2
2008年10月发布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基于2005年的1.22亿hm2耕地和《土地管理法》要求的80%以上的基本农田划定比例,提出到2020年全国基本农田面积不少于1.04亿hm2; 而2016年6月发布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调整方案》,将2020年全国基本农田数量调整为不少于1.03亿hm2。
基于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2015年全国实有耕地面积1.35亿hm2,较基于“一调”结果多出0.13亿hm2。也就是说,我们目前的农产品产出是基于1.33亿hm2耕地,而非基于1.2亿hm2耕地。在此情况下,基本农田数量不仅未相应上调,反而下调,未来农产品供给安全有可能受到威胁。为此,应基于当前的实有耕地面积,按《土地管理法》要求的80%以上的基本农田划定比例,将全国基本农田面积上调至1.08亿~1.10亿hm2。
3.1.3 强化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监管,确保优质耕地得到永久性保护
一是将“优先划”落实到位,即加强对城镇周边、交通沿线容易被占用优质耕地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的监管,保障90%以上的耕地划入永久基本农田进行保护。二是严控基本农田调出,把好补充耕地质量关,即在永久基本农田划定过程中,规范基本农田调出行为,对于补充耕地要进行更加严格的质量把关,确保质量不下降。
3.2 强化耕地建设,力争到2020年建成0.67亿hm2高标准农田
实施“藏粮于地”,必须有完好的基础设施和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即在需要生产粮食时,不因自然灾害导致粮食减产。为此需强化耕地建设。
3.2.1 整合资源,到2020年力争建成0.67亿hm2高标准农田
整合现有农田水利建设、土地整治、农业综合开发、新增千亿斤粮食产能田间工程建设、耕地质量保护与建设等各种投资渠道,按照土地平整、土壤肥沃、集中连片、设施完善、农电配套、高产稳产、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统一标准,统一布局,统筹建设,实现2016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的到2020年确保建成0.53亿hm2、力争建成0.67亿hm2集中连片、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生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目标。
3.2.2 强化耕地用途监测与质量监控体系建设,掌握耕地质量动态
一是建立耕地用途监测监管平台,由农业部门会同国土、统计等部门定期、定点对各地耕地实际种植情况进行监测和普查,监测结果与各项耕地保护、粮食及主要农产品补贴政策相挂钩。二是建立耕地质量、土壤墒情和肥料效果三大监测网络,建立国家、省、市、县耕地质量监测体系,优化监测布局,增加监测点数,改善监测条件,建立耕地质量大数据库,定期发布耕地质量监测数据。
3.3 强化耕地养育,确保耕地基础地力稳步提升
坚持“三个统筹”,即统筹当前和长远、统筹生产和生态、统筹农艺与农机,从可持续发展出发,坚持长久性的耕地地力养育; 同时,在利用中养,不宜轻言休耕。
3.3.1 科学施肥与合理耕作,提升耕地基础地力
全面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推动施肥精准化; 推广应用缓释肥料、水溶肥料、生物肥料等高效新型肥料和水肥一体化技术,提高肥料利用效率,实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统筹农艺与农机,深耕、免耕、深松、旋耕合理搭配,增施有机肥与秸秆还田相结合,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与土壤储水保肥能力。
3.3.2 调整优化种植结构,养地补肥
在东北黑土区推广玉米-大豆轮作、青贮玉米+饲料大豆混种,在北方农牧交错带推广粮-草轮作,在中部和南方地区实施粮-经、粮-饲、粮-肥轮作/间作,提高土壤肥力; 在地力严重退化区和严重的地下水漏斗区,实行季节性休耕,降低土壤水肥消耗,达到提升地力的目的。
3.4 创新土地利用与农业发展方式,确保粮食生产能力得到提升
3.4.1 优化布局,打造基础设施完备、生产能力稳定的粮食生产功能区
加快启动建立一批粮食生产功能区,力争用3年时间完成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工作,用5年时间完成建设工作,到2020年粮食生产功能区全面建成高标准农田,到2025年实现粮食生产现代化。
3.4.2 发展种养结合循环农业,促进资源循环利用
优化种养结构,实现区域内种植-养殖合理搭配和粮-畜-肥循环产业链,以种植促养殖,以养殖增肥源,以肥促种植。建设秸秆青(黄)储商品化基质工程、秸秆与畜禽粪便沼气与沼渣沼液还田利用工程,整村或整乡推进种养结构优化、促进种养业废弃物处理循环利用。
3.4.3 提升土地规模化与生产组织化水平
完善财税、信贷保险、用地用电、项目支持等政策,加大对新型土地经营模式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力度,鼓励土地流转、土地托管、代耕代收等新型土地经营模式推广,以提升土地规模化水平; 鼓励发展粮食种植大户与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村农机服务大户与农机服务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提升农业及粮食生产组织化水平。
[1] 封志明,李香莲.耕地与粮食安全战略:藏粮于土,提高中国土地资源的综合生产能力.地理学与国土研究,2000,16(3):1~5
[2] 周健民.加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设的思考.中国科学院院刊,2004,19(1):40~44
[3] 龚子同,陈鸿昭,张甘霖,等.中国土壤资源特点与粮食安全问题.生态环境,2005,14(5):783~788
[4] 许经勇.新体制下的我国粮食安全路径.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0(4):37~41
[5] 王华春,唐任伍,赵春学.实施最严格土地管理制度的一种解释——基于中国粮食供求新趋势的分析.社会科学辑刊,2004,(3):69~73
[6] 吴栋,王力,冯梅.我国粮食价格及其调控机制.中国经济热点问题探索(下),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15次会议文集,2001,432~435
[7] 杨正礼,卫鸿.我国粮食安全的基础在于“藏粮于田”.科技导报,2004,(9):14~17
[8] 党建网.习近平在湖南代表团参加审议时的重要讲话.http://www.wenming.cn/djw/gbbd/xxhtwx/201603/t20160318_3222173.shtml,2016-03-18
[9] 唐华俊.积极实施“藏粮于地”战略.农村工作通讯,2005,(3):3
[10]周小萍,陈百明,张添丁.中国“藏粮于地”粮食生产能力评估.经济地理,2008,28(3):475~478
[11]FAO.Crop Prospects and Food Situation.No.4,December 2012.http://www.fao.org/docrep/017/al995e/al995e00.pdf
[12]FAO.Crop Prospects and Food Situation.No.2,June 2016.http://www.fao.org/3/a-i5710e.pdf
[13]FAO.Crop Prospects and Food Situation.No.3,September 2016.http://www.fao.org/3/a-i6100e.pdf
[14]陈印军,尹昌斌.红黄壤地区粮食生产波动性分析.农业技术经济,1999,(1):36~38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关于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的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政府网,http://www.moa.gov.cn/govpublic/ZZYGLS/201412/t20141217_4297895.htm,2014-12-17
[16]陈印军,方琳娜,杨俊彦.我国农田土壤污染状况及防治对策.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4,35(4):1~5
[17]马克.中国应大量进口国际粮食.搜狐财经,http://business.sohu.com/20150517/n413223401.shtml,2015-05-17
[18]陈建利.高价补贴政策被指给收购粮储官员巨大寻租空间.南方都市报,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150726/052922792248.shtml,2015-07-26
[19]楼继伟.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清华大学新闻网, http://news.tsinghua.edu.cn/publish/news/4215/2015/20150505163828267529740/20150505163828267529740_.html,2015-04-24
[20]刘文昭.今日话题:粮食更该自给还是进口?腾讯评论《今日话题》栏目,第3247期, http://view.news.qq.com/a/20150810/015773.htm,2015-08-10
[21]陈印军,王勇,卢布,等.国际粮食形势及我国粮食生产潜在危机与对策.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09,30(1):9~16
STRATEGIC AND PATH SELECTION OF "STORING GRAIN IN ARABILE LAND"*
Chen Yinjun1,Yi Xiaoyan1※,Chen Jinqiang1,Chen Zhangquan2,Han Wei2,Yang Ruizhen1
(1.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2.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100026, China)
In response to a series of problems for the long-term grain storag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put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storing grain in arable land". What is "storing grain in arable land "? What is the benefit to implement this strategy? What are the challenges? And how canimplement?In recent years,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China′s grain production, the grain production stability, and low international grain prices provided the good condi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storing grain in land" strategy. However, it was not easy due to som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or example, the arable land area may be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quality of arable land and water constraint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increase of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was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the ability to resist natural disasters was low, agricultural natural disasters were prominent, large-scal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and social service level were low, grain production control was weak, large domestic grain production shrinkage and the world food price crisis would impact the action plan. The sufficient and high-quality arable land was the key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and meanwhile the land raising and use mechanism was necessary.
storing grain in arable land; food safety; arable land protection; arable land quality;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10.7621/cjarrp.1005-9121.20161202
2016-10-19
陈印军(1960—),男,河北衡水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耕地利用与粮食安全。※通讯作者:易小燕(1979—),江苏南通人,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农村发展、土地资源管理。Email:yixiaoyan@caas.cn
*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利益博弈视角的农村宅基地整理收益分享机制研究”(71303242); “十二五”农村领域国家科技计划课题“东北平原中低产田改良技术模式集成研究”(2012BAD05B01); 农业部2016年发展计划工作十大重点问题调研项目“黄淮海节水高效型耕地利用结构优化研究”
F307.11; F320
A
1005-9121[2016]12-00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