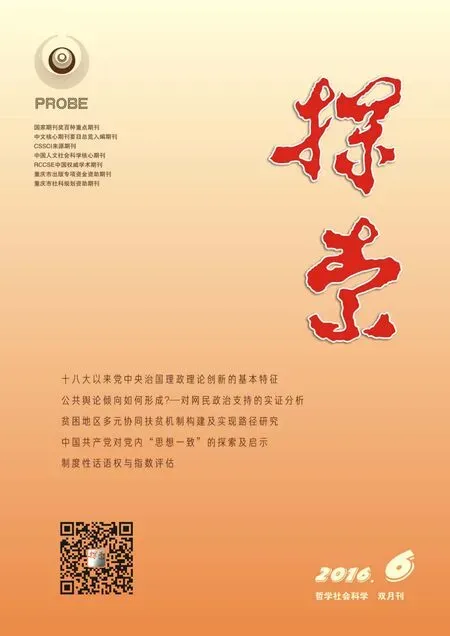探索公正理解问题的力作
——简评《政治诠释学视域中的公正问题研究》
杨海蛟
亓光博士的新著《政治诠释学视域中的公正问题研究》近期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公正作为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历来备受社会科学诸领域关注,古今中外相关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也就随之带来“如何理解公正”的新问题。该书积极回应这一重大的政治哲学问题,以独特的理论立意、广阔的学术视野、扎实的分析框架体系、崭新的研究方法、翔实的文献资料,对“理解公正”这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颇有深度和力度的探索,取得了突出成果。在此,我仅从三个方面谈谈对本书的看法。
一
众所周知,政治哲学总是以其哲学的超验性观察来透析社会政治现象,当然政治哲学也在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中不断地“与时俱进”。当代政治哲学的诠释学(解释学)转向引人注目。德沃金在《为了刺猬的正义》一书中就这样指出“在很大程度上,漫长的哲学史就是概念解释的历史。哲学家一方面在自觉而专业地解释他们所研究的概念,另一方面则帮助了被解释概念的创新。”①Ronald Dworkin.Justice for Hedgehogs,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P.157.在这一过程中,很多政治哲学家不再尝试对正义原则或者康德主义的行为规范进行评价,通过形式可理性的追诉而力图研判人类行为的特征与理性选择的客观程序,而是越来越重视理解公正问题。所谓理解公正问题,是指如果一个社会意图考量它的社会与政治原则——公正原则,那么唯一可靠的方法只有阐明这个社会的美好诉求与实践及其在历史与传统中的意义。由此便存在一个概念框架与话语解释的问题,前者是基础的、隐性的,后者是复杂的、显性的。在大家较为熟悉的理论模式中,后者占据了多数。美国政治哲学者沃尔泽就解释自己的分配正义原则,即所谓的复合平等理论。麦金太尔专门从正义与实践理性二者的历史差异性来解释两种观念的差别。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业已被证明是基于盎格鲁-美利坚传统中关于自由与平等的道德人的观念的。正是在这些观点的背后,都存在着不同公正概念框架的理解问题,进而建构了不同话语体系。它们是概念框架与话语解释的综合体。当然,在我国的公正研究中,人们依然更多地关注于社会公正、分配正义甚至生产正义的“实质内容”,或者机械地将语境论吸纳进来,但却未能真正面向理解公正的一般理念,即不论是历史解释还是社会解释,对于这些解释本身,仍然需要有一个政治哲学的解释。如果我们真正投身于这场诠释学转向中,那么我们如何对评价我们自己的社会意义,如何在平等的完备评价解释间的争论中作一个公道的第三人?假如我们无法认同某一种合理的公正解释,究竟如何进入这种解释的历史与传统、社会与实践的语境之中?倘若我们要探索自己的公正话语体系,又应该有一个怎样的“先入之见”?进而言之,诠释学转向在理解公正乃至政治哲学的发展中究竟将产生何种作用,它是充满希望的,还是已然走向没落了?
然而,只要诠释学路径在政治哲学中特别是在公正这样的本质存疑概念的解释中确立起来,那么,自然就要面对解释冲突的问题。尽管古往今来人们大多认为良政、正义、法治、和谐、稳定等是一个国家的“公器”,而社会利益、需求、实践与传统的制度建构是维系这些公器的基石,但是不同的政治主体对于如何理解这些公器、怎样评价相关制度建构的价值始终争讼不止。
正因为如此,政治哲学的诠释学转向才明确提出并奠定了解释多元主义的新传统。认同、共识不仅仅是现实政治的实践,更为主要的是对政治理论与政治哲学的挑战;不仅仅是对某个问题或价值的认同与共识,更为主要的是对于认同与共识本身的反思。对于理解公正问题而言,这种解释多元主义意味着与之相关的理论不再需要卷入对唯一的正义原则的宣誓性争论中,而是更加积极地推进这种争论。而只有更好地面对既存的争论,才谈得上推进。在我看来,公正问题的诠释学路径可能产生的最大影响就在于其核心诉求是一种诠释性沟通的观念,是一种理解的品质。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理解’这个词,即我们说某个人善于理解时所指的那种品质,其实就是从学习上的理解品质那里引申出来的。”①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克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00页。在这个意义上,假如一种公正理论可被称为是诠释性的,那么其必定会意识到其立基诸理论的片面性以及因之将必然存在的可替代解释的肯定性。而实现这一点,必然需要一种实现它的理论。
从很大程度上,直面上述问题并提出一种理论的设计,正是本书所欲实现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抱负。
二
美国学者泰勒和沃尔泽较早提出“简单调适模式”,试图以此在差异性的公正解释之间找到一种机制性的解决方法,以如实呈现所有的差异性公正解释。不过,他们对此没有进行具体的论述,而且他们也没能说明人们在社会传统与个人诸善与行为方面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怎样才是忠于歧义以及如何才能建立与之相应的制度渠道。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忽视了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歧,而这种分歧对于理解公正而言是一种系统性与基础性的偏见,而且无法避免。
在此基础上,另一位美国学者麦金太尔提出,“简单调适模式”是一种典型的自由式个人主义话语体系的产物。在这个话语体系中,真理性是调适分歧解释的基本假设。正是在这里,麦金太尔认为,只有抛弃真理性假设,才能真正实现分歧解释的调适。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在诠释学路径中的辩护性沟通才是有效的调适模式。之所以沟通本身重于真理性,根本原因在于评价某个人的公正解释就要允许对自己的解释加以修正和重构。由此,麦金太尔提出,“简单调适模式”应该被“诠释性沟通”所取代。而诠释性沟通是一种面向自我修正与重构的一种理解方式。
诠释性沟通的提出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赞同。但是,他们认为麦金太尔的认识需要进一步被丰富。特别是哈贝马斯和罗蒂提出并运用了一种非限定性交往的理想类型,并将其应用在“诠释性沟通”上,这就使其变得越发理性化与创造性了。正如哈贝马斯所言,“无论语言世界观在元历史层面上的变化被认为是存在、延异、权力或是想象,无论它是被赋予神秘的拯救内涵、审美震惊、造物主的痛苦,还是被赋予创造性的迷狂,所有这些概念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语言建构视域的创造性与一种内在世界的实践结果彻底脱离了开来,而这种内在世界的实践在语言系统中已经预先被规定了下来。”②哈贝马斯:《现代性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71页。这就意味着,解决公正理解问题不能追求一种“最终结果”,而是要将解释分歧看作是诠释性沟通自身的有机组成部分。
时至今日,诠释性沟通的理论框架依然是多元主义解释模式下分析公正等本质存疑概念的重要途径。其基本要求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假定对社会过程的自我解释性讨论是建立于一个公平性与独立性基础之上,那么只要可能,这些安排就应该影响到社会中关于共享的诸善、历史传统与政治说服的差异性理解;第二,这些代表性不可能存在之处以及任何行动要求排除一些解释之情况下我们需要同时去理解这种排他性以及变化的可能性。”③Georgia Wornke.Justice and Interpretation,Cambridge,UK:Polity Press,1992.pp.161-162.
不难发现,从知识谱系学的角度,上述理论正是本书的理论背景与逻辑起点。
三
明确了问题对象、学术使命与理论方位,在充分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批判性借鉴的基础上,本书提出了自己的论点并对其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论证。总体而言,本书的研究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资料翔实,逻辑缜密。作者阅读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从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的公正理论入手,尝试运用政治诠释学的认识路径理解公正这个重大问题,显然极具挑战性。毋庸置疑,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之所以称之为“基础性”,不仅是因为研究本身的基础性,而且是因为即便是在诠释性政治哲学中,也属于概念框架研究的基础性范围。在此基础上,才会有政治诠释学与理解公正的关系问题,才可能将历史解释与社会意义加以重估,进而才有理解公正的讨论。这种结构安排看似平淡,却并不容易掌控得当。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所言:“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之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页。
第二,立意新颖,破立兼顾。应该指出的是,从知识论路径探讨政治哲学(政治理论),对于提高理解政治价值才具有开拓性意义。人们已经习惯于在伦理学的话语框架中讨论“公正”,围绕那些分配、矫正、交换及其建构其上的主体关系的道德原则进行评价与争论,但是解释作为这些原则基础的概念却依然被称为“旁门左道”。我认为,诠释学转向破解的就是独断性的解释思维,在这里,细致研究概念解释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不仅十分恰当,而且非常重要,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客观而言,本书涉及诠释学与公正这样两个重大问题,研究难度可见一斑。将诠释学与理解公正恰如其分地“纠缠”在一起,既需要理论支撑,又需要分析技艺。政治诠释学的提出就极具勇气并十分关键。作者没有从既存的解释性政治理论模式中选择一二加以应用或重塑,而是借用伽达默尔的命题,使之重构一种框架性认识路径。并在此基础上,使得重新梳理公正概念史成为可能。特别是在公正观念与要素的阐释中,展现了政治诠释学的优势,体现了理论的深度与分析的充分性。
第三,论述严谨,观点明确。解决理解公正问题,需要立足于前人的分析模型,提出更为有效的解释框架,这就是政治诠释学必须首先建构与阐明的理由。在此基础上,只有解决了政治诠释学从理论本质、认识路径到方法工具不同层面与理解公正之间的相关性之后,“死的”政治诠释学才能进入“活的”公正解释过程中进而总揽理解公正的问题。由此,才有了从历史维度、概念维度与共识维度的理论建构,也由此证明了公正话语分析的必要性。通览本书,不难发现,这一逻辑通过作者的详细论证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在各个部分的核心观点与不同部分核心论点的衔接上,做到了丝丝入扣,很好地将一个复杂问题化解为若干简单问题,进而还维持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我一直主张政治学的青年学者特别是博士研究生应当注重基本理论研究,特别是政治哲学的研究。这对于政治学的学科、学者、学术的繁荣发展具有战略意义。毋庸置疑,作为一部青年学者的理论著作,本书还有可提高之处,例如政治诠释学的建构还颇显稚气,公正概念史、观念与要素、共识与话语分析等相关内容的起承转合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斟酌,语言仍多显晦涩。但是,瑕不掩瑜,我相信,该书的出版对我国政治学理论特别是政治哲学研究领域具有积极的意义,是超越西方政治哲学话语体系的一次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