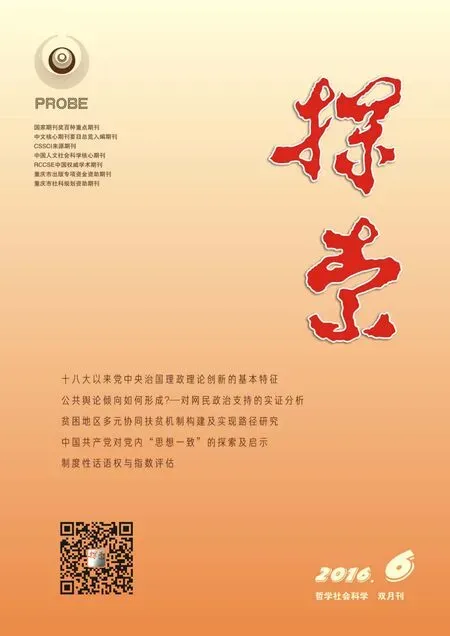波普尔的民主控制观:理论建构与思想挑战
张涵之,徐 芳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波普尔在其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提出了“民主控制理论”。波普尔的民主控制理论自提出之日起就备受质疑,这是因为它存在某些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波普尔对民主问题的认识受到了他的批判理性的影响,他在批判理性的认识方式指导下,提出了民主控制观。因此,当批判理性遭到欧克肖特、哈贝马斯等思想家的质疑时,他们对民主控制理论的指责和批判也就不可避免。尽管波普尔的民主控制理论颇有争议性,但其对思想史仍然有着独特的贡献。它继承了洛克和孟德斯鸠反对无限权力的主张,同时又突破了分权思想的局限性,在借鉴托克维尔“以社会制约权力”思想的基础上推动了民主思想由卢梭提出的“人民的统治”向民主控制阶段的发展。此外,民主控制理论对政治实践有一定的建构价值。民主控制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能为当前中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主张奠定思想基础。
波普尔对民主问题的反思与他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是互为表里的。民主控制理论恰恰是建立在批判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那么,波普尔是如何在反思理性主义的基础之上来建构民主的控制理论的?波普尔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受到了与他大致同一时期的欧克肖特、哈贝马斯的何种质疑,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是否影响了他在政治问题上的认识?波普尔在批判理性基础上提出的民主控制理论对当前中国的政治实践有着怎样的建构价值?文章将对这些问题进行逐一的考察和分析。
1 批判理性主义的前提与民主控制理论建构
批判理性主义是波普尔的认识论基础,它决定了波普尔对自然科学问题的认知方式,同时也把这种认知方式引入社会科学领域。因此,波普尔对社会、政治等问题的分析与解决离不开批判理性主义的认识方式。批判理性主义修正了自负的理性,由此波普尔对因自负的理性而造成的“人民的统治”产生了质疑,并进行了反驳。另外,波普尔以批判理性主义为前提建构了民主控制理论,以期取代民主的统治权理论。
1.1 波普尔对理性自负的质疑与对“人民的统治”的谨慎
波普尔主张民主控制理论的理由包含在他对“人民的统治”的反驳中。波普尔把“人民的统治”归于统治权理论。“人民的统治”把人民设想成具有无限理性的人,而波普尔认为人只有批判的有限理性能力。基于此,波普尔从实践操作和理论逻辑上对“人民的统治”展开了批判。他认为:
第一,现代民族国家使人民的直接统治缺乏实践可行性。人民的统治在技术操作上存在困难。相对于古希腊的城邦,现代民族国家的地理疆域大得多,人口数量迅速增长,这些客观因素致使古希腊的直接民主难以在现代民族国家充分发挥作用。即使现代社会网络技术能够克服公民参与的技术难题,但民主的效率也会大打折扣。因此,人民的自我统治和管理会因人民没有完全的理性能力而招致失败。正如波普尔所说:“在任何具体的实践的意义上,他们从未统治过他们自己。”[1]235
第二,不受约束的人民的统治存在逻辑上的悖论。波普尔认为:“一切统治权理论都是自相矛盾的。”[1]233民主的统治权理论在逻辑或理论上也不可避免存在悖论。这个悖论就是建立在多数人统治原则基础上的民主主义,容易导致暴政或者专制。在民主的统治权理论中,人民掌握了主权,获得了自由,但人民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他们无法规约自身,有时甚至可能会滥用自身的自由。仅考虑由“人民”来统治,而不考虑人民掌握政治权力以后如何控制政治权力,那么人民一旦掌握了政治权力,也可能会无限强化自己的政治权力。政治权力被无限强化、不受控制,那么离暴政就不远了。当人民无力处理公共事务时,有时可能会放弃自由而需要一位专制君主。因此,人民也可能会把政治权力拱手让给君主,从而使民主走向它的对立面。无论是暴政还是专制,从根本上讲都是理性的有限性造成的。
统治权理论在政治实践中的困境以及在逻辑上的悖论,使波普尔认识到即使是近代以来在政治发展上取得明显进步的人民掌握主权的政府形式,仍然无法避免暴政或者专制统治。人民的统治的失败归根结底是理性自负的失败,波普尔认为人民的理性不是无限的,甚至认为人民只有发现和纠正错误的能力。为此,波普尔开辟了政治学研究的新视角,把如何规约政治权力及其统治者而不是研究谁应当统治作为政治学的基本问题。
1.2 批判理性主义与民主控制理论
“人民的统治”是指人民直接掌握和行使最高的不受限制的国家权力。这种民主的统治权观念以人民道德完美、知识完善、能力完全为前提,否则怎么可能如此放心地赋予人民不受限制的统治权。然而,现实中人的理性是非常有限的,波普尔把这种有限能力称为“批判理性主义”[2]354。波普尔认为人的理性能力的有限性致使人们只能采取渐进改良的方法来解决政治问题。据此,他提出了民主控制理论。这种理论不再把“人民”置于“统治者”的地位,而是把人民作为统治者的地位降低为“控制者”。也就是说,把人民的权力分为理论层面的“主权”与实践层面的“治权”。在主权上民意仍然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在治权方面人民只是控制者,对政治权力及其统治者进行民主的控制。
民主的控制理论在制度设计上仍然采取选举制度和代议制,波普尔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看到了现有的民主制度可以确保政治权力以一种不流血的方式进行更替,同时可以“对人民所选举的官员的所作所为进行评判”[3]144。否则,一旦政府出错就通过暴力推翻现行政府,然后引进一套新的民主理论体系的推倒重来式的做法非常不利于政治稳定,不但不能促进民主国家的发展,反而会造成民主发展的停滞。此外,这种制度是一种对政治权力的民主控制方式,如果没有这种控制方式,“就没有什么现实的理由来解释政府为什么不会动用它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来达到不同于保障公民自由的目的”[4]127。因此,依据莱斯诺夫的理解,波普尔的民主观“不是人民的统治,而是一种限制权力的政府形式”[5]266。
波普尔基于批判理性而非道德理由,采取一种在试错过程中不断摸索和学习的方法,从而实现对政府的行为进行批判和讨论。因此可以说,波普尔的政治主张是建立在他的批判理性基础之上的。
2 波普尔民主控制理论面临的思想挑战
波普尔虽然以科学哲学家著称,但他却因《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而被看作政治哲学家闻名的。他与欧克肖特、哈贝马斯一样,他所关注的并不是理性主义本身,而是理性对政治的影响。他们都看到了现代政治的弊端需要深入到理性的哲学园地来分析。但他们在对理性进行具体分析时(理性如何影响政治,如何通过理性的完善来克服现代政治弊端)却出现了很大的差异。波普尔的民主控制理论因此面临着严峻的思想挑战。
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与他的自然科学的“证伪原则”是一致的,共同构成了他的哲学认识论基础。波普尔认为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不能穷尽所有的事实,只有发现错误和发现问题的能力,但“我们能够从我们的错误中学到东西”[6]266。波普尔把这种对自然科学的认识应用到了社会科学领域。因此,理解他的民主控制理论离不开对其认识论的把握。欧克肖特、哈贝马斯正是抓住了这一点,从理性主义入手,对波普尔的政治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欧克肖特可以说是一个极其自负的人,他的自负就体现在对理性主义的激烈批判上。欧克肖特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主要反映在他的《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一书中,该书也是使欧克肖特名声大噪的直接因素。这一著作之所以奠定了欧克肖特在政治哲学上的空前地位,主要是因为他对理性主义的批判直接对准了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欧克肖特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反对波普尔把“经验”作为批判理性的立足点。波普尔继承了休谟对归纳主义的批判,但他仍然没有摆脱经验的影子。波普尔虽然认为理论“在经验上是绝对不可证实的”[7]17,但却可以通过经验的证伪来加以验证。在波普尔看来,理性“不存在归纳和证明,只有批判和消除”[8]45,而理性是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这也就意味着,知识的获取是通过对事实的验证以及对违背验证的错误的纠正而实现。由此看来,波普尔认为知识来源于事实也就不难理解了。波普尔的这种理性在政治上让他采取了改良主义,通过政治错误的消除来推进政治的发展。波普尔改良主义的渐进政治工程宗旨在于避免历史规律对政治的影响。然而,在欧克肖特看来,波普尔的政治主张并没有跳出政治规律的拘囿。欧克肖特进一步认为,批判理性并不能让政治规避政治计划所带来的意识形态统治。欧克肖特把波普尔的批判理性等同于近代的技术理性。技术理性根据经验总结出规律,追求确定性,把“政治同化为工程”[9]5。这实际上仍然是使政治按照一定的规律或计划发展。然而政治是充满偶然性因素的,没有非常明显的发展规律,也不能使它按照人为的计划发展。再者政治规律或政治计划实质上是统治者的意志的表现。也就是说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仍然无法避免意识形态的统治。在这一意义上,欧克肖特坚持了波普尔政治无规律的观点,但对其论证却持否定态度。为了摆脱波普尔新实证主义的唯实论对政治的意识形态统治,作为唯心主义者,欧克肖特最终又回到了传统哲学上,认为以理性做出判断时除了个人理智,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影响。由此,欧克肖特完成了对波普尔的批判。
除了欧克肖特,哈贝马斯也是一位对波普尔进行系统批判的集大成者。哈贝马斯不但批判了波普尔的理性观,同时在批判的基础上完成了理性主义的重建,这一点是欧克肖特所不及的。欧克肖特的阐述虽然文辞优美,远胜于文风晦涩难懂的哈贝马斯,但欧克肖特没有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因此,欧克肖特的思想确切地说仅限于批判,正如莱斯诺夫所评价的那样,还是哈贝马斯的思想更具建构力,因为他在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重要而有意义的理论体系”[5]349。
波普尔却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是相通的,是可以互相借鉴的。波普尔的这种认识,注定了他要把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上。而哈贝马斯与欧克肖特一样,看到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运用到政治研究上是有危害的。在反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相通这一方面,欧克肖特与哈贝马斯是一致的。但与欧克肖特的反驳路径不同的是,哈贝马斯认为,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应用于自然科学是可以的,而且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促进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但实证主义应用于社会科学是行不通的,它不但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反而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因为这种研究方法力求摆脱价值判断,这形成了一种由技术和科学支配的统治合理性——目的理性,这种理性对社会“行使控制和监督”[10]39。基于此,在政治上技术与科学通过目的理性成了为统治者提供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对于这一点,哈贝马斯在马尔库塞对韦伯的批判中予以承认,技术与科学被实证主义者当作“一种‘意识形态’来利用”[5]353。这种意识形态充满了政治目的性,往往会把统治者的决定而不是民意当成政治抉择,与专制一样背离了民主。目的理性使人们从“神话了的权力”[11]313中得以解脱,但又陷入了技术的统治。人类社会的政治形态和政治生存状态从实质而言仍然没有改变。
此外,在哈贝马斯看来,波普尔的批判理性只能“消除民众中的谬误”[12]145,却不能增加新的知识。人类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总是会遇到各种新问题。当新的问题出现而既有的知识又无法解决时,旨在消除错误的批判理性并不能创造一种新的知识来为新问题提供一种有效的解决途径。为此,哈贝马斯在对波普尔批判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新的理性——“交往理性”。不同于波普尔的批判理性纯粹地对经验的依赖,哈贝马斯对交往理性的建构是建立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综合运用的基础之上的。这种理性从方法上突破了批判理性的局限,推动了理性的发展。它不仅能够发现问题、识别错误,还能为问题的解决提供对策。这样一种理性通过话语伦理来实现人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并以此达成共识。人们在沟通的基础上,能够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错误,并由此达成共识,实现合理的交往。因此,交往理性在哈贝马斯的设想中,能够规避冲突和风险,克服权力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哈贝马斯的这种理性建构,从政治的发展历程来看,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为一种新的民主形态——审议民主奠定了哲学基础。审议民主正是一种与交往理性相似的,建立在话语伦理基础上的,通过共识的达成来解决政治问题的民主形式。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欧克肖特与哈贝马斯都看到了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上的危害,尤其是对政治学的危害。所不同的是,哈贝马斯建构了新的理性形态,为推动新的政治形态的发展作了贡献。
3 民主控制理论对“权力制约”实践的价值指向
尽管欧克肖特、哈贝马斯对波普尔的批判具有一定道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以及民主控制理论对政治没有建设性意义。他对控制权力的必要性的论证至今仍然有现实意义,权力控制为防止权力的腐败奠定了思想基础。当前中国的政治体系强调对权力加强制约和监督,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13]。这种政治实践确切地表明政治学的基本问题已经转变为如何规约政治权力,而对权力进行制度规约可以在波普尔的民主控制理论里得到充分的论证和支持。波普尔的民主控制理论可以说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哲学思维根源之一。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实际上是对无限权力的制约,这种权力控制在思想史上其实渊源已久。对于如何制约权力,近代以来的思想家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洛克、孟德斯鸠提出了“分权”理论。洛克认为政府的权力不应当是无限的,为此把政府权力划分为立法权、司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在此基础上,孟德斯鸠进一步把政治权力划分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并最终确立了“分权与制衡”的思想。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防止政治权力的膨胀。作为民主的捍卫者,波普尔的民主控制理论着重强调的是人民对权力的控制。从理论意图来看,洛克、孟德斯鸠的“分权”与波普尔的“民主控制”都是为了抵御专制,但抵御专制的具体形态以及路径不同。如果说洛克、孟德斯鸠提出“分权”是为了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奠定基础。那么波普尔的“民主控制”所抵御的是为了防止自由民主制向极权主义专制的转变。另外,洛克、孟德斯鸠反对专制的路径是“分权”,实则是通过政治权力内部结构的调整来削弱权力。波普尔则更多强调人民对政治权力的外部“控制”。
至于对政治权力的控制,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的民主状况时已经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托克维尔依据自己的考察指出,即使是在民主政府体制下,如果人民的权力不受控制,也将会给立法、行政、司法等带来灾难。因此,他认为无限权威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不管任何人,都无力行使无限权威”[14]318。正如米歇尔斯所说,在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下,“民主制与君主制的区别已变得毫无意义——这种区别成为形式上的而非实质上的”[15]33。托克维尔不但看到了无限权威的危害,同时也认识到了在美国的社会中,已经出现了对抗民主无限权威的力量。通过考察,托克维尔发现这个力量来自于社会,社会主要通过法律来控制权力,例如陪审团等。相对于洛克、孟德斯鸠的“以权力制约权力”,托克维尔的“以社会制约权力”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
到了20世纪,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和民主理论家达尔都相继注意到了托克维尔为人类留下的思想遗产——“以社会制约权力”。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视角,采取不同的方法将这种思想发扬光大。波普尔从宏观的哲学层面论证了民主控制的合理性;达尔则从技术操作上重点解决公民如何控制权力的问题,如提出民主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公民“对议程的最终控制”[16]33。相对于达尔,波普尔的民主控制理论对托尔维尔“社会制约权力”的思想更具发展意义。波普尔果断地搁置了“谁应当统治”的争论,指出民主的本质在于对“权力及其统治者”进行制度控制。波普尔不再把人民当成政治权力的“主人”,而是政治权力的“控制者”,这在技术操作上与“人民的统治”相比,具有可行性。同时,人民对政治权力的控制是有效防止和抵御极权主义形式的“伪民主”的一种有力举措。凭借人民对政治权力的控制,才能够坚实地捍卫自由民主制,才能防止民主不被别有用心的利益集团利用。与托克维尔的民主思想没能像洛克、孟德斯鸠的分权思想一样引起广泛的关注一样,波普尔的民主控制理论也没有引起较大的反响。目前,国内外关于波普尔民主观的研究,与对他的科学哲学思想的研究相比还是较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波普尔对民主理论的进步与发展没有任何贡献,更不能说明波普尔关于民主问题的思考对政治哲学的发展不重要。
民主控制理论系统地论证了民主制的合法性。安德烈亚斯·皮克错误地认为,波普尔提出的民主面临着秩序与合法性的问题[17]。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波普尔的民主并不是对现行民主制度的否定,而是对其进行完善。波普尔回答了人民通过选举和代议制对政治权力进行制度控制的原因以及意义,这实际上是对密尔“代议制”的必要性与合法性的论证。密尔的《代议制政府》并没有确切回答“代议制”为什么是民主的最好实践形式这一问题,只是交代了代议制政府的各种问题及其可能的解决办法。因此,可以说波普尔第一次系统地论证了代议制民主的合法性。
民主控制理论降低了古典理想民主的高度,使民主在现代民族国家也能够实施。波普尔的民主思想使民主的观念由“人民的统治”“多数的统治”转向了“人民的控制”。对于这一政治哲学思想,马克·诺图洛指出波普尔的贡献在于理解了民主而不是把民主理想化。这主要是因为“人民的控制”在实践中更易于操作。迈克尔·莱斯诺夫指出,相对于当今流行的“参与民主”,波普尔关于民主的定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接近于精英主义民主,但这“不一定是更坏的”[18]。因为这种民主减轻了人民的参与困难和负担。同时,民主控制理论所倡导的“民主纠错机制”可以防范人民的主权落入专制的圈套,确保人民在主权上的地位。
波普尔的民主控制理论对当下民主政治的影响极为深远。在民主理论体系里,“人民的统治”思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占据着主流地位,但波普尔指出民主的思维不应当仅仅停留在卢梭的思想里,而应该看到卢梭之后的问题。波普尔的民主控制思维可以说一针见血地刺破了伪民主的幌子,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4 结论
经典的民主统治权理论解决了推翻封建专制以后的权力归属问题,论证了“人民主权”的合理性。但在治权方面,至于人民如何正确行使权力,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波普尔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提出了民主的控制权理论,认为民主不再仅仅只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民的统治”,而是“人民的控制”,成功地解决了“人民的统治”在政治实践中技术操作上的难题。“民主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一直是人类不懈的追求。”[19]波普尔提出的这一治权意义上的民主,突破了具有理想主义浪漫色彩的古典民主的局限。使我们意识到无论政治权力归属于谁,哪怕是人民,也要受到监督和控制。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人民的权力不被别有用心的人操控,防止民主滑向新时代的极权主义。
波普尔的民主控制理论为政治实践中的权力运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哲学思维。波普尔的民主控制理论尽管是“提炼”于特定现实情境的成果,但他对政治学基本问题的认识对当前中国面临的许多实际问题是可以借鉴的,比如如何规范政治权力的运行。从我国的腐败形势来看,一些层面的政治权力膨胀已经威胁到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加大反腐力度,对政治权力进行控制已经刻不容缓。党的十八大以来所推动的一系列反腐工程,为我国民主政治的良性发展作了突出贡献。而波普尔提出的民主控制理论正符合当前我国这一政治实践的需要,我们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成分,来为实际问题的解决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因此,可以说波普尔的民主控制理论为当前中国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奠定了合法性基础,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重要哲学之维。
参考文献:
[1]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M].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M].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马克·诺图洛.波普[M].宫睿,译.北京:中华书局,2014.
[4]POPPER K.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M].London:Routledge,1991.
[5]迈克尔·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M].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6]波普尔.客观的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M].舒炜光,等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
[7]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M].渣汝强,邱仁宗,万木春,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
[8]波普尔.实在论与科学的目标[M].刘国柱,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
[9]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M].张汝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10]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11]HABERMAS J.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M].London:Shapiro,Heinemann,1972.
[12]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3]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06.
[14]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15]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M].任军峰,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16]达尔.论民主[M].李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7]PICKEL A.Never Ask Who Should Rule:Karl Popper and Political Theory[J].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89(1):83-106.
[18]LESSONOFF M.Review Article: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J].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80(1):99-120.
[19]吴大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内在特质探索[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5(9):6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