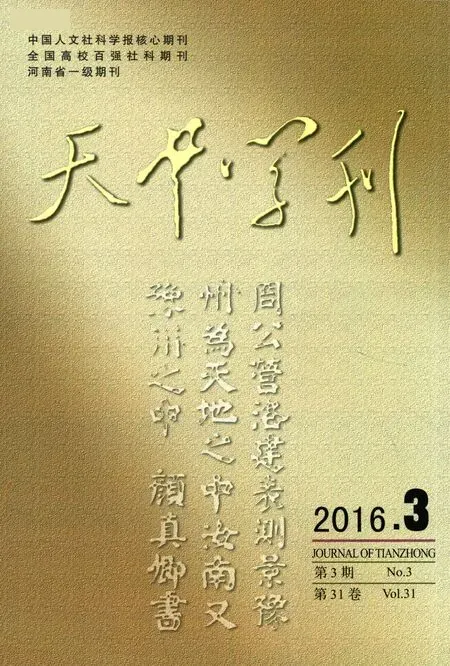《金瓶梅》经典化历程中的两大坐标轴
李建武
(广东培正学院 人文系,广东 广州 510830)
《金瓶梅》经典化历程中的两大坐标轴
李建武
(广东培正学院 人文系,广东 广州 510830)
《金瓶梅》自诞生以来有两次经典化历程:第一次是从明末到民国期间;第二次是自1949年以来。其经典化历程中形成了两大坐标轴:一是张竹坡与鲁迅共同建构的第一个坐标轴;二是袁行霈总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及其第二版。
《金瓶梅》;经典化;坐标轴;张竹坡;鲁迅;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中国大陆学术界对“经典”的关注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2005年出版了美国著名学者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1],然而时至今日,对“中国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也并未完全铺开,仍有相当领域可以开掘,如古典文学研究的权威期刊《文学遗产》近一年来围绕文学经典的问题还发表过论文[2]。就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奇书”经典化历程的坐标轴探讨而言,更是如此,虽已有笔者对《三国演义》[3]《水浒传》[4]《西游记》[5]的相关论述,但尚缺乏对《金瓶梅》的探讨。笔者以为,《金瓶梅》自诞生至今有两次经典化历程:第一次是从明末到民国期间;第二次是自1949年以来。其经典化历程中形成了两大坐标轴:一是张竹坡与鲁迅共同建构的第一个坐标轴;二是袁行霈总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及其第二版。以下就是笔者对《金瓶梅》经典化历程中的坐标轴所做探索性的论述。
一、第一大坐标轴:张竹坡与鲁迅
《金瓶梅》在经典化历程中历经坎坷。《金瓶梅》在传播之初,借助于书商的推介,被认为有所寄托。如万历本《金瓶梅词话》和崇祯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都刊载了明代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其言:“然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这是对《金瓶梅》的积极肯定,因为它已点出《金瓶梅》积极的社会意义:“劝诫”[6]178。这等于用“惩戒说”引导读者阅读它。
万历本和崇祯本对《金瓶梅》的看法基本一致,都把它看作一部非常有意义的小说,而没有把它视为一部淫书。但这些评论影响不大,因为很多人认为其中的缘由是书商出于销售的目的而故意掩饰小说宣泄淫秽的重弊。
与书商观点相呼应的是当时文学家和文学评论家的识见。明袁宏道在《觞政·十之掌故》中认为《金瓶梅》可与《庄子》《史记》《汉书》《离骚》以及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作品并驾齐驱[6]178。这是对《金瓶梅》整体成就的高度评价。明代谢肇淛在《金瓶梅跋》中则高度赞扬《金瓶梅》惟妙惟肖的人物与世情刻画的成就,说若不是因为内容淫秽的缘故,《金瓶梅》艺术成就则可以直追《水浒传》了[6]179。明末还有冯梦龙以“四大奇书”之一称赞《金瓶梅》[7]899,但《金瓶梅》在那时也并没有获得小说经典的地位。因为当时更多的人都是把小说当作茶余饭后的消遣品,小说的地位只是稍稍比“小道”“残丛小语”高一点点。
真正系统评价《金瓶梅》的是张竹坡。他从大处着眼高度评价了《金瓶梅》的成就。他说:“《金瓶》以‘冷热’二字开讲,抑孰不知此二字为一部之金钥乎?”他真正看到了《金瓶梅》写作的“内道”(深层用意)。先热后冷,这的确是潜藏于作品中的叙事暗道。他还解读了为何作品“将玉皇庙始而永福寺结者”的原因,看出了作品“以‘悌’字起,‘孝’字结”的艺术结构[8]。张竹坡也以独到的见识和眼光看出《金瓶梅》中李瓶儿、庞春梅等人的深层寓意。他说:“然则何以有瓶、梅哉?瓶因庆生也。盖云贪欲嗜恶,百骸枯尽,瓶之罄矣。特特撰出瓶儿,直令千古风流人同声一哭。”点出了李瓶儿与西门庆之间的命名关系。他又以“故瓶儿好倒插花”揭示作品情节与人物姓名命名的关系,揭示为何李瓶儿主动献爱给西门庆,并给西门庆带来价值几千两银子财产的深层原因。至于庞春梅,他说:“至于梅,又因瓶而生。何则?瓶里梅花,春光无几。则瓶罄喻骨髓暗枯,瓶梅又喻衰朽在即。”[8]道出庞春梅的姓名中暗示着好景不长的人物命运。
他还揭示了潘金莲与陈敬济之间的姓名对两人命运影响的关系:“然则金莲,岂尽无寓意哉?莲与芰,类也;陈,旧也,败也;敬、茎同音。败茎芰荷,言莲之下场头。故金莲以敬济而败。”此外,他还揭示了其他人物的姓名与其命运的内在隐喻:应伯爵解读为“应白嚼”,祝实念解读为“住十年”,常峙节解读为“常时借”,吴典恩解读为“无点恩”,韩道国解读为“寒捣鬼”等。他对《金瓶梅》细致入微的解读很多是正确的,分析也很精辟透彻。
总之,《金瓶梅》的意义价值、深层的叙事道理只有靠张竹坡这样的慧眼才能发掘并阐发出来。张竹坡的见解高人一筹,代表了明清两代对《金瓶梅》最深入和最细致的评价,故他是《金瓶梅》经典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本来,有张竹坡这样富有鉴赏能力的读者能读懂《金瓶梅》并推介它,有利于《金瓶梅》尽快实现经典化。但可惜的是,张竹坡英年早逝,年仅29岁就去世了,没能身体力行地为《金瓶梅》“非淫书说”奔走呐喊,也没有培养众多弟子来光大其敏锐的思想见解。加之《金瓶梅》确有性描写而引来争议,故而关于它的“非淫书说”被极大地“遮蔽”了。于是在清代它遭遇了一波又一波的禁毁,这使它在经典化之路上大受挫折。
王利器辑录的《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显示:虽然清代朝廷明令将《金瓶梅》写入禁毁书目里面的次数并不多,仅为3次,但清代,如在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同治等年间多次明令“禁止小说淫词”。那些“禁止淫词小说”的告示虽没有直接点《金瓶梅》的名,但实际上,《金瓶梅》每次都在禁毁之列,因为《金瓶梅》包含有2万来字的“秽笔”,而且明清时期书商出的《金瓶梅》一般都是全本、未删节版,不像我们当今出很多删节版,带有“秽笔”的《金瓶梅》自然会被官方视为洪水猛兽,列入“淫书”之列加以禁毁。在这样严厉禁毁的清代,《金瓶梅》自然遑论被社会尊奉为“文学经典”。譬如:代表官方态度的《四库全书》就未收录《金瓶梅》。可见,清代乾隆年间,处于士大夫阶层的四库馆臣是鄙视《金瓶梅》的。
当然,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官方的禁毁并不能代表《金瓶梅》真正被毁灭了。实际上,在民间,富商和高官家里仍传播着《金瓶梅》。他们把它当作文物或宝物一直收藏着,或者自娱自乐,或者等到政策宽松时择机抛售,大赚一把。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金瓶梅》也是如此。官方对它的禁毁也激励着相当一部分人偷窥《金瓶梅》,诱惑着更多的人对它关注。故《金瓶梅》虽在官方的禁毁政策的高压下,但并未遭到禁绝。
而《金瓶梅》经典化历程中的重要阶段是清末民初时期。这一时期首先略值得一提的是光绪五年至八年(1879—1882年)文龙的6万余字《评点金瓶梅》。其在第1回评就说:“《金瓶梅》淫书也,亦戒淫书也……究其根源,实戒淫书也。”[6]580其第100回评又说:“或谓《金瓶梅》淫书也,非也。淫者见之谓之淫,不淫者不谓之淫,但睹一群鸟兽孳尾而已。”[6]656但他的见解未超越张竹坡,也未超越20世纪初的文人学者,因而清末民初很少有人提及他的评点。即文龙的评点对后代的影响并不大。
清末民初也有一批文人学者从社会功效或艺术的角度去衡量《金瓶梅》的好坏。如王钟麟高度赞扬《金瓶梅》:“读小说数十百种……其好而能至者,厥惟施耐庵、王弇州(所说王弇州小说是指《金瓶梅》)、曹雪芹三氏所著之小说。”[9]433梦生《小说丛话》说:“中国小说最佳者,曰《金瓶梅》,曰《水浒传》,曰《红楼梦》,三部皆用白话体,皆不易读……我欲评此三书,第一当先评《金瓶梅》。”[6]682解弢在《小说话》中也高度评价《金瓶梅》:“做小说须独创一格,不落他人之窠臼,方为上乘。若《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儒林外史》、《水浒传》,皆能独出机轴者。”[10]558
当然,晚清和民国初期也有一些名家否定《金瓶梅》。如:冥飞《古今小说评林》从艺术上认为《金瓶梅》“其书之事实文法以及布局,绝无可取”[9]440;谢无量《明清小说论》则评之曰:“古来房中书的变相。那种单纯无意识的兽欲的描写,可见作者胸襟,煞是卑俗,说不上有何等文学的意义……”[11]持否定态度最有代表性的是胡适,他在《答钱玄同书》的信中说:“我以为……今日一面正宜力排《金瓶梅》一类之书,一面积极译著高尚的言情之作。五十年后,或稍有转移风气之希望。此种书即以文学的眼光观之,亦殊无价值。何则?文学之一要素,在于‘美感’。请问先生读《金瓶梅》,作何美感?”12]573显然,“殊无价值”一语可看出胡适对《金瓶梅》极低的评价。
然而,这时期高度评价《金瓶梅》的观点却略占上风,对后来研究者的影响很大,代表文人是鲁迅、郑振铎、钱玄同、陈独秀等。他们接过张竹坡的阐释棒,给予了《金瓶梅》极高的评价。钱玄同称其“刻画描摹,形容尽致”[12]579,“若抛弃一切世俗见解,专用文学的眼光去观察,则《金瓶梅》之位置,固亦在第一流也”[12]582。陈独秀虽承认《金瓶梅》“描写淫态”,但也高度评价它:“此书描写旧社会,真如禹鼎铸奸,无微不至。《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而文章清健自然远不及也。”[13]166郑振铎则高度评价:“《金瓶梅》的出现,可谓中国小说的发展的极峰。在文学的成就上说来,《金瓶梅》实较《水浒传》、《西游记》、《封神传》尤为伟大……只有《金瓶梅》却彻头彻尾是一部近代期的产品。不论其思想,其事实,以及描写方法,全都是近代的……是一部可诧异的伟大写实小说……在我们的小说界中,也许仅有一部而已。”[14]919
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略》[15]影响了后来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各种小说的定位。这部书第十九编、第十四编、第十五编、第十七编分别以《金瓶梅》《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为介绍核心。这种排列和介绍的分量说明鲁迅把明代四大奇书都视为小说经典。而这种排列真正奠定了《金瓶梅》的文学经典地位。不仅如此,鲁迅还勾画出《金瓶梅》在世情小说方面的突出成就:“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15]125-126“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是对《金瓶梅》艺术成就的最高评价。由于民国期间编写《中国小说史》或《中国文学史》的学者都要参考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自然,鲁迅的这一评价可以说奠定了《金瓶梅》作为文学经典的崇高地位。
所以,笔者认为,鲁迅是20世纪上半叶《金瓶梅》经典化史上的一大坐标轴,他与张竹坡一起共同撑起《金瓶梅》经典化史上的第一大坐标轴。其涵盖的时期为明末至民国期间。
二、第二大坐标轴: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及其第二版
鲁迅之后,《金瓶梅》的被经典化还应归功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各家《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这就涉及“入典率”和“入史率”的问题。的确,从外部因素判定《金瓶梅》是不是文学经典,除了考察它在民间的传播与接受情况,也可直接依据它在文学史、小说史教材中的“入典率”和“入史率”。
由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四册“第七编明代文学”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分别列为第一章、第二章、第六章,而只将《金瓶梅》列入第七章第三节,可以看出编著者并没有把《金瓶梅》当作经典文学[16]。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第二十七章的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分别述介《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17]。而且,它述介《儒林外史》《红楼梦》也是各为一节的分量。这显见,《金瓶梅》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很有地位。北大中文系的《中国小说史稿》“第五编第九章”只列了一节介绍《金瓶梅》。而其述介《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是各列一章的分量。这说明它只把《金瓶梅》当作一部重要小说,而没有视作经典小说[18]。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史教材是由袁行霈总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它的编排体例表达了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以来学术界对文学经典的公认情况。其初版的第四卷[19]与第二版的第四卷[20]是由黄霖主编的,都是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各列一章。这种编排标志着《金瓶梅》被正式而完整地确立为文学经典,其经典地位被学术界充分认可,也标志着其经典化历程很好地完成了。章培恒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下册[21]及其《中国文学史新著》下册[22]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与《红楼梦》均用一节述介,以此可看出编著者把《金瓶梅》当作了经典小说。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第四册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分别列为第三章、第四章、第八章、第九章[23],这种体例编排显示了这四部奇书同等的地位和分量。马积高等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下册[24]及其2009年修订本下册[25]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列为第二章、第三章、第六章,《金瓶梅》则只列了一节,写入第七章,这说明著者没有视《金瓶梅》为小说中的经典之作。
在此补述一下毛泽东对《金瓶梅》经典化的贡献问题。有资料显示毛泽东多次跟高级将领和省级干部谈到《金瓶梅》[26],如他说过:“《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27]他还说过:“《金瓶梅》是《红楼梦》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暴露了封建政治……”[28]1417后来文化部、中宣部同出版部门协商后,以“文学古籍刊行社”名义,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集资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重新影印了2000部。这些《金瓶梅》发行对象是各省省委书记、副书记以及同一级别的各部正副部长。所有购书者均登记在册,并且编了号[29]。但这并未真正推动《金瓶梅》阅读大众化,因为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陆,一般大众不知道有《金瓶梅》一书。只有到了1978年后,《金瓶梅》以删节版的形式获得普遍传播后,它才真正实现了阅读大众化。因而,毛泽东基本谈不上有推广《金瓶梅》的贡献,自然,笔者也就不认为毛泽东是《金瓶梅》实现经典化的重要人物。
通览《金瓶梅》的经典化历程,不难发现,虽然张竹坡对《金瓶梅》成为经典小说做了历史性的、奠基性的贡献,甚至现在的很多观点都还没有超越他的见解,但是《金瓶梅》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经典”的荣称,还得靠20世纪文学界的评论家,譬如:郑振铎[30]、李希凡[31]、任访秋[32]、徐朔方[33]、王汝梅[34]、朱星[35]、魏子云[36]、黄霖[37]、李时人[38]、石昌渝[39]等。因为只有20世纪的文学史和小说史教材,才是奠定其经典地位的关键所在;因为小说经典地位的真正确立开始于20世纪前期;因为判定小说是否经典,依据的标准是社会上众多读者的普遍共识或教材、教科书等。故张竹坡时代并未实现《金瓶梅》的经典地位,但民国的鲁迅通过《中国小说史略》基本建构起《金瓶梅》的经典地位;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只能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合在一起,共同算作《金瓶梅》第一次实现与完成经典化。而袁行霈总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才真正在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背景下,对文学经典的座次进行了一次较公正的排定,宣告了哪些文学作品可以跻身经典之中,哪些被排挤出局。故笔者认为,张竹坡与鲁迅(尤以后者为主)、袁行霈总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及其第二版构成了《金瓶梅》经典化历程的两大支点,支撑了各个时期对《金瓶梅》众多评价;同时这两项又是《金瓶梅》经典化史的两大坐标轴。而在这两大坐标轴之间,充满着各种非议、批判和禁毁。总之,《金瓶梅》成为“文学经典”,历经了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
[1]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M].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2] 詹福瑞.试论中国文学经典的累积性特征[J].文学遗产,2015(1).
[3] 李建武.《三国演义》经典化过程的曲折性[c]//郑铁生,胡世厚.第二十一届《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
[4] 李建武,孟华.《水浒传》20世纪经典化过程的阶段分期[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2(5).
[5] 李建武,辛雅静.论《西游记》400年经典化过程中的坐标轴[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3(1).
[6] 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G].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7] 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8] [清]张竹坡.张道深评金瓶梅[M].济南:齐鲁书社,1991.
[9] 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G].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10] 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G].济南:齐鲁书社,1990.
[11] 谢无量.明清小说论[J].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第17卷号外: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28.
[12] 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M].易竹贤,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
[13] 陈独秀.陈独秀书信集[M].水如,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14]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1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6]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四[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17]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下[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18] 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中国小说史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19]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4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0]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版):4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1]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22]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23] 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4] 马积高,黄钧.中国古代文学史:下[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
[25] 马积高,黄钧.中国古代文学史: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6] 刘继兴.毛泽东五评《金瓶梅》[J].记者观察,2013(10).
[27] 马广志.毛泽东四评《金瓶梅》[J].党史文苑,2005(5).
[28] 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29] 张同胜.毛泽东评《金瓶梅》的问题视域[J].菏泽学院学报,2009(3).
[30] 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M]//郑振铎文集: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31] 李希凡.《水浒》和《金瓶梅》在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的地位[N].文艺报,1957(38).
[32] 任访秋.略论《金瓶梅》中人物形象及其艺术成就[J].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62(2).
[33] 徐朔方.金瓶梅的成书以及对它的评价[M]//金瓶梅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34] 侯忠义,王汝梅.金瓶梅资料汇编[G].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35] 朱星.金瓶梅考证[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
[36] 魏子云.金瓶梅散论[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
[37] 黄霖.金瓶梅大辞典[Z].成都:巴蜀书社,1991.
[38] 李时人.金瓶梅新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39] 石昌渝.金瓶梅鉴赏辞典[Z].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 刘小兵〕
coordinate Axes in the conventionality of The Golden Lotus
LI Jian-wu
(Guangdong Peizheng college, Guangzhou 510830, chin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nventionality of The Golden Lotus, this paper divides the historical course into two phases:Generally the first phase is from late Ming Dynasty to Republic of china; the second since 1949. Furthermor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a new idea that there is a coordinate axis in each phase, which directs toward some central “person” or “works” respectively as followings: Zhang Zhupo and Lu Xun in the first phase, and the fourth volume of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iefly edited by Yuan Xingpei and its second version in the second phase.
The Golden Lotus; conventionality; coordinate axis; Zhang Zhupo; Lu Xun; Yuan Xingpei;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207.41
A
1006-5261(2016)03-0087-05
2015-06-27
2015年广东高校省级重点平台和重大科研项目(2015WTScX112);广东培正学院青年教师创新科研基金项目(15pzxyqn011)
李建武(1975—),男,湖南常德人,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