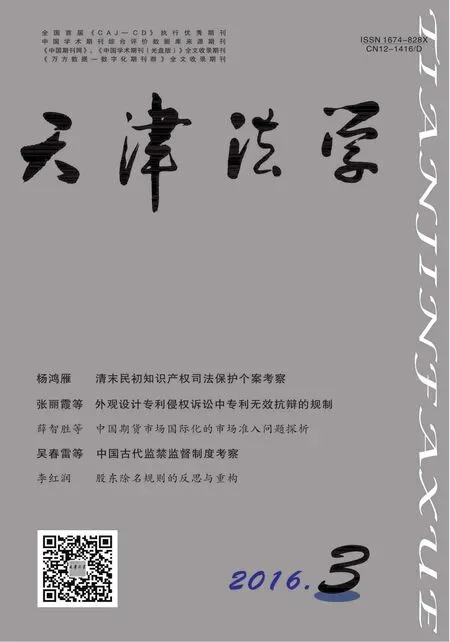清末民初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个案考察
杨鸿雁
(天津工业大学 人文与法学院,天津300387)
清末民初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个案考察
杨鸿雁
(天津工业大学 人文与法学院,天津300387)
受西方法制影响,中国于清末民初正式开始了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此间知识产权立法主要与著作权和商标权有关,这正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基础。清末著作权审判个案表明,司法对著作权的保护有限地突破了法律规定;民初的商标权审判案例表明,作为司法审判依据的知识产权立法还不够完善,法官有时只能依据法律条文、民事习惯以外的实定性较弱的“条理”来进行裁判。目前,我国知识产权司法审判是按案件性质,分别由法院中的民事、刑事、行政审判庭审理。这种分散审理的机制带来审判资源配置不合理,诉讼管辖混乱,救济程序繁杂,当事人维权成本高昂等一系列问题。随着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有望消除目前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存在的弊端。
清末民初;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著作权;商标权
随着17至19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保护与鼓励智力成果、科技创新日益成为许多国家的共识。对于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则成为近现代西方法制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时期也成为西方国家知识产权法律相继产生的时期。中国传统社会没有“知识产权”及其保护的概念,直到清末法制变革,受西方法制的影响,中国才开始了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
事实上,清末民初的知识产权立法主要与著作权与商标权有关。专利立法除《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外,就未有发展,直到1928年、1932年才又有专利法规《奖励工业品暂行条例》、《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出台,但法律层面而非部门法规层面的专利法是在1944年才颁布实施的[1]。因此本文论及清末民初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主要集中在著作权与商标权两方面。
知识产权保护在立法层面有了建设,进而才有可能进行司法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而考察司法保护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从当时与知识产权案件有关的司法判决入手。目前所见的清末民初司法判决文书专集主要有《塔景亭案牍》、《各级审判厅判牍》、《最新司法判词》与《华洋诉讼判决录》。其中收录了知识产权案件裁判文书的只有《各级审判厅判牍》与《华洋诉讼判决录》,本文所引实例均出自这两本裁判文集。
一、清末民初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基础
(一)清末民初著作权立法
郑成思先生认为:如果对版权是随着印刷术的采用而出现的这一判断不存异议的话,那么,它就应当是最早出现于中国[2]。笔者理解郑先生这里所谓的“版权”,确切地说是一种观念,而非法律上的权利。因为,以立法来保护这种权利在我国是清末以后的事了。
在中国,“版权”一词从日本的引入早于“著作权”。中国近代版权立法之前,最先介绍版权一词的是著名翻译家、学者严复①。大约在1910年后,随着一些关于版权与著作权有影响的辨析文章的发表,“著作权”比“版权”一词更能表现该种权利性质的观点渐渐成为主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10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大清著作权律》[3],没有采用“版权”,而是采用了著作权一词。
《大清著作权律》虽然因为辛亥革命爆发而未及实施,但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其基本原则和法律体系为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的著作权法所继承。1915年,北洋政府在《大清著作权律》基础上,稍作调整,制定了民国第一部《著作权法》[4],1928年国民党政府再次颁行的《著作权法》[5]。
1.上述三部法律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规定著作权的取得方式,即著作权须登记注册后才能取得,而非自动取得。《大清著作权律》第4条规定:“著作物经注册给照者,受本律保护。”民国4年《著作权法》第1条规定:“左列著作物,依本法注册专有重制之利益者为著作权”。民国17年《著作权法》第1条亦规定:“就左列著作物,依本法注册专有重制之利益者为有著作权”。三部法律规定的注册机关依次为大清国民政部、北洋政府内务部、国民政府内政部。
2.三部著作权法的第二项主要内容是规定著作权的起算。《大清著作权律》与民国4年《著作权法》均规定著作权自注册之日起算。《大清著作权律》第11条规定:“凡著作权均以注册日起算年限。”民国4年《著作权法》第11条规定:“著作权之年限自注册之日起算。”民国17年《著作权法》则有所不同,其第11条规定:“著作权之年限自最初发行之日起算。”该法虽然还强调著作权的取得须以注册为前提,但一经注册,著作权的起算则要上溯至著作物的最初发行之日。
3.三部著作权立法还列举了对著作权的侵害方式及对侵害者的处罚。《大清著作权律》第33条规定:“凡既经呈报注册给照之著作,他人不得翻印仿制,及用各种假冒方法,以侵损其著作权。”第40条规定:“凡假冒他人之著作,科以四十元以上四百元以下之罚金;知情代为出售者,罚与假冒同。”民国4年《著作权法》第25条规定:“著作权经注册后,遇有他人翻印仿制及其他各种假冒方法致损害其权利利益时,得提起诉讼。”第36条规定:“翻印仿制及以其他方法假冒他人之著作权者,处五百元以下五十元以上之罚金,其知情代为出售者亦同。”民国17年《著作权法》第23条规定:“著作权经注册后,其权利人得对于他人之翻印仿制或以其他方法侵害利益提起诉讼。”第33条规定:“翻印仿制及以其他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权者,处五百元以下五十元以上之罚金,其知情代为出售者亦同。”
由上可见,清末民初的著作权立法框架已初步成形。
(二)清末民初商标立法
商标对于清末以前的中国人是陌生的,传统中国缺乏催生商标的社会土壤。因为它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不发达,商品交易量有限,而且由于交通不便,商品以就近销售为主,减少了本来就不多的冒牌机会,因此而发生争执的情况也就更少。禁止冒牌的工作按传统习惯更多是由当地行会主持,按民间组织的规章制度处理②,因此商标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不是特别明显,社会对于商标没有迫切的需求,人们也几乎没有什么商标意识。虽然此前的时代中偶然也有商家用文字、图案来标记并突出自己商品的做法③,但这种做法更着重于宣传自己的产品而非禁止他人假冒。人们更是不曾想过要以国家法律来保护商标。这些原因导致了清末以前国家商标立法的缺失。
1840年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国门大开。伴随着侵略者的枪炮声,各种外国商品大量涌入,抢占了中国大片的商业市场,引发了出于逐利目的的假冒外国商标活动。但由于当时的中国没有商标登记注册制度,也就是说没有对商标专用权的法律保护,因此外国商人开始向本国求助,引起了英、美、日、德等国对在华商标保护问题的重视。
外国列强要求中国政府保护外国商标的活动始于1902年。当时《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谈判在上海举行,英国代表马凯向清政府提交的谈判条款草案中,首次就商标保护以及如何执行、设立相关管理机构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交涉,明确提出中国政府应在上海、广州两口岸设立货物牌号注册局所,由中国海关管理,对所有英国货物牌号进行注册,并加以保护,杜绝假冒。为此,清政府商部于1903年10月31日函请海关总税务司,要求帮助草拟商标注册章程。
1904年初,由海关副总税务司裴式楷等拟订了一份名叫《商牌挂号章程》的商标法规,全文共13条。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商标法规的草案稿。从具体条文内容来看,它只顾及英商的利益,带有很浓的殖民主义色彩。因此,一经公布后,马上引起了国人的强烈反对。
1904年3月8日,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向外务部呈文,申报了详细的修改补充意见,将原《商牌挂号章程》由13条,改为14条。其中规定办理商标注册事项由海关负责,同时将商标划分洋牌、专牌、华牌三类④,进行区别对待。对此,清朝商部表示了强烈抗议,指出无论华洋商标,均应一体保护,以示平允。基于此,商部对赫德代拟的14条进行修订后拟定了《商标注册试办章程》28条,《商标注册细目》23条,于1904年8月4日上奏,旨准颁行。是为清末中国政府批准颁行的第一部商标法规。
在《商标注册试办章程》颁布后,各国使节反对之声不断,商部决定暂缓施行该章程的大部分内容。1906年3月间,英、法等五国大使拟订了修改意见稿,送至商部,此时商部正对章程做第二次修改。1907年,机构改革后的农工商部对商标法律进行第三次修订,将原先的五种商标条例压缩成《商标章程草案》,共72条,附则3条。但草案因时局的变化而一直处于修订状态,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清政府被推翻,清朝的商标法律最终不了了之。
民国建立后,北洋政府先后两次对《商标注册试办章程》进行了修改,并于1922年最后制订了《商标法》,该法共有条文44条,实施细则37条,于1923年5月颁布实施。
从1904年的《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到1922年的《商标法》,中国的商标立法在朝代更迭中历经近20年的艰难历程,终于形成了自身相对完备的体系,使商标这一知识产权在中国的保护不再处于真空状态。
民国初期,著作权法、商标法的制定,为这两种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提供了法律基础。
二、清末著作权的司法保护
清末立法设定了著作权,人们于是有了权利救济的途径。不过,因为这种权利初设定,人们还不习惯。当自己的著作权受到侵害时,不一定能意识得到;即或能意识得到权利受损,又未必知道或者愿意通过诉讼进行救济。这应当是清末民初的各种裁判文书实录中,很少出现关于著作权诉讼案裁判文书的原因。
在清末民初的重要裁判文书专集《塔景亭案牍》、《各省审判厅判牍》、《最新司法判词》、《华洋诉讼判决录》中,只有《各省审判厅判牍》收录了一件关于著作权案件的判词,因为稀见而愈显珍贵。兹录如下:
翻刻地图 澄海商埠审判厅案[6]缘郑鬯亮籍隶揭阳,系汕埠正英学堂毕业生,现充该学堂教习,该生测绘潮州地图,于宣统元年闰二月出版,欲为专卖品。本年四月二十三日,该生向鼎新书局查出地图二十张,曾控警务公所,尚未结案。六月十五日,复以伪造盗刊等情呈诉到厅。二十日传集质讯,据郑鬯亮供称,此图载明版权所有,翻刻必究,该书局冒名盗刊,请照侵夺版权律核办。据书局冯佩卿供称,此图系郑鬯亮托敝书局代售,并未盗刊各等语。查近来中外通例,凡著作权、版权;均须禀准官厅立案,给有证书,始得专卖,该生测绘潮州地图,殊费苦心,惟未经立案,究与禀准专卖之版权有别。鼎新书局为营利起见,发售该生地图,无论盗刊与否,系由该书局查出,且当日并未与该生面商,不为无过。据供郑鬯亮托该书局代售,殊属遁辞,揣度人情,断无始而托其代售,继而诬其盗刊之理,本厅从中调停,谕令冯佩卿缴银五元来厅,转给郑鬯亮具领,为绘图报酬之资。嗣后该书局不得翻刻再卖,致干重罚,两造均愿遵断,当堂具结完案。讼费银三两应归冯佩卿负担。
本案判决书透露出以下值得关注的信息:
(一)原告强烈的著作权意识,以个案方式表明清末民初著作权立法所立足的社会土壤
本案原告诉被告鼎新书局盗刊自己测绘的潮州地图,因而诉请澄海商埠审判厅依照“侵夺版权律核办”。显然作者知道版权并非只是保护出版者、印刷者的利益,更要保护著作者的权利;知道版权保护的对象不仅有图书,而且包括地图之类;知道国家当时已有保护版权(著作权)的立法,而且知道当自己的版权(著作权)受到侵害时,可以运用诉讼的手段进行救济。这些“知道”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系统、完整的著作权意识,这在《大清著作权律》颁布初期,实属难能可贵,也表明了当时社会确实存在对著作权保护的需求。
这当中原告对于版权并非只是保护出版者、印刷者的利益,更要保护著作者权利的认识尤其值得强调。因为,中国传统的版权观念更多是以出版者而非作者为本位的。主要保护作者还是保护出版者的不同选择,体现出我国近代版权制度与古代版权保护的本质区别。《大清著作权律》中出现的权利主体已确定为“著作者”或“著作权者”了。
按照《大清著作权律》第4条的规定:“著作物经注册给照者,受本律保护。”本案原告绘制的地图未经注册给照,严格来说原告的地图不具备专卖资格,不应当受《大清著作权律》的保护,但审判法官最后还是判定鼎新书局以营利为目的,盗刊原告测绘的潮州地图的行为不无过错,因此令被告缴纳五元,由审判厅转给原告,作为其绘制地图所付出劳动的报酬,并令被告今后不得翻刻再卖。这样的裁判结果,显然是基于审判者对著作权法保护著作权人利益立法目的认识并在司法实践中扩展适用的结果,表明原告与审判者的共识:著作者权利应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必须指出,像本案原告那样具有强烈著作权意识,并能在权利受损时积极寻求司法保护的人,在清末民初时期是极其少见的。导致这种情况的因素很多:首先,因为著作权既然是指作者及其他权利人对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享有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总称,尤其是当权利人为作者自身时,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出现了,那就是大部分著作权的权利人需要拥有创作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能力且须转化为实际成果,而这种能力必然是受教育的结果,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能拥有著作权的人应接受过教育。但是在清末民初,能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中国人是少之又少的。据学者统计,当时人口的80%为文盲[7];其次,这20%受过教育的人中,又只有那些有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创作活动及成果的人才有可能具有著作权;第三,这些可能拥有著作权的人,必须知道并愿意申请注册,才能最终享有著作权;最后,当著作权权益受损时,该权利人必须有寻求司法保护的意愿并提出诉讼请求,案件才能进入司法程序,该权益才可能获得司法保护。
受社会发展状况的制约,清末民初时期符合以上条件中一项的人已属极少数,同时具备各项的更是凤毛麟角。这就是当时虽然已有著作权立法,但当事人在权益受损时寻求司法保护的案件却少之又少的原因。
(二)本案原告获得的司法保护突破了法律规定
《大清著作权律》第4条规定:“著作物经注册给照者,受本律保护。”第2条则规定了负责注册给照的机构:“凡著作物归民政部注册给照。”第3条规定了申请注册的程序:“凡以著作物呈请注册者,应由著作者备样本二份,呈送民政部;其在外省者,则呈送该管辖衙门,随时申送民政部。”
注册后,一旦出现《大清著作权律》第4章第2节“禁例”所规定的6种情形,就可以诉诸法律请求保护。《大清著作权律》第4章第3节“罚则”则规定了对侵犯著作权者的处罚。第40条规定:“凡假冒他人之著作,科以四十元以上四百元以下之罚金;知情代为出售者,罚与假冒同。”
很显然,《大清著作权律》没有采用著作权自动产生的立法模式,而是采用了注册登记制。也就是说著作权的取得须以著作物的注册登记为前提。一经注册登记,就受法律保护。反之,即使确实是自己的智力成果,未经注册登记也不能获得著作权,一旦他人侵犯,亦不能获得司法保护。
本案中原告确实是潮州地图的绘制者,但却没有办理著作权注册登记手续。如果严格按《大清著作权律》来审判的话,原告对自己绘制的潮州地图并不具有著作权,因而其诉讼请求是不应当受到法律支持的。但本案审判法官却认为:“凡著作权、版权,均须禀准官厅立案,给有证书,始得专卖,该生测绘潮州地图,殊费苦心,惟未经立案,究与禀准专卖之版权有别。”为此,并没有按《大清著作权律》对侵犯著作权行为的“罚则”中规定的数额(四十元以上四百元以下)处罚被告鼎新书局冯佩卿,而是做出了变通的判决:“谕令冯佩卿缴银五元来厅,转给郑鬯亮具领,为绘图报酬之资。嗣后该书局不得翻刻再卖,致干重罚,两造均愿遵断,当堂具结完案。讼费银三两应归冯佩卿负担”。
应当说这一判决虽然突破了《大清著作权律》的规定,对未予注册登记的著作物也提供了司法保护,但可以看出,这是符合《大清著作权律》保护智力成果的立法初衷,且这种突破是很有节制的。若原告的著作权成立,按照规定,对被告鼎新书局冯佩卿的处罚应当在四十元以上四百元以下的幅度之内,决不是区区五元加讼费银三两可以了断的。正因为原告的著作权未能成立,但他确实又为绘制地图付出了劳动与心血,所以法官才做出了上述判决,以远低于侵害著作权处罚的力度,象征性地对被告予以薄惩,表明对原告智力劳动的尊重,对被告侵害行为的否定,同时也起到敦促原告按照法律规定注册登记以获得最充分司法保护的作用。
按照法律,原告本不应当而实际上获得了司法保护,是为突破;被告受到的处罚远远低于法律规定的下限,是为有限。
这样的判决结果表明《大清著作权律》所规定的著作权注册登记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到了严格但又不失灵活的贯彻执行。本案原告因此获得了在符合著作权法立法初衷前提下的突破性司法保护。这对于推动清末著作权立法向前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三、民初商标权的司法保护
在商标立法的同时,商标纠纷自清末开始日渐增加。比较著名的有1909年左右,日商钟渊纺织公司控华商又新纺织厂冒用其蓝鱼商标纠纷[8];1909年2月,英商祥茂洋行控华商宏源洋货店私卖伪牌肥皂纠纷[9];1909年7月美孚洋行控华商协源祥号邵而康冒充美孚商标纠纷案⑤。不过,这几件商标纠纷都不是由当时业已建立的新式审判厅来审理,而是由租界会审公廨判决的。民国建立后,中国逐渐收回司法主权,关于商标纠纷的诉讼才开始由自己的审判厅审理。
1919年出版的直隶高等审判厅书记室编辑的《华洋诉讼判决录》就收录了三件由直隶高等审判厅审理并制作的商标纠纷案判决书,分别是崔雅泉与日商安达纯一因商标纠葛一案判决书,日商成愿新三与大兴料器厂因商标纠葛一案判决书,崔雅泉与日商安达纯一因商标纠葛由大理院发回更审一案判决书[10]。这三件判决书的制作时间依次为中华民国六年(1917)3月8日,中华民国六年(1917)7月14日,中华民国七年(1918)。
三件案例有以下共同特点:
(一)清末民初的商标诉讼几乎都是华洋诉讼
在笔者搜寻的资料中,无论是媒体上报道的,还是在文献资料中保存下来的商标诉讼,无不是涉外的华洋诉讼,诉讼双方当事人总是一方为华商或华人,另一方为外商或外国人。而且一审均是外商或外国人以华商或华人侵害其商标专用权为案由而提起的,也就是说一审提起诉讼的原告总是外商或外国人,被告总是华商或华人。前面提到的日商钟渊纺织公司控华商又新纺织厂冒用其蓝鱼商标纠纷,英商祥茂洋行控华商宏源洋货店私卖伪牌肥皂纠纷,美孚洋行控华商协源祥号邵而康冒充美孚商标纠纷,无不如此。
崔雅泉与日商安达纯一一案,一审由日商森下博药房控华商崔雅泉因仿造致使其生产的森下仁丹商标受到侵害为由而提起;另一件的一审则是由日商永信洋行行东成愿新三以大兴料器厂假冒其曾在日本特许局登录、并于民国四年12月22日向天津海关附设之农商部注册、天津分局挂号之铁锚樱花商标而提起。
清末民初商标诉讼当事人如此一致的特殊性,其实是当时国外经济势力借助霸权攫取在华利益的必然结果。表面上是诉讼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私利之争,更深层面上是中国与外国列强之间的利益搏弈。当时外国商品并非通过正常的贸易渠道进入中国,因此一方面中国经济完全没有与外来经济沟通、接轨的准备,不具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结构要素所需要的生长土壤与环境;另一方面,外国商品在武力护持下,蛮横地占据了中国的主要市场,极大地扰乱了中国的经济秩序,华商与外商之间冲突势所难免,而冲突的导火线就是外国商品的商标专用权。
(二)该商标纠纷在诉讼到法院之前,经历了先由原告向地方官府抗议,次由官府向交涉公署函请当地警察厅核办,再由警察厅送请地方审判厅这一特殊的诉前移送程序
以崔雅泉与日商安达纯一商标纠葛案来看,判决书中对于案件的来源交待得非常清楚:日商先是向中国地方官府提出抗议,要求官府出面禁止,后来再转由交涉公署函请天津警察厅核办,最后是由警察厅送请天津地方审判厅受理审判。同样,日商成愿新三与大兴料器厂商标纠葛一案也由日商“具情诉经日本领事署函送交涉公署转送天津地方审判厅讯办”。如此看来,清末民初外商与华商的商标纠纷首先选择的救济途径并非诉讼而是外交保护。这是当时特殊历史时期的后遗症。
近代意义的各级审判厅是1907年始在全国陆续建立起来的,既面临自身建设与完善的任务,更肩负着与外国领事裁判权相抗衡的历史使命。领事裁判权设立的目的当然是要保护该国国民、经济组织的在华利益,其基础就是赤裸裸的霸权,无所谓公平、公正可言。因此在当时的涉外诉讼中,外方为了获取利益的最大化,必然要求将纠纷呈至本国领事解决。随着清末各级审判厅在各地的陆续建立,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外国列强以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司法腐败导致司法不公,因而需要领事裁判权来维护本国国民的借口。自此以后清末民初的审判机构随着司法主权的一点点收回而逐步获得对涉外诉讼的管辖权。
诉讼案件由领事裁判向审判厅审理过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崔雅泉与日商安达纯一商标纠葛案、日商成愿新三与大兴料器厂商标纠葛案所反映的正是这一时期外国领事裁判权逐步萎缩、中国司法审判权逐渐成长的消长关系。外商们其实也清楚,如果选择诉讼的路径,案件最终是要由中国司法审判机构审理的,但他们却不愿意径直向司法机构提起诉讼,而是先经过外交“交涉”才转到审判厅。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希望受理案件的审判厅一开始就感受到来自法律以外的政治外交压力,从而占据诉讼主动,获得最大的诉讼利益。只不过从最初的外国领事直接裁判、参加会审或观审涉外案件到此时领事只能向审判厅转送涉外案件,领事裁判权日渐式微的轨迹已经铸定。
(三)审判时的特殊依据:条理
在前引崔雅泉与日商安达纯一因商标纠葛一案判决书中,多次出现“条理”一词,不仅审判厅引为裁判依据,当事人也援用“条理”争取权利。
控诉人认为“原判认定仿造,根据于‘不免类似’四字。然类似者,同类相似使普通人不能区别之意;若各有特点,普通人均能辨别其不同,则非类似。此为最公平之条理。”
直隶高等审判厅则认为日商安达纯一之仁丹商标已在上海和天津海关注册,对于我国即发生一种专卖权之效力;而崔雅泉的中国 丹商标有仿造影射安达纯一仁丹商标之嫌疑,故依据《中英并中日通商航海条约》和“条理”认定日商的仁丹商标应受法律保护,崔雅泉的中国 丹商标属摹造类似的商标,应受查处。
但对于日商请求将崔雅泉尚未卖出的中国丹或其封皮判归被控诉人自行处置,其已经发卖之货物,令其出资收回,交被控诉人毁弃的请求,则依据“条理”驳回了该项诉讼请求。
对于被控诉人确认所受之损害额,并要求崔雅泉赔偿的请求,直隶高等审判厅再一次依据“条理”加以驳回。
而在另一商标案件——日商成愿新三与大兴料器厂因商标纠葛一案的判决书中,直隶高等审判厅依据“条理”认定原判正确,铁锚樱花商标之专用权应归成愿新三所有。
那么何谓“条理”,“条理”与成文法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民初法律中的“条理”来源于日本民事立法,日本明治八年太政官布告103号裁判事务心得第3条中说:“民事裁判中如无成文法则依习惯,如无习惯则应推考条理进行裁判”。
中国清末的民事立法几乎是照搬日本立法,因此,清末《大清民律草案》第1条也规定“民事,本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法,无习惯法者,依条理。”虽然《大清民律草案》因清朝的覆亡而未及颁布实施,但在其第1条所规定的民事审判三大法源:成文法、习惯法、条理,却成为后来民国时期司法审判的主要依据,尤其在民国初期的大理院判决中,频繁地提及“条理”。再后来的《中华民国民法典》第1条则规定:“民事,法律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这里,“条理”又再变为了“法理”。
从《大清民律草案》第1条中的“条理”,变为《中华民国民法典》第1条中的“法理”,这一变化过程表明从一开始,学界及立法者对于什么是“条理”就一直意见纷歧,莫衷一是,故而一会儿称“法理”、一会儿又称“条理”。有的学者据此主张“条理”就是“法理”。推原起来,当是清末《大清民律草案》第1条中的“条理”到了《中华民国民法典》第1条中,变为了“法理”,而该条在两部法典中的作用及意义没有变化,都是要规定成文法——习惯——条理(或法理)三者在民事法律诉讼中法源地位及援用顺序。因此,认为“条理”就是“法理”。
台湾学者黄源盛就认为:“条理,有称之为法理者,系指自法律根本精神演绎而得的法律一般原则;简单的说,即适应时代环境需要,合乎理性的公平规则,它是法律价值的渊源”[11]。“一般而言,所谓‘条理’,或称‘法理’,乃指‘法之原理,其探求方法,一则应依据现行法规,并就社会的现象为研究,以求调和秩序原则;再则,应诉诸于理性及道德的知觉’”[12]。“关于‘法理’,日本法律通称‘条理’,《大清民律草案》从之”[13]。
有学者则认为,“法理”与“条理”不是一回事。民初学者黄右昌认为:“法理者,即正法之意,所谓正当之法理也。条理者即正义之意,所谓自然之道理也。一为客观的,一为主观的也。法理与条理,谓为两者多具相同之点即可,谓为直无区别,则不可也”[14]。
而梁启超则认为日本法律中的“条理”就相当于我国法律中的“情理”。他说:“条理者,日本法律上专用之一名词。裁判官于法文所不具者,则推条理以为判决。如我国所谓准情酌理也”[15]。日本学者滋贺秀三也认为,中国法中的“情理”类似于日本法中的“条理”。他说:“国法是成文的、实定性的判断基准,与此相对,情理则既没有成文、先例或习惯等任何实证基础,也完全不具有实定性,在这个意义上,只是自然的判断基准。如果套用日本的制度,姑且相当于‘条理’。”但他又认为,条理并非完全等同于情理,它们“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异”,“也就是说,虽然条理与情理在作为无实定性的判断基准这一点上相同,但前者毕竟是建立在以规范的严格规则形式为参照、并有力图发展到这种形式的指向这一思维结构之上的”[16]。
笔者认为,“条理”是指在没有法律、习惯可资征引的情况下,审判者在进行裁判时所依据的法学理论、未及颁布实施的法律、法律草案、不具有先例拘束力的判例及情理等尚未具备实定性的规则。与“法律”、“习惯”相比,“条理”的实定性最弱,因此,除非案件审判中确实没有可资援引的“法律”与“习惯”,否则不得援用“条理”。“按上述成文法——习惯——条理三者的优先顺序考虑审判的依据,对于近代法学来说属于一种一般性常识”[17]。
“条理”包含的范围相当广泛,其中首先包括法律草案,例如:前述宣统三年编纂的《大清民律草案》、民国十四年拟定的《民国民法草案》;其次包括大理院的判例、法律之类推适用、学说见解、外国的法例、义理与道德观念等[18]。“条理”的外延应当大于“法理”,“法理”只是“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
民初司法实践中,由于近代法制建设刚刚开始,加之朝代更迭的因素,使很多领域的立法成为空白。以商标法为例,清末虽有《商标章程草案》,但直到清亡,一直处于修订状态,未能生效,因此民国初期关于注册商标的保护没有可资援引的成文法;同时由于注册商标对于我国这一商品经济不发达,又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国家而言,是一种新鲜事物,当然谈不上有关于注册商标的民间习惯。也就是说,民初法官们审理注册商标案件时,既无有效的成文法可用,又无习惯法可依,于是只能依据最后的法源——条理了。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条理”作为判决依据更多出现在民初商标案中的原因。
由上可知,清末民初中国开始了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但这种保护还是初步的,在司法审判实践中,这类案件与传统民事案件相比,数量极少;保护的范围有限,主要是著作权与商标权的保护,专利保护方面的司法判决还未有发现;司法审判中可资援用的立法成果匮乏。
一个世纪后的当下,情况已有了很大的改变。全球范围内,人们已经就知识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解资源环境约束,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重要意义达成共识,2008年我国国务院发布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将知识产权发展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
就目前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来看,最高人民法院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至2013年,全国地方法院审结的知识产权一审民事案件从3万多件增长到近9万件;知识产权行政案件从近2000件增长到近3000件,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则从3000多件增长到9000多件。随着国家与社会对知识产权的日渐重视及民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增强,可以预见知识产权案件的数量还将大幅增长。
但是现行知识产权司法审判机制已经不能适应知识产权诉讼案件大幅增加且专业性极强的现实情况了。目前知识产权司法审判是按案件性质,分别由法院中的民事、刑事、行政审判庭审理。这种分散审理的机制带来审判资源配置不合理,诉讼管辖混乱,救济程序繁杂,当事人维权成本高昂等一系列问题。
2014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等多个方案。习近平主席在会上强调,包括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在内的重多举措,都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制度性措施。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有望消除目前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存在的弊端。
从清末民初到现在,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经历了一百多年漫长而艰难的历程,终于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改革时机。有理由相信知识产权在我国会得到更加妥善、合理的司法保护。
注释:
①严复在1901年与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张元济的通信中,谈及《原富》一书的翻译及版税事宜时云:“外国著书,专利、版权本有年限,或五十年,或三十年”。
②据上海左旭初商标博物馆馆长左旭初考证:“上海绮藻堂布业公所,在道光五年(1825)即开始对本行业牌号进行登记,严禁已在公所登记的牌号有重复名称出现,并对销售他人冒牌土布者,进行严厉惩处。该公所还制定《牌律》,其第6章‘冒牌罚则’第1条规定:‘同号如有顶冒他号已经注册之同路同货牌号,经本所查明或被本牌呈报确有实据者,将冒牌之货,尽数充公。如有掮客经手,必须追查姓名,由公所通告各号,以后永远不许该掮客再掮布货。’”见该作者所著《中国近代商标简史》,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③美国学者韩格理认为:“宋代(960-1279),一些商人就懂得运用‘标记’来突出他们的商品。明(1368-1644)、清(1644-1911)两代,很多在区域市场流通的商品都有‘标记’,我们就称它为‘品牌’(Brandname)和‘商标’(Trademarks)。”见(美)韩格理.中国社会与经济[M].张维安等译.台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269.
④洋牌系洋商已在外国按照该国例章挂号的商标;专牌系洋商在中国使用,但尚未在外国挂号的商标;华牌则系华商使用的商标。
⑤《致公廨函:宣统元年八月初三日》,《上海华洋诉讼案:1909-1913》,上海图书馆藏钞本。
[1]徐海燕.1944年《中华民国专利法的立法思路》,知识产权[J].2010,(5).
[2]郑成思.版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2.
[3]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54.397-404.
[4]商务印书馆.最新编订民国法令大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4.526-527.
[5]徐白齐.中华民国法规大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1065-1066.
[6]汪庆祺.各省审判厅判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31.
[7]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M].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102.
[8]佚名.不允改换商标[J].申报,1909,(2):18.
[9]佚名.英美租界公堂琐案[J].申报,1910,(3):21.
[10]直隶高等审判厅.华洋诉讼判决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99-203.209-212.236-239.
[11]黄源盛.民初法律变迁与裁判[M].台北:国立政治大学法学丛书(47),2000.70.
[12]黄源盛.民初法律变迁与裁判[M].台北:国立政治大学法学丛书(47),2000.428.
[13]黄源盛.民初法律变迁与裁判[M].台北:国立政治大学法学丛书(47),2000.428.4.
[14]黄右昌.中国司法改革之理论的基础[J].中华法学杂志[J].第1卷第5、6号合刊本.
[15]梁启超.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M].北京:中华书局,1957.12.
[16](日)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A].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35.
[17](日)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考察——作为法源的习惯[A].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54.
[18]黄源盛.民初法律变迁与裁判[M].台北:国立政治大学法学丛书(47),2000.386-387.
Case Study on the Judicial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in Late Qing and the Early Republican China
YANG Hong-yan
(School of Humanity and Law,Tianjin Polytechnic University,Tianjin 300387,China)
Affected by western legality,China began to prote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in Late Qing and the Early Republican China.In this period,intellectual property legislation was mainly about copyright and trademark right which were the basis of the judicial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The trial case of copyright in Late Qing showed that the judicial protection of copyright broke through the provisions of Qing Copyright Law;and the trial case of trademark right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China indicated that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egislation as the foundation of judicial trails was not perfect,so sometimes the judge could only base on the"method"which was weaker than legal provisions and the civil customs.At present,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judicial trial in our country is judged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case,respectively by civil division,criminal division and administrative trial division.This has brought about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the un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the judicial resources,the chaotic litigation jurisdiction,the complicated relief procedure,and the high cost of the right of the parties.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ur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it is expected to eliminate the drawbacks of the current judicial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late qing and the early republican china;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judicial protection; copyright;trademark right
D909.92
A
1674-828X(2016)03-0005-08
2016-05-05
杨鸿雁,女,天津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法律史和法律文书研究。
(责任编辑:张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