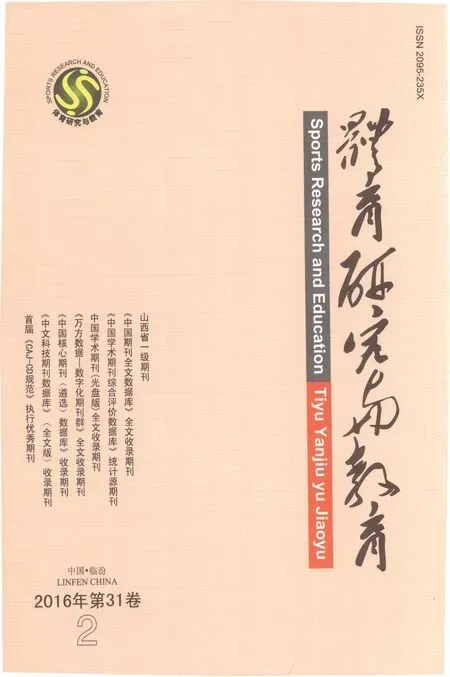论中国现代体育强国形象与体育文化符号
戴 剑,张振华,倪 娜,邢明明
美国学者蒂姆·西斯克说:“一个国家与社会在体育方面的成功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结构运行良好”。[1]中国在体育相关领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在体育“软实力”和“巧实力”方面,政府部门领导和一些媒体一直认为中国目前只是体育大国,并非体育强国,并把体育强国作为中国体育事业未来的发展的目标。我们不禁要提出这样的疑问,完成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蝶变,实现体育强国的梦想,还缺少什么?这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即体育强国不是以简单的数据来表达强弱,也不是以更快、更高、更强为基本价值取向,而是国家体育在世界体育领域的领导地位。国家体育形象的认可度是领导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因为,形象的认可度影响着人们对待事物的思想情感,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认可度是从国家体育文化符号的体验开始,如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是从洋枪洋炮等符号开始的,然后再认识西方的现代科技;现代中国对西方体育文化的认识是从奥运符号开始的,然后再认识西方现代体育运动。郭庆光教授认为:符号是信息的、外在的形式或物质载体,是信息表达和传播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要素[2]。笔者认为:任何先进性、创造性的文化,都要高度浓缩为符号表征的形式,得以表达、保存、发展和传承。可见,体育文化符号决定国家体育形象,国家体育形象决定体育强国的高度。笔者以“体育文化符号——国家体育形象——体育强国形象”为逻辑假设,从体育强国形象塑造的机制、过程和结果进行分析,以求阐述体育强国是普适性的国家体育形象。体育形象是体育强国建设之魂,体育文化符号是国家体育形象建设之魄。体育强国建设实质就是增强体育文化符号的影响力与树立国家体育形象。
1 国家体育形象与体育文化符号之间的逻辑关系
现代汉语词典中,“形象”解释为“能引起人的思想和感情活动的具体形状或姿态”;国外学者Philip Kotler认为:“形象是指人们所持有的关于某一对象的信念、观念与印象”。[3]有关国家形象的定义可谓“汗牛充栋”。学者梁晓波和杨伟芬认为,“国家形象”是世界范围内对于一个国家的整体认知和印象的抽象表现[4],是国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5];王家福等认为,“国家形象”是指“国家结构的外在形态,是国家传统、民族传统与文化传承在当代世界空间的特性化脉动的映象化张力,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历史文化传承中所形成的国家素质及其信誉的总尺度”[6];郑志强等认为,“国家体育形象”是国内、外公众,对一国体育本身、体育价值观、体育外交及其在国际体育大赛取得的成绩所给予的全方位的评价与认定的综合体[7]。体育的独特价值与传播力量,使得国家体育形象对于国家形象的树立,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为国家形象的构建,提供具有理论与实践的支撑性素材准备[8]。在世界范围内以体育形象为符号,成功树立国家形象的案例数不胜举。如:纳尔逊5曼德拉对南非非“种族隔离”国家形象的重树,就是从国家体育形象开始的。他曾经说:“体育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9]”;中国也成功地运用“乒乓球”运动向世界传递和平、友好的国家形象,实现了“小球”推动“大球”的转动;美国竞技体育的高速发展与推广,即向世界传递美国式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平等、自由和消灭了种族歧视的“自由世界灯塔”式的现代化强国形象。可见,国家体育形象即不是本质主义概念,也并非历史主义判断,而是一个需要不断构建的领域。国家体育形象可以是“某某威胁论”的消融剂,可以是传递某种思想的催化剂,也可以是国家形象重要的名片之一。体育符号构成国家体育强国形象,国家体育形象是走向强国重要的推进器之一。
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尔认为,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人自身以他自己的符号化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产品”[10]; 美国著名逻辑学家和符号学家查尔斯5皮尔斯认为,符号是某种对某人来说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种能力代表某一事物的东西[11]。因此,以符号学理论为基础研究国家体育形象,不失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最初的国家形象是以“图腾”的形式出现的,“图腾”就是一种被浓缩的民族符号,民族符号实现着民族的文化认同(culture identity),其中的identity在中文的翻译中有“身份”的含义,因此,又可以理解为文化身份认同[12]。体育文化的认同与国家体育形象构建是同形同构的,如“中国龙”在世界任何地方均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体育思想的历史成就不一定成为具备软实力的文化符号,充其量我们只能称其是一种有意识创造的体育文化现象,更不能代表国家体育形象。然而体育思想在长期自然与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历经千百年的选择和淘汰并沉淀下来,再历经凝练,不断地升华为表征符号,逐渐摆脱实物, 消弱物质性、增强精神性[13],实现体育物质和精神形象的高度浓缩定型,被中华民族认可和接受,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特质的体育文化符号。
目前,我国在体育符号领域的研究还未形成体系,对体育文化特征的认识呈现散文体和碎片化,但是,国家体育形象无论以何种路径形成,最终必定以体育文化符号的形式得以保存、发展和传播。历经磨砺的中国体育文化符号标志性特征一旦被认可和接受,便预示着中华体育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成型。体育文化符号是国家体育形象的一砖一瓦,将体育文化不断凝练为品牌水准的文化符号,众多高水准体育文化符号的集成,并形成体育文化符号的信息链条,通过多种信息渠道传递出去,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再加工,其具有的代表性、稳定性、影响力、吸引力,就会构成良好的国家体育文化形象。
2 中国体育形象需要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符号的积累、传承和创新
国家体育形象需要纵向的继承,就是体育文化符号的积累和传承。汉代思想家王允说:“庐宅始成,桑麻才有,居之历岁,子孙相续,桃李梅杏,庵丘蔽野,根茎众多,则华叶繁茂。”[14]其本意是说文化如果没有积累,就没有发展,更不可能创造新的文化符号。积累和传承就是体育文化符号的纵向发展,起到了保持民族文化“基因”属性和“血型”特质的作用,使得国家体育形象得以保持和延续,得以延着一个方向和轨迹发展。回顾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发展,经历了封建社会选择和淘汰,民族文化的冲突和融合,西方文化的冲突和渗透,仍然是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老文明,显示了中华文化的伟力。中国体育文化脱胎于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不断的创新形成了自身特有的体育文化符号,才得以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在世界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领先地位。离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构建,中国体育形象一定是“空中楼阁”。
国家体育形象需要横向选择,需要体育文化符号的不断创新。国家体育形象是动态的,横向的选择是有条件的。只有在相近的文化背景或不同文化背景发生互补时才会发生。程曼丽指出,国家形象形成和传播中经历了几级变形。在受众处理传播信息中,往往采用的是累积模式。在这种模式下, 单个信息(符号)如同一根柴, 而整体概念(形象)就是一个不断添加“薪柴”的“柴坑” 。依此类推, 国家体育形象可以比喻成一个“ 柴坑”[15]。国家体育形象拥有被内部和外部普遍接受的形象信息, 同时,众多不同主体能动地为国家形象更新着信息。这样,新的信息就是“薪柴”,不断有“薪柴”的堆积,“柴坑”的整体形状不断变化,国家形象的“薪柴坑”也就应运而生。创新是中国体育形象保持世界领先的动力源泉,但由于受近代政治上闭关锁国和“天朝”自居观念的影响,未出现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文化符号。在国家体育形象的“柴坑”中没有“薪柴”。在世界文化发展一体化进程中,被西方“奥运体育”文化符号为代表的竞技体育文化超越,并丧失了应有的时代先进性。我们要实现中华体育文化的复兴,就是要实现对中华体育文化符号的继承,并且不断创新,添加“薪柴”。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乒乓球”“鸟巢”“奥运金牌大国”等反映中国特色和国家体育形象的体育文化符号,继而在此基础上完成中华体育文化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使中华传统体育符号体现出时代的风貌,向世界展示体育强国的国家形象。可见,中华体育文化的“柴坑”需要新鲜有活力的“薪柴”。没有“薪柴”的“柴坑”是没有生命力的。
中国体育形象的建设,即不是简单的“回归和复旧”,也不是无遗传基础的、无轨迹的再选择,纵向发展和横向选择在国家体育形象的构建上是对立统一的。继承是延续的基础,创新是前进的动力。只有继承和创新得到完美统一,才可能在保持文化基因的基础上,充分认识中国体育文化的历史性的缺陷,以科学理性和科学精神实现中华体育文化的兼收并蓄和超越创新。
3 “以德相融”的“开放式”发展模式,是中华体育文化形象和体育符号创新发展的关键
“开放式”发展是体育文化形象和体育符号创新发展的关键。文化进化论认为:文化的突变是创新式发展的基础,而文化突变的必要条件是,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要素接触和融合,同质文化的积累并不能实现创新式发展。中华民族是一个有56个民族的国度。文化体系的构成是开放的,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各民族文化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接触和交融是常态化的。接触和交融的方式总体可以分为以德相融和以力相抗。以德相融往往使异质文化在相互启发和借鉴中得到发展,而以力相抗是异质文化的心理距离加大,损坏各自文化体系的发展与进步。在中国传统哲学主流思想中,“大同”“和合”“和为贵”“恭谨谦让”的中庸思想和适用理性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特点,必然是通而同之,是以德相融的开放式发展模式。纵观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各民族文化并没有在交流和共享中失去民族化和差异化,无不处处体现多民族的文化信息。正是这些文化信息定义了“以德相融”的“开放式”模式的特点:不失自我、尊重差异、多元互补、和谐发展。
在中国古代,各民族体育文化历经了长期积累、选择、变异、冲突、交融、定型的过程,形成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体育文化符号,使得中华体育文化在历史同时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如:龙舟竞渡、武术、骑术、五禽戏、八段锦、蹴鞠等大量以符号形式沉淀下来,形成中华民族稳定的体育特色文化符号。正是这些体育特色文化符号,才有中华传统体育“盛唐气象”的辉煌灿烂和“万国衣冠拜冕旒”的荣光。
近代中国是一种前现代社会的典型时期。该时期社会交往范围相对固定,结构封闭,民族间的冲突和融合不再是社会体系发展的主旋律,民族大一统的文化体系已基本形成。中华传统体育,在以天朝自居的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下,居于主流地位的“重文轻武”“尚柔守雌”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影响下,以文化“中心论”抱残守缺,未和西方以“力本论”为轴心的“尚力”思想进行交流和借鉴,形成了以“狭义民族主义”盲目排外的“唯吾独尊”发展模式,和以“民族虚无主义”为主导的、一味“全盘西化”的两种极端方式。这两种发展方式不断交替进行,成为中国近代体育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式,造成中华体育文化发展停滞不前,已有的优秀体育符号被逐渐淡化,更是离开了世界文化发展的正确轨道。
现代中华民族在改革开放的引领下,积极与西方先进体育文化开展交流,并积极融入到世界一体化的浪潮中,在碰撞交流中为体育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我们不必担心开放式发展会破坏原有的文化结构体系,甚至会造成自身文化符号的消失,因为不同的文化都有着自身特定的“色彩”。当一种文化“色彩”融入另一种文化体系时,不是原有文化“色彩”的消失或被融入文化“色彩”的替代,而是产生一种全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色彩”。新的文化“色彩”必定催生新的“文化符号”的形成。新的体育“文化符号”必树立新的体育形象,影响着世界体育文化的构建和主流文化的形成。
4 积极的体育文化符号输出是树立体育强国形象的必然途径
体育文化符号建设与发展应与国家战略相契合。刘云山同志曾经说过:“在当今时代,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16]有深邃历史底蕴的体育文化符号,只能说我们拥有了体育软硬实力基础,但体育软硬实力基础和国家正面体育形象并非孪生兄弟。正如科特勒的观点:形象是人们对一个对象所持的信仰、理念和印象,是由人对对象的主观感知而构成的。对象的真实性并不与人们的印象吻合[17]。所以,任何国家文化形象,都不是自我生成的,而是被建构、被塑造的。体育文化符号的输出力就是一种体育软实力。它影响着国家体育形象这一“无形资产”的被构建,同时关系到国家体育生存与发展。体育文化符号的输出是“我形象”与“他形象”相互印证和解释的基础,实现着“我形象”与“他形象”认同的统一。随着中国国家体育高速发展和世界体育的一体化格局的基本形成,外界需要中国帮助他们构建中国国家体育形象。正如乔舒亚·库珀·雷默在《淡色中国》中指出的那样,“中国的自我认识与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普遍认识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帮助世界认清中国体育的发展是“妖魔化发展”还是“奇迹化发展”,为世界体育文化引领发展方向,文化符号的输出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见,体育文化符号的输出和强国形象的建设应是成正比的,但目前体育文化的输出和输入的赤字是巨大的,显然与体育强国的地位不相衬。
体育文化符号的输出,要改变厚古薄今的文化传播策略,要有国际化视野,强调和“国际接轨”,要尊重被输出国的文化礼仪和风俗习惯,要尊重和保持各自的民族特色、民族特性,更不能有用“我文化”改造“他文化”的想法,要以“他文化”来解释“我文化”存在的合理性。文化社会学发展理论认为:跨文化圈传播思想,另一个文化圈总会表现出排斥,如果没有对他文化的适应性是不可能实现的。历史上佛教文化在中国的成功传播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其对中国的输入不是“长驱直入”,而是“依附迎合”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体系,以儒学和道教的理解对其教义进行再解释,从而符合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和目标取向,最终佛教文化逐渐被中华民族所接受。因此必须学会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解释和贯通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将符合当代中国发展现实的体育文化形象,“植入”到我们的文化产品与文化表达方式中,甚至可以做出一些妥协,吸收一些非本民族的文化元素,以满足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主体需要。北京残奥会一支《永不停下的舞步》,正是成功运用西方芭蕾舞的表演元素,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残疾人对人类生命本质的理解。但我们也应注意到,绝不能在与“国际接轨”的外衣掩护下,一味地迎合对方文化,泯灭我们的民族个性,丧失我们的文化品格,而应在不丢失自身符号特色的基础上,主动融入对方的文化系统。
国家体育形象的形成肇始于体育符号。中华优秀文化在传承手段和传播途径不发达的时代,身体表达成为重要的传承方式,并逐渐演变成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体育文化符号,具有极强的民族性格。例如:龙舟竞渡就是典型的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符号。其内容本身除具有体育运动的基本特征与功能之外,还有民间祈求福祉的内涵,更重要的是以龙舟竞渡为媒介纪念屈原,表达人们对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精神的赞赏。通过龙舟竞渡向后人传承和宣扬他的处世与生命哲学,以龙舟竞渡为符号,推动他的思想成为一种稳定的、形而上的主流文化,并逐渐固化下来,长期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龙舟竞渡作为体育文化符号是形而下的,却被赋予了中华民族形象的表征,在对外文化输出上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即不受语言、信仰等约束,外民族对该文化符号的接受,就是对正面中国国家体育形象的认可。由此可见,具有身体语言的体育符号,必定成为影响世界哲学思想的利器。
中华民族受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民族性格的影响,并未重视文化符号的输出。体育文化符号的对外输出更是屈指可数,美国的《新闻周刊》评出能够代表各国文化的文化符号,其中被认为属于中国的20个文化符号如下:汉语、北京故宫、长城……少林寺、功夫、西游记、天坛、毛主席、针灸、中国烹饪[15]。属于体育范畴的文化符号仅有功夫一个。难道新中国60多年的体育发展,就没有形成中国特色的现代体育文化符号吗?其实,造成这种认同缺失,是因为没有注重体育文化符号的构建和输出。目前,中华现代体育文化符号的对外输出总体表现为片面性、浅层性和零碎性。不能为异民族了解中华体育文化的特点提供体育文化符号的信息链条,更谈不上对中华民族现代体育文化的认同,也就不能为“他文化”构建中华民族国家体育正面形象提供充足内容,造成“他文化”的认识必定是陈旧的、零碎的和模糊的,甚至是矛盾的,“错位形象”的形成就不可避免。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华体育文化符号输出的过程,是中华体育文化形象的增强自身吸引力和感召力的过程,是被世界认同、接受和追随的过程,是塑造体育强国形象的必然途径。
5 结语
体育强国的建设实质上就是国家体育形象建设。永远不会有程式化的内容让我们去选择,更不可能有标准化的数据作为参照物。不同的国家一定有不同的发展道路。外界多维度对一个国家体育形象的认可水平,是被构建的,是动态的,而不是以自我评价来实现的。外界对国家体育形象的形成,是以若干个体育文化符号集合相互作用,并以各自的文化背景对体育符号集合进行解读,形成对国家体育形象的综合性评价。在进行体育文化符号创新的过程当中,首先,要警惕不良的体育行为和落后的体育思想,外界会逐渐把它物化为反面“体育文化符号”。英国曾经频发的“足球流氓”事件就是其中的代表。对国家体育形象造成的冲击和破坏是巨大的,是众多正面体育符号历经多年都无法抵消的;其次,要建立起能代表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化编码,实现与西方体育文化交流中身份的识别和文化价值差异性的区分,打破西方强势体育文化的合围,为中国体育形象的构建和跃升提供充足的素材。体育文化符号是国家体育形象的基石。体育文化符号越丰富,文化力越强,外界对国家体育文化的认识就越清晰,内部构筑就越稳固。内外对国家体育形象认可度,实际就是体育强国的建设水平。
[1] 西斯克.国泰民安体育兴:外电析中国足球热产生背景外刊外电评论即将进行世界杯的中国队[N]. 参考消息,2002- 05- 24(2).
[2]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 Philip Kotler. Marketing Management Analysis Planing Implementation and Control[M]. Upper Saddle River,NJ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Inc,1997:607.
[4] 梁晓波.国家形象的概念隐喻塑造研究[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113~117.
[5] 杨伟芬.渗透与互动:广播电视与国际关系[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6] 王家福,徐萍.国际战略学[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7] 郑志强,刘志民,刘红山,等.中国大国体育形象构建的困境与路径[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2(12):29~33.
[8] 齐晓英,郇昌店,肖林鹏.基于体育视角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3(1):12~17.
[9] 纳尔逊5曼德拉.漫漫自由路[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10] (德)恩斯特5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885.
[11] 曾于久,刘星亮.民族传统体育概论[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
[12] 雷勇.论跨界民族的文化认同及其现代建构[J]世界民族,2011(2):9~14.
[13] 张德福.体育、符号与消费社会——解读体育现象的一个新视角[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9(2):41~42.
[14] 王允.论衡.超奇篇.
[15] 程曼丽.国际传播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6] 刘云山.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 [EB/OL].http://news.xinhuanet. com/zgjx/content_10588579_4.htm.
[17] 马勒茨克.跨文化交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