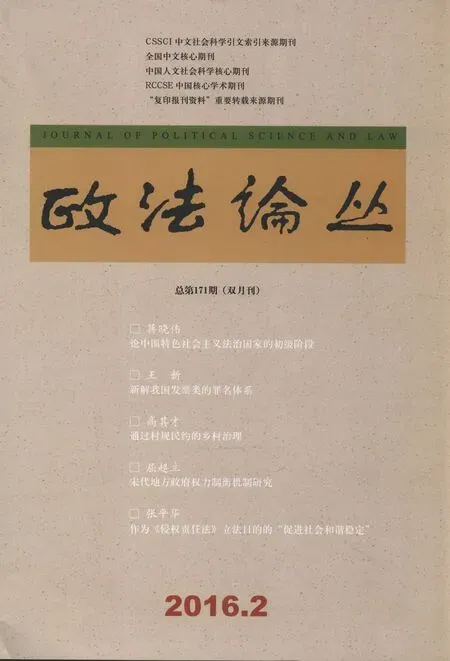公证遗嘱优先效力论争*
郑 倩 房绍坤
公证遗嘱优先效力论争*
郑倩1房绍坤2
(1.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2.烟台大学法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内容摘要】在我国继承法规定的五种遗嘱形式中,公证遗嘱因不能通过其他四种遗嘱变更或撤销而居于效力领先地位。虽然限定公证遗嘱变更、撤销的方式,以及由此衍生的优先效力均无可厚非,但这一限定的绝对化,在遗嘱人无法通过公证程序变更、撤销公证遗嘱的特殊情况下,必将限制遗嘱人变更、撤销遗嘱的自由,使遗嘱人难以依照自己的意志处分个人财产。据此,有必要对公证遗嘱的效力领先地位予以弹性调整,即在常态情况下认可公证遗嘱的优先效力,遗嘱人只能通过公证形式变更或撤销之前订立的公证遗嘱;而在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下,暂时视公证遗嘱与其他遗嘱形式效力等同,允许遗嘱人视情况选择口头或自书、代书、录音等形式遗嘱变更、撤销公证遗嘱。
【关 键 词】公证遗嘱优先效力遗嘱人自由意志
自《十二表法》首次以成文法的方式承认遗嘱的法律效力以来,①意思自治理念即与遗嘱继承结下了不解之缘。而遗嘱制度也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通过赋予遗嘱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设立遗嘱、确定遗嘱内容、自由选择法律规定的遗嘱形式以及变更、撤销②遗嘱的权利,不断追求与践行着尊重和保护自由意志与私有财产权的基本价值取向。鉴于遗嘱最直接地承载了遗嘱人处分个人财产的自由意志,我国继承法除了为遗嘱设置必要的有效要件、确保遗嘱人的意志得以实现外,还允许并引导遗嘱人合理、正当地变更、撤销已经订立的遗嘱。公证遗嘱因只能依照公证程序,不能借由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变更、撤销而在五种法定遗嘱形式中居于至高的效力位阶。随着公民私有财产的丰富、私权意识的增强以及思想观念的转变,通过遗嘱尤其是公证遗嘱自主处分遗产的方式越来越获得人们的认可和青睐。③于是,法律人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赋予公证遗嘱如此之高的优先地位,限制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变更、撤销公证遗嘱,究竟是尊重遗嘱人的意志,还是违背遗嘱人的意志。为此,学界对于公证遗嘱优先效力的正当与否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本文以民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为准据,对公证遗嘱优先效力问题进行应然的逻辑论证,并为修改继承法提供建设性方案,以期为民法典的制定以及法治国家建设尽绵薄之力。
一、公证遗嘱绝对优先效力的弊端
遗嘱于遗嘱人死亡后发生效力,故自遗嘱设立至遗嘱生效,必定存在时间差,而在这段时间内,遗嘱人在已设立的遗嘱中所表达的个人意愿很有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发生变化。既然遗嘱是被继承人处分自己遗产的意思表示,被继承人于自己意愿发生变化时就应当享有随时制定新遗嘱,变更、撤销原遗嘱的自由。详言之,自原遗嘱依法订立至遗嘱人死亡前,遗嘱人可以不问任何理由,也无需任何人同意,有权随时做出变更或撤销原遗嘱的意思表示。当然,遗嘱人在为变更、撤销遗嘱的意思表示时仍须具备遗嘱能力,并在形式上要符合相应的法律要求。这样一来,就同一遗嘱人、同一项遗产,会有若干内容相互抵触的遗嘱。公证遗嘱是所有遗嘱形式中最庄严、最正式的遗嘱形式,现行法通过对公证遗嘱的变更与撤销所做的限定性规定赋予公证遗嘱至高无上的优先地位。我国《继承法》第二十条第三款明确规定,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变更、撤销公证遗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继承法意见》)尽管没有直接限制自书等形式遗嘱变更、撤销公证遗嘱的规定,但该意见第42条规定,遗嘱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公证遗嘱为准。据此,其他形式的遗嘱即使在公证遗嘱之后订立,也不能发生变更或撤销公证遗嘱内容的效果,遗嘱人死亡后仍优先执行公证遗嘱的内容。《遗嘱公证细则》则直接明确规定对公证遗嘱的变更或撤销只能采用公证形式,履行完整的公证程序。总之,尽管诸种现行法的文字表述不同,但核心思想是一致的,即公证遗嘱在诸种遗嘱形式中其效力居于绝对优先地位,公证遗嘱可以变更、撤销其他形式的遗嘱,而其他形式遗嘱不可以变更、撤销公证遗嘱,公证遗嘱非经公证程序不得变更、撤销。
对于公证遗嘱的绝对优先效力,不乏学者及公证人员的称赞和支持。徐国栋教授主持起草的《绿色民法典草案》将公证遗嘱界定为要式遗嘱,而将公证遗嘱以外的遗嘱,包括口头遗嘱和自书遗嘱界定为略式遗嘱,[1]P235并主张“略式遗嘱不得撤销或变更要式遗嘱”。[2]P244上海市东方公证处民事部部长潘浩提出,公证遗嘱的法定要式性决定了对其的变更或撤销只能采公证形式,且此做法并不涉及限制遗嘱人变更、撤销遗嘱的权利。[3]P268大庆市公证处公证员王艳凤认为,在继承法律体系中确立公证遗嘱优于其他遗嘱形式的主导地位,有利于推进遗嘱继承制度的法制化与规范化进程。[4]P35重庆市公证处副主任何伟从公证遗嘱独有的优势、对遗嘱人真实意愿的反映程度,以及对诉讼成本的缓和能力等多方面论证了公证遗嘱优先效力的正当性。[5]P263-264
不可否认,公证遗嘱和以其为载体的被继承人的真意表示富有不可比拟的严肃性和谨慎性,但必须承认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无法利用公证遗嘱变更、撤销公证遗嘱的特殊情况,忽略个案的特殊性,以及针对该特殊性予以特殊保护的必要性而赋予公证遗嘱绝对优先效力,必将导致诸多的立法弊端。
(一)公证遗嘱的绝对优先效力剥夺了遗嘱人处分遗产的自由
遗嘱继承制度以遗嘱自由为基础信条,旨在确保遗嘱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处分个人遗产,并尽力保障该意思表示在遗嘱人死亡时得以发生法律效果。作为遗嘱的有效要件之一,遗嘱人在遗嘱中记录的个人意志必须具备真实性。故只要是符合法定的有效要件、依法成立有效的遗嘱,无论以何种法定形式为载体,势必是对遗嘱人真实意愿的反映。正因如此,五种法定形式的遗嘱应当享有平等的效力等级,任何一种遗嘱都可以变更或撤销之前订立的遗嘱,遗嘱人选择变更、撤销遗嘱的形式的自由应当成为遗嘱自由的重要内涵。赋予公证遗嘱最高的效力位阶,规定其他形式的遗嘱不得变更、撤销公证遗嘱,意味着遗嘱人在遗嘱公证后产生变化的内心真意透过其他遗嘱形式无法得以显露。这显然制约了遗嘱人对变更、撤销遗嘱权利的行使,剥夺了遗嘱人陈述处分财产最终意愿的自由与可能,严重阻碍了遗嘱目的乃至遗嘱继承制度基本精神内涵的实现。④
(二)公证遗嘱较强的证据力不意味着其效力绝对优先
笔者认为,公证遗嘱的效力优先性仅体现在程序法中的证据领域,即除存在可以推翻公证证明的证据外,法院可以直接认定公证遗嘱的效力,裁定按照该遗嘱的内容处置遗嘱人的遗产。但这一优先性只能说明公证遗嘱比其他遗嘱形式的证明力更强,但不能据此扩张解释为公证遗嘱在实体法领域中的效力绝对高于其他形式的遗嘱。⑤
(三)公证遗嘱的绝对优先效力悖于世界各国的立法潮流
我国对待公证遗嘱效力地位的立法态度与其他国家或地区普遍采取的立法例不相符合。⑥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日本所规定的遗嘱形式中,均包含公证形式。在遗嘱生效先后的判定方面,并不因遗嘱形式不同而有所差别,仅承认后订立遗嘱的效力高于前遗嘱,没有表现出公证遗嘱效力的优先性。⑦英美法系国家如英国[6]P34、美国,[7]P251-269都将签订新的遗嘱作为产生遗嘱撤销效果的原因之一,即承认后订立遗嘱的优先效力。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与《日本民法典》相似,亦规定前后遗嘱内容相抵触时,执行后订立遗嘱的内容。⑧我国香港地区的《香港遗嘱条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公证遗嘱形式,但同样采取后有效订立的遗嘱可以撤销前遗嘱的立法例,即推崇遗嘱订立时间的先后决定遗嘱效力高低的原则。[8]
二、公证遗嘱无优先效力理论的检讨
公证遗嘱绝对优先效力的立法态度和理论学说,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已经显现出无法回避的弊端。许多学者主张,判断遗嘱效力高低的标准应该是遗嘱订立的时间,而不是遗嘱的形式,公证仅仅是遗嘱真实性的证明,而不是公证遗嘱绝对优先效力的论据。公证遗嘱的绝对优先效力不仅剥夺了遗嘱人表达处分遗产意志的自由,还背离了法律的效率原则。从《公证法》和《遗嘱公证细则》等相关法规对遗嘱公证程序的规定中可知,公证遗嘱是五种法定遗嘱形式中设立过程最为复杂和严格的。自遗嘱公证后至遗嘱人死亡这段时间内,因为遗嘱人生活中各种情况的发生,会使遗嘱人有改变公证遗嘱的真实意愿,若一律要求遗嘱人必须采用公证遗嘱方可改变制定在先的公证遗嘱,则意味着,之前经历的订立公证遗嘱的复杂程序必须要重新再经历一遍,这显然极不合理地增大了变更、撤销遗嘱的成本与难度,不符合法律对效率价值的追求。[9]P179-180
在对公证遗嘱绝对优先效力的批评声中,公证遗嘱无优先效力似乎已经成为共识。在几个版本的继承法或民法典立法草案建议稿中均直接呈现出对公证遗嘱绝对优先效力的否定,“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变更撤销公证遗嘱”的字样在建议稿中不见踪影,且大都直接规定:存在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的,无论形式如何,均以最后一份遗嘱的内容为准。⑨因此,不同形式的遗嘱只要符合法定的有效要件即可具备法律效力,且这一效力应处于同一效力位阶。在这一论证之下,公证遗嘱的绝对优先效力荡然无存,公证遗嘱与其他遗嘱形式在效力等级上别无二致。
公证遗嘱无优先效力的中心思想,无非是坚持五种形式的遗嘱地位完全平等,任何后制作的遗嘱都可以变更、撤销之前设立的遗嘱,若干份遗嘱内容相互抵触的,以最后一份遗嘱的内容为准,无论其是否为公证遗嘱。这就意味着任何一种形式的遗嘱,只要是最后制作的,均可以变更、撤销制定在先的公证遗嘱。这种观点的最大或唯一益处在于,它可以在遗嘱人无法利用公证遗嘱修改公证遗嘱时确保遗嘱人意志的实现。但是,笔者认为,这种绝对地否定公证遗嘱优先效力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这是因为,公证遗嘱具有其他形式的遗嘱不可替代的优势,任何特殊情况的发生都不足以撼动公证遗嘱的优势地位。
(一)公证遗嘱制作的规范性和严肃性能确保遗嘱人意志的真实性
公证遗嘱是国家机关作为公证人参与制作的遗嘱,鉴于现行《继承法》与《继承法意见》确立了公证遗嘱绝对的优先效力,为了确保遗嘱制作的规范性和遗嘱内容的真实性,《公证法》《公证程序规则》以及《遗嘱公证细则》均有遗嘱公证程序的细致规定。遗嘱人应亲自到有管辖权的公证机构提出办理遗嘱公证的申请,公证处在接到申请后,应当着手对遗嘱人提交的公证申请书以及关涉遗嘱人身份、遗嘱内容等遗嘱公证所需的佐证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审查无疑义后作出受理申请的决定。遗嘱人可以公证自己已订立的遗嘱,亦可以在公证员的见证下口述遗嘱内容,由公证人员如实记录。随后,由公证人员结合有关证明文件以及与遗嘱人的谈话内容,依法开展遗嘱公证的实质审查阶段。审核内容主要包括:遗嘱人订立遗嘱时是否具备遗嘱能力、遗嘱中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遗嘱人就遗嘱中涉及的财产和个人事宜是否享有民事权利、是否存在引发遗嘱无效的因素等。经全面、审慎的核查确认符合法定要求后,公证机构方出具公证书证明遗嘱行为的合法性与真实性,完成遗嘱公证程序。与之相比,关于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继承法》与《继承法意见》仅规定须遗嘱人与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名、注明年月日。显然,自书、代书、录音、口头等遗嘱形式的制订过程较为简易,即使有遗嘱见证人,其见证也几乎是保障遗嘱真实有效的唯一途径。若非因产生遗嘱继承纠纷而诉至法院,作为审理案件的必经环节必须对被诉的遗嘱进行真实性与合法性的审核,以自书等形式订立的遗嘱都难以有机会获得官方的鉴定和认证。因而,这类遗嘱较容易被伪造或篡改,遗嘱内容的真实性也易于遭受质疑和反驳。而公证遗嘱则是在公证人员的监督与指导下,由具有公信力的国家公证机构按照严密、正规的法律程序,对遗嘱的合法性和真实性予以证明和肯定。简言之,公证遗嘱保障遗嘱真实合法的力度,远大于其他遗嘱形式。这就意味着,经过公证的遗嘱更有能力确保遗嘱人依照自己的意志安排遗嘱内容。即使理论上只要符合法定的有效要件,任何形式的遗嘱都是成立有效的,但在实践中,遗嘱人的意志依靠公证遗嘱付诸于实践的机率必定远远高于其他遗嘱形式。从这一角度解读,五种遗嘱形式不应该处于同一效力位阶,公证遗嘱完全有理由占据高于其他遗嘱形式的效力地位。而这一至高的效力地位,并不是对遗嘱人自由意志的制约,反而应被理解为遗嘱人真意得以实现的捍卫和保证。若轻易允许其他形式的遗嘱变更或撤销公证遗嘱,不仅有损遗嘱公证的稳定性、严肃性和权威性,更贬损了公证遗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若后订立的其他形式的遗嘱与公证遗嘱内容相抵,即便订立时间靠后,也不能排除被继承人决策的随意性,因此不能改变自书、代书等遗嘱形式对遗嘱人意思表示真实性的保证能力逊于公证遗嘱的事实,故不能承认或推定后订立的其他形式的遗嘱是对公证遗嘱的变更或撤销。
(二)公证遗嘱更能彰显效率原则
公证遗嘱尽管制作程序略显繁琐,但在其他方面所带来的效率是自书等形式的遗嘱无法媲美的。其一,公证遗嘱的严肃性及效力的优先性给遗产继承的顺利进行带来效率。公证遗嘱是国家授权的公证机构厉行缜密的法定程序进行审查和鉴定,并出具公证书的遗嘱形式。很明显,在各种遗嘱形式中,公证遗嘱最具稳定性和确定性,能够做到从源头抑制和预防遗嘱继承纠纷的发生,使遗产继承能够按照被继承人的遗嘱意志顺利进行;而其他四种遗嘱形式由于订立程序的简单与随意,致使遗嘱的内容和效力极易遭受质疑,遗嘱继承纠纷发生的可能性自然随之激增。通过北大法宝对司法案例的检索结果显示,2204件遗嘱继承纠纷案件中仅有21件涉及公证遗嘱。[10]其二,公证遗嘱因极强的证明力而在遗产纠纷诉讼中给审判程序带来效率。在诉讼中,其他形式的遗嘱须经过法院的审查核实,判断其是否为被继承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而公证遗嘱具有较强的证据效力,可以直接被法官采信,认定其记录的内容为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如此直接有力的证据效力,势必有利于缩短诉讼时间,简化诉讼进程,提高办案效率,以最少的司法资源获得最高效的裁判结果。其三,公证遗嘱具有极强的公信力给民事交易行为带来效率。遗嘱是被继承人处分财产的个人意愿的载体和证明,故而不单在诉讼法律关系中扮演证据的角色,在实体法律关系中对财产的权利归属也有证明的功能。公证遗嘱对财产权利移转信息及权利归属向外界所做的公示和认证较其他形式的遗嘱更有可信度,其真实性与合法性更容易获得遗嘱继承人及其利害关系人的承认和信服,使以遗产为标的交易关系的成立更加便捷,降低交易成本,也能确保民事交易关系的稳定。
(三)特殊情况的存在不足以撼动公证遗嘱的优势地位
依据《遗嘱公证细则》的规定,公证人员在受理遗嘱人提出的遗嘱公证申请时,有义务向遗嘱人说明公证遗嘱的法律意义与后果,其中包括在遗嘱人死亡前,对公证遗嘱的变更或撤销必须由遗嘱人提出申请并例行公证程序。由此可见,遗嘱人在办理遗嘱公证手续时,能够预见到变更、撤销公证遗嘱的程序性和复杂性。既然遗嘱人在五种法定遗嘱形式中选择公证遗嘱来呈现自己的真意,就表明遗嘱人对遗嘱公证繁密的步骤具有主观上的认同与客观上操作的可能。所以,若遗嘱人产生了变更或撤销先前订立的公证遗嘱的想法,在正常的情况下,遗嘱人理应有意愿和能力再次经历公证程序、实现变更或撤销前公证遗嘱的效果。我们不否认在遗嘱人欲实施变更、撤销行为时,可能会面临意外或突发情况,如遗嘱人病危或遭遇自然灾害等,以至遗嘱人对于办理公证有心无力。但这毕竟是发生概率极小的或然事件,而且《遗嘱公证细则》针对遗嘱人无法亲自到公证机构办理手续的情形已经采取应对措施:遗嘱人可以口头或书面申请享有管辖权的公证机构指派公证员到遗嘱人的住所办理公证手续。因此,仅以偶发的特殊情况的可能存在否定公证遗嘱的优先效力明显缺乏逻辑性与合理性。
三、公证遗嘱相对优先效力的证成
经过对公证遗嘱绝对优先效力、无优先效力理论的反思与检讨,笔者认为,公证遗嘱绝对优先效力的弊端在于过分强调公证遗嘱的优先地位,而无优先效力的观点又无视公证遗嘱的优势,绝对地否定公证遗嘱的优先效力,片面强调所有形式的遗嘱地位完全平等。这两者共同的问题是过于绝对化,然而,任何事物都不应当是绝对的,两种立场的绝对化倾向均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妨碍被继承人依自己的意志处分自己的遗产,故本文主张公证遗嘱相对优先效力。
公证遗嘱的相对优先效力,即在保持公证遗嘱常态下优先效力的同时,于特殊情况发生,若依然坚持公证遗嘱的绝对优先效力会妨碍被继承人以自己意志处分自己的遗产时,允许依照法律规定的步骤以其他形式的遗嘱变更、撤销公证遗嘱。由此推导,公证遗嘱的相对优先效力由两部分组成。首先,在正常情况下,宣示公证遗嘱的主导地位,即使公证遗嘱不是遗嘱人最后订立的遗嘱,亦优先发生法律效力。在公证遗嘱后以自书、代书、录音、口头形式订立的遗嘱,无论部分或全部内容是否与公证遗嘱相抵触,均不发生变更或撤销公证遗嘱的法律效果。其次,因特殊情况发生,遗嘱人无法采用公证形式变更、撤销公证遗嘱,且被继承人又确有变更、撤销公证遗嘱迫切需要的,将公证遗嘱与其他遗嘱形式置于同等效力位阶,无论遗嘱形式如何,均以最后设立的遗嘱为遗嘱人的最终真意并发生效力。
常态下公证遗嘱的变更或撤销由遗嘱人的申请予以启动,这其中关涉两个重要因素和条件。其一,变更或撤销公证遗嘱的申请只能由遗嘱人本人提出,不得委托他人代办;其二,遗嘱人须本人亲自前往公证机构提出申请,而且该公证机构须为遗嘱人住所地或遗嘱行为发生地的,为之前遗嘱公证行为出具公证书的公证机构。遗嘱人未能同时成就上述两个重要条件,变更、撤销公证遗嘱的新的公证程序便不能启动。依公证遗嘱的相对优先效力理论,于特殊情况发生时尽管遗嘱人客观上未成就上述两个条件,为了尊重遗嘱人自由更改个人遗嘱的意志和权利,亦允许遗嘱人根据所处的环境,选择自书、代书、录音或口头遗嘱形式变更或撤销公证遗嘱。为了确保公证遗嘱的修正不违遗嘱人的意志,对特殊情况应当予以必要的限定。第一,特殊情况的发生不以遗嘱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受其意识活动的支配和控制,更不牵涉遗嘱人对客观情况的有意改造;特殊情况产生的影响,即对变更、撤销公证遗嘱的滞碍也绝非遗嘱人的主观意欲,遗嘱人并没有否定公证遗嘱优先效力的故意;第二,特殊情况的发生,以及特殊情况产生的后果均超出遗嘱人合理控制的范围,即遗嘱人对于特殊情况发生与否,能否妨碍公证形式变更或撤销公证遗嘱均束手无策。一则,遗嘱人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意志难以阻止特殊情况的发生。虽然这种例外情况属于小概率事件,但若以遗嘱人的抵抗能力为参考系,那么小概率事件的发生也将显得十分必然。二则,特殊情况造成遗嘱人无法启动公证程序的后果超出了遗嘱人合理抵御的能力范畴,遗嘱人没有任何可替代性措施消除特殊情况引发的负面影响,恢复变更、撤销公证程序的正常进行。若因某种意外情况发生致使遗嘱人无法亲自到公证机构提交申请,尚可依《遗嘱公证细则》的便民原则,书面或口头提请具有管辖权的公证机构派遣公证人员到临时指定地点受理的,则可认定为遗嘱人所遭遇的特殊情况的后果仍在其掌控之中,尚未超出遗嘱人的合理控制范围,故在此种场合下不允许遗嘱人擅自以非公证遗嘱变更、撤销公证遗嘱。只有当遗嘱人所处的情境十分危急,以至于遗嘱人完全不可能书面或口头提请指派公证人员时,才属于超过遗嘱人应控制范围。
尽管于特殊情况发生时,无需遗嘱人成就亲自到公证机构申请启动变更、撤销公证遗嘱的程序的条件,但要以非公证遗嘱变更、撤销公证遗嘱还不能是任意的,需要具备必要的条件: 第一,遗嘱人结合客观实际情况,在所处的特殊情况允许的前提下选择恰当的遗嘱形式,并在新的遗嘱中或直接表明变更或撤销之前订立的公证遗嘱,或重新订立与公证遗嘱相抵的遗嘱,以达到默示变更或撤销公证遗嘱的效果。第二,遗嘱人在设立遗嘱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且遗嘱中表述的是遗嘱人真实的意思;第三,满足遗嘱人所选遗嘱形式相应的法律要求。
若选择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及口头遗嘱的,均需满足两个以上见证人的见证的法律要求;现行《继承法》在若干遗嘱形式中,唯独对自书遗嘱没有遗嘱见证人的要求。但面对特殊情况的发生,遗嘱见证人的职能不仅是见证遗嘱的制作过程,更要证明遗嘱人的处境的确符合特殊情况必备的基本特征。因而,即便是自书遗嘱,在特殊情况下也须具备两名以上遗嘱见证人的形式要件。至于见证人的资格问题,《继承法》和《继承法意见》仅列举出不能作为见证人的类型。笔者认为,遗嘱见证人除了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不得与遗嘱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外,还要清楚知晓且同意自己已被确立为遗嘱见证人的事实,并且了解身为见证人所要证实的事项。若对见证人的选定仅是遗嘱人的内心意向,见证过程是在见证人无知无觉的状态下进行的,则不能推定为见证人清楚知晓。另外,遗嘱见证人还要配备基本的见证能力,包括足以理解遗嘱内容的读写能力以及对外界环境和周遭境况的认知能力。在常态环境中,盲人或智力迟缓的人不能作为适格遗嘱见证人。第四,如果遗嘱人面临的特殊情况是以遗嘱人的死亡为结局,那么遗嘱见证人有义务将遗嘱人生前最后制定的遗嘱移交给出具公证书的公证机构,并向其叙述遗嘱人变更或撤销公证遗嘱的时间、地点、身体状况等,由公证机构完成登记、备案等必要手续。如果特殊情况解除后遗嘱人仍在世,则之前遗嘱人设立的其他形式的遗嘱将丧失变更或撤销公证遗嘱的效力,遗嘱人仍须亲自到原公证机构启动公证程序,重新变更、撤销公证遗嘱。
公证遗嘱相对优先效力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它在保持公证遗嘱优先效力优势的同时,又灵活地回避了绝对优先效力的弊端。换言之,它以效力的相对性吸收了效力绝对性带来的利,又巧妙地回避了效力绝对性导致的弊。而最应当称赞的是,公证遗嘱相对优先效力通过赋予被继承人于特殊情况发生时遵循自己的主观意愿,以自己有能力、有条件制作的非公证遗嘱变更、撤销公证遗嘱的权利,缓和公证遗嘱的绝对优先效力,从而为被继承人表达处分遗产个人意志创造便利的条件,使法所追求的自由价值更真切、更完整地反映和落实于继承法之中。当下,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历史时期,如何设计切实体现、反映社会主义法治观的私权制度是这一时期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笔者认为,自由观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价值观,法所追求的自由价值是私法的核心价值,是人类在法价值研究领域中探求自由的结果。作为保障公民私人财产所有权传承的继承法而言,自由价值根植于继承法的制度体系之中,并成为继承法本质属性的凝练与展现。公证遗嘱的相对优先效力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法的自由价值的根本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法治自由观的真切表达,而且不会因对自由价值的尊重与表达而牺牲法的秩序价值。
结语
任何为制度的变革所做的理论上的论证均需要制度实施的可行性予以验证,制度实施可行性论证的最好方法是制度条文设计的缜密与合理。条文难以或不能设计,便意味着变革的制度无法实施,即便理论上论证得再好,改革也是徒劳无功的。经过对公证遗嘱的绝对优先效力和无优先效力进行反思与检讨,以及对相对优先效力的进行合理性论证之后,接下来应当做的事情就是将公证遗嘱的相对优先效力落实在法律条文上。关于遗嘱形式的效力,本文将具体条文设计如下:
遗嘱人可以变更、撤销自己所立的遗嘱。
遗嘱人立有多份不同形式、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的公证遗嘱为准;没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
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变更、撤销公证遗嘱。但遗嘱人确有变更、撤销公证遗嘱的真实意愿,具有以下情形之一致使遗嘱人无法设立新公证遗嘱的,遗嘱人可以在所处环境和条件允许的前提下自行选择口头或自书、代书、录音等遗嘱形式变更、撤销公证遗嘱:
(1)遗嘱人因各种原因生命垂危的;
(2)遭遇地震、海啸、台风等自然灾害的;
(3)遭遇交通事故、火灾、核爆炸等事故灾难的;
(4)遭遇扩散性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须接受隔离的;
(5)遭遇突然袭击、公共场所骚乱等社会安全事件的;
(6)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注释:
①《十二表法》第五表第三条规定:“凡以遗嘱处分自己的财产,或对其家属指定监护人的,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参见周枏:《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024页。
②我国《继承法》规定了遗嘱的变更、撤销。但笔者认为,“遗嘱的撤销”的用语并不准确。在民法上,已生效的民事行为可以撤销,而未生效的民事行为只能撤回。遗嘱在立遗嘱人之前尚未生效,所以,只存在撤回的情形。鉴于我国现行《继承法》使用的是“遗嘱的撤销”的用语,故本文仍沿用“遗嘱的撤销”这一概念。
③公证机构每年办理遗嘱公证的数量从2000年58571件至2013年792586件的显著激增。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④参见陈苇主编:《外国继承法比较与中国民法典继承编制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7页;张玉敏(课题组负责人):《中国继承法立法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王利明:《继承法修改的若干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7期,第179-180页;郭明瑞:《<继承法>修订中的重大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0月22日,法学第A07版;郭明瑞:《论遗嘱形式瑕疵对遗嘱效力的影响》,载杨立新、刘德权、杨震主编:《继承法的现代化》,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204页;郭明瑞、张平华:《海峡两岸继承法比较研究》,载《当代法学》2004年第3期,第16-17页;杨立新:《对修正<继承法>十个问题的意见》,载陈苇主编:《中国继承法修改热点难点问题研究》,群众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龙翼飞、胡明月:《完善我国遗嘱继承制度的思考和建议》,载陈苇主编:《中国继承法修改热点难点问题研究》,群众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页;吴国平:《海峡两岸遗嘱形式及效力规则比较与大陆相关立法之重构》,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61页。
⑤参见王利明:《继承法修改的若干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7期,第179-180页;郭明瑞、张平华:《海峡两岸继承法比较研究》,载《当代法学》2004年第3期,第16-17页;吴国平:《海峡两岸遗嘱形式及效力规则比较与大陆相关立法之重构》,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61页。
⑥参见陈苇主编:《外国继承法比较与中国民法典继承编制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6-337页;郭明瑞、张平华:《海峡两岸继承法比较研究》,载《当代法学》2004年第3期,第16-17页;吴国平:《海峡两岸遗嘱形式及效力规则比较与大陆相关立法之重构》,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58-59页;陈法:《论我国公证遗嘱适用的效力位阶——以法律的价值理论与民众继承习惯的现实为视角》,载《现代法学》2012年第5期,第66-67页。
⑦《法国民法典》第1035、1036条,参见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58、759页;《德国民法典》第2232、2253-2258条,参见杜景林、卢谌译:《德国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23、525、526页;《瑞士民法典》第499-500、509-511条,参见殷生根、王燕译:《瑞士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139页;《意大利民法典》第603、679-686,参见陈国柱译:《意大利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134页;《日本民法典》第969、1022、1023条,参见渠涛编译:《最新日本民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221页。
⑧参见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191条、第1219-1222条,参见高点法学研究中心主编:《民事法规》,高点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419-423。
⑨参见张玉敏(课题组负责人):《中国继承法立法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陈苇(项目负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修正案(学者建议稿)》,载陈苇主编:《中国继承法修改热点难点问题研究》,群众出版社2013年版,第559页;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侵权行为编·继承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页;杨立新(课题组负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修正草案建议稿》,载杨立新、刘德权、杨震主编:《继承法的现代化》,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参考文献:
[1][2]徐国栋.绿色民法典草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潘浩.简论公证遗嘱的变更与撤销[J].司法,2011,10.
[4]王艳凤.自行遗嘱与公证遗嘱的高与低[J].中国公证,2006,9.
[5]何伟.公证遗嘱的效力确认研究[A].陈苇主编.中国继承法修改热点难点问题研究[C].北京:群众出版社,2013.
[6][英]安德鲁·伊沃比.继承法基础(第二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7]Jesse Dukeminier, Stanley M. Johanson, James Lindgren, Robert H. Sitkoff, Wills, Trusts and Estates[M]. ASPEN publishers, 2005.
[8]《香港遗嘱条例》[EB/OL].http://china.findlaw.cn/info/hy/shewaihunyin/fa/143002.html,2011-01-17.
[9]王利明.继承法修改的若干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2013,7.
[10]北大法宝司法案例[EB/OL].http://www.pkulaw.cn/cluster_call_form.aspx?menu_item=case,2015-3-15.
(责任编辑:孙培福)
On the Priority Validity of Notarial Testament
ZhengQianFangShao-kun
(Jili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Changchun Jilin 130012;Law School of Yantai University,Yantai Shandong 264000)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inheritance law in China, notarial testament is in priority among all the five forms of will since the other four cannot modify or revoke notarial testament. Although it’s perfectly fine that notarial testament has priority validity and can only be modified or revoked notarially. But if there is a special time that the testator cannot go through notarial procedure, forcing him to modify or revoke his notarial testament notarially anyway will be unjust and compulsive, given the testator is entitled to dispose his estate freel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often the absolute priority validity of notarial testament. Specifically acknowledge that notarial testament should be in priority and should only be modified or revoked notarially while also allow notarial testament be modified or revoked through other testament written by testator, written on behalf of testator, in the form of sound-recording or nuncupative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Key words】notarial testament; priority validity; testator; free will
【中图分类号】DF524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郑 倩(1987-),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房绍坤(1962-),男,辽宁康平人,法学博士,烟台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
*基金项目:国家基金项目《解释论视野下财产法体系研究》(14BFX08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章编号】1002—6274(2016)02—06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