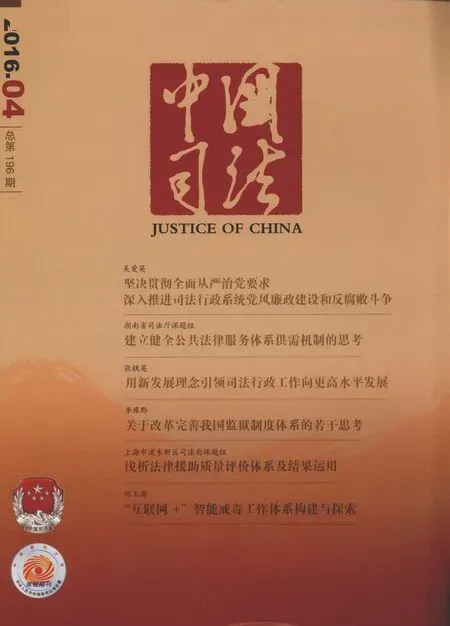律师法律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山西律师法律服务为例
郭 强(山西省司法厅)
律师法律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山西律师法律服务为例
郭 强(山西省司法厅)
当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成为必然选择。谈及此,笔者不由地想到律师法律服务的供给侧问题。
以山西为例。15.6万平方公里,3600万人口。律师事务所和执业律师两个数值,仅2015年,就分别增加28家、977名,“十二五”期间,分别增加了40%和100%,目前,分别达到640家、7200名;全行业业务收入约8亿元。山西万分之二的律师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与法治建设的步伐相比,仍显单薄,故增加绝对数值仍然是未来趋势。但笔者亦觉,单从数值上看,基本是全国平均水平,在目前需求远未及发达国家旺盛的情况下,供需关系相对还是基本适应的,究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质量”上的供需关系严重不适应。
有据可证。山西占北京的数值比例,律师事务所约为1/3,执业律师约为1/4,业务总收入仅约为7%。山西律师业务水平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高端、高收费业务长期被北、上、广等地律师占领,本土律师基本上在一些中低端、中低收费业务上争夺市场。山西律师综合素质总体不高,既懂法律又懂外语、懂金融、懂贸易的复合型人才严重短缺。山西律师事务所规模不大,至今没有百人所,近年增加的80%是个人所,合伙所尽管还占有半壁江山,但总体比重正在逐年下划;专业化程度不高,基本上是什么都会干、什么都干不精的“万金油”;品牌效应不大,放眼国内几乎没有什么知名度,影响力微弱;管理方式简单粗放,律师凝聚力差,大多单兵作战,缺乏归属感,“租赁柜台”现象较为普遍;至于国际化等更高层次更是无从谈起。这些都是山西律师法律服务市场的供给侧问题,亦或在全国有一定的代表性。
山西律师也在苦苦探索自强之路。一些律师事务所重组为全国知名律所的分所模式、与省内外多家律所的联盟模式、加盟大型律师机构的连锁店模式、改制为特殊普通合伙所模式、律所合并模式,如此等等,都是山西律师知耻而后勇的有益尝试。我们也深深为之欢欣鼓舞。
如何做大、做强、做优律师法律服务业?推进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乃必由之路。我们不妨从全要素生产率的“生产要素构成”来分析。普通生产要素构成主要是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而律师法律服务生产要素构成应当是包括理念、人才、业务、质量、管理、供给方式等多方面的综合体。这些生产要素的改革正是律师法律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
——理念先行。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创新、开放、协调、规范的发展理念必不可少。要把创新的理念融入律所管理、业务建设、队伍建设等方方面面,让创新成为常态风尚、形成深厚氛围、产生不竭动力;要以开放的理念与外界在人才、信息、业务、管理等方面打通关隘、冲破藩篱,敢于引进来、走出去,切勿固步自封、闭门造车;要以协调共进的理念实现城乡、区域以及不同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业务的协调发展,先进带动落后、强项带动弱项,实现共同进步;要以规范发展的理念保障律师业的推进发展在法律、法规、规章框架体系之内,不做出格越界之事。
——推进律师业务转型升级。律师业务转型升级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要巩固充实传统诉讼、仲裁和非诉讼业务,使其常做常新、焕发生机。在此基础上,要立足职能,发挥好律师熟悉现行法律规定的专业优势、相对客观处理法律事务的职业优势、立足经济社会生活的实践优势,紧紧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以及安全廉洁发展,围绕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围绕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围绕参与化解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参与矛盾纠纷调解、参与公共突发事件处置等,找准切入点、着力点,发挥作用、彰显优势,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的同时,完成律师业务的转型升级。
——提高律师业务结构对需求变化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灵活性和适应性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前提是预见性和超前性。要加强调查研究,及时洞察中央和地方的大政方针,捕捉信息前兆,增强对经济社会和民主法治建设走向的预见,引导律师业务未来预期,使律师业务导向适当超前至少同步于需求变化。当前在中央实施“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形势下,化解产能过剩成为重要任务,必然要依法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随之兼并重组、破产清算以及相关衍生业务将成为未来几年重要的市场预期,律师业务亟待超前谋划、调整方向、跟进服务,从而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改进律师法律服务供给方式。供给方式是沟通联系供需双方的桥梁媒介,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环节。“互联网+”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今天,在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优化和集成生产要素,改变生产要素的使用结构,提高要素使用效率,从而创造出崭新业态的生动场景下,“互联网+法律服务”的供给方式,不仅会带来律师法律服务供给方式的一场革命,而且会极大地促进律师业务分工与细化,产生律师业务的规模化效应,解决法律服务市场拓展的瓶颈问题,形成更多的特色服务品牌,带动律师法律服务供给侧的全面改革。
——提高律师队伍素质。人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没有一支高素质的律师队伍一切皆空。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职业道德素质一样都不可少。要形成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主导的继续教育培训、实习培训、岗前培训、业务骨干培训、专题培训、交流培训与律师事务所自发组织的日常集中学习培训、律师个人自主学习培训相结合的立体式人才培养体系,打造若干业务和管理领域的领军人才;要请进来、送出去,通过多种渠道方式加强人才培养;要在高端、紧缺领域和复合型方向加强人才培养;要建立社会律师与“两公”律师、老中青梯次结构合理的律师队伍;要关心律师的政治进步、个人成长,为他们发挥作用提供更多机会、搭建更好平台。
——加强律师事务所科学管理。管理也是生产力,管理也是效益。科学有效的律所管理,应当是能使律师业务分工更加有利于体现高端专业性、薪酬制度更加有利于激发创业积极性、内部运行更加有利于保障高效性和协调性。以此为标准,来衡量目前律师事务所所谓团队制和分散制、提成制和薪金制、简约制和公司制、所有权经营权统一制和分离制等各种形式的律所内部管理结构,才更有价值和意义。一句话,律师事务所管理要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鼓励价值创造为核心。
——建立律师业务质量评估体系。法律服务质量是律师的立业之本、执业之基。建立律师业务质量评估体系,既是律师增强责任心、提升服务水平的需要,也是确认律师服务成效、保护律师合法权益的需要。要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质量评估机制,按照不同律师业务类别的特点,遵循其内在规律,建立包括委托人满意度、律师自身工作量、律所管理监督、社会公众和管理机关认可度等内容的指标体系;建立专业权威的评估机构;建立客观公允的评估方法;评估的结论得到及时的公布和充分有效的运用。
——防范律师执业风险。执业风险是律师必须面对的“伴生品”,是始终悬在律师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有些律师倒在《刑法》306条的“绊马索”下,有些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被证监会的巨额罚单命中,难怪有人叹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律师事务所要建立严密的风险防控体系,加强对从接案到结案全过程的研判、审核、监督,构筑起坚固的“防火墙”。律师要加强自身素质和修养,树防线、守底线,提高抵御风险和诱惑的能力,建立与委托人之间充分的理解、尊重、信任与合作,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尽职尽责地提供服务。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要加强风险防控的教育引导,建立统一的执业保险机制,最大限度地解除律师的后顾之忧。
——鼓励建设区域性大所、强所。律所的规模是衡量律师业水平的重要标尺。四川明炬合并33家律所,捍卫本土荣耀,打造成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大所、强所之路,值得学习借鉴。作为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要鼓励支持律所搞合并,实现人合、资合、理念合、业务合、信息资源合,大家抱团取暖,互信、互联、互助、互补,产生“1+1>2”的效果,产生规模效应,降低运行成本,应对大宗业务、大数据时代的挑战。
全面依法治国正在深入推进,“十三五”规划的大幕已经开启,律师法律服务伴随经济社会前进的脚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 张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