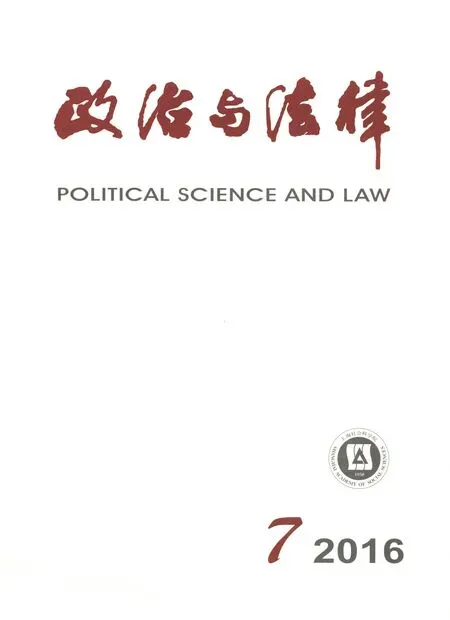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中“违背对公司忠实义务”的认定*
李 军(海南大学法学院,海南海口570228)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中“违背对公司忠实义务”的认定*
李军
(海南大学法学院,海南海口570228)
公司董事忠实义务制度的本质在于禁止董事等从事不公平的利益冲突行为。基于对公司独立及意思自治的尊重,公司法选择从程序公平的层面对利益冲突行为进行规制;而刑法基于对公平交易秩序的维护,以公司及股东对董事的抽象信赖权利作为规范目的,从实质公平层面对董事等的利益冲突行为进行判定。我国现行法上程序公平与实质公平所具体涵摄的行为类型不能完全契合,实践中出现的符合公司法中董事忠实义务程序公平要求的行为,却违背刑法中实质公平标准,从而引发刑法与公司法对该行为的违法性认定不一致的冲突。在违法相对论的思维下,可消解上述的违法性认定不一致的冲突。
董事忠实义务;程序公平;实质公平;抽象的信赖关系;违法相对论
一、问题的提出
有学者指出近几年来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犯罪案发率呈现持续上升趋势,期间案发率基本保持稳定,并没有减缓的态势,且平均的案发率为6.87%。①参见金泽刚、于鹏:《公司高管犯罪的现状、成因与对策思考》,《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当然,公司高管犯罪所涉及的罪名除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外还关涉到其他罪名,例如挪用资金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等。但是,从2006年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设立至目前为止,笔者检测到成立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案件仅3件。②该三则案例分别为:(2007)浦刑初字第1521号;(2010)卢初字第142号;(2010)陕刑二终字第20号。如此小的犯罪比例,让人不禁产生疑问,难道确实是在实务中公司高管实施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稀少所致。显然,答案是否定的。例如,名噪一时的亿阳通信案③亿阳通信案中,亿阳集团将其对南京长江三桥10%的股权,在大桥连续三年亏损的情况下,却在评估时增资10倍,最终以溢价5倍的价格转让给其子公司亿阳通信。参见陈蓉:《亿阳通信关联交易疑局》,《证券日报》2008年4月18日。以及尚德电力案④尚德电力公司的董事长施正荣,先后通过各种隐蔽的手段将尚德电力公司资产转移到其实际控制的、包括亚洲硅业、辉煌硅能源等七家公司。施正荣从中取得了巨额的个人收益,同时希望通过破产制度来免除个人债务的清偿。参见张闽:《资本多数决的滥用与纠正》,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9-60页。等就是如此。在亿阳通信案中,在亿阳通信的小股东强烈反对、相关专家认为该交易存在明显定价不当的情况下,行为人以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作为其“合法”依据,最终以60.86%的比例在股东大会中使得交易方案获得了通过。在尚德电力案中,施正荣分别通过预付款、购销合同以及无息贷款等方式使得其转移资产行为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上述案例中,行为人的行为可能已经构成了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而司法机关却免于对其进行刑事责任的追究,理由在于其不具有民事违法性。详言之,在我国学理上⑤参见前注①,金泽刚、于鹏文;顾肖荣:《论我国刑法中的背信类犯罪及其立法完善》,《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和司法实务⑥例如,在(2007)浦刑初字第1521号案中,法院认为我国《刑法》第169条之一中的“违背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判断应该依附于我国《公司法》第147条、第148条的规定。中的主流观点皆认为,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是我国《公司法》第147条、第148条在刑法上的入罪,罪状中“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的涵义应依据公司法中的忠实义务的规定予以确立。⑦例如,金泽刚、于鹏在《公司高管犯罪的现状、成因与对策》一文中指出,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是《公司法》第148条在刑法上的入罪;顾肖荣在《论我国刑法中的背信类犯罪及其立法完善》一文中认为,“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在我国《公司法》第148条中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而上述案例中的行为人的行为符合公司法中忠实义务的要求,即经股东大会通过或者董事会的同意而批准交易,因此,其并不具有民事违法性。遵从刑法的谦抑性,不具有民事违法性的行为,也不宜具有刑事违法性。但是也有学者对此指出:“《公司法》第148条第1款规定的8种情况与《刑法》第169条之一规定的6种情况,只有1至2种是相同或相似的,其余的都不同。”⑧同前注⑤,顾肖荣文。如果事实正如该观点所言,那么上述主流观点仅仅从逻辑上、形式上的角度来判定公司法与刑法关于违背公司忠实义务行为违法性是否一致的思维,是不可取的。
鉴于违背忠实义务行为的认定标准在公司法与刑法中是否一致,目前存在争议,且该认定标准对行为是否构成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评断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本文拟以公司法与刑法不同法域下对违背对公司忠实义务行为不同界定标准的梳理为切入点,明确不同法域下对违背忠实义务行为违法判断的相对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以违法相对论的思维作为破解公司法与刑法对上述问题呈现的冲突、矛盾之处。
二、违背对公司忠实义务的界定检视:公司法与刑法双重视域下的梳理
我国《刑法》第169条之一(以下简称:第169条之一)中“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以下简称:“违背对公司忠实义务”)的规定,属于空白刑法规范。“当承认空白的犯罪构成时,犯罪的构成部分内容的获得,不可能完全由刑法规范直接获得,而只能通过刑法规范的指引而导向相应的行政性法律规范。”⑨时延安:《刑法规范的结构、属性及其解释论上的意义》,《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因此,第169条之一中的“违背对公司忠实义务”必须要参照公司法中关于忠实义务的相关规定。
(一)我国《公司法》中“违背对公司忠实义务”界定之梳理
我国《公司法》第1 4 7条⑩我国《公司法》第147条第1款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第1 4 8条①我国《公司法》第1 4 8条第1款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挪用公司资金;(二)将公司资金以个人名义或者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三)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五)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六)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七)擅自披露公司秘密;(八)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是关于忠实义务的规定,虽然第1 4 7条概括性地提出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负有对公司的忠实义务(以下简称:董事忠实义务),并在148条采取列举的立法方式进一步详尽了违背对公司忠实义务的行为类型,但是对于董事忠实义务的内涵却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标准。我国公司法中董事忠实义务的设置滥觞于英美法系中的忠实义务的规定。在英美法系中,董事忠实义务虽然没有以成文法的形式对其内涵做出规定,但是在大量案例基础上,对其内涵还是达成了统一的观点。即董事忠实义务的本质就在于避免董事等与公司发生利益冲突。②See:Weinberger v.UOP,Inc,457 A.2d 701(Del.1983)[citing Guth v.Lof t,Inc.,5 A.2d 503,510(Del.1939).]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利益冲突’交易本身并不就是一种犯罪、侵权或必然地侵害公司利益,它只是一种‘事物的状态’,或者说是一种潜在的风险。事实表明,在许多情况下,尽管交易存在利益冲突,公司和股东仍然是这项交易的受惠者。因此,董事的忠实义务并不意味着他必须完全排除利益冲突交易的存在,而是要求这种利益冲突交易对公司而言必须是公正的”。③张开平:《英美公司董事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 9 9 8年版,第2 3 8页。公司法允许董事等利用其公司权力去追逐自己的利益,只要他们能够向公正方(监管机构),特别是法院,证明该笔交易尽管是利己的,但对公司也是本质上“公平”的。④See:Ober ly v.Ki rby,592 A.2d 445,467(Del.1991),quoted in Cinerama,Inc.v.Technicolor,Inc.,663 A2d 1156,1170(Del. 1995)一言以蔽之,禁止不公平的利益冲突行为才是董事忠实义务的宗旨。所以,对董事等是否履行了其忠实义务的审查,通常包含程序公平和实质公平两个层面的审查。程序公平层面的审查,是指该项交易必须要经过非利害关系股东的同意或非利害关系董事的同意,即从程序上来实现对非公平的交易的限制。实质公平层面的审查是指由法院对该交易的公平性做出最终的决定。即使该案件没有通过非利害关系的股东或非利害关系的董事的同意,只要法院认为其符合公平原则,那么该交易就是有效的,即从实质上确保利益冲突交易必须对公司而言至少是公平的。但即使该交易通过了非利害关系股东或董事的批准或同意,而法院却认为其不符合公平原则,那么该交易也是无效的。恰如特拉华州最高法院曾表示,只有通过实质性的审查,才能对忠实义务违反与否做出判断。⑤转引自李燕:《透视美国公司法上董事忠实义务——兼评我国〈公司法〉对董事忠实义务之规定》,《现代法学》2 0 0 8年第1期。所以董事忠实义务的本质是实现实质的公平,如果是程序的公平与实质公平发生冲突,则应该由前者让位于后者。
我国《公司法》中关于忠实义务的规定则是从程序公平的层面对董事忠实义务的履行与否进行界定的。首先,我国《公司法》第148条所列举的董事等违背忠实义务的行为类型中,出现了“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董事会同意”、“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等程序限定的用语。这些词语的使用,反映了公司法是从程序限定的层面对利益冲突交易进行判定的,这亦与英美法系中忠实义务审查中的程序公平原则相一致。⑥在英美法中,认为在以下情形下交易被认为是公平的:(1)在关于利害冲突和交易作出披露后,交易取得了无利害关系的董事的事先授权;(2)交易作出披露后,交易获得了无利害关系的股东的事先批准或事后认可。参见许传玺主编:《公司治理原则:分析与建议》(上卷),楼建波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48页。其次,详阅我国《公司法》第1 4 7条、第1 4 8条,发现其中并未赋予法院对董事忠实义务做公平性司法审查的权力。正如有学者指出,公司法中规定必须有章程规定或股东(大)会的同意,由此排除了司法进行实质公平审查的空间、⑦参见周林彬、方斯远:《忠实义务:趋同抑或路径依赖——一个比较法律经济学的视角》,《中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法院通常不会对被告是否忠实、行为是否合理进行实质性的判断,形式化审查是我国审判实践中最为显著的特点”。⑧王军:《公司经营者忠实和勤勉义务诉讼研究——以1 4省、直辖市的1 3 7件判决书为样本》,《北方法学》2011年第4期。
(二)我国《刑法》中“违背对公司忠实义务”界定之梳理
直观罪状,无法直接得出我国《刑法》第169条之一对忠实义务制度的维护是单一的程序公平取向或者实质公平的取向,又或者是二者皆有之的取向。其法条中,通过例示式立法模式中的明示列举部分,往往揭示了该罪的构成要件行为类型。我国《刑法》第169条之一第1款在概括规定之后,具体列举了六项(包括最后的兜底条款)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种类。这六项规定中,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出现了“无偿”、“明显不公平的条件”、“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无正当理由”等修饰程度的副词。对此,有学者认为,这些程度副词的出现,体现了关联方对公司财产的恶意处分。⑨参见贾楠:《严重非法关联交易行为犯罪化探讨》,《兰州学刊》2012年第1期。张镇:《试论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 0 0 8年第3期。
对此,笔者并不以为然,虽然这些程度副词体现了行为人主观上的蓄意,但是从行为本身来看,这些词语的使用更倾向于旨在与常规交易形成对比。无偿的提供资产,则是一种“赤裸裸的直接侵占或挪用”;⑨参见贾楠:《严重非法关联交易行为犯罪化探讨》,《兰州学刊》2012年第1期。张镇:《试论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 0 0 8年第3期。以明显的不合理的条件提供资产或担保,则“实质上是通过违反市场规律的不公平关联交易等,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⑩赵秉志:《刑法分则要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 0 1 0年版,第1 2 9页。无正当理由地放弃债权、承担债务,“必然会使公司预期可得利益灭失,减少公司的积极财产,从而损害上市公司利益。”②李山河:《论操纵上市公司罪》,《中国检察官》2 0 0 6年第1 1期。公司作为理性“经济人”,其设立及运营的目的在于赢利。上述的几类行为显然违背了公司自身赢利的宗旨。“一般来说,卖方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或买方愿意支付的最高价不属于正常意义上的事实。”③许传玺主编:《公司治理原则:分析与建议》(上卷),楼建波等译,法律出版社2 0 0 6年版,第1 9页。公司之所以接受如此违背常规交易的不公平交易条件无非是受到了他人的控制和支配。正如我国台湾地区“高等法院”《99年度聲再字第305号刑事裁定》中所指出的,忠实义务的核心内容在于董事自我交易行为之规范上,即禁止董事利用其业务执行之便,从事与公司间不合常规之交易行为。不公平是相对于公平而言的。公平,是指从公正的角度出发,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与之相关的对象。公平的市场经济秩序,应指在任何市场买卖中,没有特殊优势,诸市场参与主体平等的参与竞争。在常规交易中,公司公平且自由选择交易,发生了亏损或盈利,皆属正常。但是如果被人利用其优势地位或职权刻意控制或操纵,而达成所谓的不符合常规的“交易”,必然实质上违反了公平性原则。综上所述,可以认定我国《刑法》第169条之一条文中所明确列举的行为类型为实质上违背公平性的交易行为。
“在利益冲突之中,由于管理人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合同双方的意志,形成了一个‘虚假’的合意,从而损害了第三人(常常是公司)的利益,这也是合同外部性的一种表现。从公司利益受损的角度来判断,是实质标准;从合同双方的权力控制角度来判断,是形式标准。”④邓峰:《公司利益缺失下的利益冲突规则——基于法律文本和实践的反思》,《法学家》2009年第4期。可以说,公司法通过对程序公平限定来作为判定行为是否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的标准;而刑法则是根据交易的条件是否符合实质公平原则对之进行忠实与否的断定。简言之,对于“违背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判断,公司法侧重于程序公平性的体现,而刑法则侧重于实质公平性。
三、我国《刑法》第169条之一之规范目的——公司及股东对董事等的抽象信赖关系
从实践所发生的案例来看,公司法中的程序公平的规定,对于保障忠实义务的实现很可能形同虚设,甚至成为缺乏实质公平性之行为的“保护伞”。因为,对于一个对公司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而言,炮制出符合公司法规定的相应决策程序,并非难事。所以将程序合规作为判定实质公允的标准,严格上说并不具有逻辑意义。⑤陈亦聪、武俊桥:《上市公司非公允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制——以刑事责任为中心》,《证券市场导报》2011年8月号。“由于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犯罪所侵害的对象不同于传统的财产犯罪针对的是特定个人利益,而其更多的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侵害。”⑥同前注①,金泽刚、于鹏文。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董事等实施了实质上“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行为,其不仅损害的是公司的财产利益,还会涉及成千上万的股东的财产利益。如果对该类行为不予以及时禁止,因该行为导致公司经营失败,影响了广大投资者对证券投资的信心,进而会对整个市场经济秩序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所以,对于实质上违背忠实义务的行为必须进行禁止。
我国《刑法》将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放在分则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之中。对此我国有学者指出:“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行为人的行为既损害了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益,又破坏了国家对上市公司的正常管理秩序。”⑦冯波、刘澹:《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认定与疑难问题解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页;王鹏祥:《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的理解与适用》,《河北法学》2008年第11期;张镇:《试论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3期。法益具有解释论的机能,故对某个刑法规范所要保护的法益内容理解不同,就必然对犯罪的违法构成要件理解不同,进而导致处罚范围的宽窄不同。⑧参见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第二版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7页。不可否认,违背“对公司忠实义务”的行为定然会给上市公司造成财产损失。但对于其股票在证券市场公开交易的上市公司而言,其股东分散且涉及人数众多,董事等“违背对公司忠实义务”的行为在损害到公司财产的同时也会使得广大公众投资者产生对上市公司的不信任,最终使得金融市场的功能消失殆尽,影响市场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当刑法规制某种犯罪是为了保护多种法益时,应当根据其所属类罪的同类法益内容,确定刑法条文的主要目的,而不能本末倒置。”⑨同上注,张明楷书,第350页。根据刑法的立法体例的安排,该罪不是被设置在财产犯罪一节中,而是被放置在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一节中。可见,立法者在该罪涉及的上市公司个体利益受保护之需要与国家对上市公司(证券市场)正常秩序维护之必要之间,选择了后者。恰如有学者指出,经济刑法是保护整体经济秩序之安定性及公正性的处罚规定。⑩吴元耀:《论经济刑法概括条款之规范模式》,《军法专刊》(台北)第51卷第10期。所以,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所保护的直接法益应为国家对上市公司的正常管理秩序。
每一条刑法分则条文在不超过同类法益的范围还有属于其具体的法益。对于背信罪的所保护的法益,有学者认为“背信罪所保护法益是委托关系以及财产”、①[日]山口厚:《刑法各论》(第2版),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1页。“背信罪的本质在于,尽管事务处理人和委托者之间具有法律上所认可的信赖关系,但却损害这种关系,从而造成委托人财产上的损失”②[日]大谷实:《刑法各论》(新版第2版),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5页。。我国《刑法》第169条之一为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由于该罪的主体限定为公司的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所以,可以认为该罪为特殊背信罪。对于普通背信罪与特殊背信罪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特殊背信罪仅仅是普通背信罪的加重类型。例如,有学者认为,日本《公司法》第960条、第961条、第962条规定的特别背信罪属于刑法典中普通背信罪的加重类型。③参见前注①,山口厚书,第371页。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二者的构成要件相似,但是却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例如,有观点指出:“日本《商法》第486条之罪,于市民刑法体系上,并非侵害个人法益的刑法背信罪之单单的身份加重犯,而应赋予作为白领犯罪时,独自的社会构造与规范意义。”④转引自林誉恒:《经济犯罪与金融机构违法授信之研究》,台湾大学法律学研究所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20页。要注意的是,日本《公司法》(新颁布)中第960条至第962条另行规定的特殊背信罪,与日本《商法典》第486条、第487条(已删除)的规定基本一致,只不过日本《公司法》规定的犯罪主体与刑罚比日本商法典更加具体。
“构成要件的完全包含关系基本上固然是法条单一的一种形态,其却非判断法条单一的标准。”⑤黄荣坚:《基础刑法学》(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 7页。因此,单一条文的构成要件类似,并不足以作为特别背信罪与普通背信罪间具有法条单一性关系的依据。判断特殊背信罪的“特殊性”之所在,关键在于对规范目的的理解。背信罪的刑法条款所要保护的法益,在通说上认为亦与欺诈罪相同,只有财产法益。⑥参见Sc h/Sc h,§266,Rn.1;Wes se l s/Hi ll en kamp,Bt-2,Rn.747。转引自林山田:《刑法各论》(各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 12年版,第315页。“这里所谓对委托关系的侵犯,不是指行为人违反了与事务处理委托者的关系上所应承担的义务,而有必要理解为,是对事务处理委托者的委托利益的侵犯。”⑦参见前注①,山口厚书,第3 71页。德国通说认为,背信罪保护之法益与欺诈罪相同,只含财产法益,并未包含附加的法益侵害,而构成要件中的“违背信任”只是一种构成要件的行为样态,信赖关系不可能系法益之一种。⑧参见Lenckner,Sch觟n ke-Schr觟der,StGB,2 66,1。转引自[日]平野龙一:《刑事法研究——最终卷》,有斐阁2005年版,第74-76页。可见,按照通说的观点,普通背信罪中的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信赖关系,乃是背信罪所使用的手段,其最终的目的在于保护委托人的财产利益。后者的保障,乃以前者存在为前提。⑨张天一:《论背信罪之本质及定位》,《中原财经法学》2011年第26期。但是,笔者认为,该类观点值得商榷。因为背信罪与盗窃等普通财产罪的区别就在于背信罪中所保护的法益中包含着委托人对受托人的信赖,如果仅将该信赖理解为手段行为,那么,背信行为与盗窃等普通财产犯罪亦无不同。特殊背信罪与普通背信罪之间的本质区别应该在于,前者是对抽象信赖关系的保护,而后者注重对具体信赖关系(同时包括具体的财产利益)的保障。在普通背信罪中,委托人对于受托人的选任以及委托权限有着较强的控制权,可以说,此时委托人对受托人个人有着具体信赖关系。而对于上市公司而言,由于其经营的专业性以及股东的分散性,作为所有人的股东对公司管理的参与权被高度稀释化,其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将对公司的财产及经营的控制权概括地授予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正如有学者指出:“在涉及企业经营的代理活动中,本人甚难预见所有的交易对象,亦无法掌握交易的种种细节,因而必须授予董事或经理人更广泛的代理权,其与原本民法上所称的代理,在本质及特性上均不相同。”⑩王文宇:《公司法论》,元照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06年版,第170页。此时,已经不能再认为股东以及公司是对某一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的具体信赖,而是前者对后者专业的抽象信赖。所以,有观点指出:“董事等因其地位权限的优越性、排他的闭锁性及独自的固有性,(对其规制)须能和关于权限、地位本身滥用的危险相对处,其责任评价的程度,非同刑法背任罪系平均人的、个别的信任或信任关系,而是优越的、继续的、包括的制度和法律上的信任关系。”①转引自林誉恒:《经济犯罪与金融机构违法授信之研究》,台湾大学法律学研究所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 2 0页。
因为众多且分散的投资者与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对公司的控制力是严重失衡的,所以公司及公司股东对董事的信赖关系应为法定的抽象信赖关系。不过,此抽象信赖关系的背后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一个人的财产利益,而是涉及广大投资者对国家的上市公司管理制度的安全感、信任感。恰如有观点指出,从本质的内涵观察,此信赖关系的根本是一种社会法益,可以有效降低代理的代价,促进投资市场经济秩序之稳定以及快速发展,其主旨在于避免作为主要法益的经济秩序受到破坏。②参见吴志强:《经济刑法之背信罪与特别背信罪的再建构》,台湾大学法律学院研究所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14-217页。如是,特殊背信罪注重对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抽象信赖关系的保障,其原因在于特殊背信罪的主旨在于对市场秩序和金融秩序的维护。而且“实质标准的判断核心,在于寻求公司利益是否受损”。③参见前注④,邓峰文。即在背信罪的刑事责任上,应以公司财产利益受到损害为必要结果要件。所以,在判断公司负责人之决策是否损及公司利益时,自应以交易内容而非程序是否公平,作为评判决策是否恰当的依据。
四、刑法与公司法冲突之消解——违法相对论思维之提出
“董事只有实施了公司法上忠实义务规范所禁止的具体行为时,刑法才能将之转化为犯罪,否则刑法的调控就是刑法的滥用(激进)。”④邓多文:《董事忠实义务刑法调控机制的规范解释》,《理论月刊》2009年第6期。基于法秩序统一性的要求,作为保障法的刑法,其所规制的犯罪行为必须具有行政违法性。而我国《刑法》第169条之一基于公司及股东对公司董事等信赖关系保护的目的,侧重于从实质公平层面界定条文中“违背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内涵,这样就会产生是否属于对我国《公司法》第148条仅从程序公平层面对违反忠实义务行为的界定标准的“冒进”,是否违背了刑法谦抑性、最后手段性的机能定位等疑问。对该问题的解答在于如何理解法秩序统一性与违法判断的相对性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以违法相对论的思维可以较好的解决刑法与公司法中关于违背对公司忠实义务行为违法性冲突的问题。
(一)学说争议及述评
同一法律事实之不同法域下的违法性判断问题,一直存有争议。概括起来,该争议分为两大阵营即违法统一性与违法相对性的对立;在学理上具体涉及严格的违法一元论、缓和的违法一元论、违法相对论与违法多元论。严格的违法一元论认为,作为犯罪成立条件之一的违法性,应当在法秩序全体中进行一元化的判断。即在某法域被评价为合法的行为,则在其他的任何法域也应该评价为合法行为;相反,在某一法域被评价为违法的行为,在其他任何法域则亦应该评价为具有违法性。⑤参见童伟华:《日本刑法中违法性判断的一元论与相对论述评》,《河北法学》2009年第11期。缓和的违法一元论则主张,违法性的判断应当在整个法秩序保持一致性的同时,允许违法性的判断在不同法域的表现形式存在类别与轻重的不同。⑥参见郑泽善:《法秩序的统一性与违法的相对性》,《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年第7期。违法相对论认为,违法性的概念共通于公法、私法等所有领域但由于各个法域的目的与法律效果不同,所要求的违法程度并不相同。⑦参见[日]平野龙一:《刑法总论Ⅱ》,有斐阁1975年版,第21 8页。转引自王昭武:《法秩序统一性视野下违法判断的相对性》,《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违法多元论则主张,不同的法域甚至同一法域对于违法性的评价都是不同的。⑧有学者指出,该说被我国部分学者混同为违法相对论,无视了违法相对论与违法多元论之间的本质区别。参见王昭武:《法秩序统一性视野下违法判断的相对性》,《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脚注9。例如劳动法与刑法、民法与刑法因其目的、政策不同,故其各自对于违法性的评价也不相同。即使是刑法内部对于不同的犯罪也承认违法的相对性。⑨参见[日]山口厚:《刑法总论》(第2版),有斐阁2 0 0 7年版,第1 7 7页。转引自陈家林:《外国刑法的基础理论与研究动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0页。严格的违法一元论从逻辑的统一性认定法秩序的统一性,即其成立的前提是所有的法律规范之间的逻辑关系是相互协调一致的。按照该逻辑思路,所有的具有民事违法性的行为同时亦具有刑事违法性。该观点显然过于绝对而且与现实立法状况不符,如今在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界渐趋式微。⑩同前注⑥,郑泽善文。所以,我们通常所言的违法判断的争议是指缓和的违法一元论、违法相对论以及违法多元论之间的分歧。
违法多元论本身并不是完全排斥违法性判断的统一性,但其认为“现实法所包含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只要是在法秩序目的必要的范围内。在可能的前提下消除矛盾就够了,没有必要完全消除这些矛盾”。①[日]前田雅英:《刑法的基础总论》,有斐阁1 9 9 3年版,第1 5 9页。转引自王骏:《违法判断必须一元吗?——以刑民实体关系为视角》,《法学家》2013年第5期。违法多元论强调目的和法律效果的相对性判断,不同的法域其有着独自的目的追求,所以违法性的判断应由其所在法域的目的所决定。如果说,持违法一元论的学者是将法规范作为行为规范而言的,那么,采违法多元论的学者则是把法规范作为裁判规范,只需要遵守各自法域的裁判规则即可。②张凯:《刑民关系视野下违法一元论与相对论之对立及展开》,《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但是,“法律规范既是裁判规范,又是行为规范,但首先是作为行为规范而发挥作用”。③同前注⑤,童伟华文。如果对某一法律事实的违法性评判,无法在整体法秩序保持一致的评价,那么法律规范作为国民行为准则的作用也就随之“黯然失色”。试想,如果承认违法判断的多元论,则法律事实违法性的判断沦为司法适用者的“特权”,使得国民有可能在不能正常预测到自己行为之刑法意义及法律后果时,被认定为犯罪。并且法秩序的统一性是维持法秩序体系功能的本质性的需求。正如有观点指出的:“法秩序统一性已成为法解释学的当然前提。不仅是因为法解释学本身要求体系上的统一性(外在体系),法规范这一认识对象本身也要求具有统一秩序(内在体系)。”④[奥]EugenEhrlich:《法律的论理》,[日]河上伦译等译,みすず书房1 9 8 7年版,第1 1 6页。转引自王昭武:《法秩序统一视野下违法判断的相对性》,《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
(二)违法相对论之坚持
综上,对于违法多元论的观点,笔者并不认可,笔者更倾向于违法相对论。违法相对论与缓和的违法一元论在实际的适用结论上几乎不会形成差异,二者唯一的区别体现在:对于具有一般违法性但不具有可罚违法性的行为,缓和的违法一元论认为其具有刑法上的违法但不具有可罚违法性;而违法相对论则认为其完全可以作为正当化事由来处理。“凡是违法要素都属于构成要件要素,在违法阶层并不积极判断违法性,只是判断有无违法阻却事由。”⑤张明楷:《实质解释论的再提倡》,《中国法学》2 0 1 0年第4期。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否定了构成要件的违法推定机能,需要在违法性阶层对违法性进行第二次积极判断。在构成要件要素之外寻找违法性的依据,必然导致违法性判断的恣意,使得“理应不能为处罚奠定基础的法益侵害等也可能为违法性奠定基础,这一点本身是不妥当的”。⑥[日]山口厚:《刑法总论》(第2版),付立庆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 0 3页。同前注⑤,童伟华文。所以,笔者不认可可罚的违法性理论,所以不支持缓和的违法一元论,而是进而认为违法相对论更为可取。
上文已述,违法相对论是以坚持法秩序统一性为必要条件的,即承认一般违法性。“所谓违法性,就是对于一定的事实由国家进行否定的价值判断。”⑦对同一法律事实,在不同法域不应该给予相左的违法性评判。例如,法律不应对同一行为在民法肯定其合法性,但却又认定其具有刑事违法性。但是不容否定的是,在司法实践中对“占有”、“所有权”、“财物”等概念进行界定时,亦出现不同法域下的违法认定冲突问题。其深层原因在于,“民法中违法性的概念与地位远不如刑法明确。民法学者可能在承担民事责任、侵权行为的成立要件之一、过错、侵权行为的全部要件之综合等多种意义上把握违法性”。⑧王骏:《违法判断必须一元吗?——以刑民实体关系为视角》,《法学家》2013年第5期。参见袁彬:《刑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模式及其反思》,《中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例如,对于我国《合同法》第5 4条规定的可变更、可撤销合同而言,受害人可以选择将该类合同无效,也可以选择使合同继续有效。民法理论上通说的观点认为,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在受害人行使撤销权之前,合同是有效的。但是,从刑法的角度,“欺诈”、“胁迫”的行为本身包括了刑法上的诈骗、抢劫、强迫交易等犯罪手段。⑧王骏:《违法判断必须一元吗?——以刑民实体关系为视角》,《法学家》 2013年第5期。参见袁彬:《刑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模式及其反思》,《中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此时,就出现了行为具有民事合法性的同时具有刑事违法性的情形。这必然违背了法秩序统一性的要求。但是,有学者对此明确指出,因诈骗而缔结的合同在撤销前就是违法的,以诈骗、胁迫为理由的可被撤销的合同,就不能成为刑法中正当化理由。只不过是否作为正当化根据的合同之判断与合同之有效、无效的判断是可以分开的。⑨参见[日]佐伯仁志、道垣内弘人:《刑法与民法的对话》,于改之译,北京大学出版2012年版,第304-305页。
民法对违法性判断是一个综合意义上的判断,其通常是在“没有发生损害事实就不是违法”的理念上来理解违法,这与刑法对违法的判定显然是无法契合的。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法秩序的统一”所建立的基础是什么,换言之,法秩序在什么意义上是统一的。“对整个法律秩序的与决策对象有关的规范进行总体性的并且尽可能不矛盾的梳理,就构成了体系”。⑩[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6 5页。可以说,法秩序本身即为体系的体现,但与自然科学中唯一、确切的判断标准不同,往往是虽然“殊途”(论证方法),但总是“同归”(结论);而违法性判断属于价值判断,很多时候不仅“殊途”而且无法“同归”。这是由于逻辑推演与价值评价的本身的不同造成的,正如卡纳利斯所证实的,事实上必须分别不同的体系概念。①Canar is,Sys temdenken und Systembegr i f f in der Jur isprudenz,2.Au f l.1983.转引自:(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依卡纳利斯之见,逻辑学上公理式演绎的体系,并不适用于法学,因为逻辑学上公理式演绎的体系一致性的前提是作为体系基础之公理的无矛盾性及完整性;而为法秩序基础的各种评价原则,其无论如何均不能满足这两项要求。而法秩序中的意义一致性则是由“正义思想”所推论而得,它不是逻辑上的,而是评价上的、公理上的一致性。②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出版社2 0 0 3年版,第4 2-4 6页。如是,在判断法秩序统一性时,应是“实质上”、“评价上”意义上的一致,而不是“形式上”的一致。
(三)我国《刑法》第169条之一中“违背对公司忠实义务”违法性的界定
如上所述,在界定“违背对公司忠实义务”违法与否时,呈现出我国《刑法》与我国《公司法》中的相关规定的冲突、对立。笔者认为,以违法相对论的思维作为切入点可以破解该僵局。
一方面,违法相对论是肯定违法判断的“相对性”,即认为不同法域基于政策、目的及法律效果等因素的考虑,对于同一法律事实所要求的违法性程度是不同的。当然这种违法的不同,不仅是“量的区别”,还包括“质的区别”,即为“质量的区别”。详言之,在承认不同法域其目的的各不相同时,就意味着不法不仅仅是量上轻重的不同,在本质上也是不同的。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刑事不法行为在质上具有较深程度的伦理非价内容与社会伦理的非难性,而且在量上具有较高程度的损害性与社会危害性;相反,行政不法行为具有较低程度上的伦理可责性,在量上也不具有重大的社会危害性。④参见于改之:《刑民分界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 0 0 7年版,第2 7-2 9页。我国公司法和刑法对于董事忠实义务的界定分别从程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层面进行界定,与各个部门法的立法目的的不同密切相关。我国《公司法》中对违背忠实义务的界定没有采用从利益损害这一实质公平的层面进行判断,而是通过程序公平的层面对董事忠实义务的内涵进行界定。其原因在于:一是尊重市场活动中的意思自治,减少对交易本身设定实质性限制;二是充分尊重公司独立人格下的决策自治,因为公司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是对交易条件公平与否的最佳判断主体。⑤参见前注⑤,陈亦聪、武俊桥文。而我国《刑法》第169条之一作为特殊背信罪,出于广大投资者对上市公司规范交易秩序的信赖的保护,其具体保护的法益不再是公司个体利益,而是公司及股东对董事等抽象信赖关系。这种抽象信赖关系的背后即为公平的经济秩序,该经济秩序的稳定涉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所以不应允许以公司自治的理念,放任形式上符合公平的条件而实质不公平、有损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有必要通过刑法对该法益予以强制保障。董事等是否履行了这种抽象信赖义务,应以行为是否造成了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失为标准进行判定;这种利益受损与否的衡量,只能通过对行为进行实质公平层面的分析才能得出。
另一方面,违法相对论与违法多元论的本质不同之处体现在:前者是在维护法秩序统一性下承认违法的相对性,后者则是基本排斥法秩序一致性的。但法秩序的统一性,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实质上、评价意义上”的一致。具体而言,是指在判断违法性时,“刑法对个体性权益的保护,是在整体上与民法保持一致,并非范畴上保持一一对应的关系”。⑥时延安:《论刑事违法性判断与民事不法判断的关系》,《法学杂志》2011年第1期。进言之,刑法规范与其前规范之间是抽象的对应关系,而非具体的对应关系。所以,法域竞合下的违法判断,对同一概念的违法性理解不能仅仅涵射于某一个法律规范的事实构成之中,而是将其与所在法律整体的内容及价值追求保持一致。例如,对于开枪杀人未遂行为,行为人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可能不需要在民法上承担任何民事责任,但不意味着其不具有民事违法性。⑦同前注⑤,童伟华文。按照该实质违法性判定的思路来分析,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利用其职权优势,与公司签订的形式上符合我国《公司法》程序公平但实质不公平的交易,实际上是具有民事违法性的。恰如有观点指出,我国《刑法》从实质公平的角度对董事忠实义务所规制的行为,公司法中之所以没有明确列举出来,是因为这些行为如此明显、如此严重“违反了对公司的忠实义务”、损害了公司的利益,以至于在公司法中不需要列举出来。⑧曾宪文:《背信行为犯罪化或将成为一种趋势》,《检察日报》2 0 0 7年1 1月2 3日。其实,滥觞于英美法系的董事忠实义务界定本身就包括了程序公平审查和实质公平审查。虽然单单根据我国《公司法》第148条的规定,无法得出该结论,但是如果综观我国《公司法》第20条、第21条、第116条、第149条等规定,董事等实质上违背忠实义务的行为定然是违背了公司法的上述规定,具有民事违法性。值得注意的是,刑法对前置规范违法性的判断,只是进行刑事违法性判定的前提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刑事违法性的判断还需要根据刑法规范本身的目的及特点进行判断。
五、结语
随着法定犯膨胀时代的到来,刑法通过空白规范来柔化刑事立法的僵化成为主流趋势,但补充规范与空白刑法规范之间产生冲突与对立的现象屡屡出现,比如本文中的关于“违背对公司忠实义务”认定的争议,再如聒噪一时的帅英骗保案等。如何解决不同法域下违法性判断竞合的问题,成为当前重要理论课题。通过上文的梳理与分析,可以发现空白刑法规范与补充规范之间冲突的本质是在于如何协调法秩序统一性和违法判断相对性之间的关系。无论基于法本身对体系与秩序的依赖还是基于法律作为国民行为准则的功能体现,不同法域的违法性之间应该保持统一性。但必须要承认的是,追求绝对的法秩序的统一性只是理想状态。一部门法之所以可以成为独立的法域,就在于其独立的固有目的追求,以该目的为导向的违法性判断必然会有相对性。所以单纯的肯定或否定违法判断的统一性还是相对性都是不可取的。以违法相对论的思维,即在坚持法秩序统一性的基础上,正面承认不同法域下违法判断的相对性,才是当下理性解决冲突的途径。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补充规范与空白刑法规范之间不是具体的而是抽象的对应关系。因此,利用违法相对论解决具体争议时,需要对补充规范进行实质违法性的判断。
(责任编辑:杜小丽)
D F623
A
1005-9512(2016)07-0049-11
李军,海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为中国法学会2015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非法经营罪定罪量刑实证研究”[项目编号:CLS(2015)Y 0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