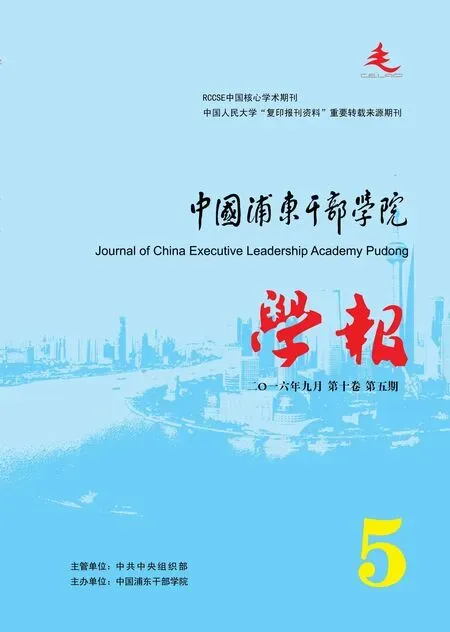《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纲导言
陈文通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北京100091)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纲导言
陈文通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北京100091)
研究和写出一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经济学家的殷切期望,也是当代经济理论界历史性的责任和使命。能否成功的关键是指导思想是否正确。这部政治经济学,既不应当是传统社会主义时代政治经济学(由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构成)的修订版,也不应当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更不应当是改革开放以后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实为西方经济学的再版,而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两个伟大发现”和“一个科学结论”)为指导,从同当代中国生产力相适应的现实经济关系出发,从改革和发展的历史经验出发,以已经认识到的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一般关系为基础,揭示出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现阶段经济运动的特殊规律。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实经济关系;改革发展历史经验;特殊规律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2015年11月23日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指的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他在讲话中着重阐述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肯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另一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和要求。他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要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1]习近平的重要讲话,是编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纲的指导思想。
这篇导言是作为编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纲的指导思想和科学方法而作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三层意思:第一,这里所说的是政治经济学,或者说,是经济科学或经济理论;而政治经济学有十分确定的研究对象。第二,政治经济学有鲜明的阶级性,这里所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或者说,是工人阶级的、劳动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为其他阶级服务的,特别是,它不是资产阶级的、资本的、财产的政治经济学。第三,政治经济学是历史科学,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适合于“当代中国”,而不是中国的其他历史时代,更不是其他国家。大纲贯彻了两个导向:科学导向和问题导向。一方面,坚持被实践反复证明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另一方面,坚持从当代中国总体的(而非个别的)、呈现规律性的(而非零散的和偶然的)现实出发,尊重已有的历史经验和研究成果。这里主要说明以下几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涵义和定位;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现状的评估;中国政治经济学需要认真反思和回答的问题;对中国政治经济学如何实行根本性变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确方法。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涵义和定位(研究对象)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三个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首先搞清楚什么是政治经济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然后是如何界定当代中国。
(一)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内涵和研究对象
政治经济学的涵义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上。研究对象既不能随意改变,也不能随意扩大或者缩小。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般内涵)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不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地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囊括所有历史时代;狭义地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只涉及人类社会的特定生产方式或某个历史时代。《资本论》所研究的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属于狭义的政治经济学。事实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问,只是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开始的,这就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就内容来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而不是财富和财富生产本身。[2](P383)财富的材料对于一切生产时代来说最初表现为共同的东西,因而表现为单纯的前提。这种前提完全处在政治经济学的考察范围之外;只有当这种材料为形式关系(生产的社会形式和经济关系)所改变,或者表现为改变这种形式关系的对象时,才列入考察的范围。换言之,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同物质结合着并作为物出现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3](P44)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但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也不是商品学。因而,政治经济学对商品的研究不同于商品学和工艺学。政治经济学归根到底主要说明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同现实的生产力相适应(或者说,现实的生产力对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以及相适应到何种程度,因而,不能不涉及现实的生产力,不能不涉及劳动的一般社会力(劳动的社会结合,通过科学利用自然力),更不能不涉及生产力在特定生产方式中的特殊实现形式(如资本的生产力);但政治经济学毕竟不是生产力学,它不研究同生产方式无关的抽象的生产力要素,不研究属于自然科学的纯粹的自然力。
一般地(广义地)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但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4](P489)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由重农学派和斯密作了正面阐述的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18世纪的产儿;而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创造。[4](P492-493)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他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然而,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剩余价值理论。[5](P4-17)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核心是剩余价值理论。区别在于,前者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或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后者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资本的政治经济学、财产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第一次科学地说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3](P589)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庸俗政治经济学相比,研究对象是根本不同的。西方经济学从资源稀缺出发,主要研究社会选择和资源配置的效率。这种理论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但主要是为资本增殖服务的,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辩护的。
归结起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是同物质结合着并作为物出现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是研究和揭示人类社会一定阶段上和一定社会形式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历史的科学,旁及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过时的形式,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其他形式。也就是说,要研究,在人类社会的一定阶段上,为什么必然地采取这样的社会形式——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而不是那种社会形式;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中,这种历史的形式为什么必然地为新的形式所取代。要把政治经济学和生产力学、商品学、工艺学等等区别开来。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和研究对象
确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首先需要界定“当代中国”。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精神,“当代中国”指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但是,正如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不能不同时考察和它相联系的那些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并存的一些落后国家的生产方式一样,“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决不能孤立地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关系,而需要涉及建国以来传统社会主义阶段的经济关系,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等等。因此,“当代中国”的起点和上限,应当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的中国,即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中国。如果把新型社会主义道路和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区别开来,那么,“当代中国”可以着重研究改革开放以后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来的中国。从历史的大跨度看问题,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不过是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段弯路。“当代中国”的下限,理论界至今尚无统一的说法。按说,应当是经济关系和社会形态发生新的全面质的变化时的中国。也就是说,现阶段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关系——私有制、资本和雇佣劳动,普遍化的商品生产或市场经济,已经基本上完成历史任务,已经具备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社会所有制,共同生产,联合劳动,以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的条件。或者说,当代中国的下限应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历史任务的时候。因此,“当代中国”处于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物的依赖关系阶段)的后半段。在这个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道路(以及其他变异形态)是同时并存的。因此,对“当代中国”的下限作下述种种理解是不确切的——第一种,理解为“基本实现现代化”之时;第二种,理解为“体制改革任务基本完成”之时;第三种,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定型”之时。现代化和制度定型,都包含在人类社会第二阶段之中。“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工业化——机器大工业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支配地位,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基本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同市场经济形式相适应的经济关系。
当代中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因此,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不应当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直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之前这个社会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如果我们把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道路分作两个阶段,那么,“当代中国”就是它的第一阶段——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预备阶段。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其基本内容来说,和前面所说的一般内容是相同的,即研究当代中国的生产方式以及同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研究这个社会阶段和社会形态经济运动的规律性。区别在于,中国现在仍然处在不断深化的改革之中,经济关系还没有稳定下来,还没有定型。因此,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不能不反映改革中经济关系变化的主要过程、阶段和变化的规律性,不能不研究带有规律性的改革阻力,不能不研究突破种种阻力的对策。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完成时代赋予它的艰巨任务:应当为寻找同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服务,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服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为应对市场经济的历史局限性提供新的理论支撑,为当前的发展和改革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二、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简要回顾和基本评估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过去和现状,是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成就和问题如何评估,至关重要。其中,坚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是一个普遍原则。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学,也需要一分为二和坚持问题导向;在肯定成绩和成功经验的同时,必须清楚中国政治经济学目前存在哪些重大和根本性的问题。
(一)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总体评估
三大划时代创新理论成果没有得到政治经济学的有力支撑。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形成了三大划时代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发展理论。这三大理论成果都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是,也存在遗憾、缺陷和不足。新民主主义理论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在襁褓之中就被“超阶段”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核心是国家社会主义和农民共产主义的混合物)所否定。其重要原因就是,这一科学理论没有得到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强有力支撑,没有说清楚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否定之否定的革命性成果,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重大理论意义在于,后发展国家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从而形成一种同后发展国家相适应的特殊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但是,对这一划时代的重大理论成果,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理论)并没有完全尽到应尽的责任,没有以更加科学的范畴和理论语言将其表述出来,没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给出质的规定性;而是主要在表面化地解读“中国特色”上做文章,既模糊了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区别,也模糊了两条不同发展道路的区别。这不仅使人们搞不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其他“主义”、制度、社会形态的区别和联系,也使西方庸俗经济学和形形色色的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潮有机可乘,以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一个人们可以任意解读和被利用的标签。包括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在内的科学发展理论,首次以理论的形式对传统发展方式提出质疑,阐明了新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内涵;但经济学家没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刻揭示出传统发展方式借以形成和难以转变的根源,也没有为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奠定现实经济基础的思路,而是更多地做文字游戏。
中国政治经济学显著滞后于政治决策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包含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理论成果——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理论,关于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和新的战略对策的理论,等等。在此期间,中国政治经济学所做出的理论贡献是,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可持续发展持积极支持的态度。一是确认商品生产的充分发展不可逾越,中国必须放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形式和交换方式应当是市场经济;二是确认以速度为中心的传统发展方式代价高昂,不可持续,中国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但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显著滞后于政治决策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在理论上没有起到先导作用,基本上是被动的;不少理论认识是比较肤浅的,实际上不过是超前接受了西方学者的观点和建议。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经济关系的大变革中,经济理论界的主流并没有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没有充分表现出“科学上的诚实”精神,缺乏理论上的彻底性,没有以科学的理论说清楚中国改革的历史必然性、性质和目标,也没有说清楚转变发展方式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而是更多地直接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老生常谈和平庸教条。一些经济学家口头上也讲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更多地是穿靴戴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题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基本上是西方经济学的中国版,既未能说服“左”的和右的两个极端的人们,也未能说服普通的工农大众,甚至也未能说服经济学家自己。越来越多的人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被边缘化了,而且,主流经济学正在以“反对教条主义”的名义,把包括马克思经济理论在内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并加以贬低和排斥。我们可以从改革和发展两个方面说明中国政治经济学界在理论认识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就对改革的理论认识来说,许多经济学家既没有科学说明中国改革的必然性和实质,也没有科学说明原有的经济关系在改革中发生了什么样质的变化。改革本来主要是为了纠正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超阶段的错误。但是,在主流经济学看来,超阶段的并不是经济制度和基本经济关系,不是所有制关系(经济制度,生产关系,分配关系),而是资源配置方式,即经济形式和交换方式;不是内在的、本质的经济关系,而是表层的、外在的经济关系。他们先是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上做文章,尔后又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做文章,但都没有触及到问题的要害。显然,主流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仍然肯定和固守社会主义改造和“继续革命”的消极成果。但是,这种认识同改革中形成的经济关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改革已经在事实上否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成果——消灭私有制,消灭个体小生产,消灭资本和雇佣劳动,使经济关系回到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国把“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是市场经济,主流经济学家没有理论勇气作出回答。“市场经济”是什么,在国际社会是尽人皆知的常识,理论上是十分确定的。然而,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对科学认识“市场经济”和改革的实质提供科学依据;而是把中央正确的政治决断和政治家的政治语言直接当作科学理论,把需要从理论上证明的东西当作先验的公理,当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既定前提和出发点。许多经济学家只是对改革的政治决策和有关文献作表面上的牵强附会的文字解读,只是在中央文献中已经提出的判断和概念的基础上进行演绎和逻辑推理。例如:既然把改革定性为“(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把我国的市场经济概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社会主义就完全可以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就必须为主体了,就必须把市场经济界定为“资源配置的方式”了。进一步的逻辑推论是:既然中国必须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而又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既然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是市场经济,那么,政治经济学也就“突破”或者“修正”了先前的理论认识:一方面,“突破”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要观点——商品生产是一种历史性的经济关系,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共同占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消除商品生产。另一方面,“修正”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常识——自由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在改革的实践面前,这些“突破”和“修正”完全是虚幻的。人们很快就发现,市场经济的自然发展(本质上是商品生产、价值形式和雇佣劳动的发展)同现实的传统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如果把发展市场经济作为前提,那就必须通过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和国有企业的“深层次”改革,为市场经济开辟道路和创造出制度基础,培育出广泛的市场主体和完善的市场体系。这种改革无非是容许私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特别是创造出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但这样一来,所有制结构、生产方式乃至国有企业的内部关系都发生了极大的、根本性的变化。事实上,市场经济不过是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发生根本性变革的结果。但是,如果按照预设的不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前提,政治经济学决不能在理论上承认这种变化;相反,必须反复申明:中国仍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改革的核心只在于解决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或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改革所改变的只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股份公司就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按要素分配包含了按劳分配;等等。这种理论概括和现实的经济关系相去甚远,根本没有理论上的说服力。
就对发展的理论认识来说,主流经济学家既没有说清楚中国传统发展方式形成的经济根源,也没有科学说明中国经济发展陷入极大困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中央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已经认识到,而且每到经济陷入困境的时候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必须改变原有的发展路子、企业经营方式、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进而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新的发展理念;认识到问题的核心是发展方式,关键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和落脚点,即发展以什么为中心。但经济学家并没有进一步说明,决定发展目的、落脚点和中心的经济关系是什么。许多经济学家把以速度为中心的传统发展方式归结为一定发展阶段的自然现象,而同现实的经济关系和发展思路无关;与此同时,用西方经济学的惯用语言说明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无非是结构性、周期性、外部冲击等等。所谓结构性就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周期性就是西方国家所说的“景气周期”;外部冲击就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导致世界市场的萎缩,从而冲击了我国的出口。另有一些经济学家则用所谓“三期叠加”“中等收入陷阱”这类玄乎的概念,说明困难的原因——按照这种“理论”,中国只能是无所作为和一蹶不振。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既同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无关,也同改革中的偏差和失误无关;既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关,也同改革中形成的新的经济基础无关。
总之,中国的主流政治经济学并没有为发展和改革提供真正科学的和充分的理论依据,没有从发展和改革的实践中系统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大落后于发展和改革的实践。其中,发展的理论避开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历史遗产,掩盖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规律;避开了发展指导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改革的理论避开了市场经济的真实属性,掩盖了经济关系发生的实质性变化,避开了“市场化改革”中的偏差和失误及其消极后果。30多年来,政治经济学更多地是在做两件事:一是引进和传播现代西方经济学;二是对中央文献作表面的牵强附会的解读。这两件事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理论创新”的名义下做的。但“中国化”和“创新”并未以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为基础。
(二)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存在“六个不够准确”
一是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准确,没有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摆在应有的重要地位。自列宁以来,理论界一直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放在列宁的概括——“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之中,而不是放在恩格斯的概括——“两个伟大发现”和“一个科学结论”——之中,不是作为最伟大的理论发现之一来对待。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理解和概括不够准确,从而被贬低、被割裂、被修改,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地位的认识也就不可能准确。在“两个伟大发现”和“一个科学结论”中,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深刻批判的产物,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法的规律为指导,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和发展趋势,为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此,共产主义不再是一种理想信念,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现实运动。但是,在“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被说成是“来源”于英国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处于和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一个强加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概念)、科学社会主义平列的位置,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学科。
二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的解读和运用不够准确。如果说,过去对经典著作的解读主要是为不断革命提供理论支撑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对经典著作的解读,都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理论依据”的。望文生义、断章取义、随心所欲、指鹿为马的解读比比皆是。例如:把《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说成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方式;把生产方式说成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而不是劳动者和生产的物质条件结合的社会方式,或生产的社会形式;把所有制仅仅说成是对生产资料的归属(法律所有权),而不是劳动和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关系,不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他们还由《资本论》得出与马克思的观点不同甚至相左的观点。例如:从“商品生产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论述得出,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是商品生产;认为《资本论》同时也是“商品经济论”“市场经济论”;认为不仅有“资本主义资本”,也有“社会主义资本”,而“资本一般”则是对这二者的进一步抽象;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一系列经济规律,如果抽掉、舍象掉其特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同时也是社会化大生产(或社会化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把《资本论》第二卷关于“资本的流通过程”的论述说成是超生产方式的再生产一般理论;认为我国改革中出现的劳动者个人股份制,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的“个人所有制”,认为股份公司就是社会所有制或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认为《资本论》第三卷否定了第一卷。一些经济学家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到的庸俗经济学家的“四个环节”及其相互关系之说,说成是马克思的辩证思想,并把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特殊关系(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说成是“生产一般”中的抽象一般关系。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公社问题的论述断章取义,加以歪曲,得出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结论;并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跨越资本主义的产物。诸如此类不准确的解读和演绎,已经进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和“马工程”的研究成果,并不断地以讹传讹。
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定位的认识不够准确。这两个概念的提出,都有具体的历史背景,都是在纠正“左”的错误、推进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提出来的。“中国特色”可以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是照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社会主义,也不是照搬其他国家(例如苏联)的社会主义;这个说法也许还有利于避免更多的争论和实现道路的顺利转变。但是,“中国特色”毕竟是一个没有质的规定性的说法,不能表明社会形态的性质和经济社会关系;没有表明它和其他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传统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共同点、历史联系、质的区别)。因此,应当用一个规范的范畴表达出来;这样的任务应当由经济学家(以及社会主义学家)来完成。然而,经济学家并没有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为依据,对“中国特色”作出科学说明,更没有提出一个科学范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可以降低人们对中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过高期待,有利于纠正超阶段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形式。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定位在何处,没有给出确切的定性,而文献本身的解释又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把中国现阶段解释为“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从而将其置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另一方面又被说成“不发达阶段”,社会主义还“不够格”。一方面说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即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另一方面又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澄清和消解这个矛盾的任务,同样落在了经济学家的身上。但是,一些经济学家的解读不仅没有澄清矛盾,反而在文献的基础上退步了,把特殊的概念变成了一般概念。总之,在这两个概念中,一方面把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社会主义画等号;一方面又把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始终没有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给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解释;始终没有从理论上把产生于落后国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直接对立物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区别开来;甚至也没有把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区别开来。
四是对改革中形成的现实经济关系和社会形态的理论概括不够准确。对改革中形成的经济关系如何从理论上加以概括,不仅关系理论的科学性,而且关系对改革实践指导的正确性。我国的改革是由中央主导的,一些重要概念必然首先出现在重要文献中。问题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在事前和事后都应当负有重要责任:事前作为理论顾问需要提供科学的咨询;事后作为专家、教授和学者需要进行准确的诠释和解读。实践证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没有真正尽到应尽的责任。除了前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重要概念以外,还有许多经不起推敲的概念和判断。例如:把我国的市场经济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市场经济说成是资源配置的方法和手段;认为我国“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了“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等等。由这些概念和判断衍生出来的概念还有:把“资本”概念一般化和物质化,将其用于所有的生产方式,并将其和生产的物质要素等同起来;把雇佣劳动说成是“合同劳动”,把私营企业中的劳资关系说成是“合作关系”或“劳动关系”;把股份公司这种资本组织形式和企业形式说成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把资本主义的企业经营制度(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和所有权相分离;企业主和其代理人相分离,形成股东大会、董事会、总经理的关系)说成是超生产方式的“现代企业制度”;把私营企业主这种人格化的资本说成是“新的社会阶层”;等等。到目前为止,理论上始终没有把市场经济理解为一种历史性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没有在理论上确认已经普遍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伴随的一系列经济现象——经济分化、制度性失业、阶级、剥削、经济危机等等。
五是对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及其根源的认识不够准确。近20多年来,我国普遍存在和反复出现的主要经济社会问题是:经济失衡、虚假增长、民生难题、贫富悬殊、蕴含危机、腐败丛生。但是,一方面,经济学家并没有说清楚哪些问题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哪些问题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并没有从现实的经济关系出发寻找问题的根源,既没有从市场经济形式本身寻找一般原因,也没有从中国现实的经济关系寻找特殊原因,更没有从改革发展中的偏差和失误中寻找原因,而是把问题归咎于诸如“初级阶段”、结构性问题、分配关系、外部冲击,以及所谓“三期叠加”和“中等收入陷阱”等等。
六是对发展和改革总体思路的认识不够准确。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出现两个有质的差别的提法: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所涉及的主要是经济管理体制,核心是扩大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自主权;二是“第二次革命”,和先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相提并论。前者是对“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为补充”的概括;后者是对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概括。“第二次革命”的对象应当是革解放后我们自己开创的超阶段的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及其计划经济体制的命,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可以认为,这是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形式的“自我变革”。改革自然包含两个层次: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但是,经济学家认为(至少是默认)市场经济只是资源配置的方法和手段;而改革的思路不涉及所有制关系的变革。因此,改革无非是“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改革思路可概括为两点:一是国有企业实行类似于农村的责任制(承包制);二是通过全民所有制内部的交换建立经济联系。二者的统一就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正是以这种“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为前提,进而得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没有根本矛盾的结论。当时能够提出这种改革思路,已经难能可贵。但经济学家应当知道,这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而是在国有经济框架内调节利益关系和利用市场机制。不仅如此,经济学家对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望文生义,进一步加以抽象和一般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本来就应当是市场经济。十四大以后的改革,和邓小平所说的改革思路有质的区别,只是经济学家仍然把市场经济说成是“方法和手段”,把改革仍然说成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但改革涉及到所有制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包含着私有制经济和雇佣劳动的自由发展,大量公有制经济的私有化或者民营化,实行国退民进和简政放权,经济关系的市场化,公有资产的资本化和资本的人格化,引进西方国家的企业制度和劳动制度。总之,实际的改革就是让资本在社会经济中起支配作用,以利润最大化为直接目的。这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个基本特征。显然,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区别只是在于,国有经济在改革中,出现了普遍的政商不分、官商结合、行政性垄断的情况。然而,经济学家和改革家们却把改革称之为“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改革的核心被说成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他们应当知道,“市场化”就是资本化;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资本起决定性作用。这种理论认识和概括,带来了两个严重的消极后果:一是在“市场化”和“产业化”这种表面化形式的掩盖下,几乎所有的产业和事业(包括教育和医疗)都成为资本的特殊投资领域,公有资产全面资本化,经济社会关系变成普遍的交易关系。二是一般意义的“市场化改革”,根本不能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经济学家把“社会主义因素”交给名不副实的虚幻的“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去体现。
(三)中国政治经济学界主要的倾向性理论观点和学派
目前,中国政治经济学界主要有四种倾向性理论观点和学术派别:
一是承袭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遗产,具有保守的或“左”的倾向的经济理论。对改革开放有疑虑、有保留,甚至明确反对市场经济。
二是号称“三超越”(超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超越传统政治经济学、超越西方经济学)的“现代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调和论和折中主义倾向的理论观点,力图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学融合起来,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寓于市场经济之中,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形式结合起来。所有背离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观点,都标榜为“理论创新”。这种观点是贴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标签的中国版的庸俗经济学。它的左翼只是限于空谈,而它的右翼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
三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名行篡改马克思经济理论之实。为了同“市场化改革”相适应,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名义下,全面任意解读和修改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重要范畴和观点(包括公有制和私有制、个人所有制和社会所有制、社会主义、股份公司、商品生产、价值、资本等等),随心所欲地断章取义和指鹿为马。实际上不过是伪装起来的西方庸俗经济学。
四是全面照搬照抄具有“新自由主义”倾向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其主要特征是从资源稀缺讲起,从人的自私本性出发,以私人产权为前提。这种理论观点虽然并没有直接进入官方文件,却已经广泛进入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大专院校的课堂。现在的青年学生所接受的教育,基本上是这种完全“西化”的经济理论。
上述四种观点和学派都不同程度地背离和否定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其中,从第二种到第四种都属于庸俗政治经济学。到目前为止,真正科学揭示中国道路经济运动规律的政治经济学,只是以幼芽的形式存在,并未引起社会的重视;只有通过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幼芽才能够茁壮成长,并成为主流形式。
三、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反思和回答的问题
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在认真反思的基础上回答:中国为什么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什么关系;中国为什么必须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什么;中国目前处在人类社会的什么阶段,是第三阶段还是第二阶段。
(一)需要重新审视和界定的几个重要概念(范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邓小平作为政治家提出的一个决定中国现阶段制度定位、改革方向和现代化目标的概念,也是一个同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传统社会主义保持距离的概念。但不能认为这是一个规范和内涵确定的理论范畴。我们知道,人类历史的各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原始共同体)、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都用一个科学的范畴加以概括,其中的关键词——原始、奴隶、封建、资本、共产——都表明了社会形态的特殊性质。我们同样知道,自从“社会主义”这个概念问世以来,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无论是否科学和可行,都有一个表明其主张和内涵的概念。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和基本特征是什么?也应当用一个科学的理论范畴加以概括和表述。党的十八大报告把“中国特色”概括为“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但人们还是搞不清楚,“中国特色”表明的是什么性质、内涵和关系。其中,“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都不可能把不同性质的社会形态区别开来。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从理论上明确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下述的哪一种:第一,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形式或具体形式;第二,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之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中的一种新的形式;第三,作为一条落后国家通往社会主义社会目标的新的途径或道路。进而必须明确回答: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什么关系,它是否已经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定和基本特征;第二,它和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传统社会主义以及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例如民主社会主义、拉美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如果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过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形式或具体形式,那么,政治经济学就必须对实践和理论之间的矛盾作出解释。是理论错了,还是实践偏了。其实,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的不过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形式或具体形式,那么,“中国特色”也就没有理论意义了,变成了一个没有概念的“概念”。这是因为,抽象理论和具体实际的不一致,同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发展道路之间的差别,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本身并无不妥,关键是这里的“社会主义”指的是什么。第一,如果确认中国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而科学社会主义不过是共产主义的同义语,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第二,如果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区别开来,把社会主义社会理解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这是列宁的说法),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这也是邓小平的意思)。但这两种说法并没有质的区别,都包含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之中;区别仅仅在于,我们在第一阶段又划分出一个“初级阶段”。但是,只要没有改变第一阶段的质的规定性,这样的划分是毫无意义的。可见,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表达的内涵是什么。如果要表达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不发达阶段”,那么,这个“初级阶段”就不能包含在“第一阶段”之中;因为“初级阶段”的内涵同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是有矛盾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为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结果和直接对立物,不可能是一个不发达阶段。既然“不发达”是当代中国的现实,那就不能将其划入社会主义社会。“不发达”仅仅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后发展国家相联系,而同社会主义社会毫无联系。反过来,如果从理论上确认中国现阶段已经是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那么,这或者意味着,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或者意味着,我们已经从理论上改变了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和理论标准——社会主义可以是“不发达”的,这无异于在理论上承认“穷社会主义”。无论如何,我们都在理论上陷入困境。走出困境的出路无非是两个:一是确认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仅仅同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相联系,并不表明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但这也就否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本身,其真实涵义不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级阶段”。二是重新定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使之适合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后发展国家;但这也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本身,也否定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既定的前提,那么,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就必须从现实的经济关系出发作出判断:当代中国是处在人类社会的第二阶段还是第三阶段?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所特有的,还是一般社会主义国家都会有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级阶段,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是经济理论界的创新,是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而权威的表述来自邓小平。但对于这个概念,理论界一开始就有不同的解读:一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二是“社会主义阶段的市场经济”,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人们强调的重点也不同:有的强调“市场经济”,有的强调“社会主义”。最重要之点在于,这个概念的提出者如何理解“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如果认为市场经济不过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法和手段,那么,“社会主义”是什么,就无关紧要了。但是,无论是主流的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都没有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看作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在主流的西方经济学那里,尽管把资源配置看作是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但始终把自由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同义语。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那里,尽管那个时代还没有提出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但明确地认为,普遍化的商品生产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可见,“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这个提法就站不住脚了。如果不能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方法和手段,而是看作一定的经济关系,看作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在交换方式上的表现,那么,“社会主义”是什么,就至关重要了。如果确认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市场经济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同义语,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就不能成立了。进一步说,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没有根本的矛盾”也就不正确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是否具有科学性,“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没有根本的矛盾”这个提法是否正确,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进一步的问题是,对于当代中国采取市场经济形式的必然性如何认识,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同样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形态的性质。也就是说,能不能在理论上把当代中国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阶段”。如果作出肯定的回答,就和市场经济不相容——除非重新定义社会主义。可见,“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阶段的市场经济”的提法,同样是站不住脚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也不是社会主义性质(或者社会,或者阶段)的市场经济,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阶段这种特殊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
上述几个概念有一个共同特点:一方面和高于资本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和市场经济(商品生产的普遍化)、生产力不发达状态联系在一起。这就必然使概念陷入矛盾和混乱之中。
(二)需要甄别和重新确认的几个判断
关于“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个提法见诸重要的中央文献,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改革不是要改变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改革带有修修补补或者改良的性质,不包含任何革命的因素;三是改革的动力不是来自制度外部。在我国改革之初,在“计划经济为主”的年代,这个提法还是可以使用的。如果把市场经济理解为“方法和手段”,如果认为改革“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那么,这个提法并无不妥。但是,按照邓小平关于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的定性,所谓“第二次革命”,就是要革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及其体制的命,或者说是“扬弃”,而且带有根本的性质。从改革的实践来看,经过30多年的改革,经济关系出现了如下重大质的变化:借以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成分和因素——公有制经济、联合劳动或合作劳动——大大减少;私有制经济,尤其是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则大大增加;金钱关系和资本关系已经渗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因此,还能不能把改革称之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中国的政治经济学需要作出明确的判断。
关于“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党的重要文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和中国特色的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在中国的实践。但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认识并不统一。按照传统社会主义教科书的解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按照邓小平在改革中的解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方法和手段”,因此,社会主义的原则就是两条: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或者共同富裕,或者不发生两极分化)。在上述解释中,隐含着这样的内容:公有制形式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只要不是私有制就是按劳分配;国家垄断资源、统一计划和统收统支就是计划经济。即使是“穷社会主义”,也没有违背“社会主义原则”。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修正了社会主义原则,既不强调公有制,也不强调按劳分配,而是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P373)但是,这个概括并不严密。第一,任何一种新的生产方式,都可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但具有社会主义本质的只有一种生产方式;第二,在个体小生产方式中,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也不存在剥削和两极分化,但并不包含任何社会主义因素;第三,共同富裕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标志,西北欧的“福利国家”也可以做到。上述关于社会主义原则的论述,都属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原则”,都没有超出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狭隘眼界。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特征应当是:实行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的社会所有制,共同生产和联合劳动,物受人支配,实行直接的劳动交换(消除商品生产,消灭阶级),社会生产实行统一组织和有计划的调节(不再由盲目的自然规律调节),每个人都可以占有全部生产力,以直接使用价值为目的。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即使按照“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原则”来衡量,从经过30多年改革的结果来看,我们能说“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吗?如果真的坚持了社会主义原则,还会普遍存在私有制、资本和雇佣劳动吗?还能够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吗?就总体而言,当代中国所坚持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还是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等价交换、资本增殖、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必须作出判断。
关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两个主体”这一始终不变的提法,跨越了两个时代:从“计划经济为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所有制关系居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这可能吗?经济学家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作出判断。从理论层面说,市场经济究竟能不能建立在“两个主体”的基础上,必须作出有理有据的明确回答。我们必须首先把基本概念搞清楚。什么是公有制,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什么是按劳分配?按照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公有制有不同的历史形式,不是任何公有制都包含社会主义关系。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是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实行共同生产和联合劳动,以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反过来说,个人占有或者私人股份、个体劳动和雇佣劳动、以交换价值或剩余价值为目的,就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从实践层面说,“两个主体”在我国究竟还是否存在,必须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强大压力下,经济理论界对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解释,可谓节节败退,越来越放宽尺度和降低标准,现在几乎面目全非了,美其名曰“新公有制”和“市场型按劳分配”。股份制=公有制,公有资产法律所有权占优势=公有制为主体;一切劳动者报酬(劳动收入)=按劳分配。这是自欺欺人。按照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政府代表的公有制不等于共同体中的公有制。国家所有制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身和基础,但国家所有制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资料(包括土地)的法律所有权和经济所有权已经分离的公有制,至少不再是完整的公有制经济;如果公有资产的法律所有权在经济上不能实现,公有制就会变得有名无实。公有资产占优势不等于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仅仅同社会所有制和联合劳动相联系。劳动者报酬和劳动收入存在于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在市场经济中,劳动者报酬是雇佣劳动者劳动力价值的表现,是以为资本提供剩余价值为前提的,根本不属于按劳分配。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出科学判断,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否要求和能不能做到“两个主体”。
(三)需要在理论上科学回答的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问题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人们整天都在讲“社会主义”,但其中的内涵大不相同,甚至相去甚远。有的把公有制、国家(政府)和社会主义画等号;有的则把“社会化”“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利益共享”等同于社会主义。如果对“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各说各话,形不成共识,研究讨论就会南辕北辙。邓小平关于改革和发展的许多论述,总是从“什么是社会主义”开始。他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6](P137-138)他还说,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6](P63-64)后来,他又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P373)邓小平谈论“社会主义”,一方面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一方面立足于中国贫穷落后的现实。因此,他始终把“消灭贫穷”“发展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相联系。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第一,经济学家不能对邓小平的话各取所需,各执一端——或者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或者强调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第二,经济学家不能到此止步,不能局限于落后国家的现实和发展道路理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从质的规定性上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上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非常重要的。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不断有人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阐述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提出质疑,甚至认为包含着空想成分。他们用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实践检验科学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社会所有制、消除商品生产、社会统一组织和有计划的调节、没有商品交换的按劳分配,都是脱离实际的空想;而现实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生产方式、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只能是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他们认为,只要坚持公有资产(所有权)占优势、国有经济掌握经济命脉、劳动收入为主,就是社会主义。更有甚者,认为只要是能够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在这种“现实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财富和价值是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等要素共同创造的,不管收入差距如何大,都不存在剥削问题(如果讲剥削,劳动也剥削资本),也不存在阶级。这种认识不仅包含着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性颠覆,而且包含着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的根本否定。对社会主义的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吗?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属于人类社会什么阶段。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定位,决定生产方式、经济关系和社会形态的性质,决不能含含糊糊、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更不能出现误判。这对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更加重要。定位的重要性首先来自对我国现阶段经济形式(交换方式、资源配置方式)的判断——是产品生产还是商品生产;是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在改革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党的十三大报告系统地阐述了这个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定位在何处,没有给出确切的定性,而不同的权威解释又充满了矛盾。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必须明确回答:第一,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是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当代中国有没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意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第二,这里所说的“初级阶段”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级阶段”;第三,这个“初级阶段”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还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第四,按照马克思对人类社会阶段的划分,当代中国是处在第三阶段还是第二阶段;第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起始阶段,还是一种独立的和资本主义并存的社会形态;第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所说的“第三种形式”是什么关系。如果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初级阶段,那么,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经济关系应当是怎样的?在当代中国现实中,存在这样的关系吗?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生产方式并存也可以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经济关系吗?
中国现阶段合乎规律形成的经济关系应当是怎样的。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关系同所处的历史阶段相一致。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应当明确回答:按照所处的历史阶段,按照客观规律,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关系总体上应当是怎样的?是以社会共同体经济、联合劳动关系为基本形式,还是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本形式?我国现阶段是否具备“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条件,是否应当和有可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中国现阶段是否已经没有阶级和剥削存在的条件?如果认为没有,对普遍存在的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又如何解释?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一事实是否可以表明,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跨越论”如何解释现阶段的经济关系?在中国现阶段,在社会主义因素和市场经济关系、公有制和私有制、资本和劳动之间,应当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平衡关系?何者必然处于主导地位或主体地位?中国现阶段经济关系的“普照之光”是什么?当代中国和西方国家是什么关系?是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大量依赖出口商品和对外巨额投资的实质是什么?驱动力来自何处,是主要来自资本,还是来自国家利益,或是来自国际义务?这种情况和过去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输出、资本输出有没有质的区别?
如何科学认识改革发展中新出现的种种严峻问题。从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出发,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回答,我国改革发展中新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主要是什么?属于什么性质?其根源(经济、社会、理论)是什么?第一,我国是否出现了同市场经济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两极分化、相对或绝对贫困、失业和经济危机。第二,我国出现的经常性经济失衡、产能普遍和严重过剩、经济运行恶性循环、资源和生态环境恶化、领导干部腐败丛生,等等,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结构性的、周期性的、技术性的,还是制度性、体制性、机制性的,或者是改革发展中的偏差和失误所致?上述种种哪些是可以避免的,哪些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可以避免而未能避免?中国的经济问题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方式、调控政策有没有直接关系?中国现阶段有没有发生经济分化、相对贫困、工人失业、经济危机的必然性?马克思的《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规律的一系列论述,特别是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理论、资本竞争理论、虚拟资本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等,对当代中国是否适用?“以速度为中心”的发展方式是怎样形成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难以转变?是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还是不端正的指导思想和包含弊端的体制造成的?“市场化改革”的涵义和实质是什么,是不是全面的商品化(包括所谓的“产业化”)、价值化、资本化?这种笼统的提法是否科学,是否适合于中国?这种改革思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是否一致?按照这种思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是否能够体现?以什么方式体现?能否一般地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质的区别在哪里?就实质而言,我国现在的经济关系是否体现了这种区别?
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立足点和主要任务是什么。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区分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资本的政治经济学、财产的政治经济学和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可见,立足点是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主要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和发展趋势,为从资本主义转向共产主义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足点和主要任务是什么,在阶级性上如何把握?应当着重为什么服务,是着重为资本、为政府服务,还是着重为劳动服务,或者三者如何兼顾?是否应当坚持“公私并存、社资兼有、劳资两利、当前和未来衔接”的复合经济制度和过渡性经济关系?进一步说,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是着重揭示当代中国经济运动的规律性,为改革发展、现代化和实现“中国梦”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并指点未来的发展方向,还是单纯为发展市场经济、资本增殖和摆脱当前的困境服务?与此相联系,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学习《资本论》,现实意义在哪里?我们应当从《资本论》中学习和吸取什么?
四、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实行根本性变革
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鉴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存在很多根本性缺陷和问题——或多或少偏离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存在诸多不准确和庸俗化倾向,在使用基本范畴方面不够严谨和科学,对改革中形成的重大经济关系判断不够准确,一系列重大问题有待于作出科学回答,因此,对中国主流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实行根本性变革。变革的基本理论依据应当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由于中国道路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存在“非此即彼”和“亦此亦彼”同时并存的特殊性质,因此,当代中国在坚持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或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的前提下,不能不容忍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资本的政治经济学、财富的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层次存在;在首先为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服务的同时,也为“资本的生产力”服务。
(一)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为指导
坚持以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既是纠正超阶段错误的理论依据,也是扭转西方经济学泛滥状态的有力武器。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必须正确地总结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不能把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偏差和失误归咎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决不能在想当然和先入为主的基础上,宣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已经“过时”,或者存在“空想”,或者宣布为“谬误”。
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学者必须系统地、原原本本地重温、研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经典著作,首先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必须把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和“一个科学结论”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深刻领会,消除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种种误解。
当代中国的经济学家必须坚持“科学上的诚实”精神,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重要范畴和重要观点,应当怀有敬畏之心,决不能出于某种超科学的需要而望文生义(例如,对商品生产、个人所有制、普照之光等等的望文生义),轻率地、随心所欲地重新解读,更不能断章取义、恶意曲解和指鹿为马。对于已经进入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工程”、中央文献的错误解读,必须加以清理,正本清源。
当代中国的经济学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为指导,在以新的实践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同时,着重揭示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产生、发展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性,科学说明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现阶段社会形态、经济关系的性质,以科学的理论成果武装广大青年学生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起来以后,在“市场经济一般”的层次上,在营利性、竞争性产业领域,在微观经济领域,在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关系范围内,在为资本增殖服务的领域,政治经济学仍然会继续吸收和运用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思想;但绝不是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学“融合起来”,不伦不类。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和“一个科学结论”,始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指导。
总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从人类社会的第二阶段出发,必须立足于既包含非此即彼又包含亦此亦彼的特殊发展道路的现阶段,必须兼顾历史任务的共同性和实现形式的差异性;必须把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纳入到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之中。
(二)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决不能一味地照抄照搬
在以往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中国的政治经济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盲目照抄照搬的问题。
在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期,主要照抄斯大林主导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照搬苏联的体制模式。在“跨越论”指导下,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名义,把“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划分为对立的和互不相干的两个部分:“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资本主义是过去,是西方;社会主义是现在,是东方。这种划分,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统统排除在“社会主义社会”之外,把同一阶段的两条道路绝对对立起来;另一方面混淆了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现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质的区别。
在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后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学界的改良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或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盛行,特别是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中国政治经济学照抄照搬苏联东欧力主改良的经济学家的论著成为一种时尚;其核心是,力图在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内部引入模拟市场机制。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新阶段,经济学界的主流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纷纷抛弃传统社会主义和苏东国家改良主义经济理论的同时,盲目地、不加鉴别地、铺天盖地地照抄照搬现代西方经济学(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并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束之高阁,或者以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教科书”都不过是穿靴戴帽。
所有的照抄照搬都是不成功的。基于历史的教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改变过去照抄照搬的传统,实行真正的理论创新。但创新必须讲究科学。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创新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在已有的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分析中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分析各主要阶级和阶层的利益诉求,对现阶段先进生产力的主要承担者(从而处于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作出准确的判断,把市场经济形式及其经济关系纳入中国道路之中,把中国道路的现阶段和共产主义的前途,以“直通车”的方式衔接起来。
(三)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不能变成懒惰的“注释经济学”
改革开放以来,很多经济学者(包括专家和教授)不是以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为指导,从现实经济关系中抽象出规律性的认识,不是为改革发展提供科学的基本理论依据,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从字面上解读、注释中央的报告、决定和领导人的讲话上。这种“解读”只应是整个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政治决策者从问题出发,求教于个别高参顾问,然后作出判断和形成政治决策,进而由文献起草班子以理论化的形式将政治决策写进中央文献。这时候,经济学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中央文献进行解读。这就是所谓“解读经济学”。一般的解读只对文献负责,而不管文献的提法是否准确和科学。即使错了,也只是将错就错,等待以后制定新文献时再作修改。有些解读和注释具有明显的各取所需、断章取义、为我所用的性质(例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解读,有的侧重于“市场经济”,有的侧重于“社会主义”);有些解读则具有投其所好、牵强附会、戴高帽子的特征。解读和注释确有一定的必要性,但这不应当成为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这样的任务主要属于政策制定部门和宣传家。有的解读和注释包含着明显的负面结果,把一些具有时效性的结论,一些不严谨、不准确、不科学的提法(概念和表述),理论化和固定化了,甚至变成了绝对真理。偏重于解读和注释,败坏了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名声。给人们的印象是,经济学家总是随波逐流,看风使舵,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讲计划经济引经据典,讲市场经济头头是道,永远是正确的。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必须力戒懒惰的“注释经济学”。
(四)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从考察现实的生产方式入手
离开生产方式谈论所有制和生产关系,是从传统社会主义时代开始的,来自斯大林的观点。一方面,离开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谈论所有制形式,把所有制变成了单纯的生产资料归属问题,把国家所有制和政府所有制(以政府为代表的公有制)等同于公有制,进而把这种公有制和消灭私有制等同于社会主义;另一方面,离开生产方式谈论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好像政府占有生产资料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之所以能够“雷打不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之所以能够提出,就是因为离开了生产方式谈论公有制、生产关系和按劳分配。在改革以前,由于对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加区分,因而把生活富裕、私有制、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由生产方式决定,并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所有制不是单纯的生产资料归属问题,而是劳动和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总和;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总是一定生产方式中的关系,是由生产的社会形式决定的;分配关系不过是生产关系的背面和表现。因此,决不能离开生产方式,抽象地谈论所有制、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同样,也不能离开生产方式说明经济社会问题及其根源。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完全在于生产方式;之所以发生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完全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
(五)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应当认真总结改革发展的经验教训
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感性认识、政治决策不能代替经济理论。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和“跟着感觉走”的;无论是事前还是事后,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没有确切和充分反映改革的实质和经济关系必然发生的变化。政治经济学必须从理论上说明,一方面,经济体制的转变,即经济形式、交换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本质上是所有制关系、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转变,而交换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不过是上述转变的表面层次或外部表现。因此,仅仅改变企业的经营方式(实行责任制),仅仅改变全民所有制内部的交换方式,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经济体制的转变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发生的,转变的结果不能失去必不可少的社会主义因素,变化的只是社会主义因素体现的载体和方式。因此,把市场经济的一般内容全部照搬到中国来,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都需要反思,总结经验教训。
中国改革的重要教训之一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至今没有从理论上说清楚,中国道路的实质和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类提法,所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是想降低科学社会主义的标准、改变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模糊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还是为了安抚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及其体制的维护者,以减少改革的阻力?不得而知。但现在总应该说清楚了。否则,任何涉及“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理论研究,必然是各说各话、南辕北辙。与此相联系,中国政治经济学始终没有从“超阶段”这个要害之处总结传统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而是仅仅把问题归结为“计划和市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中国改革的重要教训之二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和改革决策者至今没有从理论上说清楚市场经济的本质,而且前后矛盾,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开始,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方法和手段,把全民所有制内部的交换等同于市场经济,力图把市场经济直接嫁接在经营方式稍加改变了的传统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责任制)的基础上。这不可能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后来,随着交换价值的发展,交易关系无孔不入,渗入各个领域,不断地瓦解公有制经济,市场经济开始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在改革派的主导和推动下,中国走向全面的“市场化改革”之路,不仅国有经济加速度地资本化,而且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领域也趋向产业化、商品化、市场化、资本化。但是,市场经济仍然被说成是“资源配置的方法和手段”,从而掩盖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市场经济是以扭曲的方式发展的:一方面,官商结合和权钱交易司空见惯,政府机构和国有经济职能出现不同程度的异化现象;另一方面,资本越来越成为流通领域的投机资本,虚拟资本泛滥。于是,社会主义因素被抽掉了,但在理论认识上却毫无警觉、麻木不仁。如果现在还不想说清楚,将悔之晚矣!
中国改革的重要教训之三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和改革决策者没有从理论上真正搞清楚,政府机构和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至于,“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因素”失去了物质载体和实现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特殊变成了“市场经济”一般。开始,政府仍然执行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职能,资源配置的权力仍然主要掌握在政府手里;后来,又在“简政放权”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名义下,把政府职能等同于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一般职能,从而放弃社会主义因素重要承担者的职能。开始,把国有经济的改革局限于国有企业内部的改革,改革主要是以授权经营的方式模拟资本机制;后来,企业的“管家”和“国家雇员”变成了真正的主人(企业主),变成了资本的人格化,国有企业越来越成为独立的垄断资本集团——一方面经济所有权独立于国家,一方面对整个行业形成行政性垄断,社会主义因素重要承担者的职能消失了。不仅如此,在“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中,国有企业中党的领导地位被边缘化了,变成了配角和随从。如果人民政府和国有经济都不能成为体现社会主义道路和因素的载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就不能成立了。
中国发展的重要教训之一是:中国始终没有真正放弃以速度为中心的发展思路。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经济增长速度放在首位和核心位置,为此制定了一系列向有利于提高速度的产业和领域倾斜的经济政策。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速度为中心的指导思想,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两极分化、城乡分割、经济失衡、经济危机等等。很多经济学家对此提出质疑,但确有一些经济学家(尤其是综合经济部门的经济学家),反而为这种发展思路提供理论支撑——潜在增长率论、通货膨胀有益论、重化工业发展新阶段论、以高速度保就业论等等。中央曾多次试图探索“新的发展路子”,先后提出“转变企业经营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等,直到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新的发展理念,但贯彻落实都遇到很大阻力,总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现在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五项任务,但在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那里,“去产能”和“去库存”只是虚晃一枪;在金融领域,“去杠杆”反而变成了“加杠杆”;“降成本”变成了转嫁负担。与此同时,某些利益集团又在制造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以速度为中心维护的是资本的利益,以及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的特殊利益,和以人民为中心是背道而驰的。
中国发展的重要教训之二是:中国的经济运行始终没有摆脱“膨胀-收缩-再膨胀-再收缩”的恶性循环。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经济发展经历了多次反复,总是从过度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投资膨胀、货币过度投放、经济过热——开始,从而引起通货膨胀、资产泡沫、资源紧张、环境破坏、金融风险;于是,不得不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当增长速度有所下降时,就在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反对下改变政策,转而实施“投资拉动”的扩张性经济政策,并在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制造虚假的繁荣,国民经济“高位”带病运行。每一次问题突出的时候都有清醒的认识,但最后都是旧病复发。其实,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只是饮鸩止渴。经济学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根源是三个层次的:一是以速度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式;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基本矛盾和内在限制;三是“市场化改革”中的偏差和失误。这三者的合力不仅导致资本的过度积累,而且导致社会财富快速集中于极少数投机资本的人格化手里,造成了广大普通居民的消费能力远远小于资本的扩张能力和生产能力。
(六)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可以初步表明的判断和认识
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经济关系十分复杂,和经济运动的一般规律交织在一起的特殊规律,还在探索之中,但有些问题已经基本清楚,可以作出判断,并上升到理论认识。
1.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过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一种典型形态。对于中国来说,民族特色、历史特色固然不能忽视,但最主要的是,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所显示的特殊性。所谓“中国特色”本质上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社会主义”只能作为资本主义的直接对立物来理解。的确,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应当更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一定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两极分化和消灭贫穷的社会。但是,不能反过来说,凡是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凡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不出现两极分化、消灭了贫穷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孕育和脱胎于资本主义,高于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新的社会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作为资本主义直接对立物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比,是不同历史条件、不同历史形态、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体现的只是同一发展阶段的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跨越论”是不正确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不具备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但可以在不同的发展道路上完成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的历史任务,可以走一条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第三种形式。“道路”和“制度”不能混为一谈或者画等号。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是直接对立物,但同一阶段中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并不是直接对立物(虽然有一定质的区别)。中国道路有借鉴的价值,但不可能成为一种任意复制的模式。这条道路的政治前提是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而其经济社会基础是代表劳动大众利益的人民政府和掌握经济命脉的国有经济。
2.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过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道路的初级阶段”不同于“社会主义形态(制度)的初级阶段”。中国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将处于人类社会第二阶段——物的依赖关系阶段,而不是第三阶段——自由联合关系阶段,或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这是一个相当长的独立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是资本主义道路的替代形式。从建立新中国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之前,都属于这个阶段。这条道路的现阶段,和资本主义国家大体处于同一个阶段。两条道路既存在一定质的差别,也会存在某些相似性和共同点。其经济关系和政治形式除了存在非此即彼,还会存在亦此亦彼。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含在社会主义道路的奋斗目标之中,但在这个初级阶段原则上是不适用的。中国过去之所以犯超阶段的错误,就是因为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套到中国现阶段来。中国道路现阶段的经济关系具有过渡的性质,因而和某些非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具有类似性;但它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预备阶段,和形形色色的非科学社会主义有质的区别。
3.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过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道路)现阶段(这种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包含着用商品生产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作为资本成为商品;也就是说,包含着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市场经济不过是西方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表面化说法。市场经济不可能存在于作为资本主义直接对立物的社会主义社会,但可以存在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初级阶段,可以是包含一定社会主义因素的市场经济。中国现阶段的交换方式和经济形式,只能是普遍化的商品生产或市场经济,而且,只能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中发展。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不确切,没有表达出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关系,容易发生误解,容易导致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否定。无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何解释——“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阶段的市场经济”等等,都是不确切的,既混淆了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也误解了市场经济的实质。
4.所谓“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两个主体”都与事实有出入。对中国现阶段的所有制关系和生产方式不能估计过高。就形式而言,“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在“计划经济为主”的时代,基本上是成立的。但转向市场经济以后,这两个判断都是从“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市场经济是方法和手段”这两个假设前提推导出来的。但实际上,这两个假定都是有问题的。我国并没有进入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那种意义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只是走上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的路——社会主义道路,目前处于这条道路的初级阶段(关于这一点,党的十三大报告有明确的论述);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以普遍化的商品生产为载体、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以剩余价值为直接目的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式(对此,在党的十四大以前有清醒的认识,而后来却模糊了)。在中国道路的初级阶段,没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论依据,没有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理论依据。况且,中国现阶段必须采取市场经济形式,而市场经济的存在是以社会分工和产品属于产权独立的不同所有者为前提的(马克思认为,分工和私有制是同一种关系的不同表达方式)。在中国道路的现阶段发展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兼顾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必须同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和一般规律相适应,必须以中国自己的方式发展“资本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必须同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相适应,必须同时成为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基础。但是,在中国道路的现阶段,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共同占有、共同生产、联合劳动、消灭阶级、消灭剥削、以直接使用价值为目的)还不可能处于支配地位,社会主义因素主要不是通过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来实现,而是必须有新的载体和新的实现形式来实现。这种新的载体和实现形式就是执行双重职能的人民政府和国有经济。通过人民政府和国有经济的特殊职能作用,最大限度地维护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权益,并保障共产主义的前途。在这里,对老生常谈的“公有制”必须有科学的认识。公有制有不同的历史形式和不同的生产方式。公有制绝不是一个仅仅体现法律所有权的外壳。公有制是劳动者同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并占有劳动成果的制度保障。无论是私有还是公有,资产的法律所有权和经济所有权都应当在经济上得到实现。在商品生产和价值形式条件下,前者体现在利息形式上,后者体现在利润或企业主收入形式上。国有企业经过产权制度改革,国有资产的法律所有权和经济所有权分离了,法律所有权由政府机构代表,但这种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在经济上实现,基本上放弃了;经济所有权被经营者集团占有了,而且和雇佣劳动者相对立。这种公有制已经大打折扣了,甚至有名无实了。有鉴于此,所谓“公有制为主体”名不副实。问题还在于,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中国现阶段的公有制并不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劳动者报酬、劳动收入可以存在于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之中,并不等于按劳分配;中国目前基本上不存在真正的按劳分配(包括国有企业和南街村那样的“共产主义社区”)。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条件的深化改革中,不是要求既做不到又不需要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而是要求人民政府和国有经济必须以适当的形式执行体现社会主义道路和因素的职能。
5.中国改革的实质是纠正超阶段的错误和变革社会主义道路的实现形式。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要害是超阶段——所有制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形式都超越了必经的发展阶段。我们不仅要承认商品生产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而且要承认,作为商品生产普遍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把中国的改革称之为“第二次革命”是正确的(确切地说是“第三次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再一次革命),基本上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基本经济关系的否定之否定。这种革命主要是纠正两个方面的错误:一是把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等同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蓝图照猫画虎地照搬到社会主义道路的现阶段来。因此,把改革称之为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不确切的;把改革称之为“市场化改革”也是不正确的。基于这种认识,第一,中国的改革不能把市场经济建立在“责任制”的基础上;第二,也不能把改革的核心归结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从而不能一般地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从两个方面进行系统的反省:一是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经济;二是以速度为中心和反复持续地以扩张性经济政策应对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必须首先纠正“市场化改革”中的偏差和失误。自由市场经济在西方国家已经陷入困境,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基本矛盾和内在限制。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必须处理好五大关系:国有和私有;资本和劳动;政府和民众;政府和市场;城市和乡村。其中,最重要的是处理好资本和劳动、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在中国现阶段,必须保持社会主义道路(因素)和市场经济形式的平衡;资本和劳动的平衡;城乡之间的平衡。改革的关键是重新定位政府机构和国有经济的职能。政府和国有经济必须执行双重职能:一重是一般市场经济中的共同职能,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纠正市场机制带来的一部分消极后果;另一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特殊职能,作为体现“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因素”的载体。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必须为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创造制度条件。除了在总体上解决好“两个定位”以外,必须改变地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和在经济发展中的职能。地方政府不能成为市场主体,地方政府之间不应当形成市场竞争关系,不应当承担具体的增长目标。“全面小康”目标必须符合新的发展理念。最重要的是消灭贫穷(包含多重内涵的贫穷)和消除两极分化。完全不必和人均GDP、人均收入的翻番挂钩。
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必须避免发生下述三种情况: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贴标签和穿靴戴帽;对中国道路现阶段的经济关系戴高帽子;对西方经济学盲目照搬和随波逐流。
五、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所说的“方法”,不是技术性方法,而是科学研究和表述的方法,既涉及历史观,也涉及辩证法。
(一)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方法同样适用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首先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也是《资本论》的方法。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和导言中所使用的方法,在这里也是适用的。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的方法,总体而言就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或者说,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的辩证方法。在具体层次上,马克思运用了以下三个科学方法:一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也包含从本质到表面、从一般到个别的方法。这里的具体不是实例,而是抽象的具体)。二是从简单到复杂的方法(这里体现了发展演变的过程)。三是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本质上同样是历史的方法)。以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方法为指导,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值得遵循的认识。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撇开特殊的历史前提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逻辑起点和逻辑顺序,和《资本论》应当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有独特的核心范畴和逻辑体系。首先,必须说清楚“当代中国”的历史前提。在马克思那个时代,以英国为典型的西欧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地位和生产力基础已经是既定的前提,而且是自然形成的前提,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过程没有必要作为前提加以总结和论述。《资本论》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核心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和剩余价值),“普照之光”覆盖的其他生产方式可以抛开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运动过程的分析,划分为三个过程,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一个一个地揭示出来。首先是“资本的生产过程”。而生产过程从分析商品开始,因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细胞,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和基础。对资本的本质的分析,则从作为它的载体和表现形式的价值形式和货币开始。到此为止,真正的主角——资本,虽然已经包含其中,但还没有正式登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分析,是从劳动力成为商品或劳动力的买卖开始的,由此进入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生产出来以后,再转化为资本。这已经是再生产,而且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再生产。于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同时也是资本的生产。因此,资本不过是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其实,如果撇开从小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资本一开始就是前提。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积累,导致一系列社会后果,特别是贫困、失业、两极分化和经济危机。到这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和内在限制(特别是生产目的和实现手段的矛盾,资本的无限扩张和消费能力低下的矛盾;价值形式和活劳动已经微不足道的矛盾)已经清楚地揭示出来了。然后,由资本的生产过程转入“资本的流通过程”,转入资本的不断运动(循环和周转)和剩余价值的实现,转入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生产。矛盾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发展,生产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同按比例要求的矛盾,阻碍了剩余价值的实现。再然后,由资本的流通过程转入“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转入资本和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和具体形式,转入由竞争体现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表面,转入剩余价值的分配,进而转入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进一步暴露: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生产过程可以不需要资本家了;土地制度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制性因素;非生产阶级也参与剩余价值的瓜分。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是穷途末路了。
但对“当代中国”来说,历史前提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一系列革命的产物——包括推翻封建帝制的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因此,这个历史前提必须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当代中国经济运动的规律性。因此,政治经济学首先必须从“当代中国”讲起,必须从中国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讲起,着重说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当代中国的历史前提有两个:一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前提,也是新中国的历史前提;二是转向新型发展道路的历史前提,也是改革开放的历史前提。离开这个经过一系列革命变革形成的历史前提,一下子就进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虽然可以避开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但什么问题也说不清楚,连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正确性都说不清楚。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基础是改革的产物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基础,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也不是一般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传统社会主义道路”,而是“新型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中国为典型的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新型道路。因此,必须从对“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必然性的说明,转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必然性的说明。中国并不是一开始就走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是首先走上了苏联式的传统社会主义道路。这期间走了一段30年左右的弯路,是超阶段的,总体上是不成功的。在遇到巨大挫折和陷入严重困境以后,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经过扬弃,开始转向新型的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里,传统社会主义道路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身;而这个转变过程就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国目前的经济关系,不管是合乎规律的,还是背离客观规律的,都是30多年来改革和发展的产物。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建立在这个现实基础之上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对中国的现实基础作出分析和判断,必须对已经形成的理论概括作出分析和判断,直到得出规律性的认识。
(四)中国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来自中国道路现阶段的历史定位
改革的必要性来自对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经验的总结,而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则来自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来自对中国道路现阶段历史定位的科学认识。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性,首先必须确定这条道路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历史定位既决定了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也决定了当代中国基本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形式。在历史定位没有解决以前,改革有一定的盲目性(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历史定位主要决定于现实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所处的发展阶段,也决定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命力及其发展阶段的认识,决定于对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所需要的基本条件的认识。历史定位问题,关键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出理论上的说明,究竟处在人类社会的哪一个阶段。中国的特殊发展道路有可能影响现阶段的经济关系和实现形式,但不会根本改变历史定位。
(五)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以“五个区别”作为立论基础
一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和作为资本主义直接对立物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区别开来。后者作为完成形态至今还没有出现。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概念是从后者抽象出来的;而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只是前者。只有在作了这种区分以后,“社会主义”才可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简称使用。
二是把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区别开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当代中国(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制度区别开来。“道路”是实现目标的途径、路径、社会方式;制度是一定阶段具有质的规定性的经济关系的总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全过程,必然会形成若干有一定质的区别的发展阶段和经济制度。
三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初级阶段)区别开来。只有在作了这种区分以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可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初级阶段”的简称使用。
四是把人类社会第二阶段不同发展道路——主要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区别开来。这种区别不仅体现在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经济基础方面。
五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阶段具有过渡性质的经济关系和形形色色非科学社会主义(例如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区别开来。它们之间的类似性和共同点只是暂时的。
(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从现实的经济关系讲起
在阐明当代中国历史前提和历史定位的前提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进入它的“主体”部分——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涉及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等等。相对而言,历史前提、改革过程、历史定位只是造就当代中国现实经济关系的条件。政治经济学应当从哪里讲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有质的区别的。西方经济学是从资源稀缺、社会选择和资源配置效率讲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假定为合理的和永恒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从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讲起,任何生产方式都被看作是历史的。不过,在当代中国,长期稳定的经济关系,并不是单一的生产方式、经济关系和分配关系,而是多种形式并存的、混合型的经济关系;其中,每一种经济关系都会受到与之并存的其他经济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因此,《资本论》那种叙述方式:从商品、价值、货币到资本的逻辑关系,从生产过程到流通过程,再到总过程的理论体系,在这里是不适用的,是不能照搬的。当代中国需要根据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以及其他因素——国际社会的普照之光和经济秩序,未来的发展趋势,决定现实的经济(关系)结构。特别是必须把主导和主体关系确定下来,把实现形式确定下来。
(七)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需要把发展本身作为重要的考察内容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本身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和独立的意义。第一,对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来说,政治经济学不是为资本“敲丧钟”的,而是以相对特殊的方式发展“资本的生产力”;第二,通过改革形成的经济关系是否正确,主要看其是否同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第三,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实践证明,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还相当短视和肤浅。因此,在着重研究当代中国经济运动规律的基础上,还需要深入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即在总结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阐明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
[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N].经济日报,2015-11-2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郭彦英]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utlin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of Contemporary China
CHEN Wen-to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Economics,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Beijing 100091,China)
Writing a book o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of Contemporary China has been th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expectation to economists.It also serves as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of the circle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 theorists. The key to the book’s success relies on its guiding thought.The book on political economy should neither be the revised vers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itional socialist society(which consisted of the elaboration on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nor a simple combination of Marx’s Economic Theory and Western Economics.It can’t be a second edition of Western Economics under the name of“socialist market economy”.Taking basic theories of Marxism(“two great discoveries”and“one scientific conclusion”)as the ideological guideline,it must proceed from de facto economic relations in compatible with the productivity of China,on grounds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Based on our knowledge in general relationship of the second stage of human society,the book will help to reveal the special law of present economic activiti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temporary China;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de facto economic relations;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special law
F0-0
A
1674-0955(2016)05-0018-24
2016-07-10
陈文通(1941-),男,河北乐亭人,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