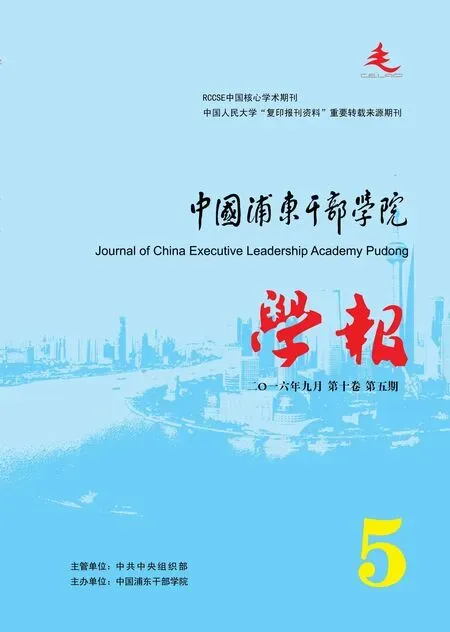关于建立“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几个重要问题
——当今的政治学概论
孙津,袁琳琳
(1.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5;2.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100871)
关于建立“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几个重要问题
——当今的政治学概论
孙津1,袁琳琳2
(1.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5;2.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100871)
从学科分类和知识结构来讲,既有的政治学就是西方政治学,其主要缺陷和弊端在于缺乏前提和自欺欺人,因此,有必要建立更具合理性、普遍性、现实性和解释力的“中国政治学”。“中国政治学”就是当今政治的理论形态,其学科的基本结构包括三个主要方面。其一,政治特性的本体形态就是设计、形成和运作“公共利益”的过程;其二,政治功能的目标旨向在于争取能够获得权力的多数;其三,政治机制的转换连接就是不同领域或方面的利益平衡和关系处理。
政治学;中国政治学;公共利益;社会联结
若干年前笔者写过一本叫做《社会政治引论》的书,在批评既有政治学的缺陷和弊端、并阐明“政治”的真实含义之后,明确提出有必要建构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政治学”。[1](P274)近一年来,学界也出现了一些类似的主张,表明建立中国政治学的确已经是一个现实需要了。但是,看似相同的要求,其实理解并不一样,相反却存在很多误解、偏向甚至错误。因此,有必要澄清认识偏向、指出为什么要建立“中国政治学”的根据,并说明“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含义和基本框架。
一、澄清几种认识偏向
在如何认识“中国政治学”尤其是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方面,当然会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看法,不过在我看来,当前最需要澄清三种主要的认识偏向。前两种由于其知识结构囿于既有的(也就是西方的)政治学而难以创新;后一种则由于逆反心理而缺乏知识运用的现实性。
先说第一种,也就是认为时代变了,中国强大了,所以需要建立“中国政治学”。比如,朱云汉教授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巨变时代”呼唤“中国政治学”》。①朱云汉的文章见《北京日报》,2016年1月25日第20版的“理论周刊”。文章正确指出,主流(也就是西方)理论存在“五种偏差与谬误”,即“当下主义、非历史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无政府主义倾向、国家中心主义”,所以“西方政治学对于现存世界欠缺批判能力”。然而这里的矛盾在于,朱教授一方面指出了主流理论的谬误和不中用,另一方面却还要在它的概念和范畴里打转转,并以此来充任建构“中国政治学”的道路设想,比如要求创设“政治正当性”的新选择、摒弃“民主”与“非民主”的二分法、更多关注广义的“良好治理”等。
造成上述矛盾或认识偏向的原因很简单,即不仅朱教授,而且几乎所有中国学者的知识结构本身就都是西方的。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强大实力举世公认,由此必然要求改变西方独大的局面,在世界新秩序中争取更大的话语权。但是,这种话语权的实质是一种力量(或者叫能力也行),而不是某一学科知识的内容表述和逻辑关系,所以这种呼唤“中国政治学”的主要根据及要求不过是一种“彼可取而代之”的心态。尽管力量大了可能有利于学科创新(包括政治创制),但仅此并不能为新的知识体系,尤其是其理论结构提供合理性,更不可能把这种增大了的力量就作为知识体系和理论结构的内容本身。因此,仅仅认识到西方政治学的弊端,也深感中国亟需增进,尤其是有效实施话语权是不够的,而且从最积极的意义上讲,由此提出的改革和建构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要求也是指“中国(政治)道路”而言的,还谈不上科学意义上的“中国政治学”——尽管这两者并不必定矛盾。
再说第二种,就是不满西方的话语统治,进而要求提出更能够解释中国政治情况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最明确表示这种看法的应该是政治学家杨光斌,而且他为此发表的文章也最多。②比如可参见杨光斌:《中国民主的巨变与走向》《用“国家治理”引领时代的话语权》《不做“合法性”概念的囚徒》,分别载于《北京日报》2015年4月13日第18版、2014年8月4日第17版、2015年11月23日第19版的“理论周刊”。杨光斌非常正确地指出,这一百多年来的西学东渐和统辖,使得中国的社会科学已经完全西方化,失去了由自己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构成的话语权,而在今天,中国政治学界简直就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一家之言”。其实,在我看来,不光政治学,显见的事实在于,只要是以现代学科方式来分类的知识,几乎统统都是西方的模式,甚至连中医理论和中国画理论也是如此,否则就可能被认为不那么“科学”。
但是,很难说杨光斌自己已经摆脱了西方政治学的知识结构桎梏,相反,他所要求的仍然是中国的话语权,而不是既有政治学本身的学科重构。因此,杨光斌认为中国今天正处在思想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新转型时代”,其标志是以中国为中心取向的“自主性”。在这种转型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是“中国的世界”,而不再是“世界的中国”。然而这样一来,不管出于多么良好的动机,总之仍然没有触动既有的政治学学科,所以也就难以提出什么新的概念和范畴。比如,杨光斌也反对民主和非民主的简单二分法,并且一直认为当今中国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治理,而治理也比民主更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综合指标。不难看出,这仍是在用既有的政治学解释新问题,而且所谓的“指标”也是西方的,甚至他所要发掘的民主“新常识”,其中的一个来源也是达尔关于“理论民主和实践民主”的关系及区分(在我们看来达尔不过是在做黔驴技穷的诡辩,不过此处不是理论的地方)。
简括地说,上述两种情况各有其合理的根据,但都不是严格学科意义上的理论创新。换句话说,这些认识的偏向都在于没有看到既有政治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所存在的致命错误,所以仍以此知识结构来承担建立“中国政治学”的要求。显然,这样不仅很难有什么创新,而且即使是针对新时代、新变化、新任务的各种新解释,也不过是在旧的知识体系中换个角度看问题而已,甚至是新瓶装旧酒。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该传承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和理论结构,并以此来建立“中国政治学”。这类看法主要在网上发布和流传。不过,问题并不在于文章是否公开或正式出版,而在于这类观点更多反映了一种逆反心理的中国中心主义,甚至是中国复古主义。其实,这种要求根本不可能做到,因为传统是可以延续的,但知识的分类学和言语形式却很难保持不变,更不可能重回古代。从实际情况来讲,不仅现在的人大多都不懂古代的概念术语,而且它们本身就歧义多多。
二、建立“中国政治学”的根据
前面说过,从学科分类和知识体系来讲,既有的政治学就是西方政治学,所以这一部分所谓的“根据”,就是具体指出既有政治学存在哪些致命缺陷和弊端,以至于必须在学科意义上重建一种政治学。缺陷和弊端当然是互为因果和互为表里的,不过相对说来(也为了表述方便),既有政治学的主要缺陷是缺乏前提,而主要弊端则是自欺欺人。至于为什么要把重建的政治学叫做“中国政治学”,将在第三节专门讨论。
先说主要缺陷,也就是缺乏前提,从而也就损毁了学科的普遍性。既有政治学在理解“政治”方面的最大错误就是故意隐去了前提,好像具体或真实“政治”的成立是不言而喻的。
事实上,政治的特性不像许多单向度或对象性以及一次性的活动那么固定,或者说那么容易把握。比如,只要有买有卖,或者用木料做几把椅子,经济活动或生产活动就可以确定无疑地成立了。不管一个人在买卖行为或生产行为之前、之中,以及之后怎么想,或者别人怎么看待他(或她)的行为,都丝毫不会改变这个行为的性质、内容、作用、特征。比如,五元钱能买两个苹果,一分木材能做两张椅子等,而且一般说来这种情况或量化标准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政治就完全不同了,因为所有意义和状态的形成都是可变的,而且同样的情况对每个人来讲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比如,当一个领导人对一份重要文件批示“可以”这两个字时,它的真实含义可能是同意、赞成、支持、怂恿、迫不得已,甚至一个陷阱。这种情况不仅使政治内容的生成具有不确定性和延时性,而且能够改变政治性质,比如变敌我矛盾为人民内部矛盾、由专门政治转为一般政治甚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地不成其为政治问题了。
我们把政治内容生成过程中人们可以言说和运作政治的各种要素叫做“社会联结”,它的存在和意义都优先于政治内容。与这个原则相一致且互为表里的运作机制,在于“政治生成”与“政治维系”的同时共存和相互作用。政治内容得以“生成”的根据,在于对社会联结的划分及其关系处理;现实政治的“维系”不仅以此为前提,而且就体现为运作各种社会联结所具有的意义或所达到的目的。由此,任何政治活动的成立,尤其是真实政治内容的生成需要一系列环节,比如至少包括政治内容、政治载体、功能关系、以及实效反馈等四个基本结构部分,其中每一个部分的实际功能都和其他部分密切关联。[2]
但是,上述政治的真实情况完全处于西方政治学的视野之外。简括地说,西方政治学先是指国家学,然后又讲权力学,其“政治”的存在和成立都是自明的;从美国提出“政治科学”以来,不仅把政治学几乎缩减为行政学,而且更加虚伪,好像那些尚不清楚的问题都已解决(或者作为形而上学加以排除),可以就政权(或政府)的构成和运作来做中性的分析了。其实,这种情况不是无知就是偏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为私有观念和私有制服务(对此这里没有篇幅来作理论),所以这种政治学不仅完全无法解释中国的政治,对于西方政治也是自欺欺人地说它要说的,隐去或回避它不想说的东西。
再说主要弊端,也就是自欺欺人。
前述所谓缺少前提的一个原因可能跟思维习惯有关,就是欧洲人好像总认为什么事物都有一种确定的存在,包括所谓“本原”,所以在政治方面主要关注实体性存在及其功能,比如城邦、国家、主权、权力等。但是,至少到了18世纪以后,一些政治功能被当作普适的道德价值了,所以就难免自欺欺人了,也就是表面上仁慈无私,实际上则是为了维护私有观念和私有制,所以就假装政治存在是自明的,不需要前提。
事实上,在洛克、卢梭、孟德斯鸠、康德等人那里,所谓天赋(其实应该说自然)人权、自由、公意、民主、法制、道德律令、公共利益等等说法都是一种应然要求,也就是属于所谓政治哲学的范畴。比如,我们都知道,卢梭自己就说他要探讨的是道理,而不是事实。但是,为了维护私有制,西方政治学后来就把这些应然因素(观念、价值、制度、做法等)当成政治本身,而且是合理的政治的原则和内容,包括直到今天所谓的民主、现代化、治理、善治等说法。
在这种情况下,既有的政治学不仅故意不去思考真实的政治,而且久而久之、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代代沿袭,使得学术界已经不会作这种思考了。相反,许多基本概念本身就是偏见。比如,“政治发展”用来指政治由“传统”向现代的变化,而这个“现代”就是指西方民主。按照这种知识结构和理解角度,中国政治不仅还不够现代,甚至多有“传统”因素,实际上也就是封建残余和各种专制。又比如,“政党政治”专指多党制运作,按照这种概念定义中国也不存在政党政治,而且那八个民主党派也很难算作政党。
由于上述缺陷和弊端,既有政治学缺乏普遍性、真实性和解释力的事实也就不难理解了。即使那些看到了中国政治的特点,甚至对此多有肯定的观点,仍然无法摆脱理论评判的西方标准。比如,贝淡宁在其《中国模式:政治精英体制与民主的局限》一书中认为,中国实行的是一种“垂直的民主精英制度”,值得西方借鉴,但在民主尤其是基层民主方面还有很多局限。其实,贝淡宁所谓的精英政治就是中国政党政治,而所谓基层民主更多属于群众路线,但所有这些都在既有政治学的理解和解释力之外,所以必然会得出民主“局限”的结论。因此,贝淡宁这种认识就好比把两个不同的学科,比如美术学和物理学拿来比较,而且还要用物理学的标准来评判美术学。然而,或许正因为西方普遍存在这种矛盾心理,他那本书才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2015年的最佳图书,并名列政治类第一。①相关报道见《参考消息》,2015年10月12日第14版、12月17日第12版。
三、“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含义
上面两节的讨论表明,建立“中国政治学”不仅需要批判的武器,而且更需要甚至就是武器的批判。换句话说,建构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政治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现有的理论工具是不足以胜任的,甚至根本就是不能用的。
简括地说,“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含义就是指当今政治的理论形态。由此,“中国政治学”不是某些观点的改变,而是在认清既有政治学缺陷和弊端的前提下,更具合理性、普遍性、解释力,以及时代特征的新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但是,学科的普遍性在于它是以不同领域(系统、方面等)的特性(质的规定性、功能、特征等)区别为划分标准的,为什么要以“中国”来为这个新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命名呢?理由主要有二:一是指当今的政治学概论,二是真实政治的特征化延续。事实上,这两方面互为表里,不仅构成了中国政治学学科含义的支撑因素,而且也反映了一般寓于特殊这个道理。
先说第一个理由。中国政治学是当今政治状况(或者叫真实的政治)的客观反映,也即对这种状况的理论抽象和解释,所以说是当今的政治学“概论”。这里的道理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含义的理解是一样的,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当今的社会主义。这种理解把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看成一个自觉的和自成体系的活动,包括从空想社会主义到今天的500年历史和可以预期或展望的将来,所以体现了历史观点和创新本质的一致性。因此,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含义不在于“中国”,而是指社会主义本身的特定历史和发展阶段,但其学科的适用域或理论内容却涵盖了下述情况,即这种社会主义是“在中国”发生和存在的,并“由中国”来担当和实施的,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同样,“中国政治学”这个概念含义指的就是当今的政治学,就其知识性的学科介绍或阐述来讲,也可以叫做当今的政治学“概论”,而有关中国的情况只是这种政治学的一部分内容,包括它们“在中国”的发生和存在,并“由中国”来担当和实施,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等。
第二个理由其实就是指中国对于“政治”的理解更加符合第二节所说的政治的真实状况。从古代到19世纪,中国思想史一贯的和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把政治看作一种功能性关系,而其结构性内容相对说来并不确定。简括地说,中国政治在社会层面强调的是伦理,在自然层面强调的是道德,而它们的根据和目的都是建立和维系等级秩序。正因为如此,比如孔子思想(主要是政治思想)的核心才是克己复礼,而不是什么“仁”啊“善”的东西,在运作机制上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近一百年来西学的主导蒙蔽了中国学界对于政治的认识,而且也使中国在思想和知识体系上全盘接受了西方对于学科的分类。因此,以“中国”作为当今政治学的命名,一方面是为了更准确地标识真实的政治情况,另一方面也更突出地体现了学科知识的创新特点。
对上述两个理由的自觉认识既是建立“中国政治学”的必须和基本前提,也是这种政治学学科含义的一项内容。由于“中国政治学”是具有普遍性的学科,而不仅仅指中国的政治,所以尽管它大大增进了理论的解释力,但却并不排斥其他政治学理论的存在及合理性,因为各种政治学本身都是具有选择性的知识体系。
四、“中国政治学”的基本框架
毫无疑问,建立中国政治学是一个浩大的学术工程,不过其核心问题和最关键的逻辑联系,都是对于“政治”的理解。限于篇幅,这里只能针对这种理解,极为简要地指出支撑中国政治学基本结构的三个主要层面,即特性、功能、机制。
第一,“政治”特性的本体形态。
简括地说,政治就是设计、形成和运作“公共利益”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讲,并不存在客观的、没有前提的、固定的“公共利益”,相反,不仅“公共利益”是制造出来的,而且正是由于人类社会不得不制造公共利益,所以才有了政治活动。换句话说,制造以及如何形成“公共利益”既是政治运作的前提,也是政治存在的本体形态。正因为如此,具体的政治内容也是随时随处不断建构出来的,而不是没有前提的和固定的。
事实上,对于公共利益的关注并不能保证真的存在什么公共利益,相反,这种关注不仅直接表明了政治的争取多数特性,而且也证实了阶级观点的真实性。如果存在公共利益,它的假定就是“全体”,或者说绝对多数,那么保护少数就是多余的;如果不存在公共利益,创设它就是为了争取多数。但是,一方面,整体的公共利益总是由各种具体的、局部的也就是相对不那么“公共的”利益构成,另一方面,“公共”的实际含义在不同的群体看来几乎永远是不一致的。因此,假定公共利益存在,那么,由于前述两方面情况,公共利益也始终呈现出一种多维的和变动的立体形态,也就是由各种不同的主张及相应实体来构成“全体”(即绝对或所有意义上的多数)。如果我们把这个立体形态中所有不同的状况进行归类,然后将它们放入或拉成一个平面,所有的不同就会呈现为等级不同的序列或高低不平的阶梯。这种序列或阶梯就是“阶级”,尽管阶级划分的依据和具体的阶级形态都是可以而且的确也是在变化的。[3]
第二,“政治”功能的目标旨向。
所有的政治功能以及政治中的所有功能都是有目标旨向的,而最基本的、也是所有功能共同的一个目标旨向,就是争取能够获得权力的多数。这种情况自古至今皆然,比如皇帝讲民心、议会讲选票、中共讲代表。因此,不管是否保护少数,少数的存在不过是多数的另一种形态。从实体存在来讲,敌、我、友的数量多少都是变动的,友对于敌和我的关系也永远都是变化着的,但敌我关系本身却是固定的,尽管敌我双方的态度可能转变,甚至位置也会发生易换。但是,决定政治这种争取多数的功能旨向的最根本依据,恰恰在于现实中并不存在既定的“权力”,一切都取决于敌、我、友的关系状态,而关键是对于“友”的争取。事实上,权力(甚至权利)本身也是由这些关系的状况产生的,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多数就代表或掌握权力,相反,权力其实就是时时刻刻、随地随处的统一战线。
第三,“政治”机制的转换连接。
出于具体的政治理念或导向,不同的政治体系都有相应的运作机制,但是,政治机制的普遍性结构则在于各相互区别方面的转换连接关系。换句话说,这种机制是一种结构性的功能,它不仅要完成具体的目标或任务,而且始终要能够对于不同方面形成并保持符合预期的维系。作为运作机制,这种转换连接的根本动力在于各关系方面的利益平衡,比较主要的或基本的关系方面包括政治领域与其他(比如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党建等)领域、专门政治与一般政治、内部利益与外部利益、全球事务与国际事务、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等。当然,转换连接的关系方面既不只是一一对应的,更不限于同一层面,而是变动的、立体的和交叉的。比如,改革开放以前所谓“计划经济”的真实含义并不是指经济本身的计划,而是”用政治计划经济”,也正因为如此,“以经济工作为中心”才就是现在最重要的政治原则和导向。
上述基本结构的三个层面仅仅是从特性、功能、机制等角度对于”政治”的理解,而这三个层面各自又分别由相应的活动环节构成,比如政治内容、政治载体、功能关系、实效反馈等,而且这些环节也是相互关联和交叉的。作为学科性的知识体系,“中国政治学”当然还包括与政治活动相关的各具体内容,比如政治学史、国际政治、比较政治,以及政治活动的主要实体、功能、形式,比如政府、政党、权力、决策、交往等。当然,体系中的各部分都需要以上述对政治的理解来保证和调整它们的逻辑一致性。比如,如果说”中国政治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具有一致性,那么主要就在于它们都是一种新的政治文明形态,不仅不主张既有政治学那种一分权利一分义务的交易,而且根本就不以任何交易为政治成立的前提。
“中国政治学”的解释力与它的合理性、普遍性和现实性是一致的,其中最主要的方面,就是对于政治活动的建构性特征的认识和把握。因此,这种解释并不被动地依据任何一种固化了的或静止的理论,而是在说明问题的同时也能动地成为真实政治的构成因素。为了更便捷地理解这个道理,下面分别以全球和中国的情况来举例说明。
先说全球的情况。比如,同样都是主权国家,有的却在核研发和利用方面受到国际社会(联合国)限制;同样都是战争,有的却被国际社会认作恐怖主义。对于这些问题,既有政治学不仅无法回答,甚至根本就没看到它们的问题性质所在,而是想当然地(习惯或偏见地)将它们归之于制度以及价值观的不同。在“中国政治学”看来,答案正在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包括在其设计、形成和运作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同“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而相关的运作不过是各种领域、方面和情况的转换。同样,任何一种真实的公共利益也都要靠争取多数来获得认同和支持,否则国际社会的合法性就无从谈起,而合作反恐、维持核不扩散体系,甚至全球气候大会等政治活动也就都不可能成立。又比如,就领域关系的转换连接来讲,是否给予某个国家,尤其是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既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而其连接转换的机制原则或根据依然是对“公共利益”的不同理解和运作,以及不同领域或方面的利益平衡和关系处理。
再说中国的情况。在我看来,中国政治的几乎所有重要方面都处于既有政治学的解释力之外,所以这里只以几个常见的名称为例就足够了。比如,“政法”(政法委、政法大学等)可以具有“政策与法制”“政治与法律”“政治的法律”等含义,但显然又都不是这些含义;“经济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经济社会规划等)可以具有“经济和社会”“经济的社会”等含义,但显然也都不是这些含义;至于“市政”(市政管委、市政工程等),肯定更不是“城市政治”的意思。对于这些情况,既有政治学完全没有解释能力,因为它的理论体系或者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内容,或者由于缺乏前提和自欺欺人而产生误解甚至偏见。事实上,在“中国政治学”来讲,这些名称或用语等情况的含义并不在于概念或术语的定义表述,而是前述“社会联结”在政治内容生成方面的作用,同时也是转换连接机制的实际应用。换句话说,对它们的理解不仅是政治的理论形态,同时也是真实政治的内容构成。
[1]孙津.社会政治引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2]孙津.政治内容的生成过程[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4,(5).
[3]孙津.阶级分析的适用针对及其变化[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1).
[责任编辑 郭彦英]Some Important Issues on Setting up the Subject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Politics
SUN Jin1&YUAN Lin-lin2
(1.School of Marxism,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2.School of Government,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ipline category and knowledge structure,the subjects of politics largely refers to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which fail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China’s practical political condition due to its limitations and selfdeception.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et up a subject of“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which is rational,universal,practical and explanatory.“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provid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politics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d includes three major aspects.Firstly,the fundamental form that reflects the essence of politics is planning,forming and pursuing public interests.Secondly,the political function aims at the access to the majority’s power.Thirdly,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mechanism relies on the equilibrium of interests among different fields and sectors with the management of social relations.
politics;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public interests;social connections
D0
A
1674-0955(2016)05-0102-06
2016-02-08
孙津(1953-),男,江苏南京人,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袁琳琳(1988-),女,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