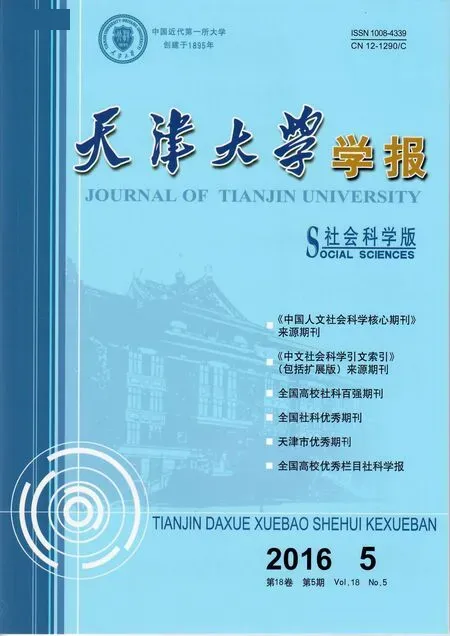再论李贺诗的“苦吟”
魏 静, 沈会祥
(1. 天津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 天津 300072; 2.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 300051)
再论李贺诗的“苦吟”
魏静1, 沈会祥2
(1. 天津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 天津 300072; 2.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 300051)
苦吟为诗是李贺把心灵生活与诗歌创作结合在一起的生活方式,乃至精神生命留存的途径。他的诗除了大量吟苦的内容,还有耽思沉溺以诗自娱的成分。李贺吟苦诗在境界塑造上体现在对导致苦闷心境的内外成因的分析提炼与对诗境的时空视域的扩展变异,他有的诗也彰显出张扬生命意欲舒展与自由的一面。苦吟在具体境界的描写方法上,可能受到《楞伽经》等佛教心性说的影响,比较注意展现“心身境”之间“三位一体、隐显互摄”的关系,以及整个心灵活动不同层面的“互触互通”、“辗转迁流”的主客时空结合的整体过程。李贺的苦吟表现在具体句法上,多用对比整合句法,通过对形容词、情态动词、动词、方位词等进行仔细地对比体味,在意绪的对比和回环往复中来彰显诗境。和别的苦吟诗人相比,李贺的苦吟既有共通之处,又有独特之处,他体现了中晚唐苦吟诗风幻诞怪奇的倾向。
李贺; 苦吟; 《楞伽经》; 心身境; 对比整合句法
李贺是中唐“苦吟”诗人的代表,也是人们对中唐诗人研究的一个热点,近年来人们对他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其“鬼才”的评价和认识、鬼神题材、生命意识、意境塑造、思维特点、语言和修辞、创作动机等方面,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是从“苦吟诗人”的角度去系统考察李贺其人其诗的研究并不多,有的文章虽然对李贺的苦吟有所涉及,也仅仅是就其诗的语言、修辞、构思等层面苦思琢磨的技术特点进行分析,缺少综合的把握。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中晚唐苦吟诗人和苦吟风气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苦思写法或内容上吟咏苦闷的问题,而是有其更加丰富复杂的内涵。把李贺作为中晚唐苦吟风气下的苦吟诗人典型进行观照,不仅有助于把握李贺“苦吟”的内涵,也能从个案的角度深化对中晚唐苦吟诗风的认识。
一、 “苦吟”是李贺把心灵生活与诗歌创作结合在一起的生活方式
李贺作为苦吟诗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以诗作为安身立命实现人生价值、乃至生命价值的途径。他在诗中对自己苦吟生活有很多自述,所谓“寻章摘句老雕虫” (《南园十三首》)[1],“歌成鬓先改”(《长歌续短歌》)[1]4409,“庞眉入苦吟”(《巴童答》)[1]4414,无论这些自我写照也好,还是从他的诗中可看到的冥想、玄思神游的习惯也好,都说明这一点。关于李贺去世时的传说,很能体现出他以诗立身的苦吟诗人的自我定位。李商隐记述李贺死时的情况道:“长吉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版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当召长吉’。长吉了不能读,下榻叩头,言阿婆老且病,贺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长吉独泣,边人尽见之。少之,长吉气绝。”[2]李贺临死前的幻想,实际上正是他人生终极追求心音的流露。这种以诗立身的自我定位,与他对人生具有强烈的功业意识有关,又与他功业受挫后迸发的生命意识结合在一起。李贺自视甚高,《金铜仙人辞汉歌并序》特意注明自己是“唐诸王孙李长吉”[1]4403,强调高贵的出身,他早年“学为尧舜文”(《赠陈商》)[1] 4417,又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具有强烈的进取心。皇族的后裔,再加上早慧的天才,使他的思绪更多地萦绕于追慕历史上雄才大略的秦皇高祖、汉武光武等人杰人主,或者汉武梁武那样文采风流的国君,以及历史上出身高贵的屈原,与汉武梁武君臣相得的才子司马相如、庾信等身上,从这些不难见到他对自我期许的内在心理图景。可是后来人生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他因名高被嫉毁,被举报应避父名“晋肃”讳而放弃科举考试。因此他的建功立业的人生图景还没有展开就戛然而止了。还不仅仅如此,现实中的李贺,无论他的家庭处境、自我形象还是健康状况,都大大迥异于他的心理欲求。他气质上本来就有“眼大心雄”(《唐儿歌》)[1]4396的一面,这不仅仅是对幼童“唐儿”的夸奖,实际也有自喻的成分,早年见到韩愈,就赞扬对方“二十八宿罗心胸,九精照耀贯当中”(《高轩过》)[1] 4430,这无疑也是他自己笼贯天地的心胸手眼的写照。从他的诗作所展现出的心灵时空视野来看,囊括宇宙古今,神游天上人间,是他的擅长。加之父亲早逝,二十来岁他就面临着贫寒病苦的威胁,妻子又早逝,他也有早衰乃至死亡的预感,后来他又做过几年奉礼郎的专职丧葬祭祀的小职,更多地接触到死亡暗淡的一面,这些都给他以极大的刺激,使他更多地转入对生命与自然本身的奥秘的探索。读佛教典籍《楞伽经》,听佛教俗讲,“听讲依大树,观书临曲沼”(《春归昌谷》)[1]4422。玄想佛教所说劫坏情形,“羲和敲日玻璃声,劫灰飞尽古今平”(《秦王饮酒》)[1]4400。好奇巫灵,沉吟《楚辞》,寻觅鬼神灵怪之踪,玄游天界仙山,冥心阴冥异域,乃至欲于玄想中与天帝同游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应该都是在生命意识刺激下精神探索的表现。
原本以皇族后裔而自命不凡的李贺,诗与酒、剑与马的豪情变成浓重的压抑,以诗人立身就成为他唯一也无奈的选择。而青春、爱情与死亡的阴影也侵袭着他,他虽然受佛教气质的熏陶,但他并没有真正受佛教的超脱一面的影响。于是他带着青春的热血,游走冥想在个人的天地里,以冷漠、无常、浓重忧愁的心态体味万事。总之,成为一个以诗人安身立命把心音寄托在诗中留存的苦吟诗人,有他诗人气质的因素,也因不幸的境遇,还因生命价值追求的强大意欲。他把诗歌创作作为追求生命不朽的方式:“惟留一简书,金泥泰山顶。”[1]4394以著书不朽自期,“巨鼻宜山褐,庞眉入苦吟”(《巴童答》)[1]4414,可以看作他苦吟为诗以之为精神生命寄托的写照。以诗立身的意识与生命意识的结合,使诗成为他生命自证自存的载体。
从他诗歌写作内容和精神的探索之旅来看,写诗也成为他心灵生活与创作结合在一起的生活方式。他的诗首先是吟苦,描写人生的种种愁苦惨淡之境,借诗来宣泄种种现实苦闷的感触。虽然他有大量鬼神诗,但从精神上看,他并非分不清现实与虚幻之间的界限。他对生死之间的隔阂是清醒理智的,并且在诗中一再地表现。再如《王浚墓下作》:“人间无阿童,犹唱水中龙。”[1]4416他对神仙也持怀疑的理性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李贺大量诗作,刻意打破隔阂、沟通阴阳,神游于现实、鬼蜮、仙界、妖魅的世界,正是他师心自怪、刻意搜求的苦吟产物,用他评价韩愈的话来说,就是“笔补造化天无功”(《高轩过》)[1]4430。明陆时雍在《诗境总论中》说他:“妖怪感人,藏其本相,异声异色,极伎俩以为之,照入法眼,自立破耳。”[3]除去里面对李贺的批评不论,所谓“极伎俩以为之,”就是把幻诞的想象作为苦思琢磨的方法来造境。而这种自苦为诗的方法并非仅仅是追求怪奇,而还浸透着作者的血肉,充斥种种苦闷甚至是恐怖的气息。为表现生命的苦闷强化而不是转移苦痛的现实感受,刻意搜求于幻诞之境就不能不说是戕害精神的自苦行为了,这些对生命苦痛的吟咏推敲,确实含有因诗而苦,自讨苦吃的味道了。
他的苦吟,不仅仅由吟苦的一面,还有耽思沉溺以诗自娱的成分。从诗作上看,他与生俱来的张扬的生命意欲,应该是在酒、诗里,在心灵化生的世界里,挥斥风云,超脱了窒碍矛盾苦闷的现实时空,乃至自我的束缚,所以苦吟应该也有苦中作乐的一面。他还是有表现对美好生命境界的耽溺的诗作,尤其是那些秀逸清新的咏物小景、高远秀美的山水之境。再有“羲和敲日玻璃声,劫灰飞尽古今平”(《秦王饮酒》)[1]4400这些游仙诗,神游于天地,任由精神生命的张扬,乃至表现了一种意欲挽天回地的豪情。还有那些悠长美好的仙境,也给人从容自由之感。他气质里本来所谓的“眼大心雄”纵逸舒展的一面,要不是名高被谤的不幸导致的苦闷与压抑,也许这类的诗作会更多一点。但总的来说,这样心理交战的煎熬,加上贫寒、健康不佳,也就逐渐耗尽了他的生命。最后,他终于融入到自己所心造的幻境,到天上去为天帝写文章去了。
二、 苦吟与对导致心境的内外成因的分析提炼
李贺诗歌的主题主要是写他张扬舒展的生命意欲,对生命青春爱情功业等的留恋与追寻。而这些又与现实产生了种种矛盾,写他追求不得的愁苦忧虑、哀怨激愤与世情诡异变幻的感触,还写了广阔生命意义上的种种恐怖怪异之境。
在诗歌境界塑造上,他的苦吟体现为对自我个体心性成因的自觉洞察和提炼,对导致心境的“身心境”内外的各原因的推敲、提炼、强化及表现。比如青春、爱情与死亡矛盾的主题。他把身内的热血、自由、壮大纵任的豪情与身外的春天、花、女性、酒等美好意象,与健康不佳产生的衰老、病苦、枯萎以及暗淡、浓愁、凝固、滞碍、无力、怨恨、无常感触乃至死亡、鬼神等类意象,加以仔细体味、洞察与琢磨,构造出凄美的诗境。再如写功业未就和知音难遇的浩叹。写他眼大心雄的心灵广阔时空视野与豪情,在功业追求与现实的矛盾产生的种种窒碍、矛盾对立,写他内心对现实乃至自我的对抗、厌恶、憎恨、忧愁、抱怨、激愤的态度,把诗与剑与马,对秦皇汉武的追慕,以屈原、司马相如、庾信自比等,与现实的无奈无力感的对比中鲜明地表现出来。
这种对自我心理底色的自觉洞视,反映在他的诗里,就是把相反的情绪、感触叠加在一起,写感受的矛盾诡异。“芙蓉泣露香兰笑”(《李凭箜篌引》)[1] 4392,“细绿及团红,当路杂啼笑”(《春归昌谷》)[1]4422,“泣”与“笑”拼接在一起。再或偏用热烈的色调衬托愁苦之境,写怨愤之情。如“百年老鴞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神弦曲》)[1]4433,这里的笑,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死神的狞笑。如“南山桂树为君死,云衫浅污红脂花”[1]4429,艳丽的猩红却表现出死亡的气息。
三、 苦吟与对诗境时空视域的扩展变异
李贺在境界的构思的方法上,体现出“境由心生”,注重主观心性镕裁的特点。在境界的时空视域的展开上,他的苦吟表现为超越现实纯任心性化境的变异化写法。他的境界主要可分为冥界仙境,移情入物的异类幻物之境,虚实结合的真幻之境和主观感触化的实境。无论是那种境界,都带有极强的主观印记。在境界塑造上,李贺的苦吟就表现为以心为源,以对情绪的深入体味为触发点,发挥幻思冥想,通过冥搜深钩,来创造极为主观变异化的境界。
他驾驭心灵追寻历史上逝去的豪主、诗魂,或寻觅传说中的女鬼女神踪迹,从生命丧失之后的冥间鬼域的角度,来表现士无知己的不甘。他笔下有抱恨而终的书鬼、死去的嫦娥、秦皇、汉武、南山新鬼等。他通过以奇幻之思、移情入无情之物,通过幻诞的场景,来变异地表现对现实的感触。如《金铜仙人辞汉歌》借写金铜仙人被搬离汉宫时告别汉武帝茂陵的依依不舍之情,抒发黍离之悲、兴亡之感。他还幻入到龙鱼等动物生灵,去感受广阔生命意义上的苦痛:“一方黑照三方紫,黄河冰合鱼龙死”(《北中寒》)[1]4429。他琢磨联想冥界的场景,表现自己早夭的忧虑:“南山何其悲,鬼雨洒空草。”[1]4411详尽地描绘出一幅冥界迎接新死鬼魂的恐怖景象。天上人间在他眼里也无常变幻,如《官街鼓》:“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催月出。……几回天上葬神仙,漏声相将无断绝。”[1]4435这类作品既是由于他在生命意识驱动下好奇的心性使然,也是他为表现苦痛感受而刻意在幻异中强化苦闷,追奇逐怪的写作策略。
他把苦痛写到触目惊心的程度,应还受佛教的影响。佛教的视野非常浩瀚,讲一念三千法界,且极力地讲人生无常痛苦,包括生老病苦,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聚会苦等可谓百忧交集,并且写六道轮回如火宅,众生无一不苦,来极说人身难得,佛说难闻,激发人对六道轮回的出离心。李贺由于境遇不佳,这些可能深化了他这种体认。
应该说,李贺的诗,不仅仅是吟苦,吟苦虽然是底色,他的诗也彰显出张扬生命意志的舒展与自由的一面,他在这些诗里,也用了很大地深思冥想的苦吟功夫。如他写高远秀逸之境:“夜峰何离离,明月落石底。徘徊沿石寻,照出高峰外。”(《长歌续短歌》)[1]4409再如写悠美从容的天界,清丽秀美的咏物之境,豪纵壮大的游仙之境等。
四、 苦吟与对“身心境”之间的整体活动的观察、对比和体味
在具体境界的描写的方法上,李贺诗的特点就是诗境给人以亲切不隔的感受,有一种真实自然的身临其境感。他的苦思,在境界观照的方法上,就表现为对“心身境”之间的整体心灵活动过程有很好的观察、对比和体味,比较注意写出在特定心态下的人在特定情境中的整体心灵活动。
在对心性的理解上,李贺应该受到《楞伽经》等佛典的影响。李贺自云“楞伽堆案前,楚辞系肘后”(《赠陈商》)[1]4416。他对《楞伽经》有仔细的解读。《楞伽经》是禅宗初祖达摩传灯印心的经典,是禅宗修习如来禅、明心见性最主要的依据,也是唐代兴盛的法相宗、唯识学等主要研习的对象,此经重点对如来藏和阿赖耶识有揭示[4]。唯识学包含着丰富的心理学内容[5]。《楞伽经》对“蕴界处”和“八识”的讨论,对于诗人在诗歌的审美境界创作中如何透视“身心境”三者的关系,及诗人对诗歌审美思维心理机制的透视可能有启发作用。
先说“蕴处界”的问题。“蕴处界”,又可称为“三科”,是佛教对宇宙万物的分类和概括,指“蕴”(五蕴)、“处”(十二处)、“界”(十八界)。“五蕴”指构成人和万物的五种类别,即 色、受、想、行、思。小乘佛教大都从狭义说五蕴,认为“人”只不过是五蕴的和合。“十二处”分两类,一是内六处: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即所谓“六根”;二是外六处:色处、声处、香处、味处、触处、法处,即所谓“六境”。“界”有种类、界限、因素等义。“十八界”指六根与六境再加上相应的“六识”,即成十八界。这种分类以人的认识为中心,构成“境”、“识”两个方面。[6]简言之,“蕴处界”也就是佛教对人的心身与外境的关系即“身心(意识)境(外境)”问题的揭示。佛教认为心生万法,心是本源,这个心,是所谓的佛性,佛教认为佛与众生在心性上等无差别,只有迷悟的不同,佛对自心是觉悟的,而众生是迷惑颠倒的,天、人、罗刹、畜生、恶鬼、地狱等六道众生因为心灵状态的不同,而感应的生命样态与所处的世界外境不同,认为六道众生的身、心、境都是由于其内在的心灵状态的优劣感应而来。法由心生的提法,在“蕴界处”即“身、心(意识)、境”三者的关系上,认为自身、外境都是内心化现的产物,认为是精神透过身体去把握感受外在世界,而产生了对自我、外在世界的存在与区别的感知,展开对自我身心和所处的外部世界的认识与运作。简言之,认为身、心、境都是一心所化,大致就是认为身、心、境是一个整体,不可分离,全部精神活动的展开就是以自我身心与所处的外部环境为体认的内容,而心灵体验的全部内容都无法离开世界中的自我本身。认为众生由于执着于有我和外境之分,才有了六道众生对外境、自我的认识,也才有了种种心灵以自我为中心攀援于外境而产生的得失忧喜等心理意识活动。这种认为世界和自我是皆由心性所显现的认识,或者说认为“心、身、境”是“三位一体、隐显互摄”的关系认识,以及境由身、心所生,心由身、境而显的关系的认识,为表现内心世界塑造诗境找到了思路。
再说八识的问题。《楞伽经》认为宇宙万有皆是虚假不实,唯是自心所现。这个心,是佛教所说的心识,佛教认为“万法唯识”。“万法”即世间一切事物和现象;“识”指心识、意识,即内心。谓世间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识”所变现,离“识”即无万物[6] 44。唯识宗认为,整个世界均由“识”所变现。“识”分八种,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意根”)识、阿赖耶(“含藏”)识[7]。在心灵运作的方式上,佛教大致认为心灵通过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的感官接触、意识把握与对比分析、情感趋避来对自身和外部世界以察觉不到的直觉方式进行绵密不断地接触、对比分析与整合,从而产生对自我、世界的认识,展开身体内外的意识活动和运作。佛教认为这些心灵活动的展开虽然不间断地进行,但认为精神活动(心)围绕着身、境展开的感官接触、意识对比、感情活动与身心动作本身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就是说:1)这一过程本身既是三位一体、隐显互摄的;2)三项心灵活动的展开又是互通互融、辗转迁流的不可分割的直觉整体过程。也就是说,心灵围绕着身与境展开的活动本身是一个内外隐显互摄且相续不断的主客时空合一的整体。自我和世界既然是心的产物,主观心灵活动的中断意味着“我与境”的消失,而心灵感受的发生即使在梦中,只要有自我的觉察,也有梦中之人、身、境,也体现着精神以“身心境”三位一体的形式运作的过程。
李贺喜读《楞伽经》,可能是受到《楞伽经》等佛教心性说的影响,李贺在诗境的创造上,苦吟一是注意展现“心身境”之间“三位一体、隐显互摄”的关系;二是通过体味冥想,写出心围绕身与外境展开心理活动时感官、意识、情感等整个心灵活动不同层面的“互触互通”;三是在境界的展开上,把心绪萦绕于身、境的整体过程,沿着情思意绪整体“辗转迁流”的特点表现出来。而上述三个方面,精神围绕着身心境活动的“三位一体、隐显互摄”与“互触互通”、“辗转迁流”又是一个主客时空结合的整体。对这个过程的自觉地透视、分析与表现,是他描绘诗境时苦吟构思的着眼点。
比如他写物境,是身心中的感受之境,“境中有人”,有感受的过程。如“娇春杨柳含烟细”(《浩歌》)[1]4399,拟人化的手法,感受的人与外境是隐显互摄的关系。杨柳细烟是写春如少女之娇媚,而“含”字则写出春之境内在的神韵和空间感,写出人在境界中对外境的体会。再比如“酒阑感觉中区窄”(《酒罢,张大彻索赠诗》)[1]4407则直接把身心内部的主观感受投射到外境上去了,外境显出感受之人的身心状态。
而在写人上,也是把心身与外境结合在一起写的情况,写出“身在境中”。比如“腰围白玉冷”(《贵公子夜阑曲》)[1]4395,“金凤刺衣着体寒”(《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并闰月之十月》)[1]4398。再如写眼中所见之他人上,李贺有拟物化的倾向,如“一双瞳人剪秋水”(《唐儿哥》)[1]4396,不但写出双眸,还写出如秋水般高远清明的内在精神境界,可谓形神兼备。从思路上看,秋水的外境有助于人内在心境的澄澈,反过来,用秋水来描写心境则体现出他对别人身心境界的体察能力。
在表现身心活动展开的时候,他注重写心灵各活动层面“互通互触”的关系,也即所谓“通感”。如“冷雨香魂吊书客”(《秋来》)[1]4400,以花香写不见其人而感其心神魂,花香给人以沉醉之感,如隐似现,把古诗人之魂恍然在侧感写出来了。再如“箫声吹日色”(《难忘曲》)[1]4415,以暖阳满照之色兼写声音之清扬感。如“一心愁谢如枯兰”(《开愁歌》)[1]4420,以花谢写心绪之凋零,来直接把内在心境外显化了。再如“玉喉窕窕排空光 ”(《洛妹真珠》)[1]4400,通过通感用形象化的手法,兼写外境的阴郁、声音与心境之浓愁。
他笔下的境界在具体的展开上,则转换描绘的视角,呈现出物境、人事、虚境交织流转的情况,体现了随着思绪的转换,整个心理活动“辗转牵引、不断流转”的过程。比如《秋来》一诗,写诗人深夜读诗,思游古今,由一己之激愤苦闷,“思牵今夜肠应直,”写被后世知音何在的焦虑叩问牵引的主观感觉,而“冷雨香魂吊书客”[1]4400,则写出诗人对古诗冥思默会,由其诗幻入其人其境,感到古诗人之魂恍然在侧,产生一种如真如幻的奇妙感触,这又是此心幻出的结果。最后是在幻觉中听见秋坟之下怨鬼的愤唱。在他冥心历史、古人的同时,照见自己与古人相通的处境,不仅油然而生我吊古人、身后谁来吊我的追问,这样,历史、现实、未来,古人、自我、后人,就这样在他心里奇妙地连通在一起,这自然是思绪流转的结果。
五、 苦吟与体现“身心境”整体活动的对比整合式句法
李贺的苦吟表现在具体句法推敲上,多用体现“身心境”整体心灵活动的对比整合式思路。他从身、心、境各角度,对特定心理状态下的心灵,以身心为中心萦绕于外境的整体过程,如上述从不同感官角度的观察、意识的分析对比、情感的体味等三位一体隐显互摄、互触互融、辗转迁流的整体过程进行分析、对比、整合,然后用对比整合的句法表现出来。在句法思路上,他一般把表感官活动的形容词如色、声、嗅、味、触及与表意识对比整合的空间、方位、时间、形态、范围、数量、程度的词等,与表内在感触的情态动词,表动作神态的动词,进行仔细地对比体味,用对比整合的方法连缀起来,来显示心灵活动的上述整体过程。他写诗多用对偶句,对偶在句法上两句形成一句,往往通过上下句之间意绪的对比和回环往复来彰显诗境,它本身的解读思路就是一种让人在上下句之间回环对比、相映互现中来体会整体诗境的过程,是接近佛教对心灵活动的对比整合机制的描述的,本时期写诗对偶法的大量应用本身,近体诗体制的兴盛,应该说就有受佛教思维方式影响的原因。李贺在句法上进行了仔细的琢磨,他不但在两句之内,更在一句之内很好地运用了这种对比整合的思路,显示了他在苦吟思路上的自觉。他主要通过特定的连缀方式,用对比和对偶的手法,把上述的感官心理触受与意识对比结合的感情活动直觉整合在一起,让读者在诗句指引下感受到境界生起的情况。
如身心与境隐显互摄的情形,就是在无我之境中也能见到人对外境的感触:如“绕堤龙骨冷,拂岸鸭头香”(《同沈驸马赋得御沟水》)[1]4393,把诗人对环境的感受化入大堤、鸭头的角度,对周围的境界予以感受,显现了身心与外境互融互摄的视角。再如“满栏花向夕”(《难忘曲》)[1]4415,以满栏花好朝向夕照的温情脉脉来写男女爱情相依心态下的所见所感,隐现出人与境隐显互摄的关系。再如“无人柳自春,草渚鸳鸯暖”(《经沙苑》)[1]4436,写春回大地,万物舒展自在安然的情境,隐含着自己独不得春的幽怨。
用情态动词来显示身心境之间的互摄互融:如“竹云愁半岭”(《蜀国弦》)[1]4396,用“愁”字连缀上下的空间比较,从人在境界中的感受入手,把身心境的隐显互摄关系和整体感受过程来直觉地整合在一起,传神写出境界。再如“悲满千里心,日暖南山石”(《客游》)[1]4416,写暖阳普照万物而己独不得与的寥落之感,通过上下句的对比映射显示出来。
用感官动词如形色、触觉、嗅觉,来表现身心境之间的互摄互融:如“舞裙香不暖,酒色上来迟”(《花游曲》)[1]4393,写出自己对宴会舞蹈氛围的冷清及孤寒落寞的感触。再如“星依云渚冷”(《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并闰月之七月》)[1]4398,写出自己对外境清寒静寂的感受,人与境之间也隐显互摄。再如“冷红泣露娇啼色”(《南山田中行》)[1]4407,通过主客隐显互摄写出人感受到的外在物境。
再如用动词的情况:如“大野生素空”(《秋凉诗寄正字十二兄》)[1]4424,用动词把空间上下的比较写出来,引导读者在回味中化出诗境。再如“落花起作回风舞”(《残丝曲》)[1]4392,拟人感和空间感均有,感受性很强。
再比如有人之境,通过对身心境隐显互摄的关系,及心理围绕着身境展开的互通互摄、辗转迁流的心灵感受整体过程的分析与观照,通过对偶的方式,让它回环往复、整体性地表现出来。如“木叶啼风雨,落照飞蛾舞。古壁生凝尘,羁魂梦中语”(《伤心行》)[1]4402。用情态动词“啼”写出愁苦的外境,落照与飞蛾的对比,加上“舞”这一动词,写出飞蛾在夕阳晚照里飞舞的空间感和寥落感,古壁和凝尘用一个“生”之动词连缀,写出墙壁由于时光久远老旧生尘的破败感,羁魂梦中语则写出诗人梦中苦闷呢喃的情形,则又隐显出诗人的精神被身心现实羁笼窒碍的情况,而这一切又是在如上古旧生尘的陋室中展开。再如“秋容满千里”(《追和何谢铜雀妓》)[1]44112,用五个字就把外境秋天遍布的气息使人生愁而现之于容色写出来了,实际上也显示出对“身心境”三位一体的隐显互摄与感官、意识、情绪的辗转迁流关系的把握。
六、 李贺的“苦吟”与中晚唐苦吟诗风
中晚唐的苦吟诗人大多是当时的穷士,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功业抱负,他们痴迷于诗歌写作,生活范围有限,且大多个性内敛关注自身内心,当时的佛禅风气的兴起,使他们在佛禅隐逸中化解精神的苦闷,也使他们对心性机制本身有了更新颖的认识视角,于是对自我内心的观照作为一种修养方式和诗歌审美方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把诗歌创造和修心、自娱结合在一起的生活方式。和别的苦吟诗人相比,李贺的苦吟既有共通之处,又有独特之处。李贺在以诗立身的苦吟诗人的自我定位上、诗歌承载生命心灵感受上、白描写心上和别的苦吟诗人相通。但是他在幻诞怪奇的境界塑造上、矫激诡异的风格上,则和别人有异。李贺在心态上,面对自己不幸的命运,采取了对抗怨怼的姿态,缺乏超脱自我的情怀和悲天悯人的意识,加之年寿短促,有生之年他没有找到对自我和现实人生的接纳包容与和解之路,没有找到归属感和安顿感。这是他的悲剧,后来的晚唐苦吟诗人则比较好地调和了这一点,比如后期的贾岛、姚合等诗人,在愤激苦闷之外,多了平和安宁的底色与休闲审美的趣味,这就是后话了。
[1][清]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4401.
[2][宋]计有功.唐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65.
[3]陈治国.李贺研究资料[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29.
[4]任继愈.宗教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448.
[5]林国良.唯识学的认知理论[J].社会科学,2000(5):65-69.
[6]方克立.中国哲学大辞典[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32.
[7]郑天挺,吴泽,杨志玖.中国历史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39.
Further Comments on Li He’s Anguish Creating in His Poems
Wei jing1, Shen Huixiang2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2.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Tianjin 300051, China)
Assiduously to poetry is a way of life for Li He to combine his spiritual life with poetry creating, and is also a way to retain his spiritual life. In addition to a lot of content of depressed chanting in his poems, some components are engrossed in self-entertainment. Li He’s anguish poetry writing in the boundary shaping now distills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uses of leading to depressed mood and the extension of space and time horizon of the variation of poem, he some poems also shows the intention to make public life of openness and freedom. Bitter songs on the description method of the state may be influenced byLankavataraSutraand the buddhist inwardness, pay more attention to show “psychosomatic state” between “trinity, sympathetic mutual perturbation” relationship, and the overall process of the whole heart activity combines subject with object to different levels’ touch each other, contact each other and exchange themselves. Li He’s bitter songs perform on the specific syntax, with heavy use of comparison and integration and careful contrast of adjectives, modal verbs, verbs, noun of locality and so on to display the realm in the contrast and reciprocating action of meaning and emotion. Compared with other bitter poetry, Li He’s bitter songs have some features in common, and have some features in unique, and reflect the tend of fantastic poetic style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Li He; anguish songs;LankavataraSutra; psychosomatic condition; comparison and integration
2015-12-15.
天津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TJZW10-1-509); 天津大学2016年度自主基金资助项目(2016XSC-0035).
魏静(1973—)女,博士,副教授.
魏静,weijing0569@126.com.
I209
A
1008-4339(2016)05-46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