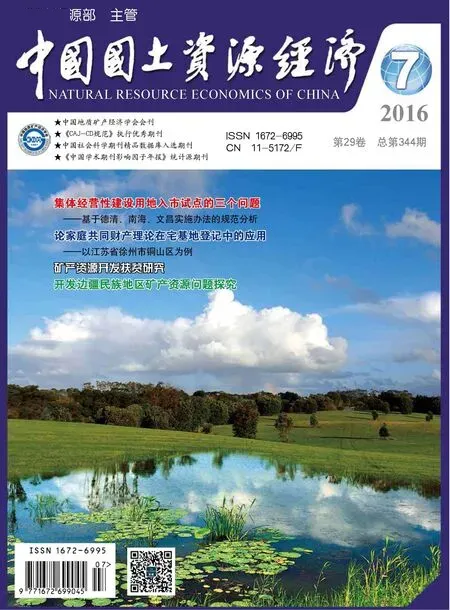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的三个问题
——基于德清、南海、文昌实施办法的规范分析
■ 宋志红
(国家行政学院,北京 100089)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的三个问题
——基于德清、南海、文昌实施办法的规范分析
■ 宋志红
(国家行政学院,北京 100089)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开展一年以来,成效初显,但也普遍存在土地所有权行使机制不顺、入市范围缺乏制度保障、调整入市中各方主体的法律地位与权利保障不明确等突出问题。建议:增强各项改革试点之间的协同性,在明确“农民集体”法律地位的基础上,结合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机制;结合征地制度改革,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范围的负面清单管理尽量扩展入市范围;理顺调整入市的法律关系,在适当扩展集体土地所有权人收回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权限范围的基础上,对收回程序和补偿等做出详细规定。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立法;试点
0 引言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要改革部署,也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点和突破口。2014年年底,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对开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2015年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此项试点工作做出了授权,允许试点地区暂时调整实施《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部分相关条款,随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正式启动。据报道,2015年6月下旬国土资源部批准了15个县(市)试点改革方案,从8月24日到9月8日不到半个月内,即有浙江德清、贵州湄潭、四川郫县的6宗地块集中入市[1]。截至目前,笔者收集到的资料显示,又新增了北京大兴、佛山南海、山西泽州、甘肃陇西、重庆大足等地的多个地块入市。
试点探索的最终目的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并为全国性的立法积累奠定基础。当前,一些试点地区就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定了规范性文件,这既是保障试点工作规范有序开展的需要,也是在立法方面的“先行先试”。对这些规范性文件进行研究,既可以深入了解试点实践动态,也能够为总结试点经验教训并推进立法变革提供借鉴。为此,笔者选取了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浙江省德清县、海南省文昌县这三个试点地区的规范性文件作为分析素材,也即《佛山市南海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管理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南海区办法》”)、《德清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德清县办法》”)和《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文昌市办法》”)。之所以选取这三个地方,是因为这三个地方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工作基础较好,其制定的实施办法相对比较成熟,具有代表性。
从这三个试点的规定来看,内容比较全面,涵盖了入市范围、入市途径、入市主体、初次入市和再次入市的方式、入市程序、权利义务关系、收益分配管理、土地收回、法律责任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尤其是对社会关注较多的历史遗留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产权确认与处理、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的收取和分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到期后土地和地上建筑物的处理等问题,都做出了或详或略的规定。总体来看,这些规定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规则、程序等方面主要借鉴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的规则,同时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并吸收了各地之前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探索的经验,内容相对成熟,对保障当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规范有序开展意义重大。与此同时,抛开细节问题,这些实施办法也存在几个突出的共性问题,亟待解决。
1 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机制未理顺
从法律角度分析,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初次入市无论是采取出让、出租还是入股方式,其供地主体均为土地所有权人。依据我国《宪法》第10条、《民法通则》第74条、《土地管理法》第10条以及《物权法》第60条等的规定,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为农民集体,分为乡(镇)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村内农民集体(生产队农民集体或村民小组农民集体)三类。同样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这三类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分别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代表行使。换言之,土地所有权人为相应的农民集体,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等只是土地所有权的代表,并非土地所有权人本身。这就好比《物权法》规定“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但国务院只是国有财产的行使代表,而并非国有财产的所有权人本身。
对照法律的规定,实践中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存在的第一个突出的普遍性问题便是不区分土地所有权人与代表人,直接将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土地所有权人。例如《文昌市办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主体为具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管理法》等的规定:“土地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民小组(经济社)或者村民委员会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采用了代表人的表述。可见办法制定者并无区分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区分土地所有权人与土地所有权代表人的意识。《南海区办法》第三条也规定:“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属村(居)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事实上,这种不区分土地所有权人与土地所有权行使代表的做法,在农村土地管理领域相当普遍,一个典型的例证便是在农村土地确权颁证中在土地所有权人一栏直接填写“某某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某某村民委员会”的情形十分常见。
在运行机制方面,《德清县办法》区分入市主体和入市实施主体,并引入了代理人作为入市实施主体。入市主体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该集体经济组织如果取得了市场主体资格,可以自己作为入市实施主体,如果没有取得市场主体资格,则可自愿委托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村经济合作社) 等代理人作为入市实施主体。《文昌市办法》也引入了代理人制度,规定土地专营公司、土地股份合作社等经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书面授权,可以代理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事项。这种做法实则是在土地所有者的代表人也缺位或者不能履行职责的情形下通过代理人来实施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其目的很明确:解决一些地方集体经济组织市场主体地位欠缺的问题。这一办法作为现实状况之下的权宜之计和无奈之举,虽然表面上看是解决了入市操作主体的问题,但在所有者和所有者代表双重缺位的情形下,如何保障代理人的行为符合被代理人的意志和利益,实在值得商榷。脱离了土地所有权人本人的代表人、代理人制度,实为无根之木,隐患无穷。
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机制的混乱,是由农民集体主体本身的虚化和虚位导致的:首先,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农民集体”本身看不见摸不着,不仅自身法律性质不明确,而且没有健全的“腿脚”,无法履行土地所有者职能。其次,作为“农民集体”之代表人的集体经济组织在很多地方并不存在,或者即便存在其组织机构也同样不健全,也无法履行土地所有者职能,这也正是德清县和文昌县设置代理人制度的原因。再次,以村为例,依据法律规定同样可以作为“农民集体”之代表人的村民委员会,虽然在各村都存在,但并不适合承担经营管理土地资产的职能。村民委员会的定位属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主要职责是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等,其组成成员并不具备经营管理集体资产的专业能力,而且村民委员会也并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并不适合成为一个市场交易的主体。不仅如此,在一些地方村民的范围与具有土地权益的农民集体成员的范围并不完全重合,村民委员会难以在经济利益方面充分代表农民集体成员的利益。总之,由村民委员会来作为土地所有权人的代表,属于典型的政社不分。
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虚位和行使机制不健全,是当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面临的突出共性问题,其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由于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农民集体法律性质不明确,权利行使机制不顺畅,既增加了农民集体内部就入市问题达成多数决策意见的难度,也极大增加了交易相对人和土地所有权人的协商成本,从而增加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交易成本;二是带来了入市决策和相应收益分配无法充分反映农民意志并保护农民利益的隐患;三是不利于农民集体一方依据诚实信用原则依法开展市场交易,当农民集体以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形态存在时,在维稳、上访等指标的考核下,集体内部的个别意见分歧很容易成为损害公平市场交易的罪魁祸首,在入市后的合同履行过程中,一旦农民集体中有人产生不满情绪,极有可能通过告状、上访等行为给地方政府施压,地方政府在上访考核的压力下也极有可能屈服并对合同履行做出非法干预或者斡旋。
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明确农民集体的法律地位并完善集体所有权的行使机制入手。实践中一些地方开展了积极探索,例如,佛山市南海区从1992年就开始探索土地股份合作制,将集体财产、集体土地和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折算成股权统一入股成立股份合作社,并由股份合作社对土地统一进行规划、管理和经营[2];2011年,南海又开始探索“政经分离”,让村(居)党组织、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其中,党组织统筹全局,主抓党务、政务和服务,村(居)委会腾出手来搞社会管理,集体经济组织则专心发展集体经济[3]。这些均是在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机制方面的大胆有益探索,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其在土地所有权人与代表人的关系上并未完全理顺,而且其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以及随之的配股上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其根源在于法律层面的顶层设计缺失,以及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农民集体”与“集体经济组织”混同的局面。在《民法总则》的起草中,是否应当对“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作出规定,也存在较大争议。笔者认为,与其舍近求远地去再构建一个作为代表的集体经济组织,不如直接对作为所有权主体的“农民集体”进行改造和完善,明确其法律性质和运行机制。当前的改革试点应当直面这一问题,建议增强改革的系统性,结合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积极探索,一方面通过明确“农民集体”的法律地位将真正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推到前台,另一方面通过股份合作的途径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机制[4]。这不仅是保障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顺利开展的前提,也是在土地公有制的框架下保障整个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能够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前提。
2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范围缺乏制度保障
按照试点工作意见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决定的规定,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范围从前提条件、土地性质、用途三个方面进行了限制:前提条件为“符合规划、符合用途管制、依法取得”;土地性质为“存量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用途为“工矿仓储、商服等经营性用途”。对前提条件的限定并无争议。但对“存量”的限定如何理解以及对经营性用途中是否包含商品房开发,却存在不同的认识,从而直接影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空间和范围。对此问题,三个试点地方也基本上是援引中央文件的表述,态度并不明朗。从前期已经入市的几宗土地来看,局限在存量建设用地就地入市。
首先,如何理解“存量”的限定,成为确定入市范围的关键。“关于入市范围,各地的认识很不一致,有的认为,可入市土地只有现状集体建设用地中符合‘两规’的经营性用地;也有的认为,可入市土地是在存量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下,符合‘两规’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包括可直接就地入市的用地和可调整入市的用地;还有的认为,可入市土地是在存量集体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下,依据‘两规’确定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5]仅从文件的字面意思判断,三种解读均可成立。但考虑到无论是中央的试点意见还是各地的实施方案均在入市途径中同时规定了“调整入市”,也即对村庄内零星、分散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按规划和计划调整到本县(市)域范围内的产业集中区入市,这也就意味着将原有的某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复垦,然后依据规划到产业集中区将某块农用地转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后入市,也符合试点意见的要求。因此,上述第一种理解显然限制过窄。综合考虑就地入市、调整入市、城中村整治入市三种途径的适用范围和后果,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范围的“存量”限制并不能理解为对土地现有用途的限制,而只是意味着对“存量集体建设用地”总规模的控制,不能增加农村建设用地的总规模,也即应当采纳上述第三种理解。否则,农村土地整治中的规划实施和用地布局调整,将缺乏征地之外的有效手段。进言之,并不能将依据规划和计划等将农用地转用后入市的情形排除在试点范围外,出于规划实施和用地布局调整的需要,将部分建设用地复垦,同时将部分非建设用地调整为经营性建设用地,均应在试点意见允许的范围内。依此类推,由于宅基地在用地管理类型上也属于建设用地,在农村土地整治中,依据规划将节余的宅基地调整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并就地入市,或者将节约的宅基地复垦后以经营性建设用地指标的方式调整到其他区域入市,也应属于试点探索的范围。
其次,对于入市后的用途是否应当排除商品房开发,也存在不同意见。实践调查发现,明确排除商品房开发的试点地方并不少见。上述三地试点办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在实施中也均予以排斥。从目前已经入市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情形来看,工业用地居首位,其次为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尚未有商品房开发用地出现。笔者认为,只要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后的地块用途不应再做额外限制,不应排除商品住宅开发。理由如下:首先,从试点意见中“工矿仓储、商服等经营性用途”的表述来看,也并没有明确排除商品住宅开发用途,强调的只是其经营性用途,商品住宅开发用地显然也属于经营性建设用地;其次,从同权同价的角度考虑,就集体建设用地上的商品房开发做出额外禁止,并没有充足的法理依据,也不利于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再次,如果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制度设计仍然禁止土地出让后用于商品住宅开发建设,那么“小产权房”的违法行为不能得到遏制,“小产权房”问题继续无解[6],“新乡贤”等回归乡里的住宅问题也始终缺乏合法途径;最后,结合征地制度改革的要求,必须逐步将征地限制在公共利益范围内,如果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禁止商品住宅开发,则必须将商品住宅开发列入征地公共利益目录,这显然是十分荒唐的。当然,在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上的商品房开发不作禁止的同时,也要将其纳入城市商品房开发轨道统一管理,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予以明确和防范,这需要对《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建制镇规划建设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予以修改。在当前试点工作中,应当允许并鼓励地方在有序可控的前提下就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后的商品住宅开发予以探索。
总之,无论是从有效限缩征地范围,还是从实现“同权同价”“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考虑,都需要尽量拓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范围。对城乡建设用地的管理应当统一通过规划和用途管制来实施,而不是额外设置歧视性制度。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会导致地方土地财政收入的减少,在经济下行、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减少、一些地方债务问题凸显的总体形势下,地方政府对征地的青睐显然远超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如果不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范围从制度上做出保障性规定,其空间难免会被挤压,改革则可能会流于形式。因此,建议结合征地制度改革,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范围采取负面清单管理制度,通过制定征地公益目录严格限制征地范围,目录之外的项目建设则一律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方式供应。
3 调整入市中各方主体的法律地位与权利保障不明确
无论以何种方式入市,产权明晰无争议是前提,因此,通过确权颁证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和存量集体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人十分必要。由于之前集体建设用地私下流转或者不规范流转的现象较为普遍,此次试点中如何处理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是各地试点要攻克的第一个难题。在此并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可资遵循,只能在遵循信赖利益保护、比例原则、合理性原则等法治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进行探索。例如《南海区办法》第20条规定对之前已经出让或者租赁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采取交易合同鉴证制度,从而实现新旧制度的有效衔接。
比处理历史遗留产权问题更为复杂的,是调整入市中的产权调整与权利保障问题。在调整入市中涉及原地块的土地所有权人、原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落地地块的土地所有权人、落地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人等多方权利主体,从而会产生一系列法律关系。据调查,当前试点地区已经报道的入市地块,全部属于就地入市的情形,尚未出现调整入市。但就地入市的空间十分有限,因此,理顺调整入市中的法律关系,是扩展入市空间之必须。
从三个试点意见的规定来看,并没有就调整入市的法律关系和利益调整做出详细规定。其中《南海区办法》没有单独规定调整入市,但规定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整备和农村综合整治;《文昌县办法》规定了调整入市的条件,但并没有就产权调整的具体事宜做出规定,在集中整治入市中则规定要达成土地整治协议;《德清县办法》第8条对涉及不同集体经济组织的异地调整入市采取了自愿协商的土地所有权调换方式。笔者认为,农民集体之间自愿的所有权调换是实施跨村(社)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调整入市的一种有效方式,但其实施范围有限,受到土地地理位置、土地所有权人交换意愿、货币补偿标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且没有解决原有土地使用权人(例如被调整地块上的原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落地地块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等)的权利保障问题。

从法律角度分析,调整入市行为可以分解为如下一系列法律关系:第一,被调整地块的土地所有权人收回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并给予补偿;第二,土地所有权人对被调整地块进行复垦并还原出土地发展权(也即产生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第三,通过土地发展权交易将该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转移到落地地块上使用;第四,落地地块的土地所有权人收回土地使用权(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并给予补偿;第五,将落地地块转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并入市。由此可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调整入市必须以“农民集体收回土地使用权”及“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交易”这两项制度为支撑。对于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各地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中已经探索出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但对于农民集体收回土地使用权,则存在收回权限、收回程序、补偿标准等一系列复杂问题。
规划的调整能否成为农民集体收回业已设定的土地用益物权的理由?《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收回土地使用权:(一)为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二)不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土地的;(三)因撤销、迁移等原因而停止使用土地的。 依照前款第(一)项规定收回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对土地使用权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该条规定的收回集体土地使用权的理由仅包括“乡村公益性建设、不按批准使用、闲置”三种情形,至于为了实施村镇规划和调整用地布局的需要将一些尚在使用的零星、分散建设用地调整到产业集中区,则不被该条规定所涵盖,从而使得此种情形下农民集体收回土地使用权缺乏法定权限。从此次地方试点的规定来看,《文昌市办法》第45条将“实施村镇规划、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规定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回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理由;《南海区办法》第54条则将“保证规划实施”规定为土地整备的理由之一。这些规定均扩展了土地管理法规定的收回范围。
笔者认为,为了保障村镇规划的实施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调整入市的顺利开展,理顺调整入市中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适当扩展农村土地所有权人收回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权限范围,并对收回程序和补偿等做出严格限制和详细规定,非常必要:第一,乡村公益性建设毫无疑问应当成为收回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法定理由,除此之外,为了保障乡镇规划的实施,也应当将实施村镇规划作为土地所有权人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法定理由。第二,为了充分保障土地使用权人的权益,应当对收回的程序做出详细规定;收回还应当参照市场价格给予公平补偿,无论是基于公益性建设,还是基于实施村镇规划调整用地,都应该给予公平补偿,既可以是土地使用权等实物补偿,也可以是货币补偿。第三,对闲置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收回,也应当明确具体条件并做出严格限制,避免随意扩大收回范围。第四,应当增强村镇规划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并加强农民在村镇规划制定中的话语权。科学而又民主的村镇规划是保障农村土地整治顺利实施的前提,正如学者所言,“集体及其成员参与村庄规划的制定程序有利于将集体建设用地所涉各种利益内化于村庄规划之中,有利于强化村庄规划在全体集体成员同意基础上的集体行动。”[7]
总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解决了此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改革探索一直面临的“合法性”问题,使得试点工作的开展得以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具体规则并没有现成的法律法规可循,需要各试点地方大胆探索。土地所有权行使机制不顺、入市范围缺乏制度保障、调整入市中各方主体的法律地位与权利保障不明确,是当前试点实践存在的突出共性问题,需要及时纠正完善。同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并不是一项孤立的改革,改革深度受制于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改革、征地制度改革、宅基地制度改革等的进展,需要改变当前各项改革试点“不打通”的局面,增进改革试点之间的协同配合并形成改革合力。
[1]新华网.国土资源部批准了15个改革试点农用地相继入市[EB/OL].(2015-12-14)[2016-06-10]. http://news.xinhuanet.com/house/cs/2015-12/14/ c_1117446498.htm.
[2]宋志红.农村土地改革调查[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50-52.
[3]黄碧云.从政经分离到经联社公司化——南海破解农村体制障碍,加速城乡统筹[N].佛山日报,2013-09-25(01).
[4]宋志红,仲济香.论“农民集体”的重塑[J].中国土地科学,2011(5):29-34.
[5]董祚继.如何买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看国土资源部权威专家讲述试点一年得与失[EB/OL].(2016-03-17)[2016-06-10].http://www.aiweibang.com/ yuedu/98579524.html.
[6]房绍坤.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几个法律问题[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15-22.
[7]陆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实证解析与立法回应[J].法商研究,2015(3):16-25.
Three Issues of Collective Operating Construction Land Entering the Market: Normative Analysis on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of Deqing, Nanhai, Wenchang
SONG Zhihong
(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89)
Since the pilot projects were launched for collective operating construction land entering the market last year, the effects are remarkable while some outstanding problems still exist. The mechanism of land ownership doesn’t exercise smoothly,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of collective operating construction land entering the market is absent, and the legal status and rights protection of the main parties is unclear. We put forward recommendations as follows: Enhance the synergies among the reform pilots, and improve the exercise mechanism of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based on clearing collective farmers' legal status in the reform pilot of collective assets shares and capabilities; combined with land requisition system reform, extend the market range of collective operating construction land as much as possible through negative list management; straighten out the legal relationship of the main parties, extend appropriately the rights of the collective landowner to recover the collective land use rights, and make detailed provisions of recovery process and compensation.
collective operating construction land; legislation; pilot
F301.2;F062.1
A
1672-6995(2016)07-0004-06
2016-06-20;
2016-07-03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5CFX048)
宋志红(1980-),女,湖北省京山县人,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教授,行政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民商法、土地法、房地产法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