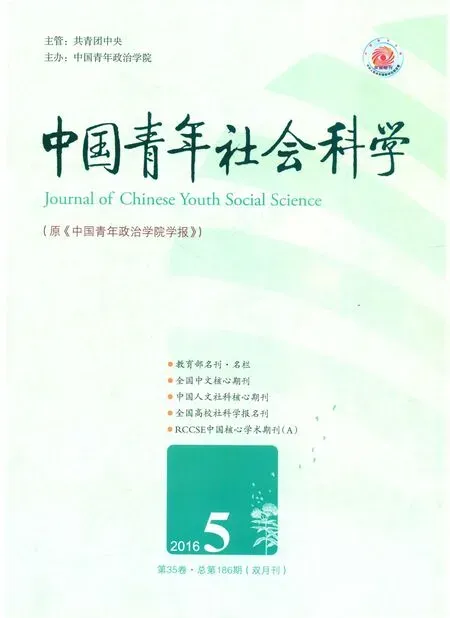康有为政治人格的形成与发展
■ 魏万磊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中文系,北京 100089)
康有为政治人格的形成与发展
■ 魏万磊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中文系,北京 100089)
康有为青年时期的认同危机未能正常解决,科举考试不顺利又加剧了这种认同失谐在其潜意识中的积淀,形成偏执型人格,其自负源自多次挫败形成的高度自卑,其武断源自启蒙教育中程式化的教育模式;康有为非白即黑的认知方式与其求知方式密切相关,有明显的“化约论”倾向,即重目标轻手段、重一般轻特殊、重整体轻局部,致使其在进化观上偏重“进”而较少考虑“化”、偏重整体渐进而否认局部突变。康有为情感强度极高,将情(包括自然情感与道德情感)奠基于“欲”和“性”的基础上,形成人欲即天理、导欲而不能去欲、情感期望高于现实需要的情感模式,并由此发展出一套为学、为人、为事的行为方式和话语系统。
康有为政治人格认同危机政治认知政治情感
在近代中国,康有为的影响力和引发的争议都是相当巨大的,正如李泽厚曾在香港发表谈话时所说的:“回顾百年以来,在观念原创性之强、之早,思想构造之系统完整,对当时影响之巨大,以及开整个时代风气等各个方面,康都远非严复、梁启超或其他人所可比拟。”[1]不管是康有为生前还是身后都有为他撰写传记和进行研究的。仅是康门弟子,就有梁启超和张伯桢(篁溪)所撰同名传记《南海康先生传》,以及陆乃翔、陆敦骏等各就其所见所闻写成的《新镌康南海先生传》,其中择其大端,叙述了康有为在各个领域的突出贡献。注重从学术意义上研究康有为思想的,除康门弟子外,还有著名学者李泰棻、孟世杰、杨克己、钱基博、钱穆、蒋廷黻、顾颉刚、周予同、侯外庐、赵丰田、宋云彬等人。
毋庸置疑,康有为有较为明显的疑古态度,而且常常有明心见理式的宗教狂想,他六经注我的学术态度和中西杂糅的知识结构发展出一套为学、为人、为事的行为方式和话语系统,成就了他从“儒家的马丁·路德”到“南海圣人”的转变。要解释康有为政治行为的内在动力和结构,离不开对他政治人格的研究,但是,从政治人格角度分析康有为的作品则寥寥无几,大多数学者也认可发生在康有为身上的一些难以用传统史学解释的现象。然而,单纯利用政治心理学的人格分析框架又有生搬硬套之嫌,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文化积淀显然是容易被忽视的社会心理环境要素。要揭示康有为由传统士子到改革主教转变过程中被遮蔽的关键质素,就需要从文本入手,条分缕析出其人格的形成与变化。本文择取文本分析的基本材料有三类:一类是康有为本人的作品,一类是同时期同侪研究康有为的作品,一类是当代研究者研究康有为的作品。对这三个维度进行综合考察不难发现,康有为政治人格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事件、关键人物和关键时间节点都具有重要意义。对康有为认同、认知、情感三个维度进行分析,是理解其偏执型政治人格形成与发展的重点。
一、康有为人格形成过程中的认同危机
康有为的启蒙教育以隔代教育为主,由于自身的天分和家庭背景,他所承受的心理压力较大。康有为自述家世时说,康家13世皆为士人,没有从事过其他职业,这种说法虽然有些言过其实,因为康家人经商、习武的都大有人在,但康有为也确实出身于官宦世家。他的高祖康辉(字文耀),在嘉庆时期中举人,曾出任广西布政使;他的曾祖康健昌(又名康式鹏),曾出任福建按察使;他的祖父康赞修(又名康以乾),曾任连州训导;他父亲康达初,也曾被录为江西补用知县。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康有为的母亲因为家中第一个男孩已经夭折急于接续香火,这对这个女子而言也构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因为“祖父母望孙切矣”,所有人对康有为的降生都充满期望。事实的确如此,加之自身早慧,康有为的幼年是在一个溺爱的家庭环境中度过的。1862年,5岁的康有为受到从伯父彝仲公的喜爱,开始接受启蒙教育,凭借能吟诵唐诗数百首,6岁时便以“鱼化龙”对“柳成絮”,从伯父大喜过望,赏以纸笔褒奖。对康有为进行启蒙教育的不仅是以男性为主,而且是以隔代教育为主,祖父辈不免对其过分关注,重学习监督而少情感沟通,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厚望其成为“将来大器”。“自八岁依于大父,饮食教诲,耳提面命,皆大父为之,亲侍十余年。”[2]由于祖父和众多学界名流交游甚广,幼年康有为随祖父四处游历,大大拓展了他的视野[3],这加速了其社会化的进程。
康有为很少在幼年经历中提到父亲,直到其9岁时,他才随父亲在任上南海学宫的崔清献祠中师从陈鹤侨先生,后又师从甲子年中举的梁舜门(健修)。但是仅仅不到两年的时间,1868年正月二十,康有为的父亲病故。在父亲弥留之际,他侍奉在侧,亲耳聆听了父亲的遗言,父亲要求他立志勉学、友爱姊弟。因为父亲去世,导致家庭经济拮据,10岁的康有为遭遇了人生第一次大变故。此后更是从原来富足的生活到“不能出游,不能购书,乃至无笔墨”,所以在康有为的儿时记忆中,尤为深刻的是母亲用私房钱应付家庭开支,尽可能让他不至于感受到生活变化得太突然。而此时的康有为虽然发奋努力,但却事与愿违,他在14岁和15岁时两次参加童子试,都未能考上。一个优等生的形象被摧毁,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心理上自然归因于科举本身的问题。但是不愿参加科举又显然和家人期望、社会评价不相符合,“于时益吐弃八股,名为学文,绝不一作,诸父极责,大诘之先祖前。”[4]康有为的认同对象是祖父以及家庭中的父辈男性,他不能违背父祖之命,但却无力展现自己的才华。
康氏家庭对康有为在科举考试上的投入是巨大的,除了父祖提供的大量藏书以外,1876年康有为第一次在广州参加乡试,未中,祖父便将他送到南海九江礼山草堂,拜康有为父亲的授业恩师、大儒朱次琦为师。不幸的是,康有为的父祖在有生之年都未能见到康有为在科举功名上有丝毫的成功迹象。光绪三年(1877年)五月,康有为的祖父去世,19岁的康有为自虐式地惩罚自己三天不吃不喝,一百多天里只吃咸菜,一年都穿着丧服,不沾任何荤腥[5]。父祖已经离世,但其所指示的科举之路仍然未能走通,科举考试对康有为而言不仅不是机会,而且还是羞辱。直到获得荫监生(父亲在任上殉职,因朝廷恩荫制度下恩诏而得)资格,康有为在科举道路上仍然十分坎坷。1878年康有为不想再参加科举考试了,结果被叔父督责,乃至断其资粮,才还乡继续乡试,但仍未考中。
毫无疑问,失去亲人的悲伤只是认同危机出现的诱因,前途茫然无望才是信心被摧毁的关键。至1878年初冬,康有为经历了人生第一次认同危机。根据他的自述,《四库全书》都看完了,每天埋头在故纸堆中,想想那些考据家著作等身,但究竟又有何用?“而私心好求安身立命之所,忽绝学捐书,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同学大怪之。以先生尚躬行,恶禅学,无有为之者。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忽思有亲不事,何学为,则即束装归庐先墓上。同门见歌哭无常,以为狂而有心疾矣。”[6]很多历史人物在无法完成自身定位、出现认同混乱时都有过类似癫狂的状态,像青年路德在修道院唱诗班突然牛吼般喊出“我是谁”,像洪秀全几次科举不中做“丁酉异梦”时的上蹿下跳,这次,康有为的“歌哭无常”也是能够理解的。家人的期待、世人对其官宦世家可能因其屡试不中而中断的社会评价、个人天分不差却数次折戟沉沙……所有这些压力让他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中爆发了。在他接受的启蒙教育模式中,“外王”之路的坎坷只能让他回归到“内圣”的反思中,显然,这样的心理防卫机制采取了“酸葡萄”式的合理化方式,其结果必然是产生对社会认可度较高的原有认同对象的攻击。
师生关系的不睦也预示了康有为试图以自己的力量突破认同混乱和传统思想的束缚。事情的起因源自对韩愈的评价所产生的分歧。在处于逆反期的康有为看来,韩愈所主张的“道”代表的恰恰是让自己无法翻身的社会正统的权威意识,所以在他看来,“昌黎道术浅薄无实际,言道当如庄、荀,言法当如管、韩,即《素问》言医亦成一体。若如昌黎,不过工为文耳,于道无与,《原道》尤极肤浅。”[7]言下之意,韩愈所原之“道”不过是“守先王”的虚名而已,于现实政治和思想进步并没有裨益。而康有为所推崇的“道”显然是改弦更张、应时而变的:“夫教之为道多矣,有以神道为教者,有以人道为教者,有合人、神为教者。要教之为义,皆在使人去恶为善而已,但其用法不同。圣者皆是医王,并明权实而双用之。”[8]康有为甚至认为,《易》中的精气、《大学》中的明德、《中庸》里的“天命”都是将“道”奠基在信仰的基础上。孔子是“人道设教”,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但君子有三畏,天命不可违。康有为显然也不信鬼神,但是他却相信“命运”,这表面看来似乎是矛盾的,但却恰恰是他理解的“道”之所在,因为他认为社会需要一种引人向善的外在力量,而这个外在力量就是“命”。
康有为对先贤韩愈的不敬让朱次琦感受到了这位徒弟的狂傲自负,但是他并未深加责罚,也未能通过理性争辩或者情感疏导的方式解决其认同危机,其结果是,康有为辞别九江先生,开始自己练习静坐。先练习五胜道,类似气功,让自己的灵魂出了自己的身体,看到自己身外有我,然后进入体内审视自己的骨骸。这一时期他还为《老子》做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飞魔入心,求道迫切”,但仍然没有真正地实现“皈依”,其实也就是没有正常地解决这次认同危机,直到他有了宗教体验。1879年正月,22岁的康有为入樵山白云洞苦修,“专讲道佛之书,养神明,弃渣滓。时或啸歌为诗文,徘徊散发,枕卧石窟瀑泉之间,席芳草,临清流,修柯遮云,清泉满听;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试之。始则诸魔杂沓,继则诸梦皆息,神明超胜,欣然自得。”[9]但是,这次宗教体验并未让他如有神助,1882年在老师朱九江先生去世的这一年,他五月份参加壬午乡试,仍然未中。三年一次的乡试让康有为在1885年再次遭遇失败。
1888年戊子年顺天乡试失败后,12月康有为第一次给清帝上书时,通篇只字未提对科举制度的不满,恐怕也是压抑心理造成的“故意的遗忘”。即便是临时增加的1889年己丑恩科乡试,康有为依旧未能如愿。直到1893年,35岁的康有为才得以中举。中举之后的1895年5月2日,康有为在第二次给清帝上书中就大段描写了科举制度“题难”“额隘”“不得不少变”,将改科举、重孔教作为重要的变法内容,这显然是对科举带来的心理伤害耿耿于怀,甚至为掩盖两年内连续两次落地之羞,不惜自毁声誉,在回忆自己乡试未中时故意作伪,说成是协办大学士徐桐从中作梗[10]。心理学研究表明,自负多半源自内心潜在的自卑感,科举考试的一系列挫败让康有为在解释失败时归因于科举制度或者他人的问题,从而以心理逃避机制完成了这次认同危机的过渡。
二、康有为认知模式中的化约论倾向
康有为对心与物的体认是传统的“内圣外王”式的,相信“明心”即可“见理”,“内圣”定可“外王”,这种认知方式显然与其求知方式密切相关。康赞修对长孙康有为疼爱有加,他的教学方式是:从儒学先贤的个人品质入手,先读纲鉴明古今历史发展线索后观大清会典、东华录通晓历史掌故,再习明史、三国志以求深入[11]。授业恩师朱次琦的教学方式大致类同,首先是道德和行为教育:敦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其次才是知识教育:经学、文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这样的“四行五学”之教首先将人的行为气质程式化,其次是议事论学都能从其中找到依据,非此即彼,认为一切现实问题的处理都能从所学的知识中寻求到答案。
康有为的认知方式中有明显的“化约论”倾向,他总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希望“一事片言而决”,所以导致很多判断难免会“不悉当者”[12],但即便如此他也坚决维护,绝不认错,更听不进善意的忠告。当朱次琦引导他走向孔子时,他充满自信地认为,自己找到了所有知识的源泉,也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于时捧手受教,乃如旅人之得宿,盲者之睹明,乃洗心绝欲,一意归依,以圣贤为必可期,以群书为三十岁前必可尽读,以一身为必能有立,以天下为必可为。”[13]既然处理任何问题都可以从知识中找到解决的办法,他对各种体系的知识进一步简化,将儒道合一,进而将春秋公羊学作为一切儒学的根本。“道教何从?从圣人;圣人何从?从孔子;孔子之道何在?在《六经》。《六经》粲然深美,浩然繁博,将何统乎?统一于《春秋》。……《春秋三传》何从乎?从公羊氏。……惟《公羊》详素王改制之义,故《春秋》之传在《公羊》也。”[14]浩繁庞杂的儒家学说被归根到一本《春秋公羊传》身上,而现实中的所有知识都可以在此基础上叠加。康有为显然认为,人类的所有知识都是可以统一在一起的,因为其正确答案只有一个;至于方式方法,也应该能够统一,因为其本源是唯一的。
这种辐合型认知模式使康有为能够将一切知识杂糅起来,并将是否实用作为判断知识有无价值的标准。根据康有为的记述,自己幼年曾一度从早到晚地读书,祖父怕他伤身体,“戒令就寝”,但他仍旧在帐中点灯,偷偷读书,这偷偷看的“邸报”(官方报纸)是为了了解当朝时事[15]。这说明康有为童年时即抱有经世致用的好奇心。即便是授业恩师朱次琦,除了预备他能应考试、取科名外,还“特别注重中国政治体制的沿革和一般所谓经世致用之学”[16]。
康有为是同时代较早接触西学的人,梁启超是光绪十六年(1890)在上海坊间看到一些中译西书的,可是康有为早在同治十三年(1874)即在梁启超出生的第二年,就在自家澹如楼读到了《瀛寰志略》《地球图》等经世之文。樵山苦修时他又遇到了他一生中的“重要他人”。翰林院编修张延秋(鼎华)与当朝四五人游樵山,相与议论康有为,“但见一土山,惟见一异人”[17]。正是由于这样的“品状”,才使得康有为逐渐声名鹊起,恍若仙人,形象神秘。他有感于张延秋知遇之恩,得以从他那里了解到更多的入世信息。他开始读一些经世致用的书,如《西国近事汇编》之类的新读物,从他那里“接触到一些西方近代的资本主义思想以及当时正在酝酿中的改良主义思潮”[18]。直到1879年底游历香港,康有为真实地感受到了两种文明之间的巨大差异,“览西人宫室之琼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19]由于这种对比使得中西方之间优劣立见,他重新查阅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买了已经翻译的西方书籍,开始了在中学基础上的西学嫁接。1882年11月份他赴京考试,回来途中他在上海购买了很多西方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的书籍。“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十一月还家,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20]一个事实是,他从上海回到广东后,立即订购了《万国公报》。有人做过统计,康有为在其后的几年里,所购图书三千余册,相当于江南制造局三十年内出版西书的四分之一,数量之大,达到惊人的程度。
正因为自认为悟透世间所有知识,1885年2月23日,康有为头疼大作,觉得马上就要不行了,他也确信自己能够完成上天交付的任务,自己拯救自己:“日读医书,继而目疼不能视文字,医者束手无法,惟裹头行吟于室。”当确信自己有可能天命不久,他还保持着高度的热情,用著书的方式来完成普度众生的职责,“数月不出,检视书记遗稿,从容待死,乃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以为吾既闻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21]这里的“人类公理”有人认为是《大同书》,有人认为是《实理公法全书》,不论是哪一本,都是在论证整个人类社会的运行机制和趋势。在《实理公法全书》中,康有为借助欧几里得《几何学》里的定义、定理、公式、证明的自然科学逻辑推演路径,用实理、公法、比例、按语等论证人类社会的政治法则和伦理法则,实际上康有为就是要使一本《实理公法全书》成为人类社会一切义理和制度的经典教科书,完成人类社会行为法则的设定,足见其认知方式中的“化约论”倾向是何等严重。
康有为的认知方式促使其世界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相信“法后”比“守先”更接近原典意义上的儒学。康有为自述他6岁开始读经,12岁接受和吸纳了经学的知识以及先秦及宋儒的经学观念,到27岁时他读尽了汉魏六朝唐宋明乃至他所在时代的义理考据之说,之后理解了孔子并非如在宋儒眼中的那么狭隘;由宋入汉,理解了经学并非如汉代一样杂乱无章;由经入史,决然抛弃古文经而转向今文经,“厉节行于后汉,探义理于宋人,既舍(郑)康成,释(朱)紫阳,一一以孔子为归。”[22]这说明康有为已经抛弃了郑玄经古文学“我注六经”的态度,同时也改变了对程朱理学的看法,从而获得了事物发展的唯一真理,而这个真理本身就存在于孔子那里,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道”就是“公羊三世说”。他兴奋地记载了自己发现真理的过程:“读至《礼运》,乃浩然长叹曰:孔子三世之变,大道之真在是矣。大同小康之道,发之明而别之精,古今之故,神圣悯世之深,在是矣;相时而推施,并行而不悖,时圣之变通尽利,在是矣。”[23]由孔子作《春秋》的“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发展到“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公羊三世说”成为康有为政治变革的道统依据,这是一种新的历史观和进化观,是对传统认知方式的一次颠覆。这种进化论观念明显带有本土特征,绝非西方意义上的进化论思想,它改变了以过去为中心的历史意识,抛弃了朱熹建构起来的天理世界观,而将社会意志及其历史规律作为现代公理提出来,以此作为政治发展的合法性依据。
康有为同时将“公羊三世说”作为判断人性进化的尺度,将道德进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和政治体制嬗变的动力和根本,这种重道德而轻制度的思想倾向带有明显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这种既溯源于传统又要破旧立新的思维方式让他的进化论观念只能是渐变论。他推崇孔子,正是由于“时圣”孔子高于清圣(如伯夷、叔齐一样节操清高的圣之清者)、任圣(如伊尹一样具有历史使命感的圣之任者)、和圣(如柳下惠一样大材小用而仍兢兢业业的圣之和者)的地方,在于其能够“主乎与时进化则变通尽利”[24]。不仅如此,孔子还将各种知识打通,通晓社会发展规律用以预测未来,“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詹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赜……以三统论诸圣,以三世推将来。”[25]所以这种将传统视为根源,同时在传统基础上发展变化的认知方式不可能是“断裂历史”的,其内涵的“渐变论”观念也让康有为终其一生坚信政治体制无法实现跨越式突破:“人道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为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由独人而渐为夫妇,由夫妇而渐为父子,由父子而渐兼锡尔类,由锡类而渐为大同,于是复为独人。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26]如果不由君主立宪制直接实行共和制,会导致暴民政治的出现,“可以亡国”[27]。
这样的认知方式常常带来理想与现实失调的矛盾,一方面,康有为有无力立刻改变国家现状、羡憎交织的忧伤。譬如看到香港的繁华和内地的破败,康有为充满羡慕之情,他在诗中写道:“灵岛神皋聚百旗,别峰通电线单微。半空楼阁凌云起,大海艨艟破浪飞。夹道红尘驰骠袅,沿山绿囿闹芳菲。伤心信美非吾土,锦帕蛮靴满目非。”[28]另一方面,康有为又深信他明白了人类进化的公理,拥有天降大任、挽既倒于狂澜、舍我其谁的豪迈,相信祖国一定会不断进步,走在世界前列。所以在中国遭受多次侵略举国一片哀叹、士子们万马齐喑的情形下,他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拯救苍生的自信。1904年6月,康有为从香港出发经海路游历欧洲,当航船驶过地中海,他发出了激情澎湃的咏叹:“滔滔洪波,邈邈天幕,几世之雄,赋诗横槊。……呜呼!文明出地形,谁纵天骄此浃渫。”[29]丝毫看不出他有些许的悲观失望。
三、欲望引导理性的情感模式
康有为认为,只有尊重人的天性,满足人的自然欲求,才符合正常的人类情感。正如康门弟子所看到的,在康有为身上,有很多似乎非常矛盾的情感体验:“他每天戒杀生,而日日食肉;每天谈一夫一妇,而自己却因无子而娶妾;每天讲男女平等,而其本家之女子未尝独立;每天说人类平等,而自己却用男仆女奴。”[30]的确,康有为除了大夫人张云珠以外,娶妾仅有姓名可考的就有5人:二姨太梁随觉(娶时17岁),三姨太何旃理(美国华侨、娶时17岁),四姨太市冈鹤子(日本女仆、娶时17岁),五姨太廖定徴,六姨太张光(娶时19岁),除了二姨太,在娶其他妾时康有为已经是五十岁开外的人了,钟鸣鼎食的生活加上庞杂的门生故旧和食客的赀费让人咂舌。
其实从康有为的情感模式上很容易理解,在现实中,完全可以认为康有为是一个快乐主义者,是崇尚感官享受的。他不仅希望废除家庭和婚姻,而且对性的看法极为前卫,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也是率性纵欲的:“凡有色欲交合之事,两欢则相合,两憎则相离,既无亲属,人人相等。夫宽游堤以待水泛,则无决漫之虞,顺乎人情以定礼律,则无淫犯之事矣。夫人禀天权,各有独立,女子既不可为男子之强力所私,其偶相交合,但以各畅天性。若夫牝牡之形,譬犹锁钥之机,纳指于口,流涎于地,何关法律而待设严防哉?筑坚城者适召炮攻,立崇堤者适来水决,必不能防,不若平之,故不若无城无堤之荡荡也。”[31]但他认为这种状态的到来只能靠人性疏导而不能靠制度安排来实现。朱熹理学接近墨家,灭人欲违反孔子之道,而“孔子之道本诸身,人身本有好货、好色、好乐之欲,圣人不禁,但欲其推以同人。盖孔孟之学在仁,故推之而弥广,朱子之学在义,故敛之而愈啬,而民情实不能绝也”[32]。
康有为重视欲望的满足,并认为现实的制度安排是灭人欲的罪魁祸首,所以对过去和现在非常焦虑,而对未来充满期盼,这也就是他改制的原因。《大同书》前几章都是在描写人类社会现实中各种各样的苦,康有为将现世的苦归结为制度的苦,而非根源于人欲,相反他对人欲是推崇的。他也曾尝试在现实中严格约束自己的欲望,譬如在祖父1877年5月去世时,他就按照古礼的要求,守了半年多的孝,“与诸父结苫庐,棺前縗绖,白衣不去,身不肉食,终是岁。于时读丧礼,因考三礼之学,造次皆守礼法古,严肃俨恪,一步不逾。”[33]但是,一个事实是,1878年冬天(12月21日),康有为的长女康同薇出生,这说明康有为在为祖父守丧期刚一结束就不再禁欲,这也验证了康有为对“人欲”的看法。在传统内圣外王的社会化方式中,诚意、正心、修身是道统,不仅政统(齐家治国平天下)要受此制约,而且学统(格物致知)也是为道统而存在的[34]。但康有为的情感模式在此基础上又分为两个层次:理想与现实。当理想社会的阶段尚未来临时,一切从俗也是绝对不能跨越的。譬如就吃肉而言,现阶段也无法实现完全禁绝,但未来是可以实现的:“大同之世,至仁之世也,可以戒杀矣。”[35]
康有为对自身价值感的体认超乎常人想象。他相信自己出生是上天的安排,他在诗里描写了自己出生时的异兆:“维吾揽揆辰,五日月维二;大火赤流屋,子夜吾生始。”[36]这种状态并非心理自骗机制的结果,而是早年认同危机没能积极解决之后,认同对象反转投射到自己身上所产生的高度自恋。1888年他第一次上书清帝时,在路上遇到了菜市口行刑的场面,他感到大不吉,家里尚有老母,自己绝不能死,但转念一想,一切皆由天命,不必犹豫。“既而思:吾既为救天下矣,生死有命,岂可中道畏缩,慷慨登车,从东南绕道行。”[37]即使戊戌政变失败后,遭遇重大挫折的他仍然认为,这不过是上天的考验,他在日本对友人说,自己之所以能够多次死里逃生,正是因为上天要他拯救中国,拯救世界:“曲线奇巧,曲曲生之。留吾身以有待,其兹中国不亡,而大道未绝耶?……顺天俟命,但行吾不忍之心,以救此万民耳!”[38]
康有为的“场独立性”很强,对待事物常常作尖锐化处理,绝不容忍丝毫的变通。正如梁启超对康有为的评价,他可以把任何手段拿来为目标服务,而绝不迁就妥协:“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39]一旦有人反驳,康有为总是认为对方浅薄、不值得争辩:“道之不行久矣,孤鹤之难鸣甚矣。”[40]在为人处世和性格上的巨大差异也成为后来师徒二人心存芥蒂的根源,梁启超晚年叹息:“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亦有然。有为常言之: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则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41]
康有为的情感强度极高,一旦认定的事情绝不会更改,而且会主动寻求自己的解释逻辑以加强其观点。正如梁启超对他的评价,康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说我”[42]。康有为对特殊事物尤其是对性的看法极其开放,他认为虽然人欲是无法禁绝的,但可以引导欲望合理发泄。在康有为看来,没有欲望就没有生命,佛家以保守灵魂为欲,儒家以仁义为欲,应该尽可能满足人的本性所需,将其个体欲求扩充到更广更高的社会追求上,从而将情感之欲转化为理智之欲。“无如不能制断不忍之欲,亦姑纵之。竭吾力之所能为,顺吾性之所得为而已。”[43]他主张一个女子可以有多个性伙伴,允许男子在医嘱下与孕妇发生性关系,“有孕之妇入院后,自以高洁寡欲、学道养身为正义,虽许其与诸男子往还,若其交合宜否,或与一男或多男交合宜否,随时由医生考验。生产之道与交合之事碍否,及与一男之交合若众男之交合碍否,或定以月数,或限以人数,务令于胎元无损,乃许行之。”[44]自由与否也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在未来的社会发展阶段——太平世,他甚至认为,在基于二人同意的基础之上甚至允许同性恋,但不允许兽交。制度只能为人性服务,“其有欢合者,不论男女之交及两男之交,皆到官立约,以免他争。”[45]
综上所述,康有为幼年时以祖父作为认同对象,青年时期因科举考试屡次失利出现过认同混乱,他的认同危机未能及时解决,偏执型人格显而易见。康有为认知方式的形成与其经世致用的社会化方式密切相关,他的认知风格偏重目标而轻视手段,一切资源都可以为目标服务,并且很少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而这种认知方式促使他较早地在本土资源中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形成了自己的进化论观念,并进而影响到其世界观的变化。康有为对性、婚姻、家庭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宇宙的看法奠基在人欲基础上,这起源于其从小形成的心理图景,在一系列抑制、升华、投射等心理机制的作用下,他的情感期望较高,情感强度较大,而且场独立性较强,这些都造就了“南海圣人”的底色。
[1]李泽厚:《李泽厚近年答问录》,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页。
[2][3][4][5][6][9][11][13][15][17][19][20][21][25][33][38]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2种)》,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2、6、7、8、9、4、7、9、9、9-10、11、13、13、7、29页。
[7]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载《追忆康有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82页。
[8]《康有为全集》(第7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4页。
[10]张勇:《康有为的“作伪”及其限度》,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
[12][3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8、87页。
[14]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页。
[16]蒋廷黻 :《中国近代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18]马勇:《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
[22]康有为:《朱九江先生佚文序》,载《不忍杂志汇编》,初集(1914)卷五,第14-15页。
[23]康有为:《孟子微》,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6页。
[24]《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68页。
[26]康有为:《论语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62页。
[27]《康有为政论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99页。
[28]马洪林:《康有为大传》,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
[29]《康有为全集》(第1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9页。
[30][37]陆乃翔 陆敦揆:《康南海先生传》(上编),广州:万木草堂刊本1929年版,第48、14页。
[31][35][44][45]康有为:《大同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0、434、163、311页。
[32]康有为:《孟子微》(卷四),上海:上海广智书局1916年刊本,第16页。
[34]王小波等:《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页。
[36]赵丰田:《康长素先生年谱稿》,北京:崇文书店1975年版,第175页。
[40]康有为:《致高丽某君书》,载《万木草堂遗稿》(卷五),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458页。
[41]丁文江 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3页。
[4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129页。
[43]康有为:《康子内外篇(外六种)》之《不忍篇》,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5 页。
(责任编辑:王俊华)
2016-06-08
魏万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本文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一般项目“康有为政治人格研究”(课题编号:1890708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