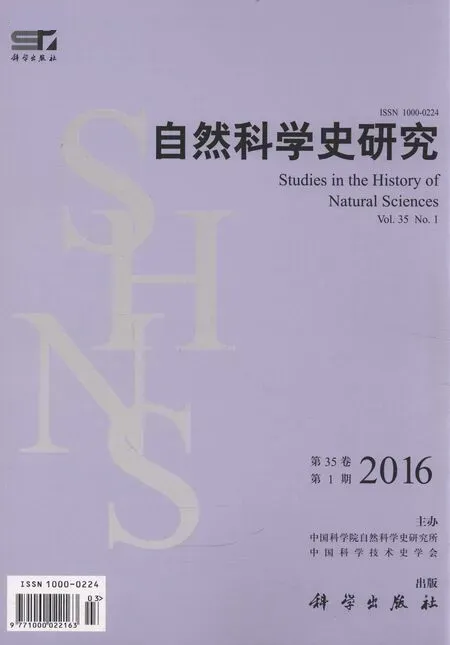儒学与科学关系再研讨
——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第9期泰山学术沙龙侧记
儒学与科学关系再研讨
——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第9期泰山学术沙龙侧记
2015年12月6日,由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举办的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第9期泰山学术沙龙在山东大学召开。沙龙领衔专家为山东省政府参事、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马来平教授。台湾东吴大学原校长刘源俊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所长刘钝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韩琦研究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尚智丛教授等近20位专家和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纪洪波等出席了沙龙。在去年召开的第3期泰山沙龙——“传统文化与中国科技的命运”的基础上,本次沙龙围绕“儒学的人文资源与科学”这一主题,按照“格物致知与科学的关系”、“《周易》、阴阳五行与科学的关系”、“儒家学派与科学的关系”以及“康熙帝与科学的关系”等专题,再度就儒学与科学关系展开研讨。
1 格物致知与科学:不相关还是具有亲和性
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畴,格物致知与科学有什么关系?这是深入探讨儒学与科学关系不可回避的问题。
山东大学何中华教授认为,格物致知与科学没有直接关系,或者说二者“不可通约”。从趋向上讲,“格致”的概念是由内而外展开的,科学则是由外而内的,二者是异质的;从对象上讲,格致之“物”与科学认知之“物”完全不同;从目的上讲,程朱格物的目的不是为了科学认知,而是为了道德修养。
马来平教授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指出,从对象上来讲,格致之“物”既包括“内事”亦包括“外事”,其“外事”即客观外物。而这种对象性的客观外物与科学认知领域的客观外物是有一致性的,并非完全无关。从目的层面来讲,尽管格致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道德修养,但在格致的过程中,的确包含了对客观外物及其规律的认知探索,这亦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马教授通过回顾格物致知的历史演变过程,深刻阐发了格物致知的认知内涵,有力回应了上述质疑。他指出,格物致知概念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重大转向,第一次是程朱理学格物致知说的形成,第二次是明清之际实学思想家格物致知观的转向。就第一次转向而言,尽管格物致知所呈现出来的认知含义还不清晰,但是它引导人们留意外物,鼓励人们在思考事物“所当然”的同时,也要思考事物的“所以然”。“所以然”未必是指关注事物的本质或内在根据,但已经有了这种倾向。因此,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说,在提升格物致知在儒学中地位的同时,客观上也使得格物致知在儒学内部开辟了一条自然研究的路径。就第二次转向而言,格物致知经由其派生的格物穷理概念对科学起到了双重正面作用。其一是促进了西方科学的传播,传教士以格物穷理的名义传播西学,大大减少了传播过程中随时可能遇到的种种阻力。其二是推动了中国古代科学的转型。明清之际的一些士人在西方科学和中国科学都是格致之学的前提下,提出了“西学中源”说。尽管“西学中源”说有失偏颇,但在实际上中西科学会通十分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古代科学即中国传统科学向近代科学的转型。这其中,格物穷理观念起到了中西会通的前提性作用。格物致知说的两次重大转向表明,作为儒学核心概念的“格物致知”与科学是有亲和性的。
尚智丛教授进一步从认识论角度讲述了格物致知与科学的亲和性。他指出,朱熹强调“格物-穷理-致知”的认识顺序,认为穷理之方法就是通过读书、论古今人物或应接事物等学习、实践活动,经过日积月累而达到顿悟。从认识论角度来讲,格物致知强调了认识对象的客观本质的存在,强调了认识活动的经验主义倾向。17世纪发展起来的近代科学主张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结合,强调实验方法、归纳方法与数学的演绎方法并重。从这一角度来说,朱熹的格物致知与近代科学不存在矛盾,相反有其一致的方面,即都存在经验主义的认识倾向。
2 《周易》、阴阳五行与科学:无用还是价值巨大
《周易》乃儒学“六经之首”,阴阳五行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它们与科学是什么关系呢?
一些专家认为,《周易》不能用于现代自然科学,阴阳五行观念已经过时:“《周易》讲生生之谓易,但如何分为阴阳、乾坤、八卦?这套东西今天不能用。科学家还讲什么八卦、五行,无聊,谁理你。”
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宋芝业副教授不同意《周易》对现代自然科学无用的观点。 他以清代为例,讲了易学对数学的促进作用。他指出,从总体上讲,易学与数学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且易学对科学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首先,以数学诠释《周易》,有助于催生数学成果。一些数学著作由对周易命题或概念的诠释而产生,如陈厚耀的《错综法义》就是通过诠释周易的命题或概念而自成体系。第二,以《周易》诠释数学,有助于数学成果的广泛传播。一些数学著作援引《周易》的编排形式以及卦画组合方式,这有利于对数学内容的理解。如汪莱的《递兼数理》就借助《周易》的卦爻系统而展开。第三,《周易》为数学的研习、传播以及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土壤。《周易》讲“大衍之数”、“天地之数”,对数持欢迎态度。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使得对数学的研究不再是“小技”,而是一种“赞天地之化育”的圣人之学。显然,这种对数的表彰大大有利于数学的传播和发展。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周易》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备受关注。“科学易”这一概念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并出现了不少的研究成果。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周易》对于现代自然科学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阴阳五行观念真的已经过时了吗?山东大学王新春教授从阴阳五行观念的历史演变回应了这一问题。他指出,阴阳五行学说在先秦时期确立,到了战国尤其是秦汉以后,逐渐成为中国人的基本常识和思想模型,生活世界乃至宇宙人生的场景均由此构建和衍生。他认为,阴阳五行是我国哲学特有的一种模型,这种模型贯穿到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并深刻塑造了传统科学。如,汉代的“卦气说”用阴阳观念来解释一年四季气候的变化;宋代的沈括用五行生尅理论来解释其水法炼铜;中医的脏象理论亦与阴阳五行学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阴阳五行观念今天看来仍然有巨大的文化价值。
山东中医药大学祝世讷教授认为,阴阳学说与自然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内在同一”。首先,阴阳学说与自然科学交叉于阴阳规律。在古代,哲学与科学尚未分化,各种知识和智慧都融合在自然哲学中。那时对自然界的阴阳规律的认识,尚未分为哲学研究与科学研究,科学认识和哲学思考融于一体。其次,中国古代科学成果中贯穿着阴阳规律。阴阳规律作为自然界的基本规律,人类从诞生开始,就直接地面对它,使其成为生产和生活中必须研究和处理的对象。在中国古代自然知识体系中,对阴阳规律的认识和总结,带有基础性和纲领性的意义。第三,20世纪以来,现代科学对世界深层本质的研究,所揭示的新的特性和规律,在原理上与阴阳学说高度一致,证明阴阳规律的普适性与深刻性。现代科学特别是其最新发展,与阴阳学说越来越紧密地走到一起。
3 儒家精神气质与科学:对立还是一致
从精神气质上看,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沙龙上,有学者认为儒家具有反智倾向,在这一点上,是与科学格格不入的:“虽然儒学有很多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其反智的因素、反智的思维,盲目地相信权威。”
身为物理学家的刘源俊教授坚定地主张,儒家有很强的科学精神。他认为,学问有三个层面:知识层面、方法层面、精神层面。从知识层面来讲,儒学和科学是两回事,但是从方法层面来看,儒学和科学相差并不多。“学问”一词,出自《中庸》。《中庸》讲“博学之、审问之、明辨之、慎思之、笃行之”。“博学之”指广泛并仔细观察和搜集事实,“审问之”是挑选其中有用的信息,“明辨之”是预测并进一步验证,“慎思之”是形成概念并构建理论,“笃行之”是付诸行动。这跟现代科学的方法很接近。从精神层面来讲,原始儒家的许多说法都是合乎“科学精神”的。如孔子就是极为理性的人,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主张“不语怪力乱神”,还强调“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些都是科学精神的极佳诠释。
对儒家是否盲目迷信权威这一问题,山东大学常春兰副教授指出,其实儒家有很强的怀疑精神。她认为,在儒学传统中,对占卜、星命、堪舆、骨相、时日吉凶的选择和鬼神传说持怀疑态度者不乏其人。这种怀疑态度发展到乾嘉考据学已然成为一种方法论了。当然,儒士们的怀疑态度不是怀疑论,却与科学所需要的怀疑精神相接近,因而在接受西方科学中起了某种积极的作用。
湖南师范大学徐仪明教授以儒家“医孝合一”的观点阐述了儒学对医学的促进作用。“医孝合一”在历史上曾经两次推动了医学的发展。从深度上讲,这个观念促进医者去深入钻研医术,以使自己达到精益求精的程度;从广度上讲,则从客观上鼓励儒家知识分子学习医术医道。
厦门大学乐爱国教授指出,儒家精神对于古代科技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就积极作用而言,中国古代科技形成、发展于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并在这一文化背景中发展至高峰;且儒家的务实精神促进了中国古代实用科技的发展。就消极作用而言,在儒家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古代科技,在整体上始终处于儒学的统摄之下,而没有完全与文化脱离开来,缺乏独立性;且儒家的务实精神又往往容易导致科技在理论方面的不足,造成中国古代科技理论性的薄弱。
4 康熙帝理学治国与科学:功过怎样评说
康熙帝热心科学,乃是不争的事实。耐人寻味的是,高举理学治国大旗的康熙时代,中国却没有像西方那样发生近代科学革命。那么,康熙帝理学治国对近代中国科学的发展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这又折射出儒学与科学什么样的关系?
刘钝研究员讲述了康熙帝改用几何原本的过程,肯定了康熙帝对于科学所作的贡献。康熙曾于1668年向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学,所用教本为利玛窦、徐光启翻译的克拉维斯评注本。20年后,白晋、张诚成为康熙帝的宫廷教师。他们先用满语讲授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由于康熙已有一定基础,不久就要求他们用尽可能少的时间讲授几何学中最实用的部分。两位教士在征得康熙同意之后,自1690年3月开始改用法国耶稣会数学家巴蒂编译的《几何原本》为教本,并将巴蒂的书译成满、汉两种文本。汉文译本后来被收入康熙御制的《数理精蕴》,成为其上编“立纲明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刘钝研究员指出,西方的几何学知识就这样以一种实用主义的面貌为更多的中国学者所理解和接受,这一过程与清初学术思潮从理学向实学的转变是相契合的。
对康熙与科技一向有精深研究的韩琦研究员考证了康熙帝一生所从事的种种科学活动,如潜心学习西学、翻译《几何原本》、组织编纂《律历渊源》、建立蒙养斋算学馆、进行地理大测量等,进而肯定了康熙帝对于科学所作的贡献。他强调,康熙从事科学活动主要是出于治国的需要,如治水、河工、测天量地等,同时也是为了“控制汉人”,提高满族人在汉族人心目中的地位。康熙对科学活动的重视,让一些文人认识到了数学的重要性,大大促进了数学的发展。但是,康熙在相当时间内垄断了部分西方科学知识,秘而不宣,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
山东师范大学的肖德武教授认为,康熙王朝是西学东渐的一个关键时期,但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期科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康熙帝本人的贡献,存在一些模糊的认识和争论。对相关问题进行澄清和辨识,不仅有利于人们准确、全面地认识该时期的科学发展史,还可以开辟一个研究儒学与科学关系的新途径和新视角。
较之去年,本期沙龙将主题划分为若干专题,并且适当延长了每一主题发言后的答辩和讨论时间。会议开得紧凑而热烈,争锋迭起,但和而不同,始终弥漫着一派儒雅的气氛。专家们提出的许多观点对进一步深化理解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学术和实践价值。出席本次沙龙的媒体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众日报》、《中华读书报》等。与会专家现场发言将在会后另行整理出版。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苗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