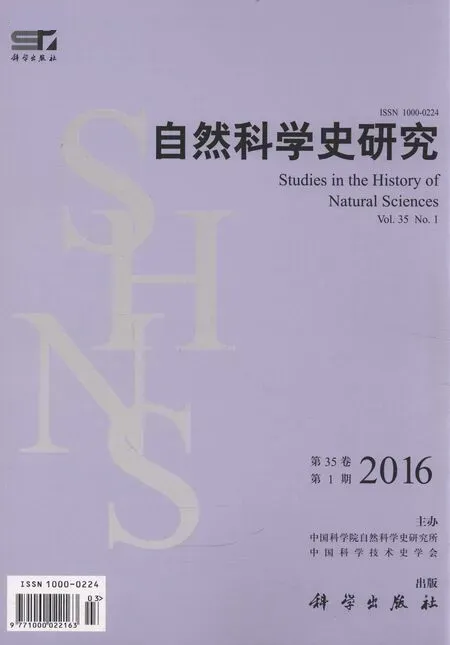康熙帝之治术与“西学中源”说新论
——《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的成书及其背景
韩 琦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康熙帝之治术与“西学中源”说新论
——《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的成书及其背景
韩 琦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明末清初西学传入中国,为达到引进之目的,出现了比较中西学术的各种说法。《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这篇由康熙帝亲自撰写的历算短文,首次明确表达了“西学中源”的观念。本文依据中西文献,特别是宫廷学者之文集,对该文写作背景、动机以及反响作深入之探讨,确定该文完成于1703年。并指出正是由于康熙的宣讲,使“西学中源”说从庙堂之说成为文人的谈资,以梅文鼎为代表的诸多文人的迎合响应以及转述,使此说成为影响清初学界的重要论说,对康熙时代乃至后来的历算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西学中源 数学 康熙 梅文鼎 《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
康熙帝的文治武功,乃至对西学的兴趣,近来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作为康熙帝唯一存世的算学论文,在清初学术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康熙帝撰写此文的确切时间、写作背景和动机如何?有何反响?对此迄今未有系统准确之阐述。本文依据中西文献,特别是宫廷学者之文集,试图对上述问题作深入探讨,并对该文形成的年代提出新说。
1 《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的写作时间
《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是一篇论述三角形的短文,其文不长,现照录全文如下:
三角形推算法论
孟子曰:规矩,方圆之至;圣人,人伦之至。益见规矩方圆乃数学之根本,太极两仪之变化也。三代以上,人心尚实,有学必精,所以考定日月之盈缩、七政之参差、鸟兽草木之应候,又以闰月定四时,庶绩咸熙者,岂偶然哉?古人璿玑齐七政,表度准南北,察两至明太阳之回转,识二分为寒暑之变迁。日月星辰交食、凌犯、入差、清濛地气之考,苟非测量,难得其详;虽有测量而无推算,势不可成。所以古人以圆容众角,众角容方,自方而三角,勾股在其中矣。勾三股四絃五者,以直角而论,乃一角九十度,并两角又九十度,即成半圜一百八十度也。若非直角,出入九十度内外者,勾股之所不能推。虽分作直形,奏(凑)合偶成,亦非数家之堂奥,何足论哉!上古若无众角归圆,何能得历之根而成八线之表?皆因习俗就易畏繁,以功名仕宦为重,敬天授时为轻,故置而不问,以至如此。康熙初年间,以历法争讼,互为讦告,至于死者,不知其几。康熙七年闰月颁历之后,钦天监再题,欲加十二月又闰,因而众论纷纷,人心不服,皆谓从古有历以来未闻一岁中再闰,因而诸王九卿等再三考察,举朝无有知历者。朕目覩其事,心中痛恨,凡万几余暇,即专志于天文历法二十余载,所以略知其大概,不至于混乱也。论者以古法今法之不同,深不知历。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疎密,非有他术也。其名色条目虽有不同,实无关于历,原所系于岁修察考之密,方圆众角之推算,测量经纬之离合。则历法行之千年,何弊之有?三角者,圜方众角之尽,精微易晓,舍此而他求,必致混杂,历不可成矣。唐一行、元郭守敬,不过借回回历少加润色,偶合一时而已,亦不能行久。可见出自意见,非有根基于算术也。历本于测量,终于推算,授之于民时,验之于交食,岂能逃于众目之所观乎?*据日本早稻田大学藏满汉合璧单刻本。现存《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有三个版本,一是康熙时代单刻本,一是《满汉七本头》本(约1707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均为满汉合璧;此外还有《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本(康熙53年内府刊本,第3集卷19)。《满汉七本头》内《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约1707年刻本,同函内有武备院员外郎和素1707年为《潘氏总论》写的序)。与满汉合璧本相比,《御制文集》本对个别文字已略有修订。蒙承志兄告知,柏林德国国家图书馆也藏有满汉合璧单刻本。
此文道出了康熙对传统勾股术和西方数学的看法,重温自己致力于学习西学的原因,最后指出历法源自中国,传于极西,明确提出了“西学中源”说。*关于“西学中源”说的最早论述,参见全汉昇:《清末的“西学源出中国”说》,《岭南学报》,1935年,4卷2期,57~102页;李兆华:《简评西学源于中法说》,《自然辩证法通讯》,1985年第6期,45~49页。
《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的写作时间,对厘清康熙时代“西学中源”说发展脉络至为关键,然而此文未署年月。金福曾推断《三角形推算法论》成书于1704年[1],现据新发现的史料,对成书年代提出新说。*笔者首先指出《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成书于1703年,参见Han Qi, “Knowledge and Power, A Social History of Transmission of Mathematic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during the Kangxi Reign (1622- 1722)”, Th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athematicians, vol. IV, ed. S. Y. Jang, Y. R. Kim, D.-W. Lee, and I. Yie. Seoul: Kyung Moon Sa. Co. Ltd., 2014, 1217- 1229.
宫廷官方文书如《起居注》、《圣祖实录》等,都没有提及此文;而一些康熙帝身边官员的文集,却常常记录皇帝的言行,可补充官方资料的不足。翰林院南书房的文人因与皇帝多有接触,留下的记载最多,不仅有扈从日记问世,文集中也多有“纪恩”诗,记述对康熙帝的感恩之情,从中可以觅得一些该文的蛛丝马迹。
査慎行(1650~1727),字他山,海宁人,康熙年间在宫廷任职,留下的材料也最多。在其《陪猎笔记》中,笔者发现一则史料,恰可为《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成书时间提供新的证据。书中记述了癸未年(1703)五月二十五日,康熙帝前往塞外之事,他和汪灏、钱名世等随驾同往,*《陪猎笔记》国家图书馆藏抄本。往返三月余。七月十一日有这样记载:“午刻传旨,问汉人中有熟精算法者,令各举所知。臣等回奏云,不敢妄举。少顷发下《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一篇,阅毕仍缴上。”次日,又谈到此文:“昨日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末后复补一段,赐臣等共阅”。
康熙自幼年起跟随传教士学习西学,倾注了大量心血,随年纪学识增长,偶有所得则沾沾自喜,并时时藉此考察汉人。康熙避暑期间撰写此文,并“问汉人中有熟精算法者”,亟待向擅长算学的汉人炫耀。翌日又补入一段,重新发下,从这一细节可知康熙对此文极为重视。
除了查慎行以外,同行的汪灏也曾提到:“七月十一日,颁示《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七月十二日,上复以三角形颁示,谕云:‘三角形之法,始自中国,流播西洋。今中国失传,而西洋仍留此学。朕年十四,因历法一案多伤人命,遂于万几暇时参详会悟,得其秘妙。’”[2]康熙对大臣重提康熙初年的历法之争,并当面阐述“西学中源”论,给随行大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查慎行、汪灏两人所记时间一致,表明康熙帝曾连续两天和汉臣谈论《三角形推算法论》,于七月十二日明确提出“西学中源”论,并将此论补入,成为《三角形推算法论》中最后一段的内容,这与现存满汉刻本若合符节。综上所述,康熙于万几余暇,酝酿多时,写成《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在1703年即已告成,成为宣扬“西学中源”说的重要作品。
癸未年康熙的随行人员中,除査慎行、汪灏、钱名世外,还包括查昇(1650~1708)、陈壮履、励廷仪、蒋廷锡和汪士鋐等人,均在翰林院南书房供职。汪士鋐对康熙帝此次出塞则有更详细的记述,还专门赋诗,其中第十首为:
宣夜周髀久乏传,圣人筹筭独先天。形成《三角》微茫辨,万古玑衡日月悬。上以从来造历之家未得其源,故积久而差,特御制《三角形论》,推测尽善。[3]
该诗与《陪猎笔记》的记述可互为佐证。显见,汪士鋐也肯定看到过康熙帝《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此诗还将周髀之说与三角并列,间接隐含了“西学中源”说。
此外,查慎行还在《人海记》中再次提到康熙的这篇短文,并记述了康熙帝对算学的浓厚兴趣以及亲自演示:
皇上精于算学,尝著《三角形论》以示内廷诸臣,茫然无有解者。一日面示臣等算法,先聚米一堆于案上,用软尺量之,围五尺三寸五分,径一尺七寸,高五寸三分,积数得四千□□九寸。复以堆垛法,一百二十五寸除之,得三二□七之数,随用一百二十五寸之铜斗量之,不差累黍。又颁示一寸斗一、八寸斗一、十八寸斗一,奭斗水于中,大小随其所受,寸寸而积,盈缩不爽。御笔推算法一纸,今存家少詹姪处。*“家少詹”即指查昇。《人海记》抄本卷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参见文献[14]。
2 《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的写作背景
《三角形推算法论》谈论的主要是三角形、勾股和测量,并衍生到西学与古代历算的关系。康熙为何在此时提出这一说法?有必要回顾此文写作前发生的史实,亦即在1703年前,有哪些重要科学活动促成了康熙帝写作此文?
1688年法国耶稣会士到北京之后的近两年间,康熙学习西学较为集中。1690年,康熙亲征噶尔丹之后,科学活动几乎终止。但到了1702年,康熙的科学活动又渐趋频繁,其原因何在?
用仪器测量远近,此一定之理,断无差舛。万一有舛,乃用法之差,非数之不准。以此算地理、算田亩,皆可顷刻立辨,但须细用工夫,方能准验,大抵不离三角形耳。三角形从前虽无此名,而历来算法必有所本,如勾股法,亦不离三角形。是此法必自古流传,特未见于书,故不知所始也。[4]
在该上谕中,康熙非常明确地指出“三角形从前虽无此名,而历来算法必有所本,如勾股法,亦不离三角形”,由此可见,此时的康熙帝注意到勾股与三角形的关系问题,认为“是此法必自古流传,特未见于书,故不知所始也。”这里他仅意识到中国古法的悠久,还没有明确提出“西学中源”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完成了《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的撰写,并在文章最后指出“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迈出了“西学中源”说关键的一步。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在这一年康熙曾派皇三子胤祉和耶稣会士安多(Antoine Thomas, 1644—1709)测量霸州和交河之间子午线一度的长度,这次活动十分重要,不仅是康熙年间全国范围内大地测量的开端,也是《皇舆全览图》绘制的基础。*关于安多的研究,参见H. Bosmans, “L’oeuvre scientifique d’Antoine Thomas de Namur, S.J. (1644- 1709) ”, Annales de la Société Scientifique de Bruxelles. 1924, T.44, pp.169- 208; T.46, pp.154- 181; Mme Yves de Thomaz de Bossierre, Un Belge mandarin à la cour de Chin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Antoine Thomas 1644- 1709. Paris, 1977. 笔者曾据中西文献讨论安多在地图测量中的贡献,参见Han Qi, “Cartography during the Times of the Kangxi Emperor: The Age and the Background”, in Jesuit Mapmaking in China: D’Anville’s “Nouvelle Atlas de la Chine” (1737). (Early Modern Catholicism and the Visual Arts Series, Vol.11). Edited by Roberto M. Ribeiro with John W. O’Malley, S.J., Philadelphia: Saint Joseph’s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51- 62.安多的工作有许多已经被国人遗忘,但实际上他的著作仍有不少流存,[5- 7]*康熙时代宫廷数学稿本多没有署名,也没有序跋和成书时间。其中《几何原本》、《算法纂要总纲》、《算法原本》、《借根方算法》等书的作者已经确定。《测量高远仪器用法》实际上也是安多的作品,参考了其拉丁文著作《数学纲要》(Synopsis mathematica)写成,结合官方史料,可考订成书时间在1702年稍前。在大地测量中的角色尤为重要。康熙十分关注国计民生,经常视察河工,量天测地成为国家治理的部分,安多作为“西洋筹人”则起到了科学顾问的重要角色。因此,几何三角知识成为康熙出行与大臣经常谈论的话题,也是他向汉人作秀、炫耀的资本。现存康熙时代宫廷数学手稿《测量高远仪器用法》与测量密切相关,正是配合1702年测量子午线一度长度所作,多方证据表明,此书亦由安多完成,限于篇幅,在此暂不详论。
3 《御制三角形论》在康熙年间的影响
杨光先反教案之后到1688—1690年间,康熙帝集中向耶稣会士学习,之后屡次打听擅长数学的汉人。大约是因为李光地的推荐,1691年底,康熙曾派人测试梅文鼎的历算水平,包括对日影观测的知识,结果令康熙颇为失望。[8]
康熙四十一年(1702)十月,康熙南巡,驻跸德州,向李光地索取所刻书籍,李光地于是进呈梅文鼎的《历学疑问》,*李清植《文贞公年谱》卷下称1699年“冬十月,校刻梅文鼎所著《历学疑问》”。但到1700~1701年间才刻成于上谷。康熙得到此书后说:“朕留心历算多年,此事朕能决其是非”。两天后见到李光地,称:“昨所呈书甚细心,且议论亦公平,此人用力深矣,朕带回宫中仔细看阅。”*梅文鼎:《历学疑问》1704年李光地恭记,康熙刊本。关于此事,参见康熙刻本《勿庵历算书目》。在德州期间,还对李光地说汉人“于算法一字不知”,*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17“理气”:“皇上去年在德州尚云汉人于算法一字不知。”又称“你们汉人全然不晓得算法,惟江南有个姓梅的他知道些。”李光地深受刺激。第二年春,康熙又南巡,把《历学疑问》发回给李光地,并说:“无疵缪,但算法未备。”李光地以为“梅子之遇,可谓千载一时。”*梅文鼎:《历学疑问》1704年李光地恭记,康熙刊本。同年春,康熙把《几何原本》、《算法原本》送给李光地,李光地“虽经指授大意,未能尽通,乃延梅子至署,于公暇讨论其说。”*李清植《文贞公年谱》卷下。与康熙赐《几何原本》、《算法原本》同时,康熙和李光地曾讨论过里差的问题,因当时传教士安多也随同测量自北京至德州子午线一度的长度。八月廿三日,康熙在灯下看梅文鼎的《历学疑问》,*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17“理气”。按:据《历学疑问》李光地恭记,1703年春,康熙即已把批点本《历学疑问》送还给李光地,与《榕村语录续集》所记时间(康熙四十二年八月)不同,应以李光地的记载为准。书中有关《周髀算经》的论说无疑引起了康熙日后对传统历算的关注。此时,康熙已经撰就《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1702~1703年间康熙频繁的历算活动是促成李光地邀请梅文鼎的重要因素,李光地以此为契机,培养年轻人才,以迎合康熙的需要。
康熙四十三年(1704)十月二十八日,康熙帝召翰林院编修王奕清、礼科给事中铨同吴暻入畅春苑,吴暻即事恭纪:
蓬莱宫外叩严关,秋水虹桥万象闲。未向君前囊白简,忽从天上写青山是日,上问臣暻曾上条陈否,顾询再四。九章秘奥亲闻语是日,上于御座论三角形法,三绝风流敢斗班与翰林诸君东西分班迎送。岂是前身老摩诘,故教名落画师间。[9]*吴暻(1662~1702),太仓人,吴伟业之子,1688年与孙致弥、汤右曾、查昇同年考中进士,与姜宸英、查慎行、蒋廷锡、钱名世多有交往。
可见,除了在热河之外,康熙在畅春园还和文人讨论“三角形法”。有意思的是,康熙在南巡期间,在沿途各地还向文人提及三角形知识。
在汉文本《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写成后,康熙还命著名满文翻译家和素(1652~1718)将其译成满文,满汉合璧本中有满文识语,汉译如下:
处在加快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对闽商团队协作精神进行反思,认识闽商团队协作精神的特点,认清闽商团队协作精神存在的缺陷,才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创新闽商团队协作精神,促进闽商事业和福建社会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召集内外给事中、郎中以下至主事以上诸员于乾清门,饬交大王、三贝勒、五贝勒、八贝勒监看,令将此汉字译成清字。是日夜晚挑灯后,钦命召来和素亦译之,遂至乾清门翻译。俟第一张卷译毕,派哈哈珠色太监吉音取走,经皇上御览,降旨称好。至第二张卷译毕,李玉、吉音一同出来传旨:今日翻译者内,无人胜过尔,尔即为状元矣。钦此。至二更事毕,汉清文稿一并加封,交给值班首领定额琛等,而后回到家。二十五日,打过百更,入内誊抄,恭呈御览。皇上命内阁排定等级,遂列于三名头等者之首。自康熙十年始,至二十四年止,与包衣三旗人一起翻译考试,五次名列头等之首,未曾记录。此次与八旗人一起考试,荷蒙圣旨表彰,无地自容,不胜感激,敬谨记载。员外郎臣和素。*承蒙承志兄翻译成汉文,吴元丰先生定稿,特致谢意。
从这这一识语可看出,康熙皇帝还将文章交给皇子阅览,并命懂得满文的和素等人翻译,显然借此想扩大此文的影响。
康熙四十二年(1703)十月,康熙帝西巡,曾向李光地问及“隐沦之士”,李光地推荐了李颙、张沐及梅文鼎。[10]四十四年(1705)二月,康熙帝南巡,巡察河工,李光地扈从:“上问曰:‘汝前道宣城处士梅文鼎者今焉在?’臣地以尚留臣署对。上曰:‘朕归时汝与偕来,朕将面见。’”[10]后康熙南下至江淮,三月朔日,江南学政张廷枢迎候圣驾,[11]“闻上与廷臣论三角算法:‘历象垂千古,天文祖帝尧。岁差时有异,日至数非遥。三角为规密,一行得算饶。微言经睿鉴,精义日星昭。’”[12]*张廷枢,康熙壬戌(1682)进士,翰林,侍直南书房,己卯主试江南,曾任刑部尚书。1705年南巡时在淮安、苏州、金山、三汊河等地,撰有“南巡扈从纪恩诗”,获赠哈密瓜、御窑烧造玻璃盘二、瓶二,还有松花砚、御墨、《皇舆表》全部。可见康熙南巡途中仍念念不忘,在江苏一带也将《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给文人传阅或宣讲。
返京途中,在四十四年(1705)四月二十日,康熙帝在山东临清州御舟召见梅文鼎,“命所乘小舟随行,二十二、二十三日并赐召对、赐食、赐坐,夜分乃罢。”二十四日,“驻跸杨村,行谢恩礼”,并命从官赋诗,当时在场的有李光地、督学杨名时和天津道蒋陈锡。([13], 20页)*所记月份有误,四月应为闰四月。梅文鼎之所以受到康熙的接见,得益于李光地的引见。一连三天,康熙在舟中接见。当时《三角法举要》已刻,梅文鼎把它进呈康熙。会见之后,康熙对李光地感叹说:“历象算法朕最留心,此学今鲜知者,如文鼎真仅见也。其人亦雅士,惜乎老矣。”[10]临别时,还特书“绩学参微”相赠。
梅文鼎对康熙的召见受宠若惊,在1706年写了感恩诗,把康熙比作尧舜,还提及《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一文:
圣神天纵绍唐虞,观天几暇明星烂。论成《三角》典谟垂,今古中西皆一贯《御制三角形论》言西学实源中法,大哉王言,著撰家皆所未及。枯朽余生何所知,聊从月令辨昏旦。幸邀顾问遵明训,疑义胸中兹释半。御札乘除迅若飞,定位开方辞莫赞。庶勤榆景答殊恩,望洋学海期登岸。([13], 21页)
梅文鼎对康熙的“西学中源”说大加赞赏,在给熊赐履的诗中(1708年),再次强调康熙论文的重要意义:
畴人守师说,蔑肯窥西书。欧罗矜别传,宁能征昔儒。二者不相通,樊然生龃龉。大哉圣人言,流传自古初。伏读圣制《三角形论》,谓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尔。天语煌煌,可息诸家聚讼。([13], 23页)
并称“至教承光霁,秘策容参证。优老宽擎跽,放归保衰病。庶此毕榆景,残篇娱短檠。” ([13], 24页)“秘策”显然指康熙的《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
梅文鼎强调康熙“西学中源”说对结束“诸家聚讼”的作用,不免有阿谀奉承之嫌。自从1702年李光地把《历学疑问》送给康熙,1703年初,康熙就把经自己批点的书还给李光地。同年,梅文鼎到保定之后,就看到了康熙的御批,在一首诗中,梅文鼎曾写道:“恭承钦若旨,授受奇文真。顿令草野目,琬琰中秘臻。诹度及刍荛,采撷兼蘩蘋。”([13],19页)诗中的“奇文”应该是指康熙的《御制三角形论》。此诗也指出康熙在批点中参考了梅文鼎的一些看法。[14- 15]
和其他文人相比,作为清代历算第一人,梅文鼎的作用显然更为重要,他在晚年终于得到了康熙帝的赞许,也成为皇帝心目中合格的“汉人”算学家。在满族君主面前,梅文鼎也总算为“汉人”赢得了面子。梅文鼎感恩戴德,自不用说,李光地荐举之功,也不可抹,他还专门将康熙和梅文鼎的召对记录下来,后收入《历学疑问》与《绩学堂文钞》之首,成为清初文坛的佳话。
梅文鼎之后,康熙时代还有一些文人也曾读过康熙的这篇论文。江西临川人李茹旻(1659—1739)在他的《李鹭洲文集》中曾提到:“我皇上敬天勤民,首重授时,万几之暇,研精推测,制为《三角筭法》一书,以垂宪万世,此真心通造化、德合阴阳而创千古之未有者矣。”*李茹旻:《李鹭洲文集》卷7,23页,乾隆十三年(1748)活字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266册。李茹旻与皇十六子、李光地、何国宗、魏廷珍等人有往来。吹捧溢美之词跃然纸上。
4 结 论
明末清初相继出现了“心同理同”、“礼失求野”、“镕西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西学中源”诸说法,[16- 18]其目的都是在为西学传播作宣传,以消弭反对学习西学之声音。发端于明清之际的“西学中源”说,由于康熙帝的提倡和梅文鼎的附和,对清代历算之学的发展产生了至为重要的影响。《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这篇由康熙帝亲自撰写的历算短文,首次明确表达了“西学中源”说。作为“西学中源”说的倡导者,康熙帝的观点无疑举足轻重。
安多参与指导的1702年的大地测量,无疑加深了康熙对勾股之术和三角测量知识的实践,安多所撰《测量高远仪器用法》则大大完善了康熙的三角测量知识。李光地时任直隶巡抚,亲眼目睹了安多的大地测量。因此,为迎合康熙,将新刊刻的梅文鼎《历学疑问》呈上,这让康熙开始重新认识传统周髀所蕴含的历算知识。如果没有安多测地工作和梅文鼎著作的双重影响,也就不会有康熙《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的诞生。
从康熙帝撰就此文的1703年到1705年的近两年间,康熙帝刊刻此文,并多次向文人宣讲,历时之长,实为罕见,由此可见他对此文的重视。甚至在1705年南巡途中,康熙在江南和大臣亦有讨论,三角知识成为沿途对话的谈资。返京途中,停留山东临清,又将此文交给梅文鼎,并相互切磋数学内容。通过文人口中相传,更有梅文鼎的阐发,《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风行一时。
康熙一生拜传教士为师,钟情数学,已为众多史料所证实。但他留下来的科学论著却十分少见。《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这篇康熙帝唯一的算学论文,后被收入御制文集,与《几暇格物编》一样,为科学史家所重视。此文所传递的信号无疑是极其明显的,正是由于康熙的宣讲,使“西学中源”说从庙堂之说,成为文人的谈资。之后,以梅文鼎为代表的诸多文人的迎合响应以及转述,使之成为影响清初学界的重要论说,对康熙时代乃至后来的科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波及晚清。康熙作为满族的君主,处心积虑想通过对西学的掌握,来证明自己圣明天纵、学问日新,文治光昭已超越唐虞三代,学问高于汉人,从而达到从文化上来制服汉人的目的,西学成为其权术和政治生命中的重要部分。后来,康熙和梅文鼎提倡的“西学中源”说,还收入《数理精蕴》(1722)开头“周髀经解”中,对有清一代历算的发展和传统历算的复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 记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攻读博士期间,笔者首次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发现《满汉七本头》一书,如获至珍,其中便有《三角形推算法论》一文的满汉对照文本,并在1996年《清华学报》发表的“君主和布衣之间:李光地在康熙时代的活动及其对科学的影响”一文中予以披露。这一史料的发现,后来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兴趣与讨论。当初对此文年代的断定,主要依据文中内容加以推测。本文撰写过程中,曾与学生潘澍原屡次提及,其中个别史料由其检出,特致谢意。
1 金福. 清初改历斗争与康熙帝天算学术——《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试析[J]. 内蒙古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科学史增刊),1989,(1): 16~23.
2 汪灏. 随銮纪恩[M]. 道光二十三年(1843)青玉山房刻《舟车所至》本. 9~10.
3 汪士鋐. 秋泉居士集[M]. 乾隆刻本,卷15. 4.
4 玄烨.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M]. 康熙刊本. 第3集卷3. 4~5.
5 韩琦. 康熙时代传入的西方数学及其对中国数学的影响[C] // 董光璧.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第一篇:数学史部分).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87~127.
6 Han Qi. Antoine Thomas, SJ, and his Mathematical Activities in China: A Preliminary Research through Chinese Sources[C]// W. F. Vande Walle (ed).TheHistoryoftheRelationsbetweentheLowCountriesandChinaintheQingEra(1644—1911).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03. 105~114.
7 韩琦等. 康熙时代西方数学在宫廷的传播——以安多和《算法纂要总纲》的编纂为例[J]. 自然科学史研究,2003,22(2): 145~155.
8 韩琦. 科学、知识与权力——日影观测与康熙在历法改革中的作用[J]. 自然科学史研究. 2011, 30(1): 1~18.
9 吴暻. 西斋集[M]. 民国二十三年(1934)盐山刘氏皕印斋校刻本. 卷13. 7.
10 梅文鼎. 绩学堂文钞·附李光地恭记[M]. 乾隆刊本.
11 圣祖实录(三). 北京:中华书局,1985. 卷219. 213.
12 张廷枢. 崇素堂诗稿[M]. 乾隆39年(1774)吉大泰等刻本. 卷2. 21.
13 梅文鼎. 绩学堂诗钞. 乾隆刊本. 卷4.
14 韩琦. 君主和布衣之间:李光地在康熙时代的活动及其对科学的影响[J]. 清华学报(台湾),1996,新26(4):421~445.
15 祝平一. 伏读圣裁——《历学疑问补》与《三角形推算法论》[J]. 新史学,2005,16(1):51~84.
16 Han Qi. Astronomy, Chinese and Western: The Influence of Xu Guangqi’s Views in the Early and Mid-Qing[C] // Jami C, Engelfriet P, Blue G (Eds).StatecraftandIntellectualRenewalinLateMingChina:TheCross-CulturalSynthesisofXuGuangqi(1562—1633). Leiden: Brill, 2001. 360~379.
17 韩琦. 白晋的《易经》研究和康熙时代的‘西学中源’说[J]. 汉学研究,1998,16(1):185~201.
18 韩琦. 明清之际‘礼失求野’论之源与流[J]. 自然科学史研究,2007,26(3):303~311.
Using Knowledge as Power: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rth of the Kangxi Emperor’s “Imperially Composed Treatise on the Derivation of Triangles” and his Theory of the Chinese Origin of Western Learning
HAN Qi
(InstitutefortheHistoryofNaturalSciences,CAS,Beijing100190,China)
Chinese literati expressed a range of different views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about the adop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In his short essay entitled “Imperially composed treatise on the derivation of triangles” (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 the Kangxi emperor first explained why he had studied Western science, and then talked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uropean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alendars. He also proposed the theory of the Chinese origin of Western learning. Based on Chinese and Western sources, especially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Chinese court officials at that time,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ain why this treatise was written in 1703, and the social context of its wide circulation among scholar officials. In addition, the paper analyses how the Kangxi emperor displayed his treatise to his subjects on different occasions between 1703—1705, including during his southern tour of the Jiangnan region. In response to this imperial theory, the famous mathematician Mei Wending (1633—1721) developed the emperor’s idea further in his own mathematical works. Through the propaganda of the Kangxi emperor and Mei Wending, the theory of the Chinese origin of Western learning was widely circulated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and had a grea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s in China.
Chinese origin of Western learning, Mathematics, Kangxi Emperor, Mei Wending
2016- 03- 01
韩琦,1963 年生,浙江嵊州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科学史和中西科学、文化交流史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康熙时期西方数学传播与影响新探”(项目编号:1157010031)
N092∶O112
A
1000- 0224(2016)01- 0001- 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