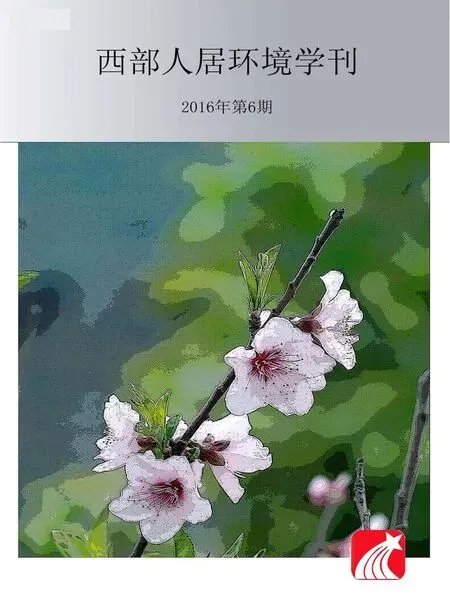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聚落研究述评*
肖路遥 周国华 唐承丽 贺艳华 高丽娟
传统聚落与人居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聚落研究述评*
肖路遥 周国华 唐承丽 贺艳华 高丽娟
通过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聚落的研究进展,将我国乡村聚落研究划分为复兴、发展、多元化3个阶段,乡村聚落研究经历了由简单向综合、从定性描述到定量分析、由空间分析向人文社会范式的转变。但是目前我国乡村聚落研究现状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是研究内容缺乏创新,原创理论相对较少;第二是研究对象较偏传统,普适性研究不够;第三是学科交叉研究不足,研究视角有待拓宽。最后提出了我国乡村聚落研究今后发展的趋势:以人为主体的微观视角下乡村聚落研究;乡村转型发展背景下乡村聚落发展与重构研究;对我国东、中、西乡村聚落和传统村落的研究;多领域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改革开放;乡村聚落;研究进展
0 引 言
聚落是指人类各种形式的居住场所,在地图上常被称为居民点,包括房屋及其相关的生产、生活设施,由各种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绿地、水源地等物质要素组成,聚落规模越大,物质要素构成越复杂,可分为乡村聚落和城市聚落两大类[1-2]。我国乡村地域广大,乡村人口众多,乡村聚落正是广大乡村地区人地关系的集中体现[3]。但是在学术界,我国乡村聚落研究长期滞后于城市聚落研究[4]。在城镇化和工业化浪潮的席卷下,去乡村化(deruralization)已经成为现代文明进程中不可逆转的趋势之一。2011年,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在城市发展遭遇千城一面的窘境时,各具特色的自然村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亡,从2000—2010年,中国自然村由363万个锐减至271万个,乡村空间衰落、故土乡愁丧失等“乡村病”问题十分严峻[5],乡村聚落空心化、农村居民点无序扩张、传统乡村聚落遭破坏等不合理的现象受到学者们的普遍重视。在城乡统筹和乡村转型背景下,乡村聚落该如何进行科学重构也成为我国乡村聚落研究新的关注点。目前,我国乡村聚落研究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仍需进一步加强。本文通过梳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乡村聚落的研究历程和主要内容,总结其研究趋势,以期为我国乡村聚落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1 我国乡村聚落研究回顾
20世纪30年代,受到西方人文地理学新思想的影响,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开始起步,乡村聚落研究也开始获得了专门发展。建国之后,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中国的人文地理学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导致有关乡村聚落的专门研究大大减少。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文地理学进入复兴阶段,学术思想大为活跃,作为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之一的乡村聚落地理,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依据近年来的文献发表数量,可以从整体上把握我国乡村聚落研究现状。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以“乡村聚落”、“乡村居民点”、“乡村居民地”“农村聚落”、“农村居民点”、“农村居民地”、“农村聚居”、“村庄”、“村落”、“空心村”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研究有关乡村聚落文献的总体发展趋势。检索结果为:改革开放以来乡村聚落研究相关文献共有7 070篇,其中核心期刊2 121篇,占总数的30%(图1)。
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聚落研究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乡村聚落研究复兴阶段;第二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乡村聚落研究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的乡村聚落研究多元化阶段。具体划分依据如下。
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乡村聚落研究复兴阶段:1978年以后,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学术思想大为活跃,与国外地理界交流增多。中国地理界开始重新评价人文地理学的地位和作用。1979年,中国地理学会在广州召开第四届全国大会,李旭东先生首先提出复兴人文地理的口号,中国乡村聚落地理作为人文地理学的分支之一也进入了复兴阶段[1]。

图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聚落研究相关文献数量统计图Fig.1 statistical figure of published studies on rural settlements in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乡村聚落研究发展阶段: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乡村人口仍然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开展乡村聚落研究成为地理工作的急迫任务,同时也是人文地理学为社会实践服务的重要课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吸引了更多学者参与乡村聚落的研究,乡村聚落研究也有了长足地发展,研究视角不断拓宽,研究内容也不断丰富,研究方法亦得到改进,乡村聚落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的乡村聚落研究多元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期可以说是我国乡村聚落研究史上一个较为明显的分界线,尤其是新世纪以后,“三农”问题日益受到重视,新农村建设步伐日渐加快,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乡村聚落的研究中[6-7],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均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新技术、新手段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乡村聚落研究的进展,乡村聚落研究进入多元化时期。
1.1 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初:乡村聚落研究的复兴阶段
1.1.1 复兴阶段的主要研究内容
1.1.1.1 乡村聚落的职能性质和类型研究
金其铭通过研究发现,江苏省乡村聚落类型可归纳为团聚状和条带状两类,其中团聚状又可分为稀疏型和密集型,条带状又可分为聚集型和散漫型[8]。金其铭、陆玉麒认为,在以服务职能来分析县内聚落体系时,可以发现集镇与村庄是处于统一矛盾中的两个方面,它们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依赖,它们的发展都受到对方的制约,同时研究县内聚落体系时,服务职能能够作为划分聚落等级的主要依据,而具有服务中心作用和城乡纽带作用的集镇也必然成为研究时注意的重点[9]。
1.1.1.2 乡村聚落的规模、分布与发展历程,研究方法以定性描述为主
在研究乡村聚落的规模与分布方面,金其铭认为江苏乡村聚落的规模虽然相差甚大,但是农村居民点的规模与分布是有律可循的,其分布密度大致可分为三级:第一级每100 km2内的农村居民点在100个以下;第二级每100 km2内有农村居民点150~200个左右;第三级每100 km2内有农村居民点300~400个[10]。侯彦周和孙冬虎分别对开封和白洋淀周围的乡村聚落进行了研究,分析了这些地区乡村聚落的发展历史[11-12]。
1.1.1.3 有关乡村聚落的整治、布局和规划等应用性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农村经济形势逐步好转,兴起了改善居住条件、大批新建房屋的高潮,再加上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农村居民点的整治、布局和规划的问题得到较多的关注。在乡村聚落整治方面,李旭旦等提出乡村聚落建设必须要进行有计划的整治,力求充分利用原有聚落进行规划和改建,认为如何有计划地整治农村聚落,使农村聚落的发展不致大量占用耕地面积,不使人均耕地面积进一步减缩,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13]。关于乡村聚落布局与规划,金其铭和李振泉对农村居民点的适宜规模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提出农村居民点的建设要按照适宜规模来进行规划和布局[10,14]。曹护九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农村建设中关于集镇的分布体系、人口结构和用地等问题做了全面的理论性探讨,并提出了一些规划的实用公式[15]。另外,叶舜赞、吴必虎等(1988)等学者都对乡村聚落的规划、整合、布局以及农村居住环境的综合改善进行了探索研究[16-17]。
1.1.2 复兴阶段的主要特征
我国乡村聚落研究于20世纪30年代随着我国近代人文地理的兴起而起步,在建国之后经历了一条曲折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后,作为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之一的乡村聚落地理也进入了复兴阶段。总体而言,该阶段虽然关于乡村聚落研究成果的数量相对较少,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已经开始摆脱传统的描述解释的轨道,走向动态分析和应用化趋向,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也崭露头角,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上,该阶段乡村聚落成果在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也要求开展更深入的乡村聚落研究。
1.2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乡村聚落研究的发展阶段
1.2.1 发展阶段的主要研究内容
1.2.1.1 乡村聚落空间结构的研究
主要研究农业地域中居民点的组织构成和变化特点,以及村庄分布、农业土地利用和网络组织构成的空间形态及其构成要素间的数量关系。范少言等把乡村聚落空间结构分为三个层次:区域乡村聚落空间结构;群体乡村聚落空间结构;单体乡村聚落空间结构,提出要从总体、群体、单体三个层面来分析乡村聚落空间结构[18]。沈克宁则从社会结构与文化习俗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富阳县龙门村聚落的空间结构[19]。陈晓健等通过乡村聚落空间形态演变和空间结构演变两方面的研究揭示了造成关中地区乡村聚落类型差异的原因及其聚落分布逐步扩散和空间结构由松散向协调发展的过程,对其乡村聚落空间发展模式进行了初步探讨[20]。
1.2.1.2 乡村聚落等级体系的研究
任何村落、集镇等都非孤立存在,它们之间、它们与高一级的行政中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有机整体。李瑛、陈宗兴利用人口、耕地、便捷度这三个指标,通过定量计算的方法,将汉中市的乡村聚落体系划分成四个等级[21]。艾南山认为村镇体系随时间的演化可分为自然聚落、田园聚落、污染聚落、生态聚落这四个阶段,自然聚落阶段无城乡区别,田园聚落阶段城镇和农村会发生分离,污染聚落阶段则会形成城镇体系和村镇体系,生态聚落阶段则实现了城乡一体化[22]。
1.2.1.3 乡村聚落演变机制的研究
在乡村聚落研究体系中,聚落演变机制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性论题,一方面它揭示了聚落产生、发展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它从宏观上阐明了聚落建设和规划进程的制约因素,在实践上为聚落发展指明了方向。王发曾认为乡村聚落由零散分布的农舍到以中心建筑物或者主要街道为线索布置各类用地,就已经基本完成了地域形态的演变过程[23]。范少言指出乡村聚落空间结构的演变主要与乡村环境条件和城镇与乡村相互作用有关,乡村劳动力生产水平的提高是乡村聚落空间结构演变的主要动力,集中和分散化是乡村聚落空间结构演变运动的基本形式[24]。
1.2.1.4 从生态学角度对乡村聚落的初步探究
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得到持续增长,与此同时人地之间的矛盾也日渐凸显。随着乡村聚落的发展,填平水塘种地、平毁树林和竹林盖房、饲养过量的家畜、豢养害兽、大范围频繁地投放鼠药等现象频现,部分学者开始注意到聚落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一些学者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乡村聚落。例如王智平应用地图作业和调查方法,分析和比较了不同地区村落体系的生态分布特征,概括总结了区域性村落生态分布的一般性原则[25]。李晓峰运用生态学理论中系统与平衡、循环与再生以及适应与共生三方面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村镇聚落环境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环境观念和环境资源利用特点等方面进行了分析[26]。
1.2.2 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
20世纪90年代初至20世纪90年代末这将近10年的时间,是我国乡村聚落研究得到较多发展的阶段,其研究的内容日益丰富,包含乡村聚落空间结构、等级体系、演变机制等方面;研究视角也逐步开阔,不仅将一些西方的理论引入乡村聚落的研究,而且还开始了从生态学观点来探讨乡村聚落的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定量化的研究方法被更多地采用,如李瑛和程宗兴运用公式来进行乡村聚落体系的空间分析[21]。
1.3 二十世纪末至今:乡村聚落研究的多元化阶段
1.3.1 多元化阶段的主要研究内容
1.3.1.1 乡村聚落空间特征、演变机制及优化的研究
乡村聚落空间特征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乡村聚落空间特征及其内在规律进行分析,它主要包括乡村聚落的规模、空间形态、空间结构、空间分布等方面的研究,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过程及其驱动机制研究是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研究的主要内容。相比较于前两个阶段,该阶段对于乡村聚落规模、空间形态以及演变机制等的研究,更加侧重于GIS空间技术以及数学模型等方法的运用,研究视角更加多元化,同时更加注重对非物质因素的研究。例如张京祥、张小林等阐述了乡村聚落体系演化理论、规划组织理论,研究了国际上对乡村聚落体系组织的战略方法[27]。冯文兰等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岷江上游乡村聚落的空间聚集特征作了定量化分析,指出应探寻适当的对策对空间分析不合理的聚落进行重建或迁建[28]。李红波、张小林等基于苏南地区土地变更调查数据,通过GIS空间分析方法,对苏南地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特征进行深入分析,初步构建了驱动力机制[29]。马晓冬、单勇兵等运用RS和GIS等技术定量分析了江苏省乡村聚落形态的空间分异特征,并进一步划分了地域类型[30-31]。李小建、乔家君、罗庆、李君等从农户自主发展能力、农户区位、农户发展环境、农户与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等方面建立了农户地理研究的基本框架,从农户地理的视角分析了乡村聚落尤其是专业村形成与演化的机理[32-35]。郭晓东等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了秦安县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化特征[36]。周国华和贺艳华等归纳出农村聚居演变三类因子,即基础因子、新型因子与突变因子,并提出农村聚居演变的“三轮”驱动机制以及3条典型驱动路径[37-38]。贺艳华、唐承丽、周国华等受启于TOD理论,借鉴以往乡村聚居单元规模与空间结构研究成果,试图提炼出一种乡村聚居空间结构优化模式——乡村公路导向发展模式(rural road-oriented development model,简称RROD模式),并引入“生活质量理论”,从乡村聚落空间功能整合、空间结构优化、空间尺度调控等三个方面研究乡村聚落空间优化问题,试图构建有效提高生活质量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框架与模式[39-40]。谭雪兰以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景观形状指数模型及聚类分析法,从空间、规模与形态等方面探讨长沙市农村居民点地域分异特征、地域类型及调控路径[41]。
1.3.1.2 乡村聚落空心化问题的研究
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乡村聚落空心化问题日益严重,造成了很多负面效应,如浪费土地资源、传统乡村聚落文化破坏、社会问题加重、村容村貌不整洁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内许多学者都积极参与乡村聚落空心化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王成新、姚士谋等通过实证研究概括了聚落空心化机制的三对矛盾:聚落离心力与向心力、经济发展与观念落后、新房建设与规划滞后[42]。冯文勇提出健全农村用地制度和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是遏制乡村聚落空心化的有效途径[43]。龙花楼等通过研究重点揭示了城乡结合部和平原农区空心化村庄发展演化的阶段特征及动力机制[44]。刘彦随认为地理学研究农村空心化问题,主要着眼于乡村地域系统综合性、动态性和区域性视角,侧重梳理并规范农村空心化现象描述与空间模式构建、形成机理与动力机制、空心化效应与响应机制、整治潜力类型与优化调控等农村空心化命题研究;提炼并发展空心村演进的生命周期、代际演替空间型式、农村空心化动力学机制和农村空心化调控“三整合”等基础理论[45]。陈玉福等基于农村空心化“生命周期”及其空间演替型式基础理论指导,将国家土地资源安全、新农村建设战略同农村空间优化、农民意愿需求相结合,研究提出城镇化引领型、中心村整合型和村内集约型等空心村整治模式[46]。
1.3.1.3 城镇化背景下乡村聚落发展研究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用地需求越来越旺盛,在城乡一体化政策的推动下,乡村聚落的发展和城镇化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于城镇化背景下乡村聚落发展的研究主要分为两部分:(1)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居民点变化的研究。何林艳等通过GIS研究方法,对吴中区农村居民点2005—2009年动态变化过程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土地利用过程中农村居民点城镇化的程度以及农村居民点变化的驱动因素[47]。(2)城镇化过程中传统乡村聚落演进的研究。张小林等基于苏南快速城市化地区乡村空间系统的演变过程分析,探讨了乡村重构内涵及其发展方向[48]。龙花楼分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影响,探讨了乡村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类型及助推机制,结合农用地整治、“空心村”整治和工矿用地整治提出了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的模式与途径,以及依托土地整治的以“自下而上”为主、“自上而下”为辅的乡村空间重构战略[49-50]。
1.3.1.4 乡村聚落生态学研究
生态环境是乡村聚落存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在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的时期,对乡村聚落生态及其运行机制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乡村聚落生态学研究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新世纪以来,我国对乡村聚落生态的研究已经有了较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1)乡村聚落生态系统的研究。陈勇探讨了乡村聚落生态系统的基本概念[51]。周秋文等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数学法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乡村聚落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方法,并运用该评价方法定量测算了桂林市东井村乡村聚落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52]。(2)乡村聚落生态区划的研究。乡村聚落生态区划的目的就是按照各地聚落所处的自然地理和生态条件,确定不同的聚落区域,用于指导各地的乡村聚落生态建设。陈勇等提出可以根据研究区域范围的大小或研究目的进行不同的乡村聚落生态区划,如我国西南地区分布着较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对这些民族聚居区可以根据其自然和生态特点进行聚落生态区划,以便因地制宜地进行生产和聚落生态建设,从而达到聚落与环境的和谐统一[51]。(3)建设生态村的研究。生态村是以人类为尺度,把人类活动结合到不损坏自然环境为特征的居住地中,支持健康地开发利用资源,能够可持续地发展到未知的未来。张蔚认为生态村作为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模式的探索,它的发展同时融合了生态、经济、社会等多重内涵。我国已经建立了各具特色的生态村[53]。在生态村建设的模式和技术路线方面,各地也进行了较多的探讨。在生态村建设的基础上,我国部分山区还进行了小康生态村建设的探索[54]。(4)乡村聚落生态位研究。生态位是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某种定性或定量的描述。其基本思想有两点:第一,生态位理论研究生物种群在生态系统中的空间位置、功能和作用;第二,生态位理论反映了生态系统的客观存在,它是生态系统结构中的一种秩序和安排。李君根据乡村聚落发展与资源环境条件的关系,初步探讨了生态位理论在乡村发展中的应用[55]。王青等以岷江上游山区聚落为研究对象,采用生态位的方法,利用遥感资料和GIS技术,提取岷江上游山区空间信息,定量研究山区聚落生态位影响尺度、人口密度及民族类型带谱垂直分异特征,并建立民族聚落生态位类型图谱[56]。
1.3.1.5 传统乡村聚落研究
中国广大地域范围内分布着为数众多的传统乡村聚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但在经济建设的大潮中,许多传统乡村聚落面临着被损毁的危险,因此对传统乡村聚落保护与开发的研究吸引了越来越多关注。(1)在景观区划与保护方面,刘沛林对传统聚落景观区划进行了较多研究,将全国传统聚落景观初步划分为 3个大尺度的景观大区、14个景观区和76个景观亚区[57],并基于景观基因完整性理念深层次地探讨了新时期古聚落的保护问题[58]。肖竞以文化景观“物质—价值”合一的视角,对四川雅安上里古镇的风水格局进行案例剖析,力图厘清我国传统聚落风水设计的文化意涵、再现其空间魅力,以求为传统历史村镇保护发展研究提供新的理论线索[59]。(2)在传统聚落发展及旅游开发方面,刘沛林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旅游开发中古村落乡村性传承情况进行了评价,评价结果显示爨底下古村落的建筑、环境、乡村文化与乡村社会等方面的乡村性传承良好,但传统乡村经济特征传承较弱[60]。赵之枫提出了针对功能多样性特征的村落分类和引导,针对营建渐进式特征的建筑营造示范与引导,以及针对村民主体性特征的村落营建保障与支撑等乡村地域建筑营建模式[61]。
1.3.2 多元化阶段的主要特征
这一阶段,新技术、新手段的综合运用,特别是遥感、GIS、数学模型和其他计算机软件的运用,使得乡村聚落研究更加方便与准确;并且开始重视对城镇化、旅游开发、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生活质量等非自然影响因素的研究;更加注重乡村聚落中人地关系的研究,从被动地解释人地关系发展为主动协调人地关系,更加强调乡村聚落的和谐发展与科学发展。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聚落研究总体上呈现出由简单向综合、从定性描述到定量分析、由空间分析向人文社会范式转变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存在基本理论探寻薄弱、主体需求关注不够、特殊性地域研究占主体、多学科融贯分析有待加强等问题。
2 当前我国乡村聚落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
2.1 研究内容缺乏创新,原创理论相对较少
我国乡村聚落研究复兴30多年以来,无论是在基础理论和方法论上,还是在研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明显发展,研究内容逐步由聚落实体空间向经济、社会等非实体空间拓展,研究深度逐步由对乡村聚落的类型、形态等的研究转向乡村聚落的演变及其驱动机制的研究。但是与城市聚落研究和国外相关研究相比较,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对于乡村聚落相关概念的定义仍有争议;研究内容缺乏有机融合;对国外理论借鉴较多而原创性理论较少等,当前我国有关乡村聚落的研究大部分是以具体的实证分析为主,并且在研究方法、研究区域等方面有较多的重叠,研究内容偏重空间特征本身,缺乏深层次理论总结。可以说我国乡村聚落研究尚未完成成熟,乡村聚落基础理论研究有待加强,研究体系需进一步完善。
2.2 研究对象较偏传统,普适性研究不够
从当前研究来看,乡村聚落研究地域逐步增多,但研究对象依然偏传统、偏特殊,普适性研究不够。乡村聚落研究的实证区域涉及黄淮海平原、晋中平原、长江沿岸、黄土高原、关中、苏南、中部农区等,逐步由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向中部农区扩展,并且在研究区域等方面有较多的重叠。另外,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主要偏向空心村、城中村、城郊村等传统型或特殊型的乡村聚落,而忽视了对一般性乡村聚落的研究,普适性研究不足。另外,研究尺度大都集中于县、市一级,对于宏观与微观尺度涉及较少。
2.3 学科交叉研究不足,研究视角有待拓宽
乡村聚落是一个包含社会、经济、生态、政治、文化等诸多要素在内的复杂系统,涉及地理学、历史学、建筑学、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等诸多学科。目前国外乡村聚落已经出现了社会、文化转向,研究内容也从注重物质实体的研究转向注重社会人文空间研究,而国内乡村聚落研究与其他学科如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交叉融合仍有不足,社会转向和文化转向亟待加强,人本主义研究方法并没有得到充分运用,研究视角也较多侧重于宏观分析,对村域、农户、个体等微观视角的研究较少,研究者大多将乡村聚落看作一个点,从宏观上来分析乡村聚落的结构特征和演变机制,乡村聚落研究缺乏微观分析的详细研究,同时,对乡村社会形态与社会问题、乡村性与城乡关系等新问题的剖析也缺乏深入研究。
3 我国乡村聚落研究展望
3.1 以人为主体的微观视角下乡村聚落研究
目前,我国对村域、农户等微观视角的研究刚刚起步,相关研究较少,研究者大多将乡村聚落看作一个点,研究的角度侧重于宏观方面。乡村聚落研究在未来应当更加侧重于农村微观的社会组织、社会形态、社会问题的研究,即研究视角由自然要素向经济社会要素转变,研究内容由物质实体空间向人转变,其发展趋势应当是以人为主体的研究,是基于村域、农户与个体的微观研究,是结合人本主义、行为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更为灵活的研究,是从人类的心理、意识、行为等主观因素出发的更为全面的研究。
3.2 乡村转型发展背景下乡村聚落发展与重构研究
乡村问题具有地域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在当今城市化的背景下,乡村地域的功能在发生变化,乡村的多功能性、乡村价值的提升日益受到重视,乡村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均经历着由传统向现代的全面转型[62]。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农业产业化与新农村建设,实现乡村转型,是解决我国城乡二元分割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在乡村转型发展的背景下,乡村聚落的发展与重构也需要考虑新的要求与原则。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生态文明等先进理念,充分借鉴吸收国外的成功经验,并结合当前我国的特殊国情,以提升乡村吸引力、乡村居民生活质量为目标,对乡村聚落的发展建设进行科学合理的指导,才能在乡村转型发展的背景下实现对乡村聚落的前瞻性和远景性的规划与布局。
3.3 对我国东、中、西乡村聚落和传统村落的研究
我国疆域辽阔,文化多样,区域分异明显,东、中、西三个区域乡村聚落特色鲜明,差异较大,传统村落亦是需要特殊关注的区域。目前国内乡村聚落研究主要还是以县域和市域尺度为主,并且在研究区域等方面有较多的重叠,缺乏从宏观尺度对东、中、西部及不同区域乡村聚落的总结与归纳。同时,我国已进行了关于传统村落保护的相关研究,但是传统村落仍在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根据统计数据,我国自然村从2000—2010年由363万个锐减至271万个,因此亟需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更加重视传统村落保护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从而推动我国传统村落保护的研究工作。
3.4 多领域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乡村聚落是一个涉及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等诸要素的复杂系统[63],目前乡村聚落研究已经较多地涉及地理学、经济学和生态学等学科,未来的发展趋势将是更多领域更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如与计算机科学和数学相结合,以适当的计算方法与计算语言建立数学模型,对乡村聚落进行模拟和仿真,预测其演变趋势;与社会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的思想理论与研究方法相结合,加强对人的研究,重视人类行为的丰富意义。乡村聚落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开展交叉学科相融合的集成研究,建立综合性分析框架是乡村聚落研究不断发展的必然趋势。
[1] 王恩涌, 赵荣, 张小林, 等. 人文地理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191.
[2] 曾山山, 周国华. 农村聚居的相关概念辨析[J].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2011(03): 26-31.
[3] 海贝贝, 李小建. 1990年以来我国乡村聚落空间特征研究评述[J]. 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3(06): 635-642.
[4] 张小林. 乡村概念辨析[J]. 地理学报, 1998(04): 79-85.
[5] 肖路遥. 基于县域尺度的湖南乡村性空间格局变化及其形成机理[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贵阳市人民政府. 新常态:传承与变革——2015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4乡村规划).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5: 13.
[6] 刘彦随, 龙花楼. 中国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研究进展及展望——建所70周年农业与乡村地理研究回顾与前瞻[J]. 地理科学进展, 2011(04): 409-416.
[7] 刘彦随, 龙花楼, 张小林, 等. 中国农业与乡村地理研究进展与展望[J]. 地理科学进展, 2011(12): 1498-1505.
[8] 金其铭. 农村聚落地理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 地理研究, 1982(03): 11-20.
[9] 金其铭, 陆玉麒. 聚落服务范围与县级聚落体系[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4(02): 87-94.
[10] 金其铭. 江苏农村聚落的规模与布局[J].建筑学报, 1983(10): 55-56.
[11] 侯彦周. 开封附近乡村聚落的发展和分布[J].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1988(01): 48-52.
[12] 孙冬虎. 白洋淀周围聚落发展及其定名的历史地理环境[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9(03): 106-110.
[13] 李旭旦, 金其铭. 江苏省农村聚落的整治问题[J]. 经济地理, 1983(02): 132-135.
[14] 李振泉. 开展我国农村聚落地理研究的主要课题[J]. 东北师大学报, 1985(03): 27-31.
[15] 曹护九. 谈谈农村集镇建设规划的几个问题[J]. 东北农学院学报, 1984(04): 81-87.
[16] 叶舜赞. 关于村镇布局的宏观特点[J]. 地理科学, 1985(02): 153-159.
[17] 吴必虎, 张晶. 乡村聚落社会的形成、扩展与整合——苏北一个自然村的分析[J].农村经济与社会, 1988(05): 10-18.
[18] 范少言, 陈宗兴. 试论乡村聚落空间结构的研究内容[J]. 经济地理, 1995(02): 44-47.
[19] 沈克宁. 富阳县龙门村聚落结构形态与社会组织[J]. 建筑学报, 1992(02): 53-58.
[20] 陈晓键, 陈宗兴. 陕西关中地区乡村聚落空间结构初探[J].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3(05): 478-485.
[21] 李瑛, 陈宗兴. 陕南乡村聚落体系的空间分析[J]. 人文地理, 1994(03): 13-21.
[22] 艾南山. 我国村镇体系的时空特点与乡村区域经济的发展[J]. 国土经济, 1995(02): 23-28.
[23] 王发曾. 论聚落演化规律与成长机制[J].学术论坛, 1991(05): 40-44.
[24] 范少言. 乡村聚落空间结构的演变机制[J].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4(04): 295-298.
[25] 王智平. 不同地区村落系统的生态分布特征[J]. 应用生态学报, 1993(04): 374-380.
[26] 李晓峰. 从生态学观点探讨传统聚居特征及承传与发展[J]. 华中建筑, 1996(04): 42-47.
[27] 张京祥, 张小林, 张伟. 试论乡村聚落体系的规划组织[J]. 人文地理, 2002(01): 85-88.
[28] 冯文兰, 周万村, 李爱农, 等. 基于GIS的岷江上游乡村聚落空间聚集特征分析——以茂县为例[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08(01): 57-61.
[29] 李红波, 张小林, 吴江国, 等. 苏南地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及其驱动机制[J]. 地理科学, 2014(04): 438-446.
[30] 马晓冬, 李全林, 沈一. 江苏省乡村聚落的形态分异及地域类型[J]. 地理学报, 2012(04): 516-525.
[31] 单勇兵, 马晓冬, 仇方道. 苏中地区乡村聚落的格局特征及类型划分[J]. 地理科学, 2012(11): 1340-1347.
[32] 乔家君, 李小建, 葛真. 基于农户调查的村域商业经济活动空间研究[J]. 经济地理, 2009, 29(05): 817-922.
[33] 李小建, 罗庆, 樊新生. 农区专业村的形成与演化机理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09, 24(02): 71-80.
[34] 李小建, 时慧娜. 基于农户视角的农区发展研究[J]. 人文地理, 2008, 22(01): 1-6.
[35] 罗庆, 李小建. 农户互动网络的演变研究——以河南省杞县孟寨村为例[J]. 改革与战略, 2011, 27(04): 93-96.
[36] 郭晓东, 马利邦, 张启媛. 基于GIS的秦安县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J]. 经济地理, 2012(07): 56-62.
[37] 周国华, 贺艳华, 唐承丽, 等. 中国农村聚居演变的驱动机制及态势分析[J]. 地理学报, 2011, 66(04): 515-524.
[38] 贺艳华, 曾山山, 唐承丽, 等. 中国中部地区农村聚居分异特征及形成机制[J]. 地理学报, 2013, 68(12): 1643-1656.
[39] 唐承丽, 贺艳华, 周国华, 等. 基于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研究[J]. 地理学报, 2014(10): 1459-1472.
[40] 贺艳华, 唐承丽, 周国华, 等. 论乡村聚居空间结构优化模式——RROD模式[J].地理研究, 2014(09): 1716-1727.
[41] 谭雪兰, 刘卓, 贺艳华, 等. 江南丘陵区农村居民点地域分异特征及类型划分——以长沙市为例[J]. 地理研究, 2015(11): 2144-2154.
[42] 王成新, 姚士谋, 陈彩虹. 中国农村聚落空心化问题实证研究[J]. 地理科学, 2005(03): 3257-3262.
[43] 冯文勇. 农村聚落空心化问题探讨——以太原盆地东南部为例[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02(04): 267-269.
[44] 龙花楼, 李裕瑞, 刘彦随. 中国空心化村庄演化特征及其动力机制[J]. 地理学报, 2009, 64(10): 1203-1213.
[45] 刘彦随, 刘玉, 翟荣新. 中国农村空心化的地理学研究与整治实践[J]. 地理学报, 2009(10): 1193-1202.
[46] 陈玉福, 孙虎, 刘彦随. 中国典型农区空心村综合整治模式[J]. 地理学报, 2010, 65(06): 727-735.
[47] 何林艳, 吴国平, 陈功勋, 等.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农村居民点的城镇化研究[J].国土资源科技管理, 2011(06): 34-39.
[48] 张小林.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乡村重构的若干思考——以江苏省苏南地区为例[C]//中国地理学会,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等. 中国地理学会2007年学术年会论文摘要集. 2007: 1.
[49] 龙花楼.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J].地理学报, 2013(08): 1019-1028.
[50] 龙花楼. 土地整治:中国乡村空间重构的必由之路[J]. 地理学报(英文版), 2014(02): 211-225.
[51] 陈勇, 陈国阶. 对乡村聚落生态研究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认识[J]. 农村生态环境, 2002(01): 54-57.
[52] 周秋文, 苏维词, 张婕, 等. 农村聚落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初探[J]. 水土保持研究, 2009(05): 121-126.
[53] 张蔚. 生态村——一种可持续社区模式的探索[J]. 建筑学报, 2010(S1): 112-115.
[54] 姜志德, 唐学玉. 小康生态村建设问题的思考[J]. 乡镇经济, 2005(07): 16-18.
[55] 李君, 陈长瑶. 生态位理论视角在乡村聚落发展中的应用[J]. 生态经济, 2010(05): 29-33.
[56] 王青, 石敏球, 郭亚琳, 等. 岷江上游山区聚落生态位垂直分异研究[J]. 地理学报, 2013(11): 1559-1567.
[57] 刘沛林, 刘春腊, 邓运员, 等. 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区划及景观基因识别要素研究[J]. 地理学报, 2010(12): 1496-1506.
[58] 刘沛林, 刘春腊, 邓运员, 等. 基于景观基因完整性理念的传统聚落保护与开发[J]. 经济地理, 2009(10): 1731-1736.
[59] 肖竞, 曹珂. 文化景观视角下传统聚落风水格局解析——以四川雅安上里古镇为例[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14, 29(03): 108-113.
[60] 刘沛林, 于海波. 旅游开发中的古村落乡村性传承评价——以北京市门头沟区爨底下村为例[J]. 地理科学, 2012(11): 1304-1310.
[61] 赵之枫, 王峥, 李云燕. 基于乡村特点的传统村落发展与营建模式研究[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16, 31(02): 11-14.
[62] 张小林, 盛明. 中国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新定向[J]. 人文地理, 2002(01): 81-84.
[63] 何仁伟, 陈国阶, 刘邵权, 等. 中国乡村聚落地理研究进展及趋向[J]. 地理科学进展, 2012(08): 1055-1062.
图片来源:
图1:作者绘制
Research Progress of Chinese Rural Settlement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XIAO Luyao, ZHOU Guohua, TANG Chengli, HE Yanhua, GAO Lijuan
The research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renaissance stage, development stage and the diversifi cation stage.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the study, there still exist some problems. Firstly, the research content is not novel. Secondly, the research object is more traditional. Thirdly, multidisciplinary fusion is not enough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 should be broadened.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research progress of rural settlement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main trends of Chinese future research on rural settlement geography should be listed as follows: (1) research on the rural settlements in human subjects under the micro perspective; (2)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and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3) research on the rural settlement in the East, middle and west of China and traditional village; (4) research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of rural settlements.
Reform and Opening up; Rural Settlements; Research Progress
TU984.11+3
A
2095-6304(2016)06-0079-07
10.13791/j.cnki.hsfwest.20160614
2016-06-04
(编辑:申钰文)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147114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41301192)
肖路遥: 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周国华( 通讯作者):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uuy828@163.com
唐承丽: 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
贺艳华: 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副教授
高丽娟: 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肖路遥, 周国华, 唐承丽, 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聚落研究述评[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16, 31(06): 7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