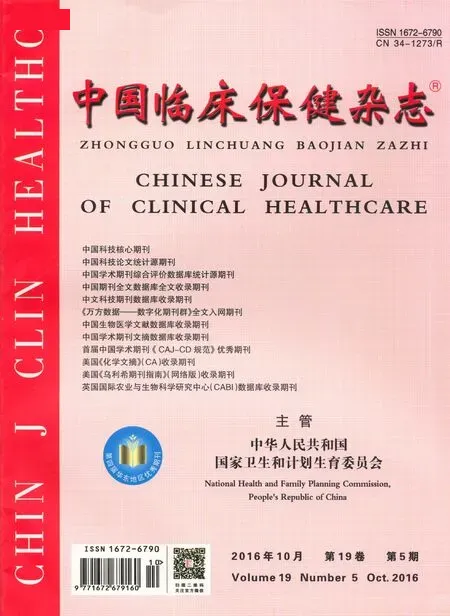中国开启肿瘤患者全面社区照护模式的思考
王玉梅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宁养病房,沈阳 110022)
·肿瘤专题·
中国开启肿瘤患者全面社区照护模式的思考
王玉梅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宁养病房,沈阳 110022)
有研究结果[1]显示,2015年,我国共有429.2万新发肿瘤病例和281.4万恶性肿瘤死亡病例,恶性肿瘤已经成为中国疾病死亡的重要原因,而且其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呈日益增长的趋势,如何更有效地防治恶性肿瘤已经成为医学界亟待解决的大事,也是社会发展中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难题。恶性肿瘤属于慢性疾病,在诊断、治疗、康复、复发、进展及临终阶段均需要专科医生、全科医生和护理人员的帮助和指导,患者的生活质量有赖于二、三级医院、社区医院及居家的医疗护理保障,因此,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有必要深入探讨贯穿肿瘤患者疾病全过程、保证在任何阶段、任何地方都能得到全面照护的本土化模式。
1 肿瘤患者开展全面社区照护的重要意义
1.1 在肿瘤预防方面的优势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40%的肿瘤可预防,40%可治愈,20%可以长期带瘤生存,国内相关文献[2]也表明,有些肿瘤是可以预防的。恶性肿瘤的发生与环境、生活方式等因素密不可分,由赫捷院士牵头进行了高质量的临床研究,得出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结果。作者认为,许多估算的肿瘤新发和死亡事件可以通过降低高危因素的流行,同时提升肿瘤医疗服务的效率而减少发生[1]。因此,非常有必要进行积极有效的社区宣教和指导,引导居民提高对危险因素的认知,改变不良生活方式,定期体检,发现症状及时就医,做到早诊断、早干预。
1.2 在肿瘤治疗方面的作用 患者在二、三级医院进行手术、放化疗等治疗后进入了随访和监护阶段[3]。回到社区和家中休养时,需要二、三级医院与社区医院良好的双向协调和沟通[4],给予药物、饮食、术后康复、功能锻炼、心理调适等方面的专业指导,通过为患者提供全面、规范的治疗和护理,可提高患者生存率,改善生活质量,减少疾病复发的可能[5]。因此,该阶段的社区照护至关重要。
1.3 社区照护是晚期肿瘤患者的福音 对于晚期肿瘤患者而言,尤其是有些老年人,出现症状后就诊时已是肿瘤晚期,失去了手术、放化疗等积极抗肿瘤治疗的机会。回归家庭和社区后,照护的重点是给予姑息治疗或临终关怀,需要有专业的社区医护人员进行规范化疼痛等症状控制、心理疏导、精神照顾及社会支持,以提高患者及亲属的生活质量为宗旨,帮助患者平静而有尊严地离世。
我国的调查显示,75%的老年患者希望以家庭病床方式得到照护[6],然而,恶性肿瘤患者中只有少数能在社区医院接受姑息医学或临终关怀服务,患者和家属更希望得到趋向于家庭化的医疗护理照顾[7]。同时,在中国,姑息医学(也被称为纾缓医学、缓和医学、宁养医学、临终关怀等)的发展缓慢,至今尚未形成规模和体系,严重制约了晚期肿瘤患者全面照护的开展和服务品质的提升,因此,在社区层面推广晚期肿瘤患者的全面照护更具重要的现实意义。
2 肿瘤患者社区照护模式
肿瘤患者的社区照护是以全科医生为主导,社区护理为支撑,政策法规为保障,保证患者在医院及医院之外的任何地方都能得到连续性的专业卫生服务。在美国,提倡以社区为基础、以护理为主的肿瘤患者照护模式[8]。在英国,90%患者生命中的最后一年都是在家中接受社区照护,成熟的社区照护体系使众多的肿瘤患者受益[9]。
2.1 服务体系 各国有着完善的医疗管理制度和强大的信息网络系统。英国的三级服务体制,包括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全科医生提供)、地级服务(社区服务)和医院服务(专科医疗服务),常见病患者须经全科医生诊疗后再转入上一级医院治疗;病情复杂则直接转诊给三级医疗机构;美国的患者出院后,上级医院将患者详细的医疗信息资料转给全科医生,保证后续治疗和康复的无缝隙延续[10]。
国外发达国家社区卫生服务的开展有赖于医疗机构合理的分工协作,可以通过社区首诊和双向转诊制度来得以实现。社区首诊主要是通过制度约束、基于居民对于全科医生或诊所的充分信任,或者通过疾病基金来实现[10]。双向转诊:全科医生或私人诊所的医生有转诊的权利,主要靠保险条款约束、或自由选择不同级别的医院提供不同层级的服务,转诊一般是从低级到高级,而不是越级转诊或随意转诊,患者病情稳定后,医院会及时将患者转回诊所或慢性病护理机构进行后期治疗。各国建立了慢性病护理机构、老年人护理机构等专业机构,为双向转诊和连续性卫生保健提供保障。
2.2 服务形式和内容
2.2.1 肿瘤患者社区照护服务形式 恶性肿瘤的预防和治疗需要个人、家庭和社会的配合,全面社区照护主要由社区卫生服务组织提供,在上级医院和专科肿瘤防治机构指导下,为肿瘤患者提供包括自我护理、社区护理等初级卫生保健和专科保健的连续照顾,此外,肿瘤患者俱乐部、肿瘤患者资源中心等其他形式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2.2.2 服务内容 早期治疗阶段:协助肿瘤专科随访与康复治疗,包括监测患者病情、出现复发或转移迹象时给予相应检查、必要时转诊给专科医生。躯体功能康复:专业护理、营养康复、运动疗法、作业疗法与职业康复等。心理疏导。生活指导:饮食、日常作息安排、体力活动、工作、生活等。
康复治疗阶段:由物理治疗、心理学、护理学和社会学多学科专家组成的康复小组共同商议、制定和指导肿瘤患者的康复计划,指导和帮助患者全面康复。康复内容包括: 功能恢复和锻炼、心理疏导、社会能力的恢复、整形修复等[11]。
晚期治疗阶段:需要全科医疗的专业照顾来完成。治疗手段包括:对于癌症晚期的患者进行全面评估,制定治疗计划,向患者和家属进行专业知识、心理疏导和精神照顾(灵性照顾)的宣教和指导[12]。
终末期:对患者实施临终关怀,宗旨是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而不是生命的长短,服务内容涉及患者身、心、社、灵全面照顾,同时还要对家属和照顾者给予支持和照料,主要内容包括:症状控制、家庭护理、心理咨询、营养评估、精神照顾指导、家庭支持服务(包括哀伤辅导)、非药物治疗等[13]。
2.3 社区护理 欧美国家于20世纪70年代进入社区护理阶段,发展已较为成熟,形成了多种社区护理服务模式,并形成了系统的社区护理机构网络和全社会参与、全民受益的新格局。国外经验表明:社区护理事业的发展,能明显减少患者的住院日、降低医疗成本、提高病床使用效率、提高社区居民对整个医疗卫生服务的满意度[14]。欧美国家的社区护理基本上实现了网络化,患者的全部资料及信息交流全部由计算机信息网络实现,并形成了不同的社区护理模式[15]。
肿瘤患者社区护理内容包括:日常护理、专科护理,营养护理,心理和精神护理,家庭支持,社会支持,临终关怀等。由医生、护士、营养师、心理学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等共同组成的团队为肿瘤患者提供护理照顾及健康指导,需要倾注大量的时间、人力和资源才能保证服务质量[16]。
3 开启肿瘤患者社区全面照护模式的思考
3.1 中国社区照护现状 我国开展肿瘤患者社区照护借鉴了欧美国家的模式,但由于政策、民众认知、医护人员素质、经济条件等不同,与欧美国家相比差别显著,目前各地还未形成统一的政策和规范。
3.1.1 社区首诊和双向转诊 社区首诊和双向转诊制度是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性、连续性的具体体现[17]。2009 年3月17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城市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分工协作机制,引导一般诊疗下沉到基层,逐步实现社区首诊、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18]。”研究表明,建立城市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双向转诊的绿色通道,可以提高患者从大医院向专职社区医院的下转率,帮助患者减少在大医院的住院时间和治疗费用,合理利用医疗资源,帮助患者及时获得规范诊疗,避免过度治疗和资源浪费[19]。
然而,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社区首诊和大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双向转诊制度发展仍然缓慢,国内严格意义上的社区首诊制度尚未建立起来;在以下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政策文件、基本药物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和绩效工资制度等不统一,不完善;双向转诊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欠缺;设备设施陈旧短缺、全科医生队伍缺口很大,且能力和素质不足、医生多点执业未全面放开;百姓“轻预防、重治疗”的不良健康观念、喜欢到大医院就医、对社区医院信任度不高;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管理不规范,无法实现信息资源共享;远程医疗技术有待进一步完善等[20]。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缺乏有效合理的双向转诊标准、 程序和监督管理方法。各地的双向转诊制度在实施上存在较大的随意性,难以保证服务质量[17]。
3.1.2 社区照护模式的发展 目前,二、三级医院与社区服务机构的转诊主要有3种模式:协议合作、 托管、 院办院管[21]。国内主要有以下几种社区照护模式:医联体模式、医院和社区机构间连续性服务模式、双向转诊模式、以医院为基础的肿瘤随访模式、“医院-社区-家庭”互动干预模式等。
医联体模式:可以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纵向流动,并盘活现有的区域医疗,但在执行过程中受利益分配、医保费用支付方式、医师多点执业等政策的制约[22]。医院和社区机构间连续性服务模式:从信息连续、机构连续、专业连续、人际连续4 个维度构建城市医院和社区卫生机构之间提供连续性医疗服务的模型,但存在社区医疗水平不足、双向转诊标准欠缺、信息共享系统不完善等方面的问题[23]。双向转诊模式:该模式的推行有利于肿瘤患者康复期的治疗,有效提高生活质量,减少并发症的出现,降低肿瘤患者医疗费用,缓解大医院压力,但国家补偿政策、激励监督机制欠缺、社区医疗机构技术力量薄弱、患者就医习惯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该模式的推广[4]。以医院为基础的肿瘤随访模式:结合主动随访和被动随访两种方法,采用信访、电话、门诊随访,家访随访等形式,进行了病案管理或医院管理性随访、康复治疗性随访或复诊随访、药物不良反应或治疗效果观察性随访、肿瘤治疗影响因素的研究性随访、肿瘤患者生存期分析的专题性随访。但存在电子病历系统不完善、患者及家属不重视、不配合等问题[24];“医院-社区-家庭”互动干预模式:该模式可改善患者的依从性,解决患者就医难的问题、而且可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25]。
3.2 开启肿瘤患者全面社区照护模式的建议
3.2.1 建立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通过相关政策的完善,保证资金和专业人员投入、实现社区首诊和双向转诊的顺利实施,加强监督、激励和管理、保障医保在社区照护中的合理覆盖和使用、保障基本设备和药品的供给。如:2014 年,甘肃省和黑龙江省对乡镇级、县级定点医疗机构的住院治疗病种进行了限制,私自越级转诊就将不予以报销等,推动了社区首诊制的实施[20]。
3.2.2 民众认知的改变 通过专业理念和知识宣教,结合相关政策引导,使民众了解并接受社区照护的服务方式和内容,增加对社区医疗服务机构的信任,遵循“小病在社区,大病在医院,康复在社区”的原则,实现肿瘤患者各阶段照护的无缝衔接。
3.2.3 加强培训和督导 建立健全全科医生和社区护理人员培训制度和规范,严格督导,提高社区医护人员的职业技能和素养,提高社区医疗服务质量。3.2.4 在各级医院之间搭建紧密的联络网 以大医院的专家团队为龙头,对二级医院和社区医院的医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或会诊,以此搭建稳固的学术交流和培训平台,联络网内的医院之间转诊标准明确,保证上转和下转均无障碍,使制度真正落实和持续化,解除社区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后顾之忧。
3.2.5 加强计算机信息网络建设 进一步动员政府和社会力量,实现各级医院的计算机网络化管理,使大中型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沟通顺畅无阻,便于进行必要的会诊和双向转诊,开展临床科研,为社区照护的发展提供循证医学证据。
3.2.6 社区照护团队的发展 除了医护人员外,需发展心理工作者、精神照顾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物理治疗师、志愿者队伍,保证肿瘤患者在社区得到“身、心、社、灵”的全面照护,使患者在社区照护中受益,提高对社区照护的依从性。
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社区照护服务模式需各方的大力投入和推进,地方政府、教育、法律和财政等多部门的共同参与和社会各部门的共同关注至关重要,只有上下一心,团结一致,才能使肿瘤患者社区照护健康稳步发展。
[1] CHEN W,ZHENG R,BAADE PD,et al.Cancer statistics in China,2015[J].CA Cancer J Clin,2016,66(2):115-132.
[2] 施萍,李俊.上海闸北区彭浦镇社区恶性肿瘤发病调查分析[J].实用全科医学,2008,6(4): 399-400.
[3] 陈海珍,张兰凤,陈建国.以医院为基础的肿瘤随访模式探讨与实践[J].中国肿瘤,2014,23(8):656-659.
[4] 张颖,赵丽波,韩磊,等.肿瘤患者双向转诊运行模式的建立与改进[J].中国医药指南,2011,9(28):378-380.
[5] 张志国,赵丽波,张颖,等.大肠癌生存者在医疗机构——社区转诊模式下的生活质量研究[J].中国全科医学,2013,16(5A),1481-1483,1486.
[6] 路雪芹,白琴.开展本土化临终关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J].中国老年医学杂志,2007,27(3): 299-300.
[7] 王慧.社区住院患者死因分析[J].中华全科医学,2010,8(2):213-214.
[8] PIEPER BB,DACHER JE.Looking backward toward our future:creating the nexus between community health nursing and palliative care[J]. J N Y State Nurses Assoc,2004,35(1):20-24.
[9] MITCHELL G,SEAMARK D.Dying in the community: general practitioner treatment of community-based patients analyzed by chart audit[J].Palliative Medicine,2003,17(3):289-292.
[10] 余红星,冯友梅,付旻,等.医疗机构分工协作的国际经验及启示——基于英国、德国、新加坡和美国的分析[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4,7(6):10-15.
[11] 曾楚华,赵莹梅,何友兼,等.癌症防治的社区服务[J].中国肿瘤,2002,11(3):144-145.
[12] ROCQUE GB,CLEARY JF.Palliative care reduces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cancer[J].Nat Rev Clin Oncol,2013,10(2):80-89.
[13] MASON B,BUCKINGHAM S,FINUCANE A,et al.Improving primary palliative care in Scotland: lessons from a mixed methods study[J].BMC Fam Pract,2015,16(1):176.
[14] 王茜,王薇,胡燕.中美社区护理现状的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全科护理,2014,12(8):679-682.
[15] 巫云辉,曹世义,邱德星,等.基于家庭医生团队的社区护理模式探讨[J].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13,30(2):109-111.
[16] 夏志平,闫文霞.社区癌症患者临终关怀的研究进展[J].当代护士,2014,(6):3-5.
[17] 毕芳,孙向军,任苒.双向转诊制度实施中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11,25(4):9-12.
[18]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N].健康报,2009-03-17(1).
[19] 罗灿红,张洁,邓水英,等.双向转诊模式的初步建立与实施体会[J].实用医技杂志,2012,19(6):659.
[20] 高启胜.我国社区首诊制影响因素鱼骨图分析[J].中华全科医学杂志,2015,13(3):341-343.
[21] 姚瑶,刘侃,罗桢妮,等.3种模式下医院医生双向转诊认知情况调查[J].中国医院管理,2012,32(3):67-69.
[22] 黄培,易利华.3种不同医联体模式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医院管理,2015,35(2):16-19.
[23] 李睿,张亮.医院和社区机构间连续性服务模型研究[J].医学与社会,2011,24(5):55-57.
[24] 陈海珍,张兰凤,陈建国.以医院为基础的肿瘤随访模式探讨与实践[J].中国肿瘤,2014,23(8):656-660.
[25] 陈红丽.“医院-社区-家庭”互动干预模式在社区老年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初探[J].实用预防医学,2014,21(2):232,248-249.
王玉梅: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缓和医疗分会副主委,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肿瘤姑息治疗与人文关怀分会副主委,辽宁省生命关怀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心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与支持治疗专业委员会肿瘤免疫营养学组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理事,东北三省肠外肠内营养学会委员,辽宁省免疫学会肿瘤免疫专业委员会副主委,辽宁省抗癌协会肿瘤心理专业委员会常委,辽宁省生命科学学会老年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曾在英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进行专业进修与培训。主持7届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发表恶性肿瘤姑息治疗专业论文30余篇。主要特长:晚期肿瘤姑息治疗,心理纾缓,灵性照顾。Email:m18940251490@163.com
R19
A
10.3969/J.issn.1672-6790.2016.05.003
2016-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