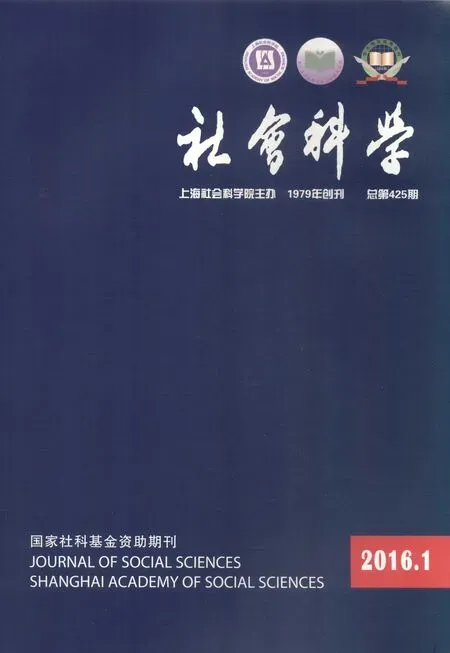天缘政治学研究:内涵、范式与价值*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
徐能武
天缘政治学研究:内涵、范式与价值*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
徐能武
当人类活动范围延伸到地球大气层外的太空时,政治学也必然发展到涵盖太空权力互动的“天缘政治学”。围绕权力展开的太空社会活动、形式和关系既是政治文明延伸的新高地,也是天缘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摒弃多尔曼之流为霸权扩张服务的太空控制论,“正本清源”后的天缘政治学研究,应把握天缘政治多样权力和共同观念实践建构的特征和规律。太空的高远位置和无疆域性特征,使得各太空主体很容易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发展军事航天技术,争先恐后地进行太空攻防对抗准备。太空技术典型的军民两用性和军备逆序效应,使得太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必然导致同归于尽,加之,太空技术作为信息流的空间段,具有和平、融合、发展的本质特征。因此,虽然天缘政治本质上仍是围绕权力展开的社会活动、形式和关系,但其权力运行并不必然导致冲突和斗争。太空技术促进人类经济社会加速融合的强大作用,使得天缘政治中进化合作远超进化冲突。世界各国在有效控制太空体系暴力的前提下,加速太空技术发展和包容、普惠、和谐的天缘政治文明建设,既反映天缘政治演进的必然趋势,也符合人类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从现有太空技术及其应用出发,构建恰当的天缘政治学理论分析框架,既是全球融合的现实命题,也是人类社会向何处拓展的未来需要。
太空;天缘政治学;和平融合发展;实践建构
政治学所关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现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人类本质属性的一种体现。广义上的政治“是人类集体生活的一种组织和安排,在这种组织和安排之下,各种组织、团体和个人通过一定的程序,实施对集体决策的影响”*① 燕继荣:《政治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因此,广义上的政治学关注的是人和人组成的社会怎样过上有组织的集体生活的问题。人类社会活动扩展到哪里,政治学研究就会跟踪到哪里。当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达到传统意义上的天际——地球大气层外的太空时,政治学也必然会从关注国内政治到国际政治,再到涵盖太空权力互动的“天缘政治学”(Astropolitics)。天缘政治学作为对天缘政治活动进行综合、分析和批判的考察而形成理论体系,既是人类政治活动太空拓展的现实要求,也是政治学自主成长的必然产物。因此,国内外学术界正在出现越来越多有关天缘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如“Anti Astropolitik Outer Space and the Orbit of Geography”; “Beyond the Sovereign Realm”; “The Geopolitics and Power Relations in and of Outer Space”; “Beyond World Risk Society”; “From Geopolitics to Astropolitics”; “Space Exploration in a Chang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he Making of New ‘Space’ Cases of Transatlantic Astropolitics”; “The Politics of Space Geostrategy in the Space Age”; “Governing the Final Frontier”; “A Polycentric Approach to Managing Space Weaponization and Debris”; “Reflections on Politics, Strategy and Norms in Outer Space”; “Space Control and Global Hegemony”; “Taking Sovereignty Out of this World Space Weapons and Empire of the Future”; “The (Power)Politics of Space”; “The Humanization of the Cosmos”; “Toward a Theory of Space Power”。,其中尤以国际期刊《天缘政治学》(Astropolitics)登载的文章为代表。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探讨空间技术发展与太空安全的互动影响*吴勤、高雁翎:《美国的空间对抗装备技术(上)》,《中国航天》2007年第7期;杨乐平:《国际外层空间安全与外空武器化评述》,载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2006: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页;徐海玉、卢亮、陈小前:《美国空天对抗政策评述》,《外国军事学术》2005年第3期;陶平、王振国、陈小前:《论空间安全》,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相关国家的太空政策、太空攻防的军事航天准备*常显奇等:《军事航天学》(第2版),国防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291页;李大光、万水献:《争夺制天权的基本特征》,《装备指挥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外层空间法与太空安全建构*高国柱:《欧盟“外空活动行为准则”草案评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李滨、赵海峰:《论外层空间活动争端的解决机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贺其治:《外层空间法》,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84页。、国际军控与太空安全*聂资鲁:《外层空间军备控制与国际法》,《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2014年版。等。国外研究则大多从空间力量建设角度谈太空安全问题*Erik Seedhouse, The New Space Race: China vs. USA, Praxis Press, 2010. p.15; Ray Williamson and Rebecca Jimerson, “Space and Military Power in East Asia: The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of Dual-Purpose Space Technologies”, Space Policy Institute, Washington D. C., 2001; David W. Ziegler, War,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ittle Brown, 1998; Ray Williamson, “Dual-Purpose Space Technologi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U.S. Policymaking”, Space Policy Institute, Washington D. C., 2001, http://www.gwu.edu/~spi/assets/docs/Collective%20Security%20in%20Space%20-%20European%20Perspectives.pdf..、太空国际军控*Detlev Wolter, “Common Security in Outer Space and International Law : A European Perspective”, Space Policy, 2006. p.19; Bhupendra Jasani, ed., Peaceful and Non-peaceful Uses of Space: Problems of Defini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an Arms Race,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1991; John M. Logsdon, James Clay Moltz and Emma S. Hinds, “Collective Security in Space: European Perspectives”, January, 2007. p.82, http://www.gwu.edu/~spi/assets/docs/Collective%20Security%20in%20Space%20-%20European%20Perspectives.pdf..、国内政治与太空政策,以及有关太空政策资料信息方面的智库、网络杂志和年鉴*如荷兰的《空间政策》(Space Policy)、美国的《今日军控》(Today Arms Control)、瑞典的《SIPRI年鉴: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等。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有关天缘政治学各主要领域的研究成果呈现出与日俱增的态势,但是在厘清其内涵、范式和价值基础上对天缘政治学进行系统科学研究的成果尚未出现。因此,当人类政治发展随着太空探索利用的步伐延伸到这一新的高地之际,如何科学构建天缘政治学的研究体系是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揭示了整个物质世界的本质特性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我们正确观察、认识世界的根本依据和科学指南。其中,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天缘政治学研究提供了系统的、全面的、彼此包容分析的理论基础。本文拟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来观察、探讨天缘政治问题,着眼太空主体交往实践,为建立一个较为科学的天缘政治学分析框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基于此,本文第一部分首先论析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阈下天缘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命题和硬核边界;接下来探讨如何摆脱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范式误导,把握天缘政治多样权力和共同观念实践建构的特征和规律,构建全新的理论范式;最后,论述天缘政治学研究作为拓展政治文明内涵和外延的理性努力,既是全球融合的现实命题,也是人类社会空间拓展未来需要的价值意义。
一、 天缘政治学探讨应先明晰其研究对象、主要命题和硬核边界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社会实践,即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交往互动实践。在太空探索利用实践中,征服太空、利用太空的能力决定着太空主体之间交往关系,而太空主体的互动关系对太空“生产力”——太空技术的发展具有反作用。“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政治是生产力和世界交往发展的产物,当不同国家进入太空展开探索、利用的社会实践活动时,各自利用太空技术为自身安全和发展服务,在国家间的互动交往中形成特定的天缘政治关系。
(一)天缘政治学主要研究围绕权力展开的太空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
由于不同情况下人类对政治本身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政治学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所提供的政治知识和研究方法也就随着政治内涵本身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天缘政治学研究的天缘政治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一部分,是人类进入太空展开探索利用实践活动以来逐步出现和成长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太空因其自然环境特征和人类太空技术的特点,是唯一真真切切、完完全全的全球公域。为什么这样说呢?其一,海洋并不是整个海洋都是公海,各国领海基线12海里内是领海,此外,200海里内是专属经济区。其二,空中公域也只是大气层内空间的一部分,因为各国领土、领海之上是其领空。其三,网络空间严格地来说,只是虚拟空间,是与实体空间迥然有别的,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它是否是与海洋、太空并列的空间,也是高度存疑的。各太空主体在最纯粹的全球公域——太空展开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凡是围绕主体间的权力而展开的社会活动、形式和关系就是这里所说的“天缘政治”。天缘政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延伸的新高地,既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太空活动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一类社会活动、形式及其关系。
在世界各国探索利用太空的社会实践中,各太空主体都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而且利益是多方面、多元化的。各太空主体的利益是在社会关系中实现的,因此,结成特定的社会关系就成为必然。利益是社会关系生成的出发点,也是社会关系维系和发展的归宿。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决定政治(关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以马克思主义宽广视野观察天缘政治问题,不难发现,各太空主体由其经济社会基础和太空技术能力的不同,反映在太空社会关系上,出现了不同太空主体之间,既有对立与斗争的关系,又有协作与联合的关系。这些不同关系的维持要靠权力进行调整、控制和支配。没有权力的作用,就会出现关系的混乱状态,从而影响太空开发利用活动的正常进行。因为,在太空社会关系运行过程中,利益的实现不是自行实现的,冲突与矛盾不可避免。一般说来,解决矛盾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矛盾双方自行解决问题,另一种则是需要通过权力的介入来解决,或者以权力为中介,或者由权力支持其中的一方压倒另一方使矛盾得到解决。天缘政治所指的正是后一种情况,即通过权力强行调节太空利益关系,保持太空主体间共同秩序的社会活动、形式及其关系。
天缘政治形成和发展是地缘政治扩展与太空战略竞争态势演变的必然产物。按照现有太空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各国太空开发利用活动都是在其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的,也就是说各国需要对自身国内不同太空主体的太空活动在国际层面承担统一的主体责任。由于国际社会至今仍然缺乏类似国内政治中的中央政府权威体系,而各国之间在太空活动领域的互动所形成的利益关系中也难免出现矛盾和冲突,由此引起的战略安全和合法权益维护问题同样需要权力强行介入来解决,这类围绕国家间权力而展开的太空社会活动、形式和关系,是人类太空社会活动的核心组成部分,即作为天缘政治学研究对象的天缘政治,对其进行科学研究既事关各国的国家安全,又事关世界和平,更事关人类的前途命运。
(二)太空战略利益博弈是天缘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命题
如果从广义上把天缘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各太空主体如何在太空社会活动、形式和关系中,通过权力这一建立在一定利益关系基础之上的内在化强制性社会关系来构建有组织的集体生活。无疑,思考主体间围绕冲突与合作、战争与和平这一主题展开的太空战略利益博弈,则是天缘政治学要研究的主要命题。“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已经提供了战争、冲突和人类解放的处方,只不过这种处方更为宏大、所需的历史时段更长而已。”*胡宗山:《主题·动力·范式·本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强调世界交往是国际社会形成的基础,国际政治中矛盾无时无处不在,矛盾的解决过程也是国际政治发展的过程。天缘政治的成长是太空主体互动中实践建构的结果,太空战略利益博弈的实质是国家间利益博弈在太空的延伸,而这一过程取决于以太空技术为支撑的太空实力。太空技术作为各国征服太空改造太空能力的标志,是太空探索利用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它的发展进步从根本上制约着天缘政治中的权力关系。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关系由“地域性的存在”逐步向“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发展、最终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类社会演进的必然历史逻辑,这种进化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9页。。认识到作为人类征服太空的“生产力”——太空技术对各太空主体交往方式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太空技术的全球化本质,既可洞悉天缘政治演化中的客观规律,又能切实理解太空冲突、太空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而是同归于尽的严重后果。因此,合作是太空安全的唯一坦途。太空技术及其应用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将成千上亿的个人纳入地球村相互依存的生活中来,与此同时,也改变和塑造着个人观察分析国际政治,尤其是天缘政治问题的眼界和方式。在信息时代,各种“信息高速公路”若没有“太空段”的衔接,信息的流动将不可能畅通,也就无法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太空和数字化生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科技的逻辑决定国际政治的逻辑,航天科技国际合作的内在要求必将克服越过国界的限制,从而为太空合作提供现在看来仍感遥远,但最终可期的美好前景。”*徐能武、彭舒帅:《混沌理论视野下外层空间安全利益博弈与汇聚研究》,《求索》2013年第8期。
太空技术“天使”、“魔鬼”兼具的特征,使得太空战略筹划尤显重要。对太空技术决定的太空能力增长的理性分析,引出权力相互依存的客观现实性,要求太空战略谋划,既要考虑自身利益,又要着眼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如何构建一个从太空技术的高度相互依存的特性出发,确保太空的战略稳定性、拓展性和可持续性的分析模型,既是对太空战略制定者智慧的考量,也是天缘政治学进行理论创新的关键和重点。美国在太空技术和航天管理上是一流的,但在太空战略推进上却出现了短板:阿波罗项目结束以来在载人航天方面缺乏明确一贯的目标和坚定的政治支持,直接后果就是载人航天的大起大落和一系列项目的半途而废。这种政治支持的动摇本身又是美国向信息化、多元化的技术—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的反映。美国航天飞机项目的终结和载人航天的未来发展问题,既集中反映了美国太空战略的动向,也对天缘政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天缘政治学对太空战略利益博弈这一主要命题的研究,需要从太空技术的现实效应和效能出发,在战略的层面研究相关政策、法律、外交、文化、哲学问题*黄嘉:《外空伦理研究》,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如何将技术动力与政治—社会目标结合起来,实现航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上述提到的美国问题,也是世界其他国家同样面临的问题。譬如,2010年6月28日,奥巴马总统公布了新的国家太空政策。该政策与布什政府相比:更加强调通过国际合作维护太空安全,倡导负责任的太空行为,在太空军控与裁军的立场上明显松动,单边主义倾向明显减弱。军事上更加注重太空态势感知、定位与侦察等太空力量的非作战应用,注重通过发展先进发射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加强快速响应能力建设。强调商业航天力量的建设,载人航天运输也实现商业化,通过政府采购等措施,培育商业发射市场,以强大的航天工业基础支撑航天事业。再如,美俄太空合作,尤其是在载人航天领域的合作(国际空间站),很多方面可能会给未来的中美太空合作提供范例。
(三)天缘政治学研究应围绕天缘政治的实质明确其硬核和边界
澄清了天缘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命题之后,就应在把握其硬核的基础上,明确天缘政治学的研究边界。“天缘政治学作为一门政治学的分支科学,它应该符合政治学的学术发展方向(或该领域)的要求。”*[俄]E·切尔托克:《21世纪航天——2101年前的发展预测》,张玉梅、杨敬荣等译,国防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一般来说,政治学主要研究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的社会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由此可知,天缘政治学就应该研究太空开发利用过程中,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的社会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具体来说,这种含义上的天缘政治学主要研究“航天在国际社会发展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组织开展航天活动及将航天活动用于国际关系的方式方法,各国为了达到政治、军事、经济、科技、信息、生态及其它目的而在国家内政外交中对航天活动的利用方法”*参见[俄]E·切尔托克《21世纪航天——2101年前的发展预测》,张玉梅、杨敬荣等译,国防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诚然,这一定义大大拓宽了天缘政治学的内涵和外延,而不是狭义地利用太空权力的“太空控制论”。天缘政治学所研究的这一人类政治文明延伸的新高地,与其他太空社会活动、形式和关系区分开来的是天缘政治同任何层面的政治一样,这种社会活动、形式和关系是围绕权力特别是国家间权力进行的。太空权力是决定天缘政治活动发展状况的根本因素。因此,与太空实践活动相关的权力是天缘政治学的硬核。围绕天缘政治中的权力展开研究,不难发现天缘政治中权力扩张的帝国逻辑与太空技术民主融合实际功效之间的悖论,从而认识到天缘政治进化合作是构建包容、普惠、和谐天缘政治秩序的必经之途。
天缘政治学作为政治学延伸发展的前沿,其硬核定位了其研究边界的原点。这也就是说,天缘政治学主要研究围绕权力特别是国家间权力而展开的太空社会活动、形式和关系。因此,不与权力直接相关的太空技术研发本身或太空开发利用的技术方案,以及围绕市场展开的纯粹的太空经济活动等,都不属于天缘政治学关注的范围。但如果是从权力的视角研究太空产业化商业化对主体间社会活动、形式和关系的建构和影响,则又可包含到天缘政治学研究的范围。天缘政治学研究的边界涵括关涉太空探索利用中所有利用权力来强行调节、控制,以建立一定政治秩序的社会活动、形式和关系。随着天缘政治的形成和发展,天缘政治学的研究边界也必然是不断浮动扩展的。从横向空间来看,人类在太空能走多远,边界就会延伸多远;从纵向深度来看,太空技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的应用和影响有多深入,边界就会拓展多深。这种人类社会实践有可能发生在太空,有可能发生在大气层空间,也有可能发生在地球表面或深层,甚至是在网络电磁空间等虚拟空间。当然,也有可能几者兼而有之。只要是围绕太空活动中的权力而展开,就属于天缘政治学研究的边界之内。
从根本上来说,围绕权力展开的天缘政治作为人类太空社会实践的核心组成部分,它的运作范围是由太空技术和太空能力所决定的,因此,它会随着太空技术及其应用的发展而发展。从1957年前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开始,早期的太空系统主要运用于侦察与核查,仅仅服务于核威慑战略,基于太空实力的权力主要在美苏核恐怖威慑中起着微妙的平衡作用,如曾被吵得沸沸扬扬的“导弹差距”威胁和星球大战计划等。天缘政治的主体主要限于美、苏两家。这是天缘政治形成的第一阶段,即起步阶段。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太空系统被广泛运用于现代战争支援,意味着有限太空战的开始。其后,在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中,太空已完全纳入联合作战。从太空多个行为体、太空技术规模和太空博弈成为国际政治主要矛盾之一等三个标准来看,“世界政治(全面)进入天缘政治时代几乎与人类迈进新世纪(几乎)是同步的。大致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基于先进太空技术的大国之间太空竞合构成了一种天缘政治的结构关系。……因此,21世纪的门槛不仅表明一个新世纪的到来,更标志着世界政治迈入了天缘政治时代的门槛”*胡键:《天缘政治与北斗外交》,《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
二、 天缘政治学研究应把握天缘政治实践建构中的范式转换
太空技术及其应用已成为世界高新技术发展水平的集中展示,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经济和国防现代化水平乃至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也是大国地位的重要支柱。天缘政治起源于国家对安全利益的关注,而基于太空系统特点出现的进化合作远超进化冲突的特征决定着天缘政治发展的进化取向。这就要求天缘政治学研究应摆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诸范式的误导,把握天缘政治多样权力和共同观念实践建构的特征和规律,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指导,积极构建符合天缘政治和平融合发展本质特征的全新范式。
(一)天缘政治学研究应摆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诸范式的误导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同的政治实践需要不同的理论范式指导。“范式也可以称为大理论,是一个理论群,是关于世界政治性质的一组假设。不同的范式关注不同的问题,运用差异的概念。”*王帆、曲博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思想、范式与命题》,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范式包括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来探讨人类活动拓展到太空这一全球公域后,不同太空主体(特别是国家)在国际互动中所产生的天缘政治问题时,不难发现,其理论假定的局限性。新现实主义虽然丢掉了古典现实主义的人性论假说,但认为只要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不变,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都会围绕权力这一轴心运转,这是不可更改的客观规律,所以也被简称为“权力范式”。这种围绕着权力争斗思考相关问题必然陷入循环论的怪圈。如果以权力政治活动为目的的情况持续下去,人类是永远没有希望的。从本体论的角度看,新现实主义具有客观唯心主义的特征,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则具有明显的循环论色彩,因此,新现实主义无法适用于天缘政治的分析。例如,作为当今太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前中情局情报分析员和美国空军学院教授艾弗里特·多尔曼将天缘政治学界定为关于太空的地缘政治研究,赤裸裸地提出“太空控制论”*Everett Dolman, Astropolitik: Classical Geopolitics in the Space Age, London: Frank Cass., 2002. p.15.。这实际上仅是现实主义“制权理论”的一个机械翻版而已。
与之相对应,新自由主义是进化性理论,其认为制度是人为的社会事实,制度可以促成国家间的合作行为。若将人在建立制度方面的能动性考虑在内,就是人通过努力可促成合作,国际政治的整体发展可以走出循环圈,不断向更趋合理的方向发展。但是,各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也是以先入为主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作为第一重假定,其哲学基础具有明显的客观唯心主义色彩。新自由主义认定国际政治中各国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会围绕权力进行理性的博弈选择。诸如在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的国际关系中不对称的相互依赖成为国家间权力一个新的重要来源,或者由霸权建立的国际制度在霸权之后,仍应维持其为“隐形霸权”服务的功能,等等。显然,这一范式并没有摆脱“权力范式”的窠臼。尽管上述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这两种理论都属于理性主义,但是,它们却给出了互相对立的结论。这种现象表明,现有的理性主义理论并不是完备的理论,也就是说,现有的理性主义理论的基本假定(无政府主义、国家行为体、国家利益最大化等)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从而导致相关理论无法恰当描述或者有效预测天缘政治中的国家互动。
建构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无疑为西方国际政治的研究范式带来了深刻的影响*Jeffrey T. Checkel,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2, 1998. pp.324-348.。建构主义认为由观念和话语构成的结构至少具有与物质结构同等重要的地位,而结构与行为之间并非理性主义所探寻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构成的关系。如果说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构成的理性主义容易陷入客观唯心主义,建构主义则具有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因为,建构主义中所谓“朋友”或“敌人”的共有观念,总体说来,都是一种主观判定。西方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将观念作为国际政治的根本原因的论断导致严重的因果解释错位,与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明显相悖。另外,建构主义否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认为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判然有别,“社会世界中的一切皆因人们的施动性活动而建构,人们在建构世界的过程中同时也深刻理解了所生活之世界”*董青岭:《复合建构主义——进化冲突与进化合作》,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建构主义强调社会实践是主体活动的建构过程,但否认其同时是一种物质运动的客观过程,并不承认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所构成的矛盾运动,看不到实践中人与自然或物的关系。因此,建构主义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并不适合于用来探讨人类社会实践扩展的天缘政治问题。
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实践作为国际政治分析的逻辑起点,重新界定了政治演变中物质与观念的辩证关系,“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感觉是客观世界、即世界自身的主观映像。”*《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页。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强调物质与观念辩证关系,以二者的“决定”与“反作用”来解释体系冲突/合作的进程选择,进一步澄清了物质结构与观念结构的互动关系。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来看,天缘政治的实践建构与持续进化取决于对两个核心变量的考察,即太空技术发展程度与天缘政治权力结构。
(二)天缘政治学研究应把握天缘政治物质权力和共有观念实践建构的特征和规律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的天缘政治学研究应从支撑太空技术的社会经济因素入手,分析太空技术的安全功效,洞悉天缘政治关系的演变和天缘政治运作过程。在诸多影响因素之中,作为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集中表现的科学技术变革与扩散,对于太空这样高度依赖科技发展的新兴战略空间而言,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强调的现代生产力最前沿的代表者——科学技术对太空主体互动关系具有决定作用,将科技本身的变革与发展纳入天缘政治演变的分析框架中,将有助于理解作为征服太空能力标志的太空技术如何对行为体和整个体系施加影响。太空技术实力是太空权力最直接最主要的来源,太空技术实力差异决定太空权力结构,物质权力决定共有观念,共有观念对物质权力变化具有反作用。一般来说,具有战略意义的技术变革或扩散容易催生分离性政治认同,而当技术发展均衡稳定时,聚合性政治认同较易形成。
因此,天缘政治学研究着重关注天缘政治演化的特征和规律,显得尤为重要。尽管目前国际上有一系列条约和文件,禁止在太空部署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然而随着世界上少数国家致力于发展太空武器,太空军事化的势头在不断发展。美国制天权理论家詹姆斯·奥伯格就曾指出,几乎可以肯定,有人会在21世纪的某个时候部署天基武器,其理由将是为了防御的需要,其方式将与20世纪后半叶核武器的发展情况十分相似,与核武器不同的是,太空武器一旦部署就可能被使用。但是,也应该看到,太空开发利用缘起于对国家安全和大国地位象征的追求,太空武器自杀伤效应导致的军备逆序和太空系统越依赖越脆弱的特点,决定太空攻防对抗准备得不偿失。天缘政治中的多极化趋势和极易非对称和平反制的态势,决定太空冲突和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而太空技术发展中非对称抗衡的局面很容易出现,因此,聚合性政治认同较易形成,“合作共赢”必将成为主体间最理性的选择和共有观念。当然,前提是各国太空技术不为强权所限制,得以自由发展,特别是那些作为非对称的和平反制手段的技术应得到宽松的发展环境。太空技术覆盖全球、跨越各域、连通民心的特征,使太空作为最典型的全球公域成为人类新型政治文明孕育、发展的最佳场所。天缘政治和平融合发展的本质特征,决定包容、普惠、和谐的天缘政治文明建设,是全球融合、世界大同的必经之途。
由此,运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天缘政治学时,应从天缘政治的技术缘起着手,探讨天缘政治中单一主体试图利用太空优势控制他国的帝国主义企图与太空技术客观上促进不同主体民主融合趋势之间的权力逻辑,强调指出帝国逻辑与民主融合的基本矛盾构成了推动天缘政治发展的内在动力。或者说,仅从太空技术的战略意义层面看,太空国家更易于围绕安全利益博弈进行攻防对抗准备。但是,当太空主体间出现势均力敌的状态,由于太空极易进行非对称反制的特点和太空技术跨越沟通的强大功能,又使得暂时或长久的太空合作成为可能。这可从天缘政治的早期表现形态——美苏太空政策分析中研究各国在天缘政治中的进化冲突与进化合作的规律。在对各国太空政策的本质和内涵进行严谨的重新评估基础上,不难发现天缘政治多样权力和共同观念实践建构的特征和规律。因此,围绕天缘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命题——太空战略安全问题逐个展开,从不同的角度剖析天缘政治中的太空武器化与军备控制、太空行为准则与环境安全、太空资源利用与合作机制、太空产业化商业化与复合依存等问题,就可构建起一个较为清晰明了的天缘政治学分析框架。
(三)天缘政治学研究应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进化取向
马克思主义对国际社会的总体思考和人类历史的深层认知,即政治关系在国际范围内的延伸与放大,本质上它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历史运动向全球范围扩展所必然带来的。“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属于进化理论,它认为历史进程是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规律深刻制约的,相信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不断演进的……。”*胡宗山:《主题·动力·范式·本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2期。政治文明的发展和人类的解放需要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基础上,准确地定位自己的历史使命,并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来制定自己的战略目标和行动方案。天缘政治说到底,是表现为太空技术的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太空作为当代最先进的生产力综合集成所作用的领域,太空技术被主要大国广泛用于国际安全互动领域,太空技术发展的程度决定着天缘政治的状态和方式。在天缘政治互动中,相关太空主体要目光远大,善于从全人类解放角度去寻找价值坐标,为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作出应有的贡献。
从太空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这一基本矛盾推动的天缘政治发展的现状出发,切实维护太空战略安全和合法权益,既事关国家发展大计,也是人类太空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在国际关系领域意味着,谁能够创造财富,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谁就能拥有话语权,拥有制定规则的权力。”*玛雅编:《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人类史上大国兴盛崭新模式》,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2页。随着世界各国太空开发利用的不断深化,维护太空战略安全和各国合法权益日显重要。为此,在把握天缘政治实质的基础上,有关国家制定一个什么样的太空战略,既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也是一个非同小可的现实问题。与一般从战略或技术的角度探讨世界各国太空探索利用问题不同,天缘政治学的研究视野应更多地关注天缘政治作为人类在太空开发利用中形成的一个复合体系,其特有的内在结构和演变规律。从太空无疆域性和各国进入太空寻求的国家利益实质上是一种技术性级差空租的特征入手,通过全面地分析天缘政治的起源、动力、本质、演进、问题、前景等主要内容,运用系统思维方法把其作为由诸多要素构成,按一定运行规律存在、发展的有机体,从而极力寻找提高其整体效能和优化参与的方法。
人类探索利用太空是史无前例的艰巨事业,仅依靠任何一国的单独力量都是相对有限的,太空技术作为最前沿科学技术的集大成者之一,其高度社会化,要求在全球范围内按照市场规律进行优化组合,才能最有效地配置资源,促进发展。因此,世界各国太空开发利用应坚持共同发展的大方向,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结成利益共同体,把技术的互补性转化为发展的互助力,不断扩大利益交汇点,实现互惠共存、互利共赢。同时,实现太空探索利用中的共同发展,根本出路在于太空技术的交流融合。创造天缘政治的美好未来,要靠各国的自身发展,更要靠各国的共同进步。各国要在切实维护现有国际太空法框架下各自拥有的相关权益的基础上,深化太空领域务实合作,积极推进技术深入交流,促进产业深度合作、优势互补,在开放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构建太空融合发展的大格局,形成命运共同体。再次,人类太空探索利用事业的进步依赖于太空的战略安全,太空战略安全是太空活动顺利开展的基础保障。太空战略安全是指在太空探索利用过程中相关国家安全互动的任何一方不会受到他方人为的系统性伤害,它并不包括太空技术限制或不足所造成的安全问题。维护太空战略安全,需要相关国家凝聚共识,积极作为,共同担当起应尽的责任。各国应维护太空战略安全,打造责任共同体,推动太空安全对话与磋商,积极推进太空国际军备控制,积极探讨建立和完善太空国际安全合作机制。
三、 天缘政治学研究既是全球融合的现实命题也是人类空间拓展的未来需要
太空探索、利用、开发的“高边疆”区域特征,对地球上的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发展都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沿着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思路,以太空技术的效应和效能分析入手,对太空技术鲜明的军民两用性、高方位带来的全天候性等特征进行战略思考。从天缘政治围绕权力实践建构的实质出发,构建一个太空技术发展与战略稳定性关系的天缘政治学研究体系框架,既可开拓人类政治文明的新高地,又能寻求人类和平融合发展之道,更是探讨人类社会向何处拓展的宏大课题。
(一)天缘政治学研究是拓展政治文明内涵和外延的理性努力
在把握天缘政治学中国际政治权力的主要功能和特征的基础上,可以看到大力推进天缘政治文明建设,既是全球融合的现实命题,也是人类社会空间拓展的未来需要。政治文明指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和政治发展取得的成果。在天缘政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立足于权力基础上的合作,以一种地球之上的国际政治很少见的方式而出现,这正是天缘政治学不同于现有一般政治学理论的地方。当在太空活动中相关国家间各种权力类型相互作用、相互强化,使得天缘政治发展既呈现出惬意的合作,也难免平添不安的冲突。从天缘政治的历史实践和基本类型来看,除共同利益、权力结构这些核心要素外,共同的基本理念和道义准则、外部强制力、认知要素、国内政治,乃至制度惯性等,都对天缘政治文明建设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如何理性地认识和利用其积极因素,防止消极因素的负面影响,趋利避害、蹄疾步稳地推进天缘政治文明进步既是天缘政治学研究的旨趣所在,也是人类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包容、普惠、和谐的天缘政治文明追求反映了人类社会政治空间拓展的趋向。政治文明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可以概括为:一是努力将人类对美好政治生活的构想付诸实践;二是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提高非暴力状态下解决政治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性;三是使所有社会成员在一种文明祥和的政治状态下各得其所,互爱互信,共存共荣*桑玉成:《现代政治文明的源起及其演进——桑玉成教授在复旦大学的讲演(节选)》,《文汇报》2003年12月29日。。当人类文明发展到能真正“上天”的高度,理应从理论上充分把握天缘政治多样权力和共同观念实践建构的本质,从而以理性且睿智的态度引导天缘政治朝着安全、美好、幸福的方向发展。
太空技术的跨域互联性和太空战导致同归于尽的必然结局,迫使理性的太空主体在天缘政治利益博弈中,采取越来越平和、越来越合理、越来越能够有效地解决主体间矛盾和冲突的方式和手段,从而也越来越有利于国际社会形成综合、共同、全面的安全观,互利、合作、共赢的发展观,开放、包容、互鉴的文明观,仁爱尚德、兼怀天下、同舟共济的道义观。立足现实放眼未来的天缘政治学研究应在继承、发展已有学界相关成果的基础上,从现有太空技术发展的实际能力和功效出发,以新的体系、新的方法丰富和发展天缘政治的学术研究,构建恰当的天缘政治学理论分析框架,拓宽其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理清太空开发利用的理念追求与实践要求的互动关系,为探寻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科学坦途提供理论支撑。
(二)天缘政治学研究是促进全球和平融合发展的现实命题
科学技术研究对象的客观性、认知规律的共同性和科研成果的普适性,决定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全球化本质。因此,具有全球化本质的太空技术的发展和扩散,有利于人类在地球村中的和谐相处与共同繁荣。随着太空技术的深入发展,太空探索利用正由主要是一种国家行为向非国家行为扩散,各种开发主体间呈现出高密度利益博弈与汇聚的状态。这种高密度利益博弈与汇聚是太空技术开发利用中个人对个人、个人对公司、公司对公司、个人对国家、公司对国家、国家对国家等高度交叉、串联、并联、平行等异常复杂的依存关系,并且这一“关系团”将继续增大,复杂化为真正意义上的混沌世界,然后发展到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最终达到你我不分的共同体。天缘政治的实践建构与持续进化不仅有助于和谐世界的建构,而且有利于推动国际社会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美好未来。
太空高科技鲜明的全人类共通的逻辑从根本上决定着天缘政治中以合作为主的政治逻辑,但这一切诚然不会自动到来,它需要理性的人类在充分领悟科技这一社会本质的基础上,利用一切政治智慧,包括均势政治导致秩序的原理来寻求太空开发利用中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如期实现*徐能武:《外层空间国际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8页。。当前,美国作为太空安全领域的唯一超级大国,加之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与中国迥异,在作为典型高阶政治的天缘政治领域,极力防范、限制,乃至施压于俄罗斯、中国等其他国家。2011年美国“奋进”号航天飞机携带着中国科学家付出心血的阿尔法磁谱仪在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之际,中国记者竟因所谓的“沃尔夫条款”而被拒之门外。2013年美国NASA禁止中国人参加讨论开普勒(Kepler)太空望远镜探索太阳系外星体的研究计划的天文会议。美国以外其他太空主体大力发展太空技术,就可以非对称和平反制手段威慑、遏制美国太空霸权企图,从而确保天缘政治的良性发展。
天缘政治学研究既是为了探讨各国人民为探索太空、利用太空、征服太空而奋斗的内在动力机制,也是为了寻找各国按照和平融合发展的天缘政治时代要求处理国与国之间矛盾和问题的基本准则。这既不会是单纯的所谓鸽派观点,也不是所谓鹰派的谋略,而应该是直面现实的真心思考。在太空中传统地理位置上的国界不复存在,有着理性智慧的人类不得不面对太空全新环境,甚至外星智慧物种的挑战。来自地球上的人类利用太空技术想从相互冲突中获利,这极易导致同归于尽而急需协调,国际政治一体化既有明显的可能性,更具有紧迫的现实性。事实上,世界各国只有真正认识到太空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并在太空探索利用的实践活动中把它付诸实施,才能从社会的层面实现人类共同利益。由此,不难推出天缘政治中合作共赢的实践必然引领全球和平融合的深入发展。
(三)天缘政治学研究是探讨人类社会向何处拓展的未来需要
人类冲出地球进入太空标志着人类开始可以以天的方式俯视大地了。探讨人类向何处去,是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两途,或者被认为是自由民主社会,这更多地是从时间——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角度所做的思考。而从空间来说,则应探讨人类在完全支配地球,如何抓住机会进一步向太空拓展的空间问题*王岳川:《空间文明时代的中国文化身份》,《学术月刊》2006年第7期。。“人类未来将在太空中生存,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人类即将耗尽全部生存资源,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这方面,天才的预言家克·埃·齐奥尔科夫斯基有句名言,‘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中’,这是绝对正确的。未来的人类是属于整个宇宙的。”*[俄]E·切尔托克:《21世纪航天——2101年前的发展预测》,张玉梅、杨敬荣等译,国防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61;21—22;64、69页。
天缘政治学研究必然要探讨人类社会向何处拓展的天缘政治演进的趋向和前途问题。经过较深入的探究,不难认识到当人类冲出地球进入浩渺沉寂的太空时,“现代国际社会的发展条件,保障国际和国家安全这一任务的特殊性,形成和保持一个国家必要的太空能力,制定和开展国际和国家航天计划的原则,为了政治、经济、军事及其它目的而利用航天活动的成果,这一切都要求在新学科(学科方向)范围内进行专业的研究”*[俄]E·切尔托克:《21世纪航天——2101年前的发展预测》,张玉梅、杨敬荣等译,国防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61;21—22;64、69页。。天缘政治是典型的多样权力和共同观念实践建构的政治社会,它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而它的存在和发展更受其内在规律的支配和作用。天缘政治建构源于国家对太空技术性级差空租的追求,由各个国家太空技术发展所决定的国家间权力分配结构直接影响到天缘政治的内部组成,而太空交往实践中形成的共有观念,特别是作为“类”的人在太空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其他可能出现的挑战,所必然出现的同类相助的合作观念要远强于地球这一狭小的摇篮之内,人类在太空的共有观念对天缘政治活动中的治理体系的进化有着不可避免的作用。
天缘政治实践正在探索和预示着人类社会光辉灿烂的文明前景。2015年7月24日美国航天局宣布,由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发现,一颗1000多光年外的行星开普勒—452b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像地球的宜居的行星,被誉为地球2.0;虽然由于其遥远的距离,对地球上的人类依然遥不可及,但太空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预示人类社会空间拓展的方向。“人类始终是理智的,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可能正是为了能使理智在宇宙得以孕育,每个人可以发挥各自的想象,大自然或超级力量在宇宙深处选定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地球,创造了人类。……未来的人类将是整个宇宙中的人类。为了这一未来,现在就应着手准备。”*[俄]E·切尔托克:《21世纪航天——2101年前的发展预测》,张玉梅、杨敬荣等译,国防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61;21—22;64、69页。由此不难理解,从终极意义上说,天缘政治学研究是探讨人类社会向何处拓展的未来需要。
结 语
通过对天缘政治学的内涵、范式和价值的研究,不难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太空技术是天缘政治进化的根本动力,各国和平利用太空的技术应不受限制地得以最好最快地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天缘政治学就是各国太空活动中关于权力分配方式和权力运行机制的研究,更直白地说,天缘政治学也就是各国太空活动中有关权力的学问。天缘政治中权力的基础是多元化的,但其最主要的来源则是太空技术形成的实力。太空技术作为太空开发利用中的第一生产力,推动着人类对太空探索和利用的不断深入。由此,各国在太空领域的互动实践也必然不断加深,太空国际关系逐渐成型,天缘政治应运而生。太空作为最真切的全球公域,各国和平探索利用太空活动不应受到限制,任何国家、任何势力无权以所谓“敌国”名义,不让他国自由和平探索利用太空。二是太空战略安全是天缘政治运作的核心目标,国际社会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太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从天缘政治发展的现状来看,国际社会在太空非军事化上虽然形成了一定共识,但对于如何推动太空军备控制以及推动何种类型军备的控制并未形成有效规范。现有太空国际安全机制仍然是以禁核(禁止天基部署核武器)不禁天(即各类对天武器和天基常规武器)为总体框架。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大力发展天基和地基反卫星武器、反导系统和全球快速打击系统,推动了太空领域攻防平衡向进攻占优转化,加深了太空战略安全的不稳定性,同时也使太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威胁日益加剧。因此,针对日益临近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旗帜鲜明、千方百计反对太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以维护太空战略安全和各国合法权益。三是和平融合发展是天缘政治的本质特征,决定包容、普惠、和谐的天缘政治文明建设是全球融合的现实需要。太空的探索利用是国家的事业,也是人类的追求。进入21世纪以来,技术的发展降低了人类探索太空的门槛,拓展了开发利用太空的规模、广度和深度,有利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增进和发展。然而,由于国家及其管辖下的企业探索利用太空的基本动因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往往以非合作甚至对抗的方式处理相关矛盾,也引发了许多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在当今各国讲求实力政策、争取太空优势、提升军事水平的时代背景下,太空军备逆序和极易非对称反制的特点,必然迫使各国认识到,积极参与推动太空国际安全合作是维护和拓展太空安全和发展利益最理性的选择。太空技术覆盖全球、跨越各域、连通民心的特征,使太空探索和利用不但有利于推动一国内部各种资源的统筹利用和各产业的协调融合,而且有利于推动世界各国的和平、融合和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潇湘子)
Connotation, Paradigm and Values in the Astropolitics Study:A Perspective from Marxism IR Theory
Xu Nengwu
Politics is bound to develop into astropolitics that explores space power interactions, as human activities expand into outer space beyond the Earth’s atmosphere. The social activities, patterns and relationships around the power not only constitute a new domain of political civilization, but also provide core content for the study of astropolitics. To clarify the misperception about astropolitics produced by Dorman and others who use the theory of space control as a means to hegemonic maintenance and expansion, this re-study of astropolitics aims to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laws of the practical construction of diverse powers and the common concepts in space politics. It is the features of lofty position and no boundaries that stimulate each space body easily to develop military space techn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security, scrambling to prepare the confrontation of attack and defense in space. Owing to a typical dual-use nature of and armaments reverse effect of space technology, the weaponization and arms race in space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perish together. In the meantime, space technologies as a space segment of information flow have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with development of peaceful and merge. Therefore, although astropolitics is still the social activities, patterns and relationships around the power in essence, the power in astropolitics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conflict or struggle. Space technology has so strong role to accelerate human economic and social integration that the evolutionary cooperation far beyond evolutionary conflict in astropolitics. It is that each country accelerates the development of space technology and construction inclusive, universal benefit and harmonious astropolitics civilization under the premise of the effective control to the space system violence can reflect not only inevitable tendency astropolitics evolution but also the objective laws of hum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Starting from existing space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a modifi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astropolitics is constructed, which serves not only as a realistic foundation for global integration, but also future needs as human society expands.
Outer Space; Astropolitics; Development of Peaceful and Merge; Practical Construction
2015-10-27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平发展背景下维护外空战略安全和合法权益研究”(项目编号:12BGJ033)的阶段性成果。
D51
A
0257-5833(2016)01-0003-12
徐能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湖南 长沙 41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