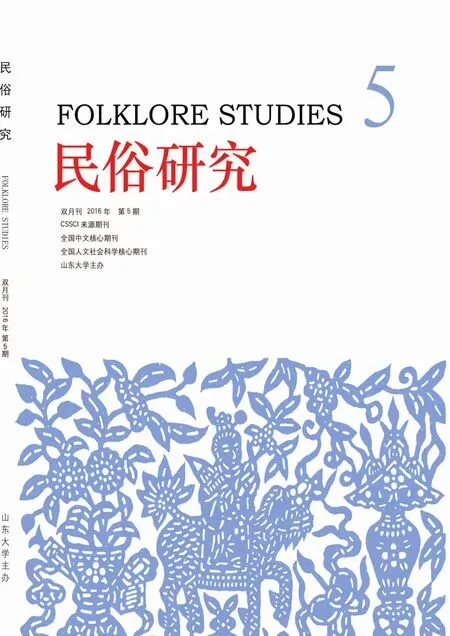消失的迷宫:沂水刘南宅传说中的神话与历史
刘宝吉
消失的迷宫:沂水刘南宅传说中的神话与历史
刘宝吉
刘南宅是明清两代山东省沂水县最有权势的缙绅世家,长期以来它一直为一个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所笼罩。这个传说的起源与刘南宅四世刘应宾的一段遇仙奇遇有着直接的关系,是明清时期吕洞宾信仰在民间盛行的一个例证。通过深入的历史考察,我们会发现,它不仅透露出一个缙绅世家在帝国之下的崛起以及在近代转型中的最终败落,还涉及到一个地方性社会神话的形成和在现代世界中的“去魅”。作为历史过程与社会情境相互作用的产物,这种类型的社会神话与地方社会权力结构有着紧密的关系,更是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集团所拥有的文化霸权的一种表征。
刘南宅;吕洞宾信仰;社会神话;文化霸权
一、小 引
1927年,山东籍青年作家刘一梦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提到Y城南门里住着一位被称为“老大人”的绅士,他家的住宅被称为南宅。“但南宅之著名,还另有原因在,据说这所住宅是八卦形式,纯阳老祖画的图,不熟悉的进去了就出不来。”*刘一梦:《斗》,《小说月报》1927年第18卷第7期。对于沂水县的居民而言,他们会很容易认出Y城就是家乡的县城,所谓“南宅”就是“刘南宅”。至于文中所说的故事更是为当地人所耳熟能详,并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版本。
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南曾说:“传说的核心,必有纪念物。无论楼台庙宇,寺社庵观,也无论是陵丘墓冢,宅门户院,总有个灵异的圣址、信仰的靶的,也可谓之传说之花坛、发源的故地,成为一个中心。”*[日]柳田国男:《传说论》,连湘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26页。无疑,像刘南宅这种以家族宅第为中心的地方传说在中国各地比较常见,并且往往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在一定意义上,它们是通过地方居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社会形式本身”*[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页。。有鉴于此,我们姑且将其称之为地方性的社会神话。如今,这座迷宫般的建筑早已湮没于历史烟尘,刘南宅传说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一个未解之谜。这个看似荒诞无稽的传说是如何构建出来的,有着怎样的历史性和现实性,又为何在当地久传不衰?
二、纯阳画图:传说框架及与吕洞宾信仰的关系
刘南宅是沂水城里明清两代缙绅世家南关刘氏家族的住宅。它南起相家槐树,北至鞍子桥,整个阳西街占去三分之二,都是水磨砖和哈巴狗子钢叉兽的瓦屋楼房。*张希周:《我所知道的刘南宅》,《沂水方志》1986年第1期。至于得名的具体原因,有两种说法:一是它地处沂水老城的西南部;二是清同治年间,捻军占领沂城,刘宅楼房大部被焚毁,后经重建,按五支分成南宅(分东院、西院)、中宅(原址)、北宅三处,其规模以南宅为最,故人们统称为刘南宅。*张希周、张之栋:《刘南宅及其大殡》,江波整理,《沂水县文史资料》第5辑,1989年,第142-144页。
刘南宅又叫“八卦宅”,它的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方,都有一对对称的门。*张之栋:《沂水古八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沂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沂水县文史资料》第10辑,1999年,第230页。传说吕洞宾因故触犯天条,遂变成一只小虫钻到刘家祖先用的笔管之中,躲过了天公的雷击。为了酬答刘家,他便按阴阳八卦的方位给刘家设计了这所住宅。它分很多小院,每个小院的布局形式都一样,小院与小院之间都有门可通,不熟悉的人进去之后,就会迷失方向,找不到出去的地方。刘家还在宅北一条东西向的水沟上修了一座鞍形石桥,为了纪念吕祖名曰“望仙桥”,而百姓皆称之为“鞍子桥”。据说每逢祭祀之日,站在桥上便可望见吕祖。*张希周、张之栋:《刘南宅及其大殡》,江波整理,《沂水县文史资料》第5辑,第142-143页。因此,刘南宅传说不仅拥有传奇性的情节,还在现实中存在着八卦宅和望仙桥这两个“纪念物”。
截止目前,刘南宅传说的最早出处是刘一梦的小说。我们还可以找到六个相关的版本,它们都来自沂水所在的鲁南地区。其中一则口述资料明显出自普通百姓,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内容:(一)老母奶奶为了帮百姓建桥,变成一个年方十七八岁的美貌女子坐在河边,打出了个招牌:“我愿嫁给一位能用钱打着我的人。”吕洞宾讥笑说这是让万夫争妻,从而遭到天谴。(二)刘南宅在书房读书,洞宾藏在他的桌子底下。屋外霹雷正急,可天兵怕伤了好人,不便下手,吕洞宾因此脱难。(三)吕洞宾建宅方式是研墨画图、吹气成真,他不仅画了八卦宅,还画了照亮刘宅的琉璃灯。刘公子研墨没有耐心,不然灯会亮到天明。*王玉兰讲述,尹相增搜集整理:《刘南宅》,赵斌主编:《日照民间故事选编》上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9-250页。老母奶奶又称“泰山老母”,即官方所称“碧霞元君”。某位作家所写的《刘南宅传奇》则提到吕洞宾化作一只蚊子藏在刘员外的笔管中,刘员外一刻不停地抄写《道德经》,从而躲过雷劈之祸。吕画了一座府第的图纸,并告诉刘员外不日将大富大贵,到时就可以按图纸盖房子。*厉周吉:《最时尚的猪》,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4-147页。这两个版本的故事框架大致相同,但也存在着细微的区别,例如:吕洞宾的躲藏处是笔管之中,还是书桌底下;吕洞宾是建造了刘南宅,还是只为刘家画了图纸。它们显然是刘南宅传说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异。
在其他的版本中,刘南宅传说有着更多的演绎成分。例如,《韩湘子写自明烛》和《李铁拐画烛》*张桂兰讲述、刘光义搜集整理:《韩湘子写自明烛》,赵斌主编:《日照民间故事选编》上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1页;熊正端搜集整理:《李铁拐画烛》,山东省临沂地区群众艺术馆、中国民研会山东省莒南县分会、山东省莒南县文化馆编:《莒南民间故事集(一)》,1987年,第72-73页。不仅主要情节转移到画烛上来,主角也变成了同在八仙之列的铁拐李和韩湘子。《一烛青松和天书石的传说》来自沂水当地,主要内容是刘南宅的刘老爷请好友吕洞宾调教自己的儿子,方式也是研墨作画,结果没有成功。*郭庆文编著:《雪山传说》,山东省地图出版社,2001年,第147-150页。另外,沂水县酒厂就在刘南宅旧址上。据说吕洞宾本是天宫中酿酒仙班的运水道人,只因偷饮了王母娘娘敬献给玉皇大帝的琼浆玉液,被贬下天庭。当时,吏部天官刘应宾正握笔给皇上写奏折,吕洞宾化作一只小飞虫藏进笔杆之内,从而避过雷劫。为报此恩,吕洞宾抽出干将、莫邪雌雄二剑,向地下一指,刘南宅内立刻现出两眼深井,并把酿制琼浆玉液的天机告知。后来,刘应宾以此酒进贡,深得皇上喜爱,于是刻石立碑,以记仙人教诲之恩。*《醇香四海醉八仙——记山东省沂水县酒厂》,马洪顺、刘长恩、陈少伟主编:《鲁酒飘香》,山东友谊书社,1992年,第342页。通过比较可知,它们都是在刘南宅传说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
中国传统民居传说可以分为规模宏大型、布局奇妙型、构造坚固型、择址灵异型、镇宅驱邪型、匠师奇技型、移民寻根型、祖辈功业型等等。其中,“布局巧妙型”的传说大都提到民居布局错综复杂,如迷宫般绕不出来。例如“八卦村”在全国各地都有,可谓不胜枚举。*谭刚毅:《论传统民居的传说类型》,《中国名城》2016年第3期。显然,刘南宅传说也可以划入这种类型。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住宅风水学著作,《黄帝宅经》一开始就宣称,宅居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人以宅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吉。若不安,即门族衰微。坟墓川冈,并同兹说。上之军国,次及州郡县邑,下之村坊署栅,乃至山居,但人所处,皆其例焉。”*《正统道藏》第4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979页。该书的宅法分二十四路,“考寻休咎,以八卦之位向”,“主于阴阳相得”*(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921页。。总之,阴阳八卦是中国宅地风水学中最为基本的理论,而刘南宅的布局方式正是这种宅居文化的体现。《黄帝宅经》早在明代就被收入《正统道藏》,吕洞宾作为道教中人,采用阴阳八卦的方式设计建造刘南宅,也算合情合理。当然,从刘南宅传说的核心内容来看,“神灵建造型”这一说法更为贴切。
蒲松龄曾说,“佛道中惟观自在,仙道中惟纯阳子,神道中惟伏魔帝,此三圣愿力宏大,欲普渡三千世界,拔尽一切苦恼,以是故祥云宝马,常杂处人间,与人最近。”*(清)蒲松龄:《关帝庙碑记》,盛伟编:《蒲松龄全集》第2册《聊斋文集》,学林出版社,1998年,第12页。诚然,在中国,香火最盛、信徒最多的神仙就要数观音、吕祖、关帝了。无论是在道教中,还是在民间信仰里,吕洞宾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不仅是全真派五阳祖师之一、钟吕内丹派代表人物,还是八仙之一、五恩主之一、五文昌之一。而且,若干行业还将吕洞宾奉为守护神,他是托梦之神、科考之神、文具之神、淘金之神、理发之神,也具有医神、武神与财神的性质。在民间传说之中,吕洞宾更是集“剑仙”、“酒仙”、“诗仙”和“色仙”于一身。显而易见,刘南宅传说的各个版本已经展现了吕洞宾的多种面相。
作为中国最知名的神仙人物之一,吕洞宾的形象是在中国近古时期好几个世纪中,由包括士大夫、道士、剧作家、商人和工匠在内的多个社会群体创造出来的。*[美]康豹:《多面相的神仙:永乐宫的吕洞宾信仰》,吴光正译,齐鲁书社,2010年,第8页。有关吕洞宾的事迹自唐末起开始流传,五代时已颇为风行。北宋时,吕洞宾成为相当知名的神仙,各地传闻层出不穷,而宋徽宗首次正式下诏敕封其为“妙通真人”。到了南宋,信众遍及社会各阶层,并被纳入官方的信仰体系当中。金元时期,随着全真教的崛起,吕洞宾被奉为“北五祖”之一,元廷先后敕封吕为“纯阳演正警化真君”和“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八仙故事的出现和各种杂剧的创作演出也极大地宣扬了吕洞宾信仰。明清两代及民国初年,随着文人和平民百姓当中扶乩风气的盛行,民间教派的不断兴起,以及相关戏曲、小说的创作出版和频繁演出,吕洞宾信仰在中国各地持续传播,长盛不衰。清嘉庆六年(1801),吕洞宾被纳入国家春秋二季的祭典;嘉庆十年(1805),吕又被封赐为“燮元赞运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详情参考萧进铭:《吕洞宾信仰源流析探》,盖建民编:《开拓者的足迹——卿希泰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2010年,第661-685页。总体来说,吕洞宾信仰开始流行于唐末五代,昌盛于宋元,鼎盛于明清,民国后趋于衰弱。
吕洞宾的生日是农历四月十四日,刘家的祭祀活动应该在这天进行。祭祀是信仰的最为重要的表达方式之一,而这种行为足以表明,吕洞宾对于刘家来说是在信仰的层面上存在着。实际上,直到今天,沂水当地仍然流传着许多关于吕洞宾的传说,如《雪山仙人桥的传说》、《四门洞为什么有四个门》、《吕洞宾与白牡丹的传说》、《白牡丹巧戏二仙》,等等。*郭庆文编著:《风景这边独好——山东沂水旅游景点传说》,山东省地图出版社,2002年,第48-52页、第56-73页。它们大多围绕着当地一处著名的景观展开,那就是四门洞。此洞内景点有洞宾堂、洞宾像、仙人炕、莲花座、仙人桥等,多与吕洞宾有关。相传当年吕洞宾云游到此,赶走了为非作歹的豺狼虎豹,在洞中修炼,八仙也常来常往。吕洞宾的相好白牡丹也跟来了,在遥遥相望的牡丹仙姑洞居住,得闲就四门洞,在仙姑洞子与心上人幽会,演绎出了许许多多的故事。*郭庆文编著:《风景这边独好——山东沂水旅游景点传说》,第24-25页。据康熙《沂水县志》卷之一《山川》载,此洞“居地下,有四门,崆峒十余里,四面皆通,容数百人”,“有龙潭、莲花台,即纯阳修真处也”*沂水县地方史志办公室编:《沂水县清志汇编》,山东省地图出版社,2003年,第12页。。可见,此种说法由来久矣,并不完全是今人的附会。
望仙石桥是沂水古八景之一,明代成化年间进士杨光溥曾有诗曰:“仙人一去几千秋,偃月空中水自流。丹就不须青鸟约,身轻直驾白云游。风飘环佩历回首,人倚栏杆尽举头。我到当时还跨鹤,腰缠十万上扬州。”清人祝植龄也有诗曰:“仙人何处度春秋,万丈高峰最上头。一片白云遮窄径,几行古柏隐层楼。笛横牛背真成幻,鹤跨缑山去不留。幸有石桥能接引,虚无指点是瀛洲。”*道光《沂水县志》卷之十《艺文》,第18页、第31-32页。众多周知,吕洞宾最为经典的神仙形象是背剑执拂的道士。因此,我们无法从这些诗句中得出此处的仙人就一定是吕洞宾的结论。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关于沂水望仙桥的记载最早见于元代。据《齐乘》称,沂水西南百里有望仙山,“县中有望仙桥,以为王乔飞舄之地,未详。”*(元)于钦撰,刘敦愿等校释:《齐乘校释》,中华书局,2012年,第32页。到了明代,嘉靖《山东通志》和《青州府志》则有完全不同的说法。望仙山位于沂水西南五十里,“相传五代唐庄宗时,有道者白日飞升,众皆仰望”,并都说明山有望仙桥。*嘉靖《山东通志》卷之六《山川下》,第13页;嘉靖《青州府志》卷六《地理志一·山川》,第22页。清代康熙《沂水县志》卷之一《山川》载,望仙山在县西南七十里,“群峰蔽日,万壑争流,亦一奇观也”,中为望仙寺,“黄龙得道于此,今有浮屠三,黄龙遗像存焉”。此外,该志卷之二《桥梁》还提到,望仙石桥位于县城西南三十五里。*沂水县地方史志办公室编:《沂水县清志汇编》,第12页、第29页。道光《沂水县志》则提到了两座望仙桥,一个在南门外;一个在县西南、距城七十里的望仙山下,并特别说明旧志有误。*道光《沂水县志》卷之二《建置·桥梁》,第39页。这一系列的证据表明,沂水历史上有着极为丰富的神仙传说,吕洞宾传说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再如,沂水县西北有大贤山,“山有织女洞,洞临沂水,高峻险绝,莫敢俯瞰。转眺而北,一瀑飞来,势若游龙。唐羽士张道通寿三百岁,作迎仙观羽化于此。”(道光《沂水县志》卷之二《建置·桥梁》,第39页)根据其弟子所刻铭文说,张道通是金代莫州(今河北省任丘市)人,号称生于唐大顺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卒于金泰和六年正月十一日,寿年三百一十八岁。他曾遇鬼谷真人,梦中传授金丹秘诀明文,又游长白山朗明洞,得董真人传教,后率徒众栖于大贤山织女洞,“炉炼丹砂,施散四方,药无不应”。张道通死后,其弟子称他“超脱凡胎”云云。参见叶涛、韩国祥主编:《中国牛郎织女传说·沂源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44-445页。而后面这座桥才是两首诗所歌咏的望仙石桥,望仙山、望仙桥和望仙寺是联系在一体的,它们所说的神仙虽有不同的说法,但与吕洞宾基本没有关系。
根据当代的县志记载,刘南宅旧址北墙外有两座桥梁,一是望仙桥,明朝洪武年间建,两孔石条桥;一是安子桥,明朝末年建,石拱桥,上刻有八仙图像和牡丹花等。*山东省沂水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沂水县志》,齐鲁书社,1997年,第387页。其中,望仙桥在安子桥向西50米处。*沂水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沂水年鉴(1991-1999)》,齐鲁书社,2000年,第426页八仙图像表明,后者确实就是刘家为纪念吕洞宾而特意修建的“鞍子桥”,而前者应该是道光《沂水县志》所提到的南门外的望仙桥。下文中我们还将会看到另一个证据:前面的望仙桥修建之时,刘家还未迁移到沂水。另外,刘家桥上望仙的传说很可能是在原有的望仙桥传说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
总之,刘南宅传说是明清时期吕洞宾信仰在民间广泛传播的一个例证。不过,作为沂水县的另一望族,刘一梦所属的“燕翼堂”也有一座迷宫似的八卦宅,但它并不与吕洞宾有关。*据说,“燕翼堂”是清朝乾隆皇帝所赐,亲笔题词。它占地2万平方米,呈八卦式,像座城堡,分4个大院、12个小院,有厅房116间,建筑形式别致,古朴典雅。院内道路用统一规格的条石铺成,不熟悉八卦宅构造的陌生人入内,往往迷失方向而不能出去。参见刘曾浩:《继承父辈遗志投身抗日斗争》,中共临沂市委编:《沂蒙烽火颂》,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59页。在刘南宅传说中,最关键的线索是南关刘氏与吕洞宾的关系。那么,它只是纯粹的附会,还是有着其他方面的原因呢?
三、原本追溯:刘应宾其人与《中丞公遇仙记》
清道光年间,刘氏重修族谱。一位进士出身的袁姓人物在作序时感叹道:“沂之世家,推南关刘氏为特盛。其先世居莱之潍县,当明中叶,有处士讳堂者,困于军灶,与子赠太常善夫公携家来沂。父子食贫,寓居治南之南庄。善夫公晚年家稍裕,仲子实始读书,以万历戊子副榜官邱县广文。再传至通议公,其门遂大,擢进士,登显仕,敡历中外,毂绩著当时。嗣后五世甲科,歌鹿鸣,贡成均者,前后踵相接,子孙繁衍,越今三百余年矣。”*袁炼:《重修刘氏族谱序》,刘敬修纂修:《刘氏族谱》卷一,沂水南关炊藜馆,1914年,第1页。文中所提到的处士刘堂、善夫公、仲子和通议公,是南关刘氏家族早期历史中四位重要的先祖。
刘氏原籍四川省内江县玉带溪村,明洪武二年迁至山东潍县马司里,成化、弘治年间,始祖刘堂迁到莒州冢头村,复迁于沂水,长子志仁居沂水南关,次子、三子则定居莒州冢头村。*刘敬修:《续修刘氏族谱序》,刘敬修纂修:《刘氏族谱》卷一,第1页。这就是沂水南关刘氏和莒县冢头刘氏的起源。迁沂之初,刘氏举家仅三口,远涉异乡,茅屋数椽,不避风雨,以贩布为生。刘堂去世后,刘志仁继承父业,“从事不数年,累致千金”,“他日营建居室数区”。他宽仁睦邻,和以处众,一邑有“刘佛”之称。*刘敬修纂修:《刘氏族谱》卷一《传》,第5页、第6页。从家族和宅第两方面来看,这对于后来的“刘南宅”都是一个关键的起点。但在当地人眼中,刘氏只是一个新来的外户寒门而已。南关刘氏之所以能够成为沂水县闻名遐迩的名门望族,与前面提到的“通议公”有着极大的关系。
刘应宾(1588-1660)是明万历壬子举人、癸丑进士,历任赞皇、南宫两县知县,礼部仪制司主事,吏部验封司郎中,文选司郎中,南京礼部郎中,吏部考功司郎中,太常寺少卿,太常寺正卿,通政使司通政使,清朝任安徽巡抚,以原品致仕,诰授通议大夫。*刘敬修纂修:《刘氏族谱》卷六,第1页。在康熙《沂水县志》卷之四《乡贤》的记载中,刘应宾是一个颇负声望的名宦。*沂水县地方史志办公室编:《沂水县清志汇编》,第67页。乾隆年间,经过清王朝的详加考核,刘应宾因为出仕两朝的经历被列入《贰臣传》乙编中。*清国史馆编:《贰臣传》卷八,第33-34页,参见周骏富编:《清代传记丛刊·名人类》(16),台北明文书局,1986年,第525-527页。这令刘氏后人颇为尴尬,但他们仍将其尊称为“中丞公”。*中丞本是汉朝官制,称御史丞或中丞。清代各省巡抚例挂衔右都御史,故而又称为大中丞。
刘家与吕祖的特殊因缘正是由刘应宾而起。族谱中的长篇传记叙述了他的不凡生平,紧接着又收录了一篇《中丞公遇仙记》。刘应宾在这篇文章中讲述了发生在1610年的一段奇遇:
明万历庚戌春三月,余岁试之后,兀坐一室,风日晴和,散步春光,因访姊夫张于书舍中。迨午送出门,适值一道人,青巾蓝袍,手摇蝇拂,与六七小儿群戏于通衢大槐之下,自言善相,又不要钱,只喫几壶酒而已。有一吕翁,时共闲立,余出,翁即指之曰:“看这秀才!”道人回顾连呼曰:“折桂客!折桂客!”翁嘿然旋去。余私念道人非皮相者,顾安所得酒乎?姊夫曰:“是不难,吾家客户有沽酒者,数壶可立贳也。”遂延入键门,而共坐石上,酒累累如双陆状,寒酒无殽,一吸而尽,十数壶只作十数口,了无酒气。余曰:“师复能饮乎?”道人笑曰:“将就将就,亦知寒士无钱,且不敢专也。”因示余曰:“目下月气未佳。”有小口语:“壬子罢了,癸丑年也罢了。”即不语。余再叩,答曰:“中年有敌国之富。”又不语。余复叩,道人曰:“好相公,中年有敌国之富,还问功名到何处乎?俟时还有一会,好与我做一道袍也。”余见师意坚,不敢复叩矣。因问师何姓氏。道人曰:“吾姓吕,号青山。”遂飘然去。余怳然若有所失。抵家,考案发,鞅鞅不得意,亡儿忽有颠脐之惊。时余年二十三,戊子生,去先生遇钟离之日多二年矣。电光易逝,前事都不复记忆。越再岁之壬子秋闱,倖捷,癸丑又捷,乃始悟“罢了”二字,仙机珍秘,不肯向人间轻泄也。独是中年之语,私心窃谓:此后三二十年间,红尘粗了,可候先生一顾,愿弃人间,从先生谒正阳,再向华峰羽谷游。而白云不来,神剑久遁。*刘敬修纂修:《刘氏族谱》卷一《传》,第19-20页。
也就是说,在刘应宾23岁的时候,一位自称吕青山的道人准确地预言了他的未来,而刘应宾认为此人就是吕洞宾。当然,除了姓名之外,吕青山在很多方面确实符合吕洞宾的形象。例如,善于饮酒会让人联想到吕洞宾的酒仙身份,而算命人是吕洞宾最为常见的形象之一。*根据学者研究,北宋文献中吕洞宾的各种形象及现身事迹主要有如下数种类型:(一)内丹专家;(二)书法家兼诗人;(三)炼丹术及医学;(四)吕洞宾墨水的疗效;(五)占卜者、招魂驱妖的赞助者;(六)算命先生;(七)商人及工匠;(八)佛教徒。参见[法]弗雷泽·巴列德安·侯赛因:《北宋文献中的吕洞宾》,李丽娟、吴光正译,赵琳校,吴光正主编:《八仙文化与八仙文学的现代阐释:二十世纪国际八仙研究论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37-544页。早在北宋,就有人称,“吕洞宾者,多游人间,颇有见之者。”例如吕曾说丁谓“状貌颇似李德裕,它日富贵,皆如之”,还曾留书与张洎,“颇言将佐鼎席之意”*(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60-561页。。丁谓和张洎是北宋时两位著名官员,这两个预言都得到了应验。同样,吕青山的惊人预见力是刘应宾将其看作吕洞宾的最重要原因。
事情并不只如此。1637年,刘应宾得病,又得到吕祖赐药一丸而愈。1643年,某位赵姓同窗告诉刘应宾,他曾在县庙遇到吕青山。吕朔望行香,并时呼诸生说:“相公,我善相,不要钱,可相相。”结果,“诸生以为狂,群起而噪之。先生向地挝土劈面捽去,诸生开眼见满地胡饼,而先生逝矣。”对此,刘应宾自言:“此与余皆一时事,不知何以迟回至月余矣。青山乃岩字,隐其名也。”*刘敬修纂修:《刘氏族谱》卷一《传》,第20页。众所周知,吕岩是吕洞宾的本名。显然,这些事件所展现的种种“超人间力量”更加强化了刘应宾原有的信念。
作为一种比较常见的仙话模式,“凡人遇仙”在南宋洪迈的《夷坚志》就已存在,小儿、娼女、商贩、店主、官吏等诸色人等均在平常场合和吕洞宾不期而遇,得到了他仙术的救助,或解脱痼疾的折磨,或扭转了贫苦的命运。另外,八仙故事多以“偶遇仙人”展开情节,叙说者是以第三人称出现的目击者,他们完全以凡夫俗子的眼光和感受来叙述自己的见闻,面临仙人在平凡生活境遇中突然显露出来的神奇本领,经历了一个由疑惑不解、惊喜意外直到恍然大悟的心理过程。八仙作为地面的散仙,平时均以普通人甚至极贫穷、丑陋的姿态出现,直至路见不平或受人欺凌,才突然施逞仙术,使情势陡转。*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史》,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571页、第579页。无疑,刘应宾的《遇仙记》具有上述的许多特征,但其叙事的独特之处在于采取了第一人称的自述,这大大增加了可信度。
在这篇文章中,刘应宾还感慨道:“今年逾耳顺,羁旅穷愁,浮沉仕路四十年,沧桑兴感,中年已属幻惑,而仙家复多隐词,余亦不复他望也。”*刘敬修纂修:《刘氏族谱》卷一《传》,第20页。据此推断,刘应宾写作此文时已六十多岁,也就是1648年左右,至于地点则是他侨居十年的扬州。从写作背景和文中细节来看,刘应宾的《遇仙记》绝非出于某种目的而进行的凭空杜撰。一方面,刘应宾由一个寒门子弟成为朝廷高官,因为这段神仙启示般的经历,吕洞宾信仰已经深深植根于他的思想世界中。另一方面,刘应宾遭逢明清鼎革之际,个人的命运不可避免地被裹挟进那段剧烈动荡的历史里。可以想见,在这段充满艰险的生活中,吕洞宾信仰在他心中是一种多么坚实的精神支撑。尽管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也许只是一个有点荒诞的“误会”。
实际上,《遇仙记》是刘应宾《平山堂诗集》的最后一篇。他还专门写有《四门洞》一诗,并附有小注:“沂水西南,去东莞古城十里余,相传为吕祖修炼处。”诗曰:“仙境窅何处,平楚一望齐。石云洞口阻,仙路深难跻。及到奥窔处,鬼神亦为迷。炬光照幽隐,山水见端倪。日月南门敞,乳芝仰面低。吾师栖真坐,玄穹幕紫泥。爰静爰清境,守一报玄闺。遵养归天阙,神剑复相携。”*刘应宾:《平山堂诗集》卷之一《五言》,清顺治刻本,第20页。其中,“吾师”一词明显地表达了刘应宾与吕洞宾之间的特殊关系,而这种师生情缘起源于他的那段奇遇。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刘应宾的七言长诗《吕祖咏》从出身到形象对吕洞宾做了全方面的歌颂。诗曰:
先生来自玉虚中,百日翩跹向吕翁。吕氏一门三世贵,流长庆远降我公。先生自少即超俗,恬淡虚无玄牝宫。从向黄梁梦里回,始知身世俱是空。愿依云房游岭洞,大道不离铅与汞。息气死心传要诀,坎离互取开妙空。先生发念炤神明,黄白小术不为动。普济须要满天下,三千之悮堪一唪。先生自是释迦肠,龙虎追随降法祥。一剑腾虚清六宇,朝游苍梧暮潇湘。粟中世界看睥睨,铛里乾坤任徜徉。黄袄皂绦云水侣,飘飘修髯善行藏。仙风嘘世百八化,西蜀相公一一写。自唐迄今几千年,变化无端谁知者。只此踏云携履游,大珰出入宗伯牧。天家之物称难遘,亦似神仙不可求。我昔会君正花柳,不见黄粱但见酒。君梦觉,我梦丑,浮生扰扰无住着,如意真宝在师手。*刘应宾:《平山堂诗集》卷之二《七言古诗》,第69页。
其中,“粟中世界看睥睨,铛里乾坤任徜徉”明显出自吕洞宾的名句“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铛内煮山川”*(清)刘体恕辑:《吕祖全书》卷四《文集中》,清同治7年(1868)刻本,第22页。。而“我昔会君正花柳,不见黄粱但见酒”一句应该就是前面的那段奇遇。如果说《遇仙记》交到了刘应宾之吕洞宾信仰的起源,那么,《吕祖咏》这首赞美诗是他的这一信仰的最好表达。
在刘氏族谱中,本来就记载了许多关于家族振兴的预言,并且多与刘应宾有关。例如,刘志仁到五十岁才得到两个儿子,说是元旦进香后城隍神恩赐的。次子刘励“攻举子业,有声黌序”,刘志仁勉励说:“汝祖固神明之荫也,今以逆旅沂上,沂之人藐我为外户,汝其大吾门,毋忽吾言也。”他还置一大鼓说:“将为汝庆鹿鸣也。”后来,刘励考中万历戊子科副榜,长子当年十月降生。刘志仁高兴地说:“不于其子,于其孙矣。”*刘侃:《二世赠太常公传》,刘敬修纂修:《刘氏族谱》卷一《传》,第6页。这个孙子就是刘应宾。再如刘应宾母亲妊娠之初,有异尼叩门说:“夫人有身,男也,后将大贵。”并留隐语云云。他出生那天下午,“邻人微闻若有音乐传空者”*刘侃:《四世祖父中丞公传》,刘敬修纂修:《刘氏族谱》卷一《传》,第14页。。还有一则传说也比较离奇:“相传广文公未达时,其夫人晨起汲水,见井中皆莲花,光艳夺目,心骇异,遂遽归告其家人。长姒至尚见一花,弟妇至则通井皆黑,一无所睹矣。故其后长支惟一举人,而广文公裔多贵显殷富。”*袁炼:《重修刘氏族谱序》,刘敬修纂修:《刘氏族谱》卷一,第2-3页。这里的“广文公”指刘励,南关刘氏的兴盛主要在他这一支。
当然,这些传说都不如刘应宾的《遇仙记》来得重要。毕竟,刘应宾是刘氏家族由寒门转向望族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人物,他本人亲自留下了这段具有相当可信性的文字。在某种意义上,《遇仙记》是刘南宅传说的一个原本,它交代了刘应宾以及刘氏家族与吕洞宾之间特殊的因缘关系。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历次重修的家谱里,《中丞公遇仙记》都被收入其中。*《刘氏族谱》共有四次纂修,始于康熙年间刘侃,继修于道光年间刘,续修于民国三年刘敬修,2008年第四次续修。鉴于刘应宾对南关刘氏家族发达的重要性,这个灵验故事本身成为了这个家族内部世代相传的“仙机珍秘”,而刘家祭祀吕洞宾当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因此,在刘南宅传说中,作为主角之一的刘家祖先、刘老爷、刘员外,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指刘应宾。不过,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刘应宾的《遇仙记》与刘南宅传说中吕祖报恩的框架之间仍有相当的差距。那么,《遇仙记》是如何转变成后来的故事呢?这个刘氏家族内的“仙机珍秘”又是如何成为沂水当地广为人知的传说呢?
四、变形机制:研磨隐喻、社会神话与文化霸权
在刘南宅传说的各个版本中,存在着一个基本因素,即刘家人为吕洞宾作画而研墨。当然,“研墨”是书香门第的一个象征。作为一位有名的“墨仙”,吕洞宾在很多故事中以制墨售墨人的形象出现。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是士人学子敬奉的五文昌*五文昌,又称“五文昌夫子”“五文昌帝君”,指“文昌帝君”“魁星星君”“朱衣神君”“纯阳帝君”“文衡帝君”。在古代,他们被看作是掌管文运的神祇。之一。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说法可以看作是关于南关刘氏望族之路的一种隐喻。
自明末以来,南关刘氏科第蝉联,代有闻人,共出了5个进士,5个举人。所谓“五世甲科”,由此可见一斑。尤其有清一代,沂水县共出了14个进士,刘家有4人;中过举者有47人,刘家有9人。这个比例之高,整个沂水县只有中过4个进士、6个举人的高氏能与之匹敌。*参见光绪《山东通志》卷九十四、九十六的进士表,以及卷一百、一百二和一百四的举人表。关于沂水进士的人数,有两人统计未在内,一是顺治二年的刘泽芳,他是以顺天宛平籍的身份参加的科举;二是嘉庆元年的王在中,他的举人、进士俱属因为“年届八十以上”而被加恩赏赐的。而且,这一切是南关刘氏从四世到十一世之间完成的。
明清以来,莒州冢头刘氏和沂水南关刘氏都成为了当地的望族,一个“人文蔚起”,一个“名宦叠出”*《潍县世谱考》,刘敬修纂修:《刘氏族谱》卷一,第1页。。刘南宅曾经三代皆有崇祠乡贤者,分别是刘应宾、刘玮和刘侃。*刘敬修纂修:《刘氏族谱》卷六,第1页、第5页。其中,刘侃字晋陶,号存菴,清康熙辛酉举人、庚辰进士。历任内阁办事中书舍人,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乙酉科山西副主考,刑部山西清吏司员外郎,礼部主客司郎中,福建泉州府知府,都转福建盐运使司运使,诰授中议大夫。*刘敬修纂修:《刘氏族谱》卷六,第5页。他在泉州知府任内,政绩卓著,“士民怀之,立祠小山丛竹之东祀焉。数年后,奉公过泉,阖郡列户,设香案欢迎,争睹其面,咸称有召南素丝之操云。”*(清)周学曾等纂修,晋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晋江县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007-1008页。刘氏一族虽然没有出过举国皆知的朝廷重臣,但这些事迹已经足以令刘氏族人长久地自豪。
除此以外,刘家还作为士绅在地方上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在此仅以刘南宅十一世刘灼为例做些介绍。刘灼字见亭,清嘉庆丙子举人,历任浙江长兴县、嘉兴、秀水等县知县,升补乍浦海防厅同知,诰授奉政大夫,诰赠资政大夫,公举乡贤。*刘敬修纂修:《刘氏族谱》卷六,第40页。回乡家居后,刘灼主要做了如下事情:一是与县官议建明志书院,并修试棚,首先捐资,邀同邑各士绅招集工匠,准备材料,年余而成。二是沂水蚕桑素鲜研究,刘灼著有《浙省蚕桑法》一册,详加考订,刊布于乡,“由是桑蚕之利以兴”。三是时值太平军、捻军各省窜扰,土匪蜂起,刘灼先为倡办团练,昼则练阵,夜则巡查,一乡赖以安全,各乡团仿办而成。“厥后凡官吾邑者,遇有疑难,咸以造访,而公遂因避尘嚣,移居葛庄之来泉别墅,不入城市。”*刘敬修:《十一世祖资政公家传》,刘敬修纂修:《刘氏族谱》卷二《传》,第26-27页。可见,刘灼一派士绅领袖的风范,所办诸事件件关系地方公益,由此不难理解为何他会被“公举乡贤”了。
在此基础上,南关刘氏逐渐成为沂水当地最有权势的缙绅世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历任县官在“为官不得罪巨室”的座右铭的指导下,每次上任、交任都要到刘宅拜客。有的未接任前还住在刘宅客厅里作行辕。如不听其支配,就干不长久。此外,清代刘家有权向县官保荐秀才,然后送沂州府复试,而沂水地方志的编纂大权一直在刘宅手中。*张希周:《我所知道的刘南宅》,《沂水方志》1986年第1期。在某种程度上,刘南宅已经成为地方领袖之家,是在沂水县除官方县衙外的另一个权力中心。
正如后人所言,“累代望族,繁衍炽昌,其间之硕德懿行,显官巍科,具载邑志。”*刘岩:《莒沂刘氏合谱序》,刘敬修纂修:《刘氏族谱》卷一,第2页。道光版《沂水县志》是刘家影响力的一个具体证据。该志卷六和卷七的《仕进》部分留下了刘家在科举等方面的辉煌记录,卷七《人物》不仅在《仕绩》部分记载了刘应宾、刘侃的事迹,还在《耆德》部分收录了刘励、刘玮、刘玠、刘鲁洙、刘绍武、刘鼎臣、刘鼎燮、刘鸣谦等人的传记,几乎成了刘家的家谱。而且,该志参阅绅士里的丙子举人刘灼,编订绅士里的辛酉拔贡、候选教谕刘承谦和邑庠生刘烺,都是这一家族中的人。*道光《沂水县志》,“修志姓氏”,第1-2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刘家掌握沂水地方志编纂大权的说法。
当然,这一切的荣光在更大程度上来自于帝国的恩赐,而不是吕洞宾的庇佑。鲁南当地有数量众多的民谚俗语,其中透露出名门望族的存在,如“沂水四大家,高、刘、袁、黄”;“蒙阴县,公一半”;莒县则是“大店庄,北杏王,功名出在小窑上”。南关刘氏的家族历史体现了这些望族的产生机制:他们大多是明清时期迁入本地,经过世代积累,最终通过以帝国科举为主的上升渠道变成了缙绅世家。刘南宅常挂有两块匾额,一是“世进士”,一是“大夫第”。*张希周、张之栋:《刘南宅及其大殡》,江波整理,沂水县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沂水县文史资料》第5辑,第143-144页。显然,后者指出了这一家族在当地的显赫身份,而前者点明了这一望族的出身途径。
我们会注意到,刘南宅传说的核心内容经过了一个明显的置换,本是刘应宾的“遇仙记”,后来却变成了吕洞宾的报恩。它还有着一个“社会化”的重大转变,即由家族内部的传说扩散为沂水当地的传说。到了后来,前者只有熟悉内情的刘氏族人才会知晓,后者则在沂水当地到了几乎人人皆知的程度。这两个转变与南关刘氏逐渐成为当地最有权势的缙绅世家密切有关。在这一过程中,刘南宅传说实际上已经转换成了关于南关刘氏家族的一个地方性的社会神话,它是通过吕洞宾报恩的故事将南关刘氏的昌盛披上了一层神化的外衣。
刘南宅传说不应该被简单地视为刘家蓄意的捏造,认为它是“封建社会”愚弄民众的工具。在它的离奇情节背后隐含着地方居民在现实面前的复杂心态,既有无奈的默认,又有欣羡之意。据说,有泥瓦匠去宅内抹墙,沾在腿上的泥几日不舍得洗,且逢人就炫耀泥是刘家的。另外,刘南宅传说还存有一种不易为人察觉的结构,即“骚仙”吕洞宾与众人爱戴的老母奶奶之间有着某种程度的对立,而这背后隐隐然所体现着的是地方缙绅家族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对立。*在《一烛青松和天书石的传说》中,某年四月八日,雪山老母约吕洞宾会友论道。两位神仙看似处于和谐的状态,但这不能完全掩盖他们之间的这种对立。参见郭庆文编著:《雪山传说》,第147页。如前所述,吕洞宾形象的形成与士大夫群体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这与老母奶奶有着明显的不同。
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曾提出的“文化霸权”的概念,后来被广泛应用于文化研究之中。他认为,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领导权”。*[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8页。所谓“文化霸权”主要指后者而言。按照有些学者的解释,与“意识形态”不同,这一概念“试图描绘一种广义的支配”,“它不但表达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它被那些实际臣属于统治阶级的人接受,视为‘一般的事实’(normal reality)或者‘常识’(commonsense)”*[英]雷蒙德·威廉姆斯:《关键词》,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02页。。它“将历史上属于某个阶级的意识形态予以自然化,使之成为一种常识”,“其要害在于权力不是作为强权而是作为‘权威’而得到行施”*[美]约翰·菲斯克等编:《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李彬译注,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123页。。我们可以将这一概念借用于地方社会文化的研究之中,用来描述这种现象:在地方社会中,与某一时期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集团(如望族)相关的一些观念广泛传播,并且得到地方居民相当程度的认同。其中,地方性的社会神话是文化霸权一种较为常见的表现形态。而刘南宅传说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它将刘氏家族在沂水县的“领导权”予以了一定程度的合理化。
刘南宅传说有着明显的地域性,其传说圈大致以沂水县城为中心,并与南关刘氏家族的影响力范围基本重合。而且,只有在沂水县这个特定的地方社会场域之内,它才具有社会神话的意义。对于地方居民来说,那个迷宫一般、夜晚灯火通明的刘南宅是这一神话最为显著的标志之一。地方传说作为口头艺术,常常体现出一种基于生活真实之上的艺术真实。刘南宅传说正是明清以来沂水当地社会现实的反映,它的形成反而进一步强化社会现实本身。这个社会神话与社会现实之间构成了巨大的张力,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共振关系,这是它“迷惑了十几代人”*张希周:《我所知道的刘南宅》,《沂水方志》1986年第1期。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条件下,“刘南宅”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住宅的名号,它逐渐演变成为南关刘氏家族的代称。
五、神话终结:刘敬修与南关刘氏在近代的败落
在刘南宅传说中,《一烛青松和天书石的传说》这个版本没有说明刘南宅的来源,而是着重解释了它败落的原因。它的主要情节是这样的:吕洞宾调教刘家大公子,让他用一个万斤石灯碗磨墨,以备画画。刘家公子没有耐心,磨了半灯碗多一点。吕洞宾只画了一根竖棍和几卷书本,随后变成了熊熊燃烧的蜡烛和四本书,书脊上还显出四行小字:磨墨不足欠恒心,夜半磕睡图舒身。欲读玉经少一本,金榜题名莫问人。后来,刘大公子果然读书一般,没中什么功名。刘南宅破败之时,那画竟在半夜三更自动飘到雪山,没入山野,变成了现在人们说的“一烛青松”和“天书石”。*郭庆文编著:《雪山传说》,第147-150页。在民间故事中,这种叙事模式是一种很常见的套路。不过,进入近代之后,刘南宅确实有衰落的趋势,其真正原因却有所不同。
虽然刘南宅公子读书是否用心,我们无从考察,但是自刘灼在嘉庆年间中举之后,刘家在科举方面的成绩确实大不如前了,直到科举废除,此后近九十年间再也没出过举人,更不要说进士了。不过,刘家在帝国的官场上仍然取得了不少的成功,尤其刘灼所属的这一支(前面提到,刘宅曾被捻军焚毁,重建后规模以南宅为最,其实就是刘灼一系)。这是因为随着晚清帝国危机不断加深,捐纳风气盛行,刘家逐渐把重心由科举转向捐纳。这一切恰恰是从刘灼开始的:清道光十五年,他以大挑一等知县分发浙江,到省后就为其二弟刘炜纳资成司务厅司务,签分兵部;四弟刘辉纳资成广文,授章丘县教谕。*刘敬修:《十一世祖资政公家传》,刘敬修纂修:《刘氏族谱》卷二《传》,第25页。
这个传统后来在刘家延续下来。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最成功的是刘灼的孙子、刘南宅十三世刘敬修,而他就是刘一梦小说里所提到的那位“老大人”。刘敬修仕途上有两次关键的提升,一次是光绪五年(1879)遵筹饷例报捐郎中,另一次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由山东顺直善后捐局加捐知府。*秦国经主编,唐益年、叶秀云副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6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88页。从一个普通的监生开始,刘敬修在帝国的官场上努力了三十余年的时间,最终升到了分守山西冀宁道的位置。*刘敬修纂修:《刘氏族谱》卷六,第40-41页。然而,没过多久,随着辛亥革命爆发、清帝宣布退位,刘敬修仓皇逃回家乡,从而成为一名遗老,直到去世。
归乡之后,刘敬修住在刘南宅的西院,门上有一匾额,上书“大夫第”三字。*张希周、张之栋:《刘南宅及其大殡》,江波整理,《沂水县文史资料》第5辑,第145-146页。他有一个重要的作为,那就是主持并出资沂水南关刘氏与莒县冢头刘氏合修家谱,从而结束了同宗同祖两支族谱分修的家族史。*四修族谱编辑工作委员会编:《刘氏族谱》卷一,2008年,第279页。当然,刘应宾的传记和《中丞公遇仙记》作为重要的文献,也都悉数收录在里面。此时民国刚刚开始,这次重修族谱的时机可谓极为微妙。面临这个崭新的时代,刘敬修用这种传统的行为回顾了家族的历史,起到了“敬宗收族”的作用,有种继往开来的意味。
进入民国以后,刘家非但没有遽然衰落,反而在当地持续发挥着多方面的影响力。具体来说,主要有四项事务:一是先后创办私立刘氏尚志小学和中学,在民国后十余年间沂水县只有这样一家中学;二是办理保卫团第三团;三是刘敬修的次子刘诚宽长期担任沂水县商会会长;四是支持沂水道院的运转。*关于刘敬修一家与近代沂水地方社会的关系,将有详文予以论述,在此不多赘言。在某种程度上,刘南宅依然是沂水县的一个权力中心。刘敬修虽然一副遗老姿态,不太管事,但俨然是当地士绅众望所归的领袖。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沂水道院与刘南宅有着莫大的关系。道院由从济南道院发展而来,是民国期间规模最大、影响最巨的新兴宗教团体。据内部文献记载,沂水道院是在刘敬修等人的推动下于1922年成立的。*《沂坛训录》第伍册,丁卯年十一月十六日午刻统坛。而且,沂水道院的办公地点与县志局并在一起,这恰恰是刘家为其提供的活动场所。*张希周、张之栋:《刘南宅及其大殡》,江波整理,《沂水县文史资料》第5辑,第145-146页。此外,刘敬修一家还在沂水道院中担任多个要职,如刘敬修是院监,次子刘诚宽是统篆掌籍、宣院掌籍、兼宣院文藏,四子刘诚厚是外宣长。*《沂水道院籍方表》,《道德杂志》1922年第2卷第9期。
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吕洞宾在道院神仙系统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他被奉为吕祖、孚圣。道院设统院、坐院、坛院、经院、慈院、宣院等六院,其中统院在六院系统最为重要,掌管全院事务。六院的每个院,都有神职与人职的两套组织。在这两套组织中,吕祖都是统院掌籍,一般道院只设有统院副掌籍。*初中池口述,范予遂整理:《我所知道的济南道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7-199页。1922年4月30日,在沂水道院成立后的第二天,吕祖降临判诗曰:“山川今又在,旧地忆胜年。云白岭深处,风清月影圆。望君心未已,思我意犹绵。日暮小桥畔,欢然话雨烟。”*《吕祖临沂水道院判诗(壬戌四月初四日)》,《道德杂志》1922年第2卷第4期。这就是迄今为止所能看到该院时间最早的乩文之一。其中,诗里的“旧地”当然就是沂水,至于“小桥”很明显指的是望仙桥。因此,刘南宅传说是理解这则判诗最为关键的密码。而且,在沂水道院的扶乩活动中,吕洞宾是降临最为频繁的神仙之一。
毋庸置疑,吕洞宾与刘家的特殊因缘是刘家参与成立道院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在某种程度上也进一步神化了这一家族。例如,在一次扶乩中,有位南岳末吏自衡山来,自称:“蒙关帝保荐是职,与刘晋陶甚相接洽。今因过坛叩幕,孚圣命笛一言以纪鸿爪。吾惟奉劝诸君,勉力道务,以弭灾劫。吾之此过,为不负矣。岂但领略风景,归与晋陶君话其家园而已耶?”*《沂坛训录》第乙册,乙丑年六月十四日事坛。这里的孚圣就是吕祖,而所谓刘晋陶就是刘南宅六世祖刘侃。由此,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测:除了刘侃外,刘家列位先祖特别是刘应宾应该也在神仙之列。简言之,与学校、保卫团和商会一样,沂水道院体现了刘南宅家族势力在当地的扩张,更是刘南宅这个社会神话在民国时期的一种延续。
1924年,刘敬修去世,享年六十七岁。*四修族谱编辑工作委员会编:《刘氏族谱》卷一,第280页。此后,他的灵枢一直停在家中,名义上是为了堪舆,实际上当时南宅财力已甚拮据。过了较长一段时间,刘家才决定破产办一个很体面的少牢礼大殡。此次大殡仪式浩繁,哀荣备至,花费巨大,可谓一时盛事。*张希周、张之栋:《刘南宅及其大殡》,江波整理,沂水县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沂水县文史资料》第5辑,第147-154页。与此同时,刘敬修还被隆重乡谥为“正和先生”,参与署名的各地名流人数接近2400人。一则诔文更是如此称颂了他归乡后的各种功德:“国体变更,风潮蓦起。团务学务,尽心桑梓。国民高小,中校连理。悬匾树碑,德望远迩。白宫题匾,褒章焕然。乡谊朝典,宠荣仔肩。道院成立,道念弥坚。仙果佛果,内外功全。正气和光,道成登仙。”*沂水县刘氏私立尚志第一国民高等小学校学生:《正和先生刘公诔》,《正和先生哀荣录》,1925年,第24页。而沂水道院全体同仁也送上挽联,上联是“道院传五千纪以前综仙佛儒基回诸生功能造成世界大同宏愿斯普”,下联是“我公超九重天而上合经坛坐慈宣各院诚恳共祝灵光常照日监在兹”*《挽联》,《正和先生哀荣录》,1925年,第28页。。可见,刘敬修已经位列仙班,这显然是由沂水道院所造就的一种“神话”。这次葬礼完全是为了支撑缙绅的架子,而刘敬修在沂水当地极高的声望和刘南宅家族自身的保守倾向则体现得淋漓尽致。
不过,随着刘敬修葬礼的结束,这个缙绅世家也开始逐步走向没落。刘诚厚是一位思想开明者,早就看不惯刘宅的一切作为,他首先脱离了家庭,参加了革命。刘诚宽担负起这个大家族的重任,他目睹大家族日渐败落,子女都长成了,但怎么节约也难以维持,最终第三团、道院、刘氏私立中学等都无力支持,相继解散,以五十多岁的年龄出外谋生去了。*张希周:《我所知道的刘南宅》,《沂水方志》1986年第1期。
当1927年刘一梦的那篇小说发表时,刘敬修已经去世。它重点描写了Y县的以南宅二大人为首的“绅派”与以葛庄袁三爷为代表的“民派”因争办牛头税而引起的明争暗斗,南宅二大人仰仗家族势力对前来说和的县长予以了惩戒,却被牵扯进了一场官司之中。*刘一梦:《斗》,《小说月报》1927年第18卷第7期。小说的中心场景是沂水县城里的刘南宅,南宅二大人的原型就是刘诚宽。刘一梦的作品是当时国内风起云涌的革命思潮的一种体现,它用艺术的力量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刘南宅是“土豪劣绅”的一个象征,是革命的对象。不久,随着北伐开始波及沂水,刘南宅这个神仙创造的宅第变成了沂水县的“头号封建堡垒”,在“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声中,它不得不紧闭了大门。*党史征委会:《沂水农民运动》,沂水县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沂水县文史资料》第2辑,1986年,第25-26页。在地方权力结构的重组过程中,刘南宅最终失去了地方领袖之家的地位,这个地方神话所依托的社会实体也消失了。
从整个家族史来看,刘应宾和刘敬修两人不仅官职级别相近,他们还都亲身经历了动荡的时代。刘应宾遭遇的只是王朝的更迭,而刘敬修则遭遇了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巨变”。更为吊诡的是,刘应宾以明朝遗老的身份归附清朝,却最终被归入“贰臣”;而刘敬修又作为清朝遗老进入了民国。如果说刘应宾开创了沂水南关刘氏的望族之路,那么,刘敬修的去世则意味着这个帝国时代产生的地方望族在某种程度上的终结。
从后来的历史来看,清朝同治年间的灾难并不是致命的,捻军虽然烧毁了刘家的宅第,但是没有切断这一家族的上升之路。随着辛亥革命和国体变动,长期滋润于帝国雨露的地方望族失去了以往的上升渠道,虽然他们在地方社会中仍然拥有相当的影响力,但在时代潮流的猛烈冲击下,很多缙绅家族像刘南宅一样秉持保守的政治倾向,没有及时进行转型,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
到了抗战时期,日军侵占沂水城,刘家后人离家避难,其宅院为日军所占,后在战火中毁坏殆尽。这样,有关刘南宅传说的最重要遗迹也不存在了。
六、结 语
作为“民众口传的历史”,刘南宅传说是历史过程与社会情境相互作用的产物。通过详细的考察,我们会发现:这则传说直接起源于刘南宅四世刘应宾的那段遇仙奇遇,它不仅透露出一个缙绅世家在帝国之下的形成隐秘和它在近代的最终败落,还体现了一个地方性社会神话的形成和消失。这种类型的社会神话与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往往是当地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集团所拥有的文化霸权的一种表征。
刘一梦的作品秉持着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并在相当程度上做到了“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德]恩格斯:《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3页。。刘南宅传说在小说中的出现本身有着深刻的历史意蕴:它与刘南宅这个缙绅家族一起,受到了一种严肃的来自于现代性的审视和质疑,并最终在现实中遭到了革命的批判。刘南宅在近代衰落与中国由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这一前所未有的世变有关,根本原因是这类帝国时代形成的传统缙绅家族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失败,而这可以看作是现代性对于这类地方性社会神话的一种“去魅”。在这个层面上,刘南宅传说以及沂水南关刘氏家族的兴衰是极具典型意义的。
[责任编辑刁统菊]
刘宝吉,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甘肃兰州 730020)。
本文系“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15LZUJBWZY12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