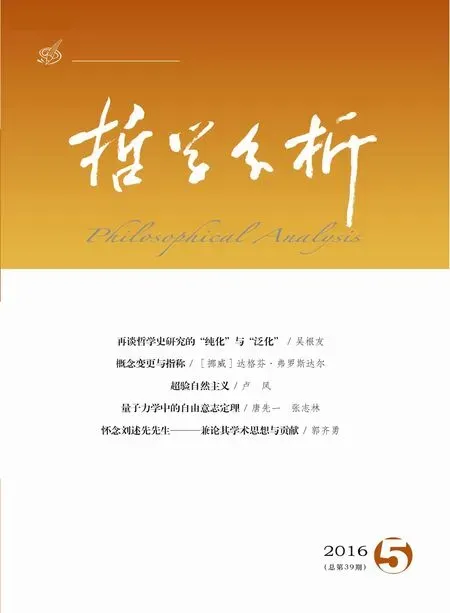通向21世纪明清学术、思想研究的新范式——《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的主要论题及其延伸性讨论
胡栋材
通向21世纪明清学术、思想研究的新范式——《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的主要论题及其延伸性讨论
胡栋材
在通向21世纪明清学术、思想研究新范式的道路上,《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在充分总结和评述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出了有力探索,特别是在某些重要方面突破前人之见并形成比较系统的观点。该书论明,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术有其哲学形上学方面的追求,且这种追求以“气化即道”的新道论为基础。与此相应,乾嘉学术内在地包含了一套哲学方法论即“人文实证主义”。“气化即道”以及“人文实证主义”的说法揭示出乾嘉学术、思想的独特性,并展现出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性价值和通向现代学术的可能性。在“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模式和话语的支配下,该书体现了宏阔的思想视野和知识视野,但其主题不够突出,这限制了讨论的力度以及深度。
明清学术;戴震;乾嘉学术;气化即道;人文实证主义;现代性的宏大叙事
如何充分认识和挖掘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术、思想的现代性价值,是摆在当代明清思想研究者面前的一大任务。以往的研究者并非没有关注此议题,但是受限于学术立场、研究方法以及时代情势等条件,未能作出整体且有深度的探究。①参见梁启超、钱穆、章太炎、刘师培、葛兆光、陈祖武、林庆彰、张寿安等关于乾嘉学术的研究成果,此处不一一罗列。相关梳理可参见吴根友:《二十世纪明清学术、思想的三大范式》,载《哲学门》2004年第2册。由吴根友教授领衔的科研团队历经多年的探索,在新近出版的《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对此议题作出了突破性的回答。该书在吞吐诸家的前提下对“明清早期启蒙说”的推展以及对乾嘉学术、思想现代性价值的阐发,都让人印象深刻;不惟如此,该书探索了明清学术、思想研究的新范式,无疑将成为21世纪以来该领域特别是乾嘉学术思想研究的重要创获。
《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以下简称“吴著”)的立场、方法与问题意识均十分明确,用作者的话说,就是如何继承并超越20世纪诸大家对明清学术研究的成就,从知识视野与思想视野的扩展的内在关系,从古典人文知识的增长与现代知识、学科体系的建立的内在关系诸角度发掘乾嘉学术的现代性意义。①参见吴根友、孙邦金等:《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435—436页。要而言之,为21世纪明清学术、思想研究(包括乾嘉学术)探索新方向以及确立新范式,成为贯彻吴著的基本学术理念。就此,笔者意图从吴著的立场、方法及问题意识等基本面向来进行相关评述,并尝试作进一步思考和讨论。这些讨论主要展现为三个重要论题:其一,乾嘉时代的哲学形上学即“新道论”的基础问题。其二,“人文实证主义”作为乾嘉学术、思想的哲学方法论问题。其三,“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范围内的明清学术、思想研究与中国传统的现代性根芽问题。笔者对这三个论题的思考和讨论,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抛砖引玉,不在于给出确定性的解答。这些探讨妥当与否,恳请作者及学界诸贤的批评和指正。
一、“气化即道”:乾嘉时代哲学形上学的基础问题
吴著的重要观察或重要论点之一,在于它认为乾嘉学者有其自身独特的哲学形上学追求,并且,这种哲学形上学追求可以被称为“新道论”。如其所论,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者在“道问学”的知识追求过程中,并未忘记对哲学的形上之道的追求,毋宁说他们“求道”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在本书中,我们试图以中国传统哲学概念——‘道论’为核心,揭示乾嘉时代的哲学形上学追求,挑战乾嘉时代无哲学的流行说法。”②吴根友、孙邦金等:《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第297页。吴著的这一重要观察或重要论点在该著第二编第一章(即《乾嘉时代的“道论”思想及其哲学的形上学追求》)有集中表现。从这些考察可以确知,戴震、章学诚、钱大昕、凌廷堪、焦循、阮元等乾嘉学者并非没有哲学形上学的论述或追求,相反,他们或隐或显,或系统或零星地阐述了“新道论”的思想。③参见同上书,第295—323页。据此,乾嘉时代无哲学可言的论调不攻自破。
乾嘉时代无哲学论调的主要代表当推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就明确指出,刘宗周是宋明时代最后一位儒者,甚至刘宗周以后的书都可以弃之不顾。④参见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540—541页。牟先生的说法当然是基于他强调儒家心性之学的基本立场,然而,现代新儒家群体本身对此说法也并不是毫无意见(如唐君毅就比较重视儒家气论思想①参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近年来,郑宗义对理学中气论思想的作用也有所反思,具体参见郑宗义:《论儒学中“气性”一路之建立》,载杨儒宾主编:《儒学的气论与工夫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191页。)。不论如何,对清代学术、思想特别是乾嘉考据学的漠视,显示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特点及其视域界限。与此相较,钱穆和余英时对明清学术、思想的相关考察,给吴著提供了更为有益的理论助援或启发。尤其是余英时对清代思想史的新解释即其“内在理路说”视域下的“儒家智识主义”之说,确实为学界重新认识清代学术与宋明理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清代学术、思想的现代性价值创造了新的路径。
有鉴于此,吴著以吞吐诸家的气魄,对20世纪国内外的明清学术、思想研究的成绩作了整体、详尽且不失允当的评论和反思,其中一项重要工作,便是汲取“儒家智识主义”之说的合理内核,即从儒学传统中发掘出最切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思想资源。正是在这个根本点上,“梁—胡”一系、“钱—余”一系与“侯—萧”一系的明清学术、思想研究产生了共振效应。然而,吴著对余英时说法的突破之处在于,余氏并没有直接肯认乾嘉学术、思想中有明确的哲学形上学追求,或者说,乾嘉学者的哲学追求仍然源自宋明理学;吴著则明确肯认乾嘉时代的学者们有自己独特哲学形上学追求,并且以“新道论”的方式来予以概括。
从学理上看,所谓乾嘉时代的“新道论”思想,显然是针对宋明理学“道统说”或天理观而言的。为此,吴著进一步揭示了二者的区隔之处:“他们(引者注:指清儒)所阐发的道论、分理说、以礼代理说等等,均表现出‘即事以穷理’的重经验、重实证思维的方法,而且他们所追求的多是‘器’中之‘道’,‘事’中之‘理’,而不是一具有形上本体特征的道、理或良知。”②吴根友、孙邦金等:《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第124页。乾嘉学者的“新道论”充满重经验、重实证的精神,这与理学家一意追求具有形上本体特征的道、理或良知的做法有本质的区别。
不仅如此,乾嘉时代的“新道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为了反对意识形态化的理学权威才得以成立的。正如吴著所论:“要而言之,……乾嘉时代的‘道论’思想,……即以‘气化生不息’的‘天道’来为人的感性生活——追求合理的情、欲之满足,提供哲学的形上学根据。通过此古老的经典权威来反对宋明以来所形成的遏制人的感性欲求的近世哲学——意识形态化的宋明理学的权威。”③同上书,第323页。乾嘉时代的“新道论”本质上是为了给合理的情欲满足提供哲学的形上学根据,就此而言,它是晚明以来反理学思潮的必然结果。这种“新道论”的基本内容,在于以“气化生不息”来统论天道与人道,其实质在于以“气化”论“道”。
事实上,在考据学的氛围之下,乾嘉学者对这种“新道论”的自觉追求并不明显,即使他们或隐或显地有这种自觉追求,其表现也难说一致。①参见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载《中国哲学思想论集》(清代篇),台北:牧童出版社1974年版,第45—46页。比如,章学诚和戴震对“新道论”的阐述就各有侧重,甚至还存在某些相冲突之处。②如吴著所指出的,戴震的道论思想显示出共时性特征,章学诚的道论思想侧重于历史性特征。参见吴根友、孙邦金等:《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第721页。如此一来,以“新道论”来概括乾嘉学者的哲学形上学追求,尽管有其充足的思想资料依据和内在理路可循,但也不能否认其中存在一定的理论上的不自洽。吴著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或正因如此,吴著的以下论述就显得格外重要:“这一新道论就其哲学的形上学基础来说,是中国传统的气论思想;就其社会哲学旨趣来说,重在批判理学的专断性与绝对性,意在把儒学从狭隘的‘道统’的禁锢中给解放出来,恢复原始儒家的自由气息与时代精神。”③吴根友、孙邦金等:《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第1115页。吴著关于乾嘉时代“新道论”的社会哲学旨趣的阐发,笔者甚为认可。然而,这里需要仔细加以辨析的是“新道论”的哲学形上学的基础问题,换句话说,我们要探讨的是:气论传统何以成为乾嘉时代“新道论”的哲学基础;抑或说,乾嘉时代学者为何会选择气本论作为其哲学形上学的立足点。
关于此问题,吴著没有作必要的论说,只是对这一思想史现象作了比较集中的描述,其中特别提到:“赵翼等人‘气外无理’之批评,应该说一方面是想从理论上避免朱子理气论易于流入玄虚之流弊,另一方面想把知识从‘天理’中给解放出来,挺立知识的独立地位。为此,乾嘉诸儒在本体论上大都接受‘气本论’的立场,只承认‘理在气中’和‘理’是具体事物之‘条理’的观念,这反映了清儒之学在本体论上相对于程朱理学的重大转变。”④同上书,第647页。为了挺立知识的独立地位,乾嘉诸儒在本体论上大多接受“气本论”的立场,这是否说明,气本论思潮的兴起与乾嘉时代重经验、重实证的学风形成有正向相关性?从戴震到赵翼乃至于从黄宗羲、王夫之到戴震,吴著利用思想史的长镜头的观察,大体彰显了从明末清初到乾嘉时代学风的转变与中国传统气论思想复起之间的密切关系,并意识到这种转变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近现代转型也有一定关联。这是否意味着,从中国思想传统的内部演变来说,气本论思潮才是关系明清儒学转型的关键性思想因素?⑤吴著指出,清代前中期崇尚“气化论”的思想家应当与黄宗羲、方以智、王夫之等人的气论思想有内在的关联性。参见吴根友、孙邦金等:《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第785页。关于此点,或参见丁为祥的思考,参见丁为祥:《气学——明清学术转换的真正开启者》,载《孔子研究》2007年第3期。
从吴著的基本态度来看,它将气本论视为乾嘉时代“新道论”的基础,这已经注意到气论、道论与晚明以来的新人文思潮之间的关系⑥对于戴震的新道论与气论思想的关系,该书参与者之一许苏民就曾多有阐发,主要参见许苏民:《戴震与中国文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同参见吴根友、孙邦金等:《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第272页。,不过,此“新道论”的基础问题还需给出进一步的反省和检讨,不能停留于粗线条的现象描述。为了更加深入地讨论气论传统与儒学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需要对以上疑问作进一步阐述。
其一,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者所持的“气本论”立场有其思想前缘,这种气本论思潮近可追溯至王夫之等明清之际诸大家,远则可溯源至王廷相乃至张载、王安石。自张岱年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气学一系的论说以来,理学、心学与气学的三系说就成为大陆学界宋明儒学研究的重要范式。只不过,张先生所说的气学一系基本是就宋明儒学或宋明理学而言的,很少论及它与清代学术与思想的关系。更糟糕的是,唯物—唯心二元对立的评价模式严重损害三系说的理论价值。倒是侯外庐先生等关于中国思想通史及其宋明理学史的研究,对此有某些讨论,然而他们大体上将气本论思潮视为反理学的内容,仍未能正视气论传统之于儒学发展的复杂面相和重要作用。
梗概而言,气论传统在中国思想史上大体呈现出几种较为典型的理论形态,即先秦的六气五行说、精气说和一气说,汉唐的元气说,北宋以后的理气说以及明末至清中期的气化即道说。汉唐之前,气论学说在各家思想中均有展现,但并没有受到儒家的高度重视。随着董仲舒以及王充等的出现,元气说成为儒道两家共同的世界观以及思想资源。①相关讨论参见冯达文:《也谈汉唐宇宙论儒学的评价问题》,载《中国哲学史》2011年第2期。彼时,佛家的代表圭峰宗密在《原人论》中便对儒道两家这种元气论的宇宙论和世界观提出强有力挑战,进而使得宋初儒者在气论问题上作出某些转进,由此出现了张载的太虚即气说和王安石的元气不动说。随着朱熹思想体系的奠定,理气论基本上取代了以往的气论学说,成为宋明理学的主流意识形态。而程朱理学内部的更新以及明中期批判理学思想的崛起,都是从理气关系这一焦点问题开始的。王廷相成为张载之后明确以气本论为思想立场的儒者,他对气化之道的重视使得其学说在明清之际诸大家以及清代学者中产生了回响。王夫之对张载与王廷相的气论思想进行综合性的创说,因而它在某种意义上使宋明儒学中气论思想得以完成。②参见陈来:《王船山的气善论与宋明儒学气论的完成——以“读孟子说”为中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实际上,气论传统在宋元明清儒学中的表现比以上所述要复杂得多,这里只是根据本文主题择要而言。详细考察可参见笔者博士论文《王廷相气论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哲学学院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二章。戴震的气化即道说,又使气本论在儒家学说中斩获了新的思想涵义。这种新涵义,就是乾嘉时代哲学形上学的基础。需留意的是,明末至清中期的气化即道说是指突破理学传统之后而言的,它与汉唐时期的元气论视域下的气化论有实质区别。
暴雨临界曲线法也是一种理论的方法,仅涉及水量平衡方程,主要思路和算法如下:①确定分析地点所在断面的安全流量;②计算最小临界雨量;③确定年最大24 h相应频率设计暴雨;④计算临界雨量;⑤确定暴雨临界曲线参数;⑥整理山洪时段雨量与累计雨量;⑦绘制暴雨临界曲线;⑧在暴雨临界曲线图中点绘实际时段雨量与累计雨量,判断山洪是否发生。这种方法综合考虑了累计降雨量与降雨强度双指标,克服了以往方法仅考虑降雨强度单指标的缺陷,最终成果为一条暴雨临界曲线,能较好地反映由暴雨引发的山洪灾害是降雨强度与累计降雨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由以上简述可知,气论传统的更新与儒学的自我转型往往构成中国思想史并生的环节。具体而言,乾嘉学者对“气化即道”的“新道论”的认同与其对理学传统的理气说及天理观、道统说的批判往往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对于乾嘉时代“新道论”视域中的气论思想,我们要采取辩证的角度予以看待,既要承认其对理学意识形态的批判态度,又要看到其中存在由“求道”向“求真”转变的思想倾向。其实,这种思想动向自明代中期就已经开始,只是经过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等的提升,到戴震这里才彻底形成了新的典范。这或许就是吴著选择以戴震为核心进行考察的原因所在。全面考察气论传统与儒学转型及其发展的复杂关系,将是未来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①关于这个论题,据笔者所知,山井涌、金观涛、刘青峰、杨儒宾、丁为祥等中外学者已经有所注意,他们所讨论的具体内容有差别,但基本上处在同一组论题。可分别参见山井涌:《戴震思想中的气》,载福永光司、山井涌编:《气的思想——中国自然观与人的观念的发展》,李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2—466页;金观涛、刘青峰:《气论与儒学的近代转型——中国与日本前现代思想的比较研究》,载《政大中文学报》2009年第11期;杨儒宾:《两种气学两种儒学——中国古代气化身体观研究》,载《中州学刊》2011年第5期;丁为祥:《气学——明清学术转换的真正开启者》,载《孔子研究》2007年第3期。,笔者尚无法对此作出系统的深度阐发,只能将这个观察提出来,以引起学界的注意。
其二,“求真”(知识论)的追求与“气本论”立场是否有内在关系,抑或,解放知识或知识论与坚持气本论有何内在关联。我们发现,儒学史上那些持“气本论”立场的思想家,普遍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求真”以及“求知”、“求实”的思想态度。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坚持“气本论”的思想家,就不会表现出对知识的追求。问题显然并非那么简单。
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都是“知”,问题在于何者优先或者二者能不能分割开。为了使这个问题更容易理解,我们可以将余英时先生“儒家智识主义”的说法作为一个典型。“儒家智识主义”是余先生解说乾嘉考据学之所以兴起的内在理路时使用的核心术语,在他看来,乾嘉学术与思想的中心议题是将知识的追求建立在儒家经典的考证之上,而这种做法在宋明理学内部一直或隐或显地潜存着。实质上,“儒家智识主义”大体指的是儒家的“道问学”,并没有提供多少新的内涵。更重要的是,余先生用“儒家智识主义”将那些“思想史上的重要事实”编织起来并予以意义化、条理化,但他忽略了更根本的一点,那就是思想家本身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问题。比如,他将王廷相和刘宗周对闻见之知的重视视为16、17世纪儒家知识论发展的新方向,并认为“这一发展是为儒家的经典研究或文献考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清代考证学在思想史上的根源正可以从这里看出来”②参见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载《中国哲学思想论集》(清代篇),第26—27页。,这就将思想家的哲学立场与其知识论态度割裂开来,最终会削弱理论的说服力。至少在现代新儒家看来,纵然王廷相和刘宗周都高度重视知识问题,但他们毕竟不处于同一个思想阵营。
只要考察王廷相与刘宗周对气论的思想态度,就不难发现,他们对气本论的赞同与其知识论追求存在一致之处。也就是说,气本论与知识论追求很可能有内在关联性。③王昌伟的考察在余英时的基础上注意到王廷相的气本论思想与其知识论追求之间的某种关联,参见Chang Woei Ong(王昌伟),“The Principles are Many:Wang Tingxiang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Mid-Ming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66,No.2,2006,pp.461—493。如果我们将这种可能性置于整个中国儒学史特别是宋元明清思想史中加以检验,就不难表明,这种内在关联性并非偶然。更准确地说,气本论思想肯认客观实在的优先性、强调现实实践对认知的重要性(“重经验、重实证”),因而持气本论立场的思想家表现出唯物论思想倾向,与实践唯物论相暗合,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会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当与此有深刻思想关系。①这一看法受金观涛、刘青峰观点的启发,但需进一步论证。参见金观涛、刘青峰:《气论与儒学的近代转型——中国与日本前现代思想的比较研究》。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那就是气本论是否意味着超越性的减煞或消解的问题。现代新儒家之所以大多轻视气本论思想,是因为他们认定在气本论思想那里,天道性命之学的超越性维度十分稀薄,而理学的根本就在于其浓厚的超越性追求。实际上,无论是程朱还是陆王,他们都没有无视气论的存在,只不过他们将气论作为天道性命之学的基础而已。这一点与乾嘉学者基本一致。问题是,他们对气论思想的认识很大程度上还停留于汉唐宇宙论的层次,没有注意到自张载、王安石以来气论传统自身的转进(现代新儒家对气论学说的认识也大体如此),而乾嘉学者的气本论思想态度则经过王夫之、戴震等的批判和重整,已经成为实现新的哲学形上学追求即“新道论”的内在构成要素。同样是以气作为道论的基础,正统的理学家与乾嘉学者之间存在异质之别。
二、“人文实证主义”:乾嘉学术、思想的哲学方法论问题
“人文实证主义”的说法是吴著在乾嘉学术、思想研究领域的一个有意味的创造。如其所言:“我们把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汉学‘力求通过文字、典章制度、语言的工具’来获得经典解释中的客观性的方法,命名为‘人文实证主义’。这一人文实证主义的方法使得乾嘉时期的哲学思考迥然有别于宋明理学的思辨哲学,与明末清初的反理学思潮亦有不同之处。明末清初的反理学思潮可以看作是乾嘉时期哲学思想的一种过渡,而乾嘉时期的人文实证主义哲学可以看作是清代哲学的典型风貌。”②吴根友、孙邦金等:《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第341页;另参见本书第1139—1145页。首先,人文实证主义将乾嘉时代学术、思想的典型特征以一种新概念的方式和盘托出;其次,它既与理学传统的道德心性之说视域下的“六经注我”的方式相区隔,又与晚明以降的反理学思潮中“我注六经”的方式有所不同;最后,人文实证主义主要展现了乾嘉学者独特的哲学方法论,即它是一种“力求通过文字、典章制度、语言的工具”来获得经典解释中的客观性方法。这种哲学方法论的实质,在于乾嘉学者对儒家经典进行研究时所采取的重实证、重经验的方式突破了传统局限,从而保证人文学释义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具有现代语文学及语言学的意涵。
人文实证主义之说是为了揭示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考据学的真义,即人文学的实证性、经典解释中的客观性,并且,这种实证性和客观性是在人文学领域进行的,充满人文的追求和关怀;也就是说,它是在“求真”的具体实践中“求道”。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吴根友2004年发表的《言、心、道——戴震语言哲学的形上学追求及其理论的开放性》一文中①参见吴根友:《言、心、道——戴震语言哲学的形上学追求及其理论的开放性》,载《哲学研究》2004年第11期。与“人文实证主义”相关的还有“知识考古学”、“古典人文知识增长”的说法。参见吴根友:《在“求是”中“求道”——“后戴震时代”与段玉裁的学术定位》,载《求道·求真·求通——中国哲学的历史展开》,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60—181页。,之后有所深化,在吴著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运用和体现。据笔者所知,“人文实证主义”之说与刘笑敢提出的“人文自然”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是力图通过创造新的概念来揭示研究对象以往被遮蔽的思想真义以及现代性价值。②参见刘笑敢:《老子之人文自然论纲》,载《哲学研究》2004年第12期。与“人文自然”的说法相比,“人文实证主义”更强调方法论的意义,而这种方法论新义的获得,不可缺少两大因素:第一,对萧萐父所说的“情感与逻辑相统一”(“双L情结”)的方法论的坚持和创新;第二,在世界哲学与比较哲学的视野下总结和熔铸新的中国哲学方法论。在某种意义上,人文实证主义之说显示了近十几年来珞珈中国哲学学派在明清哲学研究领域内方法论的自觉和创新。③参见杨海文:《“珞珈中国哲学”的学派诉求——读〈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吴根友:《珞珈中国哲学:通向未来中国哲学的一条可能之路》,参见“珞珈中国哲学”系列丛书总序,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实证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自古希腊以来就存在于西方思想史,同样,我们在先秦诸子如墨子以及名辩学派中可以发现重实证的思想传统。现代西方实证主义则与孔德有关,后来经过维也纳学派等的发展,实证主义哲学成为现当代西方哲学中的重要一环。从理论上看,“人文实证主义”的提出就是借用现代西方实证主义的结果,由于乾嘉学者的实证精神基本展现于人文经典(经史)领域并体现为多重人文学的方法和人文精神,因此作者将之概括为“人文实证主义”。可见,人文实证主义的说法之所以能被提出来,与作者广阔的思想视野和丰富的知识视野密切相关。换言之,这一说法只有在世界历史与世界哲学视野之下,并充分吸取现代西方哲学的成绩,才有可能成立。④参见吴根友、孙邦金等:《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第1143—1145页。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人文实证主义的说法将乾嘉学术、思想的研究带到了世界性的舞台。从学术研究的层面来说,人文实证主义的说法的确打开了明清思想研究的思路,开拓了新的可能。
明代中期的王廷相曾提出“道真”一说,意图融合“求真”与“求道”之间的隔阂,然而他最终只是通过“道寓于六经”(“宗经”)的途径来实现其融合知识与价值的理想,最终把儒家真理观限制在了经典的范围。③相关讨论参见蔡方鹿:《王廷相道寓于“六经”的思想》,载《现代哲学》2008年第6期。此处不宜展开讨论,具体内容参见拙文:《王廷相的“道真”观念与儒家道论传统的转向》(未刊稿)。王廷相这种在经典中“求道”的思想行为在乾嘉学者身上得到某种继续。推而言之,局限于儒家经典考证范围内的人文实证主义,如何能避免经学的独断论以及现代西方实证主义的狭隘性,使中国传统哲学走上现代性之路,不能不成为一大问题。④参见吴根友:《求道·求真·求通——中国哲学的历史展开》,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自序”。这也是吴著有欠讨论的问题。
就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人文实证主义”一说容易遭受来自三个方面的批评:其一,从字词上说,“人文”与“实证主义”的结合词是个有悖常理的提法。众所周知,实证主义意味着科学精神,而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往往被视为充满矛盾的两者,那么,人文实证主义如何避免由此而来(特别是来自以科学实证主义者)的误解,不能说不是一个问题。其二,人文实证主义的提法展现了作者超越以往的研究视野和理论创造性,但这一提法的实质内涵与儒家解释学以及余英时所说的“儒家智识主义”多有重合之处(人文实证主义一定程度上就是对它们的借鉴),如何将人文实证主义与前贤的相关理论作适度区别,需要作出进一步的论说。其三,“人文实证主义”极容易被误解为某种理论体系,而不仅仅是方法论。⑤吴根友对“人文实证主义”的乾嘉哲学方法论作了一些必要的说明,这些说明还比较简单。要使人文实证主义的说法成为当今乃至未来明清学术、思想研究的新范式内容之一,需要作进一步阐述。参见吴根友:《人文实证主义:乾嘉时代的哲学方法》,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2月15日第6版和3月1日第7版。与此相比,吴著所使用的“古典人文知识的增长”一说就妥当得多。
此处就人文实证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在儒家经典解释学历史上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作一些引申性的探讨。根据皮锡瑞的说法,“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⑥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页。。这就是说,孔子整理、删定《六经》正式拉开了儒家经典解释的序幕。后来,荀子成为儒家基本经典的重要传续者。迭至秦汉之际,儒家典籍散失严重,而对经典的系统化、制度化甚至是权威化的解释又十分迫切,因此,汉代经学在各种缘由的聚合之下迅速发展起来。①参见汤一介:《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景海峰:《儒家诠释学的三个时代》,载李明辉编:《儒家经典诠释方法》,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15—140页。在很大程度上,汉儒以经为本,对经典的解释呈现为章句之学,这其实有很强的合理性,然而章句之学流于烦琐,缺乏思想活力,其主导地位最终被义理解释路径所取代。宋代疑经思潮的开启,注定四书学的兴起是以经的权威的衰落为背景,也决定了关于“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争论只能奠立在义理之学的氛围之内。②参见陈少明:《六经注我:经学的解释学转折》,载《哲学研究》1993年第8期。更重要的是,随着陆王心学对经典的体悟及个人化、主观化的理解,对经典的真实性、客观性和权威性构成了极大挑战。对此,朱子学者特别是清代信奉朱子学的考据学家作了大量拨正工作。学界一般认为,儒家关于经典的考证到了乾嘉时代达到了顶峰,在经典解释方法上,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者只是对前贤特别是汉儒的延续,并没有贡献新的实质性内容。
人文实证主义的哲学方法论的提出,肯定了乾嘉学者在文字、音韵、训诂以及考据等方面的突出成绩,标识了儒家经典解释系统的基本成立。更重要的是,它彰显出乾嘉学者在经典解释方面超越以往的方面,即在追求经典注解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的过程中把握现实、具体的“道”。这种“新道论”的思想使其在方法上超出了以往经学解释的藩篱。因而,“人文实证主义”不仅是文本解释学的一般方法,还是中国传统学术通向现代的思想道路。
如果说重建经典解释的人文实证主义确乎是乾嘉学术界的共同方法论③参见吴根友、孙邦金等:《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第1111—1113页。,那么可以确认的是,这种看法主要是建立在现代知识论意义基础之上的。与此相关,吴著强调要从“古典人文知识增长”的角度以及“语言学转向”的角度来肯定乾嘉学者在相关方面作出的成就,这一看法同样来自现代知识视野和思想视野的交合作用。这是否意味着,人文实证主义的说法只是揭示了乾嘉学者哲学方法论的典型特征,而不能用于对乾嘉时代解释方法的全面性概括。举例来说,像赵翼这样长于诗史的学者,如果不从气本论层面揭示其与戴震哲学思想的吻合之处,我们很难以人文实证主义来定义他。④参见同上书,第641—658页。像赵翼这样的史学家和诗人,一般都会被清代学术思想研究者所忽视,而正是因为吴先生等具备广阔的视野,因此能揭示其哲学思想的隐微之处。关于吴著的知识视野、思想视野以及比较文化与比较哲学视野,参看该著第一编和第六编的内容就可了解。也就是说,人文实证主义的说法应该明晰其界限,不可被滥用。另外,人文实证主义的说法最值得肯认的地方,在于吴著是以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走向现代化的立意来论说乾嘉学者的哲学形上学追求及其方法论特质的,尽管乾嘉学者自身对此并没有充分理论自觉,但是这并不抹除他们的实际贡献,即乾嘉考据学恰恰是以一种片面的、歪曲的方式实现着中国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方式转化的工作,他们以人文实证主义的方式走上了一条新的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考之路。①参见吴根友、孙邦金等:《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第85页。
三、“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乾嘉学术、思想研究与中国的现代性根芽问题
吴著并没有简单停留于乾嘉学术、思想研究视域的更新层面,它不仅仅是为了给21世纪的明清学术、思想研究提供新的途径,其更为远大的宏旨,在于深化珞珈中国哲学学派关于明清哲学与现代化关系的论述,将侯外庐、萧萐父的“明清早期启蒙说”偏重于社会政治思想的论述方式转换到思想文化方面,从而进一步论定中国传统学术所内具的现代性思想根芽。②相关论述引自卿青:《中国文化的哲学观照——专访〈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的作者吴根友教授》,载《武汉大学报》,2016年4月6日电子版,http://news.whu.edu.cn/info/1002/45601.htm。如果我们没有抓住这一点,那么就会错失该著的研究要旨。吴著论定:“清儒重视情、欲满足的哲学当是对宋明儒学道德主义路向的纠正与转进,并且与西方近代以来提倡个性自由解放的‘现代性’有暗合、汇流之处,具有道德解放和思想启蒙的性质。本书的作者群体坚持从正面肯定晚明以来出现的新思想,并将之与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运动结合起来考察,认定这些新思想具有现代性的因素,在性质上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新文化具有相同的性质。”③吴根友、孙邦金等:《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第642—643页。另参见本书第252页,以及吴根友:《如何看待中国现代哲学问题意识的内在根芽?——从晚明以降儒家“经世哲学”的三种新动向谈起》,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吴著的作者群体之所以会从乾嘉学术、思想的研究中进一步论定中国自身的现代性因素,既与他们对明清早期启蒙说的继承与拓展的基本立场有关,也与他们的知识视野、研究视野及研究方法有关。④当然,本书作者并没有局限于“侯外庐—萧萐父”一系的明清启蒙说,如他们所论,他们是在继承梁启超—胡适,侯外庐—萧萐父、许苏民两系有关明清哲学中的现代性内容论述的基础上,借鉴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理念,深化对明清哲学中蕴含的现代性思想的论述。参见本书第297—298页。其实,在现代化理论方面,作者对日本、美国汉学界关于明清学术、思想研究的成果也有所借鉴。正如吴著所论,要论证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向现代价值观念蜕变的历程,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解释现代化的本质内涵。职是,对现代化的诠释就构成《戴震》研究要旨的关键因素之一。与此密切相关的,便是关于现代性的讨论。正是在“现代化”以及“现代性”问题上⑤现代化与现代性密切相关,但两者又有所区别,吴著对现代化有所讨论,对现代性的论述反而不多。这是吴著的一个薄弱点。相关讨论可参见唐文明:《何谓“现代性”?》,载《哲学研究》2000年第8期;陈嘉明:《“现代性”与“现代化”》,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吴著体现了其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随着世界历史时代的到来,现代化及现代性问题成为人类共同的主题。中国的现代化何以可能?中国的现代性是如何发生的?这些问题变得极为重要,且必然涉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吴著力图表明,乾嘉学术、思想中所内具的某种现代性因素,正是多元现代性的中国式表现。尤其是在价值观念、学术方法、政治制度等方面,乾嘉学者在考据学活动中表现出的现代性因素,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整理和挖掘。这些现代性的思想因素,典型地体现在“求真”、“贵我”等传统价值观向现代价值观的蜕变之上。①参见吴根友、孙邦金等:《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第1080—1097页。吴根友:《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初生历程——从李贽到戴震》,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2—75页。至于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术与思想是否对中国近现代学术与思想均发生了重要影响,这些现代性因素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是否完全相同,吴著的考察还不够具体,还需要作出更充分的阐述。②吴著考察了戴震对宋恕、章太炎、蔡元培、梁启超以及胡适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对我们认识戴震思想影响以及由清中期到近代的中国思想演变有很大助益,不过这些讨论还有待充实和提升。(参见吴根友、孙邦金等:《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第923—951页。)尤其是近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化思潮与明清学术、思想的现代性因素之间的关系,需作一些交代。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1—379页。不论如何,正是基于对中国传统自身的现代性根芽问题的思考或探索,《戴震》将乾嘉学术、思想的研究带到了一个新的境地,即真正参与到“世界性的百家争鸣”。
在此,笔者无意继续探讨中国的现代化及现代性问题,而是要指出,在乾嘉学术、思想研究与中国传统的现代性根芽问题的关系问题上,“现代性的宏大叙事”的理路似乎是被内在地规定了的。我们观察到,无论是梁启超—胡适的“文艺复兴说”,还是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包括部分日本与美国的汉学家的研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从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的现代转型的视角来研读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术与思想,这一点被吴著统归为“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思路”③吴根友、孙邦金等:《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第916、1112页。。
19世纪后半叶以来,现代化成为世界性的历史进程,而对这一世界性的历史进程的讨论,首要与卡尔·马克思(当然还有马克斯·韦伯)有关,马克思以宏大的历史观(世界历史)展开其对现代社会的理解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奠立了“现代性的宏大叙事”的思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侯外庐、萧萐父等在明清学术、思想的研究领域,自觉接受这一论说模式。在此基础上,吴著接续侯外庐、萧萐父的“现代性宏大叙事思路”,并明确认同:从万历到五四,中国传统的现代化转向中包含了现代性问题意识。这实质上是对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的阐发和运用,而马克思关于现代化以及现代社会的理解,主要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一方面,马克思是现代社会的拥护者,他高度赞扬理性、自由、启蒙等现代社会基本价值理念;另一方面,他在肯定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伟大成就的同时,坚决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本质及其带来的现代性问题(如商品拜物教)。④相关讨论参见俞吾金:《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及其启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讨论,就是从宏大历史视角出发,在实践观的基础上批判现代社会问题,这种思想特质在理论方法和形式上构成了所谓的“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即将现代性的社会现象置于宏观历史理解的基础之上。①相关讨论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95页。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讨论传统的现代性转向问题时,创造性地运用了这一论说模式。
究其实质,“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表现为一种历史—社会学的论说模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或解读即主要基于这种模式。侯外庐和萧萐父对“明清早期启蒙说”的阐发,几乎同样如此。正是在这一点上,“明清早期启蒙说”奠定了其基本立场与研究范式。《戴震》将“明清早期启蒙说”的基本立场与研究范式推展到乾嘉学术、思想的考察之中,并使其论域从历史—社会领域转向哲学—文化领域,它指出:“中国现代性思想启蒙运动,自晚明(16世纪中后叶)以降到清代乾嘉时期,以非常曲折的方式向前推进并深化着,只是由于中国历史进程的特殊性,没有西方社会那样汹涌澎湃、势如破竹而已。……当我们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狭隘视角,将现代性启蒙运动看作是人类将自己从中古宗教或伦理的种种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的自我觉醒运动,则中国传统社会所发生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自我批判运动,完全具有近现代文化的启蒙性质。”②吴根友、孙邦金等:《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第1132—1133页。论定自晚明到清代乾嘉时期中国发生了具有现代文化启蒙性质的运动,是吴著一书的意图所在。与“侯—萧”意义上的“明清早期启蒙说”相比,吴著有关“新道论”、“人文实证主义”以及“古典人文知识的增长”等论说更加注重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内部演变来进行挖掘与阐明。由于作者强调从世界哲学以及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视野下进行明清思想研究,这就使其更能阐发出乾嘉学术、思想的现代性意义。如此一来,乾嘉学术与正统理学就被建构为对立的双方,二者之间的连续性进而被遮蔽,其断裂性由此可能被放大。
透过对乾嘉学术、思想与中国文化的多方面考察,吴著认为,从学术与思想的角度看,中国有自己的现代性根芽。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应当尊重并继承自己的现代性思想传统,同时大力吸收一切外来文化的合理因素,以建设含弘光大的现代中华文化。③参见吴著“内容摘要”部分。这种论说是对“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思路的转进,即从政治、社会层面转入到思想、文化层面。至此,“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被赋予新的运用,获得了新的理论生命力。委实如此,在侯外庐以及萧萐父那里,理学的丰饶意蕴被符号化处理,理学意识形态就成为阻碍中国传统走向现代性的根本性存在。④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对理学意识形态的认识和处理显得过于简约化,这是艾尔曼对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模式下明清学术、思想研究的一个观察和反思,笔者基本认同此论。从学理上看,这种论说过于简单化,理学传统与乾嘉学术之间的异质性有被夸大之嫌。吴著一书在学术理念上继承了这种做法。相较之下,胡适所使用的“近世哲学”的思想概念更值得注意,它能表现宋元明清思想的连续性和接续性。①对此,吴著已经有所注意。作者指出:“当代的明清学术、思想研究,恰恰要从胡适的‘近世哲学’的概念里汲取思想的营养,将宋元明清学术、思想当做一个整体的思想单位,考察其中的继承与变革的关系。”具体参见此书第26—28页。进一步参见郭齐勇、吴根友主编:《近世哲学的发展与中国哲学的创造转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然而,胡适“近世哲学”的说法同样属于“现代性的宏大叙事”的理路。
要讨论中国自身的现代性根芽问题,就必定涉及“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这似乎已成为一个理论事实。只要在“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中仍然能够挖掘出传统自身的现代性因素,那么这种论说模式就有存在的必要性。问题在于,“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这一论说模式应当得到足够深入的反思。“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本身容易停留于粗线条的描摹,忽视必要的甚至关键的思想史细节。更关键的是,“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无法穷尽现代性的问题。吴著意识到了这一点,它没有囿于“明清早期启蒙说”的范围,而是将其视野扩展到整个20世纪诸大家的相关研究,在此情形之下,它通过“新道论”以及“人文实证主义”来论证乾嘉学者对于确定性知识的追求。在这种追求当中,人的主体性与知识的客观性以及古典人文知识都得到了突破性的肯认。进而,乾嘉学者对确定性知识的追求,促进了中国传统自身的现代性根芽的生长。
“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是吴著在明清学术、思想领域创造新的研究范式的内在依据。吴著的考察使其确认,乾嘉学者超越了明清之际的反理学思潮,为儒家营建了新的思想世界和人文精神理念。乾嘉学者并没有在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和重整中失去基本的信仰,只不过这种信仰表现得更为隐晦和曲折罢了。倘若乾嘉学者在理性化、客观化的考据活动中逐渐丧失了对儒家之道的信守,那么这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言,在历史的“进步”中失去信仰,是导致“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被终结的主要因素之一。②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吴著力图阐明,这种可能性至少在乾嘉学术、思想中并不存在。事实上是否如此,还要作集中性讨论。
综而言之,吴著主要以戴震为中心来探讨乾嘉学术与思想,其所涉及的领域和揭示的主题相当丰富。仅就戴震思想研究而言,该著对前贤诸说也多有超迈之处;特别是在研究视域、方法与问题意识等方面,为通向21世纪的明清学术、思想研究确立了新范式。围绕“新道论”、“人文实证主义”以及“现代性的宏大叙事”等论题,笔者提出了一些见解,并作出相关思考。这些思考比较初步,有待深化和具体化。最后需要点明的是,吴著以坚定的立论、广阔的视野和精当的方法,有力地推动了本世纪的明清学术、思想研究,并且,它表明该领域尚有某些延伸性的问题需要我们作出深入细致的探讨。
(责任编辑:肖志珂)
B2
A
2095-0047(2016)05-0028-14
胡栋材,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