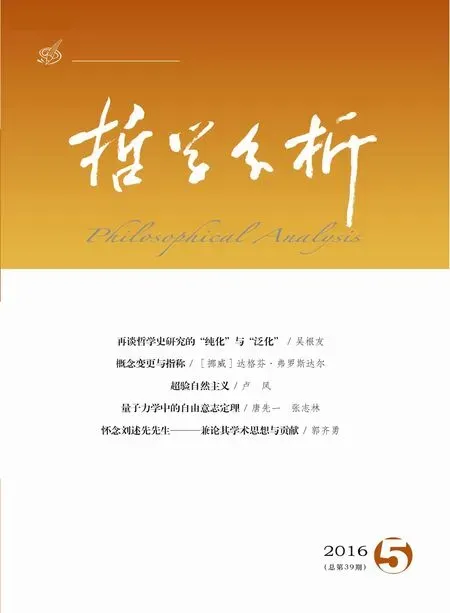戴震与中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简评吴根友等著《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
王国良
戴震与中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简评吴根友等著《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
王国良
明清时期的王夫之与戴震的哲学终结了宋明理学,开辟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新方向。王夫之、戴震哲学的巨大价值在中国近现代的学术发展中没有得到合理的绍述与发扬。吴根友等著《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一书第一次从哲学的角度对戴震和乾嘉学术做总结研究,其价值有四:一是系统总结分析了20世纪以来明清学术与思想研究的大体上的四种范式或曰四种路径;二是肯定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时代的哲学是以“道论”为其形上学;三从古典人文知识增长的新视角重新认识、评价乾嘉时代历史考据学、语言哲学的思想史意义;四是阐明“实事求是”是乾嘉学术方法的“活的精神”。
戴震;乾嘉学术;道论;实事求是
明清之际到清代中叶的学术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出现一系列大思想家与哲学学术流派,取得巨大学术成就。其中王船山与戴震双峰并峙,王船山相当于黑格尔,戴震相当于费尔巴哈。王夫之、戴震与明清时期大多数思想家一样,服膺孔孟,回到先秦儒家的源头,“六经责我开生面”,要端正中华文化发展方向,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宋明理学进行总结批判,“一破千古之惑”,基本解决了宋明理学的哲学命题,终结了宋明理学的发展,开启了中国哲学发展的近代新方向。王夫之比戴震早生一个时代,但王夫之的主要著作生前大多没有出版,基本可以确定王夫之与戴震各自相对独立地完成了对理学的总结。王夫之思想达到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最高峰,戴震对理学命题如理气、理欲、人性、才情等问题的解决更为透彻明晰。中国自鸦片战争进入近代以来,面对西学东渐的汹涌浪潮,本应加速系统总结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学术成果,特别是明清之际以来的学术成就,以与西方学术思潮相摩相荡,浴火重生,由此推进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实现中华学术的现代化。然而可悲的是,那时的学者几乎对明清之际的思想文化懵然无知(当然那时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的著作罕为人知),对此前高度发展的戴震与乾嘉学术也弃若坯土。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连一本《孔子传》都没人写。他们不是推进和发展,而是维持已经礼教化的程朱理学作为“中学”(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另一方面,功利性地忙于吸收当下立刻见效的西方先进成果(魏源、冯桂芬、郭嵩焘等),结果走上一条由器物到科技到制度到文化,即最后才明白文化重要性的节节失败的道路。只是到了清末,才有许多有志之士利用王夫之、黄宗羲、戴震等人的思想著作来宣扬变法与革命。简单利用并不等于系统总结与绍述发扬。对明清之际到清代中叶的中华思想文化的系统研究,严格来说到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出于多种复杂的原因,这些研究并未深入下去,西学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导致对中华学术的卑视。虽然“新儒学”也从此时崛起,并宣称要“接着讲”,但大部分新儒学学者是要接着宋明理学讲,或接着程朱讲,或接着陆王讲,他们对明清之际以来的哲学思想文化评价不高,把它们看作是宋明理学的余绪,甚至看作是中国文化“陷于劫运”的思想混乱的东西。结果,从大陆到港台,新儒学运动开展近百年,竟没有把中国近现代文化与古代文化传统衔接起来。西方社会在从中世纪向近代转换之际,英国、法国、德国等都相继产生一批又一批原创淋漓的哲学家,纵观中国历史,每逢社会变革、王朝更替之际,也相继涌现一批又一批大思想家和学术流派,构成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重叠叠的高峰与高潮。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来,社会运动发展波澜之壮阔、动荡之激烈、变化之奇诡,超迈历朝历代,然而(除了毛泽东之外)几乎没有产生一个像样的哲学家!许多近现代人士把自己没有能力赶超的原因归咎于古代,甚至归咎于古代先贤!对明清之际到清代中叶的哲学文化的重视与系统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开始。吴根友等著《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一书三巨册,近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是该研究领域的重大成果,从一定意义上说,该书是第一次从哲学的角度对戴震和乾嘉学术做总结研究,有重要的学术创新与积极的社会意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突破了已有乾嘉学术研究的范式。
该书总的看法是,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人,从哲学精神上继承了晚明以来的新的人文思想,但主要从学术方面推进了中国学术与思想的转向,因而是明清早期启蒙思想的继续与深化。乾嘉时代的学术与思想的转型既与当时的政治高压密切相关,也是中国传统学术向近现代转化的内在要求的体现。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的变化,既受到西方传入的学术、思想的强烈刺激,也深受乾嘉学术的内在影响,这充分体现在宋恕、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王力等人的身上。而龚自珍是乾嘉学术、思想向近现代转化的关键人物之一。从学术与思想的角度看,中国有自己的现代性根芽。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应当尊重并继承自己的现代性思想传统,同时大力吸收一切外来文化的合理因素,以建设含弘光大的现代中华文化。
从探索和创新的角度说,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系统总结分析了20世纪以来明清学术与思想研究的大体上的四种范式或曰四种路径:(1)梁启超、胡适开创以西方文艺复兴为参照系的范式,提出了明清学术、思想类似欧洲的文艺复兴的说法。(2)侯外庐、萧萐父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明清哲学,提出了明清“早期启蒙说”。(3)熊十力、冯友兰等现代新儒家,基本上将明清哲学看作宋明理学的余绪,简称之为“余绪”说。当然,新儒家内部的具体说法有十分大的差异。(4)钱穆、余英时从学术史的角度出,考察明清学术与宋明理学的内在关系,可以称之为“内在理路说”或“转出说”。非常可贵的是,作者对这几种研究范式所得研究成果的合理价值以及失误、偏见之处的评论非常精当准确,令人信服。比如梁启超,作者对梁启超的戴震与乾嘉学术的研究成果表示充分认肯和赞佩,但还是指出梁启超的研究有诸多不足之处:(1)“仅看到戴震、乾嘉学术对宋明理学‘反动’的一面,而未能更加精细、深入地看到他们之间内在联系的一面,对戴震、乾嘉学术的复杂性认识不足。”(2)梁启超动辄喜欢把明清学术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学术做比较,但“对西方哲学与文化的了解不够系统、深入,在从事比较研究时有点信手拈来的毛病,有些地方结论下的过于匆忙”①吴根友、孙邦金等:《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上卷),第16—18页。。对于钱穆的研究成果与结论,作者对其偏颇之处也作出理据充分的梳理辩证,钱穆认为戴震反复申说理字,批评宋儒理气论之谬妄,但他自己并没有就“理”字说出新意。作者认为钱穆的分析很难成立,戴震“所说之理乃是经验事实、事物中的物理与事理,宋儒所说的理首先是先验的‘天理’,然后才是万事万物的事理与物理,二者之间绝不相同。宋儒事理、物理是先验的‘天理’的具体表现而已,而戴震的事理、物理是事物本身固有的内在规定性与法则而已,只是生生不息的气化流行之‘道’具体化为不同种类事物之后的内在条理而已。此点,钱穆并不理解,故其所论亦不准确”②同上书,第36—37页。。其次,钱穆对戴震的人性论思想持批评态度,认为戴震的人性论思想背离孟子而近于荀子,与“《荀子·性恶篇》相表里”作者认为,这是钱穆对戴震人性论的误解,“戴震在人性论的问题上坚持孟子的人性善理论,充分吸收了荀子重学的思想,批评了历史上各种人性论思想特别是道家、佛教的人性论思想”①吴根友、孙邦金等:《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上卷),第38页。。其实,戴震的人性论恰恰是孟子的性善论,只是他的性善论比孟子的性善论更强调了为学与认知的一面,是借阶于荀子而发展了孟子的性善论。难道孟子的人性论就不应该继续推进与发展吗?可见钱穆的观点狭隘与保守。除此之外,作者还对港台以及现代国际汉学界部分重要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让读者一书在手,就能对该研究领域的成果与现状有一个总体的可靠的了解。
第二,对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术与思想的性质、特征及其哲学方法论,以及与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内在关联做了深入的考察,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乾嘉时代的哲学是以“道论”为其形上学。戴震与乾嘉学术,前人已经做了许多研究,该书对前人已经做过大量研究的内容,未做过多论述。但前人的研究却忽视了戴震的道论的形上学。本书对戴震以及乾嘉时代的道论展开专题研究,具有替补戴学研究空白的意义,让读者明白戴震欲所闻究竟为何道,明确地从理论上阐明了乾嘉时代哲学的整体性特征。
戴震的学术志向是“志存闻道”,戴震从两个方面论“道”,一是从宇宙论系统求道,二是从六经中明道,“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其道”,即古圣人之道,二者之道最终统一。从宇宙论方面看,戴震认为:“盈天地之间,道,其体也;阴阳,其徒也,日月星,其运行而寒暑昼夜也;山川原,丘陵溪谷,其相得而终始也。”②戴震:《法象论》,载《戴震全书》(第六卷),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343页。作者对戴震以“道论”统合历史上的理气学说,提出“气化即道”的思想给与高度评价,表现出以“道”代“理”的倾向:“古人言道,恒赅理气。”③吴根友、孙邦金等:《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中卷),第298页。道主统,理主分。道论又分为天道人道,人道来自天道,人类的生存生养,皆天道运行之自然规律,与经传中所言之道一致:“经传中或言天道,或言人道。天道,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也。人道,以生以养,行之乎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交也。凡人伦日用,无非血气心知之自然,故曰‘率性之谓道’。”④同上书,第299页。作者认为,戴震把天地、阴阳、气化、生人生物、血气心知纳入道体运行过程之中,与程朱“天理”学说有根本区别,纯粹的“天理”先于气而存在,经验世界中的“天理”与气不离不杂。“天理”作为一种思维的抽象实体从根本上说外在于阴阳二气。戴震所说的道是对阴阳二气有规则的运动状态本身的一种语言描述。⑤同上书,第301页。作者的这些分析,可说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开启了新的探索路径。
戴震与屈原一样,怀着“哀民生之多艰”的热血心肠,他在实证考据学方面取得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但他绝不是满足于为知识而知识的古文献整理,而是要通过文献考据厘清古圣贤立言之意,以此为基础重建大道,他怀经世之才,抱经世之志,希望他的学问能够匡济时艰,为生民百姓更好的生存生养提供合理性依据。戴震敢于冲破世俗的重重藩篱,挑战流行的霸权话语,提出令时人惊骇不已的哲学思想体系。当时学者大多公认戴震是治学严谨成就卓著的朴学大师,而戴震自己却认为自己平生最重要的著作是《孟子字义疏证》,戴震的学术志向就是要为百姓的生养之道提供正当性与合理性。当时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与洞察戴震高远的学术志向。洪榜在《戴先生行状》中说:“先生抱经世之才,其论治以富民为本。故常称〈汉书〉云:‘王成、黄霸、朱邑、龚遂、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民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祠,廪廪庶几德让君子之遗风,’先生未尝不三复斯言也。”①
戴震17岁时就有志闻道,并悟出明道要从语言文字入手。利用语言文字学诠释古代经典,以寻求所谓“道”,乃至对“道”作再创造,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他在给段玉裁的一封信里说:“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②戴震:《戴震全书》(第六卷),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541页。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戴震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③同上书,第370页。戴震对群经小学穷搜研讨,就是要在广泛知识的基础上确立普遍之道。即使当时许多著名学者,也并不理解戴震的追求,只欣赏戴震在六书九数、名物制度方面的考核功夫。正如段玉裁在《戴东原集序》中说,称赞先生者,都说他考核超于前古,实际上,先生之治学,凡故训、音声、算数、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恶是非,以及阴阳、气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实,目的就在于由考核通乎性与天道。“既通乎性与天道矣,而考核益精,文章益盛,用则施政利民,舍则垂世立教而不蔽。”④段玉裁:《戴东原集序》,载《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52页。戴震相信古圣贤之心志、古圣人之道的内容存在于六经之中,戴震说:“六经者,道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古圣贤往矣。其心志与天地之心协而为斯民道义之心,是之谓道。”⑤同上书,第191页。他要在经书中寻求义理,寻求治国安邦之道,“学成而民赖之以生”。他在《与某书》中说:“君子或出或处,可以不见用,用必措天下于治安。”又说:“古人之学在行事,在通民之欲,体民之情,故学成而民赖之以生。”⑥同上书,第188页。他殷切希望他的学问学识能够为国家为造福于民作些贡献。他经常说,国之本莫重于民,有一念及其民,则民受一念之福。戴震的学术志向就是志在闻道,志在通古圣贤之志,重民爱民、为百姓谋福利就是戴震通过明经而要通达的大道。
①洪榜:《戴先生行状》,载《戴震全书》(第七卷),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11页。
第三,该书把戴震的经学考据学以及语言学、音韵学等概括为语言哲学,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对戴震的研究方法内容展开研究,从语言哲学、实证哲学的独特视角研究乾嘉时代的语文学研究与考据学研究所包含的独特语言哲学特征对乾嘉时代的哲学独特性作出较新颖、独特的阐发。为戴震与乾嘉学术研究打开了一条新的路径,为中国语言哲学的发展奠定了根基,具有积极探索创新的意义。
第四,从古典人文知识增长的新视角重新认识、评价乾嘉时代古典语言学、历史考据学的思想史意义。为乾嘉时代提供了新的人文知识,从而对于当时知识界的思想变革提供了新的知识视野与思想视野。为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接受结合确立了学科基础。
第五,该书论述,戴震乾嘉学术从经学传统开出了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诸人文知识门类,为现代学术的诞生提供了自己民族的特定文化土壤,开启了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新方向,对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以新的方式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现代转化的内在理路。最后,作者从比较文化的视野,提出“实事求是”是乾嘉学术的“活的精神”,是乾嘉学术的“共同纲领”①吴根友、孙邦金等:《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下卷),第1153页。。就乾嘉学术而言,“实事求是”精神到后期有所退化,但到了近代,与西方的唯物主义哲学认识论相结合,赋予“实事求是”以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一举转化为现代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两个“实事求是”当然不能等同,但刻意贬低乾嘉学术的“实事求是”本身就是违反实事求是精神的。
戴震治学的基本方法是“实事求是”、“务求其真”,不主一家。不论何人之言,绝不肯轻易相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反复参证,梁启超认为此种精神绝似实证科学的口吻,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具有思想解放的精神。
明清之际兴起“实学”思潮。“实学”含有实用、实际之学的意思,即注重研究探索有关社会民生实际的“经世致用”和“疾虚求实”的实学思潮,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颜元、李塨为其代表。胡适《戴东原的哲学》中把戴震看成是颜李学派的南方传人,并把戴震思想与西方的“拒斥形而上学”的实用主义思潮相提并论。但“实学”二字在戴震那里同时包含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实事求是的学风和求真、求实、求是的治学精神与方法。朴学的原意就是“质朴无华之学”,自然是实学的一种。钱大昕就称赞戴震“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②钱大昕:《戴先生震传》,载《戴震全书》(第七卷),第12页。,凌廷堪更是推崇戴震治学的“事实求是”精神,说:“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③淩廷堪:《戴东原先生事略状》,载《戴震全书》(第七卷),第18页。阮元表示他本人:“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①阮元:《畴人传》,载《戴震全书》(第七卷),第59页。这些都反映了皖派学者的实学精神和科学态度。
在皖派学者中,江永是戴震的师辈,程瑶田、金榜是戴震的同辈,其余的如歙人汪莱、凌廷堪、程恩泽、洪榜,绩溪人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学界称“绩溪三胡”),黟县人俞正燮等都是戴震的学生辈。需要指出的是,皖派朴学的学者并非都是徽州人,从清代方东树到近代梁启超等人,又从“皖南学派”或“徽州学派”中分出“扬州学派”,其领袖人物为焦循、阮元,主要人物有凌廷堪、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汪中、黄承吉、任大椿、孙星衍、孔广森等。其中焦循是扬州人,阮元是江苏仪征人,段玉裁是江苏金坛人,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是江苏高邮人,孔广森是山东曲阜人、任大椿是江苏兴化人,孙星衍是江苏常州人,而凌廷堪、汪中、黄承吉虽然祖籍是徽州人,但实际上却是江苏海州人和扬州人。正是这个不拘于徽籍的学术群体构成了戴震皖派朴学的强大阵容,故有人称之为“徽扬学派”。
焦循和凌廷堪是戴震的私淑弟子,阮元则问学于焦循和凌廷堪。皖派朴学源于江永,创成于戴震,其后传人不绝,段玉裁、王念孙则是戴震的及门高足,龚自珍是段玉裁的外孙,戴震之学一直延伸至近现代。
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朴学家们所倡导的“实事求是”学风实际上是一种科学精神,这种精神继承发展了明清实学传统中的“实事求是”精神,而且影响深远,戴学所被,不徒由皖而苏而浙,且及于齐、鲁、燕、豫、岭、海之间。皖派考据学的最大成果就是形成实事求是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对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和接引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发挥了很好的铺垫作用,并与近代西方输入的唯物主义哲学相结合,形成具有唯物主义哲学基础的实事求是的认识与实践方法。
该书论证,乾嘉时代以道论为自己时代的哲学形上学,以人文实证主义为自己时代的哲学方法论,从而形成了与宋明理学迥然有别的时代哲学特征。又从古典人文知识增长的角度,重新评价了乾嘉时代的语文学研究成绩与历史考据学的研究成绩,从而在新的学术视野里考察了中国学术如何摆脱经学传统。该书论述,乾嘉学术从经学传统开出了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诸人文知识门类,从而摆脱了中国学术研究的专门化,为现代学术的诞生提供了自己民族的特定文化土壤,这一论断从新的角度,以新的方式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现代转化的内在理路。该书还揭示,戴震哲学中所包涵的语言学思想,可能对胡适的白话文革命的思想的形成具有间接的影响。
该书详细论证了,乾嘉学术所开创的“以知识说经”的方式虽然没有达到瓦解“经学”统一性的高度,但为经学的自我解体提供了学术的铺垫,乃至到了清末民初时期,传统的小学与西方传来的语言学结合在一起,乾嘉以还的“考据学”就逐渐演变成现代学术中的历史学、语言学等带有学科性质的专门学问了。因此,传统经学的瓦解不仅仅因为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外部力量冲击的结果,也与乾嘉以降中国学术内部的“以知识说经方式”的自我演变历史密切相关。这些研究成果必定会引起学界的关注,深化当代中国人对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转型的理解。
该书对前人做过较多研究的内容未展开充分研究。我认为,从著作的完整性来说,前人研究过的内容,仍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展开研究,说明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人,从哲学精神上继承了晚明以来的新的人文思想,但主要从学术方面推进了中国学术与思想的转向,因而是明清早期启蒙思想的继续与深化。而且,个人认为,戴震终结了理学,理学的一系列问题在戴震那里得到了解决——“戴震与中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并由此开启了中国哲学的近代新方向。该书中还有一些重要内容,作者已经作为中期成果提前发表,在书中未展开讨论。这些内容也可以在书中表述,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获得一种连续性的快感。
(责任编辑:肖志珂)
B2
A
2095-0047(2016)05-0004-08
王国良,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