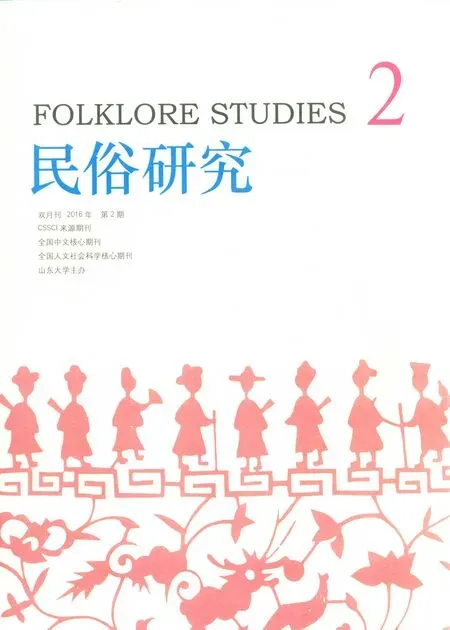论民俗艺术传播的“意义空间”
李 颖
论民俗艺术传播的“意义空间”
李颖
摘要:在媒介的发展推动下,民俗艺术传播的“意义空间”发生了衍变,从着重于文化共享过程与风俗传承认同的初始意义,渐变为由媒介科技化介入之后的被表述、被干预的意义呈现。通过现代媒介传播的民俗艺术能够被媒介能动地反映与创造,而媒介技术的影像传播也造成了民俗艺术传播现场感的缺失与人际交流的淡化,媒介科技化与民俗艺术传播的互动关系将进一步促进关于民俗艺术传播“意义空间”的探寻、阐释与反思。
关键词:民俗艺术;传播;媒介;意义空间
一、引言
民俗艺术的传播,主要经历了由前媒体时代向媒体时代的历时转变。所谓前媒体时代主要指的是现代技术手段和科技传播媒介尚未产生或发生作用的时期,这时的媒介状态主要表现为实景媒介和文本媒介,这个时期主要能与媒体时代建立延续联系的是基于印刷术发明之后的文本媒介,它们是作为媒体时代大众传播媒介中报刊、书籍的早期媒介状态;媒体时代则指伴随报刊、书籍、电视、广播等传统技术媒介,以及网络、手机等新兴技术媒介的产生和运用的时代,媒体时代包括:大众传播和新媒体传播,大众传播主要以传统技术媒介传播为主,新媒体传播则主要以网络、手机等电子新技术媒介的传播为主。民俗艺术传播的联系媒介在前媒体时代主要为实景媒介和文本媒介,在媒体时代则主要为传媒媒介。民俗艺术传播的“意义空间”,是指在其历时传播中受各种理念影响、干预、推动甚至规制的内容意义,表现出文化传承的过程性与技术演化的历史性,这主要体现在民俗艺术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其传播的内容意义发生了从初始意义向现代传媒参与下的意义衍变。
二、民俗艺术传播的初始意义
“传播”作为一个具体的实施行为,它是早已有之的,并且在传播行为产生之初,它就已与文化、艺术等建立了亲密之关系。我们把前媒体时代的尚未有现代媒介介入状态下的民俗艺术的传播意义,作为其初始意义。
民俗艺术传播的初始意义,重视的是其传播的过程和过程中的艺术的各种具体呈示与状态,它注重的是对原生态的民俗艺术关乎仪式、行为、观念、信仰等因子的一种源自生命力的自然彰显和对其间的艺术状态共享的过程,它更着重体现的是对作为民俗艺术要旨的以“传承”为核心的文化现象的认同。因此,初始意义上的民俗艺术的传播,最主要表现出的是对于传统风俗的传承以及传承过程中所显现的对于风俗传统的维护。
(一)作为文化共享的过程
我们把民俗艺术的传播作为一个“过程性”的行为状态来看待。传播本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指信息在空间上的直接式的扩散,而是指传播如何在时间上来维持它所传递出的信息的意义,因此,传播是一种创造、参与、以及维系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它的意义的重点不在于分享这个信息的行为,而是指共享这个行为所表征的文化。民俗艺术传播作为文化共享过程的意义的核心,在于将人们以集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仪式,诸如各种节庆仪俗或丧葬俗仪。民俗艺术传播在尚未涉入现代媒介之前,以实景媒介而进行的传播,其主要就是民俗的仪式传播,即使是语言类的口述民俗、造型类的器物民俗等,也大多源自或出自其中,为迎合仪式表现而作、并继而融入其中,与民俗仪式传播建立了不可分割之联系。
民俗艺术传播的初始意义,一方面它所着重体现的是民俗艺术作为仪式传播存在的过程性,另一方面,是作为这个过程性得以实现的核心存在的“文化共享”。“文化共享”体现的是作为人们群体参与、分享、联结并拥有共同信仰的民俗仪式在传播意义上的文化性特征,这个文化性特征又主要是由在传播环境中“共享文化”的人来感知的。“无论从何种角度,总会发现信息系统的一个普通特征,即意义(期待信息接受者所获得的东西)由下列因素组成:传播、接受者背景以及按预定程序做出的反应、情景。……所感知的内容受到了四个方面的影响——地位、活动、环境及阅历。但对于人,还必须加上另一个关键的方面: 文化。”*[英]爱德华·T·霍尔:《语境与意义》,[美]莫滕森编选:《跨文化传播学:东方的视角》,关世杰、胡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4页。作为传播环境参与者的人,文化之于传播的意义是通过人的感知的过程式体验,即共享过程予以传达出来。
以民俗仪式所承载的民俗艺术传播的初始意义主要从两个层面上来构成:一个是由传统社会官方视角所确定的有目的、有意识的传播行为层面,另一个则是由“眼光向下”的民间视角所组织的有目的有意识的传播行为层面,同为有目的有意识,但两个层面上的目的意识的出发点则完全不同,官方层面是为了巩固维护阶级统治而生发的传播意识与行为,民间层面则是从维护自身对于日常生活基本需求能够得到保障而出发的传播目的和行为。
例如,从秦开始、形成固定于汉,直至后朝历代渐成规模的作为历代封建王朝祭祀大典的“泰山封禅”仪式,春秋时《管子·牧民》中提及:“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祗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管仲:《管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页。其中可见,“祗山川”被认为是顺民之举,并且明确提出如果“不祗山川则威令不闻”,谁会威令不闻?管子是明确的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给予统治阶层的示告,甚而把鬼神之祀这种活动也添上官方的标签谓之曰如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从管子明显带有贵族优越感的对普通民众的“陋民”之称,可管窥即使同为源自远古原始时期的鬼神与山川祭拜仪式,到了阶级社会中,也有了阶级化的划分,统治阶级的祭祀仪式是为了使“威令闻”、使“陋民悟”。可知,官方的这种无论是“祗山川”还是“明鬼神”的祭祀仪式,都是源于巩固维护其阶级统治立场的一种传播行为,他们已经清楚认识到“祗山川”这一举动所带来的传播意义,这时的“祗山川”已经被制度化了,也就是后来被称作的“巡守”之制。在官方有目的有组织的“巡守”、“柴告”、“封禅”一系列仪式行为过程中,构建了作为官方与民众所共享、共认的以“天命思想”为引导的封建集权文化。这也体现了民俗的仪式传播作为文化共享过程所具有的对于意义建构的实质性。
与官方传播相对的民间传播层面,作为民俗艺术传播初始意义的另一个层面,也是最重要的层面,它源自于民间、传布在民间、反馈于民众,它的生活场与信息源都来自民间,它作为更普遍更广泛更原生态的民间风俗仪式的传播,其目的性意识性都较之官方层面的传播更加本真态,生活气息更加浓郁,也是民俗研究关注之重。如管子站在统治阶级立场而提出的“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之行为,实则这些敬鬼神恭祖先的仪式行为大多还是广泛传播于民间的。另外像是民间许多基于祖先崇拜的宗教性节日民俗,虽然是形成于初民社会的较为古老的仪式行为,但直至今日也还有许多民族在承袭着这些保有古老风貌的民俗仪式,如贵州苗族地区的“鼓社节”、凯里地区的杀牛祭祀的“吃牯脏”仪式,广西瑶族的“盘王节”、“达努节”等,都是以一种不定期的仪式习俗来传播对于祖先的信仰崇拜。
民间层面上的各类礼俗仪式简直多到不胜枚举,从地域、民族、空间、形式、表现、目的等等各个方面都可自成一类划分,但在前媒体时代的传播的初始意义都可以归结为:它是通过将人们以集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仪式,来创造并且维系一个能让参与者共享其文化内涵的过程,它传播的意义并不在于这个仪式行为本身,而是在于追寻这个行为所表征的文化涵义的具体过程。
(二)对于风俗传承的认同
民俗艺术传播的另一初始意义,则体现在传播主体对于传统风俗传承的认同感上。如果说,我们把民俗艺术传播作为文化共享过程的初始意义看作是基于历史横向坐标轴的传播意义“过程观”,那么,民俗艺术传播的这个初始意义则可以看作是历史纵向坐标轴上的传播意义“传承观”。传播意义的“传承观”指的是,在媒体时代尚未到来之前的前媒体时代,其时的传承就代表传播,传播也可看作是传承,传承与传播,二者之相互关系极其密切,二者的意义内涵是相通的,这是前媒体时代民俗艺术传播的一个重要的特性。
作为民俗艺术核心要旨之一的“传承”,它既是民俗艺术得以形成与生命力得以持续的内在契机,同时又承担着民俗艺术的传播任务,这是对于民俗艺术“传承”性的另一种解读。民俗艺术的传播与传承一样,自远古先民时代、自民俗艺术产生之日即已存在,只是在后世的传播因为其传播媒介的易蒙蔽性与不易辨识性而多以“传承”作为话语替代,且在古代传播媒介尚欠发达的时候,以传承代传播,更具一定的时代性。
民俗艺术研究非常重视传承问题,传承的意思是指民俗艺术在时间不断持续中的更迭延续、以及创造者与创造者之间的代代传袭、创造者与享用者之间的经久相承,它主要强调的是纵向的时间维度上的历时的延传与承袭。诸多文献典籍如《说文解字》、《尔雅》、《礼记》、《墨子》、《荀子》等中都有关于“传”字的释义、说明或使用;同样如《诗经》、《楚辞》等典籍中也出现过“承”字并伴有后世对它的注解与释义。归而结之,“传”、“承”二字共有的涵义是延续、传授、传递、继承。清代档案史料中有关于“六气相生,循环不穷,岂岁岁间断于传承之际哉”*上海书店出版社编:《清代档案史料选编 康熙朝(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673页。的记载,由其中的“岁岁间断”可知,“传承”是取自时间上的历时相承之义。
而“传播”之“播”字,对它的解释较早出现在《说文解字》中,且从晚近以来民俗学研究的一些理论性研究著述中,出现“传承”与“传布”经常合用或混用的情况,意即传播也可称作传布,“传”与“播”二字合起之义就是传扬与扩布。“传播”一词的历史渊源由来已久,承续古今之“传播”义,其所指涉的范围,包括纵向时间的历史延续与横向空间的信息传递,它更强调历时与共时共同发生的信息传递过程。
传承与传播的关系是不能分割的,“传播是传承的基础,传承是传播的深化;传播的外延大于传承,传承的内涵大于传播;传播过的未必能传承,传承下的一定始于传播。”*孙发成、程波涛:《跨学科视角下的民俗艺术传播》,《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传承比之传播更具延续性和内涵性,它在其历时延播过程中无论外延抑或内涵又与传播有着太多的交集,因此,在分析民俗艺术传播的意义时,就断然不能抛下对于能够更体现传播内涵深幽性的传承的关注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当一种民俗刚刚兴起之时,对于此种风俗的认同只在少数个体中产生,其后才逐渐得到较多数人直至族群或区域性群体的共同认可。人类的这种同感运动不断的深化,当一种有利于群体生存或发展的事象出现并经过反复的实践之后,生活在这个群体中的民众会逐渐给予这个事象一种共同的认可,这种认可导致了这种民俗事象的最终形成,也形成了民众对这种事象所传递的民风民俗传播的认可。
民众对于民俗事象的心理认同和实践认同,构成了民俗艺术得以传承的主客观条件,任何民间风俗的流行,都是不同的民众群体经过对作为风俗载体的民俗事象的反复实践与感受、最终达成的对其认同的共识。没有民众对于风俗传承的认同,民俗艺术的传播也就缺乏了因之才能产生的延续态的意义。
三、民俗艺术传播的意义衍变
媒体时代的到来,因传播观念的变化、科学技术的革命、媒介环境的变迁等因素,使得其时的传播直接影响到了人类文化的结构和形态,而它对于作为人类文化之重要构成的民俗艺术的影响也毫不例外。“时至今日,民俗信息的‘传’的传统形式正在与现代大众传播的‘传’的形式形成了全面碰撞和微妙的重整嫁接”*乌丙安:《民俗学原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79页。。民俗艺术的传播遭遇到了媒介的干预,而媒介干涉或表述过的信息又在传播流动过程中不断变化、不断构建和重新生成并传达新的意义,民俗艺术的传播由于现代媒介的介入而发生了其意义的衍变。
(一)传播中的媒介科技化
在当下社会,现代媒介对于包括民俗艺术在内的各类艺术的传播并不仅仅只是起到一种中介的作用,更准确地说是,艺术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在现代媒介中被重新塑造并得到展示。关于现代媒介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阿什德作了深刻且尖锐的揭示:“我们日常使用的媒介使观念、意图和意义进入生活,尽管媒介和内容在传播行为中是融合在一起的,但是这些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却呈现出一种独立于实在内容的现实性和重要性。所以,媒介远非信息传送的中立的通道:它们是具体的行为代理机构,是各种意义的定位和建构的表达或代表。”*[美]戴维·阿什德:《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邵志择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53-54页。媒介已经开始行使它表述与干预文化与艺术的具体行为权利了,甚而在某种程度上,媒介甚至可以建构某种关于艺术文化的新的表达。
伴随着上世纪初声、光、电技术的诞生,以视听传播技术为主的传播媒介占据了人们日常娱乐活动和文化艺术生活的中心位置,随着电脑操作的简便化、价格的日渐低廉化以及迅速普及的交互式信息网络的形成,民俗艺术的呈现渠道在当下得到了极大的拓宽,民俗艺术因子的表现空间或曰场景也得以大大的丰富。比如相关民俗因子可以出现在电视作为媒介的电视小品中、综艺节目中、MTV和卡拉OK中;也可以出现在以电脑为媒介的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三维动画、电子音乐和FLASH中;此外,无论是摄影、录像、DV电影还是装置艺术等,这些源于科技进步而出现的各式媒介类型都可以作为民俗因子呈现与传播的渠道和场境。各式以科技手段承载着的传播媒介,不论是从外在形态、还是内质特征,都表现出迥异于前媒体时代的媒介的传播质性与面貌特征。这种带有强烈的技术熏染气息的媒介,它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迅捷化、复制化与展览化导致了民俗艺术“本真性”的褪化。传统民俗艺术传达与表现的最具特色且独一无二的“本真性”被传播媒介的脱离时空限制、不断平面化与离散化的技术复制所替代,民俗艺术置身于媒体时代的传播媒介所营造的拟态环境之中,民俗艺术传播的初始意义中那个与文化共享相关的“敬仰”或“膜拜”的精神情绪在媒介拟态环境中转向了被“表述”或“展览”。
媒介的科技化传播手段对于民俗艺术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于民俗艺术传播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拓展了民俗艺术呈现的新空间、引发了民俗艺术表现的新类型,还使民俗艺术形式和内容的传播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被重塑;它有时又通过部分地改变民俗艺术的外在面貌与内在特质,来催生民俗艺术表现的新形态,并且还促使部分民俗艺术呈现越来越强的商业操作式的消费化传播态势。媒介科技化与民俗艺术传播的关系成为当下不可规避的一个命题或实际状况而存在着。
(二)媒介表述民俗艺术及生活
这主要是通过现场直播或新闻报道、广播播报等形式来表述和记录各种民俗艺术现象,用声像传播的方式较客观地再现各个民族的民俗生活和艺术形式,使之成为一种可为大众所广泛了解的民俗知识或生活阅历。
技术媒介的复制化特征使今天的民俗生活可以采用大众传媒的手段进行大量复制。仲富兰在《民俗传播学》中提到德国民俗学家保·辛格尔关于民俗传播的观点,辛格尔认为,现代技术世界的发达表面上造成了许多不利于民间文化生存的条件,但在现实上现代技术促使民俗活动的节奏加快,为民俗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涵盖面,使之可以通过互联网的通讯技术传递到超地方的领域中。*仲福兰:《民俗传播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451页。媒介反映民俗艺术及其生活变迁,就是媒介作为工具的表述功能对于民俗生活的展现,并促进了人们的相互交流、拉近了人们对己俗、他俗的文化亲缘感与认同感。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一方面,媒介在民俗艺术的传播过程中所具有的表述功能,使媒介可以对民俗艺术及生活作一种较为客观的记录与再现,但,这仅是、也只能是“较为客观”的表述。现代媒介进入人们的生活,人们生活融入媒介化的生存,这使人们在其中所接收到的关于民俗艺术及生活状态的信息,已不再是前媒体时代的那种以实景媒介呈现出的原初的自然形态的信息,而是经过媒介技术化手段加工过滤后而呈现的带有“人工修饰”痕迹的信息。其实,即使是在前媒体时代,作为大众传播纸质媒介出现之前的、作为纸媒雏形状态的文本媒介,它也同样存在着无法完全还原本初性的未经解释过的原始信息的这一状况,因为文本媒介的创作者或撰写者在把原本处于实景存在状态的民俗艺术及生活写进文本之中的这一动态过程,就已经使相关民俗信息作为被解释或重制过的信息状态见诸文本了,后世通过前代的诸多文本媒介所了解的历代民俗现象和生活,也大多是经过笔墨渲染的各态描写,这种文本媒介中的信息已无法纯粹地还原相关民俗“事实真相”了。前媒体时代已然如此,更不用说到了媒介技术化传播为主流的媒体时代,这种经调配与释义过的民俗信息就以更加常在的状态而存在了。
因此,这就使媒介对民俗艺术及生活的表述还存在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贯注于媒介中的当代思维对传统民俗艺术及其意义进行重新审视和诠释,这是在客观再现民俗艺术基础上的一种带有评论性的叙述,经由重新审视、思考和诠释过的民俗信息再以一种被重塑的特定观念与结构方式去影响大众的接受心理与观感。
在论及大众媒介的功用时,曾有传播学论者这样说道:“大众媒介的工作不仅仅是报道新闻,更重要的是将新闻组织到已有的框架之中”*潘忠堂:《架构分析:一个亟需理论澄清的领域》,《传播与社会学刊》2006年第1期。,这里的框架指的是媒介对具普遍性或特殊性的议题中的信息的选择、强调并进行传递的基于一定语词、图像、表现手段或表达方式的一种呈现模式。这种论辞更是把媒介在传播报道中的再审视与再诠释功能展现得十分透彻,媒介在组织新闻报道时如此,而在民俗艺术的传播中,民俗艺术和生活事象也是作为新闻报道的一个层面而被媒介组织和呈现。例如,在对2011年《福建日报》中有关民俗报道的叙事框架的分析中,有研究者得出《福建日报》对于“民俗事象新闻的主要叙事框架是‘保护与传承’和‘寻根与认同’”*胡丹:《论〈福建日报〉民俗报道的框架建构》,《厦门理工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的推论,认为《福建日报》在“保护与传承”的叙事框架下主要是针对有一定时效性的当地节庆民俗和民俗文化隐性嬗变这两项事实来进行报道和传播*如对当地节庆民俗的报道有:《福州满城相送拗九粥》(福州“拗九节”即孝顺节的习俗)、《“三月三”,数百村民踏青对歌》(宁德畲族“三月三”传统歌会);涉及民俗文化隐性嬗变的报道有:《90 后“讲古仙”李志勇》(其中记录道:“这样就把传承传统艺术和传播公益结合起来,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听讲古”)。,而撷取的这些事实可以凸显包括节庆民俗文化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之道,这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设定“文化遗产日”、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遗产生存境遇渐趋恶化的现状等背景密切相关。再如,《南京日报》2014年9月29日有一则《“文化遗产优雅重生”让南京更有魅力》的报道,报道述及在2014 中国南京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博览会期间,与会嘉宾参观了南京的各项文化遗产和纪念场馆,从南京博物院到江东门纪念馆,从中华门城堡到老门东,从甘熙故居到明孝陵遗址,南京古都风貌与众多历史文化印记得以多方位的呈示。这则报道对于南京历史民俗文化景观的叙述,应南京召开“名城会”之时,承2014年上半年北京鸟巢的首届环球大使圆桌论坛(论坛主要议题是“世界文化遗产如何在新时代优雅重生”)之机,并依据南京在“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论坛”上的发言,提出了南京文化遗产优雅重生的理念,应时承机地传播了南京的民俗文化遗产。
西方论者曾将媒介的这种表述定义为体现意识形态性的符码化语言,认为媒介即是一种再现的叙述,“任何对世界的叙述皆是从特定理念立场所塑造,新闻中所谓的真实事件是一个经‘选择’后的约定化过程,它们被选择并非本质上有新闻价值,而是根据不同社会背景的意识形态所建构出来的。”*崔清活:《试谈新闻叙事框架的人文导向》,《新闻记者》2005年第11期。对于民俗艺术来说,它有其不同于一般新闻事件的独特性,不能用约定俗成的传播学叙述话语和理论来对它进行简单地套定和阐释,然而,一旦当它成为了传播媒介和媒介报道的“选择”,那么经由媒介审视、诠释以及评述性的传播策略所构建的民俗艺术及其与之相关的生活、形态等的传播,又的确与深层的社会意识形态有着紧密地关联。
(三)媒介干预民俗艺术及生活
通过现代媒介传播的民俗艺术,能够被媒介能动地反映与创造,媒介所提供的时空跨越式的交互平台,使民俗艺术的各类表现形式得以在媒介平台上交流、融合、对话与碰撞,媒介在给民俗艺术提供一个足够宽广以供展演的舞台的同时,也在为诸种民俗艺术形态如何找到更适合自身生存与表现的媒介环境给出考题。物竞天择,尤其当民俗艺术遇到媒介环境中残酷的生态淘汰时,保留、传承、播布,抑或摈弃、遗忘、消逝,成为民俗艺术在传播时的一种艰难面对。
如此,为了适者生存于日息瞬变的技术化的传播媒介中,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传播环境下,传统民俗与生活会经由媒介干预而发生变迁和整合,如“通过在原有文化基础上移植、嫁接和重新生长,就有可能形成和传统民俗生活显著不同的新民俗。”*邵培仁、范红霞:《传播仪式与中国文化认同的重塑》,《当代传播》2010年第3期。或者是“为适应即时政治需求而形成的‘新传统’,……凸显的是乡土传统坚韧的适存能力。”*张士闪:《“顺水推舟”:当代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不应忘却乡土本位》,《民俗研究》2014年第1期。媒介对于民俗艺术及生活的干预,一方面促发了基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中的新民俗或新传统的出现和生长,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媒介的干预还可扩大公众影响力,反映时代精神的进步,其产生的意义则在于通过媒介的干预来提升民俗艺术传播对于受众的文化认同感的重塑力和建构力,把民俗艺术传播的效力发挥到最大化。例如,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自2006年以来,就以中国“文化遗产日”为契机成功打造了“中国记忆——文化遗产博览月”大型媒体行动*中国文化遗产日——守护我们的中国记忆[EB/OL],http://kejiao.cntv.cn/special/whyc/shouye/index.shtml,2015年3月15日访问。,每年都会派出庞大的拍摄人员和采访阵容并以多方位的取景取访等方式,对我国的文化遗产进行报道,而报道民俗艺术的传承成果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层面。央视集结大众传播与新媒体传播媒介进行的关于文化遗产的这种“中国记忆”式的介入和干预,展现了作为新媒体主力军的网络媒介的全民动员、全民呼吁和全民守护的传播力与号召力,这是对民族文化精神守护与传承的一种积极的媒介干预。
现代传播媒介通过传播建构起了当代中国民俗艺术与生活的新表征。当媒体时代来临之后,面对现代化的转型、新旧价值观的碰撞、现代与传统的断裂,媒介的介入、参与、表述和解释有助于我们追溯和重塑对传统、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认同感。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媒介的拟真性、能动性、复制性与修饰性,为大众营造了一种类似生活常态的媒介环境,这种典型环境中传播的又是经由媒介表述与干预了的民俗艺术和生活,大众的文化凝聚感、认同感与求知欲基本是由媒介技术化的声影传播而获得,这就使得媒介在促进民俗艺术传播的同时,也在弱化着民俗传播中的人际传播与群体传播,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交流越来越少,甚至有的连传承了上千年的传统节庆年俗也渐被忽略、淡化和漠视,而代之以通过快捷式的“指尖上的传播”的媒介操作方式来完成节俗礼仪。民俗艺术的媒介技术化的影像传播正使民俗艺术及生活本身与传统民俗艺术活动特有的氛围渐行渐远,民俗艺术传播的现场感的缺失与人际交流的淡化,使民俗艺术独有的感染力与触动力被削弱。
吉尔兹在其关于“地方性知识”的研究中曾指出,研究文化并不是寻求其规律的实验性科学,而是探寻其底蕴的阐释之学。民俗艺术的生命力,更深层的取决于它所涵有的价值与意义如何对民众产生适应当下环境的新的精神意义与应用意义,民俗艺术传播的意义阐释正是把民俗艺术从传播初始到当下传播的历时纵向的意义变迁串接起来,并从中探求各历史共时阶段的传播意义存在的生态均衡性。探寻民俗艺术传播的“意义空间”,也正是期冀能为应对现实环境与媒介变迁提供一定的思考与启示。
[责任编辑李浩]
On the Meaning Spac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Folk Arts
LI Ying
Influen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the meaning space of folk arts communication has evolved from focusing on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cultural sharing process and custom inheritance approval to the presentation of significance after being intervened by Sci-Tech media. Aided by modern media communication, folk arts can be reflected and created by it vigorously, and the visual communication of media technology has resulted in the loss of the presence of the folk arts communication and desalination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lk arts and media technology will further promote explor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meaning space of folk arts communication.
Key Words:folk arts; communication; media; meaning space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项目编号:13YJC76005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颖,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江苏南京 21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