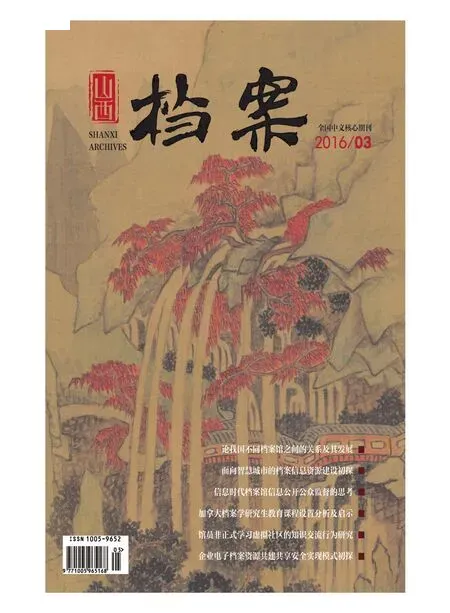档案利用评价指标述论
文/陈 通 赖敬延 Chen Tong Lai Jing-yan
档案利用评价指标述论
文/陈 通 赖敬延 Chen Tong Lai Jing-yan
摘要:从建立档案利用评价体系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学界讨论比较集中的档案利用率、档案拒用率(有效利用率)、档案利用效益评价三种评价指标深入剖析,分别讨论其在档案利用评价体系和实际工作中的理论和实际效果,以期达到引起人们在新视角下对档案利用评价指标研究的重新审视。
关键词:利用评价;档案利用率;档案拒用率;效益评价
档案利用工作位于档案工作链条的末端,正确评价档案利用工作,往往能够起到追溯评价档案工作其他环节的效果。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一方面松散的利用评价指标研究尚未建立起健康均衡的利用评价体系;另一方面,对单项评价指标的研究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如不理清阐明,对我们理解档案利用工作和档案利用评价体系的建构都将产生不利的影响。笔者将就现有的几项指标的研究情况进行简要地梳理并加以分析,以期有助于档案评价体系的建构。
一、档案利用率:档案利用的数量比例
(一)档案利用率的两种定义
顾名思义,档案利用率是指被利用档案与馆藏档案的比率,它所考察的是馆藏档案的活跃度。诸多档案学论著在讨论档案利用工作或者统计工作时都使用了这个概念。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学界也有不同的观点。何嘉荪主编《档案管理理论与实践》、陈永生著《档案工作效益论》等均认为,档案利用率是指一定时间内被提供利用档案卷(册)数与馆藏档案总量的比值。[1]另有论者认为,如此理解无异于将档案利用率等同于馆藏档案动用率,其考察的是馆藏档案的活跃点数与档案馆藏的比值,而对于档案的活跃程度则无法反映。因此提出了另一种定义,即档案利用率指一定时间内被提供利用档案卷(册)次数与馆藏档案总量的比值。这种定义将档案的利用频率作为一项考察条件列入公式,不以档案利用卷(册)数量作为唯一考察对象,从而提供了相对多样的考察视角。对比两种定义,我们可以看到,前一种定义所考察的是档案活跃点在馆藏档案中的情况,是一定时间内活跃档案在馆藏档案中的比例,是将馆藏档案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其活跃度。这种考察相对来讲是一种平面的考察,是一种馆藏档案活跃点数量的统计。而后者则更多的将视野集中在档案个体上,其考察的重点是馆藏档案的利用频率。此种考察则可视为一种立体的考察,不光考察了馆藏档案的活跃点,同时还反映了活跃点的活跃程度。前者考察的意义在于利用的广度,后者考察的意义在于利用的频度。
(二)对“提高档案利用率”的质疑
有学者对档案利用率产生质疑。其中以林清澄《“提高档案利用率”悖论》一文最具代表性。文章从不同种类档案对提供利用要求不同,导致档案工作急功近利思想产生,不利于档案利用工作横向和纵向比较等方面对学界片面“提高档案利用率”的论点提出了中肯的意见。[2]另外还有论者从档案保护的角度出发,认为片面追求提高档案利用率不利于档案实体的保护。虽然随着档案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已经渐趋消弭;但片面提高档案利用率所带来的其他负面影响依然存在,这也恰恰是档案利用评价指标单一、未形成均衡评价体系所导致的后果之一。
二、利用拒绝与有效利用:档案利用质量的正反评价
(一)档案拒用率或档案利用拒绝率
顾名思义,拒用率或利用拒绝率是考察档案提供利用过程中未能满足档案利用需求的情况,是相对于档案利用需求而言“负面效果”的考察。目前学界对此讨论的并不多,且多从图书馆学的拒借率借鉴。霍振礼、李碧清著《档案利用评价指标研究》一文中,对此用公式表示为“一定时间未能满足合理需求的档案卷次”与“一定时间利用者所提合理需求的总卷次”的百分比。[1]
此公式,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考察对象锁定为利用者,尽管公式将利用者需求限定为“合理”,但这并不能完全排除档案利用者由于自身原因导致的利用需求未被满足的情况;第二,在实际工作中,当档案利用者提供所需档案信息相对模糊(尤其是对历史研究者而言),对档案难以形成明确指向,因此在无法预知所需卷册数量的情况下,统计“一定时间利用者所提合理需求的总卷次”是十分困难的,即便有统计结果也难以保证准确。笔者以为,以下公式在实际工作中似乎更为可行,“一定时间未能满足合理需求的档案卷次”与“一定时间内档案机构提供的档案总卷次”的百分比。上述两种公式相比较而言,前者的考察重心在档案利用者的利用需求,而后者的考察重心在档案机构档案利用提供情况。除了前述后者在可行性方面更具优势外,从国际档案学发展历程来看,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档案的存在应该具有其自在的意义,而非由利用需求所决定,更非某项工作的附庸。因此,我们考察档案利用中的拒绝情况,也应当立足档案工作自身进行评价。
(二)档案有效利用率
笔者曾经提出“档案有效利用率”的观点,以之作为档案利用质量评价的指标,与档案利用率共同建构档案利用评价体系中数量评价和质量评价的两个维度。所谓有效利用,即指所利用的档案对档案利用者需求而言具有积极的效果,无论研究者所探究的“真相”,抑或是其他利用者所追求的“效力”,还是其他需求。档案有效利用与档案利用拒绝是互补的两项指标,分别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考察档案利用的实际效率。
(三)片面追求档案利用质量之弊
档案有效利用率是否越高越好?或者档案利用拒绝率是否越低越好?我们对于这两个考察指标是否以追求极限为终极目标?笔者认为,任何评价对于评价对象而言都具有潜在的导向性,档案利用评价指标也不例外。在没有建立起相对平衡的评价体系之前,任何单独的评价指标都不宜追求极端化。仅就档案利用效率评价而言,如果我们片面以达到极限为终极目的,那么,在实践中势必对档案工作其他方面产生某种程度的负面影响。以下以档案有效利用率为例稍作探讨。
1. 会降低主动提供档案利用的热情
档案机构为了更大的发挥档案作用,往往提倡提供档案利用的主动性。从档案机构的角度来看,主动提供利用可以为实现档案价值提供更多的机会和途径;从利用者的角度来看,尤其对研究者而言,他们希望能够获取更多的信息资源,尽管可能不是档案利用者明确要求,但或许是利用者确实需要的。因此,向利用者主动提供相关联档案的利用服务是应当允许适度存在并加以鼓励的。主动提供档案利用服务必然是建立在对档案用户需求预判的基础之上,应当允许有一定程度的误差。
2. 不利于相关联档案的整体性
诚然,我们当前档案管理的基本单位正逐渐变小,原本以卷、册为基本管理单位的管理模式逐渐向以件为基本单位的管理模式过渡。表面上看来似乎较之卷册式的管理模式其关联档案的整体性更为松散,实际上,由于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的介入,尤其是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云计算平台,使看似松散的管理体系其内在各层面的整体性更强也更易于把握。而一旦我们以高效的档案利用作为评价标准,无异于规定了档案利用的精确指向,从而割裂了档案文件之间的有机联系,不利于我们将相关联档案作为一个整体把握。
3. 将导致档案利用服务理念向提供档案的证据性价值倾斜
根据文件的双重价值理论,档案具有近期的证据价值和长远的文化价值。二者相比而言,前者的特征更明显一些,后者的价值往往需要研究者深入挖掘才能彰显。显而易见,在提供利用过程中,证据性价值的提供服务在满足利用者需求方面的精准度方面无疑占有优势。因此,当我们片面的追求档案有效利用率,对于档案长远文化价值的保护和提供利用将会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
三、效益评价:悖于公益的模糊评价
(一)评价效益有悖档案及档案机构职能
顾名思义,所谓效益即效果和利益。从档案及档案机构的公益性质来说,无所谓利益可言,充其量我们只能评价档案的利用效果。具体的一次档案利用活动能够产生多少的效益,并不是档案机构所应该考虑的内容。也就是说,无论档案利用所产生的后续效益多少,其档案利用者所享有的利用服务应当是同样的。而我们一旦开始评价档案利用所产生的效益时,拥有效益优势的档案利用者无疑更受拥有资源优势的档案机构的青睐,如果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拥有资源优势的档案机构与档案利用者之间将会出现类似于垄断性质的严重不对等关系,从而使档案机构在实际提供利用工作中有选择性的赋予拥有效益优势的利用者以优先权。同时,在档案机构内部,由于不同门类的档案产生的效益也有所差异,效益评价会使不同门类的档案所受到的关注度因此而不同,并由此影响到随后的后续工作的开展。
(二)档案利用效益评价的可行性难以具备
从效益评价的可行性来看,效益(尤其是社会文化效益)的量化是一个难点。以档案机构为主体通过各种方式实现的档案提供利用服务所产生的效益,从实现过程来看,可以分为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直接效益是档案机构作为效益产生主体,通过档案提供利用、档案信息编研、档案信息发布等方式对社会直接产生的效益,此种效益多为文化效益;间接效益是指档案机构通过档案用户对档案信息的利用,由档案用户作为效益产生主体所形成的效益。间接效益的形式比较多样,既可以是文化效益,也可以是经济效益,应视利用者具体产生的效益性质而定。关于经济效益的评价,国家档案局曾经针对科技档案开发利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发布《开发利用科技档案所创经济效益计算方法的规定(试行)》,仅规定了通过利用科技档案所产生经济效益的计算方法,从而实现科技档案利用所创经济效益的量化。但对于其他门类档案而言,对文化效益及其他形式的效益而言,量化仍然是一项过程相对复杂、结果难以精确的工作。因此,计算效益的可行性难以具备。
从目前来看,关于档案利用评价指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上三项,然而就档案利用评价体系的建构而言,无论指标数量还是指标间的均衡程度都是远远不够的,尚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责任编辑:阎海燕)
参考文献:
[1]霍振礼,李碧清.档案利用评价指标研究[J].档案学通讯,2002,(2).
[2]林清澄."提高档案利用率"悖论[J].档案,2001,(2).
中图分类号:G27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652(2016)03-0052-03
作者简介:
陈 通(1978—),男,吉林梅河口人,青岛理工大学档案馆馆员,硕士。
赖敬延(1967—),女,山东济南人,青岛理工大学档案馆副研究员,硕士。
Discussing the Indicators of Archival Utilization Val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