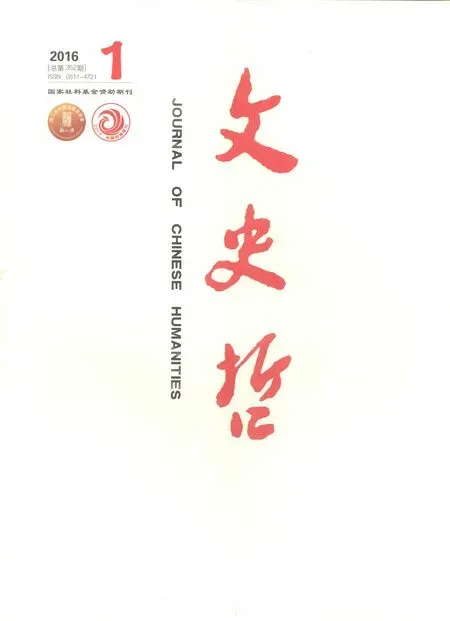新学独尊与两宋之际的颂美辞赋
刘 培
新学独尊与两宋之际的颂美辞赋
刘培
摘要:专制政治与歌颂文学是一对孪生兄弟,政治上的集权专制需要高度一致的意识形态作保障。较之其他学术,王安石所倡导的新学更具专制主义政治品格。两宋之际的新学独尊期间,专制主义政治进一步强化,歌颂文学大行其道。皇权源自暴力,但统治者更愿意让人们相信其权力是上天赐予,具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和唯一性。当时的颂美辞赋许多是为此服务的。王朝气势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两宋之际的颂美辞赋表现的王朝气势不仅仅是作家个人的感知,它还代表意识形态发声,表现的是权力对王朝气势的塑造。当时有些辞赋还直接歌颂圣王美政,积极为其寻求理论支撑。颂美辞赋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文人向极权政治展示无限雌伏、无限谄媚的心理状态的工具,它还可以构造虚假民意,图解政治意图,强化意识形态,以此向极权献忠纳诚。
关键词:新学;专制主义;歌颂文学;辞赋;意识形态
专制主义与歌颂文学是一对孪生兄弟,政治上的专制主义需要高度一致的意识形态作为保障①,这就意味着士人群体独立思考的精神可能面临着严重的遏制,文学可能矮化为服务于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和点赞器。两宋之际的新学独尊期间,专制极权进一步强化,歌颂文学大行其道。新学独尊与歌颂文学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因果联系,这是本文所要考察的重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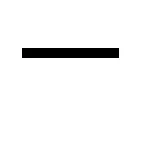
①传统中国并不存在“意识形态”这样的现代词汇,但却有一个与之相近的词语“政教”。政,不仅是指行政,还包括调整思想、规范行为等内容;教,不仅是指教育,还包括向社会全员灌输关于社会秩序的善恶标准。在宋代,担任政教任务的指导思想是儒学。不过,儒学早已内化为传统,在当时呈现为一个伸缩性很强的、流派纷呈的庞大体系。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政治形态,其侧重点和倾向性又有所不同。本文所指的专制主义严格来说其概念等同于东方专制主义,是指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最高执政者及其特权集团,统治者排斥一切形式的对最高权力的监督与约束;政治权力是高度集中而单一的,最高执政者与臣民之间是统治与效忠关系,国家资源和荣誉声望高度集中于最高执政者及其统治集团。本文所说的皇权专制,是指以维护皇帝为统治核心的专制主义,它排斥一切形式的对皇权的规范、约束与监督。
一、两宋之际的新学独尊与专制主义
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为了排除异己势力对新法的妄议,主张“一学术”,即把新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学术与政治联姻,学术借重权力来把自己的理想落实到政治层面,凭借富贵利达引诱天下士子入其彀中。在新学与其他学说的论争中,其依靠政治权势打压对手的结果,远远超出王安石们壅堵言路的初衷,而是渐变为学术、思想上的专制,并与变法期间不断加强的皇权专制互相呼应,一直以来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为之一变。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学术园地众学凝霜,一枝独放,而且还使得学术界把控的知识解释权和士大夫占据的帝王师地位,面临着失控和旁落的危险。绍圣以后,新学显贵如蔡京等,基于以吾党行吾道的考虑,一味迎合帝王,投其所好,学术失去了对皇权的约束力,独尊的新学成了皇权恶性膨胀的帮凶、皇家的奴才。学术与政治的专制主义,是导致靖康之难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促成士风低迷猥琐、文坛歌功颂德之风盛行的重要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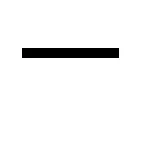
靖康之难,士大夫压抑已久的愤懑之情全面爆发,人们对蔡京的憎恨、对新学的反感,似乎出离了政争与学术之争的范畴,本该理性反思的国破家亡之痛被党同伐异所代替,置大计于不顾,快一时之恩仇。靖康元年(1126),以重新审视科场制度发端,元祐党人的后继者对新党和新学大加挞伐。这场争论源之于对辽用兵失利导致的对经义取士的反思,垄断科场的新学自然成为靶标。很快,理学传承者杨时等人发难,把蔡京与王安石联系起来,由对新学的批判引申到对王安石人格修养的攻击,直取王氏心肝。之后,高宗皇帝出于新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受到广泛质疑的考虑,施展政治平衡权术以稳固地位,团结人心,提出“最爱元祐”的口号,遂使元祐学术与新学呈鼎足之势。此时的科场经义与诗赋并重,理学思想开始大举渗透,士林也出现分化。
这种情况在绍兴和议达成时出现了转变,同样是出于对朝野横议的担忧,高宗和秦桧打算像熙宁变法时那样壅堵言路,打击对和戎政策持异见者,新学在秦桧的庇护下余焰复燃。绍圣年间新学独尊以来,并没有彻底遏制住其他学术的发展,其中理学因此而强力反弹,并在士林下层滋长蔓延,随即成为之后对抗新学和新党的主力。因此,绍兴党禁主要是针对道学党和理学的。其时,新学已经失去了北宋末期的气势,只是由于秦桧的护佑,才勉强踞于独尊的地位。权相秦桧排斥理学,提倡新学,残酷打击道学人士,学术专制与政治专制取得高度一致。据载,包括高宗在内,众人多持新学与理学各有所长之论,但是秦桧独擅新学:“绍兴十四年三月,尹和静(靖)既去,秦桧进呈讲筵阙官,因言士人读书固多,但少适用,或托以为奸,则不若不读之为愈。上曰:‘王安石、程颐之学各有所长,学者当取其所长,不执于一偏,乃为善学。’桧曰:‘陛下圣学渊奥,独见天地之大全,下视专门之陋,溺于所闻,真太山之于丘垤也。’桧所谓‘专门’,指伊川也。自赵忠简去后,桧更主荆公之学,故上训及之。然桧非但不知伊川,亦初不知荆公也。”*李心传:《道命录》卷四,知不足斋本,第42页。这则材料清楚地表明秦桧的学术好尚所在。绍兴党禁前后,学术风尚转变明显,诚如秘书正字叶谦亨所说:“向者朝论专尚程颐之学,有立说稍异者,皆不在选;前日大臣则阴佑王安石而取其说,稍涉程学者,一切摈弃。”*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34页。当时,被禁的新学核心典籍《三经新义》也恢复了科场的地位。
新学对其他学术打压最严酷恶劣的时段是在崇宁党禁和绍兴党禁期间,即权臣蔡京和秦桧分别专权之际,这也是宋廷政治专制程度最为深重的时期。一些研究者从当时相权的强势,得出君权相对削弱的结论,这种看法是相当片面的,因为无论蔡京还是秦桧,其权力均来源于皇帝,他们都是一味揣摩圣意以邀幸固宠的佞臣型人物,他们的政治倾向保持着与君王的高度一致,已经失去了其应有的对君王的匡扶救弊、拾遗补缺之任。从当时的历史来看,这些权相就是君王的代言人,君权的执行者,君过的替罪羊。因此,相权的膨胀,也就意味着君权的膨胀,被削弱的,不是君权,而是朝臣以至于整个士大夫阶层执政与参政议政的权力。在整个宋代,君主一直没有掌握住知识的解释权和信仰的垄断权,但是,掌控意识形态是专制极权的必要条件,因此,君主对知识与信仰的控制,必须假手于权相,蔡京、秦桧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帮助帝王控制意识形态,而操控的工具,则历史地落在了新学的肩上。
儒学具有强烈的参政意识和排他品格,由其发展而来的新学、理学等宋代学术继承并发展了它的这些特点,它们都主张传承道统,严格文化的边界,弘扬修齐治平的人生方向,推崇内圣外王的治国理想,凡此种种,表现出浓厚的文化本位主义和专制主义色彩。在向形而上的方向迈进时,宋代学术普遍地把等级观念——伦常,作为终极真理,使宗天神学转变为宗天哲理,把皇权确定为社会秩序乃至天地秩序的总纲。宋学是沿着韩愈以来知识界对统治失序的焦虑而发展演进的,捍卫绝对皇权是它们的共同追求,只不过宋学在发轫之初,始终掌握着知识和信仰的解释权,把对皇权的规范作为其重要目标。

新学尊经卑史的思想也助长了皇权的膨胀。王安石的历史观来源于六经,认为六经是先王之学,是治国之本;而史,记载后王之迹,是流俗之学,是治国之末。王安石的治国理想依托于虚无缥缈的尧舜之道,主张对待历史应该有先入之见,即“识”,认为王霸之道的区别只是在于帝王的心术,帝王有行尧舜之道的“识”,所行之政即是王道,反之则是霸道,这就过分突出了帝王的个人意志。这种学风容易忽视对历史成败之迹的借鉴,忽视历史发展的传承性,从而失去士人以史为鉴来规讽皇权的传统,这为帝王的独断和多欲之举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正是基于这方面的价值,以后的新学人物都积极主张尊经卑史,打击异己之学,树立帝王权威*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指出:“自王安石以猖狂诡诞之学要君窃位,自造《三经新义》,驱海内而诵习之,甚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章、蔡用事,祖述荆舒,屏弃《通鉴》为元祐学术,而十七史皆束之高阁矣。嗣是道学诸儒,讲求心性,惧门弟子之泛滥无所归也,则有诃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又有谓读史令人心粗者。此特有为言之,而空疏浅薄者托以借口,由是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彼之言曰,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85页)。况且新学学风更为务实开放,讲变通重权变,看重现实的政治需求,这不同于理学的深于道德性命之际*正如朱熹所指出的:“若夫道德性命之与刑名度数,则其精粗本末虽若有间,然其相为表里如影随形,则又不可得而分别也。今谓安石之学独有得于刑名度数,而道德性命则为有所不足,是不知其于此既有不足,则于彼也,亦将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为妙道而谓礼法事变为粗迹,此正王氏之深蔽。”(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晦庵朱文公文集》四《读两陈谏议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3823383页),这种种因素也容易使其蜕变为权臣逢迎君主、为皇权专制助力的工具。新学独尊期间,学术与政治互为奥援,相得益彰,专制极权得到强化。权臣们还通过定国是,来锻造一柄集思想与权力于一身的利剑来捍卫专制,引导舆论,打压异己,如徽宗时的丰亨豫大、高宗时的和戎等都是。
皇权的恶性膨胀、士大夫阶层帝王师地位的失落,很容易导致士人群体的人格矮化、担当意识缺失,助长文人钻营帮闲的习气,造就文人无限雌伏、无限谄媚的精神。而且,北宋后期专以经义取士的科场制度也对士子的钻营心理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专制主义往往需要不断寻求以及强调自身的合法性乃至神圣性来维持统治局面,这就需要倡导一种与意识形态合拍的文学——为专制皇权歌功颂德的文学。钻营猥琐、文丐奔竞的士风为这种文学的流行准备了条件,新学独尊、皇权独断的必然结果便是歌颂文学的发达。由于学术文化发展的惯性特征,使得两宋之际的主流文学一度沉浸在虚声颂美的气氛中,颂美辞赋的流行即是当时政治学术生态的鲜明表征。
二、辞赋对皇权神圣性的叙述
在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颂圣文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皇权源自暴力,但是统治者并不想让天生烝民只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更愿意让人们相信他们的权力是上天赐予,具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和唯一性。为此,暴力政权往往诉诸祭祀、祥瑞等来交通天人,通过强调上天因垂青现政权而赐予的风调雨顺的年景、繁杂丰茂的物产、平安祥和的生活等来宣扬皇权翼护苍生。也就是说,皇权需要凭借神权来扶佑,而且,专制程度越深,越需要证明其统治的伟大、光荣与正确,其对神权的倚重也就越强。两宋之际的歌颂文学,有相当的内容是表现极权统治的合法性和神圣性的。
古者天子建国,宗庙为先,典礼在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吉礼之中尤以每三年一次皇帝亲祀的“郊祀”天地礼(南郊)最受重视。不过这种礼仪性排场至两宋之际,其沟通天人的用意已经弱化,变成了皇家昭示其垄断神权的表演,象征意义超越了实际意义。目前能见到的这个时期的典礼赋有刘弇的《元符南郊大礼赋》和王洋的《拟进南郊大礼庆成赋》等,其重点已经不再像真宗时杨亿所作的《天禧观礼赋》、仁宗时范镇所作的《大报天赋》那样陈述上天眷顾,而是展示国家的气势和治国方略。同样的情况也表现在王观《扬都赋》、王十朋《会稽风俗赋》等地理赋方面,其彰显皇权神圣的用意退居其次,变成了对国家“气质”、“形象”的张扬,对此我们将在下文讨论。当时最能够体现皇权神圣性的是辞赋中对祥瑞的描写。
传统儒家对怪力乱神持敬而远之的怀疑态度,但又主张神道设教,为天人相与之说开启方便之门。汉代今文经学,尤其是春秋公羊学以微言大义解经,畅言祥瑞灾异,终至发展为谶纬神学。宋学总体倾向于道德理性主义,对汉学的谶纬之风大加排抑。当时的儒者基于规范皇权的目的,对灾变之说颇为注意,而对祥瑞呈现则表现得相当冷静和理性。熙宁变法期间,司马光等指出“天文之变无穷,上下傅会,不无偶合”*毕沅编集:《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1781页。。王安石则申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550页。。但是,天人相与之说从汉代以来已经发展成为儒家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处于独尊地位的新学和日益加强的皇权专制不可能抛弃对神权的控制和依傍。新党主政期间,弃灾变而兴祥瑞,为专制主义政治生态服务,为皇权专制的合法性和神圣性服务。变法以来,祥瑞不断呈现,徽宗时期,朝廷有意识渲染盛世气氛,祥瑞因此纷至沓来,蔚为大国。朝臣们的奏疏中充斥着大量针对祥瑞的贺表,诗词创作一片盛世吉祥的称颂之声,润色鸿业的辞赋自然不会缺席。承此余绪,南渡后,针对高宗再造中兴的聒噪不绝于耳,尤其是在绍兴和议达成后,出现了一个赞美高宗、韦太后、秦桧神性品格的高潮。
由于澶渊之盟的缘故,真宗时期和仁宗前期,是一个祥瑞的多发期,以后渐次消歇。神宗变法期间,鲜有祥瑞,倒是借灾异以反对变法的言论不少。周邦彦的《汴都赋》历数汴梁一带祥瑞呈现的历史,以凸显汴梁乃上天眷顾之地,笔触不及当代祥瑞。李长民的《广汴都赋》是对周邦彦赋的补充,而非踵事增华,主要补充的是徽宗时国家出现的新气象、新面貌,当时祥瑞势头正猛,赋中提及当时的盛况曰:“众制备,群音叶,天地应,神人悦,修贡效珍,应图合牒。上则膏露降,德星明,祥风至,甘露零;下则嘉禾兴,朱草生,醴泉流,浊河清。一角五趾之兽,为时而出;殊本连理之木,感气而荣。嘉林六目之龟,来游于沼;芝田千岁之鹤,下集于庭。期应绍至,不可殚形。”*本文所引辞赋均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并参校曾枣庄主编《宋代辞赋全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为行文方便,恕不一一胪列出处。指出祥瑞纷呈的原因是徽宗的大举更张和修明法度得到上天的赞许,是天人感应所致。可见当时的祥瑞纷沓是为新党和徽宗的美政在上天那里寻求合法性,而非习惯性的应景之举。从目前所见朝臣们的各色贺表来看,当时的确是一个祥瑞集中爆发的时期,而且规模空前绝后,诸如白兔、白龟、翔鹤、蟾蜍背生芝草、朱草、瑞麦、连里木、瑞木、瑞石、甘露、竹上甘露、红盐、河清、庆云、天书等等,不一而足,仅仅政和年间上奏的灵芝就有二三万本,山石变玛瑙以千百计,山崩出水晶几万斤,山溪生金数百斤,其他草木鸟兽之珍不可尽数,“皆以匣进京师”,“一时君臣称颂,祥瑞盖无虚月”*周密撰,张茂鹏点校:《齐东野语》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09页。。而且这势头也蔓延到皇宫中,蔓延到皇帝身边,譬如延福宫、端成殿等均有醴泉、灵芝、翔鹤等出现。徽宗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祥瑞灵异环绕的神仙气息氤氲的氛围中,他是个具有艺术家气质的皇帝,很容易模糊艺术与生活的界限,随着自我意识的膨胀,他的思维超越了世俗逻辑,进入自我神化的状态,他不再怀疑祥瑞的真实性,他真切地相信自己非肉身凡胎,是天才,是神。徽宗已经不再满足于祥瑞不期而至,而要使其成为常态化的生活图景,因此,他纲运天下奇石嘉木、大兴土木,以此来显示天下人神相和的时代特征。当时所建的艮岳、延福殿等,就是巨大的祥瑞之渊薮,而且徽宗本人也是一个祥瑞,过去的礼乐制度已经不能很好地沟通神人了,他要另创新制,宫中的玄圭、新制的九鼎、八宝等均成为国家的圣物,在彰显皇权神圣化过程中,他自我作古,大晟府的设立,就是在推进这项工作。徽宗在全力以赴引领他的国家和人民走进遍地祥瑞、和谐融洽、吉祥止止的时代,艮岳就是这个时代的结晶。
目前所见描绘艮岳的辞赋有两篇,即李质的《艮岳赋》和曹组的《艮岳赋应制》,李长民的《广汴赋》也稍有涉及。李质赋以游踪为线索,移步换形,详尽描绘其仙境般的美景;曹组赋则以类相从,纵笔铺排山形、水势、嘉木珍果、奇禽异兽,重在渲染气势。两赋具有一定的互补性。李赋凸显的是艮岳沟通天人的意义:“何诸山之环异,均赋美于一端。岂若兹岳,神模圣作,总众德而大备,富千岩兮万壑。”这座人造的山岳和其他那些名山相比,更具神圣性,从各地移植迁徙的种种动植物,均具有非凡的品格:“且帝泽之旁流,复上昭而下漏。宜乎绝珠殊祥,骈至迭辏。潜生沼之丹鱼,萃育薮之皓兽。神爵栖其林,麒麟臻其囿。屈轶茂而黄荚滋,紫脱华而朱英秀。何动植之休嘉,表自天之多祐。”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徽宗恩泽滂湃,天下嘉木珍物荟萃阙下,也就是说,艮岳中的在在物什,皆是祥瑞,这是一座人间的仙山。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徽宗这个从“丛霄”降临人间的旷世祥瑞盘桓于此,即使人造的山,也有了仙品。曹赋虽然声言艮岳在祈求子嗣绵绵方面的意义,但是赋作主旨则是强调徽宗旷世的神圣品格:“今以一人之尊,大统华夏,宰制万物,而役使群众,阜成兆民,而道济天下。夫惟不为动心,侔于造化,则兹岳之兴,固其所也。而况水浮陆走,天助神相,凡动之沓来,万物之享上,故适再闰而岁六周星,万壑千岩,芳菲丹青之写图障也。”艮岳的出现,是由于徽宗出神入化的统治,使天下人咸被其泽,天人相感,祥瑞麇集。曹赋也和李赋一样,指出移来艮岳的物什,皆是祥瑞:“盖闻橘不逾淮,貉不逾汶。今兹草木,来自四方,原莫知夫远近。”曹赋在盛赞皇上方面比李赋略胜一筹:“天子神圣,明堂颁制,视四海为一家,通天下为一气。考其迹则车书混同,究其理则南北无异。故草木之至微,不变根于易地,是岂资于人力,盖已默然运于天意。故五岳之设也,天临宇宙;五岳之望也,列于百神。兹岳之崇也,作配万寿。彼以滋庶物之蕃昌,此以壮天支之擢秀。是知真人膺运,非特役巨灵而驱五丁。自生民以来,盖未之有。”草木禽兽,不分南北,均在艮岳生机勃勃,这种超越生活逻辑怪事的发生,乃是徽宗的神圣光辉使然,是上天对徽宗神性的认可,是国家祥和的瑞兆,是常态化的祥瑞,也是国家吉祥的写照。


高宗禅位后,隆兴二年(1164),太庙现十二茎灵芝,高宗兴奋异常,作序以记其盛,高宗如此大肆张扬,无非是为了告诫孝宗不能忽视他这位躲在幕后的政治老人。孝宗为此赋诗一首表明态度。针对此事,薛季宣写了一篇《灵芝赋》,赋作首先点出灵芝的出现是两位皇帝的融洽关系感动了上天,于是灵芝献瑞。也许作者明白这其实是一次政治事件,高宗通过祥瑞来暗示自己的政治存在,因此赋中这样解释祥瑞出现的原因:“和气致祥,允天子之慈孝;天施地产,诚圣人之达徳也。”赋对瑞芝的描写颇为详尽:“有茁者芝,有粲其房。不植不根,于殿之梁。轮囷扶疏,馨香有馝。紫色氛氲,交光晔日。歘腾龙而翥凤,追金相而玉质。焕耀宸居,清明帝闼。阅之者神惊,瞻之者目夺。一本同柯,支生十二。错地分州,蟠天列次。瞻彼日月,膺期嗣岁。亦有律吕,八音以谐。仙馆玉楼,光于泰阶。”这个瑞兆不仅模样神奇,十二茎还暗合尧舜时天下十二州,暗示了高宗父子禅让取法尧舜,其伟大和神圣亦如尧舜。不过,薛季宣也谈祥瑞不足恃,慈孝相谐才是天下的福祉:“乃若汉之宣、章,号称七制。仁民得天,休符接至。桓、灵何道,而产中黄之藏,有芝英之瑞也。由是言之,妖祥叵测”,“逮乎季末,谀辞麕至。鬼目呈符,菌宫贺瑞。岂……于惟我后,秉文之徳。昊天景贶,三辰耀色。虽无此芝,何损于治”。灵芝的出现具有不确定性,而且与帝王的品行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妖祥叵测。他的这段议论婉而多讽,不像是在讥刺高宗等迷恋祥瑞,更像是在娇嗔,所谓曲终奏雅,这在歌颂文学中是惯用的手法。
高宗时期也有一些赋借祥瑞书写赞美国家中兴,重新确定国家的合法性,如张昌言的《琼花赋》:“盖艳冶而争妍者,众之所同;而蠲洁向白者,我之所独。是以兵火不能禁,胡尘不能辱。根常移而复还,本已枯而再续。疑神物之护持,偏化工之茂育。抑将荐瑞于中兴,而效祥于玉烛。”琼花拔出流品的美质、枯而复生的坚韧,寄托着作者对国家民族的殷切期望。与此相类者,还有苏籀的《牡丹赋》、王灼的《朝日莲赋》、李纲的《后荔支赋》、李石的《栀子赋》、何麒的《荔子赋》等。
三、辞赋对王朝气势的塑造与渲染
王朝气势是统治者所塑造的国家精神和国家形象所焕发出的力量和威势。颂美辞赋表现的王朝气势不仅仅是作家个人的感知,它是代表意识形态在发声,是人们印象中的国家权力和治国理念的综合表现。最早用辞赋来表现王朝气势的赋作是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他夸张渲染上林苑和天子游猎场面,彰显汉武帝时期高度极权政治下雄视天下、凌厉飞动的国家品格。其后,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通过对照西都与东都的品格差异,使多欲之治与纯用儒术的为政差别更为形象生动。宋代辞赋继承这一传统,在都邑、典礼、山川地理诸赋中,对王朝歌颂的着重点是呈现在一定为政方略指导下的理想化的王朝气势。
北宋时期新学独尊期间出现的两篇表现汴都的赋作——周邦彦的《汴都赋》、李长民的《广汴都赋》,与南宋初期傅共描写临安的《南都赋》颇值得注意。周邦彦的《汴都赋》作于神宗年间,在当时似乎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他又在宣和年间重新奏上。可以说,这篇赋与徽宗时期社会文化对国家气质和品格的想象深相契合,因此才会享受到这份迟到的青睐。李长民的《广汴都赋》是基于当时徽宗大兴土木增饰汴京,是对周邦彦赋后都城出现的新面貌的补充描写。
《汴都赋》的总体结构是按照方位来描写汴京的形制,其对班固《两都赋》和张衡《二京赋》的互文性观照相当明显。比如班固这样表现长安的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傍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这种拥挤场面的展示显然是一种艺术夸张,无非是为了显示长安令人难忘的繁华景象,周邦彦则针锋相对地写道:“城中则有东西之阡,南北之陌,其衢四达,其涂九轨。车不理互,人不争险易,剧骖崇期,荡夷如砥。雨毕而除,粪夷茀秽。行者不驰而安步,遗者恶拾而恣弃。跨虹梁以除病涉,列佳木以安怵惕。殊异羊肠之诘曲,或踠蹄而折。”宋都汴梁的壮丽不减大汉的长安,可是人流车流井然有序,与长安拥挤不堪对比明显。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这是周邦彦对班固赋的误读,而是他有意识地在与班固、张衡赋的比较中凸显宋都的繁荣和秩序感。班固在对西都长安的描写中还强调了商业的畸形繁荣所导致的对国家秩序的破坏:“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乡曲豪俊,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连交合众,骋骛乎其中。”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说商业的发达导致处于社会底层的商人具有拟于公卿大夫的富贵;二是说社会财富的下移滋生出一个撼摇国家权威的游食阶层。张衡《西京赋》的相应描写似乎是对这段话的阐释。传统中国重农抑商,班固、张衡赋展示的就是背离儒家治国之道,本末倒置,以及由此导致的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和对朝廷权威的撼动。周邦彦显然读懂了班固们的用意,他在描写汴梁的商业繁荣时,没有忘记强调商人对社会秩序的恪守和国家对贫富悬殊的防范:“顾中国之阛阓,丛赀币而为市,议轻重以奠贾,正行列而平肆。竭五都之瑰富,备九州之货贿,何朝满而夕除,葢趋赢而去匮。萃驵侩于五均,扰贩夫于百隧,次先后而置叙,迁有无而化滞。抑强贾之乗时,摧素封之专利,售无诡物,陈无窳器。欲商贾之阜通,乃有廛而不税,销卓、郑、猗陶之殖货,禁乘坚策肥之拟贵。道无游食以无为,矧敢婆娑而为戏。”汴梁的商业是有序的,是置于国家计划和管理之内的,繁荣的大宋是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国度,一切都在朝廷的掌控之中。当然,周邦彦所理解的汴梁和国家的形象也不同于《东都赋》和《东京赋》那样的纯用儒术、人人恪守秩序的内敛型气质,而是既具有大汉气概又具有王道之治气质的形象,是对西都和东都的兼收并蓄,兼而有之,这是对新学治国理念的形象化图解,王安石变法追求的就是富国强兵和礼法治国,既要繁荣经济又要国家掌控。因此,商业的繁荣被赋予了国家强盛的含义,而不是传统儒家所理解的政通人和、风俗淳厚。对于汴梁的商业,周邦彦的描写可谓泼墨如云,不惟一般意义的商品,而是天下所有精美罕见之物,皆荟萃于阙下:“至于羌、氐、僰、翟,儋耳、雕脚,兽居鸟语之国,皆望日而趋,累载而至,怀名琛,拽驯兽,以致于阙下者。旁午乃有帛氎罽奭,兰干细布,水精琉璃,轲虫蚌珠,宝鉴洞胆,神犀照浦。《山经》所不记,《齐谐》所不睹者,如粪如壤,积乎内府。或致白雉于越裳,或得巨獒于西旅,非威灵之遐畅,孰能出瑰奇于深阻。盖徼外能率夹种来以修好,则中土当有圣人出而宁宇。”这不是普通的商业展示,而是仁风所向、万国来朝的场面,是仁政理想的全面实现,是战胜于朝廷的图景展现。传统的儒家对武力征伐持克制态度,班固和张衡对长安的描写都突出展现不仁不义的放肆杀伐,新学和新党人物则主张富国强兵,对武力是相当重视的,因此,周邦彦反班固们之意,描写了国家军事的强大:“若夫连营百将,带甲万伍,控弦贯石,动以千数。……材能蹶张,力能挟辀,投石超距,索铁伸钩,水执鼋鼍,陆拘罴貅。异党之寇,大邦之雠,电鸷雷击,莫不系累而为囚。于是训以鹳鹅鱼丽之形,格敌击刺之法,剖微中虱,贯牢彻札,挥铊掷,举无虚发。”国家兵强马壮,慑寇服远,所向披靡,因此,战胜于朝廷的理想被军事威慑取代了:“兵甲士徒之须,好赐匪颁之用,庙郊社稷,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群臣稍廪之费,以至五谷六牲,鱼鳖鸟兽,阖国门而取足。甲不解累,刃不离。秉越匈奴而单于奔幕,抗旌西僰而冉蚁伏;南夷散徒党而入质,朝鲜畏菹醢而修睦。解编发而顶文弁,削左衽而曳华服。逆节踯躅而取祸者,折简呼之而就戮。”国富兵强,蛮夷畏惧而称臣,犯大宋天威者,虽远必诛,这是在赤裸裸地宣扬霸权之道,甚至是认可野蛮的军事征服。新学的治国理念出入王霸之道,其影响下的王朝气势正如周邦彦的这篇赋展示的,具有允文允武、厚重儒雅、沉稳有力、雄浑飞动的气概。徽宗朝,前无古人的光荣感进一步发展,周邦彦得以重进此赋,他在《重进汴都赋表》中重申了新党执政带来的光荣和辉煌:“窃惟汉晋以来,才士辈出,咸有颂述,为国光华。两京天临,三国鼎峙,奇伟之作,行于无穷。恭惟神宗皇帝盛德大业,卓高古初,积害悉平,百废再举。朝廷郊庙,罔不崇饰;仓廪府库,罔不充牣;经术学校,罔不兴作;礼乐制度,罔不厘正;攘狄斥地,罔不流行;理财禁非,动协成算。以至鬼神怀,鸟兽若。缙绅之所诵习,载籍之所编记,三五以降,莫之与京。未闻承学之臣,有所歌咏,于今无传,视古为愧。”*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28册,第230页。大宋从开国以来憧憬的强国之梦终于实现了,新法的种种举措给国家带来了新气象,徽宗的自我作古的制礼作乐之举更使大宋富丽堂皇,庄严神圣。王朝的这种气质在同时代的张鼎丞《邺都赋》、王观《扬州赋》、王仲旉《南都赋》等山川地理赋中均有体现。
李长民的《广汴都赋》作于徽宗神化国家兴味正浓、丰亨豫大的国策得到充分贯彻之时。这篇赋所描绘的王朝气势较之周邦彦赋更强调其神圣性和所向披靡、自由挥洒的任性气质,因为此时的王朝拥有一个从神霄上界降临人间的皇帝,这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李长民对徽宗增饰汴都是这样理解的:“当国家之闲暇,肆乘时而增葺,遂跨三都,越两京,儗二周而抗衡。数其南,则神霄之府,上膺南极。伟殊祥之创见,恍微妙之难测。岁在丁酉,大阐真机,用端命于上帝,而彰信于群黎。爰设定命之符,妙以虫鱼之篆。继乾元之用九,参八宝而垂范。乃严像设,只奉兹宫。俨一殿以居上,总诸天而位中。灵妃上嫔列于西,仙伯天辅列于东。谔谔群卿,峨冠景从。”国家太平无事,一种神秘的、神圣的力量在支配着王朝,主圣臣贤,祥瑞遍地,对帝都的修饰处处焕发着迷人的、非人间的光彩,班固们担忧的本末倒置,周邦彦渲染的士农工商的秩序感,此时统统不是问题,没有担忧的必要:“阅夫阛阓,则九市之富,百廛之雄,越商海贾,朝盈夕充。乃有犀象贝玉之珍,刀布泉货之通,冠裳衣履之巧,鱼盐果蓏之丰。贸迁化居,射利无穷。览夫康衢,则四通五达,连骑方轨,青槐夏荫,红尘昼起。乃有天姬之馆,后戚之里,公卿大臣之府,王侯将相之第。扶宫夹道,若北辰之藩卫。”同样是商业描写,李长民感受到的除了激动人心的繁华、奢华,没有丝毫士大夫式的担忧,大宋进入了人们向往已久的极乐国度,一切的忧愁、苦难都消失了,天下苍生脱离了尘世的苦海,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和自由,于是,商业的繁荣和极尽所能的享乐被连接在了一起:“太平既久,民俗熙熙。观夫仙倡效技,侲童逞材,或寻橦走索,舞豹戏罴,则观者为之目眩;或铿金击石,吹竹弹丝,则听者为之意迷。亦有蜀中清醥,洛下黄醅,葡萄泛觞,竹叶倾罍,羌既醉而饱德,谓‘帝力何有于我哉’。”普天之下、率土之滨,都沐浴在祥和的光彩中,人们甚至忘记了这一切美好的根源所在,神圣的皇帝所赐予的浩荡恩德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样的国度,武力征伐是多余的:“故得朝廷清明,纪纲振举,威武纷纭,声教布濩。北渐鸭绿,南洎铜柱。深极沙漠,远逾羌虏。陆詟水怀,奔走来慕。雕题、交趾、左衽、辫发之俗,愿袭于华风;金革、玉璞、犀珠、象齿之贡,愿献于御府。”国家的神圣感染了周边,边鄙之人,纷纷望风向化,此所谓战胜于朝廷也。李长民所处的时代,国家在丰亨豫大政策的指引下,在缔造一个人间天国,一个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神圣美好的、曼妙而无敌的天堂,这一切的核心,就是徽宗和襄助他的新党人物如蔡京等。赋的结尾,作者为他们献上了庄严的颂歌:“穆穆大君,天所子兮。粤自丛霄,履帝位兮。体道用神,妙莫名兮。立政造事,亶有成兮。金鼎奠邦,神奸詟兮。玉镇定命,垂奕叶兮。天地并应,符瑞著兮。膺图合牒,千百禩兮。坐以受之,开明堂兮。三灵悦豫,颂声兴兮。元臣硕辅,侍帝旁兮。相与弼亮,守太平兮。运丁壬辰,化道行兮。”亦人亦神,亦人间亦天堂,雍容华贵,神秘莫测,金声玉振,文质彬彬,这就是李长民所要表现的王朝气势。令人感慨的是,在这个神的国度,邢居实的《秋风三叠》、李纲的《秋风辞》、晁补之的《江头秋风辞》、毛滂的《拟秋兴赋》、郑刚中的《秋雨》等等,却在不和谐地吟诵着沉郁悲怆的歌调,在一派溢彩流光的氛围中,金人渡河,二圣入北,王朝大厦颓然倾覆。
南宋在绍兴和议之后,高宗在具有新学背景的权相秦桧的帮助下,努力使风雨飘摇的小朝廷焕发出一些“国家”的气象。他们憧憬的是树立其顺天应人的合法性,并且具有一些列国朝贡的气派,他们向往和平,希望来自北方的强敌压迫能够减轻或者解除。他们对国家的想象简单而质朴,新党从前的那种发扬蹈厉的气概荡然无存。傅共的《南都赋》创作于这个憧憬宁静和平之梦的时期,也很准确地诠释了王朝的国家之梦*赋中有“堂堂元老,天子之师。弥纶其缺,辅相其宜。虎节阴符,张弛随时。斟六韬于帷幄,胜百里之熊罴。端绅笏而不动,安社稷于无期。与长江而表里,夫孰得而雄雌?”这是和议以后对秦桧赞美的统一口径,因此此赋应该创作于绍兴十一年(1141)和议达成之后。。在赋中,高宗被描绘成一个振衰起弊的大英雄,他应时而出,是国家民族的救星,没有开化的江南不仅被异端思想所主宰,而且风俗简陋堕落,是高宗的降临才改变了这一切,他君临江南的理由在于拯救苍生,解放可怜的灵魂,因而受到百姓的拥戴:“吴侬伧父,徭氓蜑户,如驹犊从,如婴儿慕。填郛溢郭,如饥待哺。如舜膻行,而民风鹜。”靖康之耻就这样被遮蔽掉了,由流亡者一变而为拯救者、解放者,高宗这一转身着实令人错愕,可谓华丽之极,精彩之极。与他的光辉形象互相辉映的,则是秦桧:“堂堂元老,天子之师。弥纶其缺,辅相其宜。虎节阴符,张弛随时。斟六韬于帷幄,胜百里之熊罴。端绅笏而不动,安社稷于无期。”国家太平的取得,除了皇帝的聪明英发、教化苍生、恩泽遍施外,还有丞相的旰衣宵食、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君臣二人,构成了缔造国家的元勋群像。像完整意义的王朝一样,这个朝廷也荟萃了四方之珍物,对天下拥有绝对的主权:“四方贡异,则有桂蠹范卯,玉簟琼支,乌孙之柿,大谷之梨,千年之枸杞,万载之肉芝,会稽之竹箭,吴江之莼丝,江瑶之柱,海鲨之鬐。登乎鼎俎,竞荐新之斗奇。黜驼峰于熊掌,鄙铎俗之貔狸。萍实如斗,莲耦若船。巴邛之橘,固蒂巢仙,如瓜之枣,辟谷引年。龙眼鸭脚,湖目鸡头。”这段对临安商业繁荣的描写被涂抹上拥有四方的象征意义。而且,这个朝廷也拥有完整的朝贡体系:“马乳来于西域,人面贡于南州。杨梅卢橘,乃果中之俗物;方红陈紫,实荔枝之无俦。剨象率舞,生犀可羁。猩猩之笑,狒狒之啼。秦之吉了,陇之鹦鹉,黑衣之郎,雪衣之女。孔雀之文,翠禽之羽,或能言而诵诗,或闻声而起舞。飞走之奇,夥不可数。朝献于上苑,夕贡于玉津。藏之于内府,守之于虞人。以供燕闲之玩好,而备赐于臣邻。”域外商品汇集南都,被理解为四方所献贡物,其大国之梦是何等迫切。但是,那个让赵构们噩梦连连的北方呢,作者这样写道:“我观其北,则龙舟之耀,析木之精。上腾魁杓,前列勾陈。帝居象焉,端如北辰。欃枪敛锐,荧惑销嗔。旄头先驱,风伯清尘。既偃武而修文,益亲仁而善邻。交驰乎玉帛之使,无爱乎南北之民。”面对北方,作者收起了中央大国的虚幻派头,主张要与北方睦邻,看来,在高宗们眼中,北方才是与他们地位对等的“国家”,其他地方,因为不能对他构成威胁,被视为藩属而已。
在典礼赋中,两宋之际王朝气势的转变也有明晰的印记。如刘弇的《元符南郊大礼赋》写得极其雍容典雅,为了突出国家的气质,作者大量堆砌生僻字,以至于时人都难以卒读;王洋作于南宋初期的《拟进南郊大礼庆成赋》气魄则小得多,他只是简单铺叙典礼的过程。
在两宋之际的新学独尊期间,其意识形态中的王朝气势由沉着弘毅向内收敛,由神圣而稳健转向平易而朴实,这种转变,既有国家局势的原因,更有政治学术的原因。王霸参用的新学和新党,在南宋初期,其果敢刚毅的锐气消失殆尽,重视权变的为政风格大行其道,其所憧憬的王朝气势自然也随之发生变化。
四、辞赋对圣王美政的歌颂
对于歌颂文学来说,对政治的献媚最爽利的手段当然是直接赞美帝王,以及他所推行的“美政”。当然,如果帝王的形象已经与辅佐他的“良弼”融为一体,如蔡京之于徽宗,秦桧之于高宗,对这些权相的歌颂也是必须的。
徽宗时期对圣王美政的直接讴歌如上引李长民的《广汴都赋》,其中描绘的举国狂欢的场面其实就是在图解丰亨豫大的国是,以及襄助此事的蔡京;在一些辞赋中徽宗被描绘成神仙下凡,这也是在歌颂他超过一切帝王的不同凡响之处。就现存文献来看,绍兴和议达成之后,对圣王美政的狂热歌颂就出现了。
对于江南一带飘摇不定的南宋朝廷最大的安慰,莫过于得到大金的和平承诺。在高宗的授意、秦桧的努力下,和平终于得到了。在秉持文化中心主义的话语世界里,这件事无疑面临着诸多理论上的尴尬和滞塞,御用或者希望被御用的文人,则必须开动才智,给这件事披上华丽的外衣,打扮得尽量体面些,以使传统话语系统可以接纳它。
立足于中央王朝朝贡体系的外交思维,与周边国家以对等或者低一等的关系来缔结和约是不可想象和难以容忍的。绍兴和议,如果高宗们没有非凡的勇气和异乎寻常的决心,恐怕难以达成,就当时的情势看,这是于国于民最为务实的选择,但是,这件事能否受容于传统话语体系,则需要相当的智慧,因为高宗必须对人们有个交代,而且必须交代得有尊严、有体面,不然天下汹汹,朝野横议,会使皇家仅剩的一点颜面扫地而尽。针对此事,文人们的“急智”着实令人佩服,他们提供了摆脱这种尴尬话语窘境的绝佳思路。黄公度的《和戎国之福赋》为此事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思路:“上圣图治,远戎请和。民获安而不扰,国膺福以滋多。俯亲庶俗之情,信行蛮貊;诞保有邦之祜,时戢干戈。”开篇点题干净利落,指出和戎是远人请求,皇恩浩荡,施与了金人和平。这就轻易把屈辱的缔约行为改变成一种符合朝贡思维的施恩行为。这种思维的转化,让人击节叹赏。作者是这样理解和戎的伟大意义的:“尝闻帝王盛时,不无蛮夷猾夏。治失其术,则咸尚诈力;御得其道,则悉归陶冶。”与战争相连的是诈力,只有政治失道才弃仁义而任诈力,才会兵戈连连,民不聊生。这几句,很轻松地把孟子有关仁政的论述附会到和戎的政举之上,意在说明和戎符合圣贤古训,推动和戎的高宗被打扮成了一位仁君。作者沿袭了西汉以来的对蛮夷的看法,认为他们不讲诚信,对蛮夷的方略无非是和与战,当今之策应该恩威并施,不可好战而矜能。而且怀柔远人是圣朝明君的首选,战争是不得已的行为:“所以事彼昆夷,果见周家之盛;会于戎子,因知晋室之兴。彼有汤后征南,宣王伐北,或隆肇造之业,或启中兴之德。虽曰奉天而致讨,岂不蠹财而伤力?必也礼怀远裔,道交邻国。”战争蠹财伤力,孰若礼怀远裔,道交邻国。和戎岂止是使国家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其意义是相当深远的:“毡裘气暖,行观塞草之长;沙漠气清,坐见边烽之熄。前古既远,后王不思,惟务力制,类非德绥。”古往今来,中央帝国边境上无休止的缠斗从此一去不复返了,高宗的功绩前无古人。边境的宁靖是多少代人的梦想,而今实现了:“侯空号于定远,将徒劳于贰师。闭玉关而谢质者,不闻世祖;罢朱崖而切谏者,无复捐之。”作者通过一连串的典实,暗示了种种史实和言论,汉代的出使域外的班超、没于匈奴的李广利、贾捐之的《弃珠崖议》,等等,意在为和戎之策在历史中寻找依据,而且,被动地规避战争也被置换为主动地选择和平。作者篇末点题,指出和戎是目前国家的最好选择:“殊不知秦帝击胡,必底乱亡之患;武皇征虏,迄成虚耗之危。上方敦宠泽以抚绥,冀狼心之辑睦,务使逊安而远至,蔑有兵穷而武黩。”滥用武力使生灵涂炭,甚至亡国,唯有和戎才是圣明之举。这篇精悍的律赋机智地、全面地、创造性地阐述了和戎的伟大意义,使其合乎传统话语体系的价值标准,这是对辞臣们宣上德以尽忠孝的最好诠释。
曾协的《宾对赋》是对黄公度《和戎国之福赋》的进一步发挥,然而近乎谄媚的慷慨陈词由于过度铺陈和肆意渲染,反而放大了黄公度等解释这件事的“急智”,使得其中的牵强附会一览无余。其实,历代的那些勇于献媚的弄臣总是自作聪明地把意识形态巧妙编织的话语弄得一团糟。曾协抛弃了黄公度的那些闪转腾挪的遁词,而是径直宣扬“和”比“战”好:战争是可怕的,灾难性的;和议昭示着和平,幸福。而其背后的诸如屈辱与尊严、正义与不义等等,都被他遮蔽掉了。这篇赋首先述及“古之兴王,必有武事以震叠海内,治金伐石,昭示万代”,然后铺叙战争的恐怖和破坏性:“及其介马而驰之,莫不魂禠魄夺,拳物喘汗,侧匿鼠扶,周章鸟窜,脯尸而食,薪骸以爨。”问题在于这是传统中国政权更替的规律性暴行,与当时来自金人的军事威胁风牛马不相及。如果这篇赋是反思权力出于暴力的可怕与可恶,那应该是一篇相当具有忧患意识和“现代性”的作品,因为近代以来的有识之士一直在为如何走出传统中国的权力更替怪圈而大伤脑筋。不过这篇赋产生的语境告诉我们,这是为和戎之策“开脱”的作品,作者不可能在那个时代讨论朝廷应该和平地交接国家权力的问题。作者指出,对武力的迷恋是不足取的:“壮武威之遐暨,而不知文德之远届;愤敌国之俱立,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就是说,曾协想从“王者无外”的角度来理解和戎,但是这个角度的前提是“有征无战”,就朝廷来说,是没有这种实力和地位的,它没有其他选择,战必败,和或可苟延残喘。接下来,作者从生灵涂炭着眼来反思战争:“厥初生民,浩浩其多,林林而群。虽形万之不同,俱一气之缊。”天生烝民,其生命权是均等的,君王驱之于锋刃之端,是不仁不义之举。赋中着力突出战争给苍生带来的苦难:“若夫勒卒万旅,出车千辆,劳徒众于绝域,逞雄心于一饷。缭绕重湖,间关迭嶂,屣弃稚耄,星驰丁壮。风劲路永,天凄野旷,既啜泣以相送,复望辕而凄怆。则或马负金勒,弓间锦,怅暴骨之何所,抚游魂而伪葬。天下之人既夕得哺,当寒未纩,辍衣食之所资,足军须于塞上。曾分攘之几时,已持兵而相向。霜积锋刃,星攒铠仗。肉饫野草,血殷川浪。系赤子以为俘,乃矜功而献状。杀不辜其几何,夫焉取乎霸王?”这段文字的立意来自贾捐之的《弃珠崖议》*贾捐之《弃珠崖议》曰:“当此之时,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今天下独有关东,关东大者,独有齐楚,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人情莫亲父母,莫乐夫妇,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此社稷之忧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饥馑,保全元元也。”(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卷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19页),其中的“伪葬”与贾文中的“虚祭”形成一种关联,都指战殁无尸,亲人只好行伪葬、设虚祭以致哀矜之情。汉武帝的征珠崖,主导权在自己手里,而绍兴和议,是我方乞和,二者有本质的差别,曾协把这段历史与当下附会在一起,无非是为了使眼下的和议体面一些。以义服天下则四海归心,天下大同,这是孟子反复申说的仁政王道思想,曾协如此阐释理解战争与和平,是背面傅粉之法,潜台词就是高宗具有内圣外王的素质,那些大启土宇的帝王如汉武帝、唐太宗等辈,在高宗面前是多么的黯然失色。
和戎的另一个成果是韦后南归,文人们从高宗纯孝的角度来歌颂这件事。当然,对高宗孝道的赞美除了要塑造他内圣的品格外,也是出于当时政治策略的考量。靖康之难以后,元祐党人高举道德保守主义的大旗,对新学和新党大加挞伐。高宗和戎的最大阻力,就是来自于这种高调的道德保守主义,他们的主张虽然不识时务,但是踞守着道德的制高点,杀伤力是相当大的。客观地说,由儒家的华夷之辨所衍生的民族文化中心的观念已经积淀为一种民族心理和民族思考习惯,无条件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妥协与和议,过度地张扬民族大义而视务实变通为出卖民族利益,对国家民族利益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就当时的情势来看,汤思退的看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他说:“此皆以利害不切于己,大言误国,以邀美名。宗社之重,岂同戏剧?今日议和,正欲使军民少就休息,因得为自治之计,以待中原之变。”(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九“癸未甲申和战本末”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68页)时人李石在《送丁子近赴陕西宣谕幕序》中也说:“儒者贵仁贱权,率以战伐为愧。一遇以仓卒之变,则曰我以仁义。未效而覆军杀将,以血肉赤子、丘墟城郭者相望,岂仁义罪哉,不知权故也。”(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05册,第338页),民族文化中心观念是道德保守主义的核心。南宋朝廷要在江南立足,就必须与北方的大金媾和;媾和,就必须对付道德保守主义的挑战,尤其是作为在野清议主力的道学党人。道学人士是狂热的主战派,他们绑架民族文化中心观念,以取得在和战之争中的舆论支持,置新学与新党于道义绝境,从而实现对权力的渗透与进驻。面对挑战,高宗也必须从传统观念那里找寻有利于自己的思想来与之抗衡。他找到了孝道,这是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德保守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念。在孝道与和戎之间,存在着这样的逻辑关联,徽宗、钦宗以及高宗的生母韦后等,被作为人质扣押在金国,与金人交战,就意味着把这些人质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对高宗来说,这就是不孝,这是为传统道德不能容忍的恶行;只有与金国交好,才能换得亲人的安全。因此,对高宗纯孝的赞美,其实就是对和戎国是的赞美。高宗强调孝道,是以高调的道德主义来回敬主战派的掣肘,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作为和戎之策重大成果之一的韦后南归,被赋予了高宗内圣外王品格的堂皇基调。韦后南归后被安置于慈宁宫,王廉清的《慈宁殿赋》是专门来揭示这件盛举的重大意义的。赋中纵笔铺排韦后南归引发的天下百姓的狂热之情:“乐极者或至于抃跃,感深者争先于驰骛。沈漻晏然兮屏翳收风,叆叇不兴兮丰隆霁怒。双闳敞兮如升,万室昂兮如诉。”这件事的象征含义就在于其背后暗示着和平的永远到来,金人威胁的彻底结束,当时朝野上下都以为和戎之后就万事大吉了。万民狂欢的场景,是在歌颂由高宗开创的新纪元的开始。赋中没有忘记交代秦桧等“良弼”对开启这个伟大时代的襄助之力:“若乃万寿诞日之辰,一人会朝之际。济济峨峨,群臣在位。皆辅皋而弼夔,过房杜兮丙魏。奉玉巵兮琼甓,展采仪兮文陛。皇帝躬蹈事亲之美,以独高于万世。进退礼乐,抑崇下贵。隆帝业兮亿载欢,祝圣人兮千万岁。”衮衮诸公为太后祝寿的场面构成了一幅朝廷印象的图画,高宗和秦桧等朝廷核心,以仁孝得到远人的尊重与慕化,以仁孝取得太平和繁荣,其修为是何等的高尚、英明、睿智、圣明!而且,这仁孝也是立国的根本,高宗们的圣举向外怀柔远人、向内感召痴顽,淳风俗、厚人伦:“皇帝躬蹈事亲之美,以独高于万世。进退礼乐,抑崇下贵。隆帝业兮亿载欢,祝圣人兮千万岁。然后敷兹睿化,遍于中下。尊卑模范兮盈里闾,膏泽渗漉兮盛王霸。工在衢,士在朝,而农在野。百度修明,万几闲暇。无有遐遗,睦如姻娅。四海安若覆盂,九有基如太华。”高宗孝道的感召下,不惟化干戈为玉帛,而且境内人人各安其所,法度修明,国家安如磐石。孝道之功可谓大矣。赋的结尾,作者献上了一曲赞美纯孝的颂歌:“苍苍高旻,覆下民兮。与物为春,泽无垠兮。一人孝至,通帝意兮。金石可开,不可移兮。”“光启中兴,祖武绳兮。绍复大运,法尧舜兮。旋泽曲轸,翕然顺兮。孝道克全,鉴上天兮。寿禄万年,其永延兮。圣人孝兮,感人深。责成贤辅兮,隽功克忱。”“财丰俗阜兮,写于熏琴。百姓克爱兮,诸侯克钦。亘万国兮,得其欢心。”作者如此对高宗的孝道津津乐道,不仅在于韦后南归的人伦典范意义,而且在于弘扬孝道本身就是高宗们为和戎之策找寻到的理论武器,更在于当时向内收敛的国家气势必须以高扬人伦的旗帜来重新定位形象、树立自信。
当时负命往北国请还梓宫、太母、天眷的曹勋创作的《迎銮赋》(十篇)是针对描绘迎接太后南归整个事件的十幅图画所作的解说性文字,写得比较简略,这十篇短赋的核心,也是歌颂高宗行孝道,为天下作则。
直接歌颂圣王美政的赋作还有葛立方的《九效》,这组模仿屈原《九歌》的诗篇把颂美的情感表达得曲尽情状,殊为难得。在《慈宁》篇中,他歌颂高宗和秦桧以过人的智慧和魄力达成和议,韦后得以南归,赋中大量的香草美人的描写给高宗们涂抹上一层神仙色彩,如此歌颂当道,说明作者谄谀的手段是何等老道。作者的颂美非常周到,在《强弱》篇中,他称扬高宗和秦桧审时度势以成和戎的功绩:“拯乱兮不如图治,锐进兮不如观势。以弱为强兮以予为取,边庭无犬吠兮息旗与鼓。”在《医国》篇中,他盛赞高宗收兵权的刚毅果敢。在《君臣》篇中,他颂扬秦桧及其同党等“贤人得位”,朝廷“芳菲菲兮满堂”。《自修》、《鸣穷》两篇是作者自赞之辞,说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眼界极高的世外之士。历史上的确出现过招徕隐士以妆点朝廷多士的荒唐君王,也曾有身在丘山而志存轩冕的所谓“山中宰相”,但是像葛立方这样自抬身价以献媚邀宠的斯文败类还是比较少见的。类似的作品还有叶子彊的《迎送神辞》也是一篇模仿《九歌》的作品,其目的也是在赞美当道。
文学发展的历史也是文学作品被不断审视的历史,那些能够反映人类普遍价值追求、唤起人类共通性灵的优秀作品最终融入到民族语言的有机整体中,有些更是被经典化了,成为反映民族心理与民族品格、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而那些在当时颇为行时的向权力献媚邀宠的作品,绝大多数被历史无情地淘汰了。两宋之际的新学独尊期间,在专制主义感召下,歌颂文学大行其道,诗赋篇章汗牛充栋,但是流传下来的却非常稀少。从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寻到专制政治与歌颂文学之间的因果关联。歌颂文学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无行文人向权力展示无限雌伏、无限谄媚的心理状态的工具,它其实还是极权政治寻找统治合法性、展示统治形象、规范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歌颂文学可以构造虚假的民意,图解政治意图,强化意识形态,以此向权力献忠纳诚。
[责任编辑渭卿]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 “宋代辞赋的社会文化学研究”(12BZW037)、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重点项目“宋赋整理及其文史哲学的交叉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培,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