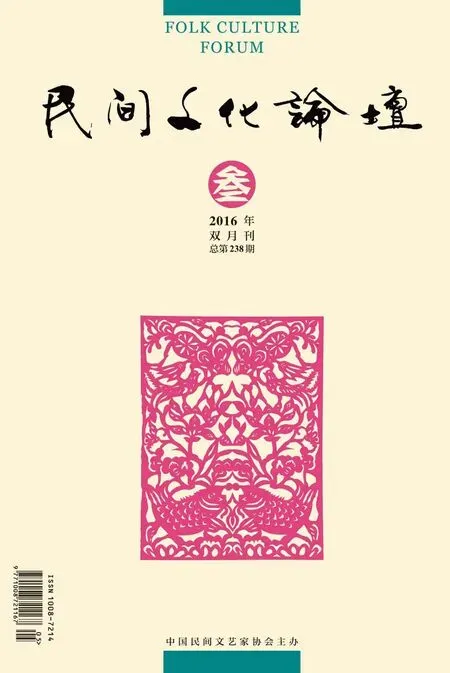从类型学、形态学到体裁学—刘锡诚《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补注
吕 微
从类型学、形态学到体裁学—刘锡诚《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补注
吕 微
刘锡诚先生《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有“类型研究与形态研究”一节,①刘锡诚:《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下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第896—903页。总结了21世纪以前中、外学者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学(分类学)与形态学研究方面取得的实绩,主要介绍了杨成志、钟敬文、艾伯华、丁乃通、刘魁立等人的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与李扬的民间故事形态研究;但于何谓类型研究(类型学)?何谓形态研究(形态学)?以及二者之间有什么异同关系?没有明确的说明,因为对此问题,中国学界一直都没能给出比较清晰的认识,以至于我在指导学生写作论文的时候,学生们也多次提出过类似的疑问。
由汤普森集大成的民间故事类型、母题研究和分类索引研究,与普罗普开创的神奇故事形态、功能研究,在研究目的和方法上有一定的差距。郑海等译汤普森《The Folktale》为《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②[美]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郑海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尽管与英文原著的书名不尽相符,却也没有违背汤普森民间故事类型、母题研究的分类学目的,即,尽管编纂世界统一的民间故事类型和母题分类索引,原本是为了成就针对民间故事叙事模式的类型研究和母题研究的类型学,但有时,编纂索引的分类学工作本身似乎已上升为唯一的目标。③汤普森“编母题索引的目的就是‘把构成传统叙事文学的成分都编排在一个单一的逻辑分类体系之中’”。户晓辉《内容与形式:再读汤普森和普罗普——“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对吕微自我批评的阅读笔记》,《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第12页。“汤普森自己把这个索引和分类比做一个大图书馆里的书籍。”同上引文,第12页。“汤普森把自己的母题分类比做图书馆里的书籍分类这一说法里已经可以自明地看出:他的母题分类的确是不管具体内容的纯粹形式分类。”同上引文,第15页(比较:“我们从汤普森把自己的母题分类比做图书馆里的书籍分类这一说法里已经可以自明地看出:他的母题分类的确是想从纯粹形式上对民间叙事的存在方式做出描述。”户晓辉《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0页)。“母题索引的分类系统。”同上引文,第15页。“母题分类体系。”同上引文,第15页。“AT分类。”同上引文,第16页。“汤普森把前人研究和收集的各种资料以及各种叙事体裁都尽量纳入自己的母题分类的动机和做法。”同上引文,第12页。“我们应该严格地把纯粹形式化的‘母题’概念限制在汤普森的母题分类体系里,换言之,只有在汤普森的母题分类体系里‘母题’才称成为‘脱语境’的纯粹重复的形式,出了这个体系,它们就可能被语境化或者被赋予内容,从而成为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体。”同上引文,第15页。“绝大多数母题分为三类。”户晓辉《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6页。
与汤普森的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母题研究一样,普罗普神奇故事形态、功能研究同样以民间故事的分类学为基础——普罗普和汤普森“他们都声称以林奈的生物学分类为榜样来研究民间文学”①户晓辉:《内容与形式:再读汤普森和普罗普——“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对吕微自我批评的阅读笔记》,《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第17页。“他们似乎都以林奈的生物学分类为榜样来研究民间文学。”户晓辉《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2页。“经过并非心血来潮,而是对材料进行精确和长时间研究的植物或动物分类法”“林奈最初的科学分类对植物学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俄]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页,第10页。——但是普罗普功能论形态学的“研究目的也不仅是植物学意义上的分类”。②户晓辉:《内容与形式:再读汤普森和普罗普——“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对吕微自我批评的阅读笔记》,《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第18页。按照普罗普自己的说法,“‘形态学’这个术语本身不是借自基本目的在于分类的植物学教程,也非借自语法学著作,它借自歌德”。③[俄]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79页。
我应该承认。“形态学”这个借自歌德……的术语,选择得并不很成功。如果选一个十分贴切的术语,那就不是用“形态学”,而是该用一个更为狭义的概念“组合”(composition)。④[俄]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87页。“普罗普……认为,他当年选择的‘形态学’这个概念不够贴切,更狭义的和更确切的概念应该是‘组合’。”户晓辉《内容与形式:再读汤普森和普罗普——“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对吕微自我批评的阅读笔记》,《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第19页。
由于“形态”是一个用以描述神奇故事在时间中生成叙事结构的概念——“普罗普认为功能不能离开叙事的时间”⑤户晓辉:《内容与形式:再读汤普森和普罗普——“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对吕微自我批评的阅读笔记》,《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第20页。“普罗普认为功能与叙事时间不能脱离。”户晓辉《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9页。——所以时间性的形态研究(形态学)的确不能等同于非时间性的类型研究(类型学)和分类研究(分类学),但与时间性的类型史、母题史研究却有异曲同工之妙(故而普罗普最终还是回到了《神奇故事的历史起源》上来⑥“在后来的著作中,普罗普自己也放弃了形式主义和形态学的分析,转而致力于对口头文学与神话、仪式和制度之间的关系作历史的和比较的研究。”[法]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第二卷,俞宣孟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128页。)。
尽管汤普森和普罗普在研究目的和方法上有一定差距,但二者的研究对象在分类学的意义上又是相互重合的,即作为普罗普形态学研究对象的神奇故事,只是汤普森民间故事分类学中的一种类型(我们通常称之为“幻想故事”),⑦“我们采用阿法纳西耶夫的故事集,研究自50号故事始,至151号故事终”“所谓神奇故事指的是阿尔奈和汤普森归在300—749号的故事”。[俄]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1页,第19页。所以说“普罗普的功能概念却已经是在AT分类法的基础上做的科学的或理论性的研究”,⑧户晓辉:《内容与形式:再读汤普森和普罗普——“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对吕微自我批评的阅读笔记》,《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第16页。是不会错的。无论汤普森的类型学还是普罗普的形态学,都以揭示民间故事叙事内容的叙事形式为研究目的(分类学是二者的基础),即无论民间故事形态学还是民间故事类型学,其研究的最终目的,都是民间故事因叙事内容的情节单元(汤普森称之为“母题”,普罗普称之为“功能”)的时间性或非时间性组合而生成的叙事形式(模式或结构,汤普森称之为“类型”,普罗普称之为“形态”)。二者之间的不同仅仅在于,“形态”“功能”是普罗普用以直观地认识民间故事在时间中如何讲述地被赋型且被赋予了使用价值(文本内意义①“在《神奇故事形态学》中,普罗普说:‘功能被理解为故事角色的某种行为,这种行为是从其行动过程的意义来确定的。’后来,在《神奇故事的结构研究与历史研究》一文中,他又明确指出:‘功能指的是从其对行动的意义的角度确定的角色行为。’”户晓辉《内容与形式:再读汤普森和普罗普——“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对吕微自我批评的阅读笔记》,《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第20页。)的概念,而“类型”“母题”是汤普森用以比较地认识民间故事在时间和空间中如何传承、传播地被赋型且被赋予了交换价值(文化间意义)的概念;所以,普罗普能够注意到功能组合的故事形态或叙事结构的时间性组合顺序,而汤普森则悬置了母题的组合在故事类型或叙事模式中组合顺序的时间性,而只考虑故事母题非时间性组合的类型模式问题。以此,故事形态学认为,故事的价值首先存在于功能结构的时间性组合即形态之中(这里暂时悬置了普罗普对《神奇故事的历史起源》的时间性研究,下同);而故事类型学认为,故事的意义首先存在于母题模式的非时间性组合即类型当中,其次才存在于母题、类型的时间性传承与空间性传播当中。普罗普认为,离开了时间性形态,离散的功能没有文本内意义;汤普森认为,即便离开了时间性、空间性,离散的母题和类型本身也还是有文化(间)意义。
以上就是我所理解的民间故事类型学研究与形态学研究之间的同与不同,其中的时间(包括空间)规定性,是区分二者的实质性指标,即二者都以认识故事内容的叙事形式为鹄的,但形态学是从文本内部肯定了故事内容-叙事形式的共时性时间性价值,而类型学是从文本外部肯定了故事内容-叙事形式的历时性时间性意义,同时类型学又从文本内部肯定了故事内容-叙事形式的共时性非时间性意义。②“戈德伯格发现,母题‘这个词指动机,一种驱动力,但《(民间文学)母题索引》中的许多条目却是静态的’。”户晓辉:《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72页。套用索绪尔的说法,类型学-分类学在否定了故事文本内部的共时性时间性的同时,肯定了故事文本外部的历时性时间性;而形态学在肯定了故事文本内部的共时性时间性的同时,却悬置了故事文本外部的历时性时间性。要而言之,类型学与形态学都以对文本之间非时间性的分类学为逻辑基础,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时间”概念之于民间故事叙事内容的叙事形式的不同用法。
普罗普的功能研究开创了对民间故事的内容进行科学研究的先例……普罗普的理论假设是这样的:凡神奇故事都是根据生活原型中的逻辑而展开其情节叙述的。普罗普有一句名言:在打开锁以前,小偷不会进门。③“偷盗不会发生在撬门之前。”[俄]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9页。反过来说,小偷不可能先进门再开锁。这就是因果的逻辑,也就是生活的逻辑。……生活现象中的行为是按照时间、因果的顺序发生的,因此,描述行为现象的功能概念也就必然会按照生活现象的顺序展开描摹生活现象的故事顺序。这就是说,我们只要把故事中描摹生活现象顺序的功能提取出来,那么功能就必然会证明生活现象的顺序和故事内容的顺序。④吕微:《母题:他者的言说方式——〈神话何为〉的自我批评》,《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第4页。
但李扬却通过文本内部的故事内容-叙事形式的非时间性规定性,质疑了普罗普关于神奇(幻想)故事的“功能时间顺序说”——鉴于神奇故事的“顺序永远是一个……功能(行为、行动、动作)如同它在书中被确定的那样,是在时间中完成的,不可能将它从时间中取消”,①[俄]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90—192页。“普罗普认为功能不能离开叙事的时间,功能的序列只能在单一的叙事时间里展开,而普罗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说神奇故事的功能顺序只有一个”②户晓辉:《内容与形式:再读汤普森和普罗普——“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对吕微自我批评的阅读笔记》,《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第20页。“普罗普认为功能与叙事时间不能脱离。”户晓辉《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8页。——的普遍有效性。
李扬认为,③李扬:《中国民间故事形态学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年。在生活的现象中,构成事件的各个要素固然按照时间和逻辑的顺序依次发生,但生活现象中的事件并不是一件接一件地单线发生的,而是诸多事件都同时发生。因此,一旦故事要描述这些在同一时间内同时发生的多线事件,而叙事本身却只能在一维的时间内以单线叙述的方法容纳多线事件,故事就必须重新组织多线事件中的各个要素,这样就发生了在一段叙事中似乎故事功能的顺序颠倒的现象,这其实是多线事件在单线故事中的要素重组。④吕微:《母题:他者的言说方式——〈神话何为〉的自我批评》,《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刘锡诚;《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下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第902页。
这就是说,民间故事的叙事形式的时间一维性,与民间故事的叙事内容的多线性事件之间的非统一性,造成了民间故事单一叙事“功能时间顺序说”的最终失效;以此,时间规定性,既是普罗普功能论形态学自我证明的条件,同时也是其自行瓦解的条件。
但是,对于当年参与了那场——从民间故事类型学和形态学角度——讨论“学科经典概念的新的理论可能性”⑤吕微、高丙中、朝戈金、户晓辉:《母题和功能:学科经典概念与新的理论可能性》,《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的诸当事人来说,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普罗普功能论形态学的叙事形式之时间性(康德所谓“先验感性论”)的有效性和无效性而导致的经验性问题,而在于以理论理性的分类学为基础的类型学研究与形态学研究能否“立足于‘他者’立场”“从歌手立场出发”⑥“这里凸显了立场的问题。可以差强人意地总结说,程式是一个更为立足于‘他者’立场的对民间演唱中特定现象的描述,而‘大词’则倾向于试图从歌手立场出发,发现歌手编创技巧和法则的努力。”朝戈金:《“大词”与歌手立场》,《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而不再遮蔽“他者的言说方式”⑦吕微:《母题:他者的言说方式——〈神话何为〉的自我批评》,《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哈贝马斯所谓“交往理性”论)的先验问题,即让“母题”“类型”“功能”“形态”等理论理性的经验性概念,能够被转换地应用于让主体间交互地表象其叙事实践的先验目的的自由意义(自由因果性),进而“国际民间文学研究领域最流行的两个关键词——母题和功能”,⑧户晓辉:《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7页。除了类型学与形态学的经验性理论使用的现实性,能否还有先验地实践使用的可能性呢?
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认识到的,由于“母题”“类型”和“功能”“形态”诸概念,只是主体理论地认识他者的经验性概念形式,而不是主体实践地自我命名的先验“概念”形式;故而,即便是在民间文学研究的人类学化乃至社会科学化的“人文”条件下,①“吊诡的是,吕微教授认为民俗学学科的学科危机源于民俗学从人文学术向社会科学转移这样一个重新定位,其中的核心问题在于人对自身存在形式即存在本质的理解。据我的知识,这恰恰体现了人文学术经历了20世纪社会科学化之后对学科人文性的回归。这种人文性又恰恰通过高丙中教授及其所援引的萨姆纳教授所高扬的‘人的生活’、甚至是‘个体的生活’得到彰显。在较早的研究中,高丙中教授亦把民俗学的人类学倾向与人文学倾向对立起来,似乎认为田野调查这种人类学方法属于社会科学倾向。问题在于,将此种强调归结为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或者在高度抽象的意义上强调民俗学研究的对象在于‘人的生活’,或许体现出民俗学者在当今学术界社会科学的强势存在的情况下不甘自弱,‘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心魔。”赵世瑜:《传承与记忆:民俗学的学科本位》,《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主体实践的先验目的的自由意义,也是不可能被直观到的,即,既不可能实践地证明经验性语境下的文本内容,也不可能实践地证明文本形式的经验性语境的自由意义。以此,在时间形式的经验性文本和语境条件下,“母题”“类型”“功能”“形态”诸概念,尽管能够或然地表象主体根据知性规律自由选择的任意性(功利性和道德性)实践,却不可能必然地表象主体根据理性法则普遍立法的自律性(道德性)实践。这样,理论理性的汤普森文故事类型学和普罗普故事形态学,一时间都陷入了从理论理性向纯粹实践理性的转换难题,如果故事类型学和故事形态学确有此内在的要求。②“当民间文学一旦被‘含’入民俗学,进而受到社会科学化提议的感召,民间文学反而会因为受到语境的束缚和规定而震惊地意识到自身自由的存在(自在),从而实现了从被规定了‘事实性质’的‘存在者’,朝向‘事情本身’的‘存在意义’,即民间文学朝向感受自身意义的现象学还原的‘存在的一跃’。”吕微:《民俗学:一门伟大的学科——从学术反思到实践科学的历史有逻辑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的西西弗斯——刘锡诚《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读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58页。
所谓“涵义”是我们从组织成一体的活动或符号中所阅读出的内容,是英语中的meaning;所谓“意义”是活动或符号所发挥的作用,显示的重要性,是英语中的signifi cance。③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57页。
这就是说,即便我们把民间故事的内容与形式置于时间性语境直观的经验性理论条件下,主体“根据模式,还可以自己按民间故事的规律编出无数个故事来”,④户晓辉:《内容与形式:再读汤普森和普罗普——“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对吕微自我批评的阅读笔记》,《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第19页。但我们从中得到的,就一定是出于自由因果性“动力”的自律性(道德性)实践意义(先验的而不是经验性的meaning),而不可能仍然是合于自然因果性“动机”的任意性(功利性或道德性)实践价值(经验性的significance)吗?
在英语、德语和法语中,“母题”这个词同时也有“动机”的意思,这似乎暗示出母题在情节中是一个促动因,当它作为一个概念存在或起作用的时候,它就分层地、有针对性地以及动态地发挥其功能。⑤户晓辉:《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81页。普罗普在此说的“组合”即英文的composition。贾放把这个词译为“组合”,朝戈金在翻译口头程式理论中的这个术语时把它译为创作或创编,指口头的、利用传统叙述单元即兴创编或现场创作。普罗普这里的composition与口头程式理论中的composition有相同也有不同。普罗普明确地说:“我将故事本身讲述时的功能顺序称为组合”,“对我来说确定民众以怎样的顺序来排列功能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说口头程式理论注意到所谓的民众在利用传统的素材和单元进行创作时有自由也有不自由(受“程式”的制约),普罗普在此并没有否认这样的自由或不自由,在这个意义上,他也是考虑并尊重民众的选择权的。①户晓辉:《内容与形式:再读汤普森和普罗普——“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对吕微自我批评的阅读笔记》,《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第19—20页。
以此,即使是在时间规定性的语境条件下,使用“母题”“类型”“功能”“形态”等经验性理论概念,我们能够“确定民众以怎样的顺序来排列功能”——表象了主体实践的“经验内容”(户晓辉)——从而“考虑并尊重民众的选择权”,但是,被表象的“民众的选择权”,却仍然是相对地“有自由也有不自由”,即或然地选择的“自由或不自由”的任意性实践,而不是必然地立法的自律性自由实践。
这里仍然有一个在什么意义上来作这种判定或者这个判断在什么意义上有效的问题。②户晓辉:《内容与形式:再读汤普森和普罗普——“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对吕微自我批评的阅读笔记》,《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第15页。既然人(民)被还原为自在者,或具有自在(由)维度的人,现代民间文学是否具有描述人(民)自在方式的概念呢?③户晓辉:《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7页。
吕微曾尝试区分汤普森母题-类型研究向主位开放的实践主观性(实践的主观间客观性),与普罗普功能-形态研究客位的理论客观性(实践的主观性),④“汤普森的母题不是像普罗普那样所设定的客位的主观形式,而是他所描述的主位的主观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汤普森的母题具有描述的客观性而不是设定的客观性。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两种主观性,一是主位的主观性,以汤普森的母题为代表,一是客位的主观性,以普罗普的功能为代表,两种主观性都有各自应用的客观价值。由于汤普森所描述的主位的主观性是一种以主位的主体间的一致同意和约定,即‘大家都可以重复使用这些母题’为前提条件的,因此,我们称这种主位的主体间的客观性为‘主体间性’,而不是普罗普的客位的主体性的客观性,即我们一般所说的主观范畴为客观事物立法的客观性。”吕微:《母题:他者的言说方式——〈神话何为〉的自我批评》,《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建构先验-交互主体的实践认识的理论路径;但户晓辉批评吕微的做法,仍然是混淆了概念的经验性理论使用的或然现实性,与先验地实践使用的应然可能性。
吕微说:“普罗普的关于功能顺序的理论,不属于纯粹的形式逻辑,而属于康德意义上的先验逻辑,也就是与内容相关的逻辑。”实际上,在我看来,康德的先验逻辑涉及的是[实践的]先验内容而非[理论的]经验内容,而普罗普的功能顺序理论既然涉及内容,那也是经验的内容,二者是有区别的。⑤户晓辉:《内容与形式:再读汤普森和普罗普——“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对吕微自我批评的阅读笔记》,《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第21页。
这就意味着,如若母题类型学和功能形态学的先验实践使用,能够表象交互主体叙事实践先验目的的自由意义,那么被表象的叙事形式必须能够必然(而不是或然)地思想道德性目的的先验内容(实践概念超验的内在使用),而不能满足于或然地直观道德性目的和功利性目的的经验性内容(理论概念的经验性内在使用)。①吕微:《民俗学:一门伟大的学科——从学术反思到实践科学的历史与逻辑研究》,“绪论 ‘内在的’和‘外在的’民间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9—42页。但是,母题类型学和功能形态学的理论视野中的民间文学叙事形式,能够承担起这样的重任吗?至少,以往的母题类型研究和功能形态研究,都还未表现出这种实践认识的现实性,以此,在2007年的讨论之后的2010年,户晓辉承认,把民间文学的“母题”“类型”“功能”“形态”等用作实践的概念,在民间文学研究的经典或者古典认识论的范式条件下,还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
描述现成对象的母题和功能是被抽掉了[现象学]时间因素的术语[除了在分类学的形式逻辑条件下,民间文学的类型学和形态学并没有被完全抽掉直观形式的时间因素——笔者补注],而[现象学地]描述存在方式的概念则是被还原到[现象学]时间之中的概念。②户晓辉:《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3页。从描述民间叙事现成对象的母题与功能追索描述民间叙事存在方式的母题与功能时,首先应该承认,毕竟,汤普森对母题以及普罗普对功能的研究和讨论,主要都是把它们当作描述民间叙事现成对象的[经验性理论]术语,而不是描述民间叙事存在方式的[先验实践]概念。③户晓辉:《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70页。在《内容与形式:再读汤普森和普罗普》一文中,户晓辉尚未完全立足于存在论的立场,而是仍然立足于认识论的立场:“我赞成丹•本-阿莫斯的说法,即‘母题’是学者的概念,是故事中存在的成分的符号,而非叙事成分本身。”户晓辉:《内容与形式:再读汤普森和普罗普——“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对吕微自我批评的阅读笔记》,《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第16页。迄今的多数学者都素朴地相信自己能够从民间文学研究的材料里直接发现和看出母题与功能的现成对象,似乎他们凭借经验就足以发现客观“存在”于研究材料里的概念。殊不知,这些学者从一开始就混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他们没有把描述民间叙事现成对象的母题和功能术语与描述民间叙事存在方式的母题和功能概念区分开来,这样,他们(包括汤普森甚至普罗普本人)讨论的实际上只是描述民间叙事现成对象的[经验性理论]术语,而不是描述民间叙事存在方式的[先验实践]概念。因此,他们不仅没有发现描述民间叙事存在方式的[先验实践]概念的答案,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提出这种[先验实践]概念的问题。我的研究将进一步揭示,母题和功能本来应该是为了描述民间叙事的动态存在方式的[先验实践]概念,但在长期的讨论中却一直主要被当作仅仅是描述民间叙事中的现成对象的[经验性理论]术语……以往描述现成(已完成)对象的母题和概念是被抽掉了[现象学]时间因素的术语,因而有[自然]形而上学色彩,我试图发掘的描述存在(未完成)方式的母题和功能是被还原到[现象学]时间之中的[先验实践]概念,因而有存在论的倚重。……即使母题和概念在迄今的民间文学学科里还不曾完全作为描述民间叙事存在方式的[先验实践]概念存在,我仍然要把它们作为这样的[先验实践]概念建立起来,并把这一点当作研究的目的之一。④户晓辉:《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2—154页。
实际上,2007年和2010年关于“学科经典概念的新的理论可能性”的讨论并没有能够继续下去,以此,从母题类型学和功能形态学的角度,证成民间文学叙事实践的自由本质——如果不是借力于先验论哲学的现象学方法——至今就还是一项尚未完成的实践性理论课题。但是,尽管,也许,我们仍然只能满足于通过母题类型学和功能形态学证成民间文学自由选择的任意性(“民众在利用传统的素材和单元进行创作时有自由也有不自由……普罗普在此并没有否认这样的自由或不自由”),却还是有学者另辟蹊径,从体裁学的角度,证成了民间文学普遍立法的自律性自由本质,从而不仅延续了2007年和2010年讨论的主旨,而且推动了这场讨论的继续扩展和深入。
从体裁(文类,Genere)的角度还原地认识民间文学自由本质的体裁学,原本就是肇始于格林兄弟,且发扬光大于马林诺夫斯基的民间文学“形式诗学”(鲍曼)①户晓辉:《民间文学的自由叙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97页。的学术传统。格林兄弟和马林诺夫斯基关于民间文学的神话、传说和童话的体裁三分法,②吕微:《“神话”概念的内容规定性与形式规定性》,《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1期。举世皆知。与汤普森基于叙事内容对民间文学的经验性理论分类学不尽相同,除了叙事内容的题材,格林兄弟和马林诺夫斯基关于民间文学体裁即民间文学叙事形式的(准)先验实践分类学,更注重民间文学诸体裁的意向性形式(先验体裁学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同与不同。即,如果我们暂时搁置(不是否定而是不设定)民间文学题材即叙事客体(对象)的经验性意向性内容(质料)——由于民间文学的叙事内容(母题和类型形式的叙事题材)总是在不同的叙事形式即不同的体裁之间流动,③“但当主人公失去原名,讲述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神圣性质——神话和传说转化成了故事,”[俄]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96页。因之叙事内容的题材就不可能被用作区分民间文学诸体裁的充分条件(可以用作区分民间文学诸体裁的必要条件)——那么,能够最终决定民间文学诸体裁之间相互区分的充分条件,就只剩下民间文学诸体裁如神话、传说、童话的先验意向性形式了。
简言之,在格林兄弟和马林诺夫斯基看来,神话、传说与童话这三种民间文学体裁的叙事形式之间能够被相互区分的先验标准就在于,交互主体先于民间文学题材的经验性意向性叙事内容,就已经对经验性意向性叙事内容之神圣、真实和虚构与否的先验意向性形式——巴斯科姆称之为“信实性”(belief)“取态”(attitude)④[美]巴斯科姆:《口头传承的形式:散体叙事》,收入[美]邓迪斯编《西方神话学读本》,朝戈金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页,第13页。Alan Dundes,Sacred Narrative:Readings in the Theory of Myth,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1984.——信仰地有所决断了,由此,神话(神圣性宗教信仰)、传说(真实性历史认知)与童话(虚构性审美游戏)才能够被相互区分为不同的体裁(而不是不同的题材)。借用康德的话说就是:神话、传说与童话的体裁间区别就在于,作为客体的经验性叙事内容与主体的信仰和非信仰形式之间不同的先验意向性关系(康德称之为“模态”,德文Modalität,英文modality⑤[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s.A74/B99-100,第67页;Immanuel Kant,Critique of Pure Reason,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Paul Guyer and Allen W.Woo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7,A74/B99-100,p.207.“‘模态’范畴有点特殊,它不是属于我们理解有关对象的条件,而是超越于一切对象之外,涉及我们认识的主体和对象之间的关系”,“模态范畴我们讲过它有一种特殊性,它不是我们的认识客体的可能性条件,而是这个客体与我们的认识主体发生关系的可能性条件,它不是用来规定科学中的某个客观对象的,而只是用来在认识论中表达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75页,第877页。),而这些不同的信仰和非信仰形式关系的先验意向性,是主体先于时间(语境)条件以及时间(语境)条件下的经验性叙事形式(类型、形态)和内容(母题、功能)而先验地为主体自身建构的,尽管主体的先验意向性形式最终要在时间(语境)条件下实现为经验性叙事形式和内容。以此,如果仅仅考虑民间文学的经验性意向性叙事内容(户晓辉称之为“现成对象”),而不考虑民间文学的先验意向性信仰和非信仰形式(户晓辉称之为“存在方式”),即不是“在交流的指涉内容之上和之外,突显出达成交流的方式”(鲍曼),①引自户晓辉:《民间文学的自由叙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97页。“表演理论更关注的是交流的形式而非内容。”同上引书,第97页。表演的“本质在于这种表演的形式而非表演的内容”,同上引书,第99页。那么,自格林兄弟——以及20世纪70年代国际民间文学界的实践转向(包括表演理论)②彭牧:《实践、文化政治学与美国民俗学的表演理论》,载《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1期。——以来一直于民间文学体裁(存在方式,鲍曼所谓“艺术表演”)研究所积累的先验实践分类学倾向,就将退回到汤普森、普罗普式的民间文学题材(现成对象)的经验性理论分类学。③吕微:《神话信仰—叙事是人的本原的存在》,杨利慧等:《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代序”,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但现在的问题是,即便我们已还原了先验实践分类学意义上民间文学诸体裁的先验意向性形式,但这样的先验意向性形式仍然可能是主体在“利用”经验性意向性叙事内容时,或然地选择的信仰或非信仰的任意性意向性形式——“民众在利用传统的素材和单元进行创作时有自由也有不自由,普罗普在此并没有否认这样的自由或不自由”,尽管“在这个意义上,他也是考虑并尊重民众的选择权的”——而不是必然地信仰的普遍立法的自律性意向性形式。但是,如果不能进一步还原出民间文学普遍立法的必然性信仰的自律性意向性形式——可称之为内在性信仰的先验意向性形式,以对应于外在性信仰和非信仰的先验意向性形式——我们就仍然无法自诩,民间文学是一门不依傍于其他学科的独立学科,即确立了自身发生与存在的无条件条件(所谓“安身立命”)的自我立法的先验基础的完善学科。④这里,我并没有区分学科对象与学科本身,而是视学科对象为学科本身的意向性相关项,以此,学科对象的起源也就是学科本身的起源,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以此,我们必须进一步确认,民间文学诸体裁或然地信仰和非信仰的任意性意向性形式,都必然包含着普遍立法的必然性信仰的自律性意向性,否则,民间文学就始终无法成就为一门以自身为(意向)目的(这是学科独立性的自我保证)且普遍合(法则)目的(这是学科完善性的自我保证)的现代性正当性学问,在最幸运的情况下,民间文学(根据民间文学诸体裁或然选择的任意性意向性形式)也只能满足于作为服务于其他学科目的的手段或工具的附庸学科。
但是这样一项艰难的任务,最终由户晓辉于2014年出版的《民间文学的自由叙事》一书在理论上完成了,即,惟当我们进一步悬置了民间文学诸体裁的任何外在地、或然地信仰或非信仰的任意性意向性形式,而最终还原到民间文学体裁内在地、必然地信仰的自律性意向性形式(无论信仰的神圣性神话也好,半信仰的真实性传说也好,还是非信仰的虚构性童话也好,都以对神圣性、真实性及虚构性叙事内容的相信即必然性信仰的意向性形式为前提,即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任何怀疑都建立在不怀疑的基础上”)——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民间文学的“纯粹体裁形式”或民间文学的“纯粹体裁性”——本身,我们才能够最终还原出民间文学实践的纯粹“形式意志”(Formwille,吕蒂)⑤户晓辉:《民间文学的自由叙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3页。的先验目的——以民间文学先验的、内在的普遍立法的必然性信仰意向性的“纯粹体裁形式”或“纯粹体裁性”本身为意向性对象的意向性目的(因为我们已经还原掉了民间文学的任何题材内容以及外在的诸体裁形式)⑥“形式就是目的,形式意志也是目的意志”“民间文学体裁叙事的表演行为不仅具有自身的形式,而且具有自身的实践目的。它不是为了其他目的或者服务于其他东西,而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形式或目的”。户晓辉:《民间文学的自由叙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3页。——的自由意义(民间文学的先验内容)。
这样,一旦我们悬置了民间文学的叙事内容及其或然性信仰和非信仰的外在性意向性的诸体裁形式,就只剩下民间文学体裁的必然性信仰的内在性意向性形式及其意向相关项——即以“纯粹体裁形式”或“纯粹体裁性”本身为目的的先验意向性对象或意向性先验内容,但这样的先验意向性对象或意向性先验内容一定就是民间文学“纯粹体裁形式”或“纯粹体裁性”的必然性信仰的内在性意向性形式自身的先验交互性,即,如果民间文学“纯粹体裁形式”或“纯粹体裁性”必然性信仰的内在性意向性是以语言的先验交互性为条件的,那么先验交互性的意向性就意味着语言对话的纯粹公共性,①内在性信仰因而也就是“内在的对话”。户晓辉:《民间文学的自由叙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6页。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没有私人语言”,以此,内在性意向性若离开了对话性语言的公共性条件即伦理上主体人格间的自由与平等,②户晓辉:《民间文学的自由叙事》,“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行为的公共伦理条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1—174页。就不可能有先验交互性的必然性信仰的内在性意向性本身③“口头语谈话本质上是某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召唤或呼唤”“口头性的要义在于保持开放性和对话性”“口头性就是对话性,是我对你的请求和要求。我邀请你来共同参与创作并欣赏民间文学的天才叙事行为,我从一开始就没有独揽这种体裁叙事行为的大权,我想和你一起分享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行为的审美快感和文学乐趣”“无论谁在表演,表演者的我总在寻找着听众的你”“民间文学……向所有人开放”“我即使有很大的权能,也无法垄断民间文学的体裁叙事行为,再高明的表演者(即使想)也不能阻止别人说与听民间文学的提出叙事行为。任何一个我(即使想)页无法独占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询问道创作权,(即使想)也不能剥夺任何一个你的创作权”。户晓辉《民间文学的自由叙事》,“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行为的公共伦理条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2—113页,第115页,第139页,第144页,第162页。——由于民间文学“纯粹体裁性”的先验交互性的意向性形式内在地指向了必然性信仰的“纯粹体裁形式”自身,所以必然性信仰的内在性意向就是主体(主观)间先验地设定的交互性意向性形式及其意向相关项(意向性对象内容或客体质料),由此而突显了民间文学必然性信仰的内在性意向性形式作为公共性对话的伦理性条件(民间文学的经典理论称之为“集体性”“口头性”)。于是,我们才幡然醒悟,所谓“民间文学”,不过就是主体的道德性先验人格(而不是人的经验性社会角色)④户晓辉:《民间文学的自由叙事》,“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行为的公共伦理条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1—174页。之间交互地负责任的“纯粹体裁性”的“纯粹体裁形式”的信仰叙事的“以言行事”(奥斯汀)。
鲍曼把责任(responsibility)当作界定“表演”的一个关键术语。⑤户晓辉:《民间文学的自由叙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97页。正因为民间文学体裁叙事的表演是一种公共的实践行为,所以,鲍曼才以卓越的洞见认为表演的本质在于为表演者和观众都赋予的责任。⑥户晓辉:《民间文学的自由叙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2页。责任之所以构成了表演的本质,恰恰因为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行为本身就是一种需要复数主体参与的伦理实践和道德行为,民间文学的文本实际上是一种公共表演的伦理实践和道德行为,因此,表演的集体性实际上具有公共特征,表演者和观(听)众在表演中都责任重大。正因为有了这种责任伦理,民间文学的体裁叙事行为才可能有[自律性而不是任意性的]自由。⑦户晓辉:《民间文学的自由叙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2页。
以此,我们才可以说,民间文学就是主体先验地、交互地、普遍地、自律地自我立法的必然性信仰的内在意向性的“纯粹体裁性”的叙事形式及其相关的叙事内容,即人与人(作为我们的我与你)的道德人格之间自由、平等地互信互爱的情感实践的审美游戏,因为,除了必然性信仰的内在意向性形式的“纯粹体裁性”叙事形式,再没有什么理由能够解释民间文学的无条件条件的自由本质了。任何功利性、实用性的理由可以解释民间文学题材的或然性叙事内容,也可以解释民间文学诸体裁的任意性信仰或非信仰形式;但是,都不足以解释民间文学体裁性的必然性信仰-叙事形式。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在主观上实然地强迫其他人自愿地加入到我与你即我们共在的合法则性、合目的性的民间文学的自由游戏当中;但是,即便没有人在主观上自愿地加入到民间文学的自由游戏当中,民间文学自由游戏的应然性原则在客观上仍然是必然地存在的。即,惟当每一个人不仅把自己视为目的,同时也把他人视为目的,不仅把他人视为实现自己的目的的手段,同时也把自己视为实现他人的目的的手段,亦即,同时视自己和他人互为手段和目的(自由的形式意志以自由的意志形式自身为目的,也就是每个人的自由意志交互地以每个人的意志自由为目的)的那一时刻,作为道德-审美的自由游戏的民间文学的任何或然性经验性意向性内容和外在性任意性意向性形式,在符合内在性必然性信仰的自律性意向性形式的原则条件下,①拉家是“你说我听,我说你听”“拉家,跟谁都可以拉家”“拉家没有观众”“拉家是双方随便聊,汇报是单方向的”“拉家是友好的”“有事就不拉家,没事就拉家”“拉家不是正式活动,拉家是随意的、不规范的”“拉家就是平常对话”。(西村真志叶:《作为日常概念的体裁——体裁概念的共同理解及其运作》,《民俗研究》,2006年第2期。)“人际交往难道不是应该平等交换吗?既然他们看重我们的知识背景,我们就不应该单方面索取村民的知识,而不贡献自己的知识!”(陈泳超:《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42页。)才必然可能(不是或然现实)地发生——回到上文所言“尚未完成的实践性理论课题”,在完成了对民间文学的“纯粹体裁形式”或“纯粹体裁性”的必然性信仰的内在性意向性形式及其意向性内容的先验还原之后,我们也就认识到了:只有把民间文学的母题类型学与功能形态学置诸“纯粹体裁性”的“纯粹体裁形式”的体裁学即先验实践分类学的理论视野中,“母题”“类型”“功能”“形态”等概念才有望从理论地直观民间文学“现成对象”的经验性概念,转换成为实践地认识民间文学“存在方式”的先验概念②“这实际上就是把‘类型’当作了描述具体文化或民族的民间故事存在方式的概念”“‘类型’是民间故事的存在方式,即民间故事以类型的形式存在”“偶然的采录更是体现了民间故事存在方式的必然性”“祁著的研究无疑让这些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重新存在了一次”“重新唤起了这些故事的存在,让它们在祁著中存在并且来和我们照面,而‘类型’不过是对这种存在和照面的一次总命名”“从名称上就可以直观出这类故事的存在方式”“这就极大地扩展了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存在空间”。户晓辉:《类型:民间故事的存在形式——读祁连休〈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民俗研究》,2007年第3期。——否则民间文学就会因其经验性意向性内容和外在性意向性形式与先验的内在性意向性形式与意向性内容的相互冲突而自行瓦解,而这也就是民间文学的无条件条件,借用康德的话说就是,民间文学必然可能(应然,不是实然)地发生与存在的理性原因或自由起源。
这样,在经历了一番对民间文学“存在方式”的先验条件的还原认识之后,中国民间文学界关于民间文学体裁或文类的内在性、必然性信仰意向性形式及其相关性对象的实践认识,就重新回到了由格林兄弟开创(但尚未完成)的“文本实践”③户晓辉:《民间文学:转向文本实践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对话的体裁叙事表演行为本身就是故事文本,文本的动态性不仅是表演造成的,而且直接体现为表演的动态性和变异性。”户晓辉:《民间文学的自由叙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6页。研究的实践研究传统,且在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就为先生一贯提倡的民间文学作为一门“文以载道”的人文学科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完善性)——《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写作目的就是为了证成民间文学作为一门“继承文以载道的传统,建构和发扬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诗学特点”①刘锡诚:《还原历史鉴往知来》,2016年3月1 5日。的独立、完善(完整)的人文学科——进一步奠定了形而上学的学理基础,即民间文学不仅仅是“言”(先生称之为“意识形态”②民间文学“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与悬浮于意识形态之上的民俗相区别”。刘锡诚:《还原历史鉴往知来》,2016年3月1 5日。),同时也是不同于经验性“语境中的民俗”的先验民俗语镜下“以言行事”的民间文学信仰-叙事的“纯粹体裁性”实践形式,以此,从类型学研究,到形态学研究,再到体裁学研究——惟有建立在先验实践分类学基础上的民间文学体裁学才能够不仅涵括了民间文学的经验性叙事内容(题材),也涵括了先验的或然性信仰和非信仰形式(诸体裁),更涵括了先验的必然性信仰形式(体裁性),即“不把整体分成部分”③户晓辉:《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70页。的真正的整体性(先验实践形式加经验性内容的整体性,而不是先验理论形式加经验性内容的整体性)研究——民间文学就将自身锻造成了一门不再依傍于旁人(如果你不想依傍于旁人,你自己就必须独立地拥有自我立法的动力学实践能力以及由此而生成的整体性认识能力)——既不依傍于历史学式的母题类型传承研究④赵世瑜:《传承与记忆:民俗学的学科本位》,《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也不借道于人类学式的功能形态研究⑤高丙中:《中国民俗学的人类学倾向》,《民俗研究》,1996年第2期。——而是拥有自身独立、完整(完善)的先验(实践)目的论和先验(认识)方法论⑥“民俗学研究的个案要看是否有助于回答民俗学是什么,或者说是民俗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在民俗学的学科本位问题没有理清之前,这个问题还不好回答。但我们如果心里没有这个学科自觉,不清楚自己做的研究对民俗学有什么贡献,这就会使研究意义大打折扣”“如果没有学科本位,缺乏问题意识的自觉性,不清楚自己要和谁对话,不明白做这个个案对民俗学有什么意义,这样的研究是没有太大价值的,这个学科也是没办法进步的”“这个问题强调的是民俗学者要修炼内功,它的繁荣不能太依赖外力。外力可以借助,但不能被它忽悠,否则就会有损于这个学科的生存”“我们的学科本位问题明确了以后,对资料的认识和对方法的思考,都可能会随着有一个新的开拓或提升”。赵世瑜:《传承与记忆:民俗学的学科本位》,《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即先验语镜的生活视界(并非经验性语境的生活世界)⑦吕微:《民俗学:一门伟大的学科——从学术反思到实践科学的历史有逻辑研究》,“民俗学的哥白尼革命——高丙中的民俗学实践‘表述’的案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527—541页。的实践科学,从而不再仅仅是为现代民族国家做文化正当性证明的向后看(传统),也不再仅仅是为现代阶级革命做政治合法性证明的向下看(现实)的经验性认识论学问,而就是为现代民主社会做日常生活合理性(通过民间文学体裁性信仰叙事的“理所当然”而)阐明的向前看(理想)的先验实践论的无用却有大用的学问。
目的王国是一个实践观念,它所要阐明的是,实际上不是真有,但通过我们的行为却可能成真的并与这一实践观念相一致的东西。⑧[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孙少伟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S.436,第103页,注释①。
在为先生《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第一版写的评论《中国民间文学的西西弗斯》中,我曾经讲到:“先生对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相互区分的立场是值得同情的,我将通过阐明自己的看法给予
I207.7
A
1008-7214(2016)03-0017-12
吕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