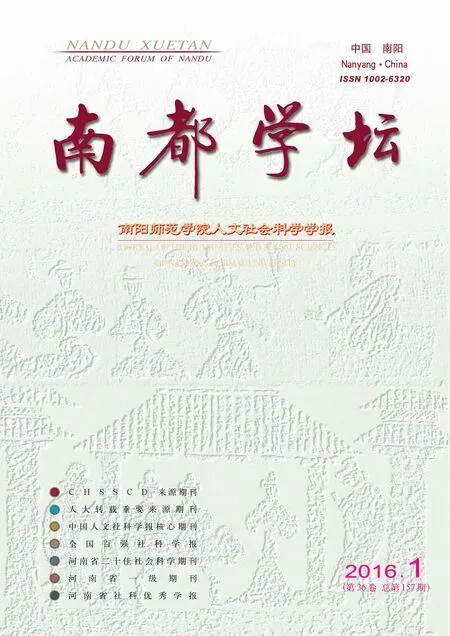《清实录》对上谕档的改纂——兼论史书与史料的关系
谢 贵 安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清实录》对上谕档的改纂——兼论史书与史料的关系
谢 贵 安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清代重要的史学典籍《清实录》,并非纯粹的史料,而是对上谕档等原始档案进行筛选、裁剪和编纂后形成的具有史料性的史书。《清实录》在改纂上谕档等档案史料时并非兼收并蓄,而是有取有舍;它在立意与点题、简化与删削、增加与完善、合并与熔铸、辨析与订误等主观思考和编纂活动中所采用的特有手法和编纂体例,蕴含着史官的心思和目的,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符合史书的性质范畴。因此,《清实录》与档案的关系应是史书与史料的关系,《清实录》是具有史料性和档案性的历史著作。
关键词:《清实录》; 上谕档; 改纂; 史书; 史料
关于《清实录》的性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将之视为档案范畴的①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文献学专业李建宏1995年所作的硕士学位论文《试论〈清实录〉的编纂》,是置于“档案文献编纂学研究方向”下的;南昌大学王立萍2009年所撰硕士学位论文《〈清实录〉的编纂理论与实践》,也是置于“档案学专业”之下。,也有将之视为史料的②陈高华、陈智超等将《清实录》看作清史史料的“基本史料”,见《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24页。,众多的史学史专著则将之视为史书即史学著作[1]143,146;[2]675。笔者以为,《清实录》(包括《宣统政纪》)既保留有浓厚的档案痕迹,又具有一定的史料属性,但更应视为史书。史料是客观的、原始的文献与档案,是纂述历史的依据和研究历史的材料,而史书则是具有明确的编纂动机、体例和书法标准的并具有主观色彩的历史著作。实录究竟是属于前者,还是倾向于后者,需要斟酌。笔者认为,《清实录》并非纯粹的史料,当然也不再是原始档案,而是对原始档案选择、裁剪和编纂后形成的具有史料性的史书,虽然载录了大量的谕旨和奏疏,但这些谕旨和奏疏是经过史官筛选、裁剪和改写的,不再属于原始史料。其实,在每部实录的前面,都有反映编纂者主观思考的《修纂凡例》,这些凡例阐述了编纂者对原始档案和史料的选择标准。如《清太祖实录·修纂凡例》载:“一、皇朝发祥之始书,自肇祖原皇帝以后世系备书。一、诸贝勒大臣等奉表劝进,上首登大宝,告天御殿,君臣朝贺仪注书。一、诸国进上尊号书……一、躬亲征讨翦灭群雄备书……”但它们并不涉及怎样具体裁剪和改写原始档案和史料。实际上,实录正是通过对档案的具体剪裁、合并和改写,使得它从史料上升为史书。《清实录》的史料大部分来源于档案,然而,却对档案进行了改写,它改写档案有其特有的手法和体例③迄今只有冯尔康:《〈雍正朝起居注〉、〈上谕内阁〉、〈清世宗实录〉资料的异同——兼论历史档案的史料价值》(载《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下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23—629页)和王素兰:《〈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研究》第四章“奏折的文献价值”之第二节“《清实录》与奏折的对比”(华东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有所论述,且与本文对象并不完全一致。。下面逐一讨论。
一、立意与点题
作为史书的《清实录》,在处理杂乱无章的档案时,为了确立主题,常常在叙述时开门见山,将主语径改为皇帝,或将奏疏归纳主题置于奏疏之首,于是产生了画龙点睛之效。
第一,将主语确定为皇帝,树立实录为皇帝立传的意识。上谕档的开头一般都是“内阁奉上谕”,而《清实录》无一例外地都将这句话改为“上谕内阁”。如《仁宗上谕档》载:嘉庆九年二月初七日,内阁奉上谕:‘朕恭阅皇考高宗纯皇帝乾隆三十一年《实录》……’”[3]第9册,37这段史料被《清仁宗实录》卷一二六“嘉庆九年二月丁卯”条改写成:“谕内阁:朕恭阅皇考高宗纯皇帝乾隆三十一年《实录》……”《仁宗上谕档》载:嘉庆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内阁奉上谕:“朕前因跸路经过地方,直隶办差官员过多,曾屡经面谕该督等,不得纷纷调派。”[3]第9册,27《清仁宗实录》卷一二五“嘉庆九年正月丁巳”条记载了这段内容,但将“内阁奉上谕”改成了“谕内阁”。档案原件作“内阁奉上谕”,主语是内阁,而《实录》改作“谕内阁”,主语是皇帝,反映了史臣在纂修实录时,考虑到了实录的对象和主体问题。《道光上谕档》载:“道光元年十月二十四日奉朱谕:‘朕恭阅嘉庆五年皇考《仁宗睿皇帝实录》……’”[3]第26册,448-449《清宣宗实录》卷二五“道光元年十月辛丑”条,将“奉朱谕”改为“谕内阁”。档案中的“奉朱谕”的主语是内阁,在《实录》中则被改成了“谕内阁”,显然也注意到了实录叙述的主体是皇帝而非内阁。《同治上谕档》载:“同治二年四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礼部奏,朝鲜国王李昇遣员以先诬未尽昭雪,请将谬妄书籍,恳恩刊正……”[4]第13册,172《清穆宗实录》卷六四“同治二年四月乙未”条亦将“内阁奉上谕”改为“谕内阁”。
第二,归纳奏疏主题,置于奏疏之首。嘉庆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有一份档案开头作:“内阁奉上谕:朕恭阅皇考《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三年八月钦奉谕旨:‘贤良大臣之子孙,已登仕籍者固多……’”[3]第5册,146而《实录》在录入这段谕旨时,略作了修改:“甄录贤良后裔,谕内阁:朕恭阅皇考《高宗纯皇帝实录》,乾隆三年八月钦奉谕旨:‘贤良大臣之子孙,已登仕籍者固多……’”[5]卷六二,“嘉庆五年三月辛巳”显然,“甄录贤良后裔”这句话是史官增加的,属史家连缀之文,意在提示这段奏疏的主题。嘉庆五年八月十二日的一份档案,一开头是:“内阁奉上谕:朕恭阅乾隆六年《实录》,内开钦奉谕旨:‘知府一官,承上接下,为州县之表率,诚亲民最要之职也……’”[3]第5册,398而《实录》则作了改写:“命督抚甄别知府。谕内阁:朕恭阅乾隆六年《实录》,内开钦奉谕旨:‘知府一官。承上接下,为州县之表率,诚亲民最要之职也……’”[5]卷七二,“嘉庆五年八月壬戌”“命督抚甄别知府”,也是实录纂修官为本段谕旨做的概括。《道光上谕档》载:“道光元年十月二十四日奉朱谕:‘……承平日久,文恬武嬉,各营伍将弁,往往自耽安逸,竟不以操练为事,而该管上司又复不加察查,以致日渐废弛……’仰见我皇考圣虑深远,有备无患之至意……若不实心操练,仍视为泛常,经朕觉察,或随时看出,决不宽恕,用副朕安不忘危,保卫民生之至意。”[3]第26册,448-449《清宣宗实录》卷二五“道光元年十月辛丑”条在记载此史料时,前面加上了“命整饬内外旗营训练”一句,为原始档案所无,在此起“开题”或“题眼”的作用。这说明《清实录》并非完全的史料汇编,而是经过史家改动了的史著,蕴含着史臣的心思和目的。
二、简化与删削
第一,简化。《清实录》改纂档案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化繁为简,简明扼要。《乾隆上谕档》载:“大学士臣于敏中等谨奏:‘前奉谕旨令主事门应兆恭绘《开国实录》一份,图内字迹应派员缮写,令[今]臣等谨拟派内阁中书德宁、爱星阿、德成、常明缮写清字,军机处行走中书范鏊、程维岳、杜兆基、关槐缮写汉字,内阁中书三官保、和绷额、舒兴阿、明善缮写蒙古字,供在南书房,敬谨缮写,以昭慎重。理合奏明,谨奏。’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三十日,奉旨:‘知道了。钦此!’”[6]第9册,553此事《清高宗实录》卷一○七五“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乙卯”条改写成:“大学士于敏中等奏:‘前奉谕旨令主事门应兆恭绘《开国实录》,图内事迹,应派员缮写。拟分清字、蒙古字、汉字,各派中书四员,在南书房恭缮。并轮派懋勤殿行走翰林一人入直,照料收发。’报闻。”这可以说是对档案进行了简化,用“派员缮写”代替了众多的人名,用“报闻”代替了“奉旨,知道了”等语。此外,《清实录》还将两条以上的文件或档案,融贯起来,用简明扼要的语言表述。关于裘行简死后其子元善受到恤赏的情况,《嘉庆上谕档》所载较繁:“嘉庆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奉上谕:胡钰奏原署直隶总督裘行简由北运河履勘各工,行至三河头地方,于二十六日身故等语,实属大奇丧。行简究竟系何病症,何以猝然竟至不起,该道既由静海县驰赴该处,则裘行简患病身故情形,必当深悉。着胡钰即行据实覆奏,不可稍有隐讳。将此传谕知之。军机大臣遵旨传谕天津道胡钰。”[3]第11册,758-759该档案又载:“查裘行简之子裘元善系监生,于戊午科顺天乡试挑取誊录,充补实录馆誊录,议叙盐大使,现在候选。臣等谨于拟写谕旨内将裘元善赏给举人。谨奏。”[3]第11册,759而《清仁宗实录》卷一六七“嘉庆十一年丙寅九月壬申”条,对此数段史料化繁为简,使行文简明扼要:“予故侍郎衔署直隶总督裘行简祭葬如总督例,谥恭勤;赏其子元善举人,一体会试。”这样一来,文字显得简明扼要。
第二,删削。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理论中,常有“史书繁简”的讨论,有不少人主张繁简适当。档案作为最原始的文件,内容具体而庞杂,连篇累牍,过于冗长,于是实录在收录档案时,做适当的删削。乾隆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大臣们在查阅郭琇参劾明珠的原疏“恭阅《实录》内,亦未载有全文”[6]第7册,192。所谓“未载有全文”,表明当时实录是记载了郭琇参劾明珠的奏疏,但却不是原疏,而是做过裁剪的。再如《同治上谕档》载,同治三年八月十二日内阁奉上谕:“国史馆奏遵保在馆出力人员分别开单请奖一折,本年该馆恭缮《宣宗成皇帝实录》黄绫本全书告成,各该员等数载以来尽心缮校,尚属著有微劳,自应量予奖励。”下面是长长的奖叙名单:
署镶黄旗汉军副都统奕庆,著交部从优议叙。内阁侍读庆钊、文堉均著以知府不论双单月,归于各项正班间用,仍在任候选;文堉并赏加道衔。检讨赵新,著交军机处记名,遇有道员缺出,请旨简放,先换顶戴。编修车顺轨,著赏加翰林院侍读衔。内阁侍读福年,著以知府不论双单月,遇缺即选,仍在任候选。长任御史孙翼谋、谭钟麟,均著作为历俸期满。左中允何廷谦,著赏加翰林院侍读衔。翰林院侍读文奎,著遇有升缺,由吏部题奏,即行升用,在任候选道。内阁侍读英廉,著以道员不论双单月,归正班间选,并赏加盐运使衔……蒙古誊录官廉樾等四员,均著先令在理藩院学习行走,作为理藩院议叙班笔帖式分缺,先选用拣发。甘肃道员苏彰阿,著赏加随带二级。户部银库员外郎英祥等二十一员,均著交部从优议叙。供事候选县丞刘赐龄等三十四员名,均著照所请给予奖叙。余依议。该部知道。单三件并发。钦此![4]第14册,284-286
这段字数约有1200字,可见原始文件的烦冗程度。对此,《清穆宗实录》作了大刀阔斧的删削,作:“以国史馆补缮《宣宗成皇帝实录》黄绫本告成,予清文总校等官署副都统奕庆、翰林院编修车顺轨等,加衔升叙有差。”[7]卷一一二,“同治三年八月庚辰”从史料价值来看,这则上谕显然要大于实录。但是,实录是经过史官主观过滤了的史书,对原始史料作了熔铸和剪裁,不再是完全原始的史料了。
第三,舍弃。档案是《清实录》撰著的基本依据,但实录并非简单的档案汇编,而是有取有舍的。《清实录》“取”的部分,在历朝实录的《修纂凡例》中已经列举,兹不重复。本处列举一些档案有而为实录舍去的事实。《乾隆上谕档》载:“(乾隆五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恭查《圣祖仁皇帝实录》共三百卷,业经恭进过二百八十一卷,尚有十九卷未进。今自十月二十四日起,除十月三十日恭值圣驾诣坛斋宿不进外,每逢双日进呈一卷,于十二月初四日可以进呈完竣。谨奏。二十三日。”[6]第13册,546此条档案史料,《清高宗实录》相应部分并未载录,表明可能舍去。《咸丰上谕档》载:“咸丰二年五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前因恭纂《宣宗成皇帝实录》,已进至道光十五年,降旨将在馆官员及誊录供事等交部议叙,兹据监修总裁等将在馆尤为出力人员,分别奏请,自应优加甄叙,以励勤劳,所有提调官内阁侍读学士文惠,翰林院侍读将元溥,着遇有升缺,先行题奏;兼提调编修葛景莱,着遇有应行开列升缺,开列在前请旨;总算官太仆寺卿廖鸿荃,着交部从优议叙;编修龙元僖,本系开列在前人员,着以应升之缺,即行升用;编修赵畇着以应升之缺,开列在前请旨……议叙捐职县丞衔徐芝,及未经掣签之供事张辉、方铨、陈松、杨瑞琛、吴嘉禾、赵棠、张澍,俟掣定职衔后,着一并分发各省,遇缺即补。余依议,该部知道。钦此!”[4]第2册,192-193这一长段文字约760字,因为过于冗长,而为《清文宗实录》所摒弃。这说明实录对档案史料并非兼收并蓄,而是有取有舍的。
三、增加与完善
上谕档等档案材料有时散乱无序,《清实录》在采用时,为了使一个历史事件表达完整,还采用了档案以外的史料来补充叙述。
第一,实录在改写档案时,常根据事实,加上档案所载事件的结果,而这些结果,是档案往往不载的。《乾隆上谕档》载:“乾隆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朕由吉林至盛京,周览山川形胜,敬稽《实录》所载,仰见列祖缔造艰难,维时宗室诸王,克奋忠勤,功成百战,开国翊运之勋,彪炳简册,深切景念。思盛京为龙兴重地,国初诸王,功烈懋著如此,并宜建祠,以酬旧勋而示来许。此地现有怡贤亲王祠,应将太庙配享之通达郡王、武功郡王、慧哲郡王、宣献郡王及礼烈亲王、饶余敏亲王、郑简亲王、颖毅亲王一并崇祀,即命曰贤王祠。令所司春秋致祭。应行典礼,该部详议以闻。祠内碑亭,可移于正中,镌勒此旨,永昭我朝宗功元祀之钜典。钦此!详议以闻,以上发抄全旨发刻。”[6]第2册,762《上谕档》到此为止,而此段史实,《清高宗实录》卷四七三几乎全载,但删去了“钦此”这样的套话以及“详议以闻,以上发抄全旨发刻”等语,并在后面还加上了此事的结果:“寻议:盛京怡贤亲王祠,正宗五间,请于室内分设三龛,每龛安奉三位。中龛,中奉通达郡王,左武功郡王,右慧哲郡王。左龛,中奉宣献郡王,左礼烈亲王,右饶余敏亲王。右龛,中奉郑简亲王,左颖毅亲王,右怡贤亲王。每龛各设一案,每案用羊一、豕一、果实五盘、尊一、炉一、镫二。每位爵三,素帛一。钦定祠名、上谕碑文及神牌清汉字样,交内阁、翰林院缮写,送盛京工部制造镌刻,移建碑亭,及祠内所供龛、案、尊、爵、炉、镫、帐幔,并交敬谨办理。每岁春秋二季,令奉天府府尹承祭。读祝、赞礼,用盛京礼部人员。神牌入祠日,先期开列盛京五部侍郎职名,奏请遣员读文致祭。从之。”[8]卷四七二,“乾隆十九年九月甲午”这就将档案的个案性和零散性,变成了史书应有的连续性和条理性了。《咸丰上谕档》载,咸丰六年十二月初四日内阁奉上谕:“庆连奏‘赏需缎匹,请饬部筹款解办’等语。实录馆全书告成,应赏缎匹,既据该织造奏称,未能依限解交,应如何折赏之处,着户部酌议(其)[具]奏。钦此!”[4]第6册,349此事《清文宗实录》卷二一四“咸丰六年十二月丁亥”条亦载此段史料,删去了套话“钦此”,加上了实际性的处理结果:“寻奏:应赏缎匹,议以现存杭细夏布抵放,毋庸另议筹款。从之。”
第二,实录除了增加结果外,还常常增加具体内容。《咸丰上谕档》载,咸丰二年三月初二日内阁奉上谕:“我朝列圣相承,山陵礼成,恭建圣德神功碑用垂不朽。我皇考宣宗成皇帝,临御天下三十年,深仁厚泽帱载弥纶,时敕几康,躬行节俭,举凡制治保邦之要,悉本忧勤惕厉之心,洵足媲美前徽,昭兹来许。乃圣怀谦抑,遗训谆谆,不得建立丰碑,颂扬功德。泣读慈谕,曷敢有违?伏念我皇考功德之盛,天下臣民共闻共见,况《实录》《圣训》,炳若日星,朕即竭虑阐扬,讵能仰赞万一。兹当慕陵奉安大礼告成,祗承先志,不敢建立圣德神功碑,谨述感恩哀恋之忱。含泪濡毫,撰成慕陵碑文一篇,用志孺慕,并当敬谨书写,即镌于隆恩门外碑石,以垂永久。我皇考在天之灵,定邀默鉴也。钦此!”[4]第2册,82《清实录》删去“钦此”后,还加上了碑文的具体内容:“碑文曰:皇考宣宗成皇帝御极之初,首戒声色货利,垂训谆谆。临莅日久,圣衷弥笃,骄奢永戒,而心虞或放,勤俭时操,犹力恐未坚。迨辛卯岁,重卜龙泉吉壤,一切规模,悉从俭约。并圣制诗章以垂法守,崇俭德,训后世,可谓至且尽矣。我皇考孝思不匮,谓斯地不独龙脉蜿蜒,且咫尺昌陵得遂依依膝下之素志。岁在戊申春三月,上恭谒诸陵,至龙泉峪大殿,召子臣同恭亲王奕至御座傍,命读朱谕,藏于殿内东楹。盖圣意深远,默定陵名,现已恭镌在石碑坊南北面,遵遗训也……敬卜于咸丰二年壬子春三月二日丑时。恭奉宣宗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成皇帝梓宫,安葬慕陵,以孝穆温厚庄肃端诚孚天裕圣成皇后孝慎敏肃哲顺和懿熙天诒圣成皇后孝全慈敬宽仁端悫符天笃圣成皇后祔。含泪濡毫,以志永慕云尔。”[9]卷五五,“咸丰二年三月壬子”这篇长达810字的碑文,应该是从御制文集中搜集来的,为《上谕档》所无,因此,《清实录》实际上是将两种史料加以整合后形成的文本,是史学工作者主观心智努力的结果。
第三,加字。《清实录》在改写档案时,为了叙述明白晓畅,有时候增加文字。如《咸丰上谕档》载,咸丰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许乃普着充实录馆总裁官,罗惇衍着充副总裁官。钦此!”[4]第3册,460而《清文宗实录》卷一一六“咸丰三年十二月丙申”将此条改写成:“命刑部尚书许乃普为实录馆总裁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罗惇衍为副总裁官。”《清实录》增加了表明身份的“刑部尚书”和“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上谕档载:咸丰四年二月十一日,内阁奉上谕:“工部尚书赵光为实录馆总裁官,彭蕴章着充副总裁官。”[4]第4册,43《清文宗实录》卷一二一“咸丰四年二月庚辰”将此改写成:“以工部尚书赵光为实录馆总裁官,兵部左侍郎彭蕴章为副总裁官。”《清实录》增加了“以字”和表明身份的“工部尚书”“兵部左侍郎”。类似的例子还有《咸丰上谕档》载,咸丰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内阁奉上谕:“花沙纳着充实录馆总裁官,穆荫着充总裁官。钦此!”[4]第4册,306而《文宗实录》卷一四九“咸丰四年十月庚申”条增改作:“以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实录馆总裁官,吏部右侍郎穆荫为副总裁官。”花沙纳前增加了“吏部尚书”,穆荫前增加了“吏部右侍郎”,信息均更具体,表述更为清晰。
四、合并与熔铸
第一,合并。《清实录》对档案的改写,有一种方式便是进行合并和拼合。《德宗实录修纂凡例》提出:“奉旨查询之件,当时未及奏覆者,应查后文;有豫载者,则书‘寻奏’云云,有应追书者,则书‘先是’云云。”这条凡例道明实录修纂时,一般是结合前后的档案文件综合考虑和叙述。其标志性的用语是“寻奏”和“先是”等。如《清圣祖实录》卷之六载:康熙元年二月庚午,“先是,平西大将军平西王吴三桂、定西将军内大臣公爱星阿等,奉命征缅。两路进兵,于顺治十八年十一月初八日会师木邦……滇南平。十二月初十日,大军凯旋。吴三桂、爱星阿等汇疏上闻。得旨:‘览王等奏,大兵进抵缅城,伪永历及其眷属全获无遗,伪巩昌王白文选逃奔茶山,大兵昼夜追及白文选并伪官四百九十九员、兵丁三千八百余名、家口七千余名,全军归降,获马象甚多,具见王等调度有方,将士同心戮力,克奏肤功。朕心深为嘉悦。在事有功官兵,着从优议叙!’”这段记述,实际上是将两份文件合并记载。本文是以记载“得旨”为主,同时通过“先是”,将此前的原委交代清楚。再如,《清高宗实录》卷一载,雍正十三年八月壬辰,“谕总理事务王大臣:‘梓宫前供膳时,闲散宗室觉罗俱在景运门外齐集。朕意欲令伊等进乾清门内瞻仰,其如何分班之处,著议奏。’寻议:‘每供膳时,宗室各三十人,觉罗各二十人,轮班瞻仰。’得旨报可”。这段文字也是将两个文件合并叙述。其一是传谕总理事务王大臣议奏宗室觉罗入乾清门内瞻仰,其二是稍后的议奏内容,实录将二份文件合并,先正面叙述前一件事,然后用“寻议”一词,引入下一件事,使整个事件过程变得完整。
第二,熔铸。《清实录》将凌乱的档案材料熔铸成流畅的叙事体。如《宣统政纪》载,宣统三年闰六月二十五日,“命学部左侍郎宝熙为实录馆副总裁”[10]卷五七,“宣统三年闰元月辛酉”。这条简略的叙述,其实是将两条杂乱的档案材料合并改写而成的。《宣统上谕档》曾收录了一份名单:
应派实录馆满副总裁名单
司法大臣绍昌
署民政大臣桂春
民政部左侍郎乌珍
度支部左侍郎绍英
朱○学部左侍郎宝熙
理藩部左侍郎达寿
在理院正卿定成
然后又录了另一份上谕:
宣统三年闰六月二十五日,内阁奉上谕:着派宝熙充实录馆副总裁。钦此![11]第37册,200-201
这两条档案材料,上一条有官职,无时间;下一条有时间,无宝熙的官职,《宣统政纪》将此二者合并成“命学部左侍郎宝熙为实录馆副总裁”一句,可谓言简意赅。再如《宣统上谕档》所收宣统元年二月初九日的一份奏章为:“军机大臣钦奉谕旨:内阁奏请勘修尊藏《实录》、红本大库工程一折,着派鹿传霖查勘修理钦此!军机大臣署名臣奕假。”[11]第35册,57此条材料被《清宣统政纪》卷八“宣统元年二月己未”条改写成叙述体的文字:“派协办大学士鹿传霖查勘修理实录、红本大库工程。”这里增加了鹿传霖的官职“协派大学士”,去掉了“钦奉谕旨”“内阁奏请”等文件语汇,使事件表述得十分清晰而流畅。《清实录》将档案体改写成叙述体,即将史料写成了史书。
五、辨析与订误
《清实录》作为后修的史书,较原始档案更为成熟,是经过辨讹和订误了的典籍。其对原始档案的订正,亦是其修纂制度和纂修体例的一个必备步骤。
第一,辨析与权衡。《清实录》在改写档案时,遇到一些难题需要解决,那就是上奏的时间与批准时间有一个时间差,实录在综合叙述时,到底依据哪一个时间,颇费周折,有时只好折中。《德宗实录修纂凡例》:“朱批奏折,敬展丹毫,事事皆蒙训示,惟原折有拜发而无批回之日,其按日可查者,俱应恭载,其无档案可查,无日可归者,统于是月末照宪纲汇载。” 如《嘉庆上谕档》载一份奏疏称:
臣等谨查乾隆三年三月上《实录》恭载将湖北巡抚张楷调补西安巡抚,二月下《实录》恭载朱批张楷奏折“已用汝为陕西巡抚矣”,蒙皇上指出垂询:二月张楷已用为陕西巡抚,何以三月内方有调补之旨。仰见皇上每日恭阅《实录》前后贯串,一字靡遗。臣等实深钦服。查纂办《实录》,凡有朱批臣工奏折,如无月日可排者,不能空无附丽,是以凡例内,仅就诸臣折内拜发日期,载于每月之末,统以“是月”二字贯之。张楷此折系二月二十七日拜发到京,钦奉朱批时已在三月中旬,兹将朱批载在二月之末,系以张楷发折日期为任,至张楷调补陕西巡抚,系三月初三日,所奉谕旨,是在朱批张楷奏折之前。谨奏。[3]第5册,99-100
这则档案说明,《清实录》在湖北巡抚张楷调任陕西巡抚的时间上,既未用二月早期的调令上奏的日期,也未用三月皇帝批准的日期,而是折中将这条任命放在二月末。这也算是当时实录修纂的一个体例。
第二,订误。《清德宗实录修纂凡例》中有一条认识到:像六科史书这样的连续的档案材料,“一有未经阅采,动辄漏略抵牾,其中事迹或始见于此,而结案远在隔年,或奉旨于前,而议上见诸后月”,并特别指出:“且档案不无疑误,须按其时事考其异同、原委脉络,画一流通,尤须与上下各卷互相考订。”因此,实录对所采史料常常进行订误,然后采用。《同治朝上谕档》在录同治元年十一月上谕时称“贾桢着充实录馆稿本总裁”[4]第12册,662,这一表述有误,故《清穆宗实录》卷五○“同治元年十一月庚午”条改为:“命大学士贾桢为实录馆监修总裁官。”因为当时的监修总裁官翁心存病死,因此贾桢是来接任翁心存监修总裁职务的,并非任稿本总裁的,当时任实录馆稿本总裁官的是周祖培。又《光绪朝上谕》档载:“光绪四年三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着派载龄充实录馆蒙古总裁官。钦此!”[11]第4册,97此处作“蒙古总裁官”,必误,因为下面还附载了一张拟选名单及朱笔圈定符号,拟选的是“应派总裁官之满洲尚书名单”,有载龄、魁龄(现在请假)、广寿、全庆四人的名字,朱笔圈中的是载龄。既然是在拟选“总裁官”,就不可能选的是“蒙古总裁官”。因此,《清德宗实录》卷六九“光绪四年三月乙丑”(十五日)条改此条更正为:“派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载龄为实录馆总裁官。”当时的蒙古总裁官为理藩院尚书皂保。《穆宗实录》修成后升赏时,皇帝称载龄是“总裁大学士载龄,在馆一年,着赏加二级”[12]卷一0四,“光绪五年十一月甲午”,根本未提他当过蒙古总裁。以上事实说明,《清实录》在采用档案史料时,是进行过辨析和订误的。
六、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清实录》与上谕等档案的关系,是史书与史料的关系,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经过史官的立意与点题、简化与删削、增加与完善、合并与熔铸、辨析与订误等主观筹划和编纂活动后,形成的具有史料性和档案性的史学著作。通过对《清实录》与上谕档改纂的分析,有助于加深对史书与史料关系的探讨,而以个案为基础的分析更有助于丰富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金毓黻.中国史学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2]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5]清仁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1987影印版.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
[7]清穆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7.
[8]清高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7.
[9]清文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0]清宣统政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2]清德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7.
[责任编辑:岳岭]
On the Compilation ofQingShiLuto the Imperial Edict Files
——Bot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Records and Historical Data
XIE Gui-a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As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classics in Qing Dynasty,QingShiLuis not purely historical, but a screening, cutting and compiling one of imperial edict files. In compiling the imperial edict files and other recorded historical data,QingShiLudidn’t swallow anything and everything, but accept some and reject some; its purpose and subject, simplifying and cutting, raise and perfection, combination and casting, discrimination and correction and the like are subjective and following the principles of compiling historical records. Theref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QingShiLuand archives should b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records and historical data, andQingShiLuwas a historical work with historical data and records.
Key words:QingShiLu; imperial edict files; compilation; historical data
中图分类号:K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16)01-0020-06
作者简介:谢贵安(1962—),湖北省襄阳市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和明清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清实录研究”,项目编号:10FZS008。
收稿日期:2015-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