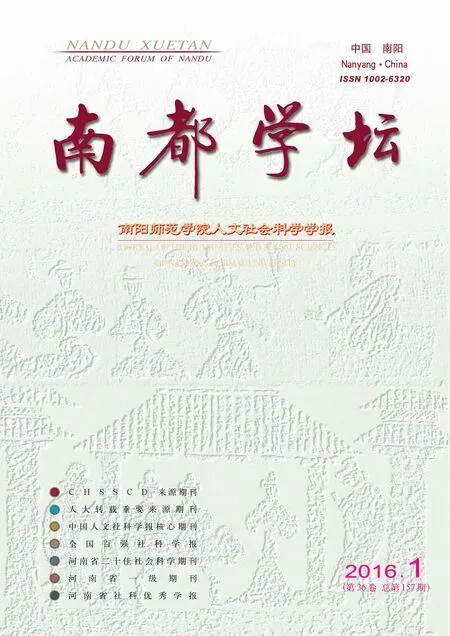汉代司隶校尉的监察区域及其权力演变
王 尔 春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91)
汉代司隶校尉的监察区域及其权力演变
王 尔 春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91)
摘要:司隶校尉是汉代国家的监察官,集中央监察与地方监察于一身,集监察权、治安权、领兵权、议政权、荐举权、社会事务管理权于一身,权大位重。但是这些权限不是初设即有的,而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其监察的地域范围也经历了一个由不固定到固定的演变过程。这表明二者之间有其必然的联系,对“京畿七郡”特定区域的监察,揭开了司隶校尉权力演变的内在原因。
关键词:汉代;司隶校尉;监察区域;权力演变
司隶校尉是汉代国家的监察官,集中央监察与地方监察于一身,集监察权、治安权、领兵权、议政权、荐举权、社会事务管理权于一身,权大位重[1]16。但是这些权限不是初设即有的,而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又与其监察的地域范围息息相关,所以本文就以司隶校尉在两汉监察区域的演变为切入点,再探司隶校尉权力演变之内在原因。
一、京畿七郡的地理位置及政治地位
《汉书·百官公卿表序》载:“司隶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节,从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蛊,督大奸猾。后罢其兵。察三辅、三河、弘农。”这里提到了司隶校尉的监察区域——三辅、三河和弘农七郡,我们就具体分析一下这七郡的政治地位,希望揭开其独立于地方监察体制——部刺史之外的内在原因。
先说三辅,即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它们是汉初内史地演变而来的,是汉代国家的京畿地区。自汉初,皇帝为自己建陵寝,设陵县,徙富商大贾、吏二千石居其中。至武帝时已有6个陵县,即高帝长陵、惠帝安陵、文帝霸陵、薄太后南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虽由太常领属,但其地处于三辅之中,必然给三辅的管理带来难度,所以《三辅黄图》言:“五方错杂,风俗不一,贵者崇侈靡,贱者薄仁义,富强则商贾为利,贫窭则盗贼不禁,闾里婚嫁尤尚财货,送死过度,故汉之京辅号为难理。”[2]卷一,83
再说弘农,是广关后增设的。武帝元鼎年间采纳杨仆建议,将函谷关东移至新安[3]卷六,183,在旧关与新关间增设一弘农郡,可见弘农郡正处于内史地域和河南郡及南阳郡的交叉地带。东汉王符言:“地[不可]无边,无边亡国。是故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三辅内入,则弘农为边;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4]卷五,258说的虽是东汉情形,但弘农郡作为三辅的东部外围,确起了“边”的作用,使三辅不致孤立无援。
最后说三河,即河南、河内、河东三郡。《汉书·元帝纪》载建昭二年三月,“益三河大郡太守秩。户十二万大郡”。可见,三河是有别于其他郡的大郡,三河太守也是有别于其他郡的太守。武帝时丞相长史田仁上书请先刺举三河,言:“三河太守皆内倚中贵人,与三公有亲属,无所畏惧,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奸吏。”[5]卷一百四,2781当时的河南、河内太守皆御史大夫杜周的父兄子弟,河东太守是石丞相子孙,其背景可见一斑。另外,三河之所以能与三辅、弘农相提并论,还在于其特有的地理位置。《史记·货殖列传》言:“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且三河之地地处东部诸侯国与西部京畿地区之间,既可与诸侯国一道屏障京畿,又可减轻京畿来自诸侯国的压力。其战略地位一直为统治者所重视。
由此看来,三辅、三河、弘农虽是不同的行政区域,但它们有相同的政治地位。三河、弘农与三辅一样不存在王国封地,已为学界公认,更据考证,三河、弘农“原则上也不封列侯”[6]36,直至哀帝时期还强调“宗室不宜典三河”[3]卷三十六,1972,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同属广义的京畿地区。因此当初设置地方监察官——部刺史时,也没有把这一地区划分出去,而是由中央监察官御史中丞以及后来增设的丞相司直监察,成为独立于地方监察体制之外的一个特殊区域。部刺史设后十三年,司隶校尉设立。司隶校尉是中央监察官,京畿七郡的地位如此特殊,自然成为其监察对象。于是司隶校尉的监察区域与京畿七郡就连在一起了。当然二者最终合而为一,还需要一个过程。
二、西汉司隶校尉监察区域的不确定性
《续汉书·百官志》关于司隶校尉记述为“孝武帝初置,持节,掌察举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并未明言司隶校尉察三辅、三河、弘农七郡,从上下句关系看,这种状况应该是指初置时期,表明此时的司隶校尉监察区域比较模糊,但以京师近郡为主是明确的。这一事实至少延续到西汉成帝时:“会北地浩商为义渠长所捕,亡,长取其母,与豭猪连系都亭下。商兄弟会宾客,自称司隶掾、长安县尉,杀义渠长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请遣史与司隶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察无状者,奏可。”[3]卷八十四,3413按,义渠属北地郡,北地郡南边紧邻京畿七郡之一的右扶风。然“商兄弟会宾客,自称司隶掾、长安县尉”就可捕杀义渠长,事后司隶校尉又参与逐捕,表明在汉成帝时期,司隶校尉的监察范围还在所谓的“京师近郡”。上文所引用的《汉书·百官公卿表序》就司隶校尉一职完整的记述是“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节,从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蛊,督大奸猾。后罢其兵。察三辅、三河、弘农。元帝初元四年去节。成帝元延四年省。绥和二年,哀帝复置”[3]卷十九上,737。从上下文关系看,司隶校尉罢兵的时间应在元帝初元四年前,之后又有废置,则其察三辅、三河、弘农七郡当在罢兵后、成帝元延四年前,哀帝绥和二年后。但如前引资料表明成帝时司隶校尉仍察京师近郡,而非只在京畿七郡内,所以笔者认为《汉书·百官公卿表序》所讲的司隶校尉监察区域,虽然具体化了,但仍不能据此断定司隶校尉监察区域由此固定下来。进一步说,在西汉,司隶校尉不但未能单单监察京畿七郡,就是京畿七郡也未只由司隶校尉监察。司隶校尉设置之初的昭帝始元元年,有司“请河内属冀州,河东属并州”[3]卷七,219,再次说明司隶校尉的监察地域与京畿七郡在理论上绝不是“一对一”的关系,京畿七郡可以看作其监察的地域主体,但绝非全部。这应该符合西汉司隶校尉监察区域事实。
三、司隶校尉的监察区域与领州问题
关于司隶校尉的领州时间,史学界颇有争议,有人认为始于西汉末,有人认为始于东汉。但不论哪种说法都需阐明司隶校尉监察三辅、三河、弘农七郡始于何时。但正如前文所述,这个监察范围在西汉是不固定的,就笔者看来,这个监察区域直至汉末也不能肯定说固定下来了,所以司隶校尉的领州时间始于西汉末的说法经不起推敲。先来看下面三则材料:
材料1《汉书·昭帝纪》:始元元年,“有司请河内属冀州,河东属并州”。
材料2《汉书·成帝纪》:鸿嘉元年,“临遣谏大夫理等举三辅、三河、弘农冤狱”。
材料3《汉书·沟洫志》:哀帝初,“平当使领河堤,奏言‘……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部刺史、三辅、三河、弘农太守举吏民能者,莫有应书”。
顾颉刚先生根据上述材料认为司隶校尉领州始于东汉。理由是:如果昭帝时就将三辅、三河、弘农立为一州而使司隶管辖,那么就不会有材料1那样的奏请;假使成帝时司隶校尉已独领一州,那么就不会出现材料2所记载的派谏大夫等进行冤狱再审工作的情况出现;直至哀帝时,臣下上书仍将七郡太守与部刺史并谈,说明至此七郡还未由司隶校尉单独管辖[7]881-882。严耕望先生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一文中反驳了顾颉刚先生的观点,主张西汉末年由司隶校尉负责管治三辅、三河、弘农郡地域。理由如下:材料1的奏请应发生在司隶校尉监察三辅、三河、弘农郡之前,因为《汉书·百官公卿表序》记载“后罢其兵。察三辅、三河、弘农”;材料2的记事或许可理解为到该时期为止,司隶校尉尚未掌管该地域,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可理解为中央官吏的派遣进行冤狱再审工作与司隶校尉监察该地域并不冲突;材料3的内容结合与之相关的丞相孔光和大司空何武的任期看,可能发生在绥和二年二月至九月,故这一事实应发生在司隶校尉暂废时期[8]298-301。
笔者仔细分析后认为,第一,顾颉刚先生对材料1的运用是正确的。因为司隶校尉是作为中央监察官出现的,初置不久即监察京畿七郡是合理的,至于有司的奏请只能说明这一监察区域并不固定。《汉书·陈汤传》载元帝时,西域副校尉陈汤“素贪,所卤获财物入塞多不法。司隶校尉移书道上,系吏士按验之”。按,“道”是指少数民族居住的县,自然不在京畿七郡内,而司隶校尉却能移书至此,再次说明司隶校尉在西汉不唯独监察京畿七郡,故司隶校尉独领一州也无从谈起。第二,对于材料3,笔者也以有关人物任职时间断代:据《汉书·哀帝纪》,哀帝是绥和二年四月即位;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丞相孔光与大司空何武都在任的时间应在绥和二年三月和四月。则材料3所记之事当发生于绥和二年三四月间,也就是成帝驾崩之际。而司隶校尉复置于哀帝绥和二年,则复置的准确时间最早也在绥和二年四月之后。看来严耕望先生所言发生在司隶校尉暂废期是有道理的,只是时间断代不够精确。至于材料2,鸿嘉元年,谏大夫举冤狱,其范围以三辅、三河、弘农各郡名相称,而未有一个总称,这至少说明京畿七郡还未由司隶校尉统领,因为这条史料紧接着还有一句话:“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敕守相,称朕意焉。”很显然其他各郡可以以所归属的部名相称,所以仅言“部刺史”即可,而无须将各郡名一一列出。因而顾颉刚先生以此作为司隶校尉未独领一州的证据是可以的,只是阐述的角度不具备说服力。综上所述,可以认定司隶校尉领州时间应该不在西汉。这就再次说明三辅、三河、弘农七郡在西汉只是司隶校尉监察的主体范围,非固定区域。我们上部分的结论仍然是正确的。
四、东汉司隶校尉监察区域的固定化问题
以上的分析告诉我们在考证司隶校尉领州时间上,不能将是否监察三辅、三河、弘农与是否独领一州按一个概念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出司隶校尉在西汉末就已独领一州的误区,也就能理解史书中很多看似模糊的记载,其实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现在我们再接着探讨司隶校尉监察区域固定的时间问题。
《续汉书·百官志四》称司隶校尉“建武中复置,并领一州”,至此司隶校尉才独领一州,也就是说这时司隶校尉的监察区域才固定下来。《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六年六月辛卯,“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这是笔者所看到的最早出现司隶作为官名与州牧并称的材料,故应该确定至迟在这一年司隶校尉就独领一州了。关于“司隶”,该纪又注引《汉官仪》曰:“司隶校尉部河南、河内、右扶风、左冯翊、京兆、河东、弘农七郡于河南洛阳,故谓东京为‘司隶’。”可见,此时司隶校尉所领的州就是由京畿七郡组成的州,也就是说西汉司隶校尉的主体监察区域与京畿七郡到此时才合而为一,终于成了一对一的关系,这个州称司隶校尉部或简称司隶。之后司隶校尉与部刺史并举、司隶与他州并称的现象屡屡出现[9]卷五,215;卷七,299。而《后汉书·公孙述传》注称:“汉以京师为司隶校尉部,置京兆尹。中兴以洛阳为司隶校尉部,置河南尹。”[9]卷十三,535此则材料关于后汉的说法是正确的,前汉的说法却未得其实。京畿七郡由司隶校尉的主体监察区域演变为司隶校尉部,司隶校尉的地方监察区域如同部刺史的监察区域一样固定了,就必然会带来不同于西汉的权力变化。
五、司隶校尉监察官身份与权力演变
首先,关于司隶校尉中央监察官与地方监察官的身份问题。
三辅是汉代的京畿地区,三河、弘农可以看作广义的京畿地区。从地位上看,这七郡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将它们交由司隶校尉监察,司隶校尉的地位不言而喻。但是这个监察区域正如前文所述,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这不仅仅与京畿七郡的特殊地位相关,而且还与司隶校尉监察官的身份相关。司隶校尉是作为中央监察官出现于汉代官制中的,“司隶诣台廷议,处九卿上,朝贺处公卿下,陪卿上。初除,诣大将军、三公,通诣持板揖。公议、朝贺无敬。台召入宫对见尚书,持板,朝贺揖”,“入宫,开中道称使者。每会,后到先去”[10]208。就秩级来说,《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自司隶至虎贲校尉,秩皆二千石”。可见司隶校尉初设就与部刺史有天壤之别。之所以在以前的文章中笔者认为其具有中央监察官与地方监察官双重身份[11]93,就在于其对京畿七郡的监察。但也正如前文所述,京畿七郡地位如此特殊,就必然需要一个不同于部刺史的监察官员,于是司隶校尉出现了,当然原因不仅仅在此。由于司隶校尉设置之因与本文主旨关系不大,暂不做论述。这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司隶校尉既然有地方监察官的一面,到了东汉独领一州,京畿七郡就常常以部相称了,司隶校尉与部刺史并列出现的状况也越来越多,司隶校尉与部刺史的地位好像也越来越接近,有治所、有所领的州,到年末也要“上计”[9]卷二,112,但是有一点刺史不具备,即中央监察官的身份。就是这一点在两汉,司隶校尉最终也不是单一的地方监察官员,所以其演变的路线与刺史变州牧、最后变为地方行政官员的轨迹无法重合。
其次,关于司隶校尉监察权外的其他行政权力的演变问题。
汉代司隶校尉是作为中央监察官出现的,其地方监察官的性质是在对京畿七郡具体监察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由于有了京畿七郡这样一个具体地域,所以在其中央官员的职权外,还有一些能与地域联系在一起的权力,如民政、交通、人事、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一些权限,“劳来贫人”[9]卷二十五,879“为封长檄”[9]卷五,209“祷祀河神”[9]卷六十一,2025“省减吏员”[9]卷一下,49“风劝良吏”[12],等等,可以统称之为社会事务管理权。这些权限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看,均出现在东汉时期。但就其权力出现的脉络,笔者以为还是源于西汉,它应该是与司隶校尉监察区域由不固定到固定的这一演变过程一脉相承的。有了固定的地域,才有司隶校尉行使社会事务管理权的具体地域环境,也才有皇帝的诏书由司隶校尉部或司隶部下达的方便条件。只不过这一地域是在东汉正式形成的,所以其社会事务管理权只能在东汉出现。从其实质看,是司隶校尉就行政事项对中央所负的责任,且这些权力具有临时委派的性质,只是下达的次数频繁些而已,可以看作司隶校尉监察权外附带拥有的权力,绝非司隶校尉权力主体。
六、结论
综上可以看出两汉统治者对待京畿七郡的良苦用心,历史证明汉统治者的运筹还是成功的。至少在东汉末,地方纷纷独立之际,京畿七郡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其地位。要想掌控全国的权力,地方豪强只能离开其势力范围跑到京畿来,董卓就是这样,但由于其根基不在京畿,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东汉虽也未能逃脱灭亡的命运,但汉祚至少又延续了若干年,其间汉献帝趁关中混乱之机曾从长安逃回洛阳,再次说明这里仍是汉朝的根基。曹操虽然没有跑到洛阳,但他把象征皇权的汉献帝从洛阳迎接到许昌,从而打赢了重新统一北方政权这场仗。从另一方面讲,袁绍在汉灵帝时任司隶校尉,董卓入关,袁绍奔往冀州,董卓笼络人心而授其渤海太守职,但袁绍“犹称兼司隶”。后袁绍以渤海起兵,自号车骑将军,仍“领司隶校尉”[9]卷七十四上,2375。继董卓之后作乱关中的李傕为车骑将军、池阳侯,也要“领司隶校尉”[13]卷六,181。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从长安逃回洛阳,曹操赶紧跑到洛阳迎接汉献帝,“天子假太祖节钺,录尚书事”。注引《献帝纪》曰:“又领司隶校尉。”[13]卷一,13种种迹象表明司隶校尉职务之重。但在混乱之际这种职务不会有什么实质性意义的,然而各政权的首脑人物还是要挂上这个职务,个中缘由令人深思:司隶校尉这一职务似乎与汉皇权紧紧连在一起了,有了它似乎就能证明这是汉家天下,有了它似乎就能证明汉家王朝的根基——京畿七郡仍在,从这个角度讲,作为监察官的司隶校尉是与汉政权相始终的。这应该是京畿七郡最终演变为司隶校尉部的意义所在。而在这演变过程中,司隶校尉的权力也出现了不少变化,很多权力都与地方行政相关,但司隶校尉并没有因此如同部刺史一样转变为地方行政官员,从而在东汉末混乱之际割据一方,反而成了各地新政权力求“合法”的象征,曹魏设、蜀汉设,曹魏“挟天子”[13]卷十一,337、蜀汉“帝室之胄”[13]卷三十五,913,唯有孙吴与汉政权无法沾边,所以其政权总是忸怩作态,封爵食邑制不敢实行,只能代以奉邑制[14]22,司隶校尉之未设也应该基于此,这就更一步表明司隶校尉与汉政权的密切关系了。当然曹魏、蜀汉所设司隶校尉的职权与两汉国家正常运作时相比已大相径庭,但它们仍与各政权的政权中心地域连在一起,这一现象的出现应该是作为皇权根基的京畿七郡与司隶校尉监察区域合而为一的结果。东汉以后,司隶校尉监察官的性质已不明显,并逐步向行政官转化。到东晋废置时,它已经完成了向行政官的过渡。失去了监察权,失去了京畿七郡,失去了汉王朝,司隶校尉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参考文献]
[1]王尔春.汉代司隶校尉权力探讨[J].南都学坛,2008(5):16-18.
[2]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韩]崔在容.西汉京畿制度的特征[J].历史研究,1996(4):24-36.
[7]顾颉刚.两汉州制考[C]//“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8.
[8]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C]//“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五.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8.
[9]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0]蔡质,撰.孙星衍,校集.汉官典职仪式选用[M]//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201-215.
[11]王尔春.论汉代司隶校尉监察权[J].河北学刊,2008(1):89-93.
[12]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M]//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6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13]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4]高敏.孙吴奉邑制考略[J].中国史研究,1985(1):19-26.
[责任编辑:刘太祥]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16)01-0007-04
作者简介:王尔春(1970—),女,汉族,黑龙江省依安县人,历史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
基金项目:2014年度河北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计划内计划重点项目“汉代司隶校尉的监察区域及其权力演变”,项目编号:S2014Z02。
收稿日期:2015-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