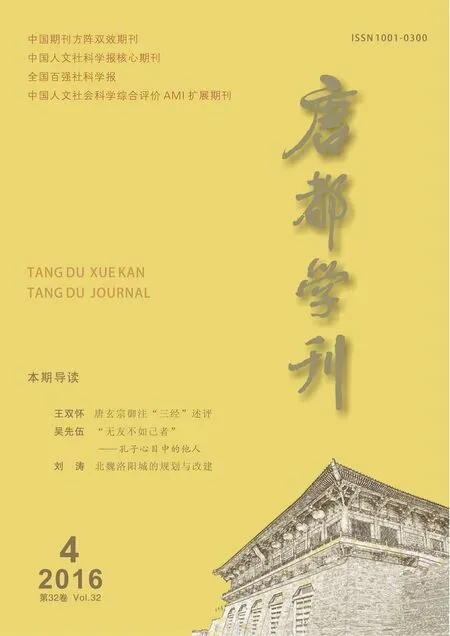医疗资源分配中的年龄主义与代际公平
王 珀
(山东交通学院 社科部,济南 250031)
【伦理学研究】
医疗资源分配中的年龄主义与代际公平
王珀
(山东交通学院 社科部,济南250031)
在医疗资源分配领域,年龄主义的分配政策主张我们应当在一定程度上优先照顾较年轻者。存在三种合理形式的年龄主义观点,这三种年龄主义可以得到丹尼尔斯和德沃金的分配正义理论的支持。但即使年龄主义分配政策是符合代际公平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老年人的需要置之不理。我们必须确保老年人都能得到充分的初级卫生保健、保守治疗和临终关怀。
医疗资源分配;年龄主义;代际公平;诺曼·丹尼尔斯;罗纳德·德沃金
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医疗资源分配的代际冲突问题日益凸显。当前我国的大量医疗资源与服务都耗费在了临终几个月的生命维持和抢救上*参见《据统计:一生八成健康投入花在临死前一个月》,搜狐健康,2008-11-25[2013-03-18],http:∥health.sohu.com/20081125/n260828968.shtml。,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分配现状,我们就必须采取某种正当的年龄主义的分配标准。年龄主义,是指在分配医疗资源的时候,根据年龄对不同患者加以区别对待的态度*年龄主义(ageism)这个术语,在有些学者那里是个贬义词,与年龄歧视(age discrimination)的含义相近;而在有些学者那里,它是个中性词,不同于年龄歧视。这里采用了第二种用法,认为只有不正当的年龄主义才属于年龄歧视。。当老年人的医疗需求与年轻人的类似医疗需求发生冲突的时候,人们常常倾向于让年轻人得到较大的优先性。年龄主义是不是一种不正当的歧视?它能否得到道德辩护?
一、三种年龄主义
Aki Tsuchiya等人认为,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年龄主义:健康最大化年龄主义、公平寿命年龄主义和生产力年龄主义*下文对这三种年龄主义的探讨部分地参考了Aki Tsuchiya,Paul Dolan,and Rebecca Shaw,“Measuring People’s Preferences Regarding Ageism in Health:Some Methodological Issues and Some Fresh Evidence”,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vol.57,no.4,2003,pp.687-696.以及N.Lievesley,R.Hayes,K.Jones,A.Clark,and G.Crosby,“Ageism and Age Discrimination in Secondary Health Care in the United Kingdom:A Review from the Literature”,London:Centre for Policy on Ageing,2009,p.10,available at [http://www.cpa.org.uk/information/reviews/CPA-ageism_and_age_discrimination_in_secondary_health_care-report.pdf],rev 2013 mar 25.。先讨论一下这三种年龄主义的基本主张,再论证其道德正当性。
1.健康最大化年龄主义(health maximisation ageism)
这是一种基于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年龄主义。功利主义主张用有限的医疗资源来实现健康收益的最大化。如何衡量健康收益?卫生经济学最常用来衡量健康收益的指标,即生命质量调整年(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s,缩写为QALYs),这个指标是由生命时间和生命质量两个变量的乘积得来的,计算式为QALY=预期生命年数×生命质量。1QALY就等于一个人以完全健康的状态生活一年所收益的价值量。
功利主义认为,对于某些昂贵性医疗资源来说,将他们用在较年轻者身上往往可以获得较大的健康收益,因此较年轻者可以得到较大的优先性。在此需分两种情形加以讨论:第一种情况,由于较年轻患者的剩余寿命一般要高于老年患者,所以在分配那些可以用来提高患者的余生生命质量的医疗资源的时候,较年轻者将得到较大的健康收益[1]。例如,一个年轻人的剩余寿命是50年,一个老年人的剩余寿命是10年,所以对于某些可以提高余生生命质量的手术(例如白内障手术和手指神经修复术)来说,剩余寿命较长的年轻人将得到较大的健康收益,因此年轻人应得到较大的优先性和较大的报销比例。据说,英国的医院不推荐那些超过70岁的老年患者去做手指神经修复手术,因为那被认为是不值得的。在英国,65岁以下的疑似心肌梗死病例将得到进一步检查和治疗,而65岁以上的疑似病例则默认不必接受进一步检查[2]。第二种情况,年轻患者在余生中的预期生命质量往往高于老年患者,所以在分配那些可以延长患者预期寿命的医疗资源的时候,功利主义将要求给较年轻者较大的优先性。例如,一个年轻人和一个老年人都患有心脏病,需要心脏移植,这名年轻人的身体其他部分是完好的,而这名老年人还患有其他各种老年人常见疾病(例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等),由于这名年轻人的预期生命质量高于这名老年人,那么在分配一次心脏移植机会的时候,即使二人在这次手术中将收获等量的寿命,健康收益标准仍要求我们把心脏分配给这个年轻患者。
2.公平寿命年龄主义(fair innings ageism)
这是一种基于平等主义分配原则的年龄主义。从终生视角的平等主义看来,衡量一个人是否属于较不利者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他在一生中能否享用足量的寿命。因此,那些预期终生寿命低于人口平均寿命水平的患者属于较不利者。一个80岁的老年人已然享受了足够长的人生、而且他的生活计划也基本上已经完成;而一个30岁的成年年轻患者还没有开始享受生活、还没有完成自己的人生计划。我们一般认为,早死是人生一大不幸,而寿终正寝则是正常的自然现象。所以,根据终生视角的平等主义,当这两个人都受到生命威胁的时候,我们应优先拯救这个年轻人的生命。例如,假设一名年轻人和一名老人都需要借助血液透析治疗来维持生命,那么这种年龄主义将主张给这个年轻人较大的报销比例。公平寿命年龄主义认为,医疗资源分配的优先目标是保障年轻人达到某个最低的寿命门槛,然后才能考虑是否让那些寿命高于这个门槛的老人活得更长。
3.生产力年龄主义(productivity ageism)
与老年人相比,较年轻者往往具有更强的工作能力,所以让较年轻者得到良好的医疗保障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经济活力。为较年轻者提供足够的预防性医疗保健,可以防止他们失去工作能力;而对于那些因病暂时丧失了工作能力的年轻人来说,如果给他们良好的医疗,就有可能使他们尽早恢复工作能力,而大多数老年患者却丧失了这种恢复工作的可能性。所以,生产力年龄主义认为,为了社会经济发展和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应当让较年轻者得到良好的医疗保障,这种偏向年轻人的政策在某些方面对老年人也是有利的,因为提高较年轻者的生产能力,有利于让老年人得到更好的生活保障。反之,如果作为社会生产主力军的年轻人的健康得不到保障,这对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也是不利的。因此根据生产力年龄主义,我们应当优先满足一名30岁农民工的医疗需求,而不是把有限的医疗资源用在抢救一位80岁的老年人身上。
二、年龄主义的道德合理性
笔者认为,上述三种年龄主义是可以得到道德辩护的。这些年龄主义标准之所以是公平的,一种最简单、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总有一天也会变成老年人[3]。只要能保证政策的可持续性与稳定性,偏向较年轻者的政策就未必属于不正当的歧视。一种合理的年龄主义与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年轻人”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群体,一个人现在属于年轻人群体,但几十年后他必将改变身份,加入老年人群体;而“男人”“女人”“白种人”和“黑种人”这些群体是具有固定特征的人群,属于这些群体的人们是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自己身份的。“年龄”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生理特征,而“性别”和“种族”却是固定不变的。因此,根据性别和种族来区别对待人们是不公平的,而根据年龄来区别对待则未必是不公平的。
年龄主义之所以看上去似乎有违代际公平,是因为在我们的语言中,“世代(generation)”这个概念的定义是含混不清的,对这个概念的错误理解将导致对代际公平的错误理解。诺曼·丹尼尔斯认为,要想讨论医疗资源分配的代际公平问题,就必须首先澄清“世代”这个概念的涵义。丹尼尔斯区分了“年龄组(age groups)”和“出生组(birth cohorts)”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年龄组是指当前处于某一年龄段的社会成员,一个年龄组群体(比方说20~30岁年龄组)是不会衰老的,但一个年龄组的成员构成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改变;一个“出生组”是指出生于某个特定时期的人群(比方说出生于1980—1990年间的出生组),它是一个固定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出生组的成员会衰老、会经历不同的年龄段,而它的成员构成却不会发生改变[4]169。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一代人”有时被用来指称一个“年龄组”,有时又被用来指称一个“出生组”,由此引起了概念上的混乱。
如果我们把代际公平理解为在某一特定时期内的不同年龄组之间的分配平等问题,那么一种向较年轻者倾斜的年龄主义政策看上去是不利于较老的年龄组的。但这种对代际公平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它暗示了这样一幅图景:在某一特定时期内,身处不同年龄组的老人和年轻人在对稀缺性医疗资源进行竞争。我们头脑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图景,是因为我们常常把公共政策看作是用来解决当前、眼下问题的,而不是用来解决长期的、关于整个生命历程(whole lifespan)问题的[4]169-171。然而,我们应当思考的代际公平问题并不是如何在特定时期内的不同年龄组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而是思考如何在不同出生组之间的进行分配的问题。前一种思维方式预设了一种“时段化视角”,而后一种思维方式则采用了一种“终生视角”。
如果我们采用整个生命历程的视角,那么在当前时期的分配中给予较年轻者的一定优待就未必属于一种“年龄歧视”。因为当前的年轻人早晚也会变老,只要能保证政策的稳定性,那么从终生视角看来就不会导致不平等[4]173。也就是说,一旦我们抛弃时段化思维,而改用整体一生的视角,我们将会更加关心不同的出生组之间的公平分配问题,而不是不同年龄组之间的公平分配问题。对不同的年龄组予以区别对待,这与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存在着本质性区别。如果我们根据性别和种族对人们区别对待,例如根据性别和种族来雇佣或解雇员工,这就是不公平的。然而,如果我们对当前的较年轻者和老年人区别对待,这未必是不公的。只要这种区别对待的政策对每个人的整个人生都可以带来同样的影响,那么这种政策就是平等对待每个人的。我们都会变老,但我们难以改变自己的种族和性别,这个浅显的事实使得年龄特征不同于性别、肤色等特征[4]169-171。
丹尼尔斯认为,对不同年龄组给予不同的对待,这恰恰是代际公平的要求。因为我们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会产生不同的需求,医疗资源分配制度必须敏感于这种差异[4]171。他设计了一个思想实验,想象我们的医疗保健政策是由一个“谨慎的终生计划者”制定的。假设我是一名“谨慎的终生计划者”,我必须在固定的资源限制之下,对我的一生的医疗投资方案做一个规划,那么我应该如何对我的生命各个阶段的医疗需求进行分配呢?我必须权衡自己在不同生命阶段的医疗需求,我不会为年老的、处于濒死阶段的自己分配过多抢救性医疗资源,因为那样做会减少我所能得到的长期护理服务以及在早年阶段的预防性治疗[4]173-174。另外,如果我不知道自己的寿命有多长,那么我就应让自己在早年阶段得到较好的医疗保障,我不会冒着早死的风险而把医疗资源留到晚年阶段才使用[2]。所以,在一个摒除了年龄、寿命等信息的无知之幕背后,理性的自利者会选择一种年龄主义的医疗保健政策。
罗纳德·德沃金也给出了一个很相似的“虚拟保险”论证,他构想了一个虚拟的自由保险市场,在这个具有平等主义精神的市场中,每个人手里都持有平等的起始资金,他们可以用这笔钱自由地为自己选择一个受用终生的医疗保险计划。德沃金让我们设想一个25岁的人该如何为自己的一生医疗需求做规划,假设他拥有平均份额的财富和中等水平的前程,他掌握了足够的医疗知识。起初他也许想要让自己所有生命阶段的医疗需求都能得到满足,但这种医疗保险的成本过于高昂,购买这种保险将会使他变得一贫如洗,所以他不得不审慎地对不同生命阶段的医疗需求加以权衡、取舍。他不会购买那种让他在不幸成为植物人时用于维持生命的医疗保险,他也不会购买那种用来让自己在临终阶段多活四五个月的医疗保险。德沃金指出,在美国有超过1/4的医疗开支是花在人们生命的最后6个月的,这种分配方式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因为一个审慎的虚拟保险购买者会更愿意把这笔钱花在早年保健上。在德沃金的思想实验中,如果大多数人都选择购买包括必要的住院治疗、孕期和儿科保健、常规体检和其他预防性医疗在内的正常医疗保险,那么全民医疗保障制度就应当提供这些医疗服务;如果大多数人不打算购买那些仅仅可以延长几个月寿命的、价格昂贵的医疗保险,那么国家通过强制性计划来迫使人们接受这种医疗保障就是不公正的[5]。
德沃金所反思的问题在我国也同样存在,据说中国人一生中的健康投入的60%~80%花在了临死前一个月的治疗上*参见《据统计:一生八成健康投入花在临死前一个月》,搜狐健康,2008-11-25[2013-03-18],http:∥health.sohu.com/20081125/n260828968.shtml。。从丹尼尔斯和德沃金所设定的终生医疗计划的自我规划者的角度看来,这笔巨额投资是不理性的。从丹尼尔斯和德沃金的论证思路看来,前面所讨论的三种年龄主义都是理性的、正当的。第一,如果我在无知之幕背后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患有何种疾病,那么我应当优先购买那些可以产生最大健康收益的医疗保险——优先让那些易于治疗的疾病得到治疗,并让那些易于预防的疾病得到预防,因为这样可以使我的预期健康寿命最大化。第二,考虑到自己有早死的风险,我应当为年轻的自己提供更好的医疗保障,因为我不太确定自己能否寿终正寝,为了确保我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生活计划(不管这个计划具体是什么样子的),我必须让自己在年轻阶段的医疗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把大部分资源都留到老年阶段使用是不理智的。第三,我也应当对自己的生产能力格外重视,让自己在青壮年时期得到相对较好的医疗保障,这样有利于增加我的终生总收入,这对我在老年阶段的生活也是有利的。
丹尼尔斯和德沃金都把在不同年龄段之间的医疗资源分配问题视作了生命历程内部的审慎规划问题,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代际公平问题。从一个终生审慎计划者看来,合理的年龄主义标准并不违背代际公平,因为它有利于满足人们一生的医疗需求。相反,对不同生命阶段的医疗需求赋予同样的优先性才是错误的。而且,优先保证年轻生产力的健康是对全体公民(也包括老年人)都有利的,如果作为社会生产的中流砥柱的中青年人的健康无法得到充足保障,就会使社会公共资源的总量受到威胁,代际公平也就无从谈起了。
需要注意的是,在现实实践中我们必须谨慎区分合理的年龄主义与不正当的年龄歧视。我们应当在分配昂贵性医疗资源的时候采用合理的年龄主义,但是在初级卫生保健、临终护理和人文关怀方面,老年人不应遭到任何歧视。C.M.克拉克认为,要想避免老年人遭受武断性的年龄歧视,就必须确立一个明确的、统一的年龄标准[6]。如果缺乏一个明确的标准,那么在个体临床层面上就很容易出现具有道德武断性的年龄歧视。这里需要区分两个层面上的年龄主义:制度层面的年龄主义与个体临床层面上的年龄主义[7]12-13。前者涉及宏观分配政策,后者则涉及医疗服务提供者的个人态度。如今,个体医务人员也扮演着医疗资源分配者的角色,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老年人将得到何种待遇,因此他们需要接受明确的年龄标准的指导。如果我们一方面提倡年龄主义,另一方面又没有给出一个公开的、统一的年龄标准,那么就可能使老年人遭受不公正的年龄歧视。正如A.B.肖所指出,尽管年龄是一个符合伦理、具有客观性且有利于降低成本效率比的分配标准,但它在实践中常常是秘密进行的,我们要想使这个标准在实践应用中更加公正,就必须对它进行公开的讨论[2]。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公开、公平的民主决策程序来制定统一的年龄标准及相关的临床实践标准,然后再对在职医务人员与医学专业的学生进行关于年龄标准的教育和培训,以此来减少具有武断性的年龄歧视[8]。
三、保障老年人的临终生命质量
采纳一种合理的年龄主义分配政策决不意味着对老年人的需要置之不理。一种遗弃老年人的政策如果足够稳定,也是可以让每个人得到平等对待的,然而这却对每个人(如果他可以活到老年的话)都是不利的。因此,无论是丹尼尔斯的审慎的终生规划者,还是德沃金的虚拟保险购买者都不会选择这样的政策。
有时候,改善老年人的生命质量未必需要花费太多的资源[6]。我们至少应保障老年人得到足够的初级卫生保健,因为此类医疗服务或药物是成本低廉、安全可靠的,可以产生较大的健康收益,即使老年人也可以从中获益*对于很多初级卫生保健服务来说,老年人反而可以从中获得较大健康收益。例如,乳腺癌多发病于40岁以后的妇女身上,其发病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而20~40岁的妇女发病率极低。因此,较年长的妇女反而可以从乳腺癌筛查中获得比年轻人更大的健康收益。。社会应让所有人,无论老少或贫富都能得到充分的初级卫生保健,这是一项人人享有的、最基本的医疗权利。尽管在分配器官移植机会的时候,较年轻者应得到较大的优先性,但在分配阿司匹林的时候,我们就不应歧视老年人了。丹尼尔·卡拉汉认为,在老年人卫生保健方面,医学的目标不是一味地延长老年人生命,而应当是改善老年人的生命质量[9]129。即使对于那些最年老、最病重的癌症患者来说,我们也不能说“没有任何举措了”,无论病情糟糕到何种程度,我们都可以为老年人提供保守治疗,从而缓解患者在临终阶段所遭受的病痛[10]。英国卫生保健体系就非常重视老年人的初级卫生保健和养老院护理,而不是延长生命的急性治疗,英国对55岁以上患者的心脏手术、重症监护及其他昂贵的技术手段设定了限制,这种分配政策成功地用较低的费用实现了较高的人口健康水平[9]1301。
事实上,与高技术医疗服务和昂贵的药物相比,老年患者更需要的是人性化关怀与尊重。调查表明,老年患者往往无法得到充分的尊敬。例如,老年患者常常在没有临床理由的情况下,从一个病房被转到另一个病房;老年患者的个人隐私和性别差异得不到充分尊重,常常不得不与异性患者共处同一个病房或隔间内;有些81岁以上的老年患者感到,当医务人员之间进行交谈的时候,他们常常把自己“当作仿佛不存在一样”[7]19-21。老年患者不是一个被遗忘的群体,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他们年纪大就不尊重他们的人格,这种年龄歧视在道德上是严重错误的。
我们一方面在老年人的临终抢救上耗费了大量医疗资源,另一方面很多临终老年人却并没有得到最起码的尊重,这种对比是值得深思的。对于大多数死在医院的患者来说,他们临别人世的画面是可悲的:繁忙、嘈杂、不干净的病房环境,医生和护士都在忙于应付患者生理指标的变化,却无暇顾及患者本人的精神需要。据统计,大概有一半的死亡都不是按照死者本人的意愿发生的,而大多数的老年人在临死的时候都没有得到专业的临终关怀服务[7]32-34。事实上,临终的老年人真正需要的是良好的保守治疗与人性化的关怀,而未必是昂贵的、具有侵入性的高科技医学干预。
我们必须重视老年人的临终需要,确保他们在这方面不遭受年龄歧视。举例说明,假设一个老年患者和一个年轻患者同样处于癌症晚期,且都处于濒死状态,我们应当对二者给予同样的保守治疗和临终关怀,让二者的病痛都能得到缓解,并同样地减少他们的精神压力。然而调查表明,即使在保守治疗和临终关怀上,高龄患者也受到了比年轻者更差的待遇[7]32。这种年龄歧视不属于上文所讨论的三种年龄主义中的任何一种,它与健康最大化、公平寿命标准和提高生产力都没有关系,因此它是得不到道德辩护的。
笔者的立场是,在分配昂贵性医疗资源的时候,采用合理的年龄主义是正当的,这并不违背代际公平;但另一方面,社会必须为老年患者提供充分的初级卫生保健、良好的保守治疗和临终关怀,对于这些需求而言,老年人不应遭受任何年龄歧视。
[1]Williams,Alan, and J.Grimley Evans.The Rationing Debate.Rationing Health Care by Age[J].BritishMedicalJournal,vol.314,No.7083,1997:820-825.
[2]Shaw,A B.In Defence of Ageism[J].JournalofMedicalEthics,vol.20,No.3,1994:188-191.
[3]Elhauge,Einer.Allocating Health Care Morally[J].CalL.Rev,vol.82,1994:1449-1544.
[4]Daniels,Norman.JustHealth:MeetingHealthNeedsFairly[M].Cambridge:Cambridge,2008.
[5]罗纳德·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M].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330-332.
[6]Clarke,Clare M.Rationing Scarce Life:Sustaining Resources on the Basis of Age[J].JournalofAdvancedNursing,vol.35,No.5,2001:799-804.
[7]Lievesley,N.et al.Ageism and Age Discrimination in Secondary Health Care in the United Kingdom:A Review from the Literature[R].London:Centre for Policy on Ageing,2009,p.56,available at [http://www.cpa.org.uk/information/reviews/CPA-ageism_and_age_discrimination_in_secondary_health_care-report.pdf],rev 2014 mar 15.
[8]Oliver,D.How Do You Stand Working with All These Old People?[J].TheHealthservicejournal,vol.117,No.6083,2007:20-21.
[9]丹尼尔·卡拉汉.老龄化和医学目的[G]∥罗纳德·蒙森.干预与反思:医学伦理学基本问题(三).林侠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10]NHS Scotland.Adding Life to Years:Report of the Expert Group on Healthcare for Older People[R].2001,Chapter 4,available at [http://www.sehd.scot.nhs.uk/publications/alty/alty-04.htm] rev 2014 mar 15.
[责任编辑王银娥]
Ageism and Intergenerational Impartiality Regardingthe Allocation of Health Care Resources
WANG Po
(DepartmentofSocialScience,ShandongJiaotongUniversity,Jinan250031,China)
When it comes to allocation of health care resources, ageists insist that the allocation policy should give certain priority to the younger ones. There exist three views about it, supported by Daniels and Dworkin’s distribution theory. It doesn’t mean the elderly should be overlooked even though the ageist distribution policy does conform to the intergenerational impartiality. Instead, adequate primary health care, conservative treatment and ultimate concern should be guaranteed for the senior citizens.
allocation of health care resources; ageism; intergenerational impartiality; Norman Daniels; Ronald Dworkin
B82-052
A
1001-0300(2016)04-0051-06
2016-03-16
王珀,男,山东济南人,山东交通学院社科部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生命伦理学、动物伦理学研究。